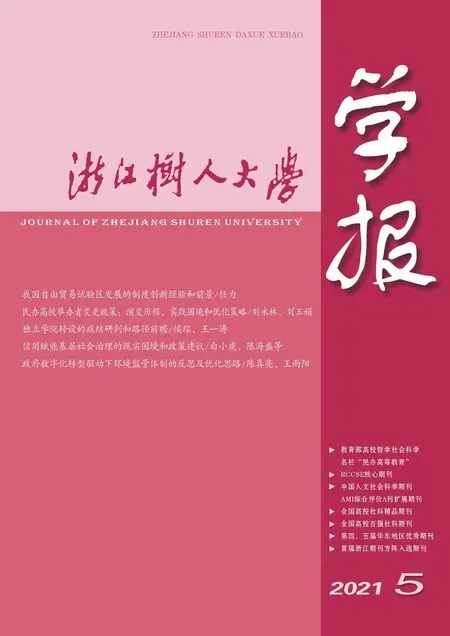大学在培养什么?
——“excellent sheep”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比较分析
2021-11-30黄冠
黄 冠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
20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路从生物、物理学士、新闻学硕士读到英文博士,后又在耶鲁大学任英文教授十载,现已转型成为专业作家的William Deresiewicz,发表了他的新书ExcellentSheep:TheMiseducationoftheAmericanEliteandtheWaytoaMeaningfulLife(以下简称ExcellentSheep)。该书一经发表就在美国教育界乃至普通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Deresiewicz以其掌握的第一手美国顶级学府的录取标准和教学资料,对美国现行的越来越注重“服务学生”和“收益”的精英教育提出了严厉批判,主张教育应该回归“人文”。ExcellentSheep可谓是Deresiewicz教育思想和主张的集大成之作,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该书在被介绍到中国后,与2012年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提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说法形成呼应(1)《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3日,第3版。,正在形成并掀起新一波对大学教育的反思。
一、“excellent sheep”概念的缘起与分析
在讨论“大学在培养什么”主题之前,先来整理下Deresiewicz在ExcellentSheep中的主要观点。该书所讲述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2)书中这三部分内容是糅合在一起的,笔者考虑到概述的直观性和准确性,将内容剥离后萃取逻辑线索。:第一部分描述了著作面向的对象——“被误导的美国精英”(miseducated american elite)的现状;第二部分重点讲述从“旧贵族”(old aristocracy)教育模式转向“新英才”(new meritocracy)教育模式的美国顶级学府存在的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出现的最重要原因是当今大学盛行的“唯物质”(materialistic)倾向——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和校友捐款,而将学生有意地向为数不多的高收入行业输送;第三部分则是对大学教育的思考和主张,认为大学教育的核心是为学生能够过“有意义的人生”(meaningful living)提供机会、帮助和引导,大学应该回归“人文”。如果ExcellentSheep的内容仅止于此,那么它与常见的高等教育批判文章几无差别,并不足以引起巨大反响。事实上,该书最大的价值是揭露了美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美国顶级高等学府的录取标准方面,各大学在筛选申请者时最核心的基准是申请人能为大学带来眼前和未来的收益,收益越大越好(3)出自:Deresiewicz W,Excellent Sheep: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Free Press,2014。后文Deresiewicz的观点都出自该书,不一一标注出处。。这种基准的逻辑表现是,在筛选申请人时,以申请人的家境和未来的成就作为最关键的考核标准,被录取的申请人在毕业后若取得成功,将为学校带来排名上的提升和资金捐助上的回馈。该书进一步指出,为了吸引更多的精英申请人,各大学狂热追求排名,为此不惜鼓励完全不可能被录取的申请人前来申请,从而降低录取率;同样为了追求排名,各大学不断提高毕业率,以至于大学的各种考核流于形式。该书这一部分内容运用了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数据分析,使得其对当今美国高等学府批判的可靠性大幅提升。在讲述美国顶级高等学府现行教育时,该书着重强调了它们的“唯物质”倾向,在规划学生的未来时存在清晰的高收入行业导向,一切的教育都指向确保学生在毕业后能够获得金钱上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最终将为学校带来更多的校友捐助收入。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美国顶级高等学府甚至不惜松动其对毕业生的资格审查,帮助学生在“简历竞赛”(arms-race of resume)中脱颖而出。Deresiewicz认为,美国大学的这种倾向一方面降低了其毕业生的质量,另一方面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并误导了学生的生涯规划,使得美国的精英阶层背离了“有意义的人生”这一“正途”,进而给整个美国社会都带来了方向性的困扰。除了对学生的教育存在偏差,Deresiewicz还认为,在美国顶级高等学府供职的教员们也误入了“唯物质”的歧途。教员们普遍追求科研成绩,在教学上花费的时间被压缩到了最少,且力求不耗心力。同时,美国大学现行的排名机制进一步助长了顶级高等学府及其教员这种追逐科研成绩的倾向,把大学变成了充斥着“刷简历”的学生、“刷科研”的教员以及“刷收入”的学校运营者的场所。在大学这个传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英集散地,唯独没有什么人愿意把心力花在“启迪学生的人生追求,帮助他们过‘有意义的人生’”这一主题之上。
在完成了对美国现行顶级高等教育的批判之后,Deresiewicz进一步指出,对美国精英阶层的误导,其实早在大学教育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认为,当今美国社会的阶层流动系统就是一个“简历竞赛”的地方,儿童从小就生活在由“好心”(well-meaning)但“揠苗助长”(helicopter)的父母营造的压力环境中,强迫他们走一条由“知名学府—专业学位—高调的华尔街职位或在有威望的医学院、法学院深造”构成的阶梯式的“成功”之路。Deresiewicz认为,这种“基于阶层”(class-based)的成长路线过于狭窄,其肤浅造成了对智慧的戕害和对道德的腐蚀。沿着这一路径成长起来的儿童被教养成献媚成人的“刷简历者”,努力在SAT测试中取得体面的成绩,并用至少是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经历来包装自己。要成功地走过这条荆棘路,需要耗费大量的心力,以至于“成功”的学生们普遍带着“压抑”和“愤世嫉俗”的情绪进入美国顶级高等学府。在Deresiewicz看来,这样的学生根本不可能从“无心教学”的教授那里学到什么,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体面的绩点,完全是托绩点通胀和师生间“互不侵犯条约”(mutual nonaggression pact)的福。这样不公平的教育系统不但会迟滞社会阶层流动,使特权永久化,而且其出产的精英完全脱离也不了解需要其领导的阶层(假定需要其领导)。虽然Deresiewicz运用大量的与学生对话的资料和实证数据展示了美国高等教育乃至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批判,但是无关其结论本身,其整个研究设计存在问题。从研究对象定位开始,Deresiewicz对“excellent sheep”或“被误导的美国精英”这一基本概念工具的内涵和外延的限定就不是十分清晰。这一概念最初是指向“HYPsters”(4)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所大学的首字母缩写组成的指代这三所名校学生的专有名词。,但有时指向了所有的常青藤学子,有时又指向了“黄金十二大”的全体学子,有时甚至扩展到排名前一百名大学的学生和它们的申请人(5)Coclanis P A,Book Review:Excellent Sheep: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The Charlotte Observer,2014-10-12,p.4.。概念工具宽泛化,一方面使得研究对象的范围普适性扩大,另一方面降低了研究的精确性和针对性,进而致使解决问题主张的适用性遭到质疑。Deresiewicz主张要解决当今美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从长期来说,需要构造更加平等、低竞争导向的儿童养成和对“成功”定义更为宽泛的社会;从短期来看,则需要在学生和教育机构中复兴强调“人性”的人文教育。如此,才能使学生和教育机构甚至美国社会可以清晰、批判性地思考长期失落的道德方向。为此,Deresiewicz甚至不惜打破美国教育界所谓的“政治正确”,将一些与宗教关系密切的高等学府作为“典范”推荐给读者。这在美国教育界引起批评的同时,得以窥探其“人文教育”外衣下的“保守主义”倾向。概括来说,Deresiewicz使用“excellent sheep”一词所指代的是在当今高校尤其是以“常青藤”为代表的名校中,活跃的擅长完成任务取得体面绩点甚至能够参加并搞定所有课外活动却未能成为良好思想者的精英群体们。Deresiewicz认为,这些被称为“excellent sheep”的精英们不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无力进行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索,而这些本来是曾经的大学教育所应培养的:“我们构建了一个教育系统,它批量生产高知的年近22却对人生应该做什么一无所知的成年人;完全不知道人生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更不理解如何去找出答案。他们擅长沿着既有的道路前进,却缺乏想象力去自行开辟,或者说没勇气,又或者缺乏自在的自由。” Deresiewicz认为,现今高等教育模式为这些精英们准备的毕业后的人生是做一个现代机械社会中顺服的齿轮。随后,Deresiewicz在Harper’sMagazine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有类似论述,无论大学和公司如何地宣称它们想要“领导者”,其实真正重点培养的都是顺服的追随者。“现在人口中的‘领导者’其实是一群以充满活力且积极向上的方式将其人生的所有都分享给主管的人。所谓‘领导者’其实是一群不会威胁到那些大而无当的主导者的小有所成的听话的‘小’成人。”(6)Deresiewicz W,The Neoliberal Arts:How Colleges have Sold Their Soul to the Market,2015-09-30,https://harpers.org/archive/2015/09/the-neoliberal-arts/.
如果ExcellentSheep仅仅是对高等教育乃至现代抚育模式的控诉,那么它已经足够有力了,但正如Deresiewicz在副标题中所暗示的,他试图指出一条通往“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例如对于刚进入大学的新生,他认为积极的扶助手段应该是以新生所处的阶层为基础来规划,而非通过竞争性的考试进行成绩排名。此外,SAT和GRE等本应用来评估智能但实际上只对能够支付额外补习费用的中上阶层有利的测试系统,都应该被抛弃。尽管使高等教育给每个人都带来好处的最终方法肯定是高等教育免费,或者起码要尽可能地便宜一些,但是这意味着增加税负,且在美国这种新自由主义市场上还会面临教育贷款和教育经费短缺等问题。此外,Deresiewicz为如今的大学生乃至所有人提出了能使教育和生活充满意义的建议,即“人文教育”。他认为,唯有“人文教育”才能培养人的思考能力,从而使其成长为有质疑精神的思考者,使人获得为自己思考的空间,进而敢于挑战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权威,并知晓为自己生活的方法。这是Deresiewicz所相信的唯一的可能不快乐但是能让人满意的方式:带着自己的选择乃至差错,过完自己的人生。因此,Deresiewicz推荐年轻人尤其是中上阶层出身的人(而非所有人)应尽量避免就读于知名高校,而应求学于那些专注教育并仍把自我培育作为核心的小型人文高校。Deresiewicz对于高等教育依旧是推崇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高等教育仍然是获得一份体面工作的必备条件,而Deresiewicz宣称自己只是希望学生们能够从事一份对他们来说有价值、真正喜欢的工作。Deresiewicz也指出,全社会都有必要关注精英高校中的精英学生们,因为在美国如今的英才教育体系里,有且只有他们才有潜力和渠道获得拥有极大公共权力的职位。Deresiewicz认为,excellent sheep现象在当今各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显得尤为严重,其产生的影响是使精英群体缺乏独立的批判思考能力,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停滞不前,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让精英群体回归“人文教育”。这种看似对于传统“顺服”品质的批判,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传统的“人文教育”,Deresiewicz的“保守主义”立场昭然若揭。
二、“excellent sheep”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比较分析
ExcellentSheep在国内被译为《优秀绵羊》(7)陈心想:《“优秀的绵羊”进华尔街》,《新闻晨报》2014年12月12日,第8版。或《常青藤的绵羊》(8)万维钢:《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南方周末》2015年7月30日,第11版。。其实,excellent除了有“优秀”这个含义外,其词义更加倾向于强调被修饰对象的“精致”,把ExcellentSheep翻译成《优秀绵羊》可以算是中规中矩的直译,但是翻译成《常青藤的绵羊》就不免有些一知半解的自作聪明了。显然,译者对书的内容有所涉猎,但只是大略浏览,所以才会给出这种哗众取宠的错误“意译”。如果详读该书,在翻译该书的核心概念“excellent sheep”时就会发现,这个概念一方面是强调其指代群体的“光鲜”和“精致”,另一方面暗示了他们对社会流俗的随波逐流,因此在翻译sheep一词时还需要考虑其隐喻的“胆小、怯懦、驯服”等贬义引申(9)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著,柯克尔译:《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页。。据此,这本书完全可以被翻译成《精致的驯服者》。美国顶级高等学府英文教授对他们高等教育养育“精致的驯服者”的指责,恰好应和了我国顶级高等学府中文教授对我们高等教育制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评(10)魏干:《谁造就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2期,第80页。。将“精致的驯服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放在一起比较后发现,它们有很多的相同点:首先,它们都是“精致”的;其次,它们指向的群体都是当今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及其预备队;再次,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上,Deresiewicz主张复兴“人文教育”并据此扭转社会的价值取向,建立指向“有意义的人生”的价值导向,而对于如何改变中国大学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现状,钱理群认为应加强“人文教育”、回归传统道德,可见两者的解决方法虽然都打着“人文主义”的旗号,但实质上都是“保守主义”导向的;最后,它们的始作俑者都是顶级高等学府中的“语文”(一个英文、一个中文)教授。
当然,两者也存在明显差异。首先,美国“精致的驯服者”强调的是“驯服”,是精英群体对当下商业社会的顺从和对完整人格、有意义人生的放弃。而中国“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强调的是“利己”,是精英群体与当下商业社会的媾和,是对传统道德规范和文人风骨的抛却。与“精致的驯服者”已经形成专著理论不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虽然普遍指向了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但是缺乏统一的表述和分析论证,更多流于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其次,在成因论证方面,Deresiewicz主张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才是根本,且承认初等教育对儿童的戕害,美国高等教育虽然是其批判的对象,但是他也承认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罪过是随波逐流,不但没有纠正社会产生的问题,还进一步加剧了其演化。而中国“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说在缺乏统一论证的同时,多数持此论者都将批判集中在中国的大学教育,选择性地忽略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影响,虽然也提及社会作为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批判,在整体论证上既不严谨也不全面。最后,“精致的驯服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两种说法所关注的重点和引发的社会思考及影响也不尽相同。前者所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落在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之上,注重探讨现代高等教育对学生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倾向的破坏以及对探索何为“有意义的人生”和如何为此展开实践的能力的疏失。后者则更加关注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认为精英群体对于自身利益的追逐会对社会的整体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其关注重点从“个人发展”转向了“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不过,两者引发的社会反响甚为相似,中美两国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道德”导向的社会氛围的培育,只是在具体操作层面,美国更倾向于借助公共媒体在社会层面营造对“有意义的人生”的共识,而中国则主要通过在高等教育中加大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素养培育的比重,试图直接纠正高等教育精英群体的“利己主义”倾向。
“利己”本是经济学为了研究需要而对人性作的劣化假设,再愚蠢的经济学者都知道人性不可能只有“利己”一个面(11)林莎、邓春玲:《“经济人”利己与利他行为的理论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第191-196页。。“利己”甚至是人性中最不重要的一个面,只不过在一个“利己”的残酷世界中也能通行的规律必然可以在有“人情”的社会中运转得更加圆润。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一知半解,造就了普通民众对“利己”的误读。从古至今,人性的善与恶是一个永恒的讨论主题。19世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用“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个现今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人性假设,几乎终结了应用社科学界围绕人性的争论。人性成了一个与其他概念工具并无本质差别的研究工具,并随着科研技术的改进而不断进化。时至今日,虽然逐渐出现了“社会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设,但是发展得最为完善也最广为接受的依旧是经常被等同于“自利人”的“经济人”假设。无论出于何种人性假设,其目的都是便于科研。即便是在文学作品中,这种对人性的假设也比比皆是,虽然这些人性假设在增强科研成果可靠性或推进剧情冲突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必须意识到“所有假设都是假的”。任何关于人性的假设都是工具性的、非真实的,就像作为一切社会科学源头的“理性人”假设遭到了来自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的挑战一样,任何关于人性的假设都不是恒定的。这些假设都是根据人类的实际需要出现的,也将随着人类需要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在人类历史中,“利己”和“利他”的争端在很多时候几乎被等同于“恶”与“善”的冲突。亚当·斯密提出的“利他源于利己”的说法在一定时期内的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善恶”之争,但也未能从根本上泯灭各方在“人性”认知上的分歧(12)事实上,很多分歧的出现是由于各方所主张的结论的适用范围不同。举例来说,在讨论成本和收益的经济人假设时,其适用范围是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并且探讨的是普遍性,而反对者往往喜欢用实际生活中的特殊事例来反驳。。“自利”作为利己主义的核心要素之一,虽然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闻名,但实际上最早和最深入对“自利”这一行为进行讨论的却是研究利己主义的哲学家们,甚至亚当·斯密本人对“自利”这一人性假设的讨论也主要是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之中。在解释人类形成道德判断的基准时,亚当·斯密认为,在他的时代,这种道德评价的逻辑回路是基于人的“自利”倾向的(13)Robert F,Biography of Smith,Liberal Democrat History Group,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14 May 2008,Retrieved on 11 June 2008.。从根本上来说,利己主义是一种定性的道德指标,认为道德健全的行为人应该从“自利”出发来规划自身的行动。中国的语文工作者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在面对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时,首先看到的就是“利己”这个舶来品,但是对于美国的语文工作者来说,“利己”却是理所应当的逻辑出发点,根本不值得关注。Deresiewicz笔下的那些“刷简历者”显然是“利己”的,在努力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但也可以看出,由于美国社会和教育体系筛选“成功”者的标准与中国不同,当中国强调“刷分”时,美国教育体系强调“刷简历”。可见,“精致的驯服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的是同一伙人、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在美国社会中“利己”不是主流价值观批判的对象,而在中国社会中“驯服”也不是主流价值观批判的对象。事实上,美国主流价值观是鼓励“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中国主流价值观是鼓励“乖顺”。比较来看,“利己”虽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不和,但作为现代社会的逻辑起点,并不能动摇现代教育的发展,相反“驯服”才可能会造成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因此,“精致的驯服者”所揭露的问题远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得严峻。在笔者看来,东西方语文工作者在对大学教育进行批判时都误解了同一个问题,即“如今的大学到底在培养什么?”
三、现今大学人才培养导向探讨与改进建议
东西方对于以大学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的批评均强调当今大学不再以“启迪学生过有意义的人生”为导向,并对大学追逐收益、教员追逐科研成果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们的叙述中,似乎现代以前的高等教育更加专注于对学生的“人文教育”,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现代大学教育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否应被批判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清以大学教育为主体的高等教育在当今教育体系和社会中的作用,一方面要探讨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要沿着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基础教育所形成的学生培养路径,来明确以大学教育为主体的高等教育在学生的培养路径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虽然大学常被以“象牙塔”的称谓来标榜其在人世中的超然独立性,但大学实际上一直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现代以前,知识存量的窄小和经济生产及人世运转的简单化,使得大学教育完全不具有普及性,并表现出显著的贵族化倾向。相对当今系统化的劳动生产技能,当时的初等教育就穷尽了对于劳动生产技能的传授,大学教育则更多地展开对于世界和人生本质这类“终极问题”的探究。尽管由于探究世界与人类本质途径的不同而衍生出诸多不同的学科,但当时各个学科对于世界和人类本质的探究并非是为了满足人类世界发展的技术需求,而是满足脱离了简单生存需要的社会精英阶层的认知需要,这就使得当时的大学教育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显著的“哲学”倾向,进而形成了导师和学生共同专注于探究“有意义的人生”这种充满“哲学”意味命题的现象。与之相比较,现代以后的人类社会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现代社会对于作为知识富集地的大学的功能定位的变化。与此同时,初等和中等乃至高等教育空前普及,人类的平均学习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且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知识获取的途径变得丰富和低廉。在这样的双重变化之下,大学的定位和功能不断演进,直到变成了如今以知识探索为核心职能、服务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引导学生对前沿领域形成认知和探究的知识生产机构。当今大学更多地将知识传承的功能托付于学生,仅在知识的来源和可靠性上为学生提供指导及支持,重点放在引导学生了解其专业领域前沿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启发学生探求“新知”。正是在这样的转变之下,大学教员更多地担负起科研工作,不断用其新的科研成果来回馈已经有了专业基础知识储备的学生。也正是出于当今社会对于大学功能需求的变化以及大学教育主旨的变化,大学不得不转变其管理机制,引导教育资源和教员向着探究“新知”的科研方向倾斜。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从小学开始,所有的教育都有着明确的终点和未来,就是“优胜劣汰”。据Deresiewicz书中描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只不过相较于只需要“刷分”的中国学生,美国学生需要“刷”更加复杂的简历。大学之前的教育有着过于清晰且死板的上升路径,小学指向初中,初中指向高中,高中指向大学。这阶梯似的进学之路,让每个学生从一开始就盯着一个目标而学习,对达成这个目标有用的就吸收,无用的就舍弃。在残酷的“升级”竞争中,学生们只知道“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看得更远”,却从来没人告诉他们其实巨人肩上的高度并不是他们的高度。大学前整整12年的“功利”教育和升学制度,早就扭曲了学生学习的意义。当今社会向学生灌输着可见的唯物质的“成功”标准,中美两国各自用了远不止12年的基础教育训练出来的“被误导的精英们”,怎么就成了大学这个只有短短4年的高等教育的产品了呢?
在当今社会精英身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恰恰是这一群体对当今社会需求和现实的回应。撇开“利己”这个涉及人性本身难分对错的问题不谈,Deresiewicz所提出的“驯服”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当今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路径,个人通过“驯服”于已有的社会规则,可以在最小的成本支出情况下获得最快、最有效的成长;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相比“保守主义”和“人文主义”诞生的旧时代,现代社会不但在物质发展上实现了空前的丰富,在知识存量和更新速度上更是之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而这正是现代社会再也无法诞生“百科全书”式大师的根本原因,也是现代人成长周期被极大延长的客观原因。旧时代的人类在到达现今大学新生的年龄时,多数已经成家立业,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年龄段开始思考人生的真谛,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是因为当时的他们已经穷尽了时代提供给他们的成长可能,需要自己去探索、发现和追求自己的人生意义。现代社会的发达既意味着更多的成长可能,也意味着更加漫长的成长周期,现代人在大学阶段还未穷尽对既有知识的学习,在这样的情况下支出大额成本去探索类似“何为‘有意义的人生’”这种无益于解决未来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面临困难的问题,不仅是违背经济理性的愚蠢选择,更是近乎无病呻吟的高谈阔论。现代人并不是不需要“有意义的人生”,也不是不再探索“有意义的人生”,只是这个对“有意义的人生”的追求被延后了。大学就像一个全新的开始,大学前教育培养出来的“严重偏科”的学生们,要在大学复健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全部技能。想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从大学教育上探讨可能路径,还要解析社会各界针对大学生“利己”行为进行夸大批判的成因。
当今社会增量放缓,存量竞争加剧,即便我国目前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口尚不足5%,但各行业在吸纳和消化高质量劳动力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大学生就业难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境下,连满足“后顾无忧”这条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人之为人”的起始条件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强求莘莘学子无私却奋进,不免强人所难。可以说,正是外部经济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才使得“利己”成为饱受批驳却愈发被大学生广为接受的行径,且对于这种行径的采纳,并非仅仅局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和各种教育背景的人群中,奉行“利己”逻辑的大有人在。那为什么被社会普遍奉行的“利己”逻辑一旦与大学生群体发生联系就会遭遇指摘,为什么社会可以接受经济社会中的“利己”逻辑却无法认同大学生的“利己”举动呢?这就不得不从社会对于大学生的期待说起了。自2 000多年前柏拉图在阿卡德米创立学园伊始,作为高校的教育机构就被赋予了为人类世界培育“精英”的使命,让人类获得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可能的机会与能力。与此类似,中华文明中对于大学的理解着眼于无限的“大学问”,而非有限的“大楼”,其培育的也应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士人学者。东西方文化对于大学的理解和预期,无一例外地注重对“无限永恒”的追求,而忽视对“有限利益”的攫取。这并非是东西方学者有意地标榜清高,而是源于大学教育在创立初期仅面向脱离物质资源再生产的少数富裕群体的贵族属性。大学的培养对象从一开始就被圈定为贵族群体,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普及化成为大学教育现代化的最主要特征。如今大学的门槛被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大学教育全民化的现象。这就造成多数大学生在毕业时实际上并未摆脱基本生存的束缚,即便他们掌握了于“有限”中追求“无限”的技能,也不得不为了获取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投入到经济竞争中去。要在经济竞争中有所成就,遵循经济活动的“利己”逻辑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可以说,正是社会对于传统大学培养经世济国士人的期待与现代大学毕业生为了解决生计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现实的脱节,才造成了各界对于大学生“利己”的放大性批判。不过,强求一个在象牙塔中养成追求“无限永恒”的技能却又不得不逡巡于柴米油盐的普通人“无私”,显然是有违道义的。事实上,“精致”正是这些在生活的重压和职场的激烈竞争之下艰难维系“精英”人设的大学生们仅有的体面。想要直面被贬为糟粕的“利己”,就不得不探讨是什么让大学生投入不体面的“利己”竞争中。简单地将大学生的“利己”行径归咎于负责传递知识的大学的培养,未免高估了大学在人性养成中的作用。
通过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要纠正大学在人才培养导向中所遇到的诘责,既要从源头上解决大学生源选拔方式中“过度竞争”的问题,也要针对大学人才培养方式作出一定的调整。首先,大学生源选拔中存在的“过度竞争”,其实质是教育资源稀缺和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衍生的问题。唯有从根本上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乃至推动实施优质教育资源和专家学者在全国高校间的规律性流动,进而实现优质大学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有序流转,才能降低特定高校在大学教育和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应全面推广和完善大学教育阶段的跨校“转学”制度,使学生可以依据其实际需要,遵照特定程序和标准来获取其希冀的教育资源。总的来说,唯有降低不同地域和高校间的教育资源差异,才有可能彻底解决大学生源选拔中出现的“过度竞争”问题,从而降低大学前教育对于学生“利己”倾向的培养和放大,使教育的全过程回归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而不再限制于对学生简单应试竞争能力的培养。其次,在整个现代教育体系中,大学作为唯一一个为学生提供了4年宽松学习氛围、一定程度上自主选择学习内容的教育阶段,需要在学生自主性和教育有效性之间作出平衡与取舍,即在保证大学生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给予大学生相对充分的认知和经营自我的时间与空间。随着大学教育的愈发专业化和当今社会知识存量和增量的快速膨胀,大学生无论是在校期间面对的学习压力还是步入社会后从事的工作难度均有显著提升,但社会各界对于大学生在工作表现和为人处世方面的期待与要求仍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通过科普教育和开放性大学建设来增进普通民众对于大学教育的理解外,如何平衡传道授业的学习任务、培育学生探究“新知”的能力和服务社会乃至人类发展技能之间的关系,正是大学扭转社会对于大学人才培养主要诘责的关键,也是大学在解决相关问题时的主要发力点。为此,可适当借鉴澳大利亚等国在大学教育改革中的经验:一是提高对于专业知识传授和考核的严格程度,让大学生的受教育习惯不出现断裂,继续加强和锻炼大学生的学习能力;二是提高大学生在课程选择中的自主性,使大学生在人生发展的可能性上有更加多元的追求。结合我国不断扩大教育资源投入的时代背景,唯有从学校和学生两方面共同入手,双方共同发力,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围绕大学人才培养导向出现的争议,从而使大学生真正成长为党和国家期待的“全面发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