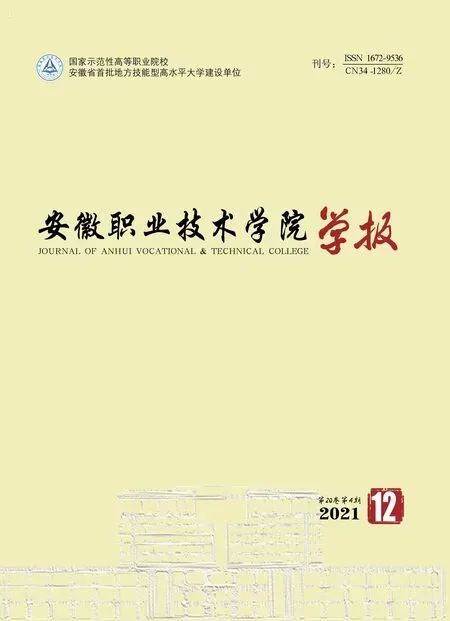从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视角分析《竹林中》的人物形象
2021-11-29王伟
王 伟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合肥 231131)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文坛的领军人物,《罗生门》《鼻子》《竹林中》等作品深受人们喜爱。《罗生门》中的老妪、《鼻子》中的老和尚,这些典型人物形象描绘得鲜明而复杂。芥川笔下的人物通常是复杂的圆形人物,即其性格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他们是典型环境的产物。也正因为此,这些人物形象才显得那么真实与深刻。芥川创作生涯短暂,但创作成就极高,文学成就比肩森鸥外、夏目漱石,作品以小说为主,共有148 篇小说,小说篇幅短小,却意蕴深刻,构思极为精巧,富有哲思与艺术性。
小说《竹林中》以审判的场景,讲述了强盗多襄丸、武士之妻真砂、武士金泽武弘之间的一段情杀故事,故事过程大体为:强盗以古镜、宝刀为由蒙骗并绑架了武士;之后当着武士的面,凌辱了武士之妻;随后在三者不同的表述中描绘了三段情节迥异的仇杀场景;结局是武士死去、堕入幽冥,强盗被捕、等待审判,武士之妻逃往寺庙忏悔、渴望救赎。小说情节在强盗、武士之妻以及武士亡灵的陈述中铺陈开来,但他们对三者间的冲突过程各执一词,表述迥异。这使得故事情节扑朔迷离,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也变得激烈异常。
《竹林中》开放式的叙述结构给故事本身提供了多元的解读可能,这唤起了读者的普遍兴趣。关于《竹林中》的先行研究,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约有一百篇左右,主要就小说叙事方式等展开了分析,观点、结论主要集中于“人性的恶”“真相不可求”等。丁璞(2007)认为小说《竹林中》主要对人性欲望进行了剖析,对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和利己主义的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描绘[1]。龚仪(2018)从日本耻感文化出发分析了小说《竹林中》中多襄丸、武宏和真砂撒谎的社会原因,认为畸形的耻感文化是导致这种悲剧的文化实质和根源[2]。乌博林(2020)提出,《竹林中》一文,芥川除了对人性的自私进行了刻画之外,还表达了对武士道精神的痛恶,认为文章主要表达了芥川对武士道精神的反对[3]。代欣(2020)从多重叙述、叙述的不可靠性角度出发,论证了《竹林中》的独特叙事手法,阐明了《竹林中》在叙事方式层面的独特艺术意义[4]。国外研究主要在日本开展,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真相不明”“无真相背后的人性之迷”等。
1 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裂变
笔者尝试运用弗洛伊德后期的“三部人格结构”对文本进行解读,认为强盗、武士之妻、武士其实是芥川笔下人格的不同组成部分,小说《竹林中》所描写的故事本身已给出完整的真相,小说中三位主角的陈述看似彼此冲突,其实都是从各自角度(即人格价值取向角度)出发所说的实情。本文将尝试从三个角色间的矛盾冲突中跳出来,跳脱固化人物,旨在从“本我、自我、超我”这三种“人格构成”的角度出发,解读《竹林中》,并尝试将强盗(本我)、武士之妻(自我)、武士(超我)容为一体,分析作者芥川龙之介在《竹林中》中所经历的人格裂变与纠结,并对一些关键词句作出分析,探究该小说中部分书写细微处的深意,尝试分析芥川的创作意图。
1.1 本我之强盗多襄丸
本我一词是由弗洛伊德于1923 年提出的心理学名词。本我是人格中最固有、最原始的部分,是生物性冲动和欲望的贮存库,是人格的生物面。本我会不顾一切地追求满足与快乐,具体体现为追求性、生理愉悦和情感快乐,本我遵循的是“快乐原则”。
小说中的强盗多襄丸野蛮而冲动,集中体现为人格中的“本我状态”,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行出发得出该结论,作为强盗,他目无法纪,充满暴力、表现得充满原始冲动和野蛮。他明确承认自己凌辱了武士之妻,杀死了武士,而且他态度极其傲慢、甚至有些理直气壮。“咱家既然落到这一步,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隐瞒什么。[5]176”从他的陈述来看,他对凌辱女子一事并不感到可耻,对杀死武士也不抱有罪恶感、不抱有歉意,他甚至以好汉自居。“可你们杀人,不用刀,用权,用钱,有时甚至是几句假仁假义的话,就能要人的命。不错,杀人不见血,人也活得挺风光,可总归是凶手哟。要讲罪孽,到底谁更坏,是你们?还是我?鬼才知道!(挖苦地一笑)[5]176”在强盗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他觉得大众是虚伪的,而自己才是坦诚的,并不觉得自己比其它人更加邪恶。可见他是不遵从道德标准,更不追求价值标准的。“觉得她美得好似天仙。顿时打定主意,即使开杀戒,除去她男人,老子也要把她弄到手不可。[5]176”多襄丸的欲望是本能式的,毫不掩饰与控制的。除了对性的绝对追求外,多襄丸也很阴险狡诈,他先以钱财为诱饵蒙骗武士进竹林,后又称武士病倒,蒙骗女子上当。他充满原始的野性与暴力,“反正得把女人抢到手,那男的就非杀不可。[5]176”“我要招的,便是这些。横竖我脑袋总有一天会悬在狱门前示众的,尽管处我极刑好啦!(态度昂然)[5]178”从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强盗多襄丸是不惧死亡的,但他却无法抗拒女子美色的诱惑,执迷于性的本能。由此可见,他所遵循的正是“快乐原则”。
笔者认为,强盗多襄丸所代表的正是人格中的本我。而整篇小说所描述的正是“本我强势宣泄、自我被本我征服,超我价值体系坍塌”的人格激变。
1.2 自我之武士妻子真砂
自我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与本我相比,自我外部性更强,自我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为使个体适应现实世界,自我对本我加以约束和压抑,自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小说中武士之妻真砂可以理解为人格构成中的自我。自我以女性的形象展现,自我与女性都呈现出一定的依附性:现实的男权社会中,女性需要依附男性,小说中的男性主角即强盗和武士。自我在现实的人格构成中也是无法独立存在的,它会偏向于本我或超我,体现出某种偏向性的价值取向,或表现得低俗、或表现得高雅。小说完整地描绘了真砂在遭遇劫难后内心摇摆、转变的过程,从反抗强盗到杀夫并自杀,冲突激烈至极,这也许正是芥川想要表达的“自己人格构成中自我的痛苦境地”。真砂曾激烈反抗多襄丸的暴行,我们可以看下她的行动:“她从怀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来。老子从没见过那么烈性的女人。……可她豁出命来,一阵乱刺。[5]177”,这可以理解为芥川的人格构成中自我对本我的抗拒,但结局显而易见,真砂抗拒失败,而被多襄丸凌辱,自我败下阵来。真砂被凌辱后的种种表现正好体现了自我所遵从的现实原则:“只听她断断续续嚷道:不是你强盗死,便是我丈夫亡,你们两个总得死一个。……你们两个,谁活我就跟谁去。[5]177”在强盗的供词里,真砂在强盗与丈夫之间的选择方式,是从现实力量角度而非道德善恶角度出发做选择,这里也体现了自我所遵从的现实原则。真砂最后逃往清水寺,暗自忏悔,我们再看一下真砂的供词,从她的忏悔中,我们可以得知武士目睹妻子受辱后一直被堵着嘴,无法说话,真砂感到羞愧、悲哀、气愤,在经历了漫长的心理斗争后,她这样说道:“你亲眼看我出丑,我就不能让你再活下去。[5]179”至此,真砂决定杀死武士,然后自尽,可最后的结果却是,她顺顺利利地杀死了武士,却自杀失败。这里体现了“自我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艰难抉择”,结果是自我毁灭了超我,自我残存了下来。真砂逃往寺庙,逃离了强盗,杀死了武士,她可以容忍自己与强盗共存于世,但却无法忍受丈夫的眼神,以至要杀死丈夫。在芥川的笔下,自我无力拒绝充满原始野性的本我,而且如果必要,它会毁灭代表善与正义的超我。
1.3 超我之武士金泽武弘
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它更加注重对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的追求,强大的超我能指导自我、并限制本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社会面,超我遵循的是“理想原则”。
武士是日本传统价值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符号,武士遵从“不畏艰难、忠于领主、勇猛争斗”的准则。将之凝练为思想,即“武士道”,包括勇、仁、忠等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日本武士极度推崇“忠”,甚至可以因此做出反人道的事情。但在小说《竹林中》里面,武士的表现却差强人意,他贪图钱财,并因此受到强盗蒙骗。他很大意,对强盗之流的卑鄙与猥琐毫无防备,对这样的陌生人过度信赖,表现得天真,耿直。从武士的供词来看,武士之妻在遭受强盗凌辱后,喊叫着让强盗杀了武士,强盗表现出对女子杀夫行为的不齿,在听到妻子的杀夫言行后,武士竟然选择饶恕强盗的罪孽,继而对妻子感到极度厌恶与绝望。笔者认为武士此刻已默许强盗杀死不忠的妻子。在武士关于三人冲突的供词里,武士一直被绑着,他的肉体并无丝毫损毁,但他却疲惫不堪,妻子的表现让他觉得屈辱,“我疲惫不堪,好不容易才从杉树下站起身子。在我面前,妻掉下的那把匕首,正闪闪发亮。我捡起来,一刀刺进了胸膛。[5]181”这里选择的是妻子的匕首,可以解读为武士是因妻子的恶意而死。从强盗、武士之妻、武士三个角色中跳脱出来看,作为超我的武士消亡得直接而彻底,在三个人格构成要素的争斗中,本我征服自我,自我抛弃超我,而超我屈辱落败,堕入了幽冥(地狱)。
2 人格构成之间力量悬殊的纷争
2.1 本我与超我之间
我们可以将三者进行分组对比,看下它们之间的力量悬殊,以及彼此间碰撞、纷争结果。就本我与超我而言,可以从强盗与武士的决斗中找到结论:“决斗的结果,也不必再说了。到第二十三回合,我一刀刺穿他的胸膛。请注意——是第二十三回合!因为跟我交手,能打到二十回合的,普天之下也只他一人啊!(欣然一笑)[5]178”强盗对于他所遇到的所有人,他都是具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基于上述台词,我们可以推断芥川的观点应该是:在所有人的人格构成中,本我与超我相比,本我具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小说中,武士所代表的超我已经非常强大,但还是在第二十三回合败下阵来,最终惜败于本我。正如前面所说,在基本具有共识性的冲突中,强盗使诈,武士被俘中。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强盗所代表的本我,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武士所代表的超我,率真、耿直、易受蒙骗。如果我们将芥川的笔下的蛮荒之地“竹林”理解为纷繁复杂的社会,那么,理想主义的超我在此处是明显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是极度脆弱的。
2.2 本我与自我之间
将本我与自我作对比,本我明显具有绝对力量优势。在强盗的供词中,武士之妻曾持刀反抗,但很快落败。“霎时间,她从怀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来。老子从没见过那么烈性的女人。……不过,老子是多襄丸,何须拔刀,结果还不是将她的匕首打落在地。[5]177”在强盗面向,武士之妻的反抗如同儿戏。强盗稍费气力就降服、凌辱了她。在武士之妻的供词中,在经历凌辱后,她的情感重点转向武士,悔恨交织,最终选择杀死武士。芥川笔下,自我最终被本我凌辱,毁灭了超我,自我同时陷入不道德的精神困境,深感罪恶,渴求救赎。
2.3 自我与超我之间
小说中武士之妻所代表的自我,武士所代表的超我,原本是夫妻,这映射了现实社会的普世价值中人们所追求的自我与超我相得益彰的理想状态,但小说却给出了悲剧性的推断。武士之妻在遭受凌辱后却表现得十分诡异,我们可以看一下她的供词:“我懵懵懂懂,朝他胸口猛一刀扎了下去。……我忍气吞声,松开尸身上的绳子。接下来——接下来,怎么样呢?我真没有勇气说出口来。要死,我已没了那份勇气![5]179”她对强盗与武士都抱有悔恨,但对丈夫武士的愤懑更甚,在经历了激烈的心理斗争后,她杀死了武士,但却无力自杀了,最终选择逃往寺庙。从人格构成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自我在本我与超我之间摇摆、被拉扯,谁的力量大就屈服于谁,自我所遵从的“现实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女子受到强盗凌辱后对武士生恨,可能是觉得武士无用,也可能是觉得自己在武士面前羞愧难当,但关键是她选择了杀死武士。在芥川的笔下,自我杀死了超我,最终自我沦入苟且偷生的境地。
3 芥川龙之介与武士角色的契合
关于芥川人格状态,我们或许可以从小说的结局,从现实中芥川的别名中探知一二。小说的结局是:强盗(本我)傲慢地供述暴行,慷慨受审;女子(自我)苟且偷生,等待救赎;武士(超我)屈辱赴死,堕入幽冥。另一方面,现实中芥川的别名有澄江堂主人、柳川隆之介,还有一个是“我鬼”,他的书斋也曾叫“我鬼窟”。如果我们将这里的我鬼与文中堕入幽冥成为亡灵的武士进行比对,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芥川的人格状态更多的是与武士相契合。
芥川的人生经历及创作风格也体现了他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否定。就人生经历而言,1915 年(23 岁),他爱上了青山女子学院英文科的才女吉田弥生,这是他的初恋,但遭到家人的反对,最终,初恋的失败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让他产生了厌世情绪,并对他以后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5 年11 月,他发表了宣泄人性丑恶的《罗生门》。芥川龙之介晚期的作品更直接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1927 年初发表了《玄鹤山房》。小说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表现了芥川对人生感到惨淡、绝望的伤感情绪。芥川没有感知到超我所推崇的传统价值体系对人的指引,在世俗的恶面前,他感到不安,充满悲观、厌世情绪。1927 年7月,芥川服安眠药自杀,他自述原因为:对未来只有朦胧的不安。
4 小说创作中的隐喻与象征
4.1 大道、竹林、杉树林等词的隐喻
首先,笔者认为小说中三位主角所走的大道之“道”与“道德、道义”中的“道”相通(日文汉字均写作“道”),意指符合道德伦理的正途、大道。三位主角在正途中行进均相安无事,但如果有人受到物质或女色的引诱进入树林便就会误入歧途,就会给人带来灾祸。其次,《竹林中》的日文名称为《藪の中》,“藪”表示“竹林”,在日文中它的发音“YABU”与“破く”(破裂)中的“破”字发音“YA⁃BU”相同。笔者认为“藪”一词包含人格构成发生分裂之意,分裂之后,进而在竹林中发生争斗纠缠。最后,小说中的杉树林也颇富深意,杉树外观奇特,树叶呈针状,浓密,郁郁葱葱。笔者认为文中的杉树林意指险境或地狱之境。武士正是被骗至其中,缚于其中,最终死于其中。
小说中重点强调了“二十三回合”这个词。在强盗与武士争斗之后,强盗胜出,但强盗对武士的功夫却大加赞赏,强调经过二十三回合才打败武士,“请注意——是第二十三回合![5]178”,芥川于1892 年出生,二十三年后是1915 年,这一年他的代表作《罗生门》诞生,在《罗生门》这篇小说中,芥川也深刻描述了人性的恶。这一年应该是他创作心理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笔者认为可以将“二十三回合”与芥川出生23 年后1915 年有深刻关联。1915 年,23 岁的芥川,在“经过二十三回”人生搏斗后开始感知到的:人格构成中的“本我”正在战胜“超我”,而“超我”正在不断堕入幽冥。
4.2 “看不见的手”的象征意义
关于武士的死,经过对三位主角的口供研读,我们可以得出三种解释。在强盗的口供中,强盗是在武士之妻的央求下,杀死了武士;在武士之妻的口供中,她羞愧难当,愤懑之至,是她自己杀死了武士。在武士的供词中,他自己对妻子感到极度失望,羞辱难当,他自己用妻子的匕首自杀的。无论哪一份供词,死因都不是直接归罪于强盗,而是归罪于武士之妻。
在武士供词的最后部分,小说写道:“天色已黑,杉树和竹子已经看不见,有人蹑足悄悄走近我身旁,我想看看是谁。然而,周围已暝色四合。是谁……谁的一只我看不见的手轻轻拔去我胸口上的匕首。[5]181”自此,武士口中血潮喷涌,堕入幽冥。这里的疑问是,前面已经写到武士自尽倒下,为什么还要描写一个人,一只看不见的手呢?笔者认为,首先不会是强盗或武士之妻,因为他们不需要蹑足悄悄靠近。其次这里不是指直观意义上的人,因为前面已经写到天色已黑,人是不能在黑暗中轻轻拔去匕首的。那么如果不是人,作者是要表达什么事物呢?这里是芥川留给我们解开全篇的钥匙:最后杀死武士的不是人,而是“看不见的手”,笔者认为“看不见的手”指的正是“人格构成中的超我所遵从和信奉的伦理价值”。它在黑暗中,在武士极度脆弱的时候,拔下了匕首,夺去了武士的生命。这种超我所信奉和遵从的世俗伦理价值体系、道德体系,笔者认为芥川在最后完成了对它的彻底否定。这应该正是芥川龙之介创作本小说的真正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