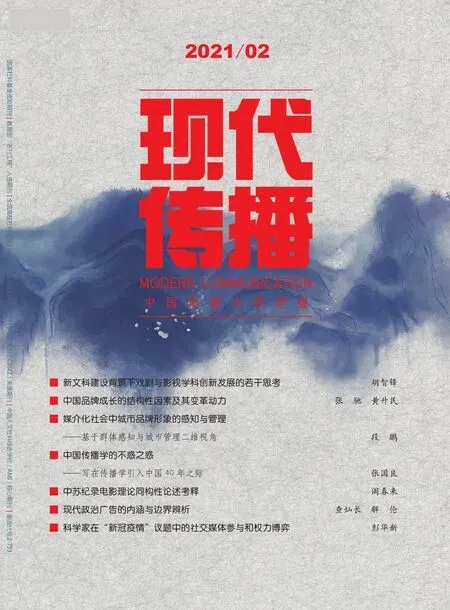一种儒家传播学思想中的自我观:兼与芝加哥传播学派自我观比较*
2021-11-29赵妍妍
■ 赵妍妍
自我观的不同也意味着传播关系及传播理论上的不同。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一种儒家意义上的自我观与西方芝加哥传播学派自我观之间的区别,考察儒家思想可能为传播学理论贡献的独特视角以及这种视角可能具有的伦理意义。当我们能够说明华夏传播学的概念和思想比西方传播学的相关概念和思想更为合理时,我们才真正开启了与西方传播学界对话的契机。而本文尝试论证先秦儒家自我观如何可能解决西方传播学自我观面临的问题,就可以作为说明华夏传播学的这种合理性的一个例证。
一、芝加哥传播学派的自我观及其理论困难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理论反对个体主义,突出个人的社会关系,认为意义是在人际传播中逐渐建构出来的。相应地,这一学派的自我观强调个体与他人互动的面向。作为这种自我观的先驱,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指出,“自我”具有多重性,包括作为认知主体的自我(即,自我中积极知觉和思考的部分)以及作为认知客体的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等经验自我(即,自我中被知觉和被思考的部分)。①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家库利(Charles Cooley)、米德(George Mead)和帕克(Robert Park)进一步突出了詹姆斯多重自我主张中的社会性。②库利提出了“镜中自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的概念,认为我们的自我观是反射性的,他人就像我们的镜子,决定了我们自我观的产生和构成:我们对他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想象、我们对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想象以及我们对他人这种认识和评价的反应是自我观的三方面构成要素。③米德继承了库利的社会性自我观以及詹姆斯对自我的区分,他将自我分为主我(I)和宾我(Me)两部分,认为“主我”是我们对他人态度的反应,而“宾我”则是我们认为的他人态度的集合④,“主我”对“宾我”做出的反应是必须与社会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在此基础上,米德还糅合了实用主义符号理论,进一步从发生学上阐明了自我的社会性。⑤他认为,通过符号这个普遍而客观的媒介,社会上分散的不同自我得以彼此联系、共享经验,从而自我总是处于动态演化之中。⑥帕克也持这种动态自我的主张,认为个体的发展是一个“动力学的过程”(dynamics process)⑦,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受到影响,继而产生自我意识和自我的概念”⑧。
可以看到,芝加哥学派的自我观至少有两方面突出特征。第一,决定自我观构成的关键要素是现实社会中的他者,也就是说,构成“自我”的关键他者是社会性、经验性的存在。第二,这种自我观尤为强调他人和社会在自我观构成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或者说,每个人的自我都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存在的。⑨
笔者认为,这种意义上的自我观至少可能面临下述几方面理论困难境。
第一,芝加哥学派把构成“自我”的他者界定为在现实社会中的他者,认为我们通过在意识和行为中内化这些现实社会中的他者对自己的期待而形成自我观。但是,这种界定不仅可能导致我们的意识和行为缺乏道德驱动力或者丧失道德上的可辩护性,而且可能导致我们无法确立自我的主体性。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现实社会中的他者不是完美的,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道德问题。如果我们的“主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他者存在的这些问题持否定态度,那么我们如何有动力来内化这些来自他者的问题期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他者的道德问题,或者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仍然在行为中内化了这些有问题的期待,那么我们的行为则不具备道德上的可辩护性。
其二,尽管芝加哥学派的动态自我观不像结构功能主义那样把自我看作是一个纯粹“刺激-反应”的机械存在⑩,但是由于芝加哥学派认为自我是由他人构成的,必须通过他人来获得自身的本质规定性,那么他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人的集合体)就在逻辑上优先于自我,因而在这种自我观的语境下,自我的个性发展及其主体性的确立就很难得到保证。
第二,芝加哥学派把“自我”看作是被社会和他人塑造的,这可能导致如下两方面问题。
首先,这种自我观可能消解了自我的社会责任(包括道德责任)。回顾芝加哥学派对于自我与社会经验之间联系的强调,以及对于自我观构成要素的解释,我们有理由认为,芝加哥学派的“自我”观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自我改变他人和社会的可能性。当然,米德有时会通过分析人类生物进化的过程来强调人具有改造环境的生命冲动,甚至认为“主我”具有反作用于社会的创造性,但是米德更强调宾我对于主我的决定作用,认为自我只有在与他人联系的情况下才能形成自我观,离开了他人和社会群体,自我根本不可能存在,更不要说具有任何创造性。类似地,虽然帕克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和作用,但是他同时认为,这种交互影响是以“每一个体都或多或少存在于其他个体的心灵之中”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会把未能获得他者的肯定或承认视为一种“让人郁闷的、甚至往往是让人心碎的经历”。
其次,作为一种外在性、社会性的建构,芝加哥学派的自我观可能因其绝对的外在指向而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区分。在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中,我们通过他人这面镜子照见自己,这意味着我们通过他人认识自己,乃至形成关于自己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自我观是由外而内形成的、以他人-自我二分架构为基础的,即,先是预设了他人与我们都是相对封闭的实体,再试图在他人与我们的对话中形成我们对自身的认识。这种他人-自我二分的架构使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变得艰难,也无法很好地解释诸如“我们与他人感同身受”这样的传播现象。尽管帕克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想象他人的处境和经历来把他人看作是与我们一样的人类个体,但是这种想象仍然是在人我二分的架构下完成的,即依然是基于自我与他人存在心理距离的预设而做出的弥合这种人我间隙的尝试。
应该说,芝加哥学派自我观面临的上述理论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它西方传播学理论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如,传播管理学派预设了主体控制世界的逻辑,批判学派提倡主体解放,这些主张都带有在自我与他人相对立的基础上确立主体性的倾向;同时,西方传播学传统中的说服、解放、认同、对话等理论共识,也体现了类似的人我两分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能需要寻找西方传播学传统之外的某种理论路径,从中发掘出解决上述理论困难的思想资源。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笔者将尝试考察一种儒家传播学思想中的自我观,并表明这种自我观如何可以规避芝加哥学派自我观的上述理论困难。而要进行这种讨论,我们要先梳理儒家文本中可能与这种自我观相关的概念和思想。
二、“身”“吾”“我”“自”“己”:先秦儒家文本中的自我概念
在先秦儒家文本中,与儒家自我观直接相关的主要有“身”“吾”“我”“自”“己”这五个概念。其中,“吾”“我”在一些文本中是成对出现的,可以作为一组概念进行文本的比较分析。类似地,“自”“己”则可以作为文本比较分析的另一组概念。以下,笔者将首先分析“身”的概念,再分别分析“吾”-“我”这组概念和“自”-“己”这组概念。
“身”的概念在先秦儒家文本中可以指代自我的物质身体(如,《论语·卫灵公》说的“杀身以成仁”),也可以指代包括物质身体和思想精神状态在内的作为整体的自我(如,《论语·学而》提到的“吾日三省吾身”)。在指代整体自我时,“身”的使用语境往往与道德修养工夫(如,“修身”)以及心灵的内省活动(如,“省吾身”“修身在正其心”)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内省活动和修养工夫有时被认为是可以推扩的,而不仅仅局限在自身之内。
再来看“吾”和“我”。从注释史上看,学界关于“吾”“我”在先秦文本中的使用方法有三种误解。一是认为“吾”与“我”的区别不大,二者主要是语音语气上的用法不同(《说文解字·我部》);二是认为“吾”与“我”在语法上存在分别,“吾”多作主语,“我”多作宾语,但在特别强调时,“我”亦可作主语;三是认为“我”是与他人相对而言的(“因人而言则曰我”),“吾”则专指自己,没有与他人相对的意味(“就己而言则曰吾”)。
然而,根据笔者考证,先秦儒家文本中“吾”“我”的关键区别既不在语气和语法上,也不完全在于是否与他人相对而言。毋宁说,“吾”“我”的区别在于,究竟侧重于主观表达还是客观陈述。“吾”的使用语境主要侧重于主观表达,如,表达自身的主观意图或心理活动(如,《孟子·梁惠王上》的“吾惛,不能进于是矣”)、主观感受或自身强烈的感情(如,《论语·卫灵公》的“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礼记·檀弓上》记录的“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认知或思想状态(如,《论语·学而》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先进》的“不吾知也”)。与之相对,“我”的使用语境则多涉及将自己对象化的倾向,侧重于客观陈述自身家庭或社会身份(如,《孟子·万章下》的“子,君也,我,臣也”;《荀子·尧问第三十二》的“我,文王之为子,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行为取向(如,《孟子·滕文公上》的“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这种区别在“吾”“我”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的情况下尤为明显。比如,《论语·雍也》中记载闵子骞的话:“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在这一句中,“我”因为自身的身份而成为他人来“复”的对象,而“吾”的语境则涉及闵子骞对自身计划的主观陈述。
与“吾”“我”之间的区别不同,先秦儒家文本中“自”和“己”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涉及与他人相对而言的语境。其中,“自”是纯粹内在指向的、多涉及我们与自身关系的语境,并且这种关系大多体现为一种自我省察和自我提升的过程,如: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孟子·公孙丑上》)
“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滕文公上》)
相比之下,“己”则更多是在与“人”相对(但未必不包含他人)的意义上说的,如:
“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上》)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孟子·万章下》)
有时,“己”也指涉自身有道德缺陷、需要被修正的部分(如,《论语·颜渊》提到的“克己复礼”)。
值得注意的是,“自”的自我省察和提升义有时还与“心”这个概念联系起来,比如,《孟子·离娄下》的一则文本指出“自反”是“存心”的表现: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孟子·离娄下》)
在宋儒那里,这种自我省察、提升进一步与克去“己私”的工夫和能力联系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在《荀子》文本中其实就已经有“公”“私”对举的现象了,只是并没有明确将“心”的自省能力与“去私”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一话题涉及宋儒关于“公”“私”(包括“私意”“私欲”这两种略有不同的心理倾向)的区分,以及这两个概念与“一体”“生生”“理”之间的关联,囿于篇幅,笔者不于此展开讨论。
三、先秦儒家自我观与芝加哥传播学派自我观的比较研究
通过上述文本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儒家的自我观虽然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芝加哥传播学派的自我观,比如二者都强调自我与社会、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联,但是二者却在下述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而这些区别同时也为我们解决芝加哥传播学派自我观的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
第一,先秦儒家一方面承认他人与我们存在关联,他人对于我们形成自我观可能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又看到,这种影响既可能是积极正面的,也可能是消极负面的,从而需要我们在这些影响之中做出选择(“择”),接受积极正面的影响(“从”善、“见贤思齐”)、规避消极负面的影响(“改”不善、“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选择他人对我们施加什么样的影响,而做出这种选择的能力和标准就在我们的“心”中。在上一节的文本分析中,我们看到,“心”具有自我省察和自我提升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自我观中“自”的面向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儒家的自我观就规避了芝加哥传播学派因为预设他人与自我之间存在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导致的理论困难。
第二,与上述特征相联系,先秦儒家自我观的关注点在于我们自身如何保持“心”的自我省察和自我提升能力,而不在于他人和社会环境对我们施加了什么影响(事实上,在宋儒那里,过分在意他人和社会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反而可能是一种“蔽”和“累”,从而是与我们的“私意”和“私欲”相联系的)。在上一节的文本分析中,我们看到,“身”和“自”的使用语境明显带有这一内涵。而“己”的文本语境虽然涉及他人对我们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与我们对自身的省察相伴随的(“己”所涉及的自省语境有时是“克己”意义上的对自身道德缺陷的修正,有时则是“为己”意义上的对修炼自身德性的专注)。至于涉及“吾”“我”的文本语境,虽然与自我省察和提升没有很大关系,但是也都没有过分强调他人和社会对我们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儒家的自我观不会面临芝加哥传播学派以他人为自我的本质规定性而可能导致的阻碍个性发展的问题。
第三,虽然先秦儒家自我观的侧重点在于我们自身(主要指我们的自我省察和提升)而不在于他人(主要指他人对我们构成自我观的影响),但是这种自我观包含了自我与他人在道德修养中相互融摄的维度,也就是说,先秦儒家意义上的“自我”非但不是被决定的(或者说,我们不是被动接受他人对我们施加的影响),而且可以进一步改变他人和社会,促进他人和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包含改变他人和社会倾向的“自我”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意义,自我的道德省察和提升也包含了我们帮助他人进行自我省察和提升的需要。在上一节对于“身”的文本分析中,我们看到,“身”的道德修养工夫并非局限于己身之内,而是可以推扩的,《大学》讲“修身为本”,最终是要至于“明明德于天下”(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先秦儒家说的是“修身”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是“明明德于天下”,而不是为了“修身”而“明明德于天下”,亦即不同于将“明明德于天下”作为实现“修身”的手段)。因此,儒家意义上的“修身”和“为己”,并不会面临诸如托马斯·胡尔卡(Thomas Hurka)提出的著名的“根本的利己主义”(foundationally egoistic)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并不像芝加哥传播学派自我观那样低估自我改变社会的可能性。
同时,先秦儒家自我观的上述特征也说明了儒家关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个有趣的立场,即,自我与他人并不是彼此封闭的实体,而是存在某种深度关联的,但这种关联不会取消自我之于他人的相对独立性。宋儒文本中经常出现的明镜比喻可以更好地诠释这个立场。明镜具有照物的特质,就像自我和他人的“明德”都是相似的自足完满。而明镜蒙尘之后不能照物,就像自我因为过分执着于自身(这种执着可能有多重表现,比如,过于在意他人的评价或者社会环境的影响,或者过于在意某些欲望的满足而被外物扰乱了心智等)而看不到自己和他人“明德”的自足完满。因而我们需要通过磨镜使之恢复能照物的状态,就像自我通过“明明德”的修身工夫来最终达致“明明德于天下”的“新民”结果。由此可见,儒家意义上的这种自我是通过消解自身的某些不当倾向而达致通达他人和外物的境界的,这一路径不同于本文第一节提到的库利“镜中自我”概念由外而内建构自我观的路径,而这种不同恰好可以为消解芝加哥学派乃至整个西方传播学理论自我-他人二元对立的路径可能带来的问题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注释:
① William James.ThePrinciplesofPsychology:TheWorksofWilliamJames.F.Burkhardt(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95;Charlene Seigfried,William James.ThePointofViewoftheOther,in:ClassicalAmericanPragmatism:ItsContemporaryVitality.S.B.Rosenthal,C.R.Hausman and D.R.Anderson(ed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85-98.
② 威廉斯的多重自我主张是一种静止的自我观,不能解释自我是如何产生的。库利和米德则通过突出自我的社会化特征解决了这个问题。
③ Charles Cooley.HumanNatureandtheSocialOrder.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2.p.184,pp.202-206.
⑤ 米德对自我的这种区分被布鲁默(Herbert Blumer)发展为一种符号互动论,详细讨论可参见布鲁默的代表作Herbert Blumer.SymbolicInteractionism:PerspectiveandMetho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9。
⑥ George Mead.ThePhilosophyoftheAc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p.201.值得注意的是,米德通过强调符号表意的普遍性,建立了普遍化的他人概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库利“镜中自我”理论可能面临的“一个个体与多人交往可能建立多个自我”的问题。根据米德的观点,主我面对的是由许多他人的平均期望逐渐建立起来的宾我,是一种普遍化的他人,或者说,是我们使这些他人一般化了,从而更加易于交流和对话。
⑧ Robert Park.Society:CollectiveBehavior,NewsandOpinions,Sociology,andModernSoclety.Glencoe,IL:The Free Press.1931.pp.261-262.
⑨ 相关讨论可参见Dmitri Shalin.ExtendedMindandEmbodiedSocietyPsychology:ContemporaryPerspectives.Society,vol.54,no.2,2017.pp.171-186;Norbert Elias.Power&Civility.The Civilizing Process:Volume II.New York:Pantheon Books.1939.p.88.
⑩ 相关讨论可参见胡翼青:《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