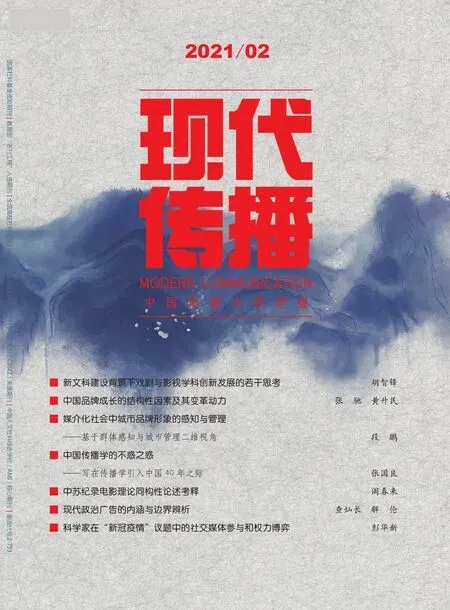试问情为何物:先秦士人“情理交融”传播价值取向*
2021-11-29束秀芳
■ 束秀芳
情感传播是近来学界较为关注的热点,那么,情为何物?这个问题是人类自我认知方面最为古老又最难以回答的问题。诺尔曼·丹森认为:“情感就是自我的感受。”而“自我感受”不会平白无故地自动出现,因此他认为:“情感存在于社会活动和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①中国情感哲学家蒙培元认为:“人的情感才是人的真实存在。”②那么我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究竟“情为何物”?我国历史上最早致力于道德观念传播的先秦士人对此有过精辟论述和卓越的传播实践。
本文基于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情感转向的研究范式,研究先秦士人道德观念传播如何体现“情理交融”价值取向。这里首先借用清代学者戴震论及的“情”与“理”关系试分析中国文化语境中“情理交融”之内涵。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关于“理”字的释义认为:先秦典籍中“理”字不多见,其字义内涵不同于后世宋儒之“理”。戴震分析先秦《孟子》《易经》《诗经》《庄子》等典籍中的“理”字,总结“理”与“情”的关系如下:“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③戴震的“理”字释义给出“情”与“理”的三重关系启示:首先是无情者无理,完全不理会“情感”的“理”是为“非理”;其次是理出乎情,应以理“节”情,在“理”的制约下释放人的“情感”;最后是“理”之节“情”应该无过无不及,达到两相和谐的“情理交融”。
先秦士人道德传播追求“情理交融”的情感取向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又有着怎样的“过”与“不及”?以下从礼情、情义、无情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以“礼”约“情”的“理性”追求
以“礼”约“情”从而实现情感理性表达,这是先秦儒家士人传播道德观念的情感取向。孔子在《礼记·礼运》篇断言:“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也。”④孔子认为人的这七种情感是无师自通、不学而能的人之本性。荀子对于“情为何物”也有过论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以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⑤荀子认为人性之核质为人情,人之情感外化而为人的欲望。荀子的这一观点与孔子言论一脉相承,在《礼运》篇中,孔子对弟子谈到人欲、情感时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⑥人的情感里面藏有人的爱恨喜恶,这种情感体验是人心的内在自我体悟,旁人不易察觉。
正是由于情感的这种自发性、隐秘性以及趋利避恶的欲望追求,孔子认为圣人治世必须“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将“人情”之治视为耕种田地,从而实现治人。孔子进一步认为:“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圣人以一人之情而知天下人之情,以治人情之欲恶。在孔子看来,“以一治天下”的这个“一”就是“礼”,因此他说:“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⑦关于以“礼”约制出自于情感的“欲望”,荀子也有过论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⑧
儒家提倡的以“礼”约“情”的理性化道德教化渗透在先秦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人的“情感”体现出一种道德之美。如《礼记》所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⑨一个人从出生、成年、成家到交友、出仕、丧亲、祭祖等,其所有行为都会受到“礼”的制约。正如徐复观所言:“通过《左传·国语》来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此一时代中,有个共同的理念,不仅范围了人生,而且也范围了宇宙,这即是礼。”⑩下文以婚“礼”与丧“礼”为例,来看此一时期以“礼”约“情”在交往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男女之情被认为是天地交合、万物生长的一种本能之情,将男女之“情”纳入“礼”的规范化轨道,被孔子认为是影响“万世之嗣”的头等大事。在先秦史料中,因男女之“情欲”而影响社稷稳定的事件屡有发生,同样,因男女美好爱情而兴国兴邦的事例也有记载,因此,司马迁在总结历史上男女之“情”与“礼”的关系时认为:“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用“礼”来规制男女之“情”,首先就是成“家”成“室”,如《左传·桓公十八年》中申繻所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通过这一句中的后四个字,可以看出在当时看来,合理的男女交往对于家庭稳定、社会稳定的重要决定作用。《孟子·滕文公下》有云:“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的这一说法,其实已将男女之情欲落实到“有家有室”这一理性轨道,实现以“礼”约“情”的目的。“礼”对于男女之“情”的理性约制,不仅体现在男女成“家”成“室”的婚姻关系的建立,还体现在围绕着“大昏”的各种礼节以及对于婚姻关系中男女权力、义务等的规制中。当代学者研究认为:“先秦的文献中能够反映出时人对于夫妻关系相敬如宾是非常推崇的,认为这是值得夸赞的道德情操的体现。”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此一时期,在“礼”的多重规制下,天然而生的男女之“情”受到压抑甚至扭曲,尤其是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性更是受到“礼”的钳制。以孟子言论为例,在《滕文公下》篇中,孟子谈到男当有“室”、女当有“家”的合理性,但是他接着强调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分析此言得知,男女因爱生情、私自约会的情况在当时也许是存在的,但却被“礼”所鄙夷、被世人唾弃。再比如孟子与淳于髡辩论“男女授受不亲”一事,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为“礼”,但是当淳于髡问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这个两难问题时,孟子答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两人的对话显露出当时社会对于“男女授受不亲”这一观念的认同,但孟子对于辩士淳于髡的“两难问题”以一个“权”字答复,又显露出当“情”与“礼”相博弈时的权衡。以点窥全,淳于髡这个“两难问题”本身就暴露了当世之时因为“礼”的约制而出现的男女交往之不合“情”现象。在男女之情这个天作之合的人类情感体验中,“礼”的出现本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和舒展“情”,但是在“礼”过度钳制“情”、甚至以“礼”的权威打压其中一方,使得男女之情尽失“天性”、女性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之后,“礼”本身也就失去了“理性”。
再以丧“礼”为例,人类对于逝去亲人的安葬之礼,可以说是人之为人最显著的情感与理性“合而为一”的行为。“葬礼”本身的人文性被视为是人类告别蛮荒、无知、本能情感的理性表达。我国先秦时期提倡的一系列丧葬之礼,就是希望将亲人离世的痛苦之“情”通过“礼”的举行而得到表达和舒缓,以求告慰生者和亡灵。以“死三日而后敛者”这一礼节为例,孔子在回答别人提问时说到:“孝子亲死,悲哀志懑,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后敛”有等待亲人复活的情感期盼,这显然受到当时科学认知水平的限制,但是“三日而后敛”这一礼节本身也很好地使得亲人离世之痛的情感得以抒发,将“悲痛之情”纳入“理性之礼”的轨道。同时,“三日而后敛”还意味着:“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由此可见,“三日”不仅是“情感”期盼的表现,也为“理性”处理丧事之必要。
另外,儒家认为:“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根据这一言论,“三年之丧”正是以时间之长来表达悲痛之深,是以“礼”舒“情”的一种表达方式。关于何以“三年之丧”,可以从孔子与其弟子宰我的一次对话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解释,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孔子以居丧不到三年是否心安反问宰我,当得到肯定回答后,孔子认为宰我“不仁”。之所以这样评价其弟子,是因为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是基于父母与子女的深厚情感,从父母养育之恩延伸而出的子女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出发,将这种“深情”用“三年之丧”的“厚礼”来表达,才能让人的悲痛之情得以释缓,是一种情感的理性表达。
先秦儒家士人不厌其烦地从各个方面谈论丧之“礼”,不可否认,丧事的礼节化处理是“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但是,当丧“礼”繁复到了无人“情”的地步,就不得不说是“过犹不及”的非“理性”之举了。例如:“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这些礼节其实已经违背了“礼出乎情”的初衷,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因此,墨家极力批判儒家士人推崇的久丧、隆丧之礼,提倡有节制地“节丧”就反而显得“理性”了。
关于“情”与“礼”的关系,司马迁作了较好总结:“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周公制“礼”以规范人类情感和行为秩序,曾在先秦时期发挥重大作用,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人作为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极力推崇,并身体力行进行广泛传播。但到了战国时期,“礼”本身的繁琐约束了人之真“性”和真“情”,使得“礼”陷入非“理性”之中,“礼”与“情”失和。
二、“情”深“义”重的“情感”取向
以“礼”约“情”,实现人的情感的“理性”表达,被“礼”约制以后的人的天然情感依然要以“情”表现和表达出来,借以和自我、他人实现交流,这个被克制的理性情感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被称作“义”。
《礼记·郊特牲》一篇中谈到“礼”与“义”的关系:“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也就是说,在“礼”的形式包裹下,“义”才是具有实质内涵的内容表达。那么,“义”具体包括什么内容?它和人的天性情感关系是怎样的呢?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一条将“情”和“义”对举,视“义”为“情”之所终:“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再来看孔子的言论:“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人之义。……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
孔子将十种人伦关系中关系主体应当具有的“义”作了交代,同时认为要实现从治“七情”到修“十义”的跨越,非“礼”不成。以“礼”治“情”而至“义”,不仅是对个体情感体验的约束,也是与他者之间的情感协调,因此可以说:依“礼”而治,对人的情感进行道德约束,使得整个社会实现德性教化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孔子所言:“圣人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人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据此可知,圣人在耕种“人情”这个田地时,以“礼”而“耕”只是手段,播撒的是“义”之种,“义”是圣人治世希望结出的果实,这个“果实”的获得,还要在“礼”耕的统领下辅之以其他手段。荀子对于“义”之“节”情也有过与孔子类似的表达:“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
关于“义”与“仁”的关系,孔子认为:“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义,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我们再根据孔子关于“仁者爱人”的相关论述,可以这样认为:“义”是人的天然情感经过“礼”的节制后的理性表现,而这个理性的“情感”要以“爱”为本,因“仁”而“义”。这种由“仁”而“义”的理性情感既可以由个体内在之“仁”外化为一种外在之“义”,也可能是在处理各种情感关系状态中的你“仁”我“义”,即所谓:“协于义,讲于仁,得之者强。”
“义”作为一种被“礼”节制后的“理性”情感,是情感的理想状态,是由“仁”爱而生的深“情”,因此,这种德性之美受到先秦时期士人们的推崇,并在其言论和行为中体现出“情”深“义”重的“情感”取向。如孟子所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吕氏春秋》中的《高义》和《上德》两篇也记载了先秦时期士人追求“义”之德性价值的相关言行,例如:“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
这些言论认为君子之行动必须出于“义”举,即使和世俗常理相违背,君子也必须把忠诚于“义”作为唯一准则。如史料记载楚国士人石奢,当他办案时发现杀人者为自己父亲,为了表达作为儿子的“孝”义和作为臣子的“忠”义,他选择自己在执法的斧刃上割颈而死。对于石奢这一“义”举,《吕氏春秋·高义》一文这样评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奢之为人臣也,可谓忠且孝矣。”再来看看其他文献中记载的关于先秦士人为了坚守“义”之德性价值而宁愿放弃生命的例子。据《史记·魏公子列传》所载,魏公子信陵君为人谦让仁慈,深得贤士拥戴,其门下七十高龄的贤士侯嬴和屠夫出身的贫士朱亥,为了报答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一个临危受命、知难而进,另一个信守诺言、自杀而亡。侯嬴与信陵君密谋“窃符救赵”一事,并让朱亥同行,以防不测,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而侯嬴因为自己年岁已大不能同行,于是对信陵君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刎,以送公子。”此二人对于信陵君的忠诚可谓是“情”深“义”重,朱亥在其后与信陵君同行窃符过程中,果然“袖四十斤铁锥,锥杀晋鄙”,而不能同行的侯嬴信守向北自杀的约定:“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刎。”
此一时期,“士为知己者死”的例子不胜枚举,实可谓“情深义重”却又“为情所困”。深情不代表真情,“义”作为被“礼”理性化的情感,是儒家士人所提倡的情感“情理合一”的理想状态,但它又始终处于情感与理性的博弈和多种关系主体的多个层面情感之“义”的争夺之中,因此,“情”深“义”重的“情感”取向落实到具体道德行为中是错综复杂的,很容易因为追求理性之“义”而远离人的本性之“情”。《庄子·盗跖》一文批评此种“义”举,认为轻视生命、为“义”而死的举动是沽名钓誉的表现,严重背离人的本性,所谓:“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这里以孟子为例,试分析儒家士人如何看待“过犹不及”之“义”举。据《孟子·告子》篇记载,告子问孟子:“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告子将人性比作杞柳,将仁义比作桮棬,认为让人的本性归于仁义,就好像用杞柳做成桮棬这种木制的杯盘一样。孟子反问道:“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反问告子是顺着杞柳本来的样子做成杯盘呢?还是毁坏杞柳本来的样子然后做成杯盘呢?如果要毁坏杞柳本来的样子才能做成杯盘,那么也要残害人的本性来成就仁义。孟子认为告子的这一说法会损害仁义本身,因此否定他。
孟子作为“舍生取义”道德理念的提倡者、传播者和践行者,可以说他在政治活动和个人生活中,将“义”之举践行到了极致。但是将孟子的此番言论与孔子“父子相隐”观念相联系,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士人对“义”这种道德情感的追求看重的是人心内在真实“情义”,不是一味追求“理性”之“义”以至于“忘情”,反对“过犹不及”。
三、“自事其心”的“无情”境界
将人的天性之“情”在“礼”的约制下实现理性“义”之表达,达到“情理交融”的理想状态,这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士人道德传播的价值取向。但是现实境况往往与理想背道而驰,到了战国时期,孔子提倡的复“礼”已经因为繁文缛节而至钳制人性,在“礼”外壳包裹下的“义”转而发展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在这种历史现实中,以庄子为代表的士人开诚布公地反对“仁义”,直呼仁义其非人情乎!
那么,庄子“无情”吗?庄子无情之“情”又体现出怎样的情理交融价值取向呢?在《庄子·人间世》一篇中,庄子提出“自事其心”的情感主张,认为:“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这种任由自己内心的情感取向、不为外物所动的情感态度,被庄子认为是一种“至德”的表现。要理解庄子“安之若命”、顺性而为的情感主张须从庄子之“道”入手,庄子将“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最后根源和人的精神或道德的最高境界,也即所谓“道通为一”。将自然秩序、社会法则、人类情感全部统一为一体的“道”决定着人与万物的本然、应然状态,而这个“不可见”“不可称”之“道”本身在庄子看来是“情理”相融的。
在《庄子·达生》篇中,庄子借孔子问道的寓言故事,以“蹈水有道”寓“道之有理”:“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这种顺水势而为的游泳之“道”暗喻“人为”应该顺应“水性”,而“水性”又暗喻“万物固有之理”,如庄子所说:“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道者必达于理。”道的固有之理在《庖丁解牛》寓言故事里也有彰显,当文惠君问庖丁何以“技盖至此乎?”时,庖丁回道:“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庖丁解牛不仅暗喻了“依乎天理”的行事主张,也暗喻了“天理可循”的价值指向。这个道之“天理”体现了道本身的理性,它与儒家的人道之“礼”不同。
庄子之“道”不仅是理性的,还是有“情”的。如《大师宗》一文对“道”的阐释:“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知北游》一文中,庄子更是开明宗义地提出:“精神生于道。”正是这个“万物之所由”之“道”主宰了自然与人间万物的情感与理性,因此,在庄子看来,大到治国理政,小到个人情感,皆应“依道而行”,实现自然之美与人间秩序的完美和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将人道、天理归而为一,而这个“道通为一”之“道”本身就是情理交融、至真至善至美的。在这一总体认识之下,就能理解庄子“自事其心”的“无情”主张。
《德充符》篇记录了庄子与惠子一次关于“人故无情”的对话,试分析如下。庄子对于惠子“人故无情乎”的提问予以明确肯定回答“然”,惠子进而追问:“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追问:“既谓之人,恶得无情?”惠子坚持“人必有情”,庄子坚持“人出于道”,那么,如何理解庄子“人之无情”的主张呢?如他所说:“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也就是说,庄子所谓的“无情”之“情”乃是指对天道之情的人为约束,是背离自然法则、扭曲人性的人为之情,如《骈拇》篇所说:“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若以人为之“正”益本性之“正”,则会与本性相违背而至失去本性之真“情”。庄子认为,人处于俗世,应该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庄子此处的“无情”之说,陈鼓应认为庄子“无情”蕴含的深层意蕴则是对情的超越和提升,即超越负累之情,将“人情”提升到“天情”和“道情”。蒙培元认为:“庄子之‘无情’决不是真无情,而是情感甚笃,情怀甚高,他的真正用意是超越世俗之情而回到天地之情。”
庄子用“任其性命之情”和“安其性命之情”来表达这种尊重人性的“无情”之“真情”。那么,庄子如何在“任情”和“安情”境界中将“天情”“道情”落实到“人情”之中,在现实交往中体现这种情感取向呢?这里用《庄子》书中关于“君子之交”的言论与故事来窥察庄子“无情”境界中真挚、深沉的交往观,以进一步论证庄子的情感价值取向。在《庄子·山木》篇中,庄子提出“以利合”和“以天属”两种不同的交往状态,并认为“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害相收也。”庄子提倡“天性相属”的“君子之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鳢;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理想中的这种遵从天性的“君子之交”又是如何体现情理交融的呢?在《大师宗》篇中,庄子从“死生”论起,论及人与人相“忘”之不得已,其实正是一种遵从天性之情的理性交往表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对悬置于生之上的死给予理性情感判断,于是便有了下文的“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不得已而“忘”情的无奈。在这一思想统领下,就可以理解庄子在此篇中设置的寓言人物相互为友、是为莫逆之交,却又在友人生病、离世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之礼的淡定,及至庄子本人对于妻死的“鼓盆而歌”。庄子基于天道理性的“忘情”思想在现实交往中表现为“淡”,但是这种“淡若水”的状态正是符合天性的表现。
进一步分析可知,在“淡”之中又蕴含着“亲”,比如上文所述的鱼儿出于本能的求生,“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以及庄子在其妻死以后的第一反应:“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另外,庄子与惠子这对好友有多次争辩、交游的记录,可谓是不加掩饰的性情之交,据《徐无鬼》篇记载,庄子送葬经过惠子之墓,自言:“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矣。”这种思念好友的真挚之情令人动容。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之“无情”观中,既有理性的智慧与克制,又显现出人天性之情中的真情与深情。按照蒙培元的话来说,就是:“不为情而情,无任何人为的做作、计较和打算,出于自然,各得其所,各顺其情。”
作为人类生存和合作基础而存在的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中交织着人性的困惑和理性的审视,哈贝马斯寄希望于通过理性化的道德实践来实现社会意识的改良,进而达成一种相互理解的合作关系。他的这一愿景,其实正是我国先秦时期士人进行道德传播的一种价值追求。先秦儒家主张以“礼”约“情”实现情深义重的情理交融,但终究没能走出情与理相悖的困局。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全力抨击这种世象,提出一种与“仁义”价值观念相左的“无情”主张,并且力主“无情”之情的情理交融、天人合一。后世学者认为庄子超世俗、超人类的情感体验是在墨家、儒家的理想社会所提供的东西完全得到以后,或者根本得不到时所需要的。先秦士人传播和践行的“情理交融”情感取向从侧面回答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情为何物”的问题,对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不乏可以奉献给整个人类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卓越智慧和价值,亦可为当下情感传播研究提供借鉴。
注释:
① [美]诺尔曼·丹森:《情感论》,魏中军、孙安迹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③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⑤ 〔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十六,第428页。
⑧ 〔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十三,第346页。
⑩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