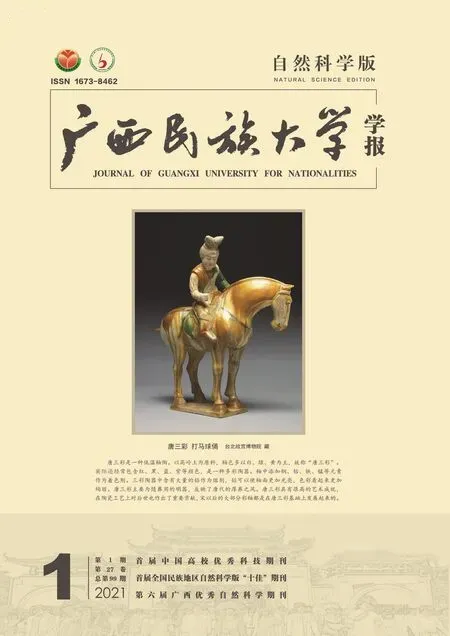抗战前中国土壤学的国际化历程*
——基于三次世界土壤学大会的考察*
2021-11-29宋元明
宋元明
(北京科技大学 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 100083)
土壤学作为近代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1924年,因欧美农业土壤学家们有意建立土壤分析和土壤分类的标准化方法,国际土壤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oil Science,简称ISSS)①现已更名为“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il Sciences”,简写为“IUSS”。得以成立,世界土壤学大会亦应运而生,成了各国土壤学家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平台。晚清时期,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近代土壤学知识传入中国,历经晚清民国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了中国近代科学中颇具特色的一个学科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学习,力图推进土壤学研究的本土化和建制化,另一方面努力融入国际学术圈,展示中国土壤学界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中国土壤学的研究成果如何从无到有,一步步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学者如何通过参加世界土壤学大会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这些活动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目前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土壤学史的研究较少,其中涉及世界土壤学大会的部分研究成果仅在少量农史著述和当事人传记中稍有论及,且皆为浮光掠影,多有错漏。[1-2]文章试图根据会议记录、报纸杂志、参会人员回忆录及传记等材料,尽可能还原此段历史之原貌,从此视角探寻抗战前中国土壤学的国际化历程。
1 世界土壤学大会的缘起与中国元素的出现
西方近代土壤学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按今日之观点,根据研究侧重点不同可分为农业地质学和农业化学两大方向。这两大方向兴起于不同地区,与当时的历史地理背景有很大关系。西欧农业历史悠久,土地资源稀缺,在拓展新的耕地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农学家们的关注点集中于如何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能力,即如何提升单位面积产量,这为农业化学学派的兴起提供了丰厚土壤,同时也涌现出了如布森戈(J.B.Boussingault)、李比希(J.von Liebig)、劳斯(J.B.Lawes)、吉尔伯特(J.H.Gilbert)等一批著名的农业化学家。与西欧不同,美国和俄国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劳动力稀缺,有大片待开垦的土地可供农业发展,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高效鉴别适宜耕作的土壤,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条件,来减少劳动力的浪费。因此,农业地质学应运而生,其中享有盛名的俄国的道库恰耶夫(V.V.Dokuchaev)、美国的马布特(C.F.Marbut)等学者对土壤的形成和发育进行了充分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欧的土壤学源于实验室,而美国和俄国的土壤学则起于野外。
土壤学作为一门科学得以形成,正是基于这两大方向的融合,而这种融合离不开世界范围的统一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就是国际土壤学会得以建立的现实需求。1909年,国际农业地质学大会的召开为学会的建立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同年,在匈牙利皇家地质学会的土壤学家们的倡议下,第一届国际农业地质学大会在布达佩斯召开,大会为期10天,来自23个国家的86名科学家相聚一堂。大会把议题限定为土壤起源和分类的一般性讨论,并建议采用统一的土壤分类体系及实验室研究方法,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愿望难以实现。会议行将结束之时,与会人员一致决定将此类会议设为常态会议。[3-4]在此次大会上,1877-1880年曾在中国游历数年的匈牙利地质学家洛川(L.Lóczy)提交了《在中国黄土上长出最好的小麦》(In China wächst auf Löβder beste Weitzen)一文,首次涉及中国议题。[5]次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吸引了全世界170名土壤学家前来参会,会议形成了3个委员会。[3]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会也是最早见于中文报道的国际土壤学会议。[6-7]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系列会议的举办,原定于1914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会议也被迫取消。战后,各国土壤学家又开始重新谋划举办新的会议。1921年9月,土壤学家海信(D.J.Hissink)和科佩克(J.Kopecky)向世界各国学者发出邀请,倡仪举办一次预备会议,商讨重启此前中断的第三次会议。次年4月,约50名土壤学家相聚布拉格,原先筹划的预备会议却意外变成第三次会议,其成果之一就是形成了5个委员会,并决定1924年的大会在罗马召开。1923年6月,在苏黎世召开的预备会议将建立国际土壤学会提上了议程。1924年5月12-19日,第四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召开,共有来自39个国家的463名代表出席。大会形成了6个委员会,这6个委员会是国际土壤学会形成的基础。此次大会的最后一天,正式宣布成立国际土壤学会,并且决定于1927年召开全新的世界土壤学大会,首次会议由美国承办。[3-4]
1927年6月13日,第一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美国通过此次大会充分展现了其作为新兴大国的科研实力,特别是会后组织的跨越美国的土壤考察活动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获得了一致好评,同时促进了各国土壤学家的交流。[8]1930年7月,第二届大会在俄国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召开,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土壤学与世界土壤学大会的缘分。[9]在此次大会上,有关中国土壤学的实地研究报告首次亮相,会员名录中也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这一切都与中国关于土壤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密切相关。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之风逐渐兴起,近代科学纷纷被引介来华,其中就包括近代土壤学。19世纪末,《农学报》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率先翻译了日本和美国的土壤学专著,土壤学知识开始成系统地传入中国。伴随着学校开设土壤学课程和留学生出国学习土壤学的潮流,这门新兴学科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1930年初,金陵大学率先在中国拉开土壤调查的序幕,在该校农经系主任卜凯(J.L.Buck)和农科主任芮思娄(J.H.Reisner)的精心筹划下,美国加州大学土壤学教授萧查理(C.F.Shaw)应邀来华主持土壤调查工作。1930年2月,萧查理来华后,率领团队对长江与黄河下游区域的土壤进行了勘测,其范围之广阔前所未有,取得成果之丰硕亦创新高。[10]
萧查理工作期满之时,恰逢第二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俄国召开,萧查理便带着在华数月的调查成果赶赴俄国。7月22日,他在“土壤命名、制图和分类”分委会上以此前研究工作为基础,做了题为“中国的土壤”(Soils of China)的报告,并提交了名为《中国土壤初步实地研究》的论文。这篇长达25页的论文不仅追溯了周朝时中国古人的土壤分类思想及对土壤特性的研究,还提及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维理士(B.Willis)、富兰克林•金(F.H.King)等西方学者对中国土壤的早期调查。萧氏根据实地考察,将所见土壤大致分为九个区域,分别为红土区域、磐层土区域、褐土区域、中部扬子受溢平原、扬子下游冲击区域、淮河流域土壤、黄河旧道淤积土、北方平原冲积土、中部平原沙姜土,从性质、起源、形态、地势、侵蚀、排水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分析,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他所率领的金陵大学土壤调查团队所做之工作。此外,他还附带介绍了铭贤学校农科主任穆懿尔(R.T.Moyer)在山西进行的土壤调查工作。[11]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中国首本土壤学专业学术期刊——《土壤专报》创刊号上刊载了萧查理的论文《中国土壤——概观之实地考察》,这篇论文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份大范围的实地土壤调查报告。[12]对比该论文与之前的会议论文可以发现,二者主体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土壤专报》所刊版本内容更多,其中绪言中多了“土壤分类”一节,各区土壤的章节下也增加了“利用”部分,文末增补了“土壤改良”一章,结论较会议论文更为充实和丰富。故萧查理在世界土壤学大会提交的论文应该更早,也是中国土壤实地研究在国际上的首次展示。①在第一届世界土壤学大会上,时任金陵大学农学教授的罗德民就准备提交题为《影响降雨地表径流的因素》(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urface Run-off of Rainfall)的学术论文,但是不知何故未能提交。
就在西方学者积极在华开展土壤调查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努力谋求土壤学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此次大会的会员名录上,首次出现了一位中国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铁明。可惜的是,作为国际土壤学会第一个中国籍会员,铁明的生平及贡献长期为学界所忽视。
铁明,1905年生于上海,由清华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大学教育学士、农学士,俄勒冈大学科学硕士。随后在印第安纳州担任化学处化验师、俄勒冈州农业试验场土壤学技副。归国后,他积极活跃在学界,曾任“国立劳动大学”教授、浙江省土壤研究所所长、“国立浙江大学”教授等职。1936年,他和邓植仪等人积极筹划,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土壤学术团体——“中国土壤肥料学会”,并当选副理事长,主持编辑发行会刊《土壤与肥料》,在当时的中国土壤学界极负盛名。[13-15]他早年曾积极谋求中国土壤学的进步,促成学科建制化,在土壤肥料学、水土保持学方面撰写了大量论文,在中国早期的土壤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中国此时尚无有组织的土壤学研究,人员也十分零散,但从铁明的当选可以看出,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有意识的积极参与并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才有了随之而来的中国土壤学的“黄金年代”。
2 第三届世界土壤学大会中的中国代表
1930年对于中国土壤学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堪称中国土壤学研究的“元年”。西方土壤学知识虽然早在晚清就已传入中国,但是由于政局动荡、资金缺乏、人才不足等原因,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是“翻译东西文书籍,讲讲外国土壤或普通学理,与本国本地毫不相关”[16]2的局面。这一状况直到1930年2月萧查理来华主持大范围土壤调查工作才得到根本改变。在此契机下,同年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土壤学研究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得以建立,第一个地方性的土壤调查所——广东土壤调查所也随之诞生。此后数年,“中央农业实验所”、浙江土壤调查所等一批机构先后开展了土壤及肥料方面的研究工作,土壤学学术共同体开始逐步形成,成绩日渐显著,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逐渐增多。
1935年7月31日,第三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英国牛津举行,50余国的400多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分为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土壤肥力、土壤形态、应用与改良土壤六个大组,宣读论文共计172篇。[17]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此次大会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举行的最后一次世界土壤学大会,同时也是中国派遣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大会。
当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将要召开的消息传回中国,国内研究土壤的主要机关决计派遣代表参会。最终,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邓植仪,中国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主任梭颇(J.Thorp)、副主任侯光炯,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主任张乃凤作为正式代表前往英国牛津。
梭颇当时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主任和首席专家,他来华工作是由时任美国农业部土壤调查处首席科学家马布特推荐,以接替1933年从地质调查所离职的美国土壤专家潘德顿(R.L.Pendle⁃ton)。他本人因故未出席此次大会,②梭颇缺席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此次大会副主席马布特会后来华做准备。不过他向大会提交了题为《中国土壤临时性地图(附说明)》的报告。选择此报告,与他此前在华的工作密切相关。1933年梭颇来华后,在侯光炯、李庆逵等人的协助下,利用两年半的时间,先后在山东、河北、陕西、甘肃、广西、广东及江西等17省进行了土壤考察,并发表了大量的考察报告,同时编制了百余幅中国土壤图,采集了万余个土壤标本,于1935年首先制作完成比例为1:750万的中国土壤概图。[18]可以说,他的报告正是土壤研究室成立五年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梭颇在报告中回顾了此前地质调查所和金陵大学的土壤调查工作,着重谈到了影响中国土壤剖面发育的三个独特的局部条件,分别为稻米种植(Rice Culture)、粪肥的使用和北方区域的大量黄土沉积。[19]
梭颇因故缺席,但是地质调查所派出了梭颇最为得力的助手——土壤研究室副主任侯光炯参会。侯光炯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1931年受聘于中国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后担任该室副主任。他和诸多中国青年土壤学家一起,一直跟随梭颇进行土壤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侯氏在此次大会上宣读了他和马溶之合作完成的《与稻米生产相关的宏观土壤特征研究》一文,该报告在国际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壤名称和水稻土形成“三育”(即淹育、潴育、潜育)特征,对水稻土的发生、层次形态划分,特别是水稻土层次形态与生产力的关系做了科学论述。[2,20-21]不仅如此,他还带来了几十份水稻土在牛津大学陈列展出,系统地展示了中国水稻土的研究成果。[22]
此次大会资格最老的中国土壤学家当属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邓植仪。他是中国自费赴美留学攻读土壤学的第一人,在威斯康星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曾在威斯康星州农事试验场短期从事土壤研究工作,回国后任教于多个农林机构,后担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1930年,他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主持了广东省各县的重要土系及土区调查,开国人主持土壤调查之先河。经过3年多的实地考察后,他于1934年出版了《广东土壤提要初集》。1935年,他又创建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是当时国内唯一培养土壤学硕士研究生的机构。同年与彭家元合著《土壤学》,是国人撰写的最早的土壤学教材之一。[23]1-18
作为当时国内土壤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邓植仪对参加此次土壤学大会颇为热心,他认为“惟是土壤研究,贵有切磋比较,方利进行,且在我国尚属幼稚时期,尤须有借助他山之处”,[24]于是积极申请参会,得到学校和政府的大力支持。1935年6月,邓氏从广州出发,遍访东南亚诸国,考察土壤,参观农业机构。后经地中海过法国,最后抵达英国。[24]他为此次大会做了充分准备,在“土壤结构及类型”(Soil Formation and Soil Types)分会场作了题为《广东省之土壤》的报告,介绍了广东省的自然状况,依据其在广东的实地调查结果,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广东省土壤调查工作和成就,主要论述了山地土壤(Upland Soils)和低地土壤(Lowland Soils)的基本情况。[25]此外,他还提交了题为《中国土壤研究的发展现状》的论文,不仅回顾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夏禹治平水土后,曾辨别九州的土壤并比较其肥力而制定赋贡之法,还着重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土壤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述及金陵大学、中国地质调查所、中山大学目前所做的工作和进展,同时也谈到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向大会提出了制定统一的土壤调查标准的建议。[26]
除中山大学外,“中央农业实验所”选派了土壤肥料系主任张乃凤出席此次大会。张乃凤先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硕士学位。1931年,张乃凤学成归国后受聘于金陵大学,主讲土壤学和肥料学。会前刚刚转往“中央农业实验所”任职。虽然此次大会的会议材料中只有其参会信息,没有其报告和论文信息,但据传记材料记载,他在会上宣读了《中国古代土壤分类》一文(也可能是口头报告或者讨论),并座谈了肥料试验的途径。[23]65-73
除了正式出席大会的三位代表外,中国还有两位青年学者列席此次会议,他们分别是牛津大学硕士廖鸿英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夏之骅。廖鸿英当时正在牛津大学进修农艺学,于1936年返回武汉大学任教,后为中国研究胰岛素的先驱之一。1942年,李约瑟在重庆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时,廖鸿英还曾担任此馆秘书长,成了李约瑟的主要助手。夏之骅则是1933年清华大学第一届24位留美公费生之一,回国后任江西农学院化学系主任、福建农改处处长等职。
从参会机构及人员来看,中方只有三家机构四个正式代表(实际参会只有三人),规模虽小,但却精干,代表了中国当时土壤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首先,从参会机构来看,这三家机构不仅创办时间最早、成果最丰硕,而且专业人员最齐备、资金也最充足。其中,中国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土壤学专业研究机构,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专款资助。自1930年开始,在潘德顿、梭颇等西方专家的指导下,短短五年时间已经发展成国内科研实力最强的土壤学研究机构,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本土土壤学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土壤学专业期刊,而且完成了全国多数地区的土壤概测。“中央农业实验所”隶属国民政府实业部,是当时中国最高农业技术研究、试验和推广机构,与同处南京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及“中央大学”农学院合作密切,下设土壤肥料系专门进行土肥研究。中山大学是当时最为知名的大学,坐落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的广东,其农学研究冠绝华南,率先创立了地方性土壤调查所,最先培育土壤学研究生,最早实现了完全由国人主持的省区土壤调查。
其次,从参会代表来看,这四位代表皆是当时中国土壤学界的中流砥柱。梭颇虽是美国人,但受雇于中国地质调查所,领导完成了对中国大部分区域的土壤概测,并且编制了第一部全国性土壤调查报告和第一幅大比例土壤概图,培养训练了一批中国青年土壤学家。侯光炯跟随梭颇多年,不仅是梭颇最重要的助手,也是土壤研究室的中方负责人之一。邓植仪执掌中山大学农科多年,一手开创中山大学土壤学科,是广东土壤调查的先驱。张乃凤在金陵大学执教土壤学多年,经验丰富,此时刚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及土壤肥料系主任。
另外,从提交的论文和报告来看,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相较于西方学者还有一定差距,但仍不失特色,不仅有取之于实地调查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关于古代中国土壤学史和当时土壤学科发展现状的介绍,充分展现了中国土壤学研究的独特性,为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土壤、中国土壤历史、中国土壤学科提供了一个窗口。以水稻土为例,水稻土是一种发育于自然土壤之上,经过人为水耕熟化、淹水种稻而形成的耕作土壤。中国的水稻土历史悠久,分布范围很广,以长江中下游平原最为集中,极具地方特色。侯光炯关于水稻土的研究,充分展示了中国土壤学家在运用西方近代土壤学理论进行土壤研究时的创造性发挥,是中国土壤学界对世界土壤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作为各国土壤学家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世界土壤学大会在中国土壤学追求国际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借助这一平台,中国学者积极与西方学者交流和合作,开展了诸多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土壤学的国际化。
3 世界土壤学大会对中国土壤学国际化的影响
第三届世界土壤学大会是中国土壤学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土壤学大会,中国学者借此机会与各国学者进行深入交流,在展现中国土壤学研究所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借助这一国际舞台扩大了国际影响力。除了参与大会报告和讨论外,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准备的土壤图和土壤标本亦在土壤科学博物馆进行展示,大小共计60余箱,数量颇多,其中尤以全国土壤图、气候图、地形图等最受大众欢迎。这些展品会后就留在英国,被该博物馆永久收藏。[27-28]
有关中国土壤学的研究也激起了与会各国专家的浓厚兴趣,他们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会上,萧查理、潘德顿以及波兰的土壤学家施特雷默(H.Stremme)对中国的土类划分提供了建议,认为有必要为之建立新种类;英国土壤学家施坦普(L.D.Stamp)和爱德华兹(M.V.Edwards)希望将中国正在进行的土壤调查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美籍水土保持学家罗德民(W.C.Low⁃dermilk)则格外关注华北的水土保持情况。[29]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继续参与或开始投入到与中国土壤学有关的研究中来,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串联起中外学者的学术网络。
以罗德民为例,他曾于20年代在金陵大学任教,对华北的水土保持研究非常深入,早在第一届世界土壤学大会时,他就计划提交在华研究水土保持的成果。即便是返回美国之后,他依旧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土壤学研究,萧查理来华某种程度上就是源于他的推荐。1942年,罗氏还作为美国科技援华的代表再次来华,在西北地区主持水土保持工作。
马布特是此次大会的副主席,也是国际土壤地理学的权威。他对中国土壤学的研究一直颇有兴趣,有意来华访问,之前因故未能成行。按照计划,他将应邀在会后前往中国指导土壤调查,会上他与侯光炯进行了交流,在谈及即将进行的中国之行时,表示“在华期间将会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土壤的研究之中”[30]。遗憾的是,他在前往中国途中不幸罹患肺炎,于1935年8月在哈尔滨去世。[31]
不只是马布特,英国的土壤肥料学专家理查生(H.L.Richardson)也在会后不久奔赴中国,而他的中国之行可能与张乃凤有关。二人不仅同为参会代表,张乃凤还于会后在理查生所在的洛桑试验站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很有可能因此结识。张氏回国后在多个省份进行氮、磷、钾三要素肥料田间试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迁至四川成都,理查生应邀来华与张乃凤合作,继续在川陕云贵等地区进行肥料试验,其结果后经张乃凤和叶和才整理成文。该工作对中国化肥使用及肥料田间试验均产生了深远影响。[23]65-73后来,理查生还将其在华研究成果提交给了1952年在都柏林召开的国际土壤学会会议上宣讲。[32]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能参加世界土壤学大会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借助此行积极与世界各地的土壤研究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调查沿途各国的土壤研究现状,参观访问了多国土壤研究机构,极大地拓宽了视野。如前所述,邓植仪借此机会,展开了历时160余天的环球农业调查,遍历欧美及东南亚诸国,对各国的农业设施、政策、试验、管理、贸易、土壤、肥料等情况进行认真考察,以寻求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良方。回国后,他撰写并出版报告,详尽地记述了考察情况及改进中国农业的意见,呼吁各界重视农业生产及教育,以复兴乡村。[24]张乃凤于会后前往英国洛桑试验站农业试验场学习田间肥料实验方法,赴瑞士维格纳(G.Wiegner)博士的土壤胶体化学实验室和荷兰格罗宁根的土壤学家海信的土壤研究室参观学习,又前往德国柯尼斯堡的米切利希(E.A.Mitscherlich)教授的土壤肥料实验室学习蜜氏肥料需要量测验法,随后前往俄国参观土壤博物馆、考察俄国著名土类,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行实习研究,前后历时半年有余。[33]侯光炯则得到苏、美、德、法、英等国代表的邀请和中华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前往各国访问和开展合作,并在国外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23]74-87
4 结语
从中国关于土壤学研究的首次出现,到中国代表首次亮相世界土壤学大会,体现了中国土壤学界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追求“引进来”,也在积极“走出去”,在实现学科建制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努力追求国际化。虽然中国的土壤学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借助世界土壤学大会这一舞台,有关中国土壤最新、最为重要的成果都得以及时展示于各国土壤学家面前,这对各国了解中国土壤学成果有着极为重要的宣传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发现,中方机构和中国学者也在有意识地构建国际学术关系网,并透过这个学术网络寻找交流合作的机会,引入西方智识,取长补短,拓宽学术视野,以期推动自身之进步。
就在第三届世界土壤学大会结束不久,中国土壤肥料学会乘中华农学会开会之便,于1936年8月23日在镇江宣告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土壤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参加第三届大会的邓植仪、侯光炯、张乃凤、夏之骅、廖鸿英均成为该会首批会员,邓植仪还因其崇高的声望当选首任理事长。中国的土壤学家开始有意识地组建本国土壤学共同体,共同推动近代中国土壤学科的发展及建制化。
第三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后,国际土壤学会计划于1937年在西班牙召开第四届世界土壤学大会,但因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而搁浅。紧随其后的“二战”导致会议一度中断。尽管如此,中国土壤学家依旧借助各种机会参与国际土壤学会议,融入国际合作,如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陈恩凤在德国留学期间就参加了1936年在德国柯尼斯堡举办的国际土壤学会会议。[34]直到1950年7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土壤学大会上,中国土壤学家李庆逵当选副主席,不仅体现了中国国际学术地位的提升,也标志着中国土壤学从此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国际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