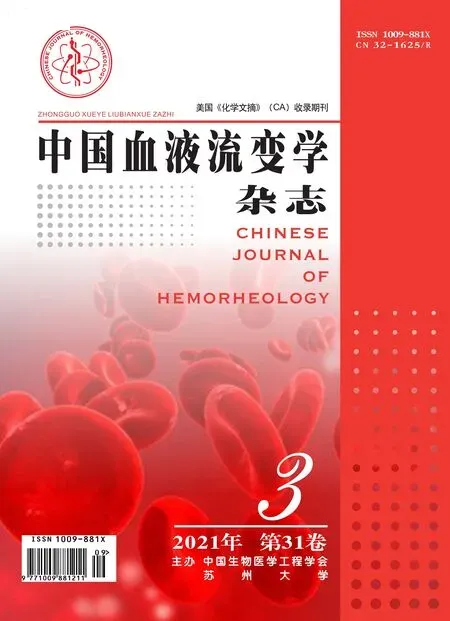Polo样激酶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2021-11-29叶芊伲董孟杰
叶芊伲,董孟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浙江 杭州 310003)
Polo样激酶1(Polo-like kinase 1, PLK1)是首个被发现的Polo样激酶,其表达量及活性在有丝分裂时呈周期性改变[1]。通过改变亚细胞定位,PLK1几乎参与有丝分裂启动、中心体成熟、纺锤体组装、染色体分离及胞质分裂等有丝分裂每一步过程,被认为是调节有丝分裂的关键蛋白[2]。PLK1已被证实在多种肿瘤类型中过表达,对诊断早期肿瘤和预测预后具有重要价值,可作为新型肿瘤标记物或肿瘤基因治疗新靶点[3]。本文将系统总结PLK1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中表达、靶向治疗及其肿瘤耐药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1 PLK1在肺癌组织中表达与肿瘤预后
PLK1在大部分恶性肿瘤细胞中呈过度表达,主要在细胞有丝分裂的G2晚期及M期表达。PLK1表达程度与NSCLC的肿瘤分期、肿瘤的发生与发展、临床预后等密切相关,具有作为治疗NSCLC靶点的潜力。Li等[4]通过免疫组织化学及qRT-PCR发现肺鳞癌组织中PLK1 mRNA及蛋白表达程度与肿瘤分化、肿瘤大小、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不同分期肺癌组织中PLK1表达强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随着分期的增高, PLK1表达的阳性率及程度亦增加。Van den Bossche等[5]研究发现肺腺癌组织均有不同程度的PLK1 mRNA和蛋白质水平上调[可高于正常肺组织5.73倍(0.742~18.846)],表达程度与肿瘤分化程度密切相关,在低分化肿瘤中尤为明显;有趣的是,非吸烟患者表现出更高的PLK1 mRNA水平。PLK1 mRNA低表达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高于PLK1 mRNA高表达组(P=0.001,HR=1.150)。基于单因素和多因素生存分析,PLK1高表达被证实是在NSCLC中一个独立的预后不良因素(HR=1.926~2.113)[4,6]。
2 以PLK1为靶点的药物研究
PLK1是细胞进程中重要的有丝分裂激酶,抑制PLK1可以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并抑制肿瘤生长,为肺癌治疗提供重要的生物学靶点。目前以PLK1为靶点药物研究分为抑制PLK1表达(如PLK1反义寡核苷酸、RNA干扰技术等)和抑制PLK1功能两种。
PLK1反义寡核苷酸(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ASOs)以剂量依赖性和序列特异性的方式抑制肿瘤组织PLK1 mRNA和蛋白质水平[7]。体外实验发现转染PLK1 ASO(pcDNA3-PLK1)的A549肺癌细胞在48 h后PLK1 mRNA表达下降61.84%,50%以上细胞停滞于G2/M期且细胞凋亡显著增加;体内实验发现PLK1 ASO对A549裸鼠移植瘤的抑制率为70%~86%[8]。Kawata等[9]研究PLK1对肺癌肝转移的影响,在接种PLK1小干扰RNA癌细胞70 d后,小鼠肝脏转移瘤(A549细胞株)明显受抑制。然而,由于ASO易受核酶攻击及RNA干扰技术安全性、稳定性问题,在临床转化及其应用上仍受限,小分子抑制剂是目前靶向PLK1的更好选择[10]。
PLK1的N-末端是高度保守的激酶结构域(kinase domain, KD),C末端是PLKs特征性结构,即polo-box结构域(polo-box domain, PBD),二者连接区域为铰链区。其中KD为催化区域,PBD则影响PLK1在细胞中的定位及调节。目前研究最多的是ATP竞争性小分子抑制剂,结合于PLK1激酶ATP结构域的结合口袋,与绞链区形成氢键[11]。利用高通量筛选、结构改造等技术方法,有效提高了对靶点的选择性,研发的药物主要包括:二氢蝶啶酮类、噻吩类、4,5-二氢-1H-喹唑啉[4,3-h]并吡唑类、2-氨基芳杂环类、苯并己内酰胺类等,部分药物已经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近年来,靶向PLKs特征性结构PBD的药物研究亦取得重要进展。2.1 靶向PLK1激酶结构域的PLK1抑制剂研发 作用于ATP区域的小分子PLK1抑制剂中,已有部分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或临床研究阶段。BI2536是第一代二氢蝶啶酮衍生物类的ATP竞争性小分子抑制剂,在A549和NCI-H460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有明显肿瘤抑制及良好的耐受性[12]。在一项Ⅰ期临床试验中,确定了BI2536在各种实体瘤中的最大耐受量和总体安全性,毒性主要表现在血液系统[13]。另两项临床试验招募了难治性或转移性NSCLC患者,分别是BI2536联合培美曲塞的Ⅰ期试验[14]和BI2536单药的Ⅱ期临床试验[15]。联合用药试验中,2 例(2/41)患者达到了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为20.1 个月;21 例(21/41)患者显示出有临床意义的病情稳定(stable disease, SD)。在单一疗法的Ⅱ期临床试验中,4.2%(4/95)患者达到PR,PFS为8.3 周。两项临床试验仅少数NSCLC患者达到了PR,大多数不良事件仅一过性影响血液系统。联合用药Ⅰ期试验中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仅为5%(n=2),经审查后PFS为20.1 个月,提示BI2536在NSCLC治疗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引发了寻找PLK1有效生物标记物以优化PLK1抑制剂的给药策略的讨论。
BI6727(Volasertib)作为第二代二氢蝶啶酮类衍生物,是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PLK1抑制剂,具有高分布量、良好组织穿透性和较长半衰期特点,同时具有高选择性(IC50=0.87 nmol/L)及高效性(EC50=1.1~37 nmol/L)[16]。令人更惊喜的是,BI6727可抑制结肠癌紫杉烷类耐药模型的肿瘤生长[16]。BI6727首次Ⅰ期临床试验中包括10 例常规治疗失败的晚期或转移NSCLC患者,评估了BI6727的最大耐受量、安全性、有效性以及PK参数[17]。目前为止,NSCLC患者参与BI6727临床试验共6项,其中5项为Ⅰ期。一项Ⅱ期临床试验评估了BI6727或培美曲塞单药及两者联合用药的疗效对比,研究纳入了131 名复发或难治性NSCLC患者[18]。研究结果显示联合用药组的ORR为21.3%,BI6727用药组的ORR为8.1%及培美曲塞用药组的ORR为10.6%,但联合用药的PFS(3.3 个月)逊于培美曲塞单药(5.3 个月)。研究中发现联合用药并没有改善PFS,对NSCLC患者的总体疗效也低于预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联合治疗中较高的ORR提示着BI6727在部分NSCLC患者中有抗肿瘤活性,只是被更大比例的未获益患者所掩盖,然而目前很少的临床试验去尝试定义有效生物标记物来明确这一部分获益的患者[19]。
Rigosertib(ON-01910)是第一个非ATP竞争性PLK1抑制剂,作用于ATP结合位点以外区域,可以避免激酶抑制剂引起的相关问题(如ATP结合位点突变而导致的获得性耐药)。ON-01910在异种移植模型中,对多种细胞株(包括紫杉醇耐药株)增殖均有抑制作用[20]。目前临床研究基于两个共3 例NSCLC患者参与的Ⅰ期临床试验,均对该药物无反应。最常见的AE包括骨骼、腹部疼痛和癌痛、恶心以及排便冲动,这些副作用与先前的PLK1抑制剂不同,可能与ON-01910的作用机制相关,早期的临床前研究尽管确定PLK1是ON-01910的主要靶点,其作用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2.2 靶向PBD的PLK1抑制剂研究 由于ATP结合域的高度保守性,靶向KD的抑制剂无法避免出现选择性问题及副作用,最近靶向PBD的PLK1抑制剂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通过高通量筛选发现的第一个小分子抑制剂为poloxin[21],是百里醌的合成类似物,能诱导HeLa细胞有丝分裂停滞和凋亡(IC50=4.8 μmol/L),并抑制异种动物模型中肿瘤生长。现已开发或鉴定了几个类似化合物,如Poloxin-2,Purpurogallin,Poloxipan,bg-34,Poloppin和Poloppin-2。此外,绿茶儿茶素被认为属于这一类PLK1抑制剂[22],但Ⅰ期临床试验探索了绿茶提取物在17 例晚期肺癌患者中的最大耐受量,结果表明所有患者均无客观反应[23]。
目前抑制PLK1仍然是需要评估的治疗策略,未来的研究应该探索抑制PLK1的潜在预测生物标记物,帮助确定合适的患者进行治疗并监测PLK1活性,验证其是否具有临床益处。
3 PLK1与肺癌耐药关系
PLK1通过多种途径参与获得性耐药,抑制PLK1可以增强化疗药物敏感性,为PLK1抑制剂与化疗药物联合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3.1 PLK1与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s, EMT) EMT是指上皮细胞转化为间质细胞的过程,通过分析肿瘤样本的基因表达谱与患者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发现EMT相关的特征基因表达与耐药性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24]。信号通路的激活对EMT启动和维持至关重要,PLK1作用于EMT信号通路,在肿瘤细胞中过表达导致耐药性的发生。Ferrarotto等[25]进行了大规模综合分析,发现EMT程度高的NSCLC细胞株对PLK1抑制剂的敏感性高于低者,且强制诱导间质表型提高了细胞的药物敏感性。抑制PLK1有利于逆转耐药,增加化疗敏感性,Fu等[26]从分子机制研究阐明PLK1通过直接或磷酸化C-RAF,触发中下游信号,导致ZEB(EMT转录诱导因子之一)的转录激活。此外,PLK1还通过AKT或FOXM1途径诱导EMT,这些信号途径共同作用于肿瘤细胞,诱导EMT及耐药性的产生。
3.2 PLK1与DNA损伤反应(DNA damage response,DDR) 细胞在DNA因药物作用而受损后,DDR激活细胞周期检查点,使细胞周期停滞,待DNA修复完成后P53失活,细胞恢复有丝分裂。PLK1可负向调节P53[27],覆盖细胞周期检查点并激活CDK1,使受损癌细胞进入周期继续有丝分裂[28-29]。此外,当DNA损伤不可修复时,检查点诱导细胞以依赖P53的方式凋亡[6]。P53表达下调的癌细胞无法诱导凋亡,反而继续增殖。PLK1通过多种途径影响DDR,使药物作用下的癌细胞在DNA受损未完全修复情况下继续增殖,表现为肿瘤细胞对药物敏感性下降,导致耐药性产生。
3.3 PLK1与染色体不稳定性(chromosomal instability,CIN) CIN是癌细胞的标志之一,已被证实能直接促进耐药性发生,机制可能是耐药基因与CIN重叠[30]。为了确保基因组稳定性,有丝分裂中期的纺锤体组装检查点(spindle assembly checkpoint, SAC)监测染色体分离的准确性,其功能异常是CIN的主要原因[31]。癌细胞中PLK1过表达,影响SAC功能,细胞无法保证正常有丝分裂促使CIN发生[32]。PLK1在CIN发生过程的具体机制及CIN诱导耐药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语
PLK1对于NSCLC发生、靶向治疗及其肿瘤耐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多种小分子抑制剂药物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部分患者从抑制PLK1中得到持久获益,但作为单一药物,PLK1抑制剂对NSCLC患者的总体疗效是有限的。在PLK1一个分子内可提供两个独立的药物靶点,将PLK1 PBD抑制剂与ATP竞争抑制剂相结合,有望在抗癌治疗中取得突破。随着PLK1在获得性耐药、与细胞毒性药物以及靶向治疗药物联合协同治疗研究深入,相信PLK1抑制剂在有效防止或延迟原发或转移性肺癌的获得性耐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随着PLK1与其他小分子药物相互作用机制研究深入,PLK1在作为辅助或调节治疗中预计将会发挥重要的临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