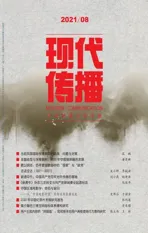《新青年》杂志三次转变与共产党新闻事业起源标志*
2021-11-29倪延年
■ 倪延年
一、《新青年》杂志的三次转变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新青年》①杂志,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起改为《新青年》),到中国共产党“三大”后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青年》季刊,再到1925年4月复刊出版《新青年》月刊(实际为不定期刊),最后于1926年7月15日出版第5期后终刊的近11年间,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转变:
(一)从自由知识分子个人刊物到知识同人刊物的转变
1915年6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东京并辅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面对国内尊孔复古思潮泛滥、各种思潮争鸣、袁世凯筹划“帝制自为”的纷乱环境,陈独秀认为“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青年是最需要改变也最容易改变思想的社会群体,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创刊。
《青年杂志》是一份面向青年读者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由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创办经营的群益书社负责印刷和发行,每月出版一册,6期为一卷,陈独秀主编,每月得编辑和稿费200(银)元。②第1卷第1号开篇署名“陈独秀”的《敬告青年》称“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欲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认为青年应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而不“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的新一代青年。③出版后不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写信给负责印刷和发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要求《青年杂志》更名,因为该会办有《上海青年》④,两个刊物名称雷同,要求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1916年3月群益书社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⑤。《青年杂志》在出满一卷共6号后,休刊半年。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并吸引名流撰稿,充实杂志内容。起初每期印1000本,以后越出越好,到1917年,销数激增,最多时一个月可印15000—16000本。⑥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月刊的社会影响很快扩散到北京,因而受到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关注。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1917年暑假期间,陈独秀离沪赴京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吸收北大文科教授钱玄同、刘半农参加《新青年》月刊编辑工作。⑦《新青年》月刊1917年8月1日出版第3卷第6号后,直到1918年1月才出版第4卷第1号,并由此完成了由原本陈独秀一人主编的“个人刊物”向北京大学一些文科教授轮流主编的“同人刊物”的转变。标志有三:一是此前各号刊物封面上的“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样没有了。二是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刊载《本志编辑部启事》称“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⑧。三是从第4卷第1号起《新青年》实行轮值编辑制。第4卷(共6号)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第五卷(共6号)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第6卷(共6号)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⑨
从第4卷第1号到第6卷第6号的两年间,《新青年》月刊随着编辑人员思想的变化,内容也渐渐发生变化。如陈独秀主编的第4卷第1号开篇是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接着是钱玄同的《论注音字母》,陶履恭的《女子问题》,胡适的《归国杂感》,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诗》,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陈独秀的《科学与基督教》(续3卷6号),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罗家伦的《青年学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通信》及《书报介绍》。李大钊编辑的第6卷第5号首篇是《马克思学说》(顾兆熊),接着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起明译)、《药》(小说,鲁迅)、《诗》(胡适的《一颗星儿》《送任叔永回四川》,陈衡哲的《鸟》《散伍归来的“吉普色”》)、《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胡适)、《马克思研究》(含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源泉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马克思传略》(刘秉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李大钊)、《巴枯宁传略》(克水)、《老子的政治哲学》(高一涵)、《随感录》(唐俟《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张赤《六十》)。⑩第6卷第5号《新青年》月刊虽然仍然维持了原先包括政论、译论、杂论、文学作品(诗歌、小说、杂感)的内容格局,但却明显突出了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发表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重要文章。新设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源泉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等3篇文章,使这一期《新青年》上研究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达到前所未有的6篇。
就在这一阶段,《新青年》月刊轮值主编钱玄同和刘半农为打破鼓吹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冷场”分别以“王敬轩”和“记者”身份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执笔署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和刘半农执笔以“记者”名义发表《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后,《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于1919年10月5日举行会议讨论刊物后续运作事宜。胡适指责钱玄同和刘半农“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编委们对胡适这种霸道作风很不满意。沈尹默直接对胡适说“你不要这么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二周兄弟(树人、作人)对胡适这种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对胡适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才缩手(沈尹默语)。会议决定《新青年》“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但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是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明显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了。
(二)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向社会主义刊物的转变
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刊载陈独秀执笔的《本志宣言》向读者昭告,“我们相信世界上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主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别国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对工农大众的剥削。陈独秀在《本志宣言》中明确表示“现在是应该抛弃(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的时候了”,标志第7卷第1号起的《新青年》月刊完成了从自由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向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刊物的转变。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掩护下秘密离京,后经津抵沪。《新青年》月刊从第7卷第4号起由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专号”,刊载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等文章,附录栏发表了《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及国内大报的舆论。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更明显加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份量,增设了《俄罗斯研究》专栏,集中介绍社会主义俄国有关情况。尤其是陈独秀《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抛弃先前崇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治,宣称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刊物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新青年》月刊愈加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加快了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主体的《新青年》月刊编辑团队的政治分裂。1920年底,陈独秀离沪赴广州任广东省教育长,决定《新青年》月刊由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主要成员陈望道主持,并把这一情况写信告知在北京的胡适、高一涵。胡适复信埋怨《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是已成之事实”,提出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同时“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陈独秀不同意胡适提出的两个办法,甚至“如此生气”。胡适1921年1月22日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高一涵等,转达陈独秀不赞成“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自九卷第一号移到北京来”及“声明不谈政治”的意见,仍主张《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因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汉译本”,还给“素不相识”的、受陈独秀委托编辑《新青年》的陈望道寄去明信片表示反对“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陈独秀坚持《新青年》在上海编辑,并表示“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但我却没有功夫帮助文章”。就这样,《新青年》编辑部仍在上海,仍由陈独秀委托的陈望道负责编辑,仍然沿着社会主义刊物的方向发展。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9月从广州回沪履职并继续主编《新青年》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1922年7月又出一期(9卷6号)又停刊。
(三)从社会主义刊物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在广州开幕(同月20日闭幕)。会议决定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推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展国共合作,同时明确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强调“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中共“三大”还未闭幕的6月15日,由广州平民书社出版发行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在广州出版。“新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由刚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主编;不再使用8卷1号始用的“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封面,改用“一只革命党人握住红旗或红色飘带从监狱窗户伸出的手,红旗(或红色飘带)被风有力地吹飘”的封面,下面方框里三排竖写12个汉字“革命党人狱中庆祝革命之声”。“新青年”三个字竖排在封面图案的右上侧。封面图案下是“中华民国邮务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再下面是“《新青年》(1923年复刊)第一期”。第一页的上半页所载《本志启事》,下半页刊登“《前锋》创刊号出版了”的广告。
目录页右首行为“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第二行为“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第三行为“共产国际号”。第四行用小号字解题“共产主义派的革命运动是现代最新进最革命的一派无产阶级思想之代表。此派的政治的组织应是各国共产党。他们联合而成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存在已经四年。新青年此次重加整顿,特为出一特号,以资研究”。接着是“目次”。这期所载内容为:未署名的《〈新青年〉之新宣言》(瞿秋白执笔)、未署名的《国际歌》(瞿秋白译),接着是瞿秋白的《赤潮曲》、瞿秋白的《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瞿秋白的《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屈维它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鸿(译)《东方问题之题要》(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之决议案)、洛若夫斯基的《共产主义之于劳动运动》、陈独秀(译)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大会之决议案)、亦农(译)的《世界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溪浈女士(译)的《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瞿秋白的《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历史》、永钊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统观》。这一期《新青年》(季刊)设有“评坛”栏,刊载了瞿秋白的《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最后是《歌谱二阕》。从《新青年》季刊所载内容、政治倾向性和文章作者、译者构成认识,“复刊”后的《新青年》季刊已完全没有《新青年》月刊的“统一战线”色彩,而是纯粹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因此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明确《新青年》(季刊)——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C·P·)。
《新青年》季刊自1923年6月15日出版第1期后,先后于1923年12月20日、1924年8月1日、1924年12月20日出版了第2、3、4期。在1924年12月20日出版的第4期上刊出《本志启事》称“从一九二五年一月起,将本志重新恢复为月刊。并拟定于世界革命领袖列宁去世之周年纪念日,刊行列宁专号,作为本志新月刊之第一号”。1925年4月22日出版恢复月刊后的《新青年》第一号“列宁号”。但恢复为“月刊”的《新青年》第二号延后至1925年6月1日才出版(延后了9天);第三号更是延后了9个月24天直到1926年3月25日才出版。第四号在1926年5月25日出版,第五号(世界革命号)于1926年7月25日出版(实际成为双月刊),实际终刊。
回顾《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终刊经历的三次转变,正如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所说“在中国旧社会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五四运动以来,《新青年》成为中国真革命之先趋”;在中共“三大”后“复刊”的《新青年》(季刊及不定期刊)则“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起源的探讨
笔者查阅了新闻史学界具有较大影响的诸种中国新闻史著作或教材,没有发现一种著作说到“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起源”这一问题。
(一)现有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起源”相关的表述
经过梳理现有新闻史著作或教材中关于《新青年》月刊在1919年12月至1920年9月间的变化,大致有如下诸种表述:
(1)1920年7、8月间,中共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并决定《新青年》从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改组成中共上海发起组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第8卷第1号发表陈独秀的政论《谈政治》一文,实际上是《新青年》改组为无产阶级刊物后的第一篇政治宣言。陈独秀抛弃先前崇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治,宣称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2)1919年12月,陈独秀在第7卷第1号上发表《本志宣言》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阀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宣布抛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则表明《新青年》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7月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新青年》由这年9月出版的第8卷第1号起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3)1920年初,复刊后的《新青年》七卷一号发表的《本志宣言》,宣布放弃自由主义的办刊方针,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5月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实践相结合的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就确定《新青年》为小组的机关刊物。
(4)“《新青年》从1920年9月出版的8卷1号起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筹建组织用以进行理论宣传的机关。这一期上发表的陈独秀的《论政治》一文,理论认识虽然还颇有模糊之处,却一方面批判了以胡适和张东荪为代表的右派以及国外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另一方面批评了以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左’派,明确地宣告了一种新的、以‘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目标的新的政治的开始。”
(5)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
(6)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本志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宣布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裂,这应视为《新青年》转变的开始。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1920年9月,《新青年》从8卷1号起,实际上已成为党的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完成其性质的根本性转变。
(7)《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改组成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刊物。第8卷第1号还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俄罗斯研究”专栏的开辟和《谈政治》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新青年》的改组基本完成,而《新青年》改组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8)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出版,从此该刊实际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刊发陈独秀《谈政治》一文,是改组后的第一篇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政治宣言。
(9)自1920年9月的8卷1号起,《新青年》成为了上海共产党人的机关刊物。
(二)关于《新青年》月刊性质变化的思考
上述论著中对《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1号的“性质定位”主要有中共上海发起组(或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人)的“机关刊物”“进行理论宣传的机关”和“公开理论刊物”三种;如何获得这一性质则有“改组成”“变成了”“确定为”“改为”“实际上已成为”和“实际改组成为”等不同说法。在核查《新青年》月刊原始文献后,发现与《新青年》月刊的实际情况不尽相符。
1.认定《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1号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的依据似乎不足
《辞海》解释“机关报”是“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等出版的报纸”。同理,“机关刊物”就是“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出版的刊物”。假如第8卷第1号《新青年》月刊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刊名与原《新青年》月刊同名、同为月刊及仍由陈独秀主编等都可解释。但:
一是“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的《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1号,标示刊物出版时间和次序的卷期编号没有从“第1卷第1号”开始,而是延续了《新青年》月刊的“第8卷第1号”。“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和“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同人刊物”应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独立刊物。假如《新青年》月刊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应是此前同人刊物的《新青年》月刊停刊,新创办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月刊。新创办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月刊理应从第1卷第1号另起编号,而不应是延续1915年9月15日创刊的《新青年》月刊的卷期序号。而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在广州出版时则不但改了出版周期(从月刊改为季刊),尤其是另起卷期号(第1号为“共产国际号”),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第8卷第1号的延续原来卷期号实质是对第7卷第1号办刊宗旨的有意识延续。
二是《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1号与原先《新青年》月刊内容格局没有根本的区别。假如《新青年》月刊已经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刊物的宗旨应是信仰和宣传共产主义,进而在内容格局上理应与前7卷的内容有根本区别。但陈独秀主编的第4卷第1号开篇是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接着是钱玄同的《论注音字母》,陶履恭的《女子问题》,胡适的《归国杂感》,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诗》,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陈独秀的《科学与基督教》(续3卷6号),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罗家伦的《青年学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通信》及《书报介绍》。同为陈独秀主编的第8卷第1号篇目为:陈独秀的《谈政治》,蔡元培的《社会主义史序》,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陶履恭的《新历史》,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康白情、双明的《诗》,沈性仁(译)的《新闻记者》,鲁迅的《风波》(小说),陈衡哲的《小雨点》(小说),汉俊(译)《女子将来的地位》,张慰慈、汉俊(译)的《俄罗斯究研》(三篇),马伯援、刘云生和文华大学学生的《社会调查》(三篇),记者的《香港罢工风潮始末记》,陈独秀的《随感录》(五篇),孙伏园(记)的《杜威演讲录》及《通信》(一—八)。可以看出《新青年》第8卷第1号的主要作者、文章内容、文章体裁及编排次序等与《新青年》第4卷第1号没有本质的区别。
三是第8卷第1号《新青年》月刊上没有标明刊物编辑出版者“中共上海发起组”。既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理应标明创办者“中共上海发起组”,但第8卷第1号《新青年》月刊上没有任何标示。自这一期刊物开始用新的封面(且第二期是罗素像),似乎不应成为关键论据。至于从这一期《新青年》月刊起由“新青年杂志社印行”,则是《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即上海群益书社)所订“合同”规定“以上各条以第七卷为试行期,第八卷以后,应否修改,由编辑部与发行部商酌定文”。后“因为《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广告的事,一日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于共事”“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办一书局)”的结果,并不是为了“改组”《新青年》月刊有意成立“上海新青年社”,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四是《新青年》第8卷第1号以后各号刊物上仍然刊载胡适、周作人等不赞成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或文学作品且一直延续到《新青年》月刊停刊。第8卷第1号上有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第2号上有周作人(译)的《玛加尔的梦》及翻译的6篇罗素的文章,第3号上有周作人(译)的《杂诗二十三首》、(译剧)《被幸福忘却的人们》和5篇著或译罗素的文章,第4号上有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译作《深夜的喇叭》和诗作,第5号上有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和译作《少年的悲哀》,第6号上有周作人(译)的《小说三篇》;第9卷第2号上有胡适的诗《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和《死者》,第3号上有胡适的《国语文法的研究法》,第4号上有周作人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第5号上有周作人的《病中的诗》和《山居杂诗》及《癫狗病》,第6号上有胡适的诗《平民学校校歌》和《希望》。
综上所述,关于1920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新青年》月刊自1920年9月1日的第8卷第1号“改组成”(或“变成了”“确定为”“改为”“实际上已成为”和“实际改组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的结论是有商榷余地的。《新青年》月刊从第8卷第1号开始,对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理论、劳动阶级利益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介绍的内容份量比例不断加强,“特别是《新青年》后期几乎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也有人认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实上的机关刊物”),但毕竟没有达到规范意义上的“机关报刊”的水平。1920年9月1日出版第8卷第1号后的《新青年》月刊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负责人陈独秀主持下,一方面保持原来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面貌,原有编者作者的来稿照旧采用(李大钊负责组织北京方面的稿件);另一方面扩充作者队伍,增添新生力量,吸收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李达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在内容上逐渐加重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比重。这样,以便于争取原有作者读者逐步跟上来,同时也避免打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招来反动势力的注目。从第8卷第1号到第9卷第6号《新青年》月刊内容重点、作者队伍和政治倾向多方面认识,尽管它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倾向性越加明显,但在本质上仍然只是由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编辑并主要是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鼓动进行社会革命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刊物”,而没有成为规范意义上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正式“机关刊物”。
2.《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1号应可认定是共产党报刊起源的标志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列·米·加拉罕1919年7月25日代表苏俄政府发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俗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产生很大的影响。正是这种社会环境及北京编辑团队的政治分化,《新青年》月刊自第7卷第1号开始完成了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向主张并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学说刊物的转折,这一办刊宗旨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定是中国共产党报刊起源的标志。
(1)《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1号《本志宣言》昭告了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的政治立场。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在《新青年》月刊创刊号上公开表示“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在“通信”栏答“读者王庸工”信中以“记者”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这一办刊宗旨在第4卷第6号前基本是得到贯彻的。陈独秀在第7卷第1号的《本志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清楚表明陈独秀单独主编的《新青年》月刊已抛弃创刊号《社说》及“通信”中“批评时政非其旨”的自由主义办刊宗旨,决意走新的道路——成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社会主义刊物”。
(2)《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1号经过了量变到质变并延续发展的转折过程。作为前奏,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同时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向世界宣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几乎成了“马克思及其学说研究”的专题号。除了篇数不多所占篇幅也不多的鲁迅小说《药》、胡适和陈衡哲诗作《一颗星儿》《送任叔永回四川》《鸟》《散伍归来的“吉普色”》及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克水《巴枯宁传略》和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学》外,重头文章都是研究“马克思及其学说”。如顾兆熊《马克思学说》,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尤其是专设的“马克思研究”专栏集中刊发了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源泉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三篇文章,使这一期《新青年》月刊的政治色彩尤为鲜明。第6卷第6号继续刊载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后,《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1号《本志宣言》宣布“抛弃”已造成无数罪恶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也就抛弃了“批评时政非其旨”的自由主义办刊宗旨。所以继续刊载宣传社会主义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6号成为“劳动节纪念专号”以及第8卷第1号发表陈独秀《谈政治》等文章。
(3)《新青年》月刊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停刊的11年间,先后刊载过三篇具有“宣言”性质的文字。第一篇是《新青年》月刊创刊号所载《敬告青年》,主旨是以“科学、民主”思想启蒙青年,宣告“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第二篇是1917年12月《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1号所载《本志宣言》,主旨是抛弃“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第三篇是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刊载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要“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而被后人认定开始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却没有刊载任何标志办刊宗旨改变的“宣言”,这只能说明该号及此后的《新青年》月刊继续延续着第7卷第1号宣布的办刊宗旨。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所以第7卷第1号上刊载《本志宣言》就明确标志着《新青年》月刊完成了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刊物的转折,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报刊起源的标志。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中,新闻事业是以新闻报刊为主体的社会新闻事业,所以中国共产党报刊的起源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起源。
(4)自1919年12月第7卷第1号至1922年7月1日出版的第9卷第6号的《新青年》月刊,在“抛弃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的宣传社会主义刊物的办刊宗旨指导下,继续抨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无穷罪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赞扬苏联十月革命,介绍世界各国的新学说、新思潮,重视并反映社会基层平民的疾苦——立足社会主义立场和宣传社会主义,这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即使是第7卷第1号上宣告“抛弃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的《本志宣言》也仅是“宣传”众多西方社会理论中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提出组织民众、推翻旧政府,建立劳动阶级掌权的“新国家”的明确奋斗目标。《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1号《本志宣言》宣告了“抛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具体的路径却仅是“打破‘天经地义’‘自故如斯’的成见”“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需要为中心”“尊重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并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及“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这仍然没有超出当时知识界通行的纯理论表述,仍是当时社会学术界鼓吹某一思想或思潮的常见路径,勾勒的仍然是自由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桃花源”,宣传的社会主义学说仍带有人道主义、空想主义的色彩。即使是在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后,该刊一方面加大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比重,另一方面仍然继续保持着“同人刊物”(“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面貌,标志是继续刊载不赞成社会主义学说的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如胡适等人的文章。
(三)共产党报刊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后发展的几个标志
共产党报刊起源之后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里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一是共产党报刊萌芽的出现。1920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为了推动和促进共产党全国组织的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办了半公开的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这是第一种以“共产党”为旗帜的报刊。它的创刊标志中国共产党报刊的萌芽正式出现——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宣告成立,所以还不能说是共产党报刊的正式诞生。
二是共产党报刊正式诞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1922年9月13日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既是中共中央第一个“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份“真正打出政治机关报旗号”的中央机关报,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报刊正式诞生的标志。由于这一阶段新闻媒介的主体是报刊,所以中国共产党报刊的诞生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诞生。
三是共产党报刊初成体系。1923年在共产党报刊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1922年9月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后,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共中央“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报《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报《前锋》(月刊)又在广州创刊,两种机关报都由瞿秋白同志主编。11月23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编、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编辑的党内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党报》(不定期刊)在上海创刊。这一系列不同功能党报的创办,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体系初成,也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体系初成。
注释:
① 本文论及的《新青年》杂志包括在上海、北京、上海及广州等地先后出版的《新青年》月刊、季刊及不定期刊等部分。时间跨度为1915年9月15日至1926年7月15日。
③ 陈独秀:《敬告青年》,上海《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④ 陈独秀《青年杂志》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青年》并不同名。《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记载当时松江(今属上海)已有(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善导报社”1915年(乙卯年)1月创刊的《青年杂志》,也是月刊(该目录第631页)。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应是和这种《青年杂志》而不是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青年》“名称雷同”改名。
⑦ 张朋:《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66页。
⑧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月刊),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⑨ 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⑩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目次》,《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