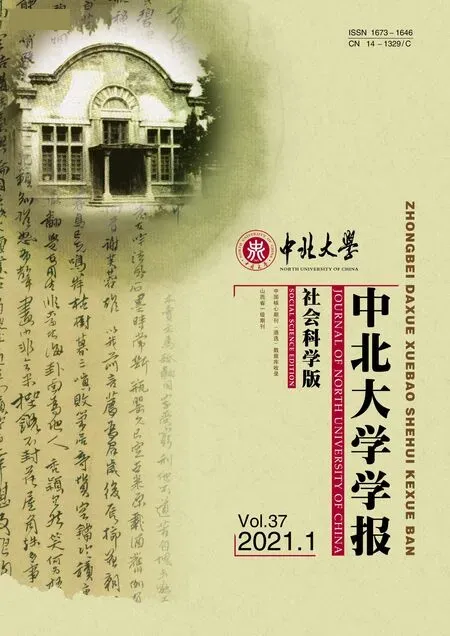从《四川好人》与《圣经》的互文浅析布莱希特的反宗教理念
2021-11-29李慕晗张世胜
李慕晗, 张世胜
(西安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0 引 言
作为布莱希特的代表作之一, 《四川好人》在国内的研究虽已深入, 但大多集中在陌生化理论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方面。 事实上, 通过与《圣经》互文, 布莱希特在剧中对18世纪的宗教进行间离, 把当时的宗教加以陌生化, 揭示出其全部怪异之处, 体现的正是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反宗教理念。
布莱希特对《圣经》自幼就非常熟悉。 布莱希特的父亲是天主教徒, 母亲则是新教徒, 在布莱希特受洗时, 父母就决定让他学习新教教义。 除了在家耳濡目染, 布莱希特在幼儿园、 教会学校以及中学期间也一直选修神学课程。 这为他日后很多作品都包含圣经元素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 布莱希特并非将《圣经》看做上帝的指示。 他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到了道德标准与真实行为之间的矛盾。 “他在作品中通过《圣经》中的引文和典故, 以全新的方式寻求对基督教的批判性考察。”[1]18对于布莱希特来说, 宗教不是基于信仰和人类榜样, 而是基于政治和权力主张, 这与其他商业政策、 强权政治或国家政策的选择没有任何不同。
随着第一部抨击资产道德虚伪的短剧《巴尔》发表, 布莱希特在2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这让他从根本上质疑基督教的根源。 他认为宗教就像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批评一样:“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是人民的鸦片。”[2]2他将希望寄托在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 他之后陆续发表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带有左派倾向。 《四川好人》创作于1941年, 在纳粹迫害下过着流亡生活的布莱希特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反动, 并逐渐形成只有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并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理念。 在《四川好人》中, 布莱希特所描绘的正是一个民不聊生、 自私自利的世界, 文中的三位神仙不仅没有消除社会矛盾, 反而更加证明了道德和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
1 民众对神仙下凡的期待
《四川好人》虽然故事地点设在四川, 但布莱希特将其描述为“一个半欧化的城市……它适用于所有存在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地方”[3]2。 联系时代背景, 剧中的四川实际上和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本质区别。 布莱希特用陌生化理论在开篇就提醒观众要带着审视批判的眼光思考之后的情节, 这样的手法也为本剧的主题埋下了伏笔。
卖水人老王的自白描述了一个颠连穷困、 民不聊生的社会。 “缺水的时候耗费苦力, 水多的时候挣不到钱”[3]3直接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生活质量没有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将生活希望寄托于神仙下凡, 期待他们了解民间疾苦, 解救众生。 老王担心人们争先恐后恭候神仙光临, 想第一个表示欢迎。 老王代表的是普通的雇佣劳动者, 达官贵人则是资本家。 资本家没有生活压力, 却仍然在迎接神仙时和劳动者产生竞争关系, 对利益最大化的掠夺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分配不均, 贫富差距过大。
老王对神仙虔诚的迎接与《圣经·创世纪》里先知亚伯拉罕迎接上帝可谓如出一辙。 卖水人老王毕恭毕敬地在城门口等待, 恭候神仙的光临。 “他跪倒在地上。”[3]4而在《圣经·创世纪》第18章中, 上帝耶和华在亚伯拉罕面前显现, 亚伯拉罕便去迎接耶和华和两位天使, 俯伏在地请求服侍三人:“容我拿点水来, 你们洗洗脚, 在树下歇息歇息。”[4]23老王卖水人的身份, 也和亚伯拉罕拿水毫无二致。
就目的而言, 序幕里与圣经的互文表现了人们对神仙救世的深信不疑, 正如《圣经·创世纪》里亚伯拉罕对上帝深具信心。 理想中的神仙角色可总结为两点: 一方面, 神仙是全知全能的, 了解人间怨声载道, 心里十分不安, 因此, 下凡解救众生。 老王认为达官贵人会将神仙包围, 印证了对救世主下凡的期待。 另一方面, 神仙是正义的裁判, 惩恶扬善, “只有神仙才能明察真情”[3]167。 老王帮神仙找住处时, 程先生害怕地不敢让神仙进门, “里面准有坏人……他害怕瞒不过你们的眼睛”[3]6。 当老王说到科文省发洪水时, 也简单地将其归咎为那里的人不敬神。
前文神仙与上帝的类比铺垫制造了更大的反差效果。 神仙的行为很快就磨灭了人们的期望。 神仙要求老王为其寻找住处, 却三次被拒绝。 神仙看到了人的自私自利, 道德败坏, 却无能为力, 自承“使命已经失败”[3]7。 理想中的神仙形象和实际角色相去甚远。 就下凡目的而言, 上帝下凡是为了拯救世人, 惩奸除恶; 神仙下凡是为了找一个好人证明他们存在的合理性。 而从实践方法来看, 上帝是直接执行者, 神仙是由代理人代为行善。
这里的反差效果是布莱希特间离化处理的结果。 《四川好人》开篇与《圣经》的互文制造了一种审美幻觉: 神仙与上帝形象近乎重合。 但随后神仙提出借宿的要求以及他们说出下凡的目的, 却又和《圣经》中的情节发展相去甚远。 上帝听闻了所多玛和蛾摩拉城的罪恶, 因此, 派两名天使下去查看印证, 两名天使下凡遇到罗得。 罗得邀请天使进屋过夜, 天使却坚持在街上过夜。 天使见到了所多玛城的罪恶, 便要毁灭这地方, 但是上帝怜恤罗得, 便将其与家人安置城外免于灾祸。 相比之下, 三位神仙不仅因借宿的事要求凡人帮助, 而且看到了社会的败德辱行却无能为力并产生自我怀疑。 这就打破了人们的惯常思维, 将熟悉的内容陌生化, 引起观众的惊愕与思考: 为什么神仙在更贴近现实的剧中社会里变得碌碌无为, 不辨是非?观众从而认识到宗教在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毫无意义的。
2 好人在社会处处碰壁
在金钱主宰一切的世界里, 布莱希特通过宗教间离的剧情, 展露了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法则”。 剧中的神仙通过寻找代理人的方式执行他们的任务, 极力想证明在这个礼乐崩坏的社会仍有品德高尚的好人存在。 作为神仙的代理人, 沈黛的妓女身份也是布莱希特陌生化处理的表现, 妓女在观众的认知里本应是伤风败俗的代表, 剧中却是唯一一个向神仙提供住宿的好人。 妓女在剧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妇女的一员, 是剥削制度下受压迫的劳苦大众。 身份与行为的不符让观众能够运用理智思考沈黛所代表的受压迫阶级, 从而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神仙对沈黛提出的戒律要求和《圣经》里对大众的要求大同小异。 沈黛的标准是“守住德行, 孝顺父母, 诚实做人, 不伤天害理, 损人利己, 落井下石”[3]15。 《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中要求的是:“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奸淫、 偷盗、 作假见证陷害人、 贪恋他人财物”[4]118。
尽管戒律内涵相同, 沈黛执行时却处处碰壁, 究其原因, 神仙的戒律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成员及阶层需按照资本主义制度所要求的方式行事。 剥削制度以不可见的方式不知不觉地引导着社会成员的行为, 即经济竞争、 追逐利润、 剥削利用。 在商业和生产主导的社会, 人逐渐丧失了他的中心地位。 市场的产生使无限度地追求利润成为社会法则; 剥削工人不再被看作是有违道德的行为; 经济竞争毫无节制、 残酷无情。 正如布莱希特研究专家克劳斯穆勒所说:“神仙为了证明世界存在的合理性, 通过戒律和要求其得到执行的权力赋予了这个世界一个仍充满人道精神的假象。”[5]287
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在本剧中的集中表现可总结为两点。 其一, 人受限于市场及经济机器所代表的无形法则, 失去了自由决定的权利。 卖水人老王“在缺水的时候, 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 水多的时候, 挣不到钱”[3]3。 当水供不应求时, 耗费的是人的劳力; 当水供大于求时, 减少的是人的利润。 市场推动人们向前, 弱肉强食的法则使竞争变得残酷无情, 道德感降低。 老王唱的“雨中卖水人之歌”讲述了他做的一个梦: 七年不下雨, 人们趋之若鹜, 只为买到老王的水。 老王垄断市场, 论滴称水, 抬高水价, 看着众人向他哀求饮水。 “七年” “做梦”这些要素同时也在《圣经·创世纪》第41章中出现。 法老梦到七只肥壮的母牛在河边吃草, 之后又出现了七只干瘦丑陋的母牛, 并吃掉了那七只肥壮的母牛。 法老命约瑟解梦, 约瑟解释说, 肥壮的母牛对应丰年, 而干瘦的母牛象征荒年,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 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 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 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4]67。 为了避免荒年的危机, 约瑟将丰年的粮食提前积存, 等到荒年时再开仓放粮, 救济众人。 由此可见, 《圣经》里这一切实现的前提是经济上人为调节供需平衡, 道德上对他人心怀怜悯, 爱人如己。 在人受市场支配、 彼此缺乏同情的资本主义社会, 约瑟对埃及人这样的救赎是不会实现的。
其二, 资本主义是个人利益至上。 剧中描写的也是一个剥削制度下拜金的“四川”[6], 个人寻求新机会, 获取财产, 享受财富。 社会法则让人的性格也产生变化: 吝啬、 贪婪、 懒惰、 占有欲强烈。 剧中的杨森为了谋取飞行员职位, 以爱情为由欺骗沈黛, 与沈黛结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骗得500银元。 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体现得淋漓尽致。 《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中要求妻子服从丈夫, 如同服从主, 丈夫也要如爱自己身体一般爱自己的妻子。[4]337在财富方面, 《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中规定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 他不是厌恶这个、 喜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 轻视那个。 不能既服事神, 又服事财富。[4]10爱伴侣如身体意味着爱人如己, 服事神则代表虔诚而追求道义。 这和个人利益优先、 消费享受财富的社会原则截然相反, 《圣经》里倡导的道德观自然难以形成。
这样的现状让好人沈黛难以既遵守道德又维持生计, 只有假扮表哥隋达, 摒弃道德, 残酷剥削, 才能挽救生意。 沈黛最初假扮隋达是出于无奈, 但随着假扮次数增多, 隋达解决了穷人寄生店内不肯罢休、 杨森好吃懒做且骗取钱财等问题。 作为贪婪自私的剥削者, 隋达的行为违背了神的戒律, 却符合这个社会的法则。 “布莱希特将善与恶、 真与假、 美与丑共存的‘非典型性’人物形象赋予主人公沈黛, 沈黛的双重人物形象代表了在社会环境的剥削下人的两面性, 反映了布莱希特对现实生存世界的无可奈何。”[7]这部譬喻剧最终揭示了一个现实: 神灵所要求的爱人如己在一个以剥削和自我异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难以实现的。[1]323
3 神明救世的幻想破灭
沈黛与隋达的交替出现, 代表着沈黛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与杨森的婚姻、 孩子的即将出世、 剥削工人维持烟店等种种矛盾交织产生, 最终将剧情推向全剧的高潮——法庭审判。 神仙在法庭审判环节似乎满足了人们的期待, 担任了正义裁判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 神仙自从首次下凡, 后面几次出现都是在老王的梦里, 这也暗示了神仙既逃避社会现实, 也无力干预社会运行。
对比前文提到的神仙的理想角色, 剧中的三位神仙既非全知全能, 更做不到惩恶扬善。 《圣经·阿摩司书》第8章里上帝看到了以色列的恶, 便要使审判之日降临。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使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 干渴非因无水, 而是因为听不到耶和华的话。”[3]1479相比之下, 当老王向神仙报告社会的罪恶时, 神仙却不以为然, 不辨是非:“我们能承认我们的戒律不适用吗?我们应当抛弃我们的戒律吗?(顽固地)永远不能!这个世界应当改变吗?怎样改变?谁来改变?不, 它一切都很正常。”[3]179
审判时神仙关心的只是能否找到证明他们存在意义的好人沈黛。 当沈黛无力地控诉道德使命与剥削制度的双重压迫时, 神仙自欺欺人地相信沈黛“只要你好, 一切都会变好的”[3]180。 当好人与恶人的冲突到达顶点时, 神仙“脚踏祥云飘然升去”[3]180。 按照传统古希腊戏剧的情节发展, 当困境难以解决时, 会有神仙降临解决难题。 本剧则完全相反, 神仙在紧要关头逃离凡间, 返回了“虚无缥缈”中。 最后的收场白给这部剧留下了一个开放结局, 布莱希特启发观众自己去寻找一个理想结局:“我们未能找到解决办法, 金钱也枉然。 应该是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也许应当是别的神仙?抑或一个神仙也不要?我们已无能为力, 这不是装模作样。”[3]182-183
4 结 语
戏剧必须投身于现实中去, 才有可能和有权利创造出效果卓著的现实的画面。[8]14从20世纪德国工人运动开始, 教育剧这种以宣传教育为目的的戏剧形式逐渐流行, 布莱希特正是教育剧的倡导者。 教育剧的表现客体多种多样, 本剧就出现了家庭、 通货膨胀、 宗教三个主题。 杨森娶沈黛只是为了500银币、 老王趁干旱高价卖水、 神仙也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这些略显夸张的事件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 传递给观众知识, 促使观众做出选择。 和传统的戏剧相比, 布莱希特将宗教进行陌生化处理, “把陌生化手法与戏剧改造世界的斗争直接联系起来”[9], 观众能更好地参与其中并产生共鸣。 基督教主张人对命运不可控制, 人需要上帝。 《四川好人》则证明了人的命运在自己手中。 从这个角度看, 这部寓言剧也可被理解为一场革命实践的理论依据, “是成千上万作为观众的沉默的人民汲取批判思维和反抗力量的来源”[10]。 它启发人们改变现实, 使人民和谐成为可能。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 任何意识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布莱希特根据现实描绘了一部资本主义的社会图景, 观众受此影响, 也会参与改造世界的活动。 雅恩克诺普夫在《布莱希特手册》中写道:“只有观众自己才能创造一个美好结局, 也就是投身实践, 变革社会。”[11]428布莱希特没有直接表达对《圣经》的批评, 但他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体现在戏剧所描绘的现实中,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戏剧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