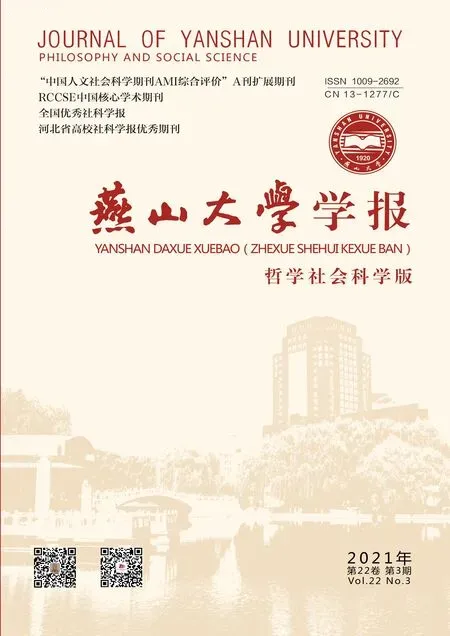类型经验与范式差异:新世纪韩国犯罪片对香港电影印记的沿袭与改造
2021-11-29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350117)
一、 引言
“19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电影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自由贸易时代的大势所趋下,政府于1984年对电影法进行了第五次修订”[1],由此,韩国电影市场走向完全自由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恰逢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警察故事》(1985)、《英雄本色》(1986)、《龙虎风云》(1987)、《卡门旺角》(1988)、《喋血双雄》(1989)等代表着亚洲电影产业最高水平的影片涌入韩国电影市场。冥冥之中,已经为二者在日后的“重逢”埋下历史的因缘。
波德维尔认为:“类型身上纵有文化对话的痕迹,但他们彼此之间,其实亦存在对话,一种‘文本呼唤’”[2]160,这种“呼唤”在韩国电影与香港电影的交互中尤为强烈,以至于形成一种藕断丝连的关系。杜琪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改良”的写实性暴力美学,会在黄海边的一个半岛上重新上演,并且更加逼真、血腥。除此之外,二者都在各自产量、质量并举的黄金时期,表达了相同的困惑与迷惘——现代化发展、全球化资本运作中社会的异化及文化身份的焦虑。 香港的文化底蕴“处于一种难以自我化解的矛盾之中:既求助于中华文化传统,又轻视和嘲弄这个传统,这是一种殖民文化的矛盾心态”[3]。相较之下,韩国社会的“矛盾心态”更为突出,东西文化盘根错节地聚拢于一体:“韩国以美国为模式发展近现代化,一直在追随近代精神的一面,即科学主义、合理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但实际上支配韩国社会的不仅是这些,在朝鲜后期定位的儒教习惯,就像拧麻花一样将社会缠绕成一种特别的扭曲形态。”[4]
二、 类型经验差异:人治反思与法制反思
香港警匪片的文化变奏大致经历“人治”到“法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创作倾向,区分为两种,一种是邵氏国语片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另一种是粤语片所象征的岭南文化,它们无一例外地同时传递了一种区域性的朴素道德观念,用以维系社会系统的运作,有学者总结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5]。
这种朴素的公民意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学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并成为其衍生与扩展。因此,“人治”观念以人际关系作为纽带,贯穿五十、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并在八十年代演化为香港警匪片或黑帮片中频繁强调的“情义”。但在“九七”前后,大量B级片以及“银河映像”出品的一系列黑帮片、警匪片,完全颠覆香港电影黄金时期所奠定的“人治”江湖,情义老大、江湖信义、浪漫的英雄主义随着“九七”的到来被一一消解,尤其在CEPA签订后,《伤城》(2006)、《黑社会》(2005)、《放·逐》(2006)、《机动部队》(2003)等电影,放弃对“人治社会”的盲目崇拜,转而思考“人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朝鲜战争后,韩国立马投入美国资本的怀抱,用不到40年的时间成就“汉江奇迹”的称谓。但经济的快速提升需要付出代价,韩国的代价是民主失衡,从朴正熙的威权政府到全斗焕的军人政府,呼喊民主的声音愈发振耳,权力领袖的威信跌入谷底,“亚洲四小龙”“汉江奇迹”缔造者手里握着血红色的资本。因此,新世纪韩国犯罪片略过“人治”反思,其早已被验之无效,社会并不怀有对“人治”的期待。但随着政府的持续不作为,以及李明博、朴槿惠等领导人频出的丑闻,韩国社会方才意识到并不是“人治”出现问题,权力的滥用与腐败是必然,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制度的制衡原则,发挥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措施规制权力与人性。韩国犯罪片这才发现一条独具特色的表达出口——“法制”反思,如《杀人回忆》(2003)、《奥罗拉公主》(2005)、《那家伙的声音》(2007)、《七天》(2007)、《追击者》(2008)、《看见恶魔》(2010)、《黄海》(2010)、《孩子们》(2011)、《局内人》(2015)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批判权力结构、法律体系与政治体制,维系社会的纽带不是兄弟间惺惺相惜的男性情谊或带有温情色彩的“道义”,而是冷冰冰的界定权利与义务的制度。
“人治”思想在吴宇森、林岭东手里具化为“情义”,并成为香港电影的金字招牌。在《英雄本色》所衍生的大量英雄片中,情义是电影所赞美的,警与警之间不再是同事、上下级的关系,而是相互珍惜的兄弟情谊,匪与匪之间出生入死的过命交情取代尔虞我诈,甚至警匪间身份、意识形态等不可逾越的鸿沟亦被惺惺相惜的兄弟情义所填平,像《喋血双雄》中杀手小庄(周润发饰)和警探李鹰(李修贤饰)间本应剑拔弩张的对立,也被相同境遇的生死之交所消解。80年代香港黑帮片、警匪片对男性情谊的高度赞扬模糊法治、道德的界限,人与人之间感性的情义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不二方式。
无独有偶,90年代以匪为主角的黑帮片也一再重申香港社会的“人治”特点。但“随着九七将近,港人的身份归属出现某种失重、迷茫,个体生存的集体焦虑感和危机感在对周遭一切的不信任感支配下,香港人更加相信个人奋斗的力量”[6],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斗狠比勇的黑帮片,如《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98古惑仔之龙争虎斗》(1998)、《0记三合会档案》(1999)等。在这些黑帮片中,勇敢、理智、富有正义感的执法人员是缺失的,其象征的法制精神是不存在的,解决纷争的机制,则依据黑帮间相互承认的“灰色秩序”——道义,它来自儒家传统“人治”的古风,依旧是家长制的层级结构,严格的辈分排位,就像波德维尔所说:“影片其实尊重传统家庭长幼有序的观念,因为黑帮青少年没有挑战父权代表人物的权威,他们不单不是青少年犯罪,更成为听话的儿子。”[2]34
黄金时期的香港电影,在亚洲范围内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毋庸置疑。韩国学者Jinhee Choi认为:“20世纪90年代,香港动作片的流行重新唤醒了韩国黑帮电影,香港动作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上映。二三十岁的观众更熟悉香港黑帮传奇,而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黑帮电影。吴宇森、王晶和林岭东导演的黑帮电影迅速占领了韩国市场。香港动作电影的成功导致了韩国进口电影数量的急剧增长:1987年不到20部,但在两年内就有了近90部,直到1993年总进口量一直保持在70部以上。香港动作片/警匪片的繁荣也与韩国电影业的发行变化同步。”[7]61因此,当我们仔细翻阅新世纪前为数不多的韩国警匪片、黑帮片,如《两个刑警》(1993)、《心跳》(1997)、《日出城市》(1999)等影片时,无一例外都是对“情义”的讴歌与赞扬。
可以说,香港犯罪题材电影促成韩国犯罪片的繁荣,至今,依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香港犯罪电影的类型成规(繁华城市夜景、狭窄街道、写实的暴力美学),被韩国犯罪片保存、发扬。但颇为吊诡的是,90年代零星的韩国犯罪电影,还在“生搬硬套”香港电影的类型传统,在新世纪初,就涌现出大批如《我要复仇》(2002)、《杀人回忆》、《老男孩》(2003)等将历史与现实融入类型经验的优秀犯罪片,将反思政治、权力作为麾旗,书写民族经验与当代韩国困境。不禁令人思考,是什么原因促成“零零星星”到“喷涌而出”的发生,以及从“仿造”他山之石到琢自身之玉的转变。
“当代韩国电影的有趣之处在于,20世纪80年代共同的政治历史如何成为吸引观众的商业诱饵。”[7]9事实上,这一论断“不准确”地揭示了韩国犯罪片的商业秘密,因为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共同的政治历史”吸引观众,而是那一时期的“政治历史”作为韩民族警惕权力、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吸引人。具体来说,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造成韩国大型企业破产,银行持有的可支配外汇储蓄不足80亿美元,韩国经济处于奔溃的边缘,于是韩国政府申请国家经济破产,并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550亿美元。韩国人从“汉江奇迹”的经济快速增长中猛然醒来,发现过去向西方靠拢的几十年发展,以及所经历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韩国人在可以想象的最短时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了大范围的生产、建设、交流和消费活动,同时也以同样大规模和快速的方式面临着与这些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风险。”[8]而政府的不作为以及权贵资本的累积,扩大了这种“压缩的现代性”的悲剧。在历史上,这种“现代性”的根源——西方化范式,造成韩国普通民众的被压迫性地位,日本以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和平协商后将其移植,韩国统治集团更是以“威权政府”“军人政府”的形式命令他们接受。简言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神话”破灭,多数韩国民众发现自身努力促成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被压缩的现代性,是官僚集团与权贵阶层夺取利益的一种“说辞”,于是这种警惕、怀疑,便与民族历史、社会现实、政治运动相交织,成为有效调动观众情绪的重要方式。
不可否认的是,韩国犯罪片或多或少都有控诉“人治”的内容,比如对个人权力滥用的表现,但往往批判的是权力顶峰的人物,相比香港警匪片、黑帮片对权力底层——普通警察、黑帮份子、市井小贩的关注,新世纪韩国犯罪片更容易上升至国家公权力或制度(检察官、法官、司法制度、政府体制)层面,因此,多了一份对“法制”控诉的意味。就其整体特征而言,贯穿韩国犯罪片始终的是“法制”观念,通过“制度”的客观性、强制性力量规范社会的复杂关系。所以,在韩国犯罪片中,警匪的关系是冷静的,警察抓匪徒是权利与义务的要求,匪徒作恶是人性驱使,没有行走江湖的道义,更不会披上浪漫主义的温情色彩。
三、 “港味”惯例的承袭与改写:叙事模式、警察符号、空间造型
电影学者赵卫防认为“港味”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港式人文理念”,二是“类型化”,三是“极致化”的内容与形式。其中,“港式人文理念”是“港味”的精神核心,具体表现为“注重对生命个体的生存和情感的关注,并以此来表达出一种人性的复杂”[9],大致经历“从关注群体或符号性个体—关注真实个体—关注兄弟情义—关注卧底或夹心人等更为复杂的人文关怀的流变过程”[10]。可以说,对港人及市民阶层生活、精神状态的关注,构成了“港味”的核心部分。而韩国社会,如前所述,并不怀有对“人治”社会的向往,在朝鲜战争后就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现代性”俨然成为当下韩国社会的关键词。因此,它更多是强调“法制”与“制度”的强制性规范作用,并作为一种文化经验持续地影响韩国电影。这导致韩国犯罪片,虽然深受香港警匪片、黑帮片、动作片的影响,但在强大的经验性外力下,不自觉地对犯罪片的类型范式做出更符合现实图景的改写与超越。
1. 叙事模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无论是吴宇森,还是杜琪峰,香港犯罪电影都有一个共通的,却也隐蔽的类型惯例——自下而上的叙事模式。如上文所述,香港黑帮片、警匪片的关键词是“人治”,而“人治”是人在运作、管理社会,操作的主体必然落入基层,并通过底层矛盾展现“人治”社会的复杂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黄金时期的香港黑帮片多是描绘地盘瓜分、聚众斗殴,以及为什么警匪片多是刻画基层警员的矛盾性形象。这种叙事模式从80年代初期一直延续至“九七”,并在“九七”前后达到巅峰。
如果说香港电影处理犯罪题材是自下而上的叙事模式,从底层向上思考“人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那么韩国犯罪片则是对其进行大幅度的改写,甚至是颠覆,叙事模式与香港犯罪电影完全相左,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倾向。如涉及军政高官权力腐败的《王者》(2017)、权力合谋的《协商》(2018)、直接触及韩国政治制度的《恐怖直播》。可以说,韩国犯罪片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不仅仅是个案,而是一种独特的现象,符合韩国犯罪片警惕权力、反思制度的整体特征。为了洞悉权力的本质以及现实制度的运转模式,不可避免地从权力制高点往下叙事,以权力的源头为切入点,更直接、更根本地剖析制度的溃烂处。
这种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也意图表明韩国犯罪片潜在的文化逻辑,即韩国的自我形象书写建立在两种对立且成功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追求财富、权力、欲望的资本主义梦想,和挖掘真实、真理、理想的现实主义情结。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杂糅在韩国犯罪片中,等待主角调和,而主角会因为反派掩盖过去或真相的行为陷入困顿,在与文明恶棍的缠斗中,凭借最后一丝真、善、美的美好愿景,做出选择并完成使命。事实上,这呼应了韩国在深度现代化进程下个体容易在“文明”急流中随波逐流的隐喻性要求,即使文明与资本势不可挡,只要停下追逐欲望的脚步,主流价值取向就能回归正轨。
2. 好警察、坏警察与“缺失”的警察
对于犯罪题材的类型电影而言,警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类型角色。香港基于对“人治”社会的崇拜与反思,其警察形象经常出现两种极端——好警察与坏警察,“好的好到无以复加,坏的坏到千夫所指,都是极端化的”[11]53。铺展开香港电影的历史,这两种极端化的警察形象有着明晰的时间脉络,贯穿香港犯罪题材电影对“人治”社会的两种态度,从赞扬到反思。首先是赞扬“人治”社会的警察,如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以及吴宇森的《喋血双雄》,这些香港黄金时期的警匪片或黑帮片,强调警察是社会的执法者,惩恶扬善,并作为“人治”社会的一部分保障社会制度的运作,不受罪犯侵蚀。
随着“九七”到来,港人对“人治”社会失去信心,导致警察这一曾经的象征性角色出现转变,不再是大智大勇、慷慨就义的英雄形象,甚至不再被塑造为好人,一种较为另类的警察角色——“黑帮警察”应运而生。“九七”前后大批影片都力图解构之前银幕的经典形象,这当然包括警察这一重要角色,如《暗花》中替黑势力卖命的警探阿深、《机动部队》中和当地黑帮纠缠不清的肥沙、《无间道》(2002)中的双面警察刘健明,都是“黑帮警察”的典型代表,他们替黑势力做事,性格狡黠,道貌岸然。坏警察角色的出现,不仅呼应了港人集体对香港前途叵测的猜疑,更表达了一种“道义不在,公正苍白”[12]的悲观情绪。
与香港警察“好的好到无以复加,坏的坏到千夫所指”相比,韩国犯罪片中的警察形象则属于“被遗忘”“缺失”的角色,因为在根本性反思制度、权力的类型经验中,警察这一角色能提供的实质性帮助甚微,既不能推动剧情发展,亦不能使观众认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类型图腾存在,以便观众识别。但理解韩国犯罪片警察“缺失”的含义,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在类型中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恰恰相反,正因为警察的庸碌无为,才凸显出韩国犯罪片批判“法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的思想色彩。韩国学者Kelly Y.Jeong就注意到朴赞郁“复仇三部曲”中警察的“缺失”,他认为:“三部曲中对警察的描写,是当代韩国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评论的一种方式。……三部曲把警察描绘成无能的官僚。重要的是,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但没有造成影响。”[13]177
平庸、缺失的警察形象,在韩国犯罪片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中,以及探究权力、制度本质的语境下,有了批判的意味——“这些电影表明,警察只是穿着衣服的人,和其他人一样有经济需求。……法律站在了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一边,法律权威和正义的国家机关似乎变得权力分散。”[13]178具体而言,韩国犯罪片中“缺失”的警察,一般同强势、精明的上级或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一起出现,以警察的庸碌衬托当权者的狡黠,体现的正是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况且,在韩国社会“法制反思”的语境中,观众能够迅速将等级鲜明的社会结构与犯罪片范式结合,并意识到制度框架、范式惯例中警察符号的缺失,从而在“体制”中思考警察缺失的原因,在缺失的现象中反推“制度”的盲点。
3. 空间造型:立体城市空间与封闭式空间
“港味”的特征之一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达到一种非常极致化的程度”[9]。其中,“极致化”可谓是香港电影最为显著的特征,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尽皆过火,尽皆癫狂”[2]7。香港,一个立锥之地,寸土寸金,每个香港人都格外重视空间的运用,香港电影也不例外,尤其是黑帮片、警匪片的追逐戏,上天入地,狭小的空间不仅没有限制动作的伸展,反而利用其狭窄但富有立体纵深感的城市空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绝伦的追逐场面。当然,香港黑帮片、警匪片对城市空间的极致化运用,绝不仅局限于楼道、街道间的追逐,更重要的是将犯罪的滋生地——立体的城市,作为展现香港人文理念或“人治”社会的重要途径。
电梯、隧道、地下车库、地下赌场、监控室等封闭式空间,也是香港黑帮片、警匪片的一种空间图腾,在立体城市的基础上,为影迷构建了一个全景式的香港地图,并试图通过幽闭空间的氛围,渲染打斗、追逐戏码的紧张气氛,借用狭窄且封闭的空间,完成一系列高难度武打动作,使动作的张力在狭小的空间内释放,满足观众对打斗快感的期待。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成为香港犯罪题材电影中枪战、武打场面的独特美学体验,譬如《寒战2》(2016)中的隧道驳火场面、地铁枪战、爆破戏码。
香港黑帮片、警匪片对封闭式空间的运用,不仅成为“港味”的一部分被保留至今,更流传到海外,成为韩国犯罪片中的香港印记,如《新世界》中黑老大丁青在电梯中被砍杀的窒息感;《黄海》中楼道间翻来覆去的追杀;《孤胆特工》极度密闭的厕所缠斗,以及在各式各样狭小空间内的飞檐走壁、翻转腾挪,无一不是香港电影给予的灵感。但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的韩国犯罪片不仅善于在肌理上发挥封闭式空间所带来的技术效果,更将封闭式空间及其所带来的绝望感、压抑感、窒息感,深化为韩国犯罪片的独特美学体验。“韩国犯罪片的一大美学特征便是压抑阴暗的影像风格。它们常常借助各种或封闭昏暗或颓败萧瑟的空间,渲染凛冽的氛围,深入社会的暗礁,描绘人性的灰色。”[14]其中,《下水井》(2014)最为典型,影片的黑色基调使得城市格外潮湿阴冷,和其他犯罪题材电影一样,雨水冲刷着城市的罪恶,积水下布满着纵横交错的下水管道,里面住着一个男人,他精心将下水道改造成一个独立的王国,通过摄像头监视路人,锁定“猎物”。影片全程都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空间中进行,没有精彩的打斗和追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度病态的男人在密闭空间中所造成的窒息感和压抑感,让人绝望。事实上,在封闭式空间中表现犯罪行径,并不是韩国犯罪片的独创,在黑色电影中也有相似的类型图景,保尔夫认为:“幽闭式空间是‘黑色电影’的特征,几乎找不到蓝天、路的出口,每个空间都被分割成封闭的世界。”[15]但韩国犯罪片对封闭式空间的运用更为极致,它不仅仅是单个或者若干场景、段落涉及封闭空间,往往是整部电影都在压迫、窒息的封闭式空间中度过,在密闭的空间中感受罪犯的绝望与无奈,这或许与韩国民族性格“恨”,渴望体验绝望的特质有密切联系。
四、朦胧诗意与生理痛感:暴力美学的风格化到写实化
讨论香港电影的“暴力美学”,吴宇森、杜琪峰是两位关键性人物,可以说,两位分别代表着香港电影黄金时期以及“九七”后香港电影对“暴力美学”的不同体会。首先,黄金时期警匪片、黑帮片对暴力的展示,无疑受到传统武侠片、古装片中“武之舞”的影响,即注重动作的形式美感,格外注重动作的一板一眼,姿势灵巧、清奇,富有流动感和韵律感,大卫·波德维尔称之为:“停、打、停(pause/burst/pause)的布局”[2]142。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通过缩放和膨胀、紧张和缓慢、静止和运动等对立元素冲突而产生的美感,和京剧中的“亮相”颇为相似。吴宇森深谙此道,他善于使用慢镜头凝聚时间,配合港式剪辑侧重关键部分的原则,凸显重要时刻和场景。好莱坞犯罪题材电影对中弹的表现,往往用一个镜头呈现从中弹到倒下的完整过程,而《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纵横四海》《喋血街头》等电影,则忽略动作冗杂的部分,利用慢镜头延长重要时间(中弹或倒地的一瞬间),“既突出了对抗的意味,又用形式上的变化造成美感”[16]。高度风格化的暴力展示——白鸽、教堂与打不完的子弹,不仅成为吴宇森电影的识别符码,也为吴宇森的“英雄系列”、林岭东的“风云系列”打开销路,带来香港电影的高潮,就此,吴宇森的英雄片成为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代表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吴宇森希望达到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效果,在某种程度上限制香港“暴力美学”的突破,因为在那一时期,几乎是清一色的带有朦胧、写意性质的暴力展示,所塑造的形象“在枪林弹雨之中始终保持镇定自若,潇洒自如,面带微笑,心境坦然幽默,动作敏捷飘逸,充满舞蹈韵味”[11]55,很少有对痛苦、残忍、血腥的直接描写,或对死亡、伤痕的直接呈现。从这一点看,韩国犯罪片与黄金时期的香港警匪片、黑帮片,二者对暴力的“上镜头性”表现大相径庭,韩国犯罪片对暴力的艺术化表达相当写实,并且伴随着强烈痛感—— 一种生理刺激后贯穿全身的伤痛感,直面人性的原始暴力本能,生吃章鱼、割舌头、切耳朵等等,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暴力行为所带来的伤害,以及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
香港电影的“暴力美学”注重暴力行为的结果展现,用慢镜头表现中枪或倒下的一瞬间,并利用瞬间的结果抒怀、安抚观众情绪,而韩国犯罪片则对暴力的过程情有独钟,以冷静的姿态,直面暴力带来的物理性伤痕,拨动观众的生理性痛感神经。
暴力的风格化表达,“意味着电影不再提供社会楷模和道德指南,电影也不承担对观众的教化责任,电影只提供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17]。对韩国犯罪片而言,暴力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还是对血淋淋残酷现实的正视,震慑、对抗着造成人性异化的资本社会。我们必须公开、认真地审视暴力残酷行径与社会批判之间的常见联系。有学者将韩国现代史概括为民主运动史[18],贯穿历史主线的是民众的呼喊与反抗,而政府的裙带资本主义作风,造成如今韩国社会就业机会与经济发展速度不成正比;实际收入水平得不到提高;“无就业增长”和“无收入增长”;贫富差异两极化;“财阀经济”过度占用国家资源等问题。简言之,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被极大压缩,社会现实异常残酷,韩驻华大使张夏成称其为“韩式资本主义”[19]。
“公开的残忍性和性行为通常在美学上是合理的,因为它们被视为对资产阶级文雅或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了反抗高度“文明”的“韩式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压迫,韩国犯罪片挖掘人性深渊,并希望通过写实地记录暴力本能的原始性、残酷性,营造出“原始”“野蛮”对抗“文明”的氛围。具体来说,韩国犯罪片经常出现对残酷图景、生理痛感的持续性关注与偏好,如《追击者》中高高跃起的铁锤与残肢;《看见恶魔》中血腥的折磨与掉落的头颅,都试图将观众拉回到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不仅是一种充满暴力的环境,而且是一种‘意义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一种存在许多主观理解的状态”中[20],重新回到那个没有政治、秩序与道德约束的人类原始社会中,提醒政府、司法、秩序存在的本质意义。
可以说,韩国犯罪片对暴力麻木、客观,近乎于科学实验的态度,完全放弃秩序、道德、意识形态上的教化,而对施暴过程毫无偏见的记录,意味着对暴力本能的狂热崇拜,是对现有秩序、体制的挑衅。从这一方面看,写实并带有痛感的“暴力美学”是韩国社会异质性历史的一种呈现。其塑造的人物及其行为举止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暴力性本能,表明它始终试图从本我的层面讨论暴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与韩国犯罪片挖掘人性深渊的特质不谋而合,毕竟,人性到底离不开本我层面的原始需求。
韩国社会从朝鲜战争到民主运动,列强掠夺、民族分裂与政府强权共存于一体,韩国在割裂的历史中摇曳,并被一层叠着一层早该解决却未解决的历史问题纠结缠绕,同时展现着殖民、冷战、后冷战,在经济复苏后,又被“韩式资本主义”所操控。因此,基于现实与历史的严峻要求,韩国电影人无法对暴力产生“诗情画意”般的朦胧情感,而是用写实的笔触将暴力真实的一面铺展开,通过生理性的痛感、野蛮的本能呼唤民众对暴力的记忆,对抗看似文明实则不公的现代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