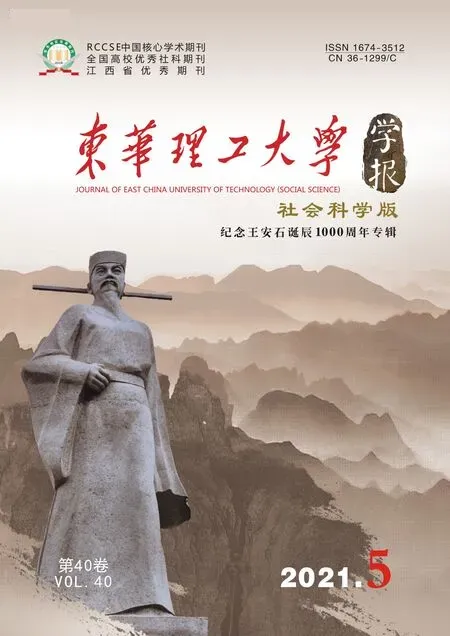沙皇俄国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王安石
2021-11-29彭屾
彭 屾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王安石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改革家,其不凡之处除了在北宋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大显改革身手之外,还在于他为人处事的生活细节中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品质风范[1]。据元朝丞相脱脱撰《宋史》所载,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王安石先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之后不久又改封荆国公。观荆公一生,最令世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他在神宗朝主持的“熙宁变法”。从南宋至晚清,历朝历代官方对王安石变法基本持否定态度,文人墨客对王安石的褒贬也从未停息。近代以来,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严复、胡适等人,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倡导创新,对王安石的改革持积极态度[2]。其中,身为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先生将王安石与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齐名,给予了“拗相公”王安石极高的肯定,直言不讳地称其变法为“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3]84。尽管古今中外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可谓千家千言,但其大无畏的变革精神影响深远,不断启发着后人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
1 俄国汉学家王西里对王安石的研究
自俄国汉学诞生以来,中国历史问题一直都是汉学家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蜚声海内外的北宋宰相王安石自然不会被俄国汉学家们所忽视。早在十九世纪,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王西里(1818—1900)就已经注意到了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王西里”是他按照自己姓氏的俄文发音想出的中国式名字,而今多译为“瓦西里耶夫”。1818年,这位汉学家出生于俄国下诺夫哥罗德市,1834年进入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班,师从俄国蒙古学奠基人科瓦列夫斯基(1800—1878)。1837 年开始跟随汉语教研室主任西维洛夫学习汉语。1839年11月以学员身份被编入第十二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赴华学习汉、藏、梵文,1850年返回俄国,1864年获博士学位,1886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王西里一生著述丰富、博学多能,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和宗教等领域建树不凡。这位精通汉语的俄国学者不仅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而且还客观地评价了每一阶段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1880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在这部作品中便有两处提及了王安石。纵观全书目录(共十五章),作者为每个章节都设置了意义鲜明的标题,直观地向读者呈现了其在创作过程中的构思。王西里在本书第二章“儒家的第二个阶段”中列举了部分“极受儒家推崇”的经典汉籍,在介绍《盐铁论》时将西汉御史大夫桑弘羊称为“王安石的前辈”[2],同时指出在当时的俄国有人把王安石比作“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不过遗憾的是,对于在俄国出现的这种类比现象,作者并未给出任何解释性说明,而且文中也找不到相关的文献引用。
但从“虚无主义”在俄国传播的历史背景可以推断,始作俑者或许认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旧交替的俄国与十一世纪积贫积弱且亟待革新的北宋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的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曾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言壮语,其敢于打破陈规旧制的思想与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虚无主义者挑战传统的精神颇为相似,理应被视为宋神宗一朝的“新人”。至于为何将桑弘羊视作王安石的“前辈”,以笔者愚见,或许是王西里认为汉武帝时期朝廷推行的盐铁官营和均输政策与宋神宗一朝实行的“均输法”之间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的主要目的都在于调节商品物资的流通,平抑市场价格。此外,王西里还在第十二章“语言学·评论·古董”中写道:“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催生出许多新的思想(现在有人无缘无故地将王安石看作是一位社会主义者)”[4]293这段话是作者在介绍中国文学史上的评论性著作时的一番陈述,而句中提到的“新的思想”应该是指北宋时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和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理学。关于王安石在俄国被人视为“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作者在书中仍没有具体说明相关原委。笔者以为,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在当时的俄国与西欧,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将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法误解为是一种试图将“土地国有化”的行为,进而认为王安石早在十一世纪就曾试图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
2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
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得益于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二人的政治论战,王安石在俄国的知晓度又一次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众所周知,在1905年革命的冲击过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政权风雨飘摇,社会危机四伏,整个帝国正面临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与此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日益活跃,国家未来的发展走向,成为众人时刻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在此背景下,1906年3月,时任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的普列汉诺夫(1856—1918)于《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五期上发表了《论俄国的土地问题》(1)文章被收录在1926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第15卷》(《Сочинения Текст Г.В.Плеханов Т.15》)。总共二十四卷本的《普列汉诺夫文集》由苏联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大卫·梁赞诺夫(Рязанов Д.Б.)负责编撰并出版。1921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后,梁赞诺夫主持了对马恩著作的首次大规模编辑与出版工作。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在俄国实行土地国有化,认为国家应该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任何形式的土地国有化在性质上都是反动的,“这种制度无疑是一切东方专制大国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莫斯科版,在这种陈旧的体制下,土地与农民都将变成国家的私产”[5]31。此外,为了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还从法国人雷克吕(2)埃里塞·雷克吕(élisée Reclus,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1882年编写的《新世界地理学:地球与人:第七卷——东亚篇:中华帝国、朝鲜和日本》中摘得了与王安石有关的材料。“您是否偶然读到过埃里赛·雷克吕地理学第七卷中专门讲述中国的内容?如果是的话,那么您可能还记得其中的一件轶事,讲的是‘在经历各种导致朝代更迭与革命的变故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摈弃了公有制(以前也存在)理念并试图推行新的制度。1069年,中国皇帝宋神宗的顾问兼友人王安石发布了一项废除私有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国家变成了唯一的资产所有者,并负责分配所有产品,而产品的生产则必须在朝廷官员的监督下进行。这一举措引起了一些官员和旧时封建大地主们的极为强烈的反对,然而王安石还是使得自己国家维持‘共产主义制度’达15年之久。‘但是统治的改变足以推翻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既无法满足百姓的愿望,也不符合高级官僚的追求,而且还造就了一整类的调查员并把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地主’。雷克吕说,中国朝臣的这种‘共产主义’经验是有史以来朝廷为改革社会而做出的力度最大的尝试。此话事出有因,雷克吕是在表达一种暗示,即在无政府主义者心中,社会民主党人一直都在追求还原出中国的那种‘共产主义’形式。”[5]31在引述完以上内容后,普列汉诺夫话锋一转,旋即指出雷克吕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地理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位非常糟糕的社会学家,其著作中关于十一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故事是从俄国人杂哈劳(3)原名伊万·伊里奇·扎哈罗夫(Захаров И.И.),俄国汉学家、外交官,精通汉文和满文。1851—1864年任驻伊犁领事。1868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执教,1879年获评教授职称。著有《满俄大辞典》《满语语法》《中国西部领土记述》《中国人口历史评述》等作品。那里不加任何批判照搬而来的,书中所说的“王安石的尝试还延伸到动产方面”的提法是十分可疑的。他还补充道:“王安石所进行的革命很可能类似于我们国家皇族领地上有时由官员执行且令农民极为不满的公有土地的那种事情,只不过与之相比在规模上要大多了。对社会民主党成员而言,这种‘尝试’甚少有吸引人之处。”[5]32普列汉诺夫将社会民主工党成员中那些支持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群体比作“俄国的王安石们”,并表示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特别的期待,只有不幸的后果。
面对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来自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布尔什维克一派的列宁却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并发表了《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其中特别提到了“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主张。列宁在《纲领》正文的注释中着重驳斥了普列汉诺夫所列举的王安石事例。“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5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是一目了然的。真所谓qui prouve trop,ne prouve rien(谁过多地证明,谁就什么也没有证明)。如果二十世纪的俄国可以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谈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6]226经过分析以上论述可以发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这句话并不是出自普列汉诺夫之口,而是列宁对他所持论据作出的补充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存山先生曾专门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所谓‘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乃是断章取义,是对列宁观点的一个误引。”[7]至于这是中国学界中普遍存在的误引现象,还是不同学者对注释原文有着各自的理解,本文在此存而不论。倘若就事论事,通过解读列宁在括号内增加的二级注解,我们可以首先明确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列宁前半句陈述足以说明他本人认可王安石“改革家”的称号,但尚未表现出批评或赞赏的态度;其二,列宁认为王安石的确尝试过推行“土地国有”制度,但改革不幸以失败告终。另外,在通读完一级注释的全文后可以注意到,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其实并没有在“王安石能否担得起改革家这一名号”的问题上发生纠结,二人也并未回避王安石落得失败下场的史实,“覆辙”和“未成”两词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了双方在事实上都承认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存在,这一点不可忽略,值得重视。
然而,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王安石在北宋时期推行过的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均不包含“土地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内容,即便是熙宁五年(1072)颁布的方田均税法也只是一项解决各地田赋不均、税户隐田逃税情况的改革新政,其目的不外乎增加朝廷的赋税收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核心统治观念。总之,历史上的王安石从未提出过任何带有“土地国有化”色彩的主张。由此可见,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列宁,在理解涉及“土地改革”的新法方面皆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然而,就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汉学在彼时的俄国并非大行其道的人文学科,即使是在汉学圈内也鲜有汉学家对王安石进行过研究,相关成果极少,故而这些人可用的参考文献也非常有限。再者,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都不曾深入研究过十一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熙宁变法期间的各项举措,所以对变法的实质自然不甚明了,只能浮于表面,从而得出不严谨的结论。因此,只能说“王安石”这一人名在外界看来更像是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论战过程中用来敲打对方的“史料工具”。实际上,普列汉诺夫说有人会“重蹈王安石的覆辙”,意在暗讽列宁在一定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做法就如同王安石在十一世纪的中国推行土地改革制度,极有可能遭遇到彻底的失败。显然,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主张是坚决反对的,其潜台词就是:将土地国有化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当时的俄国。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列宁补充相关注释意在证明普列汉诺夫于《日记》中发出的“警告”只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类比罢了,从理论上说并不成立,而且放在俄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站不住脚的。在此基调之下,列宁在注释的后半部分以较为婉转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反对的理由,其核心观点可以解读为:“二十世纪的俄国”与“十一世纪的中国”在社会性质方面全然各异,前者在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之后已逐渐步入资本主义时代,而后者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则还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二者不可能相提并论。因此,在列宁看来,普列汉诺夫抨击自己的言论着实是一种借古喻今式的伪论据,“王安石”这个概念并不适合被当成经典论据引入两人的论战之中,换言之,拿一位十一世纪中国改革家当枪使的做法断不可取。
经过上文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偶现于普、列二人争论中的“王安石线索”最初来源似乎都指向了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的著作,而且通过查找法文原著的确可以看到在书中第578页存在一条“Zakharov, mémoire cité(杂哈劳,引文)”的文献脚注,不过这简单的“引文”二字却终究不能道明雷克吕是在杂哈劳具体哪部作品里读到了北宋“共产主义革命”的故事,注释中此等重要信息的缺失着实令人遗憾。不过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问题的存在也给大家创造了更多思考的空间。因此,本文有必要针对上述疑问进行更加深入的溯源调查。
相关资料显示,《普列汉诺夫文集:第24卷》收集了其本人从1892至1925年在苏联、德国、法国以及瑞士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的31篇文章,经查找后发现,在第一篇文章《农民的解放》中存在关键线索。普列汉诺夫在讲述俄国农民土地分配问题的第九部分中添加了一条层次复杂的文献引用脚注,他写道:“关于中国的论述可以参阅科汉诺夫斯基所著《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农业》(4)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и земледелие в Китае.Владивосток:тип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1909.一书中第12页前后的内容(本书作者主要利用了杂哈劳佳作长文《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中的材料,其原文被收录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第2卷本中。可惜我手头只有此文的德语译稿,就是《Arbeiten der russischen Gesandschaft in China 〔俄罗斯驻华使团文集〕》书中《Ueber Grundeigenthum in China〔关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一文)。此外还可参考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兄弟合著的《中华帝国》(5)Elisée et Onésime.L′Empire du Milieu: Le Climat, Le Sol, Les Races, La Richesse de La Chine[M].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1902.本书第五部分第二章“中国农业”中第三小节“土地使用权”详细论述了中国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发展历史。雷克吕兄弟二人中的年幼者是奥尼齐姆·雷克吕(Onésime Reclus,1837-1916),法国地理学家,最早提出了“francophonie(法语国家)”一词。第499-503页的内容。”[5]26行文至此,思路渐明,注释里详细的描述足可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无论是法国的雷克吕,还是俄国的科汉诺夫斯基,二人在个人专著中都参考过杂哈劳撰写的《中国的土地所有制》。青年时期的杂哈劳曾在沃罗涅日宗教学校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学习,1839年便以学员身份被编入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次年抵达中国,后于1850年返回俄国,《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一书正是其在北京生活期间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大作。二十世纪的俄国汉学家尼基福罗夫(1920—1990)认为杂哈劳是“俄国第一个对中国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人,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分析”[8]9,这部作品细致地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土地面积和土地政策的变化情况,对后来包括苏联时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文献流传的历史脉络来看,杂哈劳所著的《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一书是整条传播链的最初端口,书中部分内容起初被埃里赛·雷克吕采纳,而后者著作中的相关信息又“反哺”了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而此书的德译本亦从侧面起到了催化剂般的作用。
3 汉学家伊凤阁对王安石的研究
沙皇俄国时期另一位研究王安石的著名学者就是开创俄国西夏学研究领域的汉学家伊凤阁(1878—1937)。190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蒙语专业,师从王西里和孟第(1833—1913)学习汉语,并于同年留校任教。1902年前往北京进修,曾担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是一位在多个领域都建树不凡的汉学大家,一生发表作品达二十余种,但其早年的学术兴趣还是集中在中国思想史领域,曾重点关注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社会变革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变革思想。1909年他以《王安石及其变法》一文参加硕士论文答辩并获得相应学位。1913年通过题为《中国哲学资料导论——法家韩非子》的博士论文答辩并升任教授。这两篇学位论文后来也成了伊凤阁最早出版的两部专著。在中国历史上,韩非子与王安石都是推行过重大改革的政治家,在思想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传承性。因此,苏联汉学家霍赫洛夫(1929—2015)和尼基福罗夫认为伊凤阁对韩非子、王安石二人的研究是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851—1893)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延续,而且还与俄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9]296。为了防止1905年的革命再度爆发并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俄国首相斯托雷平(1862—1911)于1906年11月开始推行旨在消灭村社制度、促进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土地改革。在这种强烈的变革氛围影响之下,研究中国历史的伊凤阁在北宋王朝“首相”王安石的身上看到了新的学术研究方向,由此便诞生了沙皇俄国汉学史上第一部专门讲述王安石及其变法历史的学术专著。
《王安石及其变法》全书共分为七章:序言;唐末至宋神宗时期的历史概况;王安石生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改革(均输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选拔官员及军队设置);结语——司马光论改革;文学作品范例。最后的附录中还有苏轼、苏洵关于改革的奏章。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序言中批评性地审视了欧洲学者对王安石的研究,他开门见山地写道:“直到当下,大多数欧洲学者依然视中国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种原始聚合体。自古以来形成的生存法则始终未变,宗法体制得以保留,丝毫不损。少有文献讨论过其中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有的人认为,在中国不存在社会史,只有政治史。狭义上讲,就是指从华夏一统到清朝数千年间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权更迭的历史。但史实却给了我们机会对中国社会史进行总结,即如何在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特定的社会关系。研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现象具有重大意义,其实在很多方面都能看出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遵循着相同的进化规律,正如《不列颠百科》中的解释:‘从部落社会开始,土地在各地就逐渐被分配给村庄、家庭和个人。’历史证明,如今欧洲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中国早已存在,有必要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观察和运用。中国历史(特别是汉、唐及宋代)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以借此来研究其国家社会和经济现象,但由于中西民族起源间的巨大差异,人们对此了解和研究得并不充分。”[10]1-2通过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伊凤阁认为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史外壳下蕴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其研究目标也不只限于解读变法的具体措施以及分析其可行性与合理性,而且还试图在此基础上开辟出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而改变欧洲学者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刻板印象。
整体而言,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王安石变法具体的过程以及苏轼、司马光所属的保守派与之斗争的历史。不同于大部分俄国汉学家只利用汉籍文献的做法,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作者伊凤阁还参考了许多西欧汉学家的相关著作,这一点与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所见略同。其中汉语文献有《文献通考》《经义考》《庄子》《荀子》《唐书》《康熙字典》《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司马文公文集》《通典》《通鉴纲目》《五代史》和《史记》等;欧洲语言文献中除了有俄国汉学家巴拉第(1817—1878)(6)俗名卡法罗夫(Кафаров П.И.),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第十三、十五届领班。先后三次来到中国,停留居住达三十年。著有《汉俄合璧韵编》《佛陀传》和《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著作集》等作品。、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和杂哈劳的作品外,还包括冯秉正(1669—1748)、梅辉立(1831—1878)、沙畹(1865—1918)、毕瓯(1774—1862)、顾赛芬(1835—1919)、福兰阁(1863—1946)、翟理斯(1845—1935)、理雅各(1815—1897)、福开森(1866—1945)和夏德(1845—1927)的著述。然而,在作者大量引用外文文献的同时,尼基福罗夫却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他评价道:“研究的深度不够影响了作者之前既定的目标,部分章节纯粹是汉籍文献原话的翻译而已。作者本人提出的一些观点颇为天真,比如王安石变法失败既有过分自信的因素,还有用人不当的原因。不过,作者的其他论点在当下还是成立的。例如,面对外敌,中国必须通过变法来加强国家利益;王安石的改革具有非常明显的创新特征等。”[8]22此外,关于作者对参考文献中杂哈劳著作《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的评价,即“尽管作者利用汉语文献叙述得十分清楚,但一个重要的缺憾在于,将中国学者对某一著名事件的评价与自己的观点杂糅在了一起”[8]23,尼基福罗夫直截了当地指出,以上缺憾在作者自己的书中怕也是不少的。实际上,伊凤阁的研究基本沿袭了中国学者的传统观点,没能彻底实现他在前言中设立的目标,全书结论很少,说服力也不强。
4 结语
尽管王安石其人在历史上饱受争议,但其个人厚植于心的家国情怀、变革求新的开拓思想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跨越千年,远播四海,在众多迥异于中华文化的他者语境中找到了积极的共鸣。正如十八世纪的欧洲,当各国相继掀起反宗教束缚和封建专制的启蒙运动,提倡理性和开明的西方思想家意外地在中国圣贤哲学学说中寻得了“灵感”,由此整个欧洲便刮起了一股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风”。无独有偶,100多年前,在亟待变革的沙皇俄国,一阵新鲜的“王安石之风”席卷而来,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位生活于中国十一世纪的东方改革家,以期在他的故事中找到为己所用的“密码”。
总之,通过考察和梳理相关史料和学术成果,王安石变法在沙皇俄国时期的研究特点也随之呈现。第一,研究人员类型多样,所涉领域各异。从十九世纪中叶的杂哈劳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伊凤阁,这其中不仅有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高等教育机构研究专家,甚至还有革命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他们在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都曾大量参考过早先以及同时代西欧学者的相关研究,二者间互有影响、渗透。这一现象也从侧面折射出俄国汉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整体特征,即汉学著作中的中国信息通过俄罗斯文化精英们的大脑加工和过滤之后再在其作品中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学著作更多的是为俄罗斯思想文化界提供了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资料[11]449。第二,沙皇俄国时期的王安石研究与俄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尽管俄国在1861年经历了农奴制改革,但由于其国内封建残余势力依旧强大,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同期的西欧。然而,随着新生资本主义力量的不断增长,整个社会都在密切关注着土地话题,而十一世纪就曾“试水”过大规模土地改革的王安石则无疑为那时的俄国大众提供了绝佳的范例。如此一来,俄国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自然都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十月革命”爆发以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内集中出现。第三,王安石对俄国人而言,符号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按照他们的理解,王安石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土地改革方式来践行“社会主义”理念的先驱,其变法行为早已升华为一种精神层面的象征。因此,通过这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惯于从东方找寻“参照素材”的汉学家对俄国这股“王安石之风”的形成起过促进作用,但在核心思想文化领域,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从不曾占据显著位置。王安石的变法对俄国社会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