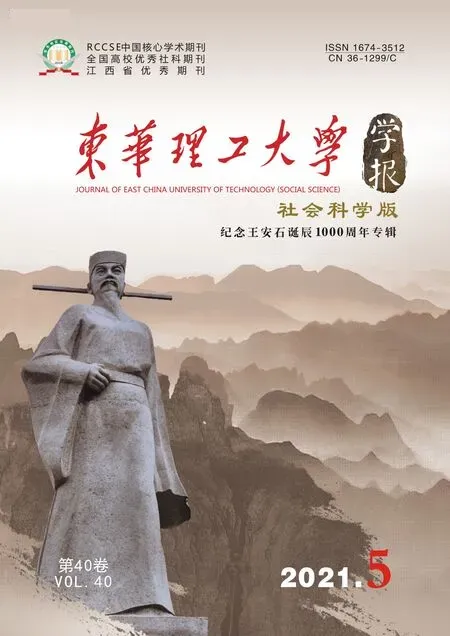论王安石《字说》的语言学意义
2021-12-15邓海霞
邓海霞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宋徽宗时期,《字说》开始在学堂盛行,经生们解读经典、学作策略都采用《字说》的理论,朝廷开科取士也以《字说》为据。徽宗诏令太学官根据《字说》修定五经,受到时人的推崇。随着王安石的失势,《字说》被禁止,文献中虽然保留了个别当世以及后世文人对王安石《字说》字义解释的诟病之语,但也不乏赞美之词。《字说》虽已散佚大半,但仍可从其辑本、笔记与对其的二度引用中管中窥豹,了解王安石的语言文字观。王水照等主编的《王安石全集》第一册有张钰翰收集整理的《字说》五卷,约计一百五十余条解说,下文笔者将结合历史文献以及语言学知识对王安石《字说》进行研读分析。
1 王安石著述《字说》的初衷
元丰三年(1086),六十岁的王安石退居钟山,但仍然笔耕不辍,创作语言文字类著作《字说》。他对《字说》的写成非常自信,当年就向朝廷献上《进〈字说〉子》《进〈字说〉表》《〈字说〉序》等奏议,并且书写了两首与《字说》有关的七绝诗。下面文字记叙了王安石著述《字说》的缘由:
《子》:顷蒙圣问俯及,退复黾勉讨论[1]237。
《表》:臣顷御燕闲,亲承训敕,抱疴负忧,久无所成。虽尝有献,大惧浼冒。退复自力,用忘疾惫。咨诹讨论,博尽所疑。冀或涓尘,有助深崇。谨勒成《字说》二十四卷,随表上进。道衰以隐,官失学废,循而发之,实在圣时[1]236。
提举成都府路学事翟栖筠奏中也有论及王安石所处时代的语言使用环境:
王安石参酌古今篆隶而为《字说》,此造道之指南,而穷经之要术也。然字形、书画纤悉委曲,咸有不易之体,世之学者知究其义,而至于形画,则或略而不讲,从俗就简,转易偏旁。传习既殊,渐失本真。如期、朔之类从月,股、肱之类从肉,胜、服之类从舟,丹、青之类从丹,靡有不辨。而今书者乃一之,若此者不可胜举,故幼学之士终年诵书,徒识字之近似,而不知字之正形,甚可叹也云云。愿诏儒臣重加修定,去其讹谬,存其至当,一以王安石《字说》为正,分次部类,号为《新定五经字样》,颁之庠序[2]2187。
从上文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王安石所处时代语言文字的使用比较混乱、缺乏规范。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古人在造字之初都有一定的理据,具体体现在汉字的构型和部件上。然而在文字的流传过程中,汉字的字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些已经不大容易看出最初的造字本义;而且人们在书写汉字的时候,也比较随意,出现了异体字、简体字等情况,从而造成了字体的混淆,给学习者带来一定的困惑。王安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想用自己平生所学所研的文字学知识来教导莘莘学子。他将著述完成的《字说》献给皇帝,希望通过国家的力量颁布天下,成为学子们学习经学的一本工具书类教材。这本教材一经发布,就具有了权威地位。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
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3]45。
《东轩笔录》卷十记载:
熙宁中,诏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经义,经成,加荆公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雱龙图阁直学士,同日授命,故韩参政绛贺诗日:“陈前舆服同桓傅,拜后金珠有鲁公。”[4]3315
《字说》写成之后,王氏父子得到朝廷很高的礼遇,父子同日加封,王安石封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子王雱封为龙图阁直学士[5]。天下学子都以《字说》之学为宗,科举考试也以其学说作为录取的标准。翰林学士、参知政事韩绛写诗祝贺,将他们和善于解说儒家经典而被皇帝恩赐辎车、乘马的东汉桓荣作比,甚至和周公、鲁公相提并论,可见其地位之高。
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
荆公《字说》成,以为可亚六经[6]94。
当时一些士大夫酷好《字说》,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记载:
《字说》盛行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字说备检》一卷,又以类相从为《字会》二十卷。故相吴元中试辟雍程文,尽用《字说》,特免省。门下侍郎薛肇明作诗奏御,亦用《字说》中语。予少时见族伯父彦远和霄字韵诗云:“虽贫未肯气如霄。”人莫能晓。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说》‘霄’字,云:凡气升此而消焉。”其奥如此。乡中前辈胡浚明尤酷好《字说》,尝因浴出,大喜曰:“吾适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说》‘直’字云:‘在隐可使十目视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时此学既废,予平生惟见王瞻叔参政笃好不衰。每相见,必谈《字说》,至暮不杂他语;虽病,亦拥被指画诵说,不少辍。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3]191。
可见,当时王安石《字说》的受重视程度。王安石本人对他的《字说》也是十分自信的,他在《字说》序中以“天之将兴斯文也,而以予赞其始”自命,又感叹“庸讵非天之将兴斯文也!”[7]456同时,对一位深受儒家传统熏染的中古文人来说,他对自己的著作也是颇为谦逊的。王安石有两首七绝诗谈及《字说》:
正名百物自轩辕,野老何知强讨论。但可与人漫酱瓿,岂能令鬼哭黄昏[8]538。——《进〈字说〉》
鼎湖龙去字书存,开辟神机有圣孙。湖海老臣无四目,谩将糟粕污修门[8]538。——《成〈字说〉后》
在这两首诗中,王安石表示自己没有仓颉双瞳四目的天赋,对于文字也是强作讨论,并称自己创作的《字说》为糟粕,是非功过由后人来评说。可见,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也对语言文字研究的不易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王安石晚年用尽毕生之学,创作了二十四卷本大体量的语言文字类著作《字说》,又几经修订整理,流传天下。其本意是力图阐明字的义理,剖析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为百物正名,帮助人们正确地使用语言文字,同时为推行其“新学”“新政”作辅助性工具,其真诚谦逊的为学态度和刻苦勤勉的实干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2 历史上关于《字说》的评价
历史上关于《字说》的评价大都是贬义的,主要见于宋人的笔记,且多有重复出现者,兹列举主要几种评述如下: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成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党伐之论,于是浸闓;黄冈之贬,盖不特坐诗祸也[9]27。——《邵氏闻见录》(与《后山谈丛》《高斋漫录》同)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鳲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9]27——《高斋漫录》(与《鹤林玉露》同)
世传东坡问荆公:“何以谓之‘波’?”曰:“波者,水之皮。”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也?”[9]27——《鹤林玉露》(与《高斋漫录》《调谑编》所载雷同)
《字说》中确实有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不当解释,像苏轼这样博学、耿介之士等提出批评也是在所难免,然而这种批评仅是个别现象的指摘,比如“犇”“麤”造字之初,字形的创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先人选择三只鹿堆叠表示粗之意,三只牛堆叠表示奔腾之意,都是无理据可考的,在使用中还会遵守约定俗成的原则,不会轻易改变字的结构和意义。同理,造字中声符的选择也是带有随意性的。宋人笔记中保留的这类批评文字,带有戏谑讥讽的性质,更多地掺杂着政治因素,历史上并不一定必有其事,《字说》上也不一定实有其语。
王荆公晚喜《字说》,客曰:“霸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曰:“如时雨化之耳。”其务凿无定如此。《三经新义》,颁于学官,数年之后,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请易去[10]3。——《邵氏闻见后录》

但也有对《字说》持肯定态度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下。
叶大庆《考古质疑》:
近世王文公,其说经亦多解字,如曰:人为之谓伪,位者人之所立,讼者言之于公,与夫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歃血自明为盟,两户相合而为门,以兆鼓则曰鼗,与邑交则曰郊,同田为富,分贝为贫之类。无所穿凿,至理自明,亦何议哉!有如“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晦庵亦或取之。惟是不可解者,亦必从而为之说,遂有勉强之患,所以不免众人之讥也[11]29。
《文献通考》“经籍”十七《字说》下:
然遂谓之皆无足取,则过也。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元丰三年条下,引倪氏《思经堂杂志》曰:“荆公《字说》,以转注、假借皆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为徇也。若其间说象形、象意处,亦自有当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东南为便,不见其害[12]1614。
宋人李焘在《说文解字五音韵谱自序》中的说法颇为公允:
安石初是《说文》,覃思颇有所悟,故其解经合处亦不为少。独恨求之太凿,所失更多。不幸骤贵,附和者益众而凿愈甚[13]1745。
王安石《字说》从颁布到被禁大约经历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其间学者对《字说》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这种批评更多地掺杂政治因素,而且大多是对王安石《字说》中个别条目解说不当的批评,相对于《字说》二十四卷本的体量和数千的条目来说,上述批评还略显单薄了点。只有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站在历史的角度,既指摘不当之处,又不全盘否定,才是不抱成见的立论。
3 王安石《字说》的语言学意义
靖康元年六月《字说》被禁用,直至最后在历史上散佚。《字说》中尚有哪些精华,至今只能从辑录中窥见了。联系历史文献,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知识,从现存《字说》的条目解释来看,王安石对语言文字规律的认识还是比较超前的,对一些语言文字现象的把握也是比较准确,并非如上述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穿凿附会。《字说》在我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历史上还是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的,其对后世辞书的编纂也有很大的影响。
3.1 王安石具有创新精神,认识到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
王安石在其《字说》的上表文字和序中也曾表明自己对古文字有较深入的学习[14]。《字说》中的“秉”字条,王解释为“从又从禾”[15]191。考“秉”字的小篆字形就是手持一把禾苗,表示握住的意思。“农”字条解释为“从臼,从囟,欲无失时,故以辰”。《说文解字》“农”字条字形同此。小篆从晨,囟(xìn)声,字形像拿着农具去耕种。可见王安石是根据小篆字形来解说字义的,并非完全杜撰或随意附会。
王安石曾全面研读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其较好地保留了“古字”的字形,并详细地研读了文字形体所代表的原始意义。他说古文字的字形是“上下内外,初终前后,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邪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每一个汉字的笔画和构型都“其形之衡纵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然而“秦烧《诗》《书》,杀学士,而于是时始变古而为隶”。在文字的演变过程中,汉字的图画性特征越来越弱化,而汉字的符号性特征越来越加强,以至于王安石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汉字的原始字形已不再敏感,使用也较为随意,于是他深深地感慨“盖天之丧斯文也,不然,则秦何力之能为”[1]236。
显然,王安石的意识是比较超前的,他已经了解到文字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最早的汉字是根据字义来绘形的,而小篆是文字早期的形式,较好地保留了古文的造字意图,从早期字形上解释字的本义,更容易厘清文字演变的来龙去脉。
王安石《字说》继承了《说文解字》解说文字的体例,即辨析字形,据形解义。如:“举,从手从与。以手致而与人之意,献酬之意也。”“美,从羊从大。谓羊之大者方美。”“年,禾一成为年。”这些都是建立在汉字形体基础上比较合理的解释。《字说》还对《说文解字》进行了补充说明。如“鼓”,《说文解字》解释:“击鼓也。”这是“鼓”的本义。王安石则补充了“鼓以作为事”“故凡作乐皆曰鼓”等引申义,这是语言演变发展中的后起义。这些新词新义的记录对于后人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又如“门”,《说文解字》释为“闻也。从二户,象形”,王安石解释得更为具体详细:“二户相合而为门”,小篆的“门”字形更像两扇对开的门,显然王安石对字形的说解更为直接精当。
《说文解字》:“左,手相左助也。”“右,手口相助也。”段玉裁注释为:“以手助手,是曰左,以口助手,是曰右。” 显然这是不正确的。王安石认为:“以左助之为佐,以右助之为佑。”“左”“右” 都是手,用作动词时,写成“佐”“佑”,本义都是以手助人。王安石的解释比许慎和段玉裁的解释更为合理。甲骨文中就有很多形似“手”的造字部件,它们参与了很多汉字的构造,刻在左边就表示左手,刻在右边就表示右手,小篆中的“左右”是已经线条化了的文字,许慎和段玉裁可能并没有看到过甲骨文字,所以说解有不合理之处。而王安石也可能没有看到过这些古老的文字,但他凭借多年语言文字运用和研究的功力看出了文字的发展变化,“左”“右”是早期字形,而“佐”“佑”是后起字。语言在发展变化中日益精密和系统化,“左”“右”后来专指方位,而“佐”“佑”作动词,表示辅佐护佑。可见,王安石《字说》的体例本质上是跟许慎的《说文解字》一脉相承的,并非某些批评家所认为的妄自创新,穿凿附会。

语言文字的使用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中,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无视新的语言文字现象显然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王安石继承了中国古代字书《说文解字》分门别类、据形说义的传统,对部分词语的字形字义进行了补充说明,并记录分析了部分词语的后起义,具有创新和求实的精神。
3.2 认识到语言的本质是声音,对“右文说”和同源字理论有补充和启发作用
王安石认为:“发敛呼吸,抑扬合散,虚实清浊,自然之声也。”“人声为言,述以为字。字虽人之所制,本实出于自然。”“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亦皆有义”[7]879。可见,王安石比较清楚地意识到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声音来传情达意,而文字是对声音的记录,因此声音是第一位的,文字是第二位的,这比较符合现代语言学对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认识。而在王安石之前,人们往往将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王安石常用声训来释义。如:
芥者,界也。发汗散气,界我者也。
琮,宗也。万物祖天,而地为之宗。
桧,柏叶松身,则叶与身皆曲。枞,松叶柏身,则叶与身皆直。枞以直而从之,桧以曲而会之。以直而从之,故音从容之从;以曲而会之,故音会计之会[15]230。
许慎将汉字的造字方法总结为“六书”,其中形声为最主要的造字方法,早在甲骨文时代,形声字就占据了汉字总量的十分之六七。杨树达指出:“盖文字之未立,言语先之,文字起而代言,肖其声则传其义。中土文书,以形声字为夥,谓形声字声不寓义,是直谓中土语言不含义也。”[16]13其早期留学日本,接受了较为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他肯定了形声字的声符也具有表义的作用。其实,《说文解字》中许多形声字的声符都是表音兼表义的,许慎虽没有明确说明,但其在对字形的说解中,常常会用“亦声”这个术语,来表示形声兼会意。如《说文解字》:“婢,女之卑者也。从女、卑,卑亦声。”而王安石认识到声符兼表义的功能,他释义往往从声符上着眼辨析,注意到声符相同,意义相关,指出“字者,始于一二,而生生至于无穷,如母之字子”,初步意识到汉字中的同源字现象。如释“农”字,先辨形析义,然后指出:“农者,本也,故又训厚。浓,水厚;醲,酒厚;襛,衣厚。”其指出有“农”声符的字都有“厚”义。后人段玉裁也指出“凡农声之字皆训厚”。王力《同源字典》也引用《字说》:“水厚为浓,汁厚为脓,酒厚为醲,衣厚为襛,花木厚为穠,诸字同源。”[17]610又如:“茨”,《说文解字》释为:“茅盖屋,从草,次声。”段玉裁亦指出:“次草为之也。此形声包会意。”《字说》:“次草谓之茨。”意指将茅草有序编排形成草屋顶,“茨”的语源正好是次序的“次”,“次”是声符,也兼会意。
语言在发展初期,声音和意义的组合是任意的。但是,在语言日益精密化、系统化的发展过程中,新词新义会不断产生,新词新义是按照一定规律在旧词旧义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语音上必然与旧词相同或相近。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语言现象。王子韶撰成《字解》二十卷,其核心内容就是形声字的声符具有表义功能,后世一般称这种语言文字理论为“右文说”。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18]98。
段玉裁认为,《说文解字》中有一类字同声必同义,形声字往往形声兼会意。近人章炳麟进一步看到同声符的字有相同的语源,认为汉语并非一盘散沙式的发展,并作《文始》以语根来系联汉字,指明语源。王力先生也指出,《说文解字》中有一类会意兼形声字,许慎用术语“亦声”来表示,即声符不仅在声音上近似,在意义上也有关联。王力在前人基础上,将同声符的汉字进一步系联,编写了《同源字典》,较为全面地探讨汉语的语源。从《字说》到《文始》再到《同源字典》,人们一步一步认识到语言发展的规律性,而王安石对声符表义的先期探索,给后世启发良多。
3.3 认识到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注意从实践中解释词义,对后世辞书编纂有借鉴意义
王安石认为,人生而有情,情发而为声,文字可视而知,可听而思,自然之义也。王安石已经意识到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形体是可以识别的,声音是可以传达意义的,而造字的本源也是可以追溯的。这些认识都是比较符合现代语言学中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而文字又是符号的符号理论。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王安石认为在语言中,意义是最重要的。汉字作为一套符号系统,声音是载体,字形是标志,意义是核心。所以,王安石对汉字的解释始终把字义的解说和辨析放在第一位。
王安石还十分重视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向劳动人民学习,从方言口语中获得线索,从而对字词作出正确的解释,这对于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比如最开始他解释《诗经》中“八月剥枣”为“剥枣者,剥其皮而进之,养老故也”。其后来了解到村民们把打枣叫作“扑枣”,才开始认识到先前解释的错误,“剥枣”原来并不是把枣皮剥掉,而是把枣子从树上打下。把枣皮剥下而食,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他随即向皇帝启奏删掉原先错误的解释,可见他对待学术还是十分严谨的。又如他对“飞”字的解释:
王荆公作《字说》,一日踌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妇适伺见,因请其故,公曰:“解飞字未得。”妇曰:“鸟反爪而升也。”公以为然[19]495。
我们知道在造字之初,对于动物类名词,常常是描绘其形状和其最主要的特征。甲骨文中的动物类汉字主要是对动物的侧面进行描绘,并且要选择动物最具区别特征的地方去突出,这样汉字的区别特征才会明显,语言的社会性、符号性才会体现,才能顺利完成交际任务。“飞”字的造字也是如此,描绘了视觉中人们所看到的鸟类飞翔的侧面形象,并且突出了鸟宽大的翅膀和有利的爪子。汉字在隶变之后,字的象形意味减弱,符号性突出,已经很难看出“飞”字造字的象形理据,即使博学如王安石这样的大家在识别“飞”字的原始造字意图上也不敏感,而王安石的“子妇”却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一语点破梦中人。王安石觉得有理,就采纳了她的说解。其实不论鸟是不是反爪,古人造字之初,受制于简陋的书写工具,造字求的是神似,而不是精准地刻画。部分借此而批评王安石穿凿附会的学者显然是有失公允,反倒是王安石并不因人废言的求知精神值得敬佩。
古书由于流传久远,文字在使用过程中假借、通假、借用现象非常普遍,有时候单靠文字的记载,用字面意义来解读古书,不一定能获得正解。这时候从方言和口语中寻求解读的线索不失为一条获得语言真知的途径,因为语言是靠口耳相传的,古人的用字用语习惯必然会在方言土语中有所保留。比如,《字说》中“豝,所谓娄猪,豝,犹娄也”,就是用方言来互训。豝,指母猪,方言中也把母猪叫作“娄猪”,二者都指肥胖的母猪,在古书中娄猪又隐喻不守妇道的妇女。
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之学又叫小学,古代的字书兼有百科全书性质,从《说文》到《尔雅》都辑录了许多名物说解的条目,《字说》也不例外,对名物的说解十分精到。比如对“鸿”这种鸟类,引《易》“随时之义,大矣哉!”,阐述人类赋予这种鸟类独有的社会学意义。在“鹅”字条下引用《禽经》:“鹅见异类,差翅鸣;鸡见同类,拊翅鸣。”通过王安石描述这两种禽类动作行为的细微差异,可见其观察的细致,引用的精当。释“芦”字而兼带说明芦、萑、荻、蒹、葭、菼、苇、薍等字,揭示名物之间的细微差别,以及植物得名的缘由。如:
芦谓之葭,其小曰萑;荻谓之蒹,其小曰苇。其始生曰菼,又谓之薍。荻强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故谓之荻。菼中赤,始生末黑,黑已而赤,故谓之菼。其根旁行,牵揉槃互,其行无辩矣,而又强焉,故又谓之薍。薍之始生,常以无辨,唯其强也,乃能为薍[15]211。
《字说》对我国古代名物考证类字书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科普教学,但这种科普教学是混合在语言文字的学习之中的。孔子说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后世对《诗经》作出训诂,也对其中涉及的名物作出了考证。汉代《尔雅》开创了我国辞书以义归类的编排体系,对同类别名物也作出了大量细致的解释和考证。王安石的《字说》也不例外,从现有辑录的条目来看,涉及很多名物考证条目。《字说》虽后世失传,但在同期或后期的名物考证类专著中,常保留有《字说》对名物独到的说解。陆佃编写《埤雅》《尔雅新义》,常引用《字说》的条目,如:
豺亦兽也,乃能获兽,能胜其类,又知以时祭,可谓才矣[15]208。
南宋罗愿撰《尔雅翼》亦常引用《字说》的说解。沈括也常用《字说》的理论来解字。明代李时珍采集百草,撰著《本草纲目》,书中对药草名义的解释也常引用《字说》,如“生薑”条引用《字说》:“薑,能疆御百邪,故谓之薑。”[15]218“松柏”条引用《字说》:“松柏为百木之长,松犹公也,柏犹伯也,故松从公,柏从白。”[15]202此外,梅膺祚编纂《字汇》和张自烈纂《正字通》,都引用了《字说》的解说。可见,王安石的《字说》对当时以及后世辞书的编纂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 结语
一部《字说》诠解字义不下数千条,而攻击王安石《字说》流传下来的也就几十条,但这几十条的影响极大,以至于后人往往忽略了《字说》中的精华。中国的文字有数万个,要把任何一个字的来龙去脉都解释得合情合理的确很难。站在历史的角度,不能对古人求全责备。王安石之所以创作《字说》是有感于当时人们对汉字知识的欠缺和使用上的混乱。他力图通过阐明汉字的源流演变、剖析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关系来对语言文字使用做出规范。虽然有个别穿凿附会之处,但其基本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王安石晚年以衰朽之身,凭毕生所学,呕心沥血创作《字说》,尽管确有不如人意之处,但绝不是粗劣之作。它总结了当时的语言文字现象,体现了较为先进的语言文字观,保留了很多汉字发展演变中的珍贵语料,也启发了后世辞书的编纂,在我国语言文字研究历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