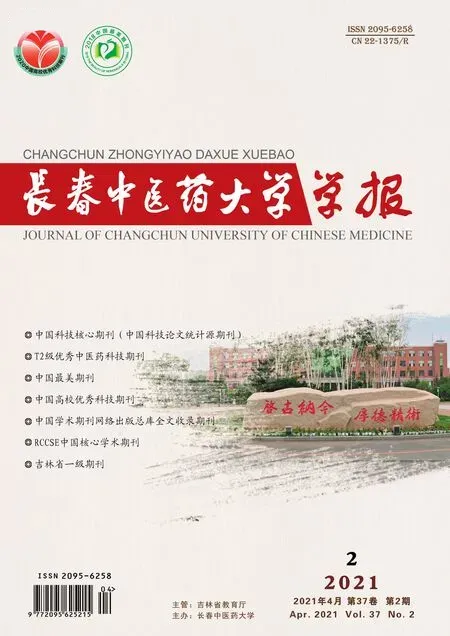《松峰说疫》疫病防治特色
2021-11-29马金玲张文风
魏 岩,马金玲,张文风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松峰说疫》是清代温疫学派主要医家刘奎的代表著作,约撰写于乾隆五十年(即1785 年)[1]。该书是继吴又可《温疫论》后又一部较为全面的温疫学专著,内容丰富详实,共6 卷,分别为述古、论治、杂疫、辨疑、诸方和运气,首创疫病的三疫说,提出“瘟疫者,不过疫中之一症耳,始终感温热之疠气而发,故以瘟疫别之,此外尚有寒疫、杂疫之殊。”明确瘟疫即为温热性质的疫病,疫病非并全部为瘟疫,还有寒疫和杂疫,规范了疫病理论,建立了中医疫病框架;同时还在疫病治疗、预防及小儿疫病防治方面有独到见解,为中医疫病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松峰说疫》一书在疫病的治疗和防治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在治疗上提出疫病治疗最宜通变,首创了“瘟疫统治八法”,并在仲景六经辨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经验,独创“瘟疫六经治法”,针对三阴三阳经传变的瘟疫病机、临床表现、治法及用药进行详细论述;同时还总结了历代医家防治疫病的有效方剂和自创防治疫病新方,专门设立了诸方一卷,记载65 首避瘟方和45 首除瘟方,使用方法除内服法外,还有熏烧、悬挂佩戴、喷鼻取嚏等。该书是历代温疫著作中关于疫病防治论述最为系统的一部著作,深入研究其疫病防治方法及用方用药特色,能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国传统医学对现代急性传染性疾病的临床指导作用,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新发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防治提供可靠借鉴。
1 治疫原则
《松峰说疫》卷二“论治”篇中详细阐述了疫病治疗的原则、方法、疫病杂症治法用药,特别是瘟疫统治八法和瘟疫六经治法,曾一度广为使用。刘奎指出:“惟至于疫,变化莫测,为症多端……临症施治者,最不宜忽也。”疫病复杂多变,“其症则千奇百怪”,临床不易把握,因此治疗上要“舍病治因”,辨清邪气所在部位,“单刀直入,批隙导窾”,切中病机,随宜用药。
瘟疫的发生原因:“盖有因食、因酒、因痰、因惊、因郁、因气、因思水不与、因饮水过多、因过服凉药、因误服温补、因服诸药错误、因信巫祝耽搁……皆当暂舍其所患之瘟,而求其弊,以治其因也。”在审因论治的同时,“再佐以治瘟疫之药始得,非全抛而舍之之谓也。”且以“瘟疫为主”,更要辨清兼证,“治兼之药佐之矣。”这与吴又可所提出的“舍病治药”“舍病治弊”的治疗思想一脉相承。故在治疗过程中,要“必深明乎司天在泉之岁,正气客气之殊,五运六气之微,阴阳四时之异,或亢旱而燥热烦灼,或霖雨而寒湿郁蒸,或忽寒而忽暖,或倏晴而倏阴,或七情之有偏注,或六欲之有慝情,或老少强弱之异质,或富贵贫贱之殊途,细心入理,再加以望闻问切,一一详参”,且“看其人之老少虚实,病之浅深进退”,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体现了瘟疫治疗中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的思想。
2 治疫方法
瘟疫的病因不同,表现各异,治法也各不相同,千变万化。刘奎在书中创造性提出极具特色的“瘟疫统治八法”,采用解毒、助汗、针刮、除秽、涌吐、菴熨、符咒、宜忌八法来祛除病邪,体现了温疫学派以逐邪为第一要义的学术思想。八法中解毒、助汗等方法仍有其实用性。
2.1 解毒
瘟疫的发生以“饥寒辛苦之辈感者居多,年高虚怯之人感之偏重”,都有毒气为患,在未发病时,就有毒气伏藏,而发病之时,毒气发作导致各种症状出现,汗下后余毒往往未尽,提出“毒气与瘟疫相为终始”,因此,治疗以解毒清热为第一大法,但是在药物选择上并不用黄芩、黄连、栀子之类的苦寒药物,而是采用绿豆、金银花等甘寒清透之品解疫毒,并自创2 首新方,一首为金豆解毒煎(金银花、绿豆皮、生甘草、陈皮、蝉蜕),并指出“此方于瘟疫九传中,皆可加减消息用之” 。《古今名方》引蒲辅周经验方,在金豆解毒煎基础上加减,用于瘟疫流行时未病预防或已感染者治疗[2]。另外一首是绿糖饮,将绿豆煮酽汤,加洋糖与饮,冷热随病者之便,以此代茶,渴即与饮,饥则拌糖,并食其豆。可用于瘟疫初终,“乃平易中之最佳最捷方也”,该方用药简洁,易于取材,是“治瘟疫之良剂”。同时,在瘟症杂症治略中被用于瘟疫在表而衄血者。现在很多地区依然应用绿糖饮治疗瘟疫[3]。
2.2 助汗
历代温疫学家都非常重视汗法。吴又可的《温疫论》中将“汗、吐、下”作为瘟疫逐邪治法,戴天章的《广瘟疫论》认为,汗法是治时疫一大法。《松峰说疫》中也认为,不论伤寒还是瘟疫的治疗,汗法都有很大的作用,“汗易出,而邪易散”,强调瘟疫不能强发其汗,否则会加重津伤,故多选用和平无碍的方法。书中“助汗”章节中共载有19 种取汗方法,有传统汤液内服方法,如用白粳米和连须葱头加水煮粥的葱头粳米粥;或用梨、生姜捣汁入童便的姜梨饮;亦有点眼取汗、塞鼻取汗、沐浴等外用法,如用冰片、枯矾、粉草共为细末的点眼取汗方;用麝香、黄连、朱砂、斑蝥共为细末的塞鼻手握出汗方;或用桃枝煎汤沐浴方;或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藁本、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这些方法简便易行,实用性较强。此外,八法中的菴熨法亦是“瘟疫取汗之良方”。特别是针对瘟疫中气虚弱不任用药攻击的患者,用菴熨法治之,可以“滞行邪散,其效如神”。刘奎用生葱、生姜、生萝卜共捣微烂,入锅炒热,用布包熨患处,觉透为度,汗出而愈。
3 治疫方药
对于瘟疫用药,刘奎提出,要“按其脉症”,切中病机,“单刀直入”,且药物不宜过多,“多不过五六味而止”,同时还要根据病人体质、病位深浅、病情轻重而权衡用量。
3.1 立方用药特色
书中卷二列举了瘟疫应用药152 种,包括发表、寒凉、逐邪、温补等方面, 结合瘟疫杂症简方、避瘟方及除瘟方等具体方药应用,现对该书特色药物分析如下。
3.1.1 清热药 在152 味用药中,寒凉药物最多,为42 味,占总药味的27.6%,说明瘟疫以热证为主,热者寒之,清热药在瘟疫治疗中最为常用。而在清热药中又以清热解毒药(15 味,占清热药的35.7%)为多,与刘奎治疗瘟疫以解毒法为第一大法相统一。在清热解毒药物中,刘奎善用生甘草,绿豆衣等,如前提到的金豆解毒煎、绿糖饮及专点伤寒瘟疫的普救五瘟丹、治疗葡萄疫的加减羚羊角散等。刘奎认为,“生甘草解一切毒,入凉剂则能清热,亦能通行十二经”,《药品化义》“甘草,生用凉而泻火,主散表邪,消痈肿,利咽痛,解百药毒,除胃积热,去尿管痛,此甘凉除热之力也” 。朱丹溪云:生甘草大缓诸火邪。现代研究也表明甘草对多种病毒具有抑制作用[4-5]。
清热药使用中,刘奎明确提出:“治瘟疫慎用古方大寒剂”,如黄连、黄柏、龙胆草、苦参大苦大寒等药,皆当慎用。刘奎认为,今人体质素秉薄弱,不耐寒凉,加之瘟疫之火,因邪而生,邪散而火自退,若用大寒之品直折其火,还未祛邪却先受寒凉之祸。3.1.2 补虚药 瘟疫用药中第二位为温补药,共20味,占总药味的13.2%,体现了瘟疫治疗过程中在逐邪为主外,还兼顾扶正。关于补虚药的应用,刘奎提出,“疫病所用补药,总以人参为最,以其能大补元气。加入解表药中而汗易出,加入攻里药中而阴不亡”,但一般不用黄芪、白术之类,同时可用山西潞安府党参代替人参,以扶正而除邪。
3.1.3 解表药 瘟疫用药中第三位为解表药,共19味。其中以浮萍为首位,浮萍味甘性寒,为解表剂,刘奎认为,瘟疫发汗,莫过于浮萍,“其性凉散,入肺经,达皮肤,发汗甚于麻黄”。提出以浮萍代麻黄的思想,可谓独树一帜,给后人很大的启示。书中共有10 首以浮萍为主组成的方剂,如治疗瘟疫太阳头项痛的元霜丹,治疗阳明泄泻的浮萍葛根芍药汤,治疗太阴腹满嗌干的浮萍地黄汤等。
3.2 具体方药应用
由于疫病本身病种较多,即使同一病种由于地域、患病者体质、疾病所处不同病变阶段等因素不同,故疫病治疗中所涉及的药物种类较多,范围较广,医家常常不拘泥于某方某药,即所谓“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来无方也”。就其药物使用方法来看,大多以传统汤液内服为主,但《松峰说疫》在疫病防治中采用了较多颇具特色的外治法,如熏烧、佩戴、塞鼻、点眼、噙化、手握、煎汤沐浴、探吐等,其中用熏烧和佩戴除秽祛邪的方法对现今急性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有借鉴意义。
3.2.1 熏烧 熏烧是指通过熏烧药物,使其烟气上熏以除秽祛疫的一种外用方法。此法制作简单、取效迅速,是《松峰说疫》最为广泛运用的外用方法。在《松峰说疫·卷之二》“除秽”中,刘奎创制了苍降反魂香,即将苍术和降真香等分研末,揉入艾叶内熏烧。苍术芳香燥湿除秽;降香为诸香之首,除邪。二者合用芳香辟秽以祛疫。除此之外,书中还有16 首熏烧方用来预防瘟疫,如避瘟方中所记载的5 首避瘟丹,均是通过熏烧的方法来“避一切秽恶邪气”,可以每用一丸焚之,良久又焚一丸,略有香气即妙;或于正月初一平旦,焚一炷避除一岁瘟疫邪气;或五六月,于久无居住的官舍旅馆终日焚之,可以避瘟。
熏烧所用药物主要有苍术、降香、艾叶、乳香、细辛、川芎等。在《云南发布新版人感染禽流感中医药预防方案》提出,可用艾叶等芳香化浊类中药熏烧以除瘴避秽[6]。现代研究也证实,苍术的有效成分苍术酮可以显著缓解甲型流感病毒诱导的损伤,从而起到防治流感的作用[7-8];同时有人使用苍术艾叶香熏蒸进行空气消毒,结果证明,该法能有效杀灭空气中的细菌,并对人体无不良作用[9]。
3.2.2 佩戴 佩戴是指在将芳香除秽类中药用绢布或绛囊包裹制成香囊随身佩戴或将其悬挂于住所,以起到预防或治疗疫病的作用。此法简单实用,且装饰美观,可作为防治瘟疫的常用方法。书中在“除秽”章节中制定新方除秽靖瘟丹,将苍术、降真香、川芎等35 味药物研磨成末装入绛囊,约二三钱,阖家分带,起到已病易愈,未病不染的作用。在避瘟方中也有老君神明散、务成子萤火丸、避瘟方、藜芦散等复方用来佩带或悬挂来预防瘟疫。如务成子萤火丸用红绸缝三角囊盛五丸,可带左臂上,也可挂于门户,以避瘟疾恶气。此外,亦可用单味药物悬挂或佩戴,如将马蹄屑用绛囊盛好佩戴,可预防热病;或悬挂马尾松枝,可免瘟疫。现代研究中,李立等[10]研究发现,通过佩戴含有芳香类中药的香囊能够减低流感症状发生率,改善局部咽痛、乏力、咳嗽等症状,能够预防季节性流行性感冒。
这两种防治疫病的外用方法,简便易行,可以将佩戴方或者悬挂方制成精美的装饰品使用,将熏烧方制成蚊香、熏香等使用,这样既易于人们接受,又能够更好的发挥其防治疫病。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制定了由苍术、艾叶等组成的防感香囊,随身佩戴,或挂于车内以起到预防作用[11]。
4 防疫措施
中医历来重视疫病的预防,《内经》中就将“正气存内”和“避其毒气”作为疫病预防的重要原则,在其思想影响下,温疫学派也在疫病的预防方面格外重视,《松峰说疫》中除了上述有关药物预防瘟疫的基础上,也就截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实施隔离、注重消毒等提出具体防疫措施。
刘奎提出,“试观入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以是知青蝇所聚之处,皆疫邪秽气之所钟也”,说明青蝇是疫病的传播媒介,故在“避瘟方”中记载逐蝇祛疫法,相传极效。同时注意对饮用水及居住处进行消毒,如在时瘟疫流行时期,在水缸内投黑豆一握,或将贯众、苍术浸水用,或将赤小豆、糯米浸水缸中,每日取水用,则全家无恙。此外,刘奎也比较注重自身防护,提出一些入病家不染方,如以麻油涂鼻孔后入瘟加,出再取嚏,则不染。这些有创见性的防护措施和认识,对后世医家预防疫病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和可靠借鉴。
5 瘟疫的宜忌和善后
在瘟疫治疗过程中,刘奎亦非常重视瘟疫的宜忌和善后,提出“不知所宜,不能以速愈;不知所忌,不足以益疾。”并给出瘟疫预防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衣被不可太暖,宁可稍薄;不可恼怒;食莫过饱等。同时,也应注意疫病后期调养,因此,此时“气血苟不充足”,若不注重调养,则“酿成终身之患”。在调养过程中一是忌淫欲,以防止“积损成劳,尫羸损寿”,二是忌劳顿以防“疲弊筋力,未老先衰”,三是忌忍饥以防“脾胃之病成”。
中华民族在抗击疫病的悠久历史中,不但总结了丰富而独特的疫病防治理论,还积累了许多宝贵而实用的经验。《松峰说疫》不但创立疫病三疫说,完善了疫病理论体系,对疫病的防治,还提出瘟疫统治八法,瘟疫应用药、避瘟方、除瘟方等创新性内容,为后世医家防治疫病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解毒、助汗等逐邪方法,熏烧、佩戴等外用手段,为现今临床防治急性传染性疾病提供了中医思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应始终保持着传承传统中医的特色,又应根据复杂多变的传染病情况,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发挥中医抗疫优势,使中医药更好为人民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