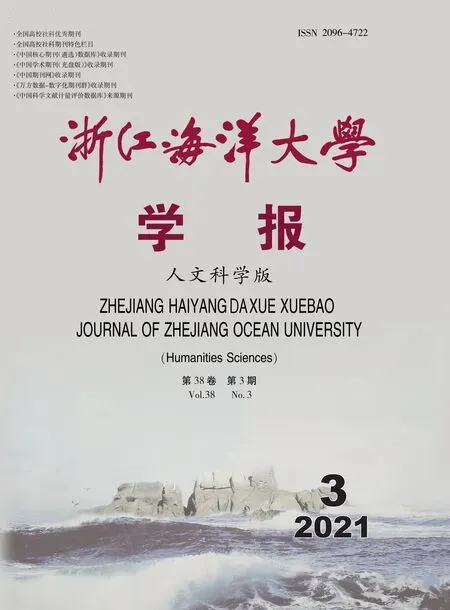王修植与盛宣怀往来函札五通考释
2021-11-29石一民
石一民
(浙江海洋大学 图书馆,浙江 舟山 316022)
王修植(1860—1902),字菀生,号俨庵,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二品衔直隶补用道。[1]光绪二十年(1894)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896—1901)任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今天津大学)总办,其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897—1900)兼任卢汉铁路学堂总办,期间在两校的招生、延请教习、教学管理诸环节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2]然有关王修植的史料稀缺且分散,论者寥寥。在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简称“盛档”)中,保存有王修植与盛宣怀往来函札16 通,其中王修植致盛宣怀函札14 通,盛宣怀致王修植函札2 通,这些函札绝大多数均未公开刊行过。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次沂,别署愚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中国第一代实业家、教育家,曾先后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是王修植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的官员。“盛档”所见16 通王修植与盛宣怀往来函札,其最早时间是1895 年12 月,最晚时间是1901 年;其中1895 年2 通,1897 年4 通,1898 年4 通,1899 年3 通,1900 年1 通,1901 年2 通。这些函札为了解王修植与盛宣怀的交往以及北洋大学堂的早期历史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兹将其中5通未刊函札整理出来,考释人事,以飨同好。
一、王修植致盛宣怀函(一)
杏翁方伯大人阁下:
赐书并隆赙二十金、缎幛一悬,降受拜登,存亡均感。日维起居万福。弟遭逢大故,本应守庐读礼,稍遂哀思。无如亲老家贫,尚须饥驱四境,业于月初拜墓而行。抵申后闻从者南旋在即,满拟少住十日,藉以亲领训词,嗣闻台旌须于二十日由津启行,榜人以河冰相促,急不能待,遂于十七日附轮北上,五角六张,何相遇之疏耶?前委拟《格致书院章程》,弟哀毁之余,思绪恶劣,拉杂书此,芜谬实多,于九月初函致钱少云兄转呈,谅经钧览。此事虽细,实为今日开倡风气之先声。夫今日风气之不开,惟士大夫为尤甚;而中国受病最深最毒之处,实由于此。明公先觉觉民,首以学堂、书院为要务,本树人之义,运救世之心,此正四百兆黄人所引领仰望者也。未审一切规模,秋冬以来有否楚楚部署?云泥既左,不获追随鞭蹬,渥领谠言,惆怅临风,良用歉仄。公余少暇,尚乞时赐箴规,无任感盼。肃此留呈,恭请崇安。伏惟朗鉴不宣。制愚弟王修植顿首。[3]050665
案:本函未署年月日。信封署“内函敬求转呈津海关道盛大人钧启,修植拜托”“招商局代投”,信封上有收信人印注:“光绪貳拾壹年拾壹月廿日到”。可见本函作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前,时盛宣怀任津海关道兼北洋大学堂督办。函中云“弟遭逢大故”,指王修植遭逢母丧。王修植在本年九月初致钱少云函中亦提及此事:“弟自遭大故,心绪恶劣万分,于前月初五日返里。先慈丧葬各事,至月杪甫楚楚就绪。……弟拟于十月初即行买棹来津。”落款书“九月初五日”。[3]044290据知王修植因母亲去世,于本年八月初五日返回定海故里,到月底丧事料理完毕。本函云“业于月初拜墓而行”,与上引致钱少云函中所云“弟拟于十月初即行买棹来津”时间吻合,说明王修植于十月初离开定海。途经上海时,听说盛宣怀不久将从天津来沪,为见盛一面,打算在沪再逗留几天,但后来又听说盛“须于二十日由津启行”,船夫“以河冰相促,急不能待”,遂于十月十七日乘轮船北上天津。据《王文韶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二十三日记:“杏孙(指盛宣怀)辞行赴沪”,[4]920可见盛宣怀二十三日始由天津启行,较预定时间又晚了三天。据本函内“遂于十七日附轮北上”“肃此留呈”等句,以及王修植回天津后于本年十一月十六日致盛宣怀函中称“下走北上濒行时,肃留芜椾,托钟鹤笙兄转呈,谅经钧览”,[3]050664可进一步判断本函作于王修植自沪赴津前一天或当天,于临行时留下此函,托钟天纬(字鹤笙)转交盛宣怀。故本函的写作时间当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十六日或十七日。函末署“制”,因作于丁忧之时。
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宣怀曾计划在天津创办格致书院。本年八月初七日钟天纬致函盛宣怀:“王菀生太史丁艰过沪,业已晤谈。据云,吾师欲开格致书院,仍照天纬原议,以出题考课为纲,以翻译格致新报、泰西政治诸书及考求工艺,给以专利凭据为目,自是正办,无任欣慰。”[5]由本函可知,盛宣怀曾委托王修植编拟《格致书院章程》。王修植在定海丁忧期间拟就后,于九月初五日致函钱少云转呈盛宣怀,函中告以“前承杏翁观察委拟《格致书院章程》,蹉跎至今,昨甫草草属稿,率尔操觚,诸多挂漏,尚乞高明削正,再行转呈杏翁”,[3]044290说的正是此事。王修植编拟的《格致书院章程》迄今仍保存在“盛档”中,档案索取号044577-2。
王修植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任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总办后,与学堂创办人盛宣怀频有联络,自无庸赘言。然本函表明,最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和盛宣怀的关系就已很密切。盛宣怀不仅是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人,还曾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至次年九月任该校督办,王修植能出任该校总办一职,当与盛宣怀的提携是分不开的,此前他是北洋水师学堂会办。此外,从本函还可知道,王修植与钱少云有交往。钱少云(1853—?),名鑅,字少云(一作绍云),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光绪七年(1881)举人。时为直隶候补道,供职海关道署。历任津榆铁路会办、芦保铁路总办等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至八月曾短暂出任北洋大学堂总办。
二、王修植致盛宣怀函(二)
杏翁奉常大人阁下:
前肃贺椷,计尘霁览。韶华阅半,春寒犹劲,伏维兴居曼福,摄卫咸宜,幸甚幸甚!晚自去冬接办头等学堂,已逾三月,历验各学生所习,通晓西学颇不乏人。惟于中国文字,求其斐然可观者,殊觉寥寥。因添购《东莱博议》及字典等书,令汉教习加功讲解。查此等学生,前系洋教习招取,故于中学茫无头绪,今虽极力挽回,恐非二三年不能睹其成效。至二等学堂汉文功课,前奉钧谕,命晚协同照料,遵经会同蔡令兆基传知各教习,加意训迪。查该堂惟四班学生于洋汉文均有门径,再加精进,将来可成中西兼全之材,足以仰副栽培厚意。晚视事以来,每日进堂一次,除督率各教习认真训导外,已无余事,堂中例行公牍亦形清简。自问年力正强,平时于欧西新学及中外交涉事宜亦颇留心讲肄,辄意得所,藉手表见于时,惟兹壮志,久在高明洞鉴之中。顷闻津榆铁路总办黄花农观察昨已面禀夔帅,力辞差使,想经咨商阁下,另行派员接办。晚值此暇晷,正思习勤,且张戟门观察与晚谊属同乡,颇称契洽,和衷共济,当不至有所龃龉。夙蒙垂爱,用敢自媒,驱之策之,惟所命焉。再,关外铁路学堂向归铁路总办遥制,惟开创之时,既未妥立章程,又学堂相距较远,不免因兼辖而忽之,浸成鞭长莫及之势,以致该堂学生洋汉文俱无足取。似此有名无实,于事何裨?晚意拟请将铁路学堂并归大学堂,一切课程得以一律整顿,所有经费亦可藉资贴补,成材节用,庶几两得其宜。是否有当,并乞裁示。专肃,祗请荩安,统希澄察。晚生王修植顿首。[3]044215
案:本函未署年月日。信封署“寄上海二马路宝源祥投呈太常寺少堂盛大人勋启”“天津王谨缄”,收信人印注“光绪貳拾叁年二月十七日到”。信封盖有天津邮戳,日期显示“MAR 15 1897”,据知本函写作时间最迟不会晚于1897 年3 月15 日,最有可能作于信函投递前一日,即1897 年3 月14 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时盛宣怀在上海,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太常寺少卿。王修植写作本函时,已担任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总办,但他任此职的具体时间史无明文。函中谓“晚自去冬接办头等学堂,已逾三月”云云;又,王修植本月另有一通致盛宣怀函,落款书“二月二十五”,内有“顾视事以来,于兹四月耳”“上年十一月中,修植牌示诸生”两句,[3]044214综合两函所述,可推断王修植始任总办时间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二十五日前后。北洋大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设有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各一所,分别相当于大学本科和大学预科。学校开办之初,头等学堂总办为伍廷芳,伍氏出任驻美公使后,王修植始继任此职。据史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十九日,清廷颁旨,伍廷芳充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6]又,《王文韶日记》本年十一月初八日记:“伍秩庸(廷芳)以候选道加四品卿衔出使美国,过此一谈,亦行色匆匆也。”[4]975可见,伍廷芳在出使美国前,还曾于十一月到过天津,约于本月初八日离开天津,自此完全脱离了北洋大学堂。据此,王修植就任总办一职,当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十九日之后、十一月初八日之前,与上文所推断的时间相吻合。
函中云:“历验各学生所习,通晓西学颇不乏人。惟于中国文字,求其斐然可观者,殊觉寥寥。……查此等学生,前系洋教习招取,故于中学茫无头绪,今虽极力挽回,恐非二三年不能睹其成效。”从这段话来看,北洋大学堂之前在招生和教学上有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当时有很多学生系洋教习招取,招生考试时注重“西学”,故这些学生“中学”基础较差。王修植出任总办后,极力主张“西学”“中学”并重,为此,“添购《东莱博议》及字典等书,令汉教习加功讲解”,但他又认为要取得成效,至少需要二三年的时间。
由本函可知,当时作为头等学堂总办的王修植,其主要工作任务有二:一是“督率各教习认真训导”;二是处理“堂中例行公牍”。此外,从“二等学堂汉文功课,前奉钧谕命晚协同照料,遵经会同蔡令兆基传知各教习,加意训迪”句看,盛宣怀不仅让王修植“照料”头等学堂的汉文功课,即担任头等学堂汉文总教习,还让其“协同照料”二等学堂的汉文功课。但王修植似乎办事效率很高,处理完这些事务后还有余力和时间,听说津榆铁路总办黄建筦已提出辞职,便向盛宣怀自荐,希望能兼任津榆铁路总办一职。函中的“黄花农”“张戟门”分别指黄建筦(字花农、华农)和张振棨(字戟门),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 年1 月)津榆铁路划归中国铁路总公司时,盛宣怀便派黄、张两人接管。张振棨是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故王修植以同乡相称。“夔帅”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字夔石)。
在本函的最后,王修植建议将前一年底成立的山海关铁路学堂(即函中所云“关外铁路学堂”)归并北洋大学堂,理由是山海关铁路学堂自成立后一直归津榆铁路总办管辖,但该学堂与津榆铁路总局相距较远,管理不便,有鞭长莫及之感;若将其并入北洋大学堂,则“一切课程得以一律整顿,所有经费亦可藉资贴补,成材节用,庶几两得其宜”。此建议不久便成为事实。
三、盛宣怀致王修植函(一)
宛生仁兄大人阁下:
昨奉惠书,惓存良至,感何可任!敬审育英励才,勋福俱懋,甚副颂仰。津堂以西学定班次,头等学生由洋教习招选,但求合洋课之班,不暇问中学之本;二等前三班病亦由此,皆势使然也。今令补读中书,逆流推挽,功效较迟。执事大雅扶轮,督课有法,但使三年有成,亦未为晚矣。西国以学堂为绝大经济,理其事者常殚精嫥力,以穷年毕世为期。执事槃才远志,宜其目无全牛。惟华农观察虽辞路差,以其情形熟习,上下灵通,古榆归并之始,卢保开办之初,头绪千万,资其经画,先已商由夔帅坚留,换羽移宫,无是事也。铁路学堂并归大学堂,自是正办,丁总教习早有斯议,曾□□□①章程,当再具牍分行耳。专复,敬请台安。诸希朗照,不备。愚弟顿首。已。[3]044586-3
案:现存盛宣怀致王修植函,“盛档”中仅见2 通,其中之一即为本函,弥足珍贵。本函未署年月,从函中内容来看,本函为答复王修植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来函而作;而就函中“昨奉惠书”句来推断,其写作时间当在本年二月十七日盛宣怀收到王修植函后不久。“已”疑为“巳”字之讹写,指巳日,则盛的复函盖作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二十二日,此日为辛巳日。
从盛的回复看,王修植“补读中书”的做法得到了盛宣怀的肯定,然对王修植提出的兼职津榆铁路的要求,盛称已坚留黄建筦,并无换人之事而予以婉拒。至于王修植提出的将山海关铁路学堂归并北洋大学堂的建议,盛宣怀其实亦早有此意。仅仅过了一月,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盛宣怀便令山海关铁路学堂归并北洋大学堂,并派王修植兼管,于本年五月十一日正式开课。[3]097688-36然历时不久,两校学生间发生摩擦,新任津榆铁路督办胡燏棻以此为由提出迁校,山海关铁路学堂遂于本年十月二十一日迁回山海关办学。[7]与此同时,盛宣怀决定在北洋大学堂内自办卢汉铁路学堂,由王修植兼任该学堂总办,于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开学。[8]
四、盛宣怀致王修植函(二)
宛生仁兄大人阁下:
月前匆促南旋,远承枉送。屏营衢路,眷恋良殷。顷奉惠函,敬谂动定绥和,荩劳懋著,慰如远颂。承寄学堂课卷二百零五本,敬已收悉,容即详加批阅,再行寄收。惟堂中派往日本之高等学生共计几名?祈速见示,并加考语,以凭核办。南洋公学已咨送六名,然少一名额,已不能补,殊可怅也。
阁下极承荣仲相优待,所有直属各学堂、农工商局办理情形,并大差如何布置?伊藤如何接待?伊藤此次来华,是否真心联络中国,互相维护?望随时详细函示,弟颇愿闻之也。专复,敬请台安。诸惟亮察不具。愚弟盛顿首,七月廿八。[3]044423-3
案:本函未署年份,系日为“七月廿八”,函中提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事,可推断本函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八日,时伊藤博文正在天津访问。从函中所云“顷奉惠函”“专复”看,本函系为答复王修植来函而作,但王之原函在“盛档”中已佚失。
函中云:“承寄学堂课卷二百零五本,敬已收悉,容即详加批阅,再行寄收。”在“再行寄收”四字处,原为“酌给花红,以示奖励”八字,后划掉改为“再行寄收”。由此可见,当时盛宣怀虽已不再担任北洋大学堂督办,但王修植仍将学生中文课卷寄给在上海的盛批阅,评出优劣,作为学生评优奖励的依据。王修植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对盛宣怀的尊重,但从中亦说明盛虽离开了天津,却并未移交北洋大学堂事务,对该校仍然关心有加。据“盛档”等诸多史料记载,王修植、蔡绍基(二等学堂总办)、丁家立(总教习)等人,凡遇学堂人事任命、中外教习聘定、经费收支以及学生招考、评优和毕业安排等事务,均书函请禀盛宣怀。[9-10]本函提及的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之事,亦可说明这一点。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接到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学生游学日本的上谕后,饬令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迅速核办。盛宣怀在本函中询问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派往日本留学学生人数,“祈速见示,并加考语,以凭核办”,可见北洋大学堂赴日留学名单需报盛宣怀核准。本函还提及南洋公学本年将派遣6 名学生赴日本留学,也为中国早期留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
函中所云“阁下极承荣仲相优待”,“荣仲相”指荣禄。荣禄,字仲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至八月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盛宣怀此言合乎实情,荣禄任直隶总督期间,对王修植极为重用,陆续委任其办理御路、天津行宫操场工程、农工商局开办事宜,以及改书院为学堂、接待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等一系列重大事务。[11]函中提及的“大差”即指天津行宫、操场工程,属于慈禧太后、光绪帝至天津阅兵的筹备。盛宣怀对上述天津政事颇为关注,故在函中询及,并希望王修植“随时详细函示”,从中亦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
五、王修植致盛宣怀函(三)
谨禀大人阁下:
敬禀者,本月初十日接奉钧谕,敬聆壹是。所有职堂派往日本学生,二班、三班、四班均各挑选一名,计共三名,业经备文,详请鉴核。一俟奉到训示,自当遵办。
日相伊藤于前月二十六日抵津,荣相派职道先期至塘沽接迓,水师营务处预设行馆。次日荣相在北洋医学堂设席款待,二十九日仍派职道送至马家堡。伊侯此次来华,未奉国书,究是游客,今一例优待,与使臣无甚区别,深恐各国游历人员援以为例,此后难为继耳。当职道与伊藤相见时,渠即以“中国如有咨询借助之处,甚愿竭力相助”为言,词意肫挚,似属真情。盖旅大之事早伏于马关一盟,阋墙而召外侮操戈者,当有悔心矣。
天津行宫、操场工程业已过半,现闻有改调南苑阅操之说,然未奉谕旨,一切仍赶紧兴作,敬谨豫备。
津门各书院,前奉廷旨严催,已议归并,改为高等、中等及小学堂三所。农工商分局亦于前月十六日暂假朝鲜公所设局,正在会议商办。而朝局忽变,是以概从缓图,容俟将来举办稍有端倪,谨当随时禀闻。专肃禀复,祗请钧安,伏乞垂鉴。职道王修植谨禀。[3]044423-1
案:本函未署年月日。信封署“内禀函寄上海二马路宝源祥”“督办芦汉铁路大臣行台盛大人钧启”“北洋大学堂谨缄”,收信人印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到”。信封盖有天津邮戳,日期显示“SEP 29 98”,据知本函写作时间最迟不晚于1898 年9 月29 日,最有可能作于信函投递前一日,即1898 年9 月28 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时戊戌政变已发生,故函中有“朝局忽变”之语。
本函为复盛宣怀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来函而作,信端云“本月初十日接奉钧谕”一语,亦可佐证,盛函见上文。盛宣怀在函中询及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派往日本留学学生人数,王修植告以“职堂(指头等学堂)派往日本学生,二班、三班、四班均各挑选一名,计共三名”。这3 名学生都被派遣到日本的著名学府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在日本文部省文书课明治三十二年(1899)第861 号文件的两个附件中,保存有这3 名学生的有关信息:
附件一中记载:
黎科,二十岁,广东新会人;
张煜全,十九岁,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
王建组,二十一岁,广东番禺人。
附件二中记载:
黎科,为天津大学一级生,八年英语修了,学习土木科;
张煜全,为天津大学二级生,八年英语修了,学习政治科;
王建组,为天津大学二级生,八年英语修了,学习政治科。[12]
这次北洋大学堂派遣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学生,除上列头等学堂黎科等3 名学生外,还有二等学堂张奎等3 名学生,总计6 名,这是北洋大学堂首次派遣学生赴日留学。同期留日的学生,还有来自上海南洋公学、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储材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和湖北自强学堂等学校。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统计1898 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共18 人,[13]这数字显然有误。如上所述,本年仅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就各派遣了6 名学生;此外据有关史料记载,上海广方言馆派遣了6 名学生,江南储材学堂派遣了7 名学生,江南水师学堂派遣了1 名学生,[14]则仅以上学校就共派遣了26 名学生赴日本留学。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天津行宫操场工程及当时天津各学堂、农工商局开办情形,《国闻报》等报纸亦有报道,但本函所述系作者亲身经历,真实可信,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函中云:“天津行宫、操场工程业已过半,现闻有改调南苑阅操之说,然未奉谕旨,一切仍赶紧兴作,敬谨豫备。”可见,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三日,天津行宫、操场工程的施工仍在紧张进行中。次日,清廷发布上谕,取消原定九月之天津阅兵。[15]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又发布上谕,命清军四大主力部队之一董福祥部甘军主力“即行移扎南苑,认真操练,以便简派王大臣随时校阅,俾成劲旅”[16]。同日,工科给事中张仲炘就英人以保护使馆为名拟派兵进京一事奏称:“臣思前次谕旨停止巡幸天津,而于南苑阅操一节并未声叙。拟请宣谕,酌调董军数营或聂军、袁军数营,驰赴南苑驰札,听候简阅,一面密饬戒备,有警即援。届期仍请钦派王大臣前往校阅,以掩外人耳目,庶几人不惊惶而防范益密矣。”[17]据此,甘军主力开赴南苑,应与当时英、德、俄三国军队进入北京的行动有关。然据本函可知,在八月十四日发布取消天津阅兵上谕之前,已有取消阅兵、受阅部队改调南苑阅操之传闻。张折中所云“前次谕旨停止巡幸天津,而于南苑阅操一节并未声叙”,亦可证明此前已有“南苑阅操”之说。
注释:
① 此三字原文字迹潦草,不易识读。观其字形,极似“据拟送”三字,然未敢肯定,故以“□□□”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