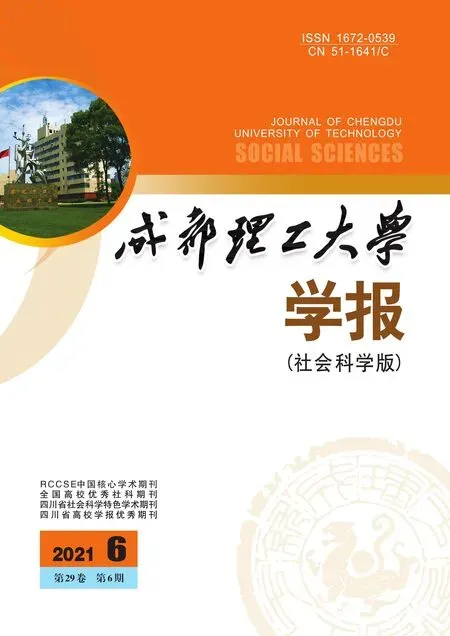方以智的理一分殊诠释学路径探析
2021-11-29凌绅燊
凌绅燊
(1.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阳 550025;2.江西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新余 338000)
方以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现代学人多认为其成就可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相提并论。近年,随着方以智著作的整理、出版,学界对方以智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热情,主要在易学思想、三教关系、性论、会通中西等方面成果丰富,然方以智思想中较有代表的理一分殊之特征,学界研究较少,本文便从此处着手以期对方以智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一、理一分殊溯源
理一分殊是中国思想史上对道体进行探索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易传》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304,又讲“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1]289,可谓是理一分殊思想的重要依证。然此命题的提出是在宋代。关于理一分殊,程颐说道:“《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2]以此来对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与墨氏二本无分的异趣进行了说明。朱熹对其的观点较为认同,并说道: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3]410
其下又说道:
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牿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3]410
太极是所以然者,是万事万物产生之依据,“太极生两仪”,“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虽然不同,然追其原始,受阴阳五行之气而生却是相同,即所谓理一。天道流行于个体,使万物各得其宜,便出现了种种不同,也即是所谓万殊。理一而万殊,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亦不至于墨氏兼爱无父之弊。万殊而理一,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亦“不牿于为我之私”。可见掌握理一分殊之精髓对于避免“兼爱”“为我”有重要之意义。朱熹所就学之李侗曾对朱熹说:“而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4]可以看出,李侗将理一分殊作为区分儒学与异端的标志。
理一分殊思想对方以智的影响非常之大,其对理一分殊的运用主要集中在“道”“性”“教”三个方面,此三方面是与其对《中庸》的重视分不开的,其认为“《中庸》以三句约万理矣”[5]15,此三句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6]。依此方以智将理一分殊运用得活灵活现,以下对此逐一释之。
二、理一分殊在“道”中之运用
《易传》中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268-269,又讲“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即是道,两仪即是阴阳。方以智在对道的阐述上主要从太极的普遍性与化生的角度来进行,由此将太极与阴阳的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而这其中理一分殊思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太极之普遍性
方以智在其著作中多有提到“太极”,当然在其诸多哲学概念中有“公因”“公心”“至善”“所以”等,乍一看似乎和“太极”无异,但究其实际便会发现此诸概念为针对“各一理”之理而发,而“太极”则是针对“共一理”之理而发,此诸概念可谓是方以智揭示“太极”之理的不同表达,可见他们与“太极”之间不能简单等同。从易学本身来看太极,太极无声无臭,不可用有无言之,也不能随意用图像来表示,但是对易学的解读又不得不借助简洁明了的图像来辅助语言诠释。周敦颐之后的学者从对所传之《太极图》进行的解读来看,太极可以以“圜(圆)象”来进行表示,但是不能就此便将太极本身视为“圜(圆)象”。方以智认为“万有万无,莫非太极”[7]120,其又有“两间皆气也,而所以为气者在其中,即万物共一太极,而物物各一太极也”[8]1210之说,“万物共一太极”“物物各一太极”可见在方以智那里太极是普遍存在的。“太极”是两间之所以然,他决定着鸿蒙开辟以及古今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是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太极无不冒,若要再追究下去则有不得已而命之者,则其“原自历然”,实则太极即是“所以”,正如“先统后后亦先,体统用用即体矣。以故新其号曰太极,愚醒之曰太无,而实之曰所以”[9]94一样,其借助“所以”来揭示太极的本质。太极永恒存在,永不改变其作为万事万物之所以然的本质属性。
太极以一切法、一切物为护身符,故太极为都符。太极最善逃,而人不能逃,此太极之所以毒也。彼谤太极、驾太极之上以自逃者,蚤(早)已为太极所藏,而彼不知也。彼乌知呼“太极”者何?呼“天地”者何?呼“易”者何?呼“物”者何?呼“心”者何?同在此中,随呼即是,不呼亦是。[9]289
太极寓于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表现形式,太极又为万物之体,为“都符”即总符,人不能以一事一物来限量太极,正如不可以一事一物来限量圣人一般。“太极最善逃”,即是太极不局限于自身又不得不通过万物来表现,太极藏于天地万物之中,虽然不可见,“彼谤太极、驾太极之上以自逃者,蚤(早)已为太极所藏,而彼不知也”,但是人又处处在其规范、笼罩下。“彼乌知呼‘太极’者何?呼‘天地’者何?呼‘易’者何?呼‘物’者何?呼‘心’者何?同在此中,随呼即是,不呼亦是。”此“太极”“天地”“易”“物”“心”诸称呼,看似不同,然则所指实一。又:
太极也,精一也,时中也,混成也,环中也,真如也,圆相也,皆一心也,皆一宗也,因时设施异耳。各有方言,各记成书,各有称谓。此尊此之称谓,彼尊彼之称谓,各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则何不信天地本无此称谓,而可以自我称谓之耶?何不信天地本无法,而可以自我凭空一画画出耶?[9]30
“太极也,精一也,时中也,混成也,环中也,真如也,圆相也,皆一心也,皆一宗也,因时设施异耳”,此种种称呼虽都是对宇宙本体的称谓,然究其实际,所指皆一,因时而异。各有其方言,“各记成书”,又各有称谓,此尊此,彼尊彼,“各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追究天地之始,虽有物而无名,物实存,名随人类社会发展而有,然不同之地,不同之时其名亦有所异,然究其实际则为一,不通称谓则乱矣。
可知,从“所以”上来讲,太极具有理一的特点,从“因时设施”上来讲,其又具有分殊性,正如前所说“万物共一太极”“物物各一太极”,太极普遍存在,同时亦体现了理一分殊之原则。
(二)一与二
“太极”是作为万事万物之本体的绝对性存在的,其实现是靠自身的衍演来展现的,方以智将此称为“衍古太极”,“太极老翁尝以无所得之围谋必不免之范,若曰不可见者,人何以见?应以见载不见。于是乎作费藏隐之器,授之天地,而自碎其身,以为之用”[7]135,认为太极若要显现其自身“不可见”的本性,便要“自碎其身”来发用其体,此又表现为逐层递进然同时又是步步回归的过程。
方以智将“大一”比作太极,将《礼运》中“大一”与“天地”比作太极与两仪:“智曰:《礼运》曰,礼本于大一,分为天地,即太极两仪也。……故自一至万谓之大两,而太极者大一也。大两即大一,而不妨分之以为用。”[8]9“大一”必然要分为天地两端,对于一切阴阳和合之物来讲,莫大于天地,对于“太极”的逻辑演变法则实际上也是事物的演变法则,正所谓“万物共一太极,而物物各一太极也”,所以太极的“一而二”模式也适用于世间一切物,也即是说任何事物莫不在进行“一而二”的演变模式。太极不断地一分为二,也说明了这正是表现太极为“大一”的必需条件,这也显示了太极的“合-分”的意蕴。
太极虽在不断进行“合-分”的模式,然其“分”后所形成的两端亦有侧重:
衍古太极者,始皆阳而无阴,阳之所不足处,则为阴,盖主阳也。圣人曰:初不得谓之二,又不得谓之一;一阴而一阳,一阴即一阳……当阴含阳之时,亦重阳也;当阳冲阴而包之之时,亦重阳也。自此对待相交而生生不已,皆阳统阴,犹天统地、夫统妻、君统臣也。[9]100
对于太极衍演来讲,“始皆阳而无阴,阳之所不足处,则为阴”,为“主阳”。圣人立教对于初始“不得谓之二”,又“不得谓之一”,“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10]4“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10]4实现本能即阴,而所以成即阳,说太极要不落阴阳,不离阴阳,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重阳”者,说明在太极分为阴阳两端之后,太极之两端亦有主次,所以有主次,“圣教惟在善用其当有者”[8]3耳。方以智在立说的过程中对于此可以说非常重视,也使得其思想特征由此而显。其认为:“大要明体则暗用,明用则暗体,双明即双暗,遂有三表、三遮。”[7]20凸显体则会使用不显,凸显用则会使体不显,体用都凸显便会体用都不显。对于世间之说教亦如此,往往强调一方面会使另一方面不显,强调另一方面会使这一方面不显,两方面都强调会使两方面都不显。“故《易》无体,因谓之无体之体耳。总之,即用是体,而逼人亲见至体之方便,原不可少。”[7]27《易》无体,“即用是体”,“逼人亲见至体之方便”。其认为:“人泥于二,不能见一。故掩画后之对待,以从画前之绝待,借设蜃楼,夺人俗见耳。一用于二,即二是一,宁舍画后而有画前之洸洋可执哉?”[7]目录2人不能胶泥于二,这样会使一不能见。一用于二,通过二便可探究一,即二是一,舍弃画后想要去探究画前是不足取的。又:“掩对待之二,所以巧于逼见至体之一也。究竟绝待在对待中,即用是体,岂有离二之一乎?所谓绝者,因世俗之相待而进一层耳”[7]8。对于“即用是体,而逼人亲见至体之方便”,此处认为,之所以“掩对待之二”,是为了“逼见至体之一”。其又用比世俗之相待更进一层的绝待来表达,绝待在对待中,至体之一就在对待之二中,即用是体,通过用来探究体,用不离体,一不离二,不是去二外另寻求个一。对于一,其说道:“大一曰:我以天地卦爻为我,久舍身以充周之世,有谈道而言行不合吾天地卦爻之凡者,顾乃高榜于天地卦爻之外,妄曰知我,我岂受之?”[7]26自太极生两仪而下,太极便寓于“天地卦爻”,谈论道不与“吾天地卦爻之凡”相合,而去“天地卦爻”之外进行探究,依此为观,能说知太极,能说知一吗?可见一便在二中,即用是体。“故曰:因二为真一,执一为遁一,贞一则二神,离二则一死。”[7]189-190此句话可以说将一与二的关系描写得恰到好处,从这也可以看出理一分殊思想的运用。不止于此,其另有详细之论述:
曰:圣人以天视,视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信如斯耶,斯可语矣。……孔子善巧,而名字之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礼运》善巧,而理数之曰:“礼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天地之数,止有一二而毕矣。……冒天下之道者,大二即大一而已矣。[7]29-30
其中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从万物之名字来讲,又对理数进行说明,将理一分殊融入其中。认为天地之数,一二可以尽之。无论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还是“礼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抑或是其他种种都符合一与二的逻辑关系。按照这种逻辑关系,天地未分前、天地已分后;人之未分前、人之已生后;未画前、已画后,都难逃出此逻辑关系所表现的法则,大二即大一可冒天下之道。此处之大一在逻辑关系上即是理一,大二即是分殊。将《礼运》之大一与《易传》之太极思想合论,可见自太极而下,在化生的过程中大两即大一,而大两是大一的不同表现形态,“不妨分之以为用”。到此可以明显地看到与“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10]5所表达的思想可谓是高度契合。在此种逻辑中太极即是理一,阴阳即是分殊。理一并不妨碍其用之分殊;其用之分殊,并不妨碍其生成之理一。另:
“一生二,二生三”,非老子之教父乎?印度之伊帝目胸表一卍五叶,或纲六相,或立三玄三要,或立五位君臣,或指首罗而扫之。虽非实法,然何所逃于大一之分天地、天地之为大一乎?彼炫专门,重在遮二显一,迸遮一而使自得之耳。[7]31
即便是老子之立说,印度之伊帝目诸说,虽然非实法,依然逃脱不出“大一之分天地、天地之为大一”,可见理一分殊思想之运用普遍存在。方以智立说具有明显地将理一分殊思想运用于其体系内的特征:通过对一与二关系的论述,将理一分殊思想运用得活灵活现,使理一分殊的普遍性得以呈现。
方以智在对“道”进行分析时,主要从太极之普遍性,一与二的关系上着手,然无论太极之普遍性,抑或一与二的关系问题,其中都明显存在着理一分殊的思想原则。
三、理一分殊在“性”中之运用
方以智本《中庸》之“天命之谓性”来论说性之名与实:“有情无情,莫不由焉,名之曰道。由与由者,求其主而不得,名之曰天命。以名其生机之流注焉,名之曰性,以名其功能之蕴藏焉。”[7]204-205道之浩荡何处而非命?性之名因天道流注于个体而始有。方以智说:“言性所自,而曰‘天命之谓性’,究何谓耶?”曰:“孟子注之矣:‘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一丝尚疑,请自剥复而研极之。”[5]18-19其称孟子注之“天命之谓性”,实际上是方以智自己引用孟子言注之。其如此这般,可以说是为了对天命之性之不可测不可知的神性进行揭示,圣人之德行由性体所出、天命所至,若能对此有知,子孝臣忠等皆为性之必然,此可以算识得天、性为一之率性境界。又:“虚无不塞,实无不充者,气也,而神贯之。神用无体,风之济虚也,孰为之耶?故邈其生成无体之体曰性,此不可睹闻者也。”[7]26-27其认为性无定体,倘若使其有定体便会有定相,则会落于物。早在《庄子》中就有:“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夫奚足以至乎先?”[11]对于天道或者性来讲,如果落为可见之物,又怎么足以成为价值之源、万物之本呢?方以智常用“中”来揭示“性”:
中也者,非动非静,常动常静,不可思议之极致也。首云天命之谓性,未发故属天,不属人。其曰性者中也,不妨随时发为率性之道,修道之教。末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至者中也,而不妨随时发为三德、五道、九经。此中三教至理,无不贯彻。[12]55
所谓“中”,“非动非静,常动常静,不可思议之极致也”。方以智将《论语》《中庸》《周易》综合起来论性,通过“中”来揭示“性”之神性。虽谓“此中三教至理”,并非定论,但可以看出其烹炮三教之端倪。又:
且论性而必索之于未形未气之先,则必失之于已形已气之后,是偏认寂寞者为性也。……学人于此达其生生之本,则三界万法,实非他物,今古可以一贯,有无可以不二矣。[12]47-48
论性若是“必索之于未形未气之先”,便会“失之于已形已气之后”,是为有所偏于性之寂。聂双江、罗念庵等人主张求未发之寂体,正所谓“推极于先,性体始见耳”之实指。佛氏以寂静言法性,正似此处之“是偏认寂寞者为性也”之所指,则其不达生生之本。
其论性亦与命相连:“气聚则生、气散而死者,命根也;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性体也。……如波荡水,全水在波;如水成波,全波是水。此性命之不可二者也”[7]206。命根“气聚则生、气散而死”,性体“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此处便显示出性命之“不可一”。性命又“不可二”,正如“如波荡水,全水在波;如水成波,全波是水”一般。又:
性者,天之命也。圣人,性之不惑者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昭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言,无不处其极也。……诚而不息则虚,虚则明,明则照天地而无遗,此尽性命之道也。[12]21
性为天之命,圣人为性之不惑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百姓与圣人性不殊,然之所以有区分则在于圣人为“性之不惑者”,而百姓情之所昏甚而至于终身不自睹。圣人知人性皆善,可以循此不间断而至于圣,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如何尽性命之道呢?“诚而不息则虚,虚则明,明则照天地而无遗,此尽性命之道也”,而这其中可以看出“诚而不息”之重要性,“天命之谓性”“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可见尽性命之道亦要遵循生生之德。
基于此,方以智从公性、独性两层来论性。“公性则无始之性,独性则水火草木与人物各得之性也。”[9]167其所说之“无始”即是“先天”之另一种说法,公性是先天存在,后天寓于物中,不随物之消亡而消亡的性。其之所以被称为公性是因为“所以为独性者,无始以前之公性也”[9]168,公性是独性皆具的依据。何谓独性?“独性则水火草木与人物各得之性也”。又:
物各一理,而共一理也,谓之天理。气分阴阳,则二其性;分五行,则五其性。人物灵蠢各殊,是曰独性,而公性则一也。公性在独性中,遂缘习性。故学以剥复而用之,明辩而晦养之。[5]3-4
戴蒙曰:太一片(爿)而为阴阳,阴阳各一其性;分而为五行,五行各一其性;殽而为万物,万物各一其性。……此无所不学则无所不能者,即“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是人之性也,是独性也。所以为独性者,无始以前之公性也。[9]167-168
独性是人物、物物相别的特殊属性。“质论人之独性,原是无所不学则无所不能之性,而公性即和其中”[9]180,倘若就人而言,独性可谓是人先天所禀赋之认识能力。但是人与自然界的动植物毕竟有所不同,“公性在独性中,遂缘习性。故学以剥复而用之,明辩而晦养之”,独性要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独性之改变称为习性。后天的学习对于先天独性的保持和发挥是非常重要的。公性与独性的关系和公因与反因的关系一致,“公性在独性中”,公性寓于独性,又“所以为独性者,无始以前之公性也”,公性是独性皆具的依据,又是独性之统。“公性则一”也可以看出公性亦具有“绝待”性。公性具有理一的特点,独性具有分殊的特征。
可以看出,方以智论性命、公性独性皆不出理一分殊之模式,正如“此性命之不可一者也”“此性命之不可二者也”与“人物灵蠢各殊,是曰独性,而公性则一也”之所述,可见理一分殊思想在方以智论性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四、理一分殊在“教”中之运用
方以智赋予了“政府”特殊的含义,“天之政府,必以立教为权”[7]109。“以立教为权”之“政府”在一个国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之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有着深层次的根源。方以智主张用“宰理”对政治生活进行重新规范。他认为天道是礼乐制度、政治思想、施政纲领等的合理性来源,应当谴责不顾民众切身需求的行为与做法,强调发挥“宰理”的积极作用,“问宰理,曰:‘仁义。’问物理,曰:‘阴阳刚柔。’问至理,曰:‘所以为宰,所以为物者也。’”[13]所谓“宰理”,在其处可以说是“仁义”,发挥“宰理”的积极作用,也即是发挥仁义的积极作用。其下又加以说法,所谓“物理”,“阴阳刚柔”也。《周易·说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326可见,所谓“宰理”“物理”也是对天道、地道、人道之独特提炼。不止于此,其认为还有“至理”,所谓“至理”即“所以为宰,所以为物者”,正如“太极”是所以然者,是万事万物所以存在之依据。由此亦可以看出,其所谓“宰理”之背后亦有太极之作用存在,太极之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亦无处不在。宰理关乎人道之兴衰,而其中“政府”占有显著位置,“舍政府之尊,又安有至尊之尊耶”[5]3,可见政府所处位置至关重要。对于传统的君臣关系来讲,屡屡产生自上而下之压制和自下而上之篡权,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可谓历史发展的线条之一,君主与官僚集团之间之不合也是此起彼伏的发生,人民群众对所谓的“肉食者”之间的权力斗争表现出十分冷漠的态度。“先民有言:‘询于刍荛。’”[14]古贤者有言,有疑事应当与薪采者谋之,为了助力儒家“询于刍荛”政治理想的实现,方以智突出政府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也是方以智对“政府”处理“君”“民”关系的考察。方以智提出,“人知圣人以仁义为政而已矣,曾知政府既立,下以治万古之民,而上即以治万古之君乎。”[7]120由此可知,方以智认为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有着双重的作用,既规范民众行为又防止君主专制对群体生活造成的危害。政府是公共的,不是一家一姓的暴力机器,从理论层面上来讲,对由君主专制向政府管理进行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或即流而表源,或称先以化后,权在政府宰民,并以宰君,主仆一家,森森即是浑浑,果会通乎?何碍偏举。”[5]13君为主,民为仆,设立政府是为了使君民一家,实现仁义的政治理想。方以智正是想通过对政府角色的塑造来对当时所面临的现状进行调节,由此便可看出其意义之所在。
又:
编氓于里正,邑令于郡守,监司于开府,以次上属,而内属东西台三省,省各有长,而属于宰辅,君乃俨然统之,此无对之尊也。然当知凝命布政咸若率俾者,为直无对之尊也。非惟君相操此权也,郡邑里正皆有凝命布政之君道焉。[7]114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各级政府方以智也有所构思,其所构思的出发点是为了使社会和谐、国家安宁,各级之间“以次上属”。对于凝命布政权力的行使,不但君相,郡邑里正都有对此行使的能动性,可见此一方面可使国家政权一统,另一方面亦可发挥地方之灵活性。正如“万物共一太极”“物物各一太极”之思路一般,可以说方以智对“以立教为权”之政府的构建是跟其对“道”的阐发一致的,其中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思想。在凝命布政之道上,体现了理一,在各级政府实际操作运行中则又有分殊之性。
不但“以立教为权”之政府,即便对于立教之典籍亦如此,方以智对此说道:
若正襟儒者鄙唾《六经》,《六经》一贱,则守臆藐视之,无忌惮者群起矣。今日久舞狻猊狎侮之戏,痛厌六瑟。六瑟之堂,若不注“信述好学”之真我,专袭“《六经》注我”之抗说,乃瓜坑砥柱也。有真知《六经》之注我者,知天地之注《六经》乎?我即《六经》,然后可云“《六经》注我”。既知《六经》即我,仍何妨于我注《六经》乎?天地注曰:无声无臭,表于伦物,烟烟煴煴,醇于经史。[7]137-138
在如此长的经学历史中,有两大诠释传统值得我们多加关注。即汉儒之“我注六经”和宋儒之“六经注我”已然形成,且二者之间对立尖锐,从恪守家法的角度来讲,坚持此对立,是立学之根基。关于“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方以智认识到片面的恪守某种“阵营”都是不足取的,倘若真能做到“六经注我”,则“我即《六经》”,即便是“我注六经”也无妨。从中也可以看出方以智所认为的,正确解经势必要突破此对立,超越汉、宋儒之解经传统,使得己之生命精神与六经所蕴涵之生命精神融贯为一,如此解经才能避免汉儒、宋儒解经之片面性。可见,此中亦体现了理一分殊思想原则,倘若体认到六经中所蕴含的天地之理,以及由此而阐发之理,所谓“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只不过是分殊而已,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无论对于“以立教为权”之政府,还是立教之六经,其中所蕴含的大道不可不体认,只有体认了其中之内涵,也即理一,对于其所操作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殊就好理解了。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方以智的思想体系中,以《易》为枢纽,通过《易》将其他诸说统摄其中,处处显示着易学色彩。方以智在对易学进行阐发的时候以“一以贯之”作为方法,在理论建构之中通过“无极”“有极”来凸显“太极”,并对太极衍演的形式进行了探究,而这种种都体现着理一分殊的运用。其对理一分殊的运用可以说是以中庸之首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纲目来进行的,通过对“道”“性”“教”进行剖析将理一分殊思想运用得活灵活现。不但如此,在论述过程中其还将《易传》中太极思想、《礼运》中大一思想与之合论,在思维方法、理论架构等方面将理一分殊思想原则完整地体现出来,通过此为正学、传道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