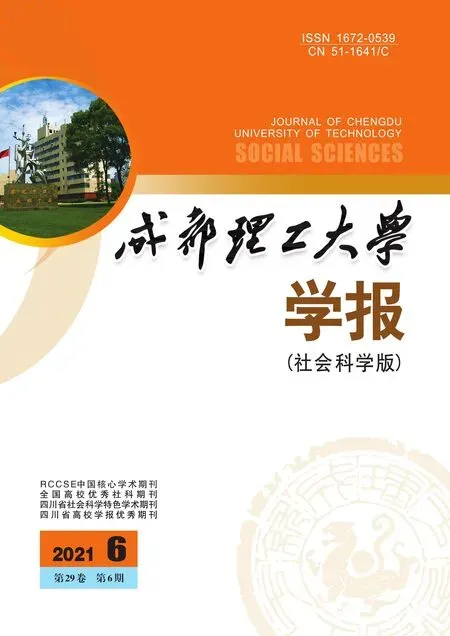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代际正义范式
2021-11-29吴天成
支 果,吴天成
(四川轻化工大学 法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一、引言
著作权的时间性作为与有形财产权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历来为人关注,对著作权进行时间限制始于1710年的《安妮法令》(StatuteofAnne),该法规定作者对手稿、图书等的复制权利原则上仅享有14年,其后作者仍在世的延长至28年。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最初颇具争议,社会各界对著作权是永久权还是有限期权看法不一,该问题在1769年和1774年得到集中讨论。1769年米勒诉泰勒(Millarv.Taylor)案中,因米勒对作品Seasons所享有的权利依照《安妮法令》最迟于1757年便已不存在,米勒若欲对该作品继续主张权利,便只能寻求普通法上与物权一般的无限期财产权保护,该案由当时的王座法院(King’s Bench)立案审理,米勒对作品的主张最终因曼斯菲尔德、威尔逊以及阿斯顿的多数票支持,获得普通法上的永久权利(1)。“但是显然主要是由于后果而不是逻辑关系,菲尔德的意见没有永久占上风”[1],五年后由上议院受理的唐纳森诉贝克特案(Donaldsonv.Becket)得出了与米勒诉泰勒案截然相反的结果,该案被看作对米勒诉泰勒案事实上的上诉审,结束了著作权是否应当进行期限限制的法律争论,奠定了著作权时间限制的基础而延续至今[2]。虽然英国上议院在实然法层面终结了著作权期限限制的正当性之争,但该问题在理论层面上至今仍为从事著作权法研究的学者所讨论,各家之言,不一而足。因著作权存在的正当性解释在理论上的分歧,对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解释大致分两类,一类因循制定法权的功利主义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利益平衡角度、法政策学角度以及公共利益角度进行讨论,主要是对米勒案以及唐纳森案中反对永久权的解释的深化与延续。另一类解释是基于自然权利论,通过对洛克、康德等的财产权思想进行梳理,认为自然权利论仍可得出著作权应当作时间限制,这类解释则是对米勒案与唐纳森案中支持永久权的解释的发展与转圜。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功利主义的解释还是自然权利的解释均为“同时性”解释而非“历时性”解释,而历时性问题仍然重要。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系统讨论历时性的代际正义问题时述及,如果不讨论代与代之间的正义问题,那么对公平的正义的解释就是不完全的[3]。申言之,对作为一种具有历时性特征的分配正义的安排的著作权时间限制进行正当性解释,显然需要在纵向的时间线上进行一定的考量,如果对其正当性的解释不涉及历时性的代际正义问题,其解释显然是不完整的。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代际正义的角度,运用与著作权时间限制理论相契合的论证代际正义的功利主义论、义务论以及共同体义务论对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进行补充解释(2)。
二、著作权时间限制的功利主义代际正义论证
功利主义被表述为“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法学的功利主义理论由英国学者边沁系统阐释,其认为功利主义是政府决策的唯一依据,是立法的唯一导向,“组成共同体的个人的幸福,或曰其快乐和安全,是立法者应当记住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他是唯一的标准……除痛苦或快乐外,没有什么最终使得一个人去干”[4]。因此,立法的出发点是为给予法律所及之处的共同体成员最大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强调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依“总体效用”和“平均效用”的效用划分标准,功利主义可以被分为“总体的功利主义”和“平均的功利主义”,总体的功利主义强调整个社会的快乐和幸福总量的增加,公式化为社会成员的幸福快乐的总和。平均的功利主义强调单个共同体成员快乐和幸福均值的增加[5]。在共同体成员确定的情况下,单个的共同体成员的幸福和快乐增加即可达成增进社会总体幸福和快乐的目的。那么功利主义解释下的著作权法立法目的便是增进社会内部成员的福乐。著作权时间限制的功利主义解释源于美国,美国宪法中的“知识产权条款”开宗明义地提出:“通过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作者和发明人对其作品和发明以专有权利,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发展。”(3)我国著作权法亦有规定,著作权法是“为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而制定。依功利主义的解释逻辑,“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立法者考虑的目的,这就要求他必须了解他们的值”[4]86,作品首先被定位为一种公共产品,属于公有“物”,作品体现的文化需求是“幸福”和“快乐”的子集,能满足社会共同体间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其应当是政府决策的考量因素,因此在功利主义视角下政府的社会政策安排所欲增进的整个社会的幸福和快乐显然包含文化产出,表现形式即为作品的产出。在确定作品的效用之后,还须将其最大化,方为功利主义的追求。因此,著作权法的经济分析认为,若完全否认著作权的存在,则会打击创作热情,降低文学艺术作品的产出,因而法律赋予作者对其作品以专有权用以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从而提高文学艺术品的产出;但若赋予作品永久权,则会阻碍公众获取作品,得到“幸福”和“快乐”,运用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就会得出赋予作者永久权无法达到社会幸福指数总收益的最大化,进而认为赋予作者对其智力成果享有财产权的同时对著作财产权进行期限限制方能实现既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亦能保证公众对作品的使用,增进新作品的产生,最终达到社会文化总收益的最大化,增进社会福祉。据此,基于作品的公共产品属性,为照顾公共利益而对作者的著作权进行期限限制便顺理成章,一旦著作财产权期限届满即进入公有领域,公有领域作品只增不减,人们得以利用的作品亦只增不减,这合理地促进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平均上都达到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在功利主义看来,著作权时间限制是一种公共利益的考量、社会政策的安排以及利益平衡的结果。
上述解释是一种横向的同时性的代内正义视角(至少未明确探讨其中的代际正义)(4)。除代内正义外,功利主义还关心代际正义,功利主义对代际正义的解释是运用功利主义原则对代际正义的可能进行证成。功利主义认为,我们不应当只关心当下人的幸福,还需关心后代人的幸福,当代人和后代人虽然具有“非同一性”特征,但仍然值得我们关心,当代人对后代人负有义务,功利主义关心当代人的行为对后代人的影响,当代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应当选择能够促进后代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现有解释将作品的功效笼统地置于当代人们的幸福追求来进行考量,只考虑到同一时空中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政策平衡,而未对功利主义关心的代际正义进行解释,下面运用功利主义的方法从历时性的代际正义角度对该论证进行补充阐述。功利主义在代际正义问题上不存在时间上的偏爱,保持一种“时间中立”的视角,将整个人类社会作为其论证的对象,无论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还是未来的人,都是其重视的对象,“以整个人类存在的时间为背景,来考虑一个行为对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幸福所产生的作用”。因此,“如果当代人的行为能‘增进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最大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在道德上正当的行为或者‘善’的行为,否则就是一种道德上不正当的行为或者‘恶’的行为”[6]。就著作权的法律政策安排而言,可以推论出功利主义导向的结果:著作权的法律制度设计应当满足“作品的产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每一代社会上的人的幸福需求”,无论是当代社会还是后代社会,作品的产出都应达到最大化,也即处于一种纯增长态势。同前所述,如果将著作权安排为一种永久权利,则存在权利人及其后人可以一劳永逸的可能,而时间长河上所有世代的他人均需付费,此种安排一则不利于激励权利人从事新的创作,二则打击社会公众运用作品从事新创作的热情,在代际关系承继的过程中,作品虽不言其减少,但可以预见绝对比对著作权进行时效限制后产出的作品少,更甚言之,对作品进行时效限制后的历代作品产出会是不作此安排的几何倍数。因此,从功利主义追求幸福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显然应当对著作权进行时间限制,以保证代际正义。著作权保护期限从最初的“14+14”模式到现在的“身后+50/70年”模式,一般认为作者在世时应当对其作品进行保护,此法更易于激励著作权人进行创作,而基于对作者后代生存生活的考量,将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延长至其去世后50年或70年[7]。而后作品即进入公有领域,所有人在不侵害作者人格利益的前提下得以利用该作品。虽然对去世后的财产权利的存续问题存在争议,但对作者在世时享有权利这点无太大争议,在期限长度上为什么作此安排?虽然现有解释中未有此明确表述,但从著作权有效期的期限(跨代)来看,功利主义释论所提及的公共利益考量中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一种“代际利益”,著作权时间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后代人的幸福快乐追求,也即一种文化繁荣的承继。因此,著作权时间限制的制度安排存在内生的代际正义价值考量。
三、代际正义的义务论与著作权时间限制
著作权时间限制的另一种解释是从自然法权角度,在洛克、康德的财产权理论中寻觅普通法财产权限制的逻辑自洽,面对功利主义的质疑(5),自然权利论者认为可以运用洛克在《政府论》中论证财产权的正当性时所提及的附加条件以及康德的权利普遍原则,推导出基于对第三人的关照,给予著作权以时间限制。与功利主义看中结果的正当性不同,此种解释是基于行为本身正当性的道义论解释,这与论证代际正义的义务论有相同的关注点,下面从代际正义的义务论角度对此进行补强解释。
义务论在现代伦理学中以黄金法则及康德的绝对律令为代表。黄金法则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其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形式,亦强调“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你们也要怎么待人”的积极形式。这与同样具有直觉主义色彩的自然权利论高度契合,与洛克讨论财产权时所述的“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的语境相通,你若通过劳动获取自然状态下的劳动对象为财产,那么就应当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劳动对象给他人[8],因为你也愿意别人同意且支持你获取自然状态下的劳动对象,那么你在将劳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时就应当对他人报以同样的心态。或者,“你也不愿意别人独占所有劳动资源而将你排斥在外”。在黄金法则的视阈下其视野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个人如何对待整体以及整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9]。因而代际正义的研究者将黄金法则扩展到代际正义中去阐述,在代际关系当中,“无论何事,当代人愿意后代人怎么对待自己,当代人也应该怎样对待后人”,或者“当代人所不希望的,也不应施加给后代人”[6]51-52。将著作权时间限制的自然法思想置于代际正义的黄金法则中也是相通的,Wendy J. Gordon认为从代际平等角度看,“后代创造者应当与他们前辈那样自由运用自己的才能,每代人都被允许使用先前的创作,自由才是可能的。”[10]在未出现著作权之前,作品是自由流通且无偿的,著作权出现之后,几乎所有作者都得以无偿利用前人的成果,那么即使当下确立了著作权,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形式,当下的人不愿认同前人的智力劳动成果是永久有效的,那么这种观念也应及于后代人。或者说,前人去世后当下人得以无偿使用智力劳动成果,则当下人去世后后代人也应无偿使用其智力成果,主张著作财产权具备永久性的行为本身具有不正当性。
除此之外,在知识产权作为私权存在的正当性解释理论中,康德的财产权利观被用以借鉴,在康德的财产权利观里,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应尊重他人获得财产的自由,通过“目的—对象”得到的财产权应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因为相互的尊重,普遍理性就会要求人们相互克制,由此衍生财产权的限制[11]。就著作权的产生与限制而言,Robert P. Merges教授在梳理康德的财产权利观后认为,财产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若符合康德的普遍理性原则,就会产生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同样地,为了符合普遍理性原则,就要求该种权利受到时间上的限制。”[12]194Merges教授对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的此种解释还尚显模糊(6)[12]193-194,虽然康德的权利普遍原则可推出权利限制,但康德的权利普遍原则是如何衍生出知识产权时间限制的?仍然需要作进一步解释。代际正义对康德权利观衍生的义务论的运用可提供知识产权时间限制的“康德式”逻辑思路。权利普遍原则是康德普遍理性原则的延展,“绝对律令”是其上位理论,其“绝对律令”为伦理学中一元义务论的另一种释义。包括黄金法则在内,康德的“绝对律令”可转化为三种公式化表达:(1)一个人据以行动的准则应该能够成为普遍准则;(2)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自己和他人同样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3)一个人的行动准则只能是可能目的世界普遍立法成员的准则[13]。“绝对律令”的道德情操在于,每个人都应将他人看得和自己同样重要,不应把他人看作行动的工具,而应是目的。每个当代人不仅应将同时代的自己和他人当作目的,也应将后代人作为自己的目的。将后代人作为目的,就要求关心后代人的文化生活是当代人的目的,作者去世后将作品强制进入公有领域,能更好地满足后代人——也即康德语境中的他人——的意志自由,尽管当代人通过“目的—对象”获取著作权具有正当性,但不能对他人的意志自由——也即知识产权领域所述之言论自由、信息自由——产生不当阻碍,因而对著作权进行了诸如有效期、合理使用、法定许可、权利穷竭等一系列限制,而其中时间上的限制与其他限制不同,是一种纵向上的限制,其完全将当代人的自由考量排除在外,因而其惠及的只可能是后代人的自由,显然考量的是后代人的自由,是一种代际正义的考虑。另一方面,同前文论述功利主义时所述,著作权在进行时间限制时,对于其效力期限长度的选择至少包含作者在世时段。功利主义认为,对著作权进行时间限制既能激励创作热情,又能促进作品传播,从而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但在最佳保护期上却无法确证,无法通过计算得出作者在世期间对著作财产权进行保护才是最佳的。本文认为,这与自然权利论存在潜意识层面上的共谋,自然权利视角下对著作财产权进行时间限制是为保护后代人的利益,这是从行为本身出发推导出行为本身应当受限,因为其需要考虑后代人的自由,所以著作财产权从获取之时便意味其天然附随时间限制,其著作财产权只能在生前享有。因此,每个理性的人都会认为通过劳动、自由意志获取的知识财产是正当的,除为后代人考虑而让作品在作者去世后进入公有领域外,作者生前财产权应当是有效的。这种先验主义的感性材料亦为功利主义计算时需要考虑的方面,若将著作财产权的效力期间限定在生前会伤害作者的情感,打击作者的创作热情,故而尽管无法确证对作品的保护及于作者一生能获得最佳收益,但至少能证明不作此安排必定减少文化收益。功利主义不得不考虑理性人的道义情感,这从侧面补证著作权时间限制存在基于自然权利视角的代际正义考虑,著作权时间限制在自然权利论下亦为正当,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四、跨代共同体义务论与著作权时间限制
在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正当性理论中,未有直接明确涉及代际正义的共同体理论的论述,Robert P. Merges教授在运用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来解释其书《知识产权正当性解释》中所述“分配正义与知识产权”时虽论及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问题,但未明确涉及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论述,也未曾涉及罗尔斯在完善其代际正义论证以衔接其正义理论时所用的共同体理论,而从事代际正义的共同体义务论研究的诸多学者的独到见解确对解释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有着较大程度的说服力。因此,本文除从代际正义角度对功利主义以及义务论这两种与著作权时间限制直接相关的理论进行补充外,还将从代际正义角度将共同体义务论这个不太为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论证所运用的理论引入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辩护中。
与上文所述论证代际正义的义务论不同,尽管共同体义务论在论证代际正义时是以“义务”为导向,但共同体义务论是整体到整体的义务,是一种直接义务,更多体现的是以奉献为内容的责任,而代际正义的义务论则是在确定个体权利后衍生出的从个体到个体再到整体的义务,是一种间接的由点到面的关系,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权利义务对等关系。代际正义的共同体义务理论是在人类共同体理论基础上衍生而来,人类共同体理论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认为人类在为一定行为的时候要考虑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因此考虑到整个人类的发展,当代人所做的决策应当符合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一般认为,代际正义的共同体义务说可追溯至英国学者柏克的国家观。柏克认为,国家是一项契约关系,但不同于社会公众私人之间签订的一般契约可以任意解除,“它乃是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伙关系,是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道德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关系。由于这样一种合伙关系的目的无法在许多代人之间达到,所以国家就变成了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14]在柏克看来,关心科学、艺术的发展是国家“伟大的初始契约”,是一种具有最高义务的法律,不可以由人任意变更解除。R. George Wight教授进一步阐释柏克的这种观点,“传统宗教基础下我们对未来世代的文化承诺否认任何特定世代享有特权地位,或者否认任何世代享有剥夺和消散而不是增强和传播其先辈成就的许可权。”[15]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义务促进文化发展,并进行必要的文化积累以确保后代人拥有继续促进文化发展的条件。每一代人的责任是将先辈传下来的文化积累不减少地传给后代,同时每一代人又有义务创造新的文化条件以供后代人利用。为了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Wight教授认为,“每一代人都会从其前辈的累积牺牲和投资中受益,并必然会为后继者做出牺牲和投资。”这是一种纯粹的奉献责任,当每一代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就达到了平等。据此,著作权法在赋予作者就其作品以著作权后,应在一定时间后使这种权利消散,以供后代人取用,这是时间长河中的每一代人为人类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所应负的责任。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论证的代际正义实现方式受到质疑后运用社会共同体理论对其代际正义理论进行修正时提出,各世代应当遵循一种储存原则:“我们不去想象一种(假设的和非历史的)各代之间的直接性契约,相反,我们却可以要求各方一致达成一种储存原则,该储存原则须服从于他们必定要求其前辈各代所遵循的进一步的条件要求。因此,正确的原则便是,任何一代(和所有各代)社会成员所采用的原则,也正是他们这一代人所要遵循的原则,亦是他们可能要求前面各代人(和以后各代人)所要遵循的原则,无论往前(或往后)追溯多远。”[16]具体到著作权法,从人类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实践理性出发,为人类科学文化的不断繁荣发展,各方世代在“原初状态”下即达成一种储存原则,每一代都应该为后代储存足够的文化积累并传承下去,使得文化得以不断繁荣。因此不能给予作者就其作品无限期的保护,因为那样会阻碍作品的传播。这与著作权时间限制理论中的目的解释吻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促进文化繁荣,因而作品在一段时期过后应当流入公有领域以供他人使用,美国版权法学者帕特森和林德伯格即认为版权法将作品从公有领域中拿出给予财产权保护后,最终再次流入公有领域的原因在于“通过鼓励形式上永恒存在的新作品,在促进知识储备有利于当代学习的同时,也有助于子孙后代社会文化的繁荣。”[17]从形式上讲,本文运用代际正义的共同体义务论论证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时与功利主义有相似的地方,二者均涉及经济收益问题,功利主义与共同体义务论都认为对著作权进行时间限制能够增进文化收入。但这并不能将二者等同,经济分析只是一种工具,工具具有价值中立的属性,道德关注点的不同才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功利主义考虑结果的正当性;共同体义务论考虑的则是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其关心的是责任问题。功利主义强调效益最大化,在功利主义的视角下,著作权时间限制的具体值需在满足作品产出最大化时才是最优的,同上文所述,这是难以计算甚至是无法计算的。而共同体义务论则无须达到最大化,仅须进行必要的存储即可,在计算著作权时间限制的长度时仅需在合理的区间内即可。代际正义的共同体义务论在解释著作权时间限制时能为功利主义与自然权利论提供融通手段,避免二者相互攻讦的。从人类共同体利益出发阐释科学文化发展对著作权时间效力的限制可以避免从著作财产权存在的正当性出发谈论著作权的限制,无论著作权以何种理论受到保护,其都应当因考虑人类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而受到限制。
五、结论
在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解释上,尽管以往解释没有明确提出代际正义问题,但著作权时间限制的确存在代际正义的价值考量。无论是功利主义理论还是自然权利理论都能从代际正义角度对著作权时间限制进行合理解释,因而代际正义问题不会成为两理论的攻讦点。除上述两理论外,代际正义的人类共同体理论着眼于人类科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而对著作权进行时间限制的解释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著作权法限制著作权的时间效力具备正当性。
注释:
(1)Millar v. Taylor, 4 burr. 2303, 98 Eng. Rep. 201.
(2)代际正义的论证路径主要分为义务论论证路径和权利论论证路径,本文所论及的几种代际正义理论主要为义务论论证路径,即以当代人对未来世代的人存在义务为起点,论证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
(3)U.S.Constitution.Article1Section8.
(4)单就著作权时间限制来看,其中蕴含了代际正义,这是本文的观点。但考虑到以往功利主义对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整体解释的上位解释是基于一种横向存在的代内正义解释,著作权时间限制是基于这种上位解释而进行的从一般到具体的解释,因而实质上功利主义对著作权时间限制的解释出发点仍然是基于代内正义,而不存在代际正义的考量。
(5)在著作权存在的正当性理论中,自然权利论受质疑的一点是,如果著作财产权属于自然权利,那么作为普通法财产权的著作财产权就应当不受时间上的限制,而现实却需要对著作财产权的效力进行时间限制,普通法财产权理论无法对此作出恰当的解释。
(6)Merges教授解释康德的财产权利观下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时认为,对知识产权进行时间限制是为个人与他人的自由提供一种融通方式,但未解释这种融通方式的来由,仅根据“存在即合理”,将时间限制被广泛采用作为对融通方式提供的强有力证据,“证明大家在何为公平上,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