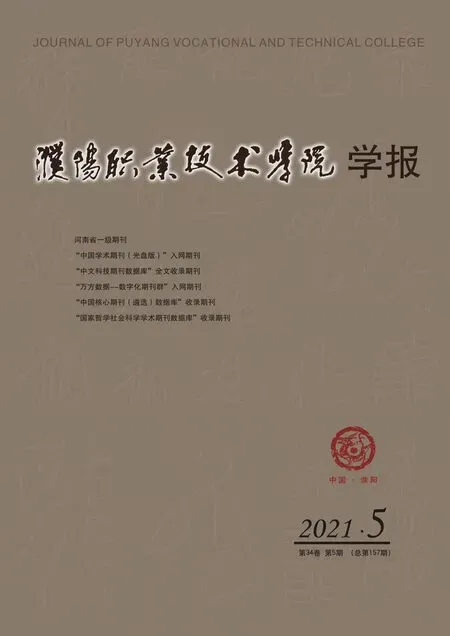《世说新语》中的“以龙喻人”现象
2021-11-28王占阳
王占阳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中国被称为“龙的国度”,中华儿女被称为“龙的传人”,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龙文化内涵不断演变。何星亮先生认为中国龙文化大体经历了图腾崇拜、神灵崇拜、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印度龙崇拜与中国龙崇拜相结合四个阶段[1](57)。如此分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崇拜”,所论述的“龙文化”只是作为神灵和帝王的龙的文化,忽略了龙的人格化与世俗化,在汉末至两晋南北朝以前,龙文化是一种“崇拜文化”。
虽然古代崇龙、尊龙观念盛行,龙被赋予诸多美好的品质,如《周易·乾卦》中以龙喻君子际遇,在屈原的《离骚》之中以“虬龙鸾凤”象征君子,但龙并未真正与社会大众发生直接关联。这些记载并没有确指,只是作为一种精神符号而存在,到了后来这些精神符号又专指帝王了。先秦两汉时期并无真正意义上的龙型人物,这种情况的改变从汉末开始。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始出现一种新思潮,在这一时期,人和人格本身日益成为哲学和文艺的中心[2](85),龙作为帝王专属和象征的意义相对弱化,民间龙文化从此开始逐步发展,并由此形成宫廷与市井、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中,前者更强调龙的神圣性,象征帝王,突出神格;后者强调龙的世俗性,强调人性,突出人格[3](170)。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以龙喻人”现象的大量出现标志着龙的人格化、世俗化在魏晋开始并完成。评价标准突出表现为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能力等方面,人的内在精神性成为最高的标准与原则,这为古老的龙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一、荀氏“八龙”
东汉荀淑育有八子,《后汉书》言:“(荀淑)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4](2049)《世说新语》德行门载其事迹: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5](8)
在《世说新语》中对于荀淑八子的记载不在少数,如言语门载荀爽举贤不避亲[5](68);品藻门中以陈纪比荀爽,陈纪即陈元方,以孝著称,与其父陈寔、其弟陈谌号为“三君”[6](559)。但纵观史书,“八龙”之中惟荀爽有传,其余诸子则附见于别传,甚至并不见于史传。而《后汉书》又载荀爽在其晚年辅佐董卓[4](2057),其道德本应受到批判,史书仍为其立传,颇有赞誉。
汉魏时人之所以会给“八龙”如此之高的评价,便在于颍川荀氏从荀淑之时起便是魏晋时代的名门望族,在强调门阀的魏晋时代,荀氏子弟因其家族声望而誉为“龙”型人物。但通过此记载我们会发现魏晋时期“龙”从帝王下移至世家大族,家望成为人物评价的重要标准。
二、“龙跃云津”之陆氏兄弟
《世说新语》载,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6](475)
张华是西晋时期的名士,颇有识人之才,举人之功,张华对陆机兄弟评价非常之高,这也为陆机兄弟赢得了不少声望,使二陆兄弟成为当时的名家,称颂一时:
有问秀才:“吴旧姓何如?”答曰:“……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 ”[6](476、477)
二陆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声誉,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文章秀丽,特别是陆机,他的文学才能得到当时人的一致认可,《晋书·陆机传》载:
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云尝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 ”其为人所推服如此。[7](1480-1481)
《世说新语》文学门中也两次记载孙兴公对其文章的点评,并将其与潘岳作对比: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6](287)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6](288)南朝钟嵘也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而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时期独特的文学风貌在后来的文学史上被称为“太康诗风”。陆机流传下来的诗共105首,赋27篇,都是难得的佳作。陆云的文学才能较其兄稍差,然亦名动当时。以文学之能而言,二陆不负“龙”名。
三、许氏“二龙”
《世说新语》赏誉门载: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见许子政弱冠之时,叹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 ”[6](457-458)
谢子微即谢甄,刘孝标注引《汝南先贤传》言其“明识人伦,虽郭林宗不及甄之鉴也”。有识人之能的谢子微如此高度评价许虔、许劭兄弟,并将许虔与当时名士陈仲举、范孟博齐观。同样,从《世说新语》及史书记载中发现,许氏兄弟最大的才能也是能够识人。
许虔生平不见于史传,只在《后汉书·许劭传》中一带而过:“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8](2235)在《世说新语》中也仅上述一条记载。《后汉书》中记载许劭的才能在品评人物上:“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8](2234)许邵常在每月初一主持对当代人物或诗文字画的品评、褒贬活动,后来便成为“月旦评”,影响极大。无论是谁,一经品题,便身价百倍。在《世说新语》中并没有专门记载许劭的文字,只在刘孝标的注中多次称引,均显示其有人物品评之能,其中最广为流传的点评便是称曹操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基本奠定了后世对曹操基调评价。
但许劭主持的月旦评本身也颇受批评,一月便评一次,未免有些草率,而且评价也多有不公,诸葛恪便认为许子将兴起的人物点评风潮是天下动荡的原因:“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雠。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
四、“卧龙”——诸葛亮
诸葛亮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世说新语》中对诸葛亮的记载很少,品藻门论诸葛三兄弟时称其为“龙”: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6](556-557)
这是《世说新语》中唯一一条称许诸葛亮的记载。相比而言,《世说新语》对其兄诸葛瑾和弟诸葛诞的记载却更加详细,但后世诸葛亮的名望却远胜其兄弟,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与史料来源有关,《世说新语》是根据已有材料编辑的,且偏于轶事传闻,蜀国留下的这方面材料相对较少;其次,刘义庆之时主流文化是曹魏和两晋文化,虽然后世多以蜀国为汉朝余续,但在当时并未代表主流,故而选取较少。
诸葛亮被称为“卧龙”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徐庶向刘备举荐诸葛亮,云:“诸葛孔明者,卧龙也!”[9](912)言诸葛亮为“卧龙”更多地是表明他有政治才能,“每自比于管仲、乐毅”[9](911)。管仲,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九合诸侯;乐毅,战国后期军事家,率燕国等五国联军伐齐,连下七十余城。诸葛亮以此二人自比,可见他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及政治军事才能。天下大乱之时,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看中的也是他的政治才能而非其他。
到了后来,儒家道德评价体系的再次建立使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渐让位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君之心,这便为其“卧龙”的名号增添了新的内容,诸葛亮之才能与道德均不负于“卧龙”之名。
五、“惊龙”——王羲之
作为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在《世说新语》中的记载颇多,而与龙发生关联的则只有一条,并记载于容止门中,这也是魏晋时期唯一一位以容貌举止获得龙的称誉的人:“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10](688)
字如其人,这也更说明以“惊龙”喻王羲之颇为贴切。以龙称人容貌并非《世说新语》新创,史载黄帝便是“龙颜,有圣德”[11](5)。后来历代帝王都会被记载有龙颜。这里的龙颜更多的是政治功能,体现出威严、肃穆之感。这里将王羲之喻为“惊龙”则与此不同,如《洛神赋》中描绘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甄姬一样,这里更多地是表现王羲之闲适飘逸的体态与这种体态下所蕴含的风度气韵,坦腹东床的王羲之与魏晋时期所倡导的自由不羁、超脱俗世的人生态度高度契合,这也是其获得高度赞美的原因所在。
《晋书》则以“飘若浮云,矫若惊龙”[12](3093)称赞其书法笔势。王羲之擅长行书,《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用“惊龙”来形容自然合适。而字如其人,潇洒飘逸的行书正体现了王羲之自由从适的容貌举止与人生态度。
六、“五色之龙章”——顾荣
顾荣字彦先,西晋末年大臣、名士,《世说新语》赏誉门赞其“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6](476)。顾荣喜琴瑟、擅文章,故言其为八音琴瑟、五色龙章,但又因顾荣擅言语、品格高,此处又以八音琴瑟、五色龙章来分别比喻其言语、品格。顾荣病逝,友人张季鹰于其床上鼓琴,遗憾顾荣不能复赏,由此可见顾彦先之喜琴爱琴[5](70)。顾彦先又善言语,如八音之琴瑟,能开导人情。言语门载晋元帝在南渡之后,居于他邦,心中凄切惭愧,每每忧思,顾荣开导晋元帝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5](100)顾荣以商、周迁都的历史为镜鉴,告诉晋元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道理,并以此解开其心结,可谓八音琴瑟,载其好音。
“龙章”原指帝王衣服上的纹饰,五色龙章言其华美。到了魏晋时期便以其形容人的文采、风采。时人评价顾彦先也多与陆机、陆云并列,二陆以文章闻名,顾荣与其并列,文章自是不俗,至少符合当时人的审美标准。五色龙章又言其人格之美: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相助,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5](28)
在魏晋时期,等级秩序十分严格,“行炙人”是底层下人,当时名士甚至认为与这些人交谈是对自己人格、情性的亵渎,是一种耻辱,而这里顾荣见“行炙人”有“欲炙之色”,便将自己的给了他,这在当时名士看来无疑是一种自卑自贱的行为,故“同坐嗤之”。后来“行炙人”多次救顾荣于危难,成为一时美谈。虽不能说顾荣完全摒弃了当时社会的等级观念,但是他能够如此对待“行炙人”,亦不愧于“龙章”之誉。
七、结语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而大量出现的“以龙喻人”现象,充分体现了“龙文化”的下移,魏晋时期成为龙文化的重要转折期。而荀氏“八龙”以世家声望取得龙名,陆机兄弟以文章著称,许氏兄弟以识人获誉,诸葛亮以政治军事才能及道德获“卧龙”美誉,王羲之则以其容止、书法誉为“惊龙”,顾荣以擅琴瑟文章、会言语、道德高被誉为“五色龙章”。不同的才能、品性均有可能得到“龙”的美誉,充分体现了龙在魏晋时期的世俗化与人格化倾向,这对后世龙文化深入民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