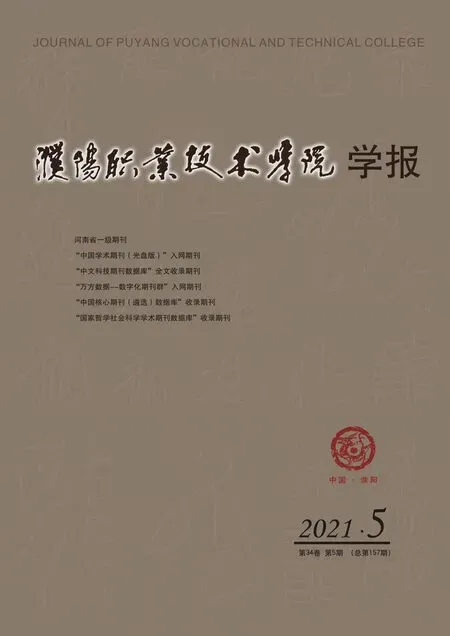跨族裔电影中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困境
——以李安早期作品为例
2021-11-28李法娟
李法娟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作为一名移民导演,李安早期的电影《推手》(1991)和《喜宴》(1993)均以华人移民为题材,从自身“流散者”的角度出发,展现了华人移居到美国之后伴随而来的种种问题。在这类移民题材的电影中,作为作者身份的导演往往采用流散叙事的手法来建构镜像语言,具有极强的流浪意识和漂泊意识,而影片当中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问题便成为书写的重要症结。离散族裔的社会现象以及移民身份的定位难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也持续存在,李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敏锐地觉察到了移居到海外的人们所要经受的困境,在影片中探讨民族之间的差异、代际之间的矛盾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所给人带来的生存危机。二十余载匆匆而过,现在的跨族裔、移民群体也很难逃脱身份定位的尴尬处境,尽管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移民后裔,他们在尝试着介入社会现实、建构独有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也无法避免地经历着身份认同带给人的焦虑。对处于异国他乡的个体来说,自身所存有的文化记忆以及“他者”的介入也不断促发着人们对身份认同的找寻。但是,人们在进行身份认同的同时,是否也在不断解构着自身的身份?亦或者说,个体是否从来都不曾有固定的身份,只是处于不断的生发过程?李安电影结局的中庸之道或许能给我们启发。
一、文化记忆:找寻认同的源动力
“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扬·阿斯曼提出,并首次运用于人类学的研究当中,后逐渐引入到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首先应该是对以往真实事件的真实回忆,是这些“真实事件”本身,同时也是一种解释和证明[1](12)。人们进行回忆的过程就是在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从而确证自己是处于整体中的一员,以拥有一种集体身份。同时,社会也通过这种方法,将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保存下来,保持文化的连续性,提供给人们建构文化身份的依据。但是,文化记忆也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框架,以求得世代传承,它所具有的群体性、重构性等特点使得文化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义广阔的生成空间[2](187),由此文化记忆在现实空间和人们的心灵空间中获得重生。所以,在移民题材的电影中,人物总是通过文化记忆来确证自己的身份,试图在社会环境改变的处境中弥合过往自己和现世自己的差异,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电影《推手》当中,朱老被儿子接到美国生活,但始终活跃在中国城中,对于朱老来说,与中华同胞们打交道、谈论过往的生活经历就是找寻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而对于《喜宴》中的顾威威来说,自己的文化记忆却在不断加深她的认同焦虑,对过往生活的追寻让她更加迷茫。所以,对于身居异乡的移民来说,文化记忆的存留是人们找寻自己身份认同的本源动力,也是人们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本缘由。
(一)作为救赎的记忆
“人是文化的存在”[3](170),人们的文化记忆不仅能够定义个体的自我,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个体的未来。所以,一个人的文化记忆对于个体的身份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群体性和共享性的文化记忆来形成相似的价值取向获得身份认同,从而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确证自己的身份归属。李安作为一名移民导演,在早期的作品当中,将镜头聚焦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在不同群体的文化记忆当中展现两者之间的裂痕,并将身份认同的困惑融入到镜像当中,从而探讨人的身份归属问题。在影片《推手》中,李安对朗雄饰演的朱老和高爸爸这两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父亲形象的刻画,展现了中国文化在海外文化面前所遭受的冲击,以及群体之间异质的文化记忆给人带来的精神困顿。《推手》中朱老作为一名退休的太极拳教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他有清晰严苛的国别意识和民族意识,并坚守着自身的文化记忆。他排斥英语,看不惯美国儿媳不吃肉的饮食习惯,坚持每天练习太极和书法,这些都是自身文化记忆的现实呈现。面对裹挟而来的异质文化,朱老并没有对自己的文化记忆产生怀疑,依旧坚守着自己以往的身份认同,以便在他乡寻得一丝安慰。所以,对朱老来说,他的家国意识要求他极力维护自己家庭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作为身处他乡的“漂泊者“,朱老自身已有的文化记忆对他起到了救赎的作用,让他在海外异国坚守自己的信仰,明确自己的归属,认证自己的身份认同。
(二)作为妨害的记忆
记忆一方面让人清楚过往,明晰自己的归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过去也是一份难以摆脱的沉重负担”[1](243),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起到妨害的作用。对于《喜宴》当中的顾威威来说,自身的文化记忆便加深了她的身份认同焦虑。顾微微到美国三年多,却始终没有得到一张绿卡,也没有正式工作,为了获取在美国生存下去的机会,选择了与同性恋的高伟同假结婚。虽然顾威威的身边没有现实明显的文化对抗,但是现实并不理想的环境让她只能够在以往的回忆中过活。没有和高伟同结婚之前,她住在一间类似仓库的房子里,听着台湾的流行音乐,用来遮蔽房外繁杂的噪音,只有这样她才能安心画画。与其说她用台湾音乐来盖住噪音,不如说是用音乐唤起自己的家国想象和文化记忆,以此逃避美国社会给自己施加的种种压力。面临无房可住的处境,她甚至希望自己被美国警察赶出美国境内,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顾威威无法告别过去,始终把回到本土当作自己的退路,可是尽管如此,顾威威在面对高伟同提出的荒诞要求,依旧不假思索地同意,以此来换取能够生活在美国的机会。所以,文化记忆对于顾威威来说并不能让她确证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是让她在内心深处产生更大的矛盾,从而造成自我的分裂,并产生孤独的异质感。顾威威面对不断更新的现实生活,未来的不确定性只能让她更加怀恋过去,同时过去的文化记忆又加深了自身的分裂,从而加重了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二、“他者”介入:找寻认同的驱动力
“他者”作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重要的概念之一,并没有一致的固定内涵,在不同的领域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涵义和用法。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他者”是一种他性,即异己性,指与自我不同、不属于自我本性的或者外在于自我的特性[1](214)。同时,“他者”的生成必须存在于关系当中,具体来说,“存在于两组关系之中,一组为同一/同者与他者;一组为自我/主体与他者”[4](167),表现为主体内部的分裂和主体外部的差异。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组关系处于交融的状态,主体内部的分裂隐匿在主体与外部的差异当中,通过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表现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存在着两元对立的世界,“他者”并不是单一的他性,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对照是一种多元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多元关系的对照当中,主体也不断审视和重建自我,更新着自己的存在。所以,“他者”的存在一方面对主体确证自己的身份归属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者”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得个体的身份认同只能在动态当中不断发展,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归属。在《推手》和《喜宴》当中,朱老面对不同的民族,将“他者”与自我的差异置于交融之上,确证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但却在现实生活当中居于困境。高伟同面对“他者”的介入坦然接受,不断顺应着美国文化,但是却难逃以往的文化记忆对自己的影响,于是在动态当中不断调整着自己,企图确证自己的身份认同。
(一)从属性的“他者”
主体对一片土地的感觉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成的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会让主体产生对土地的依恋情绪,这也就是“恋地情结”,这种依恋是一种持久并且难以表达的情感,而民族中心主义就是“恋地情结”的典型表征。“民族中心主义是人类的普遍特征”[5](44),人们总是将自己的民族看作世界的中心,由此建构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在此基础上塑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与自己民族不符合的一部分,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看为“他者”,因此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那里,其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自然而然地将东方文化看作了“他者”。而我们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从本民族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记忆出发,自然也将西方看作为“他者”,所以在跨族裔电影当中,就难免体现与自我相异的他性,面对身边的他性存在,个体怎样认识自我、怎样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便成为了电影必须要探讨的主题。李安在《推手》当中,通过朱老这一形象的塑造,成功地肯定了本民族文化,通过朱老自身和美国文化的对比,找寻到了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朱老作为一名太极拳教授,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化表达,由于跟随儿子移民到美国,环境的改变、生活习惯的不同,让朱老内心产生了深深的孤独感。他将美国人看作“他者”,在觉察到自己儿媳不吃肉的习惯时,向自己的儿子询问“这美国女人,光吃青菜怎么顶事?”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探析出朱老始终将自己与“他者”对立,尽管是面对自己的儿媳妇,他也是用“美国女人”来称呼。朱老之所以看重这种他性,是因为朱老与“他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语言交流的不通,生活习惯的大相径庭,价值观念的截然不同,让朱老与儿媳玛莎的相处变得异常艰难。朱老将本民族文化放置在美国文化之上,将“他者”放置在从属位置,以此确证自己不同于“他者”的、属于本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可是,处于美国这一大环境当中,尽管自己确证了自己的身份归属,面对他国文化的侵袭,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他者”的介入也必定会造成个体身份的认同焦虑。影片最后,导演将朱老放置在美国耸立的高楼前,近景和远景的交替使用便是对其无所适从的迷茫感进行的镜头表达。
(二)建构性的“他者”
相对于从属性的“他者”对人们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影响,建构性的“他者”更加多元,对跨族裔群体的身份认同也起到更为深刻的作用。这是因为建构性的“他者”往往对自我起到建构甚至是掌控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自我原有的身份认同。同时,人们跨越族裔和国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面对身边的“他者”,主体内心的“恋地情结”会被激发出来,但是当这种情感被强烈地感受到时,就说明主体已经离开了这片土地,作为家园寄托和记忆储存的土地就成为了一种符号化的存在。所以,跨族裔群体一方面要经受离国之后强烈的恋地情结,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处境对自我的影响。对于长期居于海外的移民来说,他们不得不打破民族之间的各种壁垒,克服语言的障碍和文化间的隔阂,以便能够在西方霸权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偏见中更好地生活。他们试图与身边的“他者”相处,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在两者的交往当中不断更新自己的身份认同。《喜宴》当中的高伟同便是如此,由于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他逐渐适应了美国的环境。他能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习得美国的饮食习惯,工作上也能得心应手,并且在美国的土地上培养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明确了自己的性取向,并根据环境的转换和自身的需求更新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与“他者”的交往当中,面对异己的他性,他没有将差异性放置于两者关系的顶层,而是在接受这些差异的基础之上,寻求着交往和融合,试图弥合两方文化之间的鸿沟。但是,当面对自己父母的逼婚,他又不得不向传统的伦理文化妥协,隐瞒自己的性取向,选择与一位没有感情的女性假结婚,以维持家庭的和谐。其实,高伟同来到美国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逃避父母以及原乡带给自己的束缚,但是尽管实现了逃离并完全适应了他乡的生活方式,也依旧没有勇气完全割离过往的记忆,也没有真正地抛却过往的身份归属。
三、找寻认同的永恒焦虑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正如美国学者阿帕杜莱所讲的,“如今我们所处的世界似乎是根状茎式的,甚至是精神分裂式的:一方面召唤出理论去解说无根、异化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心理疏离,一方面营造着电子媒介下亲密感的幻想”[6](37)。世界在不断融合,但是个体的无根性却不断加强,身份归属也越来越模糊。所以,对于跨族裔群体来说,作为移民身份的个体无法逃离“他者”的异化和被“他者”的命运,也无法从根本上逃脱文化记忆对自我的影响,因此,他们身份的无根性和个体与群体的疏离感便更加强烈。而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由于个体的身份认定具有多层面的特点,移民群体往往需要从族裔身份、社会身份、文化身份等多维度进行思考,但这难免陷入永恒的焦虑当中。这是由于人们对于安全的本能需要,会促使人们寻求一个固定的程式,并在这程式当中获得永恒的安全感,但是,人自身便是变动不居的,不可能永远生长于一个程式内。身份从来不是同一的或统一的,也不是永远处于一个不变的状态,身份应该是多元的或破碎的,同时也处于持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倘若非得确证自己的身份认同,那将会陷入到一个永恒的焦虑陷阱。
(一)源于安全需要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们对于安全的需求仅次于对维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转的生理需求,也是人类作为一个自然有机体进入到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需求。而对于跨族裔群体来说,陌生的生活环境、异质的文化观念、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些都会激发个体的生存焦虑,他们无法确知和认识自我,对现实处境充满怀疑情绪,甚至产生无力逃脱的脆弱感和无助感。所以,个体的不安全感与对安全的渴望,驱使人们不得不找寻自我存在的归属,来确证自己的身份。就像顾威威为了一张绿卡,选择与一名同性恋假结婚,以获得能够在美国生存的国籍身份,朱老为了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只能用每周去教太极拳的方式来排遣自己,进而在美国获得被人认可的社会身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社会及群体对自己的认同,进而寻求自己的身份归属。但是,对安全的需求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具有着不可完成性,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也不可能因为国籍身份和社会身份的获得而终止,个体精神的无处皈依才是身份无法获得认同的缘由。
(二)不可完成的身份认同
当我们在谈到“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假定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内在于我的主体性之中的一个基本身份,一个区别于你、区别于他的独立的身份”[7](28),所以,自我身份的确认必须有一个“他者”的存在。而自我在与“他者”的参照当中,自我的记忆会不断被激活,以反观自我和自身,自我再借助这一反观回归到自我记忆当中,更新着自我的存在。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谁需要身份?》一文中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分析了身份认同丰富的语义内涵,他认为身份认同是一种建构,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总是在建构的过程之中[8](2-6)。所以,身份认同作为一种建构,它导向身份的动态而非固定的静态,人的一生也不可能只有一个身份。因此,企图寻求一个固定永恒的身份是不切实际的,而固执于一个不符合自身发展的身份最终导致的只能是永恒的焦虑。与其拘泥于“我是谁”等本源性的疑问,倒不如将重点聚焦到“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等发展性的问题,在动态发展的过程当中更新自我,建构自我,将身份认同放置在不可完成、永恒开放的状态中找寻。李安的影片大都采用中庸的结局,《喜宴》和《推手》都没有展现故事的最终结尾,这种处理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李安自身对于身份认同找寻的困顿。高伟同和自己的爱人西蒙还有顾威威三人相拥目送父母的离开,看似达到了一种和谐,但是所有人都在向现实妥协着,高爸爸最后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动作,这也是在向现实投降,他们在身份认同的危机面前,在背后做出了本不应该的牺牲。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当中,移民群体只有不断更新自我、建构自身,而不是企图寻求一个固定静止的身份,不再去发现身份,而是去生产身份,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够摆脱现实的困境和心理的困顿以及身份认同的焦虑。
四、结语
跨族裔生活成为当代重要的社会现象,伴随而来的跨族裔电影创作也日益繁荣,这类影片在展现移民居于海外所经历的现实处境和所体会的精神感受的同时,也难逃对身份认同困境的探讨。大多数有着移民生活经历的导演纷纷开始进行跨族裔创作,由于导演自身移民的身份,在构建电影语言时所体现的思想内涵也更加真实深刻。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新时期移民题材的电影也不再仅限于对原乡的找寻,而是试图融入到移民地区的主流文化当中,在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找寻到一种能够完全适应现实社会又不抛却过去记忆的身份归属,以一种具有独立性、包容性的文化身份立场和多元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传统的本民族文化和当下的异域文化,建构一种永不终结的、不可完成的身份认同。所以,跨族裔导演在塑造人物形象乃至建构电影语言时,应既不脱离自身传统的本民族文化视野,也不对异域文化采取敌对态度,在不断生成、建构的过程当中赢得自身的话语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身份认同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