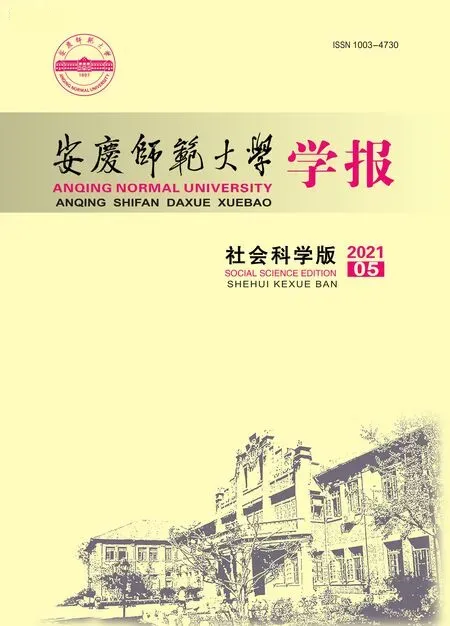从“汉民族国家”到“中华民族国家”
——孙中山民族国家理论的历史转变
2021-11-28才圣
才 圣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天津300134)
“民族”与“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百年变革之中的一大主题。在中国由传统“天下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都曾提出过自己的民族理论与相应的政策主张,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且在制度层面得到过全面落实的,当属孙中山。他所倡导的构筑“中华民族国家”被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成为那一时期国家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并非最初就将构筑“中华民族国家”作为自己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从1894 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到1925 年病逝的30 年间,孙中山的民族政策历经了由“汉民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再到“中华民族国家”三次转变,跨度大,变化快。“汉民族国家”“五族共和国家”与“中华民族国家”三者之间究竟具有怎样实质的差别?孙中山为何会摒弃前两者,而最终选择了“中华民族国家”作为自己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又是哪些关键因素促使孙中山在民族政策方向上做出如此频繁和重大的调整?有关这些问题的解答,无疑对我们理解中国由传统“天下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型进程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追求“汉民族国家”
1894 年,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并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入会誓词,所谓“鞑虏”即指清朝的满族统治者。1905 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又同样写入同盟会的十六字革命纲领,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
事实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口号并非孙中山的首倡,最早出现于朱元璋北伐元大都时发表的北伐檄文:“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1]
中国自古以来受“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认为华夏民族(即生活在中原内的汉族)的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四周的蛮夷戎狄(即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因此,只有身处文明中心的华夏才可以成为天下秩序的主导力量。但是,“华夷之辨”所体现的只是中国古代华夏民族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化优越感”。“‘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2]所谓华夷之“辨”,事实上乃是“文化”之辨、“文明”之辨,而非“血统”之辨、“人种”之辨。因此,所谓的华夏民族(即汉族)并非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人种共同体”,而是一个“文明共同体”。任何非汉族成员只要接受汉族文化,就会得到汉族群体的认同,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可以说,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华”与“夷”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分野。正如韩愈所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近于中国则中国之”。
由于元代的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始终拒绝接受汉族文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才会在“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作用下,视其为“夷狄”,并把“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作为推翻元朝统治的政治动员口号。
然而比起元代的蒙古统治者,清代的满族统治者在是否接受汉族文化这一问题上,表现却大为不同。早在康乾时期,满族统治者即对汉文化表示敬意[3]。至19 世纪初,满人的汉化进程已呈不可逆转之势[4]。19世纪末,满族统治者更是向汉人开放自己的世居之地东北,并在随后的新政改革中,极力化解“满汉畛域”,废止满汉之间的通婚禁令[5]。可以说,清代的满族,无论是其居住地还是其民族,都整体性地归并、融入于中华一体。因此,孙中山将早已高度汉化的满人依然视为“鞑虏”,无疑带有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色彩,事实上也否认了中国自古以来“接受了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的这一传统。章太炎就曾明确表示:“纵令华有文化之意,岂得曰凡有文化者,尽为中国人乎?”[6]735
在当时的革命党人眼中,只有汉人才可称得上是中国人,而满人作为异族胡虏,应当被汉人驱逐出中国。1906 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曾明确指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7]14在晚清革命的理论阐述中,革命党人成功构建起了一个“中国人=汉人”公式。这对后来民国的国家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清中国传统天下秩序遭遇西方“民族主义”(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思潮的猛烈冲击,中国社会被迫开启了由“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历程。建设“民族国家”,可以说是当时全体中国人的共识。然而,在建设“民族国家”的具体路径选择上,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其一为梁启超提出的“合群救国论”与“大民族主义论”,即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8]。而这一主张被当时的晚清政府所采纳,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应当遵循“先国家、后民族”的道路,即以国家现有疆域为基础,打造一个与国家相等身的“大民族”。因此,晚清统治者曾积极推行帝国边疆地区的“行省化”和针对非汉民族的“同化”等“新政”,试图通过政治整合与文化整合手段,将边疆少数民族整合进“汉族”,以建设一个同化其他少数民族的“大汉族国家”。按照晚清政府的政治构想,这一未来国家的地域范围既包括汉人生活的中原内地,也包括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人口范围既涵盖汉族,也涵盖未来将被汉文化所整合的边疆少数民族。
与梁启超和当时的晚清政府截然不同的是,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人看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却应当遵循“先民族、后国家”的道路,即以现有“汉族”这一民族的尺寸,来设计未来中国的疆域范围。依照此种建国思路,不仅满人应当被驱逐出中国的范围,蒙古、西藏、新疆亦不在中国的范围之内,章太炎就曾在《中华民国解》中说道:“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6]738因此,不同于晚清政府努力打造的“大汉族国家”,革命党人所寻求建立的新中国,乃是一个人口范围仅限于汉族(而无需整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域范围仅辖中原内地的单纯的“汉民族国家”。
晚清革命党人所宣扬的这种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观念,其主要目标就是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以唤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之心,最大限度动员革命力量。但是,这种观念也同时将中国引向了一个埋有隐患的未来,即一旦“鞑虏”被驱逐,满清政府被推翻,中国就有陷入民族分裂的可能。因为,已经与汉族在文化上高度融合的满族尚且被革命党人排斥在“中国”之外,更遑论蒙古、西藏和新疆,其必然会随着清政府的垮台与“中国”分道扬镳。
孙中山试图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旗帜之下,建构一个单纯的“汉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不经意间给中国埋下了民族分裂的巨大隐患,而如何去化解这一隐患,对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人而言,乃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二、打造“五族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呐喊之声骤然沉寂,转而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对于当时的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人而言,如何能够全面继承清朝留下的广袤领土这一政治遗产,尽快摆脱革命动员时期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观念给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避免满、蒙、维、藏等少数民族在汉人“驱逐鞑虏”的革命动员中走向独立自决,乃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当务之急。而“五族共和”的提出,正是孙中山针对这一问题紧急出台的一项补救措施。
所谓五族共和,就是建立“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平等共处、互亲互爱的中华民国。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于《临时大总统宣言》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独立,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9]1912 年3 月11 日,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条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10]为更加直观体现“五族共和”,中华民国还放弃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所用的象征内地十八省独立的十八星旗,而是将国旗确定为分别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彻底抛弃了革命时代“驱逐鞑虏”、追求建立单一“汉民族国家”的政治构想,转而试图建立一个由“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享的“多民族国家”。在1912年9月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西北协进会演讲中,孙中山明确表示“但愿五大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共赴国家之事”[7]115;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讲:“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7]107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对“五族共和”多有赞许和期待:五大民族能够在“中华民国”这一共同的政治屋顶之下,同为国家平等的公民、同为国家政治的主人、同为国家命运的主宰。
“五族共和”的提出,使得新生的中华民国合法继承了清朝原有的统治疆域,暂时避免了由政权更迭带来的国家分裂,并开启了各族人民在共和政体下共谋、共享“共和之福”的历史进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孙中山关于“五族共和”的政治畅想依然蕴藏着一定的理论局限和政治危机。因为,五族共和的主体是相互平等的“五族”而非“一族”,其最终目标是将中华民国建设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而非“单一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就必须扭转自晚清以来谋求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对于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及其对于本民族的世居地域的传统自治权,中央政府亦必须给予正式承认。例如,继承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1912年8月制定颁布的《蒙古待遇条例》中就明确规定:“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11]
“五族共和”本身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整合手段,而是一种消极的“承认政治”,它并没有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在共和体制下恢复、重建并增进民族关系提供更为积极的制度保障。
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认为,人们是通过追问他们“认同谁”和他们感到“与谁休戚相关”,来决定他们想与谁分享一个国家的,而此种认同感实是源自于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而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之间难以共享的恰恰是这些东西[12]。印度学者巴赫拉也曾断言:为了使许多族群共同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需要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中提炼出一个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其基础是历史中各族长期共享的社会伦理、生活方式和彼此的文化认同,而凡是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族群间的“共同文化”,凡是近代没有发展出以这样的“共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多民族的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nationstates),必然存在解体的风险[13]。
反观民国初年,这样一种能够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所共同分享的历史和文化是不存在的。虽然清王朝在此前治理中国的二百余年间,统辖了前所未有的为数众多的民族集团——汉时之西域,唐时之吐蕃,明时之蒙古,全被其纳入版图——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屋顶之下。然而,直至1884 年,清王朝却始终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推行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尤其对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实行更加严格的管控,并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分化、封禁、隔离几乎贯穿了清政府民族政治的始终[14]。这种民族政策直接导致了清帝国治下的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其他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缺乏了解,情感淡漠,更遑论形成相互的认同意识。因此在民国初年,孙中山试图通过“五族共和”这种消极的“承认政治”来整合已经相互隔绝长达二百余年的五大民族,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民国建立之初的边疆形势(尤其是蒙藏地区)也给“五族共和”的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912 年,外蒙古即在宗教首领八世哲布尊丹巴的领导下宣布独立,建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并同时向内蒙古、新疆等地的蒙古各旗发出了统一蒙古的“谕令”,劝谕各旗“一体归顺”,甚至一度出兵进犯内蒙古[15]。1915年6月,在沙俄的干涉下,《中俄蒙协约》签订,虽然条约中明确规定了中国对于外蒙古的“宗主权”,但却也使得外蒙古成为了一个以“自治”为名、行“独立”之实的“国中之国”[16]。1912年,西藏宗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下达了所谓的“驱汉令”,将清政府在西藏苦心经营的“驻藏大臣”及其一整套行政、军事体系,全部驱离西藏,以至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西藏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
由此可见,“五族共和”这一脆弱的政治纽带,根本无法有效连结中华民国初年的几大民族。能否探索一条全新的、姿态更为积极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架构来凝聚各个民族,对于孙中山而言,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构筑“中华民族国家”
1919 年,曾对五族共和报以极大热情的孙中山,开始在其撰写的《三民主义》中对五族共和的政治立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中华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17]154
仅仅时隔八年,孙中山的政治立场何以在1919 年这一时间点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由热情倡导“五族共和”转为严厉批判“五族共和”?这一方面源自于当时国内危机的边疆形势给“五族共和”带来的现实冲击,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世界政治格局发生的剧烈变动有莫大的关联。
1914年至19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场大战中,两个老牌的多民族国家,即“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终沦为战败国。而这两个多民族国家内部频频爆发的民族矛盾和此起彼伏的民族分离运动,也让它们在战争中饱尝苦头。例如在1916 年,奥斯曼帝国内部爆发了阿拉伯起义,使帝国原本在中东大好的战场形势迅速逆转,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军队伤亡惨重。
一战后期,为处理即将战败的奥匈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即主张任何一个民族均有权自主决定其自身的政治存在及其类型。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在向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了其认为是促进世界和平“唯一可行”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第十点和第十二点分别提出了应允许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内部各民族走向“自决”。事实上,为挽救帝国内部的民族分裂危机,奥匈帝国曾经试图用“联邦制”来化解其内部少数民族的自决诉求,以换得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但威尔逊总统对此却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哈布斯堡王朝谋求建立“联邦制国家”的观念不可行,这一答复直接为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分裂吹响了号角。最终,曾经辉煌一时、跻身世界八大强国的奥匈帝国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土崩瓦解,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随之在内外交困中走向民族分裂。
这两个庞大、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极大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理,从此东欧和南欧的土地上出现了一批崭新的“民族国家”,如波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这是20世纪世界掀起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这一发生在1918年的重大政治事件,一定对远在中国的孙中山心里造成强烈的震撼。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当时孙中山的心里一定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同为“多民族结构”的中华民国避免发生类似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分裂悲剧?由此,孙中山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热情赞许“五族共和”转而激烈批判“五族共和”。这一转变正是孙中山在世界“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历史背景下,鉴于国内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对中华民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做出的深刻反思。
孙中山认识到,在一个“民族主义”思潮风靡的世界里,试图通过“多民族共和”体制来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是不可行的。“通过提倡‘五族共和’来达到保全国土之目的,这种思想从逻辑上来看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五族共和’的行为主体是‘五族’,因而‘五族’之间的‘共和’能否成立,即‘五族’是否能够共同携手建设‘中华民国’,其前提并不在于其中一个民族是否能够振臂一呼,而在于五个民族是否能够达成共识。”[18]203鉴于当时中国的实际形势,即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下,“即使只有其中一个民族中出现要求民族独立的声音,‘五族共和’的口号就不仅失去统一中国、保全领土的意义,反而可能会被一部分人用来作为主张独立的根据。”[18]204因此,1919年之后,孙中山便彻底放弃了“五族共和”的政治立场,转而积极倡导要将“五族”整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构筑“中华民族国家”。
1920年,孙中山在《修改章程之说明》中指出:“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7]328至于如何实现“把我们中国所有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这一目标,孙中山提出了用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文化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同化理论”。
1921 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提出:“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此时单讲汉族,不虑满、蒙、回、藏不愿意吗?……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中心,使之同化于我们。”[7]345“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民族主义的国家。”[7]344
从孙中山的以上表述来看,他所积极倡导的“中华民族”,事实上就是一个同化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改名换姓了的“大汉族”。经过多年的政治实践,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如想从根本上化解“民族主义”的冲击和挑战,中国就必须坚定迈向建构“中华民族国家”的政治道路上来。
与此前革命时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单纯的“汉民族国家”这一“先民族、后国家”的政治道路相比,构筑“中华民族国家”显然是一条“先国家、后民族”的政治道路,即以现有的国家疆域为基础,打造一个与国家疆域相等身的“大民族”。此时孙中山脑海中所建构的中华民国,乃是一个人口范围既涵盖汉族,也涵盖其他少数民族、地域范围既下辖传统的中原内地,也下辖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单一民族国家”。这无疑超越了其在革命年代所持有的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观念,也重新站到了当年与之对立的梁启超先生和晚清政府的“合群救国”与“大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此前消极的“五族共和”相比,构筑“中华民族国家”无疑是一项更为积极的民族政策,其直接目标即是通过“文化同化”手段,将中华民国这一“多民族国家”,整合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由此一劳永逸地杜绝因“民族自决”带来的“领土分裂”。
至此,构筑“中华民族国家”,成为了孙中山在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的最终取向。虽然1924 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曾一度提出“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19],似乎昭示着孙中山先生在民族政策上的再次转向。但据学者研究,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内容,事实上是孙中山在苏俄的压力之下被迫做出妥协之后,才公开发表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并不赞同,并始终坚持自己非常清晰的主见[20]。
四、结 语
孙中山构筑“中华民族国家”的政治畅想,体现了其在波诡云谲的近代,对于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的良苦用心。比起“多民族国家”体制,“单一民族国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彻底杜绝“民族问题”。然而,在构筑“中华民族国家”的具体路径上,孙中山却选择了明显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同化主义”模式。从实际的政策效果上来看,同化主义自20 世纪以来往往会遭致“反抗性民族主义”,即少数民族会为了保护其语言、文化和自治制度而战,有时就是暴力抗争。这一模式在现代文明的映射下,已然丧失了其正当性与合法性,这也正是孙中山民族国家理论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