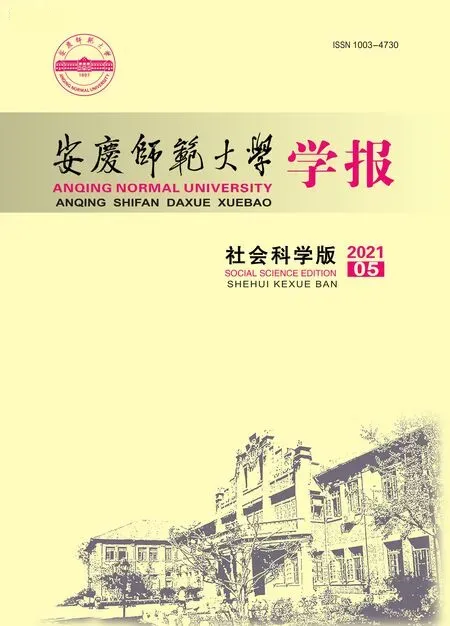宁默而生:南宋社会舆论的另一面相
2021-11-28徐紫林
徐紫林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宋代作为中世重要变革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彰显出与前后朝代显著的差异。整个社会的言论格局同样产生变迁,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其中两宋君主以“誓不杀言官”及一系列保障言论自由的政治措施获得了宋人及后世的广泛赞誉①宋人何坦言:“我宋之祖宗,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西畴老人常言·原治》,丛书集成初编第369册,第13页。)叶适言:“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二《国本中》,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48页。)南宋时期的陈傅良也夸赞:“朝家以不杀士为国是。”(《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父(第三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明清思想家王夫之认为“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宋论》卷一《太祖誓不杀士大夫》,收录于《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4页。)。近年来,随着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宋代言论自由度受到了学界的特别关注,大多认为宋代有着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和高度的言论、思想自由。陈寅恪曾言“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1],程民生认为“宋代思想界、政治理论界并没有绝对权威不可侵犯,言论度相当大”[2],赵云泽指出“宋代是古代社会中言论最为清明的一个时期”[3],李国文认为“宋朝居民的自由程度绝非前朝所能企及”[4],魏海岩断言“宋代是古代时政舆论发展的高峰时期……仿佛一切运作全凭舆论”[5]。所有探讨这一问题的学者都从正面对宋代舆论环境给予高度评价。
作为北宋的延续,南宋承袭北宋政治制度,未有颠覆性的变革。这也极容易造成对于南宋政治结构认知落入“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窠臼中。实际上,南宋与北宋政治生态存在很大差异,最为突出的政治特征莫过于君主独断的加强与权臣秉政的频出。从理论上说,政治生态一经改变,则势必会对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全局性的弥散影响,言论自由格局也在覆盖影响下悄然发生转变。南宋君相将臣僚的决策话语权集中起来,不断压缩参议朝政的论政空间,甚至倡兴文字狱等高压极端措施整肃异论者,钳制思想言论,其他诸如武臣、近习、宦官等势力对于士大夫话语权的侵预,致使社会舆论呈现出集体失语或谄谀盛行的畸形状态,这不禁要对宋代言论所谓的自由、清明印象产生了困惑和疑问。浸润于特殊政治生态环境中的南宋朝野仍能保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自由言论的锐气与精神吗?宋代言论自由度是否还存在另一面相?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南宋政治势力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试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共治落幕:南宋君主对于士大夫论政自由的限制
首先,南宋君主对于独断有着高度的自觉与向往,不断压缩士大夫议政空间。北宋相对宽松舆论环境的形成取决于赵宋优待士大夫与不杀言官的祖宗家法。为后人一再引用的“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以视为士阶层在政治运作中占据轴心位置,拥有强大的政事话语权。这种士大夫对权力能动的分享是北宋立国以来所建构的中央控制模式的产物。君主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依靠官僚群体治理国家。但至南宋时,金蒙环伺造成外部形势的恶化,生存空间日朘月削,加之共治体制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逼迫南宋君主更加注重内部秩序的稳定,做出应急性调整,谋求逆转中枢的制衡结构,建立具有个人意志色彩的独裁体制。极权体制的建立昭告士大夫政事话语权已被剥夺殆尽,回归北宋共治理想模式的艰难努力以失败告终。独裁统治路径一经确立,很快纳入赵宋祖宗家法范畴,成为君主奉行的治国圭臬。因此能够看到南宋诸帝对独断专行孜孜不倦的追求,打破人主与百官“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的固有平衡,建立某些特定的制度、运作机制将话语权集中,压缩朝野“公议”空间。
宋高宗出于维护独裁权力的需要,联手秦桧创建绍兴体制。为了贯彻对金妥协的政治路线,不仅取消了以往的朝议及集议制度,甚至动用国家权力严厉整肃对体制有异议的朝野士大夫。在绍兴体制建立后的年代里,尽管也有部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敢于鲠言直议,但旋即遭到仕途上无情的打压,伴随禁令愈密,“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对李光、胡铨、张浚等主战派的贬黜无不显示出此时政治生态已经背离北宋优待言事者的宽松政策。高宗对于敢言刚直士风的重创致使社会舆论呈现一元化状态,官僚士大夫们“口虽竞而心疲,心虽愤而气荼”心忧国事的热情全面退去,很少再对王朝的安危畅所欲言。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敏感地记录了这一变化:“自定和策动之后,士大夫无有敢少违其意者(按:指高宗与秦桧),故一时轮对臣僚,但毛举细务,以应诏旨。”[6]2013
宋孝宗被誉为南宋最为杰出的君主[6]692,论者通常概括其在位的多数时期政治①韩冠群根据孝宗对军政文书通进渠道建立的动态考察,认为宋孝宗统治的前二十年确是君主独断专治,但在后七年时间里,无论是文官制度的制约还是个人因素而言,中枢政治又回到君臣共治的格局中,参见氏文《南宋孝宗朝君主独断统治及其演变——基于军政文书通进运行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137页。特点为“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体制”“独断的政治运营”②参见王德忠:《宋孝宗加强专制集权浅论》,《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何忠礼:《南宋政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4-238页;小林晃:《南宋孝宗朝における太上皇帝の影响力と皇帝侧近政治》《东洋史研究》第71卷,第1号,2012年;藤本猛:《武臣の清要——南宋孝宗朝的政治状况与閤门舍人》,《东洋史研究》第63卷,第1号,2004年。。孝宗亲历秦桧专权,不愿蠹政之弊再现,不予官员久任。史称孝宗朝“勤于论相,数置而亟免”[7]。据统计,孝宗朝共计16 位宰相,平均任期只有1.5 年,远低于南宋宰相平均任期3.4 年[8],出任参知政事者竟高达三十四人。多数官员不出数月,就将其调换“丞薄不数月望为郎,自郎不数月望为卿监”[6]3962,致使官员施政方针大多未及实施,“练兵以图恢复而将数易”,“择人以守郡国而守数易”,结果“官无成绩”[9]11967。与之相对的是孝宗“躬亲权纲,不以责任臣下”现象的突出[9]12027。与高宗朝一样,每有国家大事,孝宗同样不实行集议。兼听是假,独断是真的政治倾向致使朝臣在处理政务中或禀承人主风旨,或畏葸避事,缄默不言。《宋史·徐谊传》载:“孝宗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唯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9]12083
宋宁宗时,鉴于外朝道学士大夫大量入朝,势力不断扩大,及赵汝愚废父立子推动内禅对于皇权严重侵犯的忌惮。宁宗排斥官僚政治决策,更多通过“御笔”指挥政事,突出君主在行政命令发布中扮演的权威姿态。黄度对肩负国政的官僚群体不能议政,致使国政混乱的事态进行猛烈批评:“祖宗以来,人主虽独断于上,但天下事必经中书,未有直以御笔裁处的……近来台谏、给舍屡有更易,中书无所参预,御笔渐多,实骇观听!”在官僚集团眼中御笔是君主“私的王言”对朝廷“公言”的侵害[10],大夫群体遭到冷遇,只能在官僚体制运行中暗默旁观。
其次,南宋君主对于进言的实际态度,影响士大夫言事的积极性。北宋君主对于言路尤为重视,基本上恪守虚已纳谏的祖宗家法,鼓励直言极谏。如宋太宗反对以妄言入罪,表示“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11]仁宗曾言“朕未尝以言罪人”[12],程颐称赞哲宗容受谠言:“朝廷宽大,不欲以言罪人。”[13]北宋所凸显出的“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自由言论的状态与君主积极鼓励进言密切相关。但这一情况至南宋时已大有不同,尽管君主仍表示出在意舆情风向,容受谠言,致力于信息渠道建设的纳谏姿态。但归根结底,言路必须服务于君主,这一原则必将限制南宋朝臣进言的内容与范围。正如邓小南所言:“统治者历来警惕言路批评‘过度’,更不容其站到君主意志的对立面。”[14]孝宗乾道四年(1168)欲再次对金用兵,遂将参政蒋芾擢为右相都督军队。但蒋芾以“天时人事未至”不同意北伐,孝宗大怒,罢其相位,出知绍兴府[9]11819。光宗时期,围绕过宫事件的争执加重了光宗与臣僚之间的隔阂,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对朝野此起彼伏的劝谏,光宗以表面应和,背后贬黜进劝朝臣的方式予以回应。楼钥就此批评道:“比年以来,朝行不闻直声,而有以多言被黜者。虽蒙宽恩,此从外补,不加之罪,然士气消沮,无敢出位而论事者。”[15]卫泾更直斥光宗“听纳虽广,诚意不加,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16]。理宗朝,殿中侍御史杜范批评宋理宗“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实”[9]12282。敏感的朝臣会对君主的实际执政倾向小心观望与揣摩,先行过滤会引惹君主不悦的进奏内容。因此经常能够在南宋史料中看到臣僚禀承人主风旨,逢迎上意的情形。朱熹曾提醒孝宗:“今日言事官欲论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17]2733乾道年间参政蒋芾对孝宗解释江西水灾隐匿原因时强调“州县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乐闻”[18]。
一般而言,高居政治顶峰的人主,深知广开言路,延展视听,以便施政,共治模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但当政治结构发生逆转,君主谋求独断,对士大夫论政空间不断压缩,对敢批逆鳞直言逐渐反感。凡此种种,促使南宋士大夫对进言内容反复斟酌。
二、文狱迭兴:南宋权臣对于朝野舆论的钳制
南宋政治生态中另一突出现象即是权臣秉政,仅统计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位专权时间,便长达七十余年,占据南宋国祚的一半。权臣专政局面的形成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权臣对于左右舆论尤为重视,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管控。
确定导墙基坑开挖线,并报监理验收合格后进行基坑开挖,施工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轴线、标高以及坡度,导墙沟槽机械开挖至离设计高程差0.2 m时,采用人工清理至设计高程。施工平台边坡采用编织袋装砂砾护坡,以保持施工平台边坡稳定。
首先,把持言路。言路在宋代语境中广义上指的是朝野向君主进言的渠道,狭义上即指台谏系统[19]。台谏在宋代政治运作中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大凡政局变动、官员进退无不与之产生紧密联系。台官“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官廊庙则宰相待罪”,被视为宋代元气所在。权臣清醒知道扼制舆论与专擅朝政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最为关键的就是“择人为台谏”,让左右舆论的台谏官为己所用。权臣或以高官厚禄诱以柔佞而无名望的幸进之徒,如秦桧任相期间“每除台谏,必以其耳目”[20],凡台谏附已者“辄以政府报之”[9]13765,黄达如、曹筠、罗汝楫等谏官都是按此升迁,或以酒肉拉拢、订立约言,史弥远秉政时“凡除台谏,必先期请见,饷以酒肴”[21]。梁成大、李知孝、莫泽等谏官“皆其私人”。控制台谏选任后,便利用台官,钳制舆论。如绍兴和议前后,秦桧鉴于朝野议论汹汹,此起彼伏的反对声,采纳中书舍人勾龙如渊的建议“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阴受意旨的台谏官们将异论者定位“怀奸”分子,请求“明诏大臣,崇奖廉隅,退抑奸险”“尽诛前此异议之士,庶几以杜后患。”在高宗的认可下,秦桧不断以台谏贬黜坚持异议的士大夫“每要去一人时,只云劾某人去,台谏便着寻事上之”,胡铨、王庶、张九成、赵鼎等一批主战官僚都被劾为“小人”,遭到政治迫害。持续的弹劾令政治氛围肃杀凄戾,至绍兴中后期,已很难见到朝野异论者。史称“秦桧在相位,颐指所欲为,上下奔走,无敢议者”[22]。
除台谏以外,注重防范壅蔽的宋代君主强调进言渠道的多样性,建立了相互补充,共同发挥进言作用的舆情沟通机制,诸如近臣宣召、经筵咨询、官员入对等。权臣对于这些舆情渠道的管控也同样重视。如秦桧首创“每除言路,必兼经筵”政治模式,经筵交流是君主了解舆情的重要方式之一[23],具有固定性与时间更较宽裕的特点,君主与士大夫能够在经筵场域中更为充裕的商谈政务,士大夫也更容易引导君主做出决策。故而经筵详情成为权臣汲汲关心的内容,秦桧以台谏兼经筵讲读官,从而达到交通台谏的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君主通过其他官员获得异已信息的可能。“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秦桧把持了经筵这个舆情交流渠道,占据了君主最后的空间,形成对于朝堂舆论的全面掌握。在此背景下,士大夫逐渐对进言丧失信心“自桧扼塞言路,士风寝衰”“朝士多务缄默”[24]。这一模式也为继任权臣所沿用,韩侂胄时期“台丞、谏长暨副端、正言、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9]3815。另如孝宗时期,胡铨向孝宗提出起居官应获得直接上殿奏事的权力,本着增加广开言路防范壅蔽的政治目的,孝宗“诏从之”。至度宗时期,起居舍人王应麟通过“牒阁门直前奏对”弹劾贾似道,虽未成功,但引起贾似道的警觉。贾似道认为这一特权存在让度宗接受诸多不利己信息的可能,于是“方袖疏待班,台臣亟疏论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废”[9]12990,切断了度宗与起居官的沟通渠道。
其次,屡兴文禁。作为权臣专制政治中普遍具有的政治文化行为与突出表现形态,文禁、语禁等成为铲除异己、钳制舆论的有效形式,并呈现诸多新特征。
第一,管控对象呈现广泛性。北宋党争中的文字狱,对被遭贬后的官员大多无意穷追猛打,但至南宋,得势方多有将反对派及及相交者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意。相对北宋零星的文字狱来说,南宋文字狱的外在表象趋于一致性,凸显出规模特征。绍兴八年(1138)胡铨因乞斩秦桧,先是被贬至福州,后再遭除名勒停发配新州。秦桧对于胡铨的迫害激起了民间舆论的同情与义愤,江西隐居诗人王庭珪作《诗胡邦衡之新州》送行。诗文在士大夫之间广为流传,数年后被人告发,秦桧以“谤讪朝政”罪将其流放编管。此案祸及多人,不仅王廷珪“父子俱系狱”,连逮赣、吉两州守臣、通判等六位官员因对王庭珪诗文“不切究之”均降官一级。王庭珪诗文案迫使诸多声援胡铨者害怕因祸上身,纷纷缄默不言,“一时士大夫畏罪钳舌,莫敢与立谈。”同样,江西运判张常将前帅张宗元与主战派张浚交通的书信上交朝廷,诬陷其图谋不轨,受到牵连者“多逮数十家”。史载秦桧实施文字狱过程中“凡与之交际者,亦必被祸不少贷”。
权臣打击对象并非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对于普通百姓也同样如此。绍兴十一年(1141)侍郎张九成父亲去世,遂来到高僧宗杲所居住的径山,为父亲“修崇”。宗杲借机夸将张九成誉为“神臂弓”并赋诗“神臂弓一发,透过千重甲;子细拈来看,当甚臭皮袜!”[25]23-24秦桧认为诗中“臭皮袜”有影射自己的嫌疑,诏宗皋“毁衣牒,窜衡州”[26]。绍兴十五年(1145)秦桧设宴,席间有伶人用隐语指斥秦桧卑躬屈膝,为稳坐太师交椅,不顾南宋国家大义,将恢复中原、迎还徽钦二圣忘却脑后。当场文武百官听闻“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27]251。绍兴十六年(1146)年方十四岁的王谊,因在塾中拈纸写“可斩秦桧以谢天下”被人告发,秦桧大怒,王谊编置象台,其叔王苹受到牵连,坐“知而不告”废置终身[28]232。庆元元年(1195)故丞相赵汝愚暴死,民间争相悼念,太学生敖陶孙酒意酣张后,题诗“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痛斥韩侂胄迫害忠良,秉政误国,愧对先祖北宋名臣韩琦。韩侂胄阅后立即下令“捕治之”,敖陶孙“移送大理劾其事,掠治无完肤”,“送岭南编管”[28]310。此事后,临安虽仍有悼诗出现,但都不敢署名多“赋诗摹印,揭之都市,而匿其名”[17]4852。理宗时期,史弥远阴谋废立、逼死济王引起朝野震动,掀起声讨高潮。史弥远唆使言官对反对者罗织罪名,进行弹劾,一时“名人贤士,排斥殆尽”。朝堂舆论虽然得以控制,但史弥远忌讳民间异已意见。言官李知孝与江湖诗人曾极有私仇,正巧临安府书商陈起刊出收录曾诗的《江湖集》,李知孝便诬陷该集有影射史弥远专政之嫌,一帮趋炎附势之徒在诗集中积极寻找能影射罗织的罪证。刘克庄的“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轮”一联被认定为指斥史弥远跋扈擅权,曾极的“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一联被说成是对贬居济王的同情。不久《江湖集》被禁止刊行,书商陈起被黥面流放,刘克庄、曾极等诗人均遭到严惩。更为严重的是,史弥远借此机会,实施诗禁,至此以后“南宋诗坛万马齐喑,变得死一般沉寂”[29]。社会地位卑微的伶人、戏言的顽童、佛门高僧、醉酒的太学生、混迹江湖的游士都成为管控对象,可见权臣们心胸的狭隘与手段的毒辣,以及对于民间舆论控制的严密。
第二,惩处程度呈现残酷性。对于南宋权臣来说,制造文禁除了攫取权力,营造利已的政治环境才是最终目的。从南宋因言获罪类型来看,基本囊括了古代严刑罪名,诸如“帮讪朝政”“动摇国是”“指斥乘舆”等。这些罪名轻则流放千里,重则处以极刑,为祸之烈令人发指。宋代奉行崇儒政策,太学逐渐成为影响朝野重要的民间舆论重镇,被誉为“社会舆论之喉舌”[30]。其臧否人物、议论朝政直接影响政治走向与官员进退。因此考察南宋权臣对于太学生进言的应对,不失为理解言论管控的良好切片。
宁宗庆元元年(1195)韩侂胄以党植罪名攻罢赵汝愚,激起强烈的反对声浪。太学生杨宏等六人集体上疏朝廷希望挽留赵汝愚。韩侂胄欲以“妄乱上疏,扇摇国是”之名“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但遭到中书舍人邓驿的强烈反对:
自建太学以来,上书言事者无时无之。累朝仁圣相继,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圣明初政,仁厚播闻。睿断过严,人情震骇。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行[31]。
邓驿认为宋代以宽仁为本,太学生上书本属常态,北宋时仅以“听读”略加小惩,现却处以编管过于严苛。但韩侂胄并未理睬,连夜逮捕了这些太学生,并强行押送贬所。宋代对于官员的贬谪制度中,轻者是送某地居住,稍重为安置,再重才为编管。可见,对于太学生们属于从重处罚。
理宗丁大全当政后,广植私党,把持言路,朝中正直朝士先后遭到贬黜,太学生陈宜中等六人上疏揭露丁大全奸恶。丁大全指使监察御史弹劾六位学生,开除学籍,流放边州管制。对陈宜中等人的处罚激起太学其他师生的强烈不满,纷纷出门礼送,以示对高压政策的不屈服。丁大全怒不可遏,诏令三学禁止论政,并立碑迫使学管签名,以示遵循不议国政的圣旨。禁止太学论政,直接切断了体制外力量干涉政务的可能。
三、佞幸得势:南宋其他政治势力对士大夫话语权的侵预
宋代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建立一系列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稳定的制度,其中对于外戚、武臣、阉宦乱政再度发生,制定了种种祖宗家法予以抑制。但尽管如此,囿于部分特殊情况,这些势力马灯似地接连在南宋政治舞台上展现影响力,形成对于士大夫群体的掣肘。
高宗初期,宋金战事犬牙交错,武将权势上升,逐渐形成与士大夫群体分庭抗礼的局面。武将“与庙堂诸公并相往还”频繁干预朝政,汪藻在奏议中言:
诏侍从集议者,所以慎之重之,博众人之见也。而诸将必在焉。夫诸将者,听命于朝廷而为之使者也,乃使之从容预谋,彼既各售其说[6]908。
太常少卿陈戬也在奏疏中反对诸将随时进见,不准其参与谋议政务。武将群体侵夺士大夫们话语权程度可见一斑,士大夫在武将群体的排挤下逐渐被边缘化。尤为明显的例子是官员铨选事务上,士大夫影响力不断退却,宋制规定“中书掌文事,枢密院掌武备”,官员的进退须经决策层的讨论,但这一时期不少文臣、地方州县长吏已不再由中书省任命,而是武将自行除授。绍兴四年(1134)刘大中奏言“文臣除授,未有不由中书者。近钱圻等除授,乃密院直降札子。”孝宗时期,鉴于前朝宰臣专权,对于官僚群体并不信任,选择近习群体加强对朝政的控制,“近习得以乘间而议政”[7]670。龙大渊、张说、曾觌等近习势力与日俱增,权倾朝野,频繁干政。孝宗“所与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也”,致使政令“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9]12754。
虽然士大夫们对此予以强烈抵制,限制近习势力的奏疏片如雨下,但在孝宗的庇佑下,反对近习的行动并没有取得太大的实际效果,反而弹劾的士大夫们接连遭到罢黜“自是无敢言者”[6]103。官僚群体受到打压,话语权遭到严重侵犯“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反出入其门墙(按:指近习),承望其风旨”[17]587。理宗中后期,朝政腐朽,昏聩日甚,敢言直谏的官员不断遭到贬黜,嬖宠浸盛,佞幸用事。卢允升、董宋臣等内侍窃弄权柄,将不附已的言官全部贬黜“其力能去台谏、排大臣,至结凶渠以致大祸”。至此官僚“奉行惟谨”[32],“庙堂不敢言,台谏长期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33]。
南宋部分时期诸多政治势力对于士大夫政治主体地位的打压,致使论政话语权受到严重侵夺。高压政治下少有敢于坚持直言的官员,这种情形的出现,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官员个人品质的优劣。而是浸润于“奉上”思想所致,俗语言“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员对于进言言论的取舍明显受到“顺从上峰”文化的影响及政治局势的左右。
四、余论:言论自由受限对南宋政治的影响
靖康之变,北方沦陷,南宋偏安东南,金蒙相继入侵,压缩了南宋王朝的生存空间。促使南宋君主倾向建立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体制,这一模式当出现君主暗弱时便会衍生出权相或其他政治势力秉政的特殊形态。但无论是何种形态,统治者出于维护专制权力与统治秩序的需要,都会选择高压政策管控言论,这种做法对整个南宋政治产生诸多影响。
第一,造成南宋士大夫的精神意识大受残害,任何异议者被迫禁声,不敢再参与政治讨论。虽然宋代祖宗家法一再呼吁“养臣下敢言之气”[34],君主与朝廷表现出对于舆情的渴求与焦虑,但在南宋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决策者对于进言“沽名卖直”地反感,在直面“直言”“敢言”中又表现出“不乐闻”的真实态度。为了适应政治体制,保全自身安全,官僚集团噤若寒蝉,畏缩不言情况皆非鲜见。例如秦桧与高宗对外卑躬屈膝,力主和议,大肆迫害主战者,致使诸多朝臣“自此绝口不言兵,而专意于浮屠竺幹之书”[35]。史弥远任相时,台官每至上奏时“笔不敢下,称量议论之异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决,吞吐不能”[36]。贾似道专政,直言朝政利弊与其相左者“悉遭贬窜,自此中外钳口结舌,无人敢奏。”这种情形的出现是由政治生态遽变后士大夫群体的一种集体性应对,不能简单归结于个人的品质优劣。高度集中的话语权与朝野的缄默交叉迭合共同构成南宋社会舆论特有的内涵以及感应特征。
第二,夸饰统治,诱导歌功颂德,以至朝野弥漫着阿谀谄媚的风气。严厉整肃与谄媚之风互为因果,共同构成南宋高压政治的表现形态。如绍兴体制建立后,朝野士大夫出于因专制政治的压迫而产生适应性应对,不时主动进献谗诗谀文。连史家郑樵、大儒朱熹等都曾加入其中夸饰“中兴”,遑论其他草偃风从的无节文人,一时间文丐竞奔。这种贯穿南宋上下,不言自明的虚饰,形成强大的舆论压迫力。占支配的谗谀声音日益得势,即使有少异论声音,在“沉默的螺旋”社会心理影响下,这一小部分人力图避免单独持有异论而产生的被孤立,选择妥协与趋从,社会舆论逐渐一元化,谁也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秦桧)日使士人歌诵太平中兴盛治之美,故言路绝矣!”[31]1479
第三,迫使南宋政治精英更加关注地方事务。美国宋学界有一个观点,即从北宋至南宋,政治精英策略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注意力开始由国家转向地方,更多关注地方事务的建设,呈现出“地方主义”的倾向[37]。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南宋士大夫们丧失政事话语权紧密相关。北宋中期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气在急遽恶化的政治生态中遭到重创,士大夫无法为政务畅所欲言,政风逐渐呈现苟且萎靡之势,已全然无复北宋那种“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自由言论的锐气与精神。许多士大夫困顿于仕进,原先更高的政治追求已不再切实可行,只能将目光由向上转而向下,主动或被动的下沉民间。由于南宋对外和战不定,国家精力集中于边患,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趋于松弛,拥有地方事务话语权的士大夫们能够更为积极致力于地方建设,成为南宋乡村社会中维护秩序稳定的重要协调力量。士大夫们也以乡村安定为己任,实现自身价值。这也是南宋中后期国家力量不断在地方退却,但大规模农民起义数量不多,地方秩序总体稳定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