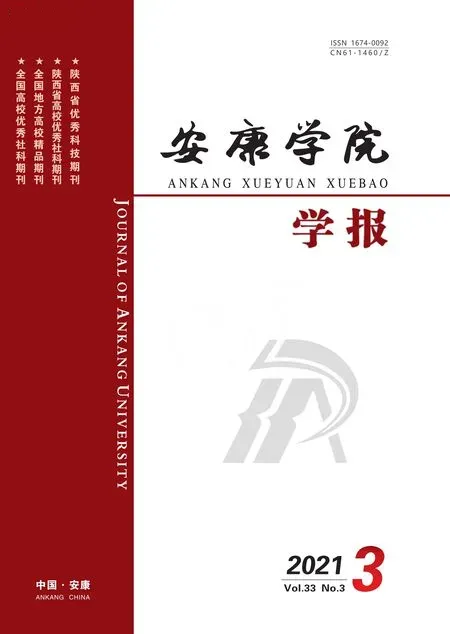论《巴黎圣母院》原型之谜
2021-11-28龚东风
龚东风
(温州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一、引言
浪漫主义是欧洲近代史上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历史进程,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伟大转折,在欧洲古典主义走向式微的时代,浪漫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它最有资格荣膺“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桂冠[1]。耶拿派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 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先驱,一位最活跃的鼓吹者和预言家,他认为人性有一种令人可畏的、不可磨灭的倾向,这是一种总想摆脱时代桎梏的强烈欲望。施莱格尔于十八世纪末发表的《卢琴德》,突破了神学原教旨主义对“自由意志”施加的种种限制,起到了打破传统,把人文思想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效果。斯塔尔夫人(1766—1817) 在《论德国与德国人的风俗》专门辟出章节讨论文学艺术,详细介绍德国的小说、诗歌、美术、戏剧及史学著作,同时向读者推荐歌德、莱辛、席勒等德国著名作家,这部作品是欧洲新文艺思潮的催化剂,对法国十九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不少学者认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是欧洲浪漫主义的真正发端,约翰·赫尔德(1744—1803)是浪漫主义哲学的先驱之一,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以个性的方式表达各种经验,这个观点是对古典主义“永恒哲学”的革命和颠覆。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首先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其次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对科学原理的追求远远超过对宗教的信仰,他把追求科学真知和逻辑思维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即便如此,他一直为人类的自由思想所陶醉。
约翰·席勒(1759—1805) 对欧洲浪漫主义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游戏驱动说”(spieltrieb),该学说认为文学家和艺术家解放自身的途径在于保持玩家的游戏心态,也就是能够成为自由想象和自由发挥的思想行者。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要善于打破旧规则,发明新玩法。弗里德里希·谢林(1775—1854)认为任何一种艺术品,如果只是一种自然或科学的附庸,只是日常观察和缜密记录的衍生物,只是由精确的数学公式推导而来,那么它就等同死亡。作为文化瑰宝,经典名著之所以能够为全世界读者所喜爱主要是因为它的精神光芒,而作家的艺术禀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魅力和生命力。
十八世纪结构主义理论有一种普遍观念,那就是既然存在着物质,必定有一种值得遵从的普遍结构,雨果则认为这种观点荒谬至极,因为过分强调物质的稳定结构会使艺术家作茧自缚而窒息他们的创造精神,他一方面同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一起否认世界上一切事物存在绝对结构的观点,一方面吸取德国浪漫派的经验,从欧洲童话、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民谣等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巴黎圣母院》因此而诞生,法国评论家克里斯蒂安·艾马尔伊(Christian Amalyi)当时称赞该书是“呼之即来的一场革命的浪漫主义编年史”。
二、《巴黎圣母院》的物理原型
《巴黎圣母院》围绕一座命运多舛的古老教堂讲述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悲剧故事,其物理原型当然是贯穿整部作品的巴黎圣母院本身,它是一个载入了宗教史、艺术史和科学史的建筑标本,在建成以来的八百多年里,这座具有地标性质的大教堂见证了巴黎市民的悲欢离合和法国波诡云谲的沧桑历史。维克多·雨果(1802—1885) 在探索这座历尽沧桑的“哥特式作品”的时候,在两座钟塔之一的阴暗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中世纪留下的手迹——希腊文字ΑΝΑΓΚΗ,这些字母所蕴含的悲惨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天才作家,由此激发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写下了这本同名巨著。
巴黎是法国的心脏,它诞生在形状像摇篮一样的西岱岛上,岛屿东端的圣母院在中世纪是这座城市的灵魂以及法国人民的精神圣殿,它像荷马史诗和罗马编年史一样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工程,目睹了法兰西历史上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青年作家在书中能够对这座教堂展开细致入微的物理描述,离不开索瓦尔的三卷本著作《巴黎城市古董的历史与寻踪》 (1724),关于它未来的命运,作家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预测:“几个世纪以前在墙上写下这个单词的人(下文将论及这位‘作者’是谁)已经不在了,永远不在了,也该轮到这个单词从教堂的额角上消失了。这座教堂本身或许也会很快从大地上消失吧”[2]。学者程曾厚称雨果是先知先觉的预言家,他“为人类建造了一座其大无比的文学殿堂”[3],对于这座教堂的遭际,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第五卷专门辟出“这个消灭那个”这一章节,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宏观视野预言这座教堂必然倒塌[2]201,作家一语成谶,这座同高卢民族荣辱与共的哥特式大教堂在2019年4月15日被大火焚毁,从古代占卜家的角度来说,这是它的宿命,以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观点来看,人们更有理由相信思想的圣殿与任何宏伟的土木工程相比,前者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后者是终将蒙尘的物质存在。
维克多·雨果对欧洲文学经典——从荷马史诗、希腊戏剧、圣经故事再到格林童话——有精到的研究,他本人看重文学原创性,对“相同的神话、相同的灾难、相同的英雄,人人都从荷马那里汲取灵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罗马照搬希腊,维吉尔抄袭荷马,史诗和它所表现的社会一样,在自我旋转中磨损了自我,史诗在奄奄一息中走近尾声[4]8。早在他青年时期写成的《〈克伦威尔〉序言》毫不讳言地对古典主义诗学下了病危通知书,然而他的浪漫主义作品却并未向中古时期的欧洲文学传统彻底告别,雨果声称作为智慧的上层建筑和思想的最新载体,纸的圣经是高尚无比的,它那巨大的头颅是一切想象的蜂房,隐藏在茫茫的云雾深处[2]217。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巴黎圣母院》如同一座富丽堂皇的艺术迷宫,迂回曲折的诗学厅廊通向每一个复杂的密室,读者需要用文本细读的策略,对照《〈克伦威尔〉序言》提到的古代神谱对作品本身反复研读并审视其主题,才能读懂作者的文心曲笔并揭晓谜底,从而深刻领悟他的多重政治隐喻。
三、《巴黎圣母院》的艺术原型
在创作《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维克多·雨果的政治立场逐渐从拥护王朝的保守理念向支持共和的进步思想转变,在文艺方面他摈弃古典主义文风,成为浪漫主义激进派的旗手,这部作品本身是雨果把诗歌和戏剧新理论应用于创作实践的重要成果。为了伸张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不遗余力地同主张“正本清源”的文学理论家交锋,同古典主义的“歌利亚”作战,不过在这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之中,他采用了古曲新用的创作策略,而不是轻率地同传统文学割裂开来。事实上雨果对欧洲古典主义的严厉批判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扬弃:“一种唯灵论的宗教悄悄地钻进古代社会的心里,杀死古代社会,并在老朽文明的尸体里,播下现代文明的萌芽。”他还说:“万事不可能没有根由,第二个时期总是在第一个时期萌发。”事实上,雨果对欧洲传统文化始终怀着一种敬畏的态度,《巴黎圣母院》这座文学大厦的地基建立在欧洲尤其是法兰西的古代艺术之上,其叙事结构系统性地采用了众多原型,举其要者,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巴黎圣母院》的第一个艺术原型是魔法换子(Changeling)的古老传说。为了起到吓唬小孩以及警示父母的作用,欧洲社会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民间故事,海涅(1797—1856)也曾以这个题材创作了《调换来的怪孩子》:粗心的父母如果不谨慎地履行看护孩子的责任,巫师转瞬之间就会抱走摇篮中聪明又可爱的婴儿,留下一个又丑又笨的孩子。迷信的人们认为吉卜赛人擅长妖术和蛊魅,他们不断传播坐在大篷车里的流浪者和马戏团的魔术师如何拐骗小孩,抢东西和吃人肉的故事,久而久之人们对波西米亚人形成了偏见,如同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正如小说中那个老妇人在法庭上对爱斯梅拉达所作的不利证词:波西米亚人是一群把银币变枯叶的女巫和妖僧。巴格特·尚特孚勒里在出门看望熟人的功夫,唯一的宝贝女儿小阿涅丝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罗圈腿、独眼、驼背的小怪物”[2]248,为了避免进一步刺激已经发疯的母亲,街坊邻居随即把这个“可怕的畜生”抱走,遗弃在圣母院前廊的弃儿放置处。年轻的孚罗洛神甫收养了这个孩子,他就是伽西莫多,而那个被调包的小阿涅丝长大后则成为埃及丐王的妹妹爱斯梅拉达。
《巴黎圣母院》的第二个艺术原型是《美女与野兽》。维克多·雨果高度赞赏法国女作家勒普兰斯·德·博蒙(1711—1780) 在欧洲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方面所做的贡献,在他看来,原创离不开口笔相承的民间传说,人们可以用历史的直觉阐释现代艺术之谜[4]21。把《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和博蒙的童话故事《美女与野兽》加以对比,很难相信两者之间在题材方面的高度相似性纯粹是一种巧合。除了对古老的童话母题进行深度重构,雨果对作品人物的名字也做了讽寓化处理,作家借“诗人兼剧作家”甘果瓦提出一个问题:“拉·爱斯梅拉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小说的答案是:La Esmeralda是巴黎圣迹区纯洁又美丽的埃及宝石[5]318。“伽西莫多”是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这一天孚罗洛收养了这个半人半兽(Quasimodo) 的小生灵,这个在爱斯梅拉达面前以“怪物和野兽”自称的弃儿,是以圣母院碉楼顶端的驱魔怪兽赛克罗平为模型来塑造的。按照美丑对比的创作理论,爱斯美拉达和伽西莫多就是旧版《美女与野兽》故事新编,在这个加强版的童话故事中,个体无法抗拒的天命把两个小人物的命运扭结在一起:“野兽”按照义父的指示乘着夜色跟踪并掳掠美女、美女不计前嫌给予受刑台上的“野兽”滴水活命之恩,骇人的“独眼兽”从巴尔维广场的绞刑架上把爱斯梅拉达抢到圣母院的高塔里并像喷火龙一样守护着她,“野兽”潜入隼山墓地的地窖里与绞死的美女成婚。作家把极度的美和极度的丑相对照,美丑并置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把孚罗洛神甫黑色教袍下的丑恶与淫邪,皇家骑兵队长弗比斯英俊外表下的虚伪与肮脏以及伽西莫多的兽面与人心展示在读者前面,达到了惊人听闻的戏剧效果。
《巴黎圣母院》的第三个艺术原型来自《旧约·士师记》,同时也采用了《荷马史诗》的典故。约翰·弥尔顿1671年把这个圣经故事改编为悲剧《力士参孙》,这个故事的本末是这样的:参孙作为以色列士师二十年,曾用驴腮骨击杀一千非利士人,后来由于妻子大利拉的出卖,天机泄露后被俘,剜去双眼,罚做苦役,非利士人在胜利日威逼他表演武艺,为了报仇雪恨,他摧毁了大厅的支柱,和敌人同归于尽。雨果在第十卷中描述的教堂攻守大战所依托的典故来源看似纷繁复杂其实大有章法可循:伽西莫多、沙多倍尔以及波西米亚人三方展开的教堂攻防战皆为争夺爱斯梅拉达而来,就像希腊联军为了夺回海伦而攻打特洛伊城堡一样。伽西莫多出于误会,只身在教堂塔顶同前来营救爱斯梅拉达的数千攻城者展开殊死搏斗,他同攻城大军展开血战的一幕首先让读者联想到的故事蓝本是弥尔顿的著名诗篇,而惨烈的激战过程主要参照了《荷马史诗》的宏大叙事策略:丐王克洛潘·图意弗力敌皇家卫队的战斗场面是赫克托耳同阿喀琉斯对决的再现[6],甘果瓦受神甫的蒙蔽把“自己的妻子”骗出教堂最终使她深陷死地的做法,就是雨果版的特洛伊木马计。天才作家要有化古典为神奇的想象力,当历代传说中的人物和事迹置换一种面目和脚本在《巴黎圣母院》再次登场的时候,他们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立体化了。
《巴黎圣母院》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原型来自《俄狄浦斯王》。雨果在古代戏剧的基础之上对宿命论主题进一步演绎,小说在序言中开诚布公地承认该书的渊源是希腊悲剧故事,命运是整部小说的主线。亚里士多德认为《俄狄浦斯王》是希腊悲剧的典范,按照他的诗学理论,所谓的悲剧是主人公出乎意料地遭到一连串的不幸打击最终导致覆灭的故事,目的在于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从而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并使迷途者改邪归正[7]。为了证明雨果对索福克勒斯悲剧故事的借鉴,不妨花时间再比照一下《俄狄浦斯王》广为人知的故事情节: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神那里得知,由于以前犯下的罪过,自己的儿子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他于是抛弃了婴儿俄狄浦斯,被科任托斯国王吕波斯收养的俄狄浦斯长大后得到了同样的神谕,为了反抗命运他逃亡忒拜,在路上打死了事后证明是其生父的老者。俄狄浦斯后来成为忒拜之王并娶了先王的遗孀——也就是生母伊俄卡斯忒,忒拜发生瘟疫时,神指示必须找到杀害先王拉伊俄斯的凶手并驱逐出境才能平息祸患,俄狄浦斯王于是千方百计查访凶手,结果发现杀父娶母的正是他自己,悲剧以伊俄卡斯忒自杀,俄狄浦斯王刺瞎双眼,请求放逐落幕。
所谓的原型(Archetype)即事物的原始模型和古老形态,它既是实体建筑的前代蓝本,又是每一代作家建造艺术宫殿的设计图纸,《巴黎圣母院》反映了中世纪走到尽头时法国社会的主要图景——既有阴谋与爱情又有侠义与恩仇,小说承袭了《俄狄浦斯王》的主要元素和叙事模式,自始至终笼罩着神谕和宿命的悲剧色彩[8]。《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模型在《巴黎圣母院》里至少有三个接榫点,第一点是罪与罚的因果报应,巴格特·尚特孚勒里年轻时沦落风尘,女儿阿涅丝的诞生为她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她找埃及女人为孩子算命,从而导致不满一岁的婴儿被盗,这位母亲绝望之下到格雷沃广场的罗兰塔做了隐修女。第二点是二十岁的义侄伽西莫多同十六岁的叔叔若望塔顶对决的情节,孚罗洛的这位弟弟在对哥哥彻底失望之后奋不顾身地加入争夺爱斯梅拉达的攻城队伍,他乘云梯第一个爬上墙头之后试图把伽西莫多的另外一只眼睛射瞎,却被这位暴怒的金刚倒提双脚挥舞一阵后甩在墙上,最终落得一个粉身碎骨的下场。第三点是伽西莫多的弑父情节,这个先是被埃及人调包,后来被年轻教士孚罗洛收为养子的“小妖怪”长大后成为教堂的敲钟人,当他得知孚罗洛正是加害爱斯梅拉达的罪魁祸首后,毫不犹豫地把这位养父从教堂的塔楼上推了下去。悲剧高潮是母亲出于对埃及女巫的仇恨,同时受到神甫的欺骗,牢牢钳住了逃亡中的爱斯梅拉达,母女重逢之夜,却是生别死离之时,母亲成了把女儿送上绞刑架的帮凶。
四、《巴黎圣母院》的讽寓叙事
后世的文艺创作需要前代原型作为参考,但借鉴以往模型并不意味着简单复制,而是一个继承基础上的价值再创造过程。雨果断定前代作家无论如何写不出《美女与野兽》的博蒙版,就艺术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言,他认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众多特征表明“古代文艺中的滑稽与美,其契合是密切而又富于创造性的,即便是民间最淳朴的传说,有时也以令人赞美的直觉解释现代艺术之谜”[4]21,他进一步指出历代欧洲文艺作品主要有三大题材,诗人和作家将理想寄寓于颂歌,真实维系于正剧,而把伟大托付于史诗,而这三种文艺题材又离不开三大源头,即《圣经》、荷马史诗以及莎士比亚戏剧。雨果丝毫没有掩饰《巴黎圣母院》与欧洲古代文学的继承关系,但这位作家在传承的同时拒绝模仿前人、挂靠大师或者嫁接典范。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文艺发明家,他宁可做荆棘或大蓟,像雪松和棕榈树那样受到同一片大地的滋养,也不愿做木耳和苔藓那样的寄生物,在他看来,巨人身上的寄生虫,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侏儒而已。《巴黎圣母院》打破了古典主义的诗学桎梏,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他要做的事是:举起榔头砸烂理论、诗学和体系,推倒挡住自由之门的石灰墙[4]36-38,雨果把古希腊戏剧和莎士比亚戏剧相结合,采用正剧和外传、庄严和滑稽相互渗透的交响叙事策略为读者建造了一座艺术神殿。雨果没有把涉及众多人物命运的多重悲剧局限于二十四小时的室内独幕剧,而是扩展为一四八二年的巴黎广场剧,描绘的是十五世纪法国的全部历史画卷,一位二十九岁的青年作家具有如此宏大的格局,的确无愧于文学奇才的称谓。
《巴黎圣母院》的讽寓叙事集中体现在该书的最后一卷,它所描绘的大结局是中世纪神权社会的死亡证明,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得到了一个悲剧的收场”——活下来的甘果瓦和弗比斯也不例外,由于伽西莫多挖去了义父的心脏,这位神甫落得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第二年他的政治伙伴路易十一国王也死去了。作者把巴黎圣母院作为重要原型并非向这座古老的教堂致敬,而是借助黑色的死亡意象向十五世纪表达哀思:属于帝王将相和封建教会的圣殿迟早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然而《巴黎圣母院》的悲剧叙事并非表明雨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拥护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这一思想体现在1859年出版的《历代传说集》中。这本诗集从亚当夏娃的人类童年时代一直写到二十世纪,在《海茫茫》《天苍苍》两首诗中对未来世界所做的预言是最富有远见的启示录,作者通过这部诗集表达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觉醒的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普罗大众才是推翻神权和皇权统治并促进社会进步的澎湃动力。《巴黎圣母院》预言一个美好的十六世纪即将到来,如果把整部小说看成一份礼赞革命精神的加密电报,其哲学隐喻的全部密码在本书第五卷可以找到,作家对巴黎圣母院倒塌的预言是一个革命者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准确判断,所谓的宿命和神谕只不过是社会观察家敏锐地发现了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一种人力无法逆转的历史必然性。
雨果认为一切文明始于神权政治而终于共和体制,墙体上布满历代君王雕像的巴黎圣母院是一座堡垒,是封建皇权和宗教神权的复合体。面对十五世纪印刷术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路易十一国王和神甫当年站在教堂的围墙上一边惶恐地目睹青铜破城锤的猛攻,一边哀叹“塔快要倒了”[2]202。在物质世界里,印刷术要消灭教堂;在文艺领域,浪漫主义必将取代“唯理性主义”和“三一律”。若望和贫民窟的人们攻打巴黎圣母院是作者的一种政治隐喻,1789年起义者攻打巴士底狱是它的故事原型,出于情节设计的需要,雨果在书中调换了进攻者和防卫者的角色。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研读整部作品,任何一位细心的读者不难在第五卷第二章“这个要消灭那个”里发现作家讽寓叙事的命意以及伟大作品的主题所在。
五、结语
《巴黎圣母院》作为浪漫主义经典代表作之一,具有诗学意义上的跨领域映射功能[9],它把教堂的物理原型作为演绎一系列悲剧故事的实验剧场,对欧洲社会尤其是法国的宗教、哲学、伦理和政治议题展开讽寓叙事,设置了许多“难解之谜”。作者在序言中自称“曾多方寻思,尽力猜测那痛苦的灵魂是谁,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罪恶的或悲惨的印记留在古老教堂的额角上之后才肯离开人世。”谜底就在该书第二部第七卷第四章《命运》,熟谙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字的孚罗洛神甫在预感到自己注定要和神权一起消亡的下场时,心情沉重地用罗盘针刻下了这几个字母,其无法抗拒的命运母题——旧事物必然消亡,新思想定将永存——是整部小说的灵魂和主线,至于宗教与神权的总代表孚罗洛神甫以及这个手迹的存在与消亡究竟是历史真实抑或作者的文学发明,需要读者用文艺逻辑加以审视和剖析。
雨果有自己的逻辑哲学,他认为最好的书籍才是最好的教堂,最好的作家也是最好的牧师,每一位天才作家或诗人既是一名出色的建筑师又是一座永不磨灭的纪念碑:诗人但丁是十三世纪最后的一座罗曼式教堂,剧作家莎士比亚是十六世纪最后的一座哥特式大教堂。人类有两种书籍,两种记事簿,两种经典,那就是建筑术和印刷术,一种是石头上的圣经,一种是纸张上的圣经[5]217。自古以来宏伟的建筑物一直是人类的大型书籍,记录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况和文化遗产,然而自从古腾堡发明活版印刷术以来,哪怕是镌刻在石碑上最坚固耐磨的汉谟拉比法典,也要让位于印刷术带来的书刊。自1163年奠基到1345年完工,建筑工匠历时一百八十多年建造的巴黎圣母院多灾多难:从1789年革命者的营房到1830年战斗者的堡垒,屡遭兵燹。从1827年10月《〈克伦威尔〉序言》宣布“又一个时代即将开始”到1831年3月《巴黎圣母院》的出版,年轻的雨果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就建造了一座文学圣殿,他以此宣示古典的建筑实体永不复返地死亡了,印刷术取而代之,书籍成为新生的思想载体。“书籍消灭建筑,教堂必将倒塌”的预言是雨果通过其作品做出的科学论断。
1833年,《漫画报》刊登了一副雨果的肖像画,伟人的身影嵌入了背后那座哥特式建筑,雨果的朋友,著名记者奥古斯特·瓦克里注意到教堂的正面恰好构成了作家姓氏的首字母“H”[10]。Victor Hugo这一名字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他的人生阅历和终身成就无愧于“伟大”与“胜利”这两个法语单词,一些法国历史学家认为他的生与死和波拿巴·拿破仑一样,是法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其庞大的物理原型相比,《巴黎圣母院》“这部最好的书——也是最永恒的建筑”[2]204问世以来在全世界拥有巨大发行量和热心读者的事实足以说明它在普通百姓的书房和心灵殿堂里所占据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