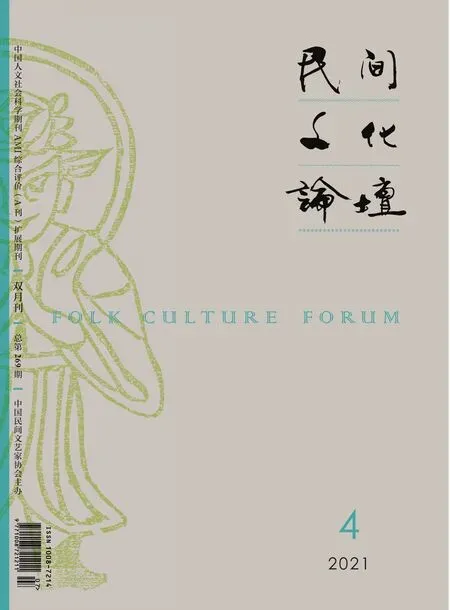朝向“一国民俗学”:柳田国男的传说研究
2021-11-28程梦稷
程梦稷
柳田国男在展开有关传说的数次民俗学演讲(昭和十三年,1938)之前,就已经通过《民间传承论》(1934)与《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这两本书完成了他在民俗研究方法论上的体系化过程。①[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基于“为了真正的学问而奋起”,建成“国民的学问”的志向,他在《民间传承论》中提出了作为其民俗研究整体框架的“民俗三分类”,即“眼的采集(生活外形/行为传承)”“耳的采集(生活解说/口头传承)”与“心的采集(生活意识/信仰传承)”。②相关学术史背景参见[日]川田稔:《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构想》,郭连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王京:《柳田国男与“一国民俗学”的成立》,《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一般看来,民俗资料的分类乃是一种收集、整理资料的技术性问题。然而,在柳田国男的民俗研究中,这一套分类体系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理论基础,明确了各个门类在民俗研究整体格局中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而柳田国男在日本民俗学讲座上对于民间传说的一系列讨论,同样是内在于这一整体研究设想而存在,并从这种整体观出发赋予其意义的。
这一系列以传说为主题的演讲后来整理为《传说论》出版,至今仍被公认为传说研究的经典之作。③柳田国男的《传说论》于1940年由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是日本最早系统论述传说的概论性著作。该作由连湘翻译,张紫晨校订,于1985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列入“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至今仍是民间文学领域有关传说研究的经典论著之一。在《传说论》的第一章“传说的定义”中,柳田国男开宗明义重申了他对于“民间传承”的分类体系,并把他所讨论的“传说”(伝説,でんせつ)置于“民俗三分类”的第二类与第三类,即“口头传承”与“信仰传承”之间,“使之起到桥梁、沟通的作用,以利研究工作”。④[日]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紫晨校,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页。下文引用本书内容仅随文标注页码。柳田国男对传说的这种定位相当独特,尤其是他特意将“传说”与歌谣、谚语以及民间故事等民间口头传承的其他文类区别开来,赋予其“第三类民俗”,也就是“信仰”的属性,由此体现出他对“传说”的特殊认识。
虽然在《传说论》当中,柳田国男并未对作为“心的采集”的“生活意识”详细展开说明,但在《民间传承论》等相关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柳田国男所提出的“民俗三分类”背后的考虑。他强调,“眼的采集(生活外形/行为传承)”“耳的采集(生活解说/口头传承)”与“心的采集(生活意识/信仰传承)”并非平行罗列,而是在文化意义上存在着层次分别。其中,“以信仰为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意识、精神生活构成社会变化的重要因子”,并从背后约束和作用于行为传承与口头传承。因此,“第三类才是我们做学问的目的,……第一类和第二类是达到第三类所要经历的中间阶段。”①[日]川田稔:《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构想》,郭连友译,第53—54页。也就是说,精神层面“以信仰为中心”的生活意识作为人们思考、行动的基础,规定了行为传承、口头传承的形态与变迁,因此,不论讨论的对象具体为何,柳田国男民俗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落实在对于信仰传承的思考上。
一、以“信仰”之名:传说的文类特征
在对传说这种双重属性的定位基础上,柳田国男所总结的传说的几大特质亦是水到渠成,尤其是他在探讨传说与故事的区别时,提出了许多有关传说文类特征的关键见解,这些也正是柳田国男《传说论》在当代民间文学研究中最常被征引的学术贡献。
首先,基于传说作为“口头传承”的这一定位,柳田国男在《传说论》第二章“传说的形成”与第三章“传说的特点”中着重强调了传说在历史中所具有的“变迁性”:“传说却长期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传授上,不可避免地慢慢起着变化。……仔细地观察时,从这当中可以窥见时间的进展给予人类社会巨大变革的某些痕迹。”(第9页)由此可见,历史变迁乃是柳田国男观察传说的出发点,而这一历史的眼光正构成全书对传说展开思考的基本脉络。
其次,传说与故事、谣谚等其他“口头传承”的文类不同,它同时也具有“信仰传承”的属性,因此,传说与故事(昔话,むかしばなし)等文类在“信仰”的意义上构成本质区别。柳田国男指出,“传说有人信。故事则不然。”(第26页)这就把对于“传说”的文类界定拉回到作为叙事主体的“人群”上来。一方面,故事的讲述者总是“将个人置之度外”,而传说则与此相反,如果听话人对讲述的内容表示怀疑,反而会把讲述人惹恼。当代传说研究对于民间传说在实际生活中的话语属性的强调,与这一点有着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在共时维度的人群区隔之外,柳田国男更强调从历时维度观察传说“可信度”的失落,他指出,同样一则传说在不同讲述主体的口中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同一家人,老少两代,态度就常常不一样,”(第26页)对于祖先而言的“传说”,在后代的讲述中可能就变成了“故事”。不过,柳田国男虽然注意到讲述主体对于“传说”这一文类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恰恰由于传说的文类特征建立在“信仰”这一抽象概念的基础上,柳田国男对于“主体”的界定乃是从宏观的历史、地理维度展开的。
具体而言,柳田国男对传说的文类特征提出了著名的“纪念物”概念。他认为,“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第26页)站在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立场上,这一点不难理解。倘若一则口头作品在一个限制性的时空中被视为“传说”,则必须有具体可感的“实物”依据,能够唤起人们对于地方、历史、宗教等共同体的实际感知,与更大的人群联系起来,滋生一种对其所属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当代学界往往以解释性、地方性、信实性来归纳传说的文类特征,其缘由亦与传说关联于“实物”的这种信实感有关。需要注意的是,柳田国男此处的论述同样是基于他对于“信仰”的特定认识而展开的,因此他所说的“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塚,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眼前的实物唤起了人们的记忆,而记忆又联系着古代信仰。”(第26—27页)也就是说,柳田国男所说的“纪念物”本质上是“信仰的中心点”,而他全书举例中的传说“纪念物”也无一不是承载着一定神圣性的信仰的“圣址”。出于这种理解,柳田国男所提出的“纪念物”的概念在他的论述里比较偏重在历史人事的范畴,而难以覆盖到解释性的物产、动植物等其他类型,相对于当下学界所讨论的民间传说而言有所窄化。①对此,陈泳超提出,“纪念物”这一概念可以稍作调整,以“实物”概念来加以界定:“按照这样的界定,无论是人物传说、事件传说还是地方风物传说,归根到底都是地方风物传说,都必须落实到传说实践者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某些‘实物’之上。”参见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最后,传说的第三个特点是“叙述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可变性”(第27页)。这一点同样是从柳田国男在界定传说时所根源的“信仰”属性生发而来。由于传说的口头传承先在地要求听者的心理状态是“知而信”,在信仰的基础上,同一个“传说圈”的人或多或少地共享着同一套地方性知识,因此,讲述人可以依据讲述的具体语境,略去对话双方共同的本土知识背景,如此一来,一则传说既可以是简单直接的一句陈述,也可以作为构件,组合在一个更为复杂的传说之中。
在关于“托宣”唱词的讨论中,柳田国男再次涉及这一问题,他认为,由于信仰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剥落,原本作为“传说”而成立的“托宣”在长时段、跨地域的传播中不断程式化,成为一种“不顾时间、地点的真实而单纯追求寻欢作乐者的玩赏品”(第127页),这样就离开了原本作为“信仰传承”的“传说”,逐渐向单一维度的“口头传承”靠拢,最终变成有着固定程式的“故事”展演。柳田国男的这种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传说研究来说无疑是有着启示意义的。与其他许多口传形式不同,传说很多时候并不具备纯粹的表演性,而是与地方人群、信仰语境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在传说研究中,故事形态、史诗演唱的诸多研究范式往往难以发挥其效力。与此同时,对于地方人群来说,传说的意义恰恰在于其基于“人群的信仰”所联结的社会、文化功能。因此,关于民间传说的研究还需另辟他径,从地方社会与人群信仰的角度开掘其讨论空间。
二、传说之“变”:从历史到田野
“历史”与“信仰”这两个关键词为柳田国男界定传说的文类特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理解其立场与出发点的基础上,柳田国男关于传说、历史、信仰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存在值得我们讨论与商榷的余地。
柳田国男将“传说逐渐与历史远离的倾向”作为传说的“第四个特点”展开讨论。如果说柳田国男所归纳的传说的前三个特点仍是就其本身的文类特征而言,那么,“第四个特点”则不仅更接近一种外部关系论,而且事实上同样是通过传说作为“信仰传承”的认识而得出的判断。不难看到,即便是关于传说与历史关系本身的讨论,柳田国男也同样是从历时的视角展开。他首先为传说与历史排列出一个单向发展的文体序列,认为在无文字时代,人们并没有把传说和历史分别开来,只是到了“做文字记载的年代,人们则又非常审慎地甄别了浩瀚的材料,取舍严格,没有把什么都一古脑儿写进去”,(第29页)而这些既有人群相信,也有“纪念物”的口头传承就作为“传说”被“历史”淘汰下来。
柳田国男进而总结道,传说并非静态的“历史与文学的混合体”,而是随着历史的推进而在这一“历史—文学”的光谱上游移:
传说的一端,有时非常接近于历史,甚至界限模糊难以分辨;而其另一端又与文学相近,……非但如此,这两极之间的距离,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化而在拉长,也是事实。(第30页)
柳田国男的这一判断是基于一种文明进化史观而展开的推论。他认为:
古时的人们坚信传说,较之现在有几个容易偏信的重要原因。……其中一个最有意思的深刻变化,就是对“古时候”所持的看法。当时的人,不是把它视为时间上的“大以前”,而是把它理解成为与“如今”完全不同的社会,各种奇异的法则行之无阻的特殊世界。这种想象,起了决定作用。(第32页)
而“历史向前发展了,影响波及到传说”(第33页),历史教育对古代传说的祛魅“使得‘信不下去了’的东西,越来越多,与日俱增”(第34页)。虽然柳田国男自己也在叙述中承认,由于传说相对于故事等文类而言,较少受到形式的限制,加上与之关联的“纪念物”尚未湮灭,传说便可以与历史、时政评论等多种文类结合起来,因此显得生机勃勃,“很有长久存在下去的趋势”(第27—28页),然而,归根结底,柳田国男所定义的“传说”乃是一种“信仰传承”,而从他所预设的进化论的角度观之,古代信仰必定随着“人类认识发展、智能提高、思想开化”而受到冲击,因此,这种虽有“口头传承”之形,却实为“信仰传承”,在根本上由人们的观念所支撑的传说,“不动摇,不起变化,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第29页)。
然而,以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后见之明观之,传说变迁的“生命史”有其独立且自足的动态机制。作为民间口头叙事的传说始终与地方人群、社会历史保持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绝非被动地依附于历史,随着历史理性的强大而日趋衰弱。而所谓“信仰”,其定义也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古代信仰”的范畴内,更不应片面地赋予其或原始、或神圣的文化想象,支撑“传说”的“信仰”始终活态地存在于地方人群的生活世界之中。考虑到这种单向度的文化进化论预设,柳田国男关于“传说”与“历史”由远古时候二位一体的状态不断渐行渐远,乃至最终“会有断线的一天”(第30页)的这种线性判断无疑是需要警惕的。
在柳田国男关于传说与历史关系的讨论中,对当下民间传说研究而言或许最有意义的在于他所提出的“传说的第二次改革(合理化)运动”(第34页)。柳田国男对于传说的界定乃是从讲述主体出发,诉诸人群的“信仰”。他认为,在一些人以一种戏谑、娱乐的态度将古时候的传说作为故事来讲述的同时,也总有一些人出于对家族、地方等文化共同体的维护,而试图将原有的传说以新的形态保留、传承下去,于是他们“千方百计,东拆西补,开始搞起了补遗修缮工作。把漏洞填补起来,润之以新词,把信不下去的部分,剔出,涂之以新的色彩。”(第34页)换言之,倘若不根据现实的情况加以修补,则“传说”难以成立,“信仰”随之消亡,家族、地方的文化共同体亦将难以维系。
这种讨论从“人之常情”出发,触及传说传承变异的机制。然而,柳田国男的出发点并非将传说视作一种社会性的“话语”,而是仍然将关注点放在信仰的传承上。他认为,人们出于对祖辈传递而来的文化传统的信仰,“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所谓‘传说合理化’的运动”(第46页),这种思路一方面不免将传说的传承动因纯粹化、理想化,仅仅归因于“不该责难”的人们的“心情”(第46页),而忽略了传说传承机制中实际可能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权力动机。另一方面,在这番讨论中,柳田国男虽然注意到历史典籍、石碑刻文等文字资料所代表的主流、正统意识形态在传说的历史化、合理化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他并未将这种历史变量与互动关系本身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话题,而是率然加以价值评判,站在为传说正本清源的立场上消极看待,认为这些危害到传说真实面目的“合理化运动”为学者的研究造成了“本不应该”的“人为的干扰”(第48页)。然而,传说的背后究竟是否存在一个“纯净”的“古人生活(信仰)真实图景”,而毫无任何社会、历史的所谓“人为”因素的参与,这一点同样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在《传说论》的“自序”中,柳田国男对这种偏重古代文献、书面文本的历史性研究倾向有所反思:
为了说明传说的近代相的需要,我这次多少进行了一些关于历史化问题的评论和探讨。但对广大读者诸君,是决不推崇这种做法。因为,即便不从这方面着手,传说的研究工作也完全可以进行得很好的。所以宁可避开历史上的事实,从别的方面进行研究,兴味更浓,功效亦大。采集方法虽然也可以搜录现成的传说,但不如直接从当地老年人的口中听取那些毫无做作的倾吐之谈更好。
可以看出,柳田国男并非没有意识到传说研究“现世相”的意义,尤其是他也承认真正有活力的传说研究应当建立在更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只不过就《传说论》一书的讨论而言,他的问题意识并不在此,所以并没有在这一方向上展开而已。
三、从“传说圈”到“共同体”
目前学术界对于柳田国男《传说论》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传说圈”的概念上,①相关论文举要如乌丙安:《论中国风物传说圈》,《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2期;李娟:《“传说圈”理论的接受与建构》,《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而与前述思路一脉相承,柳田国男提出这一概念的语境仍然是他对传说讲述主体的“信仰”的强调:
不管别处(别人)有多少类似的说法,也不管别人是怎样证实其自己的真实性的,只是“我行我素”,“我说我的理”,坚持己说、固执己见。至多,在固定的小集团内议论着……这就是一般人对传说所抱的态度。这个“小集团”有大有小,因之,也就又被人们分成为“著名的”或“不著名的”,而又形成了传说的另一特征。为了研究工作上的方便,我们常把一个个传说流行着的处所,称做“传说圈”。(第49页)
柳田国男从作为“信仰小集团”的人群现象出发,提出“传说圈”这一概念,并注意到不同的“传说圈”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接触、影响,甚至冲突、斗争的情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传说圈”构成对于当代传说研究而言最具启发性与阐释效力的概念工具。
针对这些有着不同说法的“传说圈”,柳田国男将其分为“吞并”和“共存”两种情况。“吞并”即是指在同类型“传说圈”相互接触的地方,存在冲突的说法一方被归并,后来趋于统一,而相对妥协、折中的办法则是找到能够容纳不同说法同时成立的合理化的解释。譬如虽然日本各地都有弘法大师使井口涌出圣水的传说,但如果弘法大师终生都在日本国土内来回旅行,那么日本各地的说法也就自然不存在孰真孰假的问题了。
与“吞并”相对的另一种情况则是“共存”,也就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或文化习俗的区隔,各个孤立存在的“传说圈”分别流传着相互矛盾的同类传说。对于这些情况,柳田国男并未对其背后的机制展开讨论,而是直接把作为不同讲述主体的人群一一映射到相应的地域空间之中,这样一来,本应建立在人群信仰上的“传说圈”便被置换到宏观地理的层面。因此,柳田国男的关注点不在于不同讲述主体的话语关系或地方人群的信仰语境,而传说研究的重心亦随之被引渡到了传说的宏观地域分布与传播问题上。事实上,柳田国男在举例分析中,无一不是以日本全国范围为基础,对各个地方(而非具体人群)的传说类型做比较。例如在对各个孤立存在的“传说圈”的类型比较中,柳田国男把“传说的异常的统一”(第119页)理解为“一源”的传播,认为传说必定发源于特定一地,而其他流传着相似传说的地方,则是文化传播与扩散的结果。他进而直接将这一判断作为论据,将传说研究纳入“一国民俗学”的文化共同体论述中,认为“本属同一国家同一民族之中的传说,有类似的固有信仰,实不足奇”(第119页)。
虽然柳田国男通过“传说圈”概念的提出,注意到了人们对于传说的“信仰”并非均质的,但他的视角仍是基于宏观的历史、地理比较。比如前文提到他以宏观的时代序列讨论传说的失落,而在空间维度上他也同样先在地预设了同一地区人群信仰的一致性,然而,即便是“地区”的范畴他也始终没有明确加以界定,显然,这种未经田野检验的时空同质性定论过于草率。
事实上,柳田国男借由“传说圈”概念对传说进行的比较研究,其目标从来不在于传说的“相异性”“斗争性”,而在于文化共同体的信仰建构。譬如他认为,人们普遍怀有一种“倘若可能,我们也愿意同你们一道相信”(第32页)的想法。在柳田国男眼中,人们的这种想法不单单是出于社交礼节,而且也是出于相互肯定、相互承认的下意识,由此建构着不同人群的共同信仰。在对不同“传说圈”的讨论中,柳田国男更感兴趣的在于更大范围人群的“共同相信”(第32页)。从他的例证讨论中也不难看到,尽管“传说圈”表面看来是地方性的,然而,不论是相互接触、吞并的“传说圈”,还是那些各自孤立却高度相似、有着共同来源的“传说圈”,却在不断的叠加与建构中使得“传说圈”的概念在根本上仍然指向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同体论述。正如柳田国男自陈:
(这些传说)在全国各地(虽在说法和细节上稍有小异)广为流布着,时而漂过海洋,一直传到伊豆三宅……这件事即便在今天尚未得到充分的解释,总还是应承认,在民间,在普通的人们中间,蕴藏了一种巨大的、敦厚的力量。作者想要考察的,也正是这一点。(第114页)
从“传说圈”的概念出发,柳田国男认为,民间存在着某种超越地方社群的文化共同体的精神联系,而这恰恰是使得日本成为一个包容各种地方差异的民族国家的基础。
这一文化取向固然是柳田国男建立其“一国民俗学”的整体设想与学术史背景使然,但在方法论层面,这种宏观研究的基本取向亦对传说形态的探讨有所遮蔽。譬如,类似于民间故事形态学中的“生命树”①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概念,柳田国男也注意到传说的生长变异问题:
传说,不单纯是种子落了下来,发了幼芽,而应比做土壤的营养、空气的力量等,用眼睛不能得见的因素,催其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多少年来飘逸着芳香。所以,我们在列举其枝枝丫丫的分杈问题之前,首先必须看清其主干和主根。(第61—62页)
这里姑且不论柳田国男对于“枝枝丫丫的分杈问题”的回答往往落脚在不同地域之间的传播所带来的文本细节的置换,单从这段表述中也不难看到,柳田国男事实上并不看重这些传说生长过程中的“枝枝丫丫”,而是始终关注传说的“主干和主根”。在他看来,不论是社会历史还是地方人群,这些林林总总的变异机制归根结底“也总是因为有了那茁壮的母本,才有了后来枝头嫁接的可能”(第140页)。在传说变异的现象之中,他所关心的实际上是更为本源性的宏观文化命题。然而,若将视角调整到传说在地方人群间的实际话语形态,则恰恰是这些与人群、语境相关联的“枝丫”,为我们提供了窥见传说变异与传承机制的可能。由此可见,柳田国男的传说研究并不纯粹是作为民间口头讲述的传说本体的文类研究,而是从作为“口头传承”的传说出发,最终旨在通过其作为“信仰传承”的属性,抵达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一种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得以在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将柳田国男的观察与论述作为传说研究的经典与路标,时时对话、回顾,在当下的传说研究中重新建立“口头传承”与“信仰传承”的联结。
正如柳田国男所倡议的“一国民俗学”乃是要建立“国民的学问”②相关学术史背景可参见王京:《柳田国男与“一国民俗学”的成立》,《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从作为“信仰传承”的传说出发,柳田国男的民俗研究最终指向的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日本民族,而他对于传说与历史、传说与信仰关系的讨论事实上也都是统合在这一论述脉络之中的,即如他在《传说论》全书结尾所言: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的年代,就从这些传说中得到了“圣者伟哉”的虔诚信仰根据,并感觉到本身与民族最可尊贵的核心,保持着息息相通的联系。……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承认这博大的思想倾向,并朝着崭新的文化领域前进下去!(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