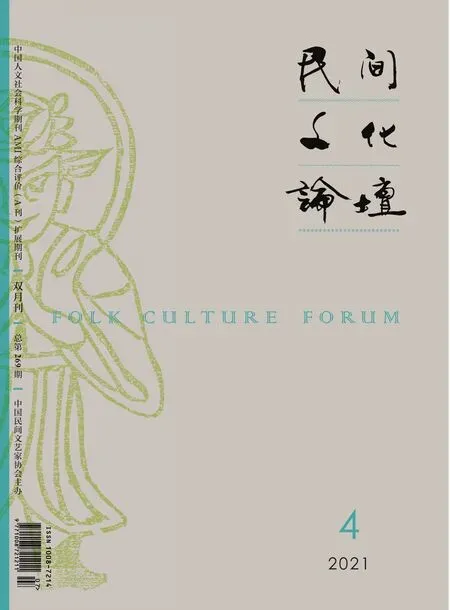解析日常文化中的量化结果诸态
2021-11-28吴秀杰
吴秀杰
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的《结果型社会——日常文化的诸多层面》①Hermann, Bausinger, Ergebnisgesellschaft. Facetten der Alltagskultur. Tübingen: Tübinger Vereinigung für Völkskunde e.V., 2015. 中译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2021 年出版。是一本“小”书。首先,它的篇幅小。德文版总共150页,翻译成中文大约在10万字左右;其次,它的论题小。正如副标题所示,书中讨论的是“日常文化的诸多层面”,没有奔放豪迈的宏大主题。第三,它的预设读者群小,出版方不是某家著名出版社,而是图宾根民俗学会。然而,我认为这是一本可以归为“大家小书”类的轻学术作品,或者可以这样说,这是学术作品中的“散文”。文学作品中耐看的散文,往往不是因为抒情充沛或者词句华丽,而是因为作者能将丰富的知识娓娓道来;学术作品中的“大家小书”与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作者具备专业领域内的博闻洞见,能在不经意中把同行们关注的论题串起来。鲍辛格把这本“小”书放在图宾根民俗学会出版人的手上,毫无疑问充满了象征意味:这是作者奉献给自己所归属的那个学术共同体的一份特殊礼物,是合作、团结和友谊的见证。不过,这是一份没有回忆的纪念,书中讨论的对象并不是这个学术共同体本身,而是其研究对象。书中的观察素材都来源于德国,虽然不是关于当地日常生活的系统性民族志,但是对于理解德国现状则多有助益。
带着鲍辛格的书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意味着双重的幸运。一方面,这里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镇;另一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设有一个德文书系列“德意志文库”,而且颇为青睐“大家小书”类型的著作。促成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的人很多。动手翻译这本小书的契机,是2018年初杨利慧、巴莫曲布嫫召集的那场“敬文沙龙”。那时我自己刚刚开始读这本书,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印象并得到与会学者的反馈;岳永逸帮我牵线与出版人谭徐锋相识,而后者慨然承诺出版此书,让我有动力把翻译这本书的事情做下去。还有很多人的助力,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一本外文书能变成白纸上的中文汉字,离不开特定学术共同体的支持与帮助。正如德文版一样,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是合作、团结和友谊的见证。谭徐锋工作室的编辑们认真负责的校对和修改,让文字变得更为准确和通畅;德文书版权方图宾根民俗学会和作者鲍辛格也乐见本书的中文之旅成行,免费提供了中文版权;图宾根大学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研究所(Ludwig-Uhland-Institut für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简称LUI)的卡琳•比尔科特(Karin Bürkert)还特意为中文版编写了主要参考文献列表。因此,这本书不乏学术著作之实,值得写一篇较长的书评文章。
本文由三部分组成。首先介绍作者,而后介绍鲍辛格的著作风格,第三部分则是一个应用“案例”,即我自己如何在本书的启发下去观察新冠疫情下德国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层面。
一、鲍辛格其人
赫尔曼•鲍辛格是德国民俗学界备受尊敬的老前辈。我自认为是他的“粉丝”,希望这个带有娱乐文化色彩的用词不会给人带来有失敬意的印象。一般而言,成为“粉丝”的先决条件是:对一个人略有所知,有深入了解其人的愿望却无法企及,那是一种若即不肯离、飘忽把握不准的状态,而这正是我看鲍辛格这位学术前辈的著作时产生的感觉。梳理鲍辛格的学术生平,是一件挑战性极大的事情:我自己写不来,也没有看到哪位德国学者有文章或者著作来应对这一挑战。七八年前,我曾经偶遇一位来自美国的民俗学博士生,她打算把鲍辛格的学术传记写成博士论文,当时正在德国搜集资料。至于后来这份计划是不是完成了,我无从知晓,至少迄今我还没看到公开出版。如果有一本分量十足的鲍辛格的学术传记,像人类学家斯坦利•谭拜尔(Stanley J. Tambiah)梳理埃德蒙•利奇①Stanley J.Tambiah, Edmund Leach:An Anthropological Life. Cambrid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02.学术生平那样的鲍辛格传记,我会非常愿意第一时间动手翻译的。
鲍辛格生于192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没能逃过应征入伍的命运,从战俘营回来之后他才开始就读于图宾根大学,主修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并兼修教育学课程。他的家境并不好,读语言文学专业获得教师任职资格,由此获得一份稳定的生计,这是当时许多家境清寒、却渴望读书的年轻人做出的理性选择。从进入大学开始,读书求知、教书育人,他一直是图宾根大学的一分子,去美国俄勒冈大学当一年客座教授,也是在大学间交流项目的框架下进行的。他掌门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学研究所(Ludwig-Uhland-Institut für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简称LUI)长达32年之久,开设的课程没有重复的,提交的研究项目资助申请没有被毙掉的。那时德国大学里的人文学科在真正实践着“教学相长”的原则,教授和学生之间讨论问题的气氛非常浓烈,鲍辛格涉猎的知识范围之广、兴趣之多,使他断然不会在课堂上重复陈旧的老生常谈,让自己感到乏味。“一位现象级人物”,他的“徒子徒孙”都没法不叹服。2006年,为庆祝鲍辛格教授的八十寿辰,他的晚辈弟子们策划了一场就其学术生涯与他的对谈,三代学人共同完成一本很特别的学术史追溯,书名精准地映射出鲍辛格给自身的学术定位:《日常生活的启蒙者》。①[德]赫尔曼•鲍辛格、沃尔夫冈•卡舒巴等:《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吴秀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这位“启蒙者”从来没打算居高临下地“开导”陌生人,他总是从自己最了解的、地处德国西南的巴登-符腾堡州文化为出发点,跟本地人说本地事儿,做到了“有一件东西,我看到了你却看不到……”。鲍辛格不是那种充满精英意识的人,他甚至都不觉得自己在知识上有优越感。然而,他的文字总能发人深省,用心者总可以从中举一反三,豁然开朗。他出场的公众活动,无论是新书发布会还是专题论坛,从来都不会缺少听众,但他从不以公众人物自居。什么时候他觉得过自己是公众人物呢?可能只有一次吧,他说。他去一个以前没去过的牙医诊所看牙,当他被叫进诊室时,医生拿起病历本,看到上面的名字,不无惊喜地问他:“啊,您就是那位大学教授?我读过您的书!”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两个相距那么遥远的学科会产生交集,一位属于精英社会阶层的牙医居然读过他的书、记住了他的名字,这让他对自己的影响面之广、力度之大有了一些具体的印象。不过,这位有名气的人,从心里把自己看成“小地方的人”。2009年,他被授予巴登-符腾堡州功勋奖章,以表彰他对地方文化研究的功绩。那年夏天,我们在柏林召集了一个研讨会,②这个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柏林工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当时我在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从基金会申请到了这次研讨会的经费资助,并实际张罗了这次会议,但会议是以该主办方的名义举办。会议由我做开场介绍。很荣幸地请到他来做演讲,在介绍这位嘉宾时,我提到他不久前被州长授予奖章的事情。会下他问我:“您怎么知道这事儿呢?我们那个小地方的事儿。”在柏林,谁敢说巴登-符腾堡州是个“小地方”呢!那是有海德堡大学、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的地方,那里的大学有五百多年的历史,那里是学术和思想的策源地!
鲍辛格不觉得自己是国际知名学者,或者他根本就认为自己走不出“那个小地方”——地方知识太丰富,“吾生有涯而学无涯”。欧美的同行知道他倒也罢,毕竟语言上或者地理上的距离不那么大;为什么日本学者、中国学者会知道他的名字,这着实让他感到奇怪,东亚对他来说真的太遥远。鲍辛格的文字处处体现出一种不敢断言、不敢绝对化、无法脱除自身主观性的谦逊,以及有机会说出自己想法的那种欣喜。那是一种基于“小地方的人”这一身份认同油然而生的谦逊,赋予他一种包容庸常的大格局气象,即便在自己最有资格说话的领域里,他也不会言之凿凿、气势凌人。比如,关于战后的图宾根大学,他这样定位自己作为“时代见证人”(Zeitzeuge)的角色:
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时代见证人呢?对时间进程特别留意、精准的观察、敏锐的判断、不带偏见地重述事实、能清醒而客观地进行描述,这是必备的。冷眼一看这种设想也颇有道理。但是,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这么看也行:如果一个人的基因不捣乱,如果有一位靠谱的家庭医生,多运动,健康地摄入营养,那么这人就能成为时代见证人。当然,一个人得有足够的能力对当时的各种关联情形做适当的描述,才可以担当时代见证人(的角色)。但是,这里涉及的是往昔的关联情形,一般来说,只有亲历的那群人,他们的时代见证人能力才会派上用场。因此,我们可以让事情变得简单和庸俗一些,这样来表述答案:要活得长久,才能成为时代见证人。③Hermann Bausinger, Nachkriegsuni. Kleine Tübinger Rückblenden. Tübingen: Verlag klöpfer, narr, 2019,p7.
我之所以被这段文字特别打动,是因为从中读出了鲍辛格教授的那种谦逊,以及他平淡讲述中隐藏的高标尺。鲍辛格从战俘营归来,作为大学生、助教、教授一直都在图宾根大学求学、授业解惑、参与大学的行政管理、把民俗学改名为经验文化学、把研究所从哲学系改到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系,工作直到荣休年龄,而后每天到大学专门给他提供的空间(资料室兼办公室)去著书写文章。关于战后岁月的大学历史,还能有谁比他更有资格称得上是“时代见证人”呢?可是,他的说法显得那么云淡风轻的,好像全部重点都在“活得长久”这一必要条件上。然而, “一个人得有足够的能力对当时的各种关联情形做适当的描述”,这一要求相当高的充分条件,在他那里却是“当然”的。具备这种能力的人,需要满足哪些要求呢?鲍辛格对此毫不含糊:“对时间进程特别留意、精准的观察、敏锐的判断、不带偏见地重述事实、能清醒而客观地进行描述。”做过口述史访谈的人都会知道,找到完美的“时代见证人”实际上几乎不可能,而历史书写者的挑战恰好在于能够意识到其中的不完美之处,并以理想化的标杆为参照尺度而进行相应的交叉校验。鲍辛格在关照自身作为“时代见证人”的角色时的自我意识,何尝不是来自于他职业生涯中对口承传统的研究呢。鲍辛格从一桶水里小心翼翼地舀出一碗,心存谦卑,放在读者面前时还小声说上一句“不成敬意”。也许有人会把它当成止渴的甘霖一饮而尽,有人会把它当成护身辟邪的“圣水”而珍藏慎用。我大概属于后者。所以,这本“轻”学术的小书,在我这里也会变得分量很重。
二、鲍辛格的书
《结果型社会:日常文化的诸多层面》这本书的内容也许可以总结如下:对日常生活各领域的观察表明,我们似乎处处都以量化的结果为取向;重视数量的做法,并不能简单地归于社会更新加速、机会供给增多,因为很多貌似新潮的做法其实并未走出传统行为模式的窠臼;放慢速度的做法,未必会提供良方;破除以结果为取向,这关乎朴素、减少愿望、承认限度,需要的是笃定而放松地面对各种可能性,也许也需要学会放弃。在“引言”和“结语”两篇之外,作者还选取了16个日常生活的领域来进行分析,每个话题单独成篇,每篇的文字长度不过四五千字,而全书的长度在十万字上下。德文版的书中,作者没有添加注释,没有列出参考书目,而是把提到的作者和书名融入文本当中。
在鲍辛格看来,这种风格的学术写作是他在卸掉教授职责之后获得的一种自由:没必要去顾及学术从业者的写作规范,不必严格地去总结他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不必让参考文献林立,如同一排排墓碑一样;不必去刻意搭建某个理论,或者为自己的理论不足而竭力辩护。这些学术从业者必备的技能,他都掌握得很纯熟。前文提到的那本为庆祝鲍辛格八十诞辰的谈话体学术传记《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将他至2006年发表的著作、学术文章按照编年整理列出。2014年在准备中文版时,我在鲍辛格本人以及助手的帮助下补充了他在2007—2013年间的著作目录,目的也是为了存留一份资料。这份1951—2013年间的论著目录在中文版中占据了76页的篇幅。此后他几乎每年都有书出版,这本《结果型社会》就是其中之一;他撰写的《施瓦本文学史》聚焦于那些主流文学史忽略的文学作品——地方上的文学杂志、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历书上的故事,教会提供的图文资料,他带着文学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叙述一个地区的文学生活①Hermann Bausinger, Eine schwöb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Tübingen: Klöpfer & Meyer, 2017.;作为时代见证人,他在《战后的大学》②Hermann Bausinger, Nachkriegsuni. Kleine Tübinger Rückblenden. Tübingen: Verlag klöpfer, narr, 2019.这本“小书”中将图宾根大学经历的种种危机处理娓娓道来,让人看到“学术与政治”这个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大问题在大学日常实践中的呈现。最近的一本小书,是他与一位有移民背景的绿党女政治家、巴登-符腾堡州议会主席穆特•阿亚斯(Muhterem Aras)关于“家乡”(Heimat)这一概念的对话,而民俗学界关于“在开放社会中如何有意识地面对‘家乡’概念”的讨论,则是由鲍辛格一篇发表在1990年的论文而引发的。①Aras, Muhterem/Bausinger, Hermann. Heimat. Kann die weg? Ein Gespröch. Tübingen: klöpfer, narr, 2019.
当鲍辛格不再正式承担学术责任之后,他有意地选择写“小书”这种举重若轻的做法,尽管他也无惧于拿出厚重之作。他在195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已经长达239页,题目为《活态讲述》,研究的是符腾堡北部地区的口传作品;而1961年出版的《技术世界的民间文化》则经受住了学术共同体的多年检验。该书在德国已经出了第3版,被翻译成英文(1990)、日文(2005)、意大利文(2005)以及中文(2014)②[德]鲍辛格:《技术世界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他不光能写这些专题研究著作,也能在不减损专业质量的前提下,把专业知识深入浅出讲给更大范围内的读者。他曾经应一家出版社之邀,在该社策划的“当代学问”系列中撰写了其中的一本,即《民俗学:从古典学到文化分析》。③Bausinger, Hermann. Volkskunde. Von der Altertumsforschung zur Kulturanalyse. Darmstadt: Carl Habel Verlag, 1971.尽管他本人对“民俗学”的说法并不满意,但是出版社却不能舍弃这个学科概念,否则读者会感到难以定位。在这本书问世的同一年,即1971年,鲍辛格把自己执教的民俗学研究所改名为经验文化研究所。这本书在德国已经出版了第4版, 1990年被翻译成法文。当鲍辛格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时(《技术世界的民间文化》的英文版在1990年出版),他已经马上就要步入法定的荣休年龄,他自己早已把这些研究远远地甩在身后;而使用其他学术界“小语种”语言的学者对他的关注则更迟滞些。在这个意义上,把鲍辛格视为民俗学探险队的先锋队员,实非虚美夸饰。
谈到鲍辛格的著作,我会避免将这份长长的论著目录中的任何一本(篇)看作他的“代表作”,因为他的每项成果都不足以“代表”全体。我们往往习惯于一位大学者会提出一个、甚至一套理论,可适用的范围越大,便越显得有深度、有水平。但是,鲍辛格显然没有把提出理论看成自己的学术使命。他的目标是解释人的日常生活,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是如何变成习以为常的,因为这里才隐藏着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的深层根源,而理论只是解释现象的工具而已。学者声称自己并不致力于构建理论,或者最多以罗伯特 K. •莫顿所言的“中型理论”为目标,在今天已经变得比较容易被接受,甚至在有着较强理论自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学者们都自甘放下构建“宏大理论”的雄心。但是,让我们回到二战后的学术语境:以传统为对象的民俗学一方面得面对20世纪风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抵抗那种摧枯拉朽、高歌猛进、扫荡一切的嚣张,同时需警惕19世纪浪漫主义式滥情于“乡间传统”对这一学科的侵害,还要高举以凡俗日常为目标、抽象理论为工具的大旗,在自己的田野小路上跋涉,争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许置身于这样的氛围当中我们才能够想象,在当时的处境下,鲍辛格需要有多大的底气和自信,才能淡定地说出来:我不在意理论。
从鲍辛格的观察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很多理论家们的借鉴。他对自身作为“日常生活的启蒙者”的定位,得益于图宾根的哲学家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近视域的伦理”这一概念;对“民俗主义”现象的解释,依托于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非同时性的同时呈现”(Gleichzeitigkeit der Ungleichzeitigkeit)。这两位哲人都是图宾根大学的教授,是近在咫尺的思想源泉。然而,他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也跨越不同学科,前辈学者的描述和分析让他看到人们当下行为的历史延续性。比如,在《结果型社会》这本书里,鲍辛格几次提到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西美尔大概是最能吸引民俗学者的社会学家,因为他关注的话题太有市井气息:城市化,时装,货币,饮食仪式。此外,还有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同时代、远不及韦伯名气大但重要程度不相上下的维尔纳•索姆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和卡尔•比歇尔(Karl Bücher,1847—1930)——索姆巴特曾经指出价值伸张的物化性(Versachlichung),饮食奢侈也是凸显地位的手段,只是在底层社会那里奢侈的标志是以量取胜而已,而同样的现象在几十年之后依然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当中;卡尔•比歇尔则是劳动社会学的奠基人,曾经系统地考察工作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两位学者在当时归属于“国家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一个如今已经不存在的专业,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前工业时代的经济生活以及工业时代的社会转型。多年以后,索姆巴特和卡尔•比歇尔(尤其是后者)被社会人类学重新发现。当人类学学者受到卡尔•波兰尼的提醒后发现劳动力已然成为“虚拟商品”之后,他们迫切地想弄清楚前工业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本质究竟是什么,此时重拾卡尔•比歇尔的著作,仿佛遭遇海难者看到远处海岸的微茫灯火。比索姆巴特更不为人知的诺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堂弟——的社会学论文集也在鲍辛格的阅读范围,更无需说那些19世纪或者更早的作家作品,从特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到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鲍辛格对他们的引述似乎信手拈来,毕竟他就读的是德国语言文学专业。
“读鲍辛格的书,是能在人前吹牛的利器”,这几乎可以说是我的肺腑之言,同时也带着一种无论在哪里踹一脚都会引起雪崩而让自己被掩埋的不安。如我这种从他的书中定点式获取片段知识的做法,大概也会被鲍辛格归为“半教育”(这一概念出自特奥多•W. 阿多诺)现象。阿多诺在半个世纪前指出,“半教育”(Halbbildung)不是教育的一半,而是教育的反面。接受“半教育”的人恰好是那些力图获得教育的人;那些兴高采烈地传播教育的人,就是直接毁灭教育的人。文化产业不间歇地把打磨过的教育碎片提供给我们,让我们感觉好像手里有些什么,但实际上我们无法将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于是,教育凋落成闲侃的谈资、成了某种态度,用以获得发言机会和群体归属。鲍辛格对“半教育”现象的解释是,教育的原本目标在于获取一个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最重要的表达形式,那是一个会形成区隔的领域,在那里等级阶序得到公认,经典著作居于核心。然而,何为经典这一标准在不断改变,由教育而形成的区隔领域的边际线日益模糊,阶序变得不再明晰,一清二楚的文化价值建设不复存在。也正因为教育的阶序性结构还依然存在,并且还在发挥一定的作用,“半教育”才成为人们努力的目标。正如同“半真相”最终会比谎言更为糟糕和危险一样,“半知识”和“半教育”也是如此:两个受到“半教育”的人碰到一起,合起来的结果不是完整的教育,而是无稽之谈。
正是出于对“半教育”陷阱的畏惧,我在翻译鲍辛格的书时总会感到某种畏缩感。他的书和文章大多具有很强的地方关联性,这与中国的读者相距太远。在这方面,也许《结果型社会》算是例外,在全球化趋势几十年以及技术世界趋同后,书中提到的很多现象一定程度上在中国也不陌生。此外,另一个考虑也是令我犹豫的原因:鲍辛格的书,也许能帮助人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以及自身的行为方式,却无法提供处理和走出日常困境的办法和途径。甚至,他对日常现象的阐释也不会是线条明晰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口号,给民众以他们能“快刀斩乱麻”式地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幻象,已经被实践证明这类口号难以兑现;而在学术问题上给出干净利落的答案背后,往往是削足适履式的损害。习惯于获取短、平、快结论并期待学术领袖的读者,难免会有“不过瘾”的感觉,因为他们在这里望不见灯塔,找不到拿过来便可用的现成范式,也看不到一位能指点江山的学术领袖。鲍辛格的同事伯恩德•尤尔根•瓦内肯曾经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鲍辛格:
我想象中的鲍辛格雕像应该是这样的:站立的姿势,不超过真人的大小。没有底座。典雅的大衣、围巾。他的右臂做着指点方向的动作,但不是那种领袖式满怀希望、指点江山、规划未来的姿势。相反,他的姿势显得友好可亲、随时乐于给人提供帮助,就好像他正在指点一个来访者,如何顺利地将车开进停车位一样。①[德]赫尔曼•鲍辛格、沃尔夫冈•卡舒巴等著,《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吴秀杰译,第30页。
值得说明的是,鲍辛格尽管是学术界的一位“现象级”人物,但他的学术方式不是民俗学的圭臬,甚至他也代表不了德国的民俗学——他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说来不可思议,鲍辛格这位深深植根于乡土、接地气(bodenständig)的学者发出的声音,在很多热爱传统、热爱民俗的人听起来未免有些刺耳。比如,他很早就告诉博士生们不必以占有完备的资料来要求自己,因为那是没有人能达到的目标;他提醒人们不要把“传统”和“民间”浪漫化,实际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载歌载舞的节日习俗,如今纷至沓来的习俗庆典是把不同空间里的习俗进行叠加的结果;哪怕在昔日的乡村田园中,驱动人的行为的因素也不一定、或者说首要的不是美德和高尚情操;他告诫人们,对那些在书本上读到的民间知识尤其要细加甄别,因为那很可能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他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去“呵护”传统。正好相反,他认为辩证传统的要义,只是为了发现当下日常生活中真正的新颖之处,只有这些节点才有可能产生新事物,而大多数我们以为是现代技术世界新事物的东西其实并不新。在涉及学者的任务范围时,他甚至走得更远:将前人已经知道的知识,重新讲述给当下的读者,也是学者的应有之义,不要寄希望于每一句话都是发前人所未知:人类不是一直在复述已有的知识,使之得以传承吗?
鲍辛格这些听似“异类”的看法,源于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取向:民俗学的对象——无论是当下还是过去——都不是本体论的存在,而是知识生成的结果。近年来,我有幸通过翻译接触到科学史的视角,关注到历史学家对知识产出之历史情形的描述。②[德]薛凤、[美]柯安哲编:《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吴秀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关于专项知识的保密和公开问题,关于书籍太多、信息过剩的问题,在16世纪都曾经是让人们感到焦虑不堪的新问题,与今天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本关于中世纪女性生育健康的书,对学术界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和伤害。莫妮卡•格林(Monica H. Green)在一篇资料丰富的长文中揭示了一个错误断言的由来,这个断言的内容是:在男性权力还没有占据女性身体的“黄金时代”,女性从事医学实践、彼此自由地分享关乎自己身体的知识,只有女性才拥有某些关于女性身体的“天然”知识。这一断言来自一本在1971年初版时只有45页、完全基于二手材料拼凑而成的一本小书《女巫、助产婆和护士》(Witches, Midwives, and Nurses),该书的两位作者中,艾伦瑞克(Babara Ehrenreich)是一位获得生物学博士的美国专栏作家、公共知识分子,英格利希(Deidre English)则是一位记者。这本书几乎被翻译成各种西方语言,长销不衰。更令人遗憾痛心的是,这本书的影响远超出一般的通俗读物,而且进入专业知识生产的循环当中。当著名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对分娩进行人类学比较研究的奠基人布丽吉特•乔丹(Brigitte Jordan)在自己的著作中接受了前者给出的历史描述之后,这一断言便借助于乔丹的著作被纳入更大的学术生产范围。在格林看来,这种大范围的以讹传讹,阻碍了对复杂历史状况的进一步探讨,一个貌似为女性主义发声的不实断言在实际上伤害了女性主义的学术探索。①[美]莫妮卡•H.格林:“让社会性别进入女性医疗史”,见《科学史新论》,第389—447页。乔丹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道:“在一千多年里,分娩无可争议地是助产婆的领域。那个(近代以前)时期的助产婆也许是民间治疗者,她们不光照顾分娩,也在总体上负责普通人的保健需求……分娩被明确地认定为女人的事情,这一界定显然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②转引自格林的文章,见注释12,第397页。这种描述往昔风俗的方式和风格,让人感到多么似曾相识!
科学史和民俗学,两个原本没有很多交集的学科意外地相遇,像是在给鲍辛格的观点做了一份扎实的注脚。
三、读以致用:新冠疫情观察的“案例”
我并不寄希望于通过读鲍辛格的书来找到自己的研究题目,而是要借助于书中的智慧来理解在德国的日常生活。鲍辛格在书中检视了16个日常生活中的截图,所涉及的话题包括体育排名榜,成就管控,信息获取,社交密度,流言蜚语,购物,着装,账户余额,餐食习惯,疾病处置,性爱安排,旅行,收藏,习俗庆典,游戏,知识竞答。在2020年读这本书时,让人不由得最想翻看 “病有所得”这一节,参照着去观察德国的新冠疫情应对。
在这一章里,鲍辛格首先从“疾病收益”(德语为Krankheitsgewinn,英语为morbid gain)这个被多方使用概念说起:医学上用来讨论疾病——一种与惯常的生活状态完全隔断的情形——的心理学背景;哲学家把患病看作一个人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思考、获得人生智慧的契机;平常人也会把(不严重的)疾病与一些正面的经验连在一起:安静、休息、得到关照、战胜疾病的体验,都可以被感知为是收益。在面对疾病时,结果型取向的做法体现为:许多人医学知识有限,却掌握大量医学词汇;对不适症状,要求有明确的疾病名称和证据(拍片或者化验结果);无论病情严重与否,都要求医生给出药物治疗方案——如果得不到医生开具的处方药,很多人会寻找另类医学疗法,自己购买非处方药;讲述自身病情病史成为社交谈话之一部分的情形变得普遍,人们通过讲述,把疾病的负面体验转化为正面的结果。一种根植于传统、今天仍然没有得到纠正的做法是:那些不会导致惯常生活完全停摆的疾病,则难以被当成疾病看待。带着这些画面来观察德国的新冠疫情应对,会有一切都似曾相识的感觉——前所未有的疫情,并不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人类行为。
新冠病毒(Covid-19)在2020年1月就在德国有感染者,由于发现早、检测及时,传播链在初期得到遏制,但到2021年3月形成了蔓延之势。但是,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新冠疫情状况算不上是灾难,只能说是一种对大众健康形成严重威胁的传染病。从世界卫生组织(WHO)到各国健康部门以及私营机构都在汇总数据,德国的数据显得亮眼,绝对死亡人数以及病亡率都处于相对低水平,而社会停摆措施(民间戏称为“家里蹲”)则相对宽松,限制居民外出的做法除了在个别疫情暴发点短暂实行以外,并没有在大范围内成为常态,在户外公园散步、运动一直都没有禁止;最严格时,不在一起居住者的聚会人数限定为二人。这种“一枝独秀”的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系列受文化影响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吗?是因为德国人性格中的“理性”使然吗?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外力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德国的联邦制的社会管理机制,联邦和各州政府快速出台的纾困举措,抗疫的目标定位于在避免医疗资源崩溃的前提下将经济损失最小化、做长期与病毒共存的准备,这些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如果从个体应对新冠病毒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此番的病毒应对恰似日常疾病应对方式的放大。对“疾病收益”的意识是人们最先乐于表达的感慨:终于能安静下来,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做了多年来一直想做、但苦于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重新看到代际、邻里、社区之间的关爱和互助,归属感增强,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呼吁全社会要关照那些“风险群体”(年长的以及有基础病的人),其中不乏有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公益活动来救助那些受打击最大的群体,尤其是那些无法举办音乐会、展览的艺术家们以及精神文化创造者以及为他们提供辅助服务的人员。
公众看重结果的取向,表现在特别看重那些能以数字方式展示的结果,这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负责传染病监测和应对的联邦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简称RKI,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疾控中心)在官方网站上每天发布感染人数的细分信息。这些数据是由各县的卫生局逐级上报汇总而成,每24小时更新一次,周末两天的数据往往会低于平日,这是由于上报延迟造成的。但是,延迟报告的病案并没有掉出统计数据,会体现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对此,科赫研究所在新闻发布会上不厌其烦地对公众进行解释,其中也包括如何正确解读相关数据。比如,当时的感染人数少并不意味着德国的疫情管理比其他国家好,只是因为德国还在疫情发展初期;初期病亡数极少并不意味着病亡率低,只是从染病到死亡会有一段时间。总体上,科赫研究所要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不要轻视病毒的危害,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在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出现的灾难情景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这里。当时还有另外一份数据源备受关注,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根据互联网上的信息抓取汇总的数据,那里显示的感染人数以及病亡人数总是高于科赫研究所官方网站上的数据。科赫研究所属于联邦政府的官方机构,他们给出的任何信息、意见和建议,都具有指导全国抗疫安排的意义,需要基层付诸实施。因此,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都是所长亲自出场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表述也非常谨慎。当病毒学家们意识到对这一病毒有很多知识盲点时,发言人就变得更加小心翼翼,这就让公众开始怀疑官方机构是否有隐瞒实情的嫌疑。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非常关注相关信息,于是几乎每次新闻发布会的实况转播我都会跟踪观看。我不是数据怀疑派,也不苛责记者们的追问,明白记者们也是在替他们的受众发出质疑。过分看重数字式结果的取向带来的负面效果,在疫情中让人看得更加真切:人际间最宝贵的资源——信任——受到极大伤害。一个场景令我难忘:当科赫研究所的所长威勒(Lothar Wieler)又一次被问到为什么他提供的数据感染人数要低于其他数据源时,教授说:“请您相信,我们是掌握了自己专业技能的人。请您相信我。”这几乎是在以个人的信誉为机构的信誉背书,一种退无可退的处境。可以说,这是整个疫情新闻中让我感到最为难过的画面,最直观地感受到以量化形式的结果为取向的做法有多么荒谬。
科赫研究所提供的是流行病学的数据和知识,而公众对新冠病毒最新研究状况的了解只能来自于专业的病毒学家。在此期间,公共传媒想方设法让专业学者发声,给公众提供相关知识,其中最为出色的是柏林的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教授开设的科普广播节目。德罗斯滕是专门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专家,从武汉获得病毒基因数据之后,他的实验室很快便开发出检测工具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他的专业知识背景是无可置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同意开设科普广播专栏的理由,因为他用不着花太多时间准备,就几乎可以回答这一领域的任何问题。偏巧他也有语言表达方面的天赋,有本事把复杂的事情解说得让外行人也能听懂。这个广播节目的听众超过一百万,这是他本人以及主办者都未曾想到的。我自己以及周围认识的人,几乎都成了这一节目系列的听众。这也是对渴求医学知识这一做法的放大,因为还没有通俗医学读物让公众获取相关信息,而专业论文是普通人看不到、也看不懂的。德罗斯滕会挑选出一些尚未正式发表的预印本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媒体上带来某种轰动效应的论文,向听众转述病毒学家的论点。他的科普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光表述病毒学知识,另一方面也让听众了解知识产出过程。比如,他曾经直言自己对一篇论文的不屑,认为该文章对病毒基因变异的分析采用了哺乳动物基因变异的理论,实验做得也不干净。据说他的这些广播节目马上就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传播,其中也包括汉语。一旦这种“教育”资源变得火热之后,各种以专家、医生名义评点病毒、抗疫的做法便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其中也包括完全否认疫情严重性的各种阴谋论论调。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一些此前几十年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词汇,仿佛大家都可以对病毒、疫情、患者治疗发表些自己的看法。这些一知半解的知识、不全面的信息,自以为是的质疑权威的态度,恰好符合“半教育”情形下的状况:一群受到“半教育”的人并没有带来知识社会应有的理性,反倒成了反智 “阴谋论”的滥觞。
口罩成为本次全球疫情中讨论最多的话题。在民众是否应该戴口罩阻止病毒扩散这一问题上,德国的抗疫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呼吁民众不要使用医用口罩(当时口罩为紧缺医用品,仅供医护人员使用),到建议民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自制的普通口罩即可),再到出台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违者罚款的新规。疫情之初,在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很少有人戴口罩,这被解释为是由文化因素造成的“非理性”行为,因为这里没有像东亚那样的“戴口罩文化”。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的话,后来的事态发展则足以说明,文化因素的屏障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击破的。可能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利他的公共道德要求与对抗疾病中“手段即结果”行为模式的叠加,使得戴口罩戴做法很快被接受,也给“违者罚款”的公共管理政策提供了理由。
夏季到来让疫情缓解,而进入八月份之后,德国以及欧洲各国的新增感染人数都在急剧增加,随着秋冬将至,流感与新冠疫情的叠加会使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尽管防疫政策如履薄冰,德国疫情的第二次高峰还是在圣诞节前出现了。病毒感染者的病程和症重程度显示出极大的个体差异,如此一来,人们对该疾病的感知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人而异。虽然有个案表明,私人聚会和庆祝活动是新冠传播的重要源头,但是限制私人活动的方案却极难获得认可。总理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严正提醒公民,不要忘记遵守抗疫规则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祭出“责任”这面道德大旗的做法,实为罕见之举,这也足以说明问题的含混性、复杂性和艰难性。
对于日常表象不要快速给出非黑即白的解释,这是鲍辛格倡导的经验文化研究认为有必要让其长鸣不止的警钟。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研究进路也难以获得线条清晰的框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沿着鲍辛格的思路去观察,我们几乎看不到有所谓的“典型的德国人”现象,在诸如“理性”“严谨”“秩序”“做事一丝不苟”这类标签下,可以看到很多以获取(显示为数字的)结果为目标的行动主义。比如,在入境口岸临时增加新冠病毒检测站,为那些从国外度假回来的人做咽拭子采样。尽管病毒学家从专业角度认为,目标不确定的海量检测是对检测资源的极大浪费,但是这种能“立竿见影”的举措仍然被当作获取执政资本的利器,仍在各地大量实行。以数字形式展示出来的结果,是对复杂的实际状态的极简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的数据仍然是政策出台的依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数据是每10万人口7天内新增感染数。如果这项指标达到50以下,就可以考虑到逐步放开限制措施,恢复正常。但是,这个目标目前似乎还难以实现。当全球各地接种疫苗普遍展开以后,已完成的疫苗接种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又成了一个颇为直观的结果,很容易被公众用来衡量抗疫施政的成功与否。数字背后那些复杂关联会遭到无视,在遭遇严重疫情之后,社会是变得更加公正和自由还是正好相反,分化和对立是变得更加严重还是得到弥合,共同体变得更加团结还是更进一步走向分崩离析,这些才是真正的结果。数字形式的结果,尤其是在流行病控制方面,虽然是万万不可忽视的,但是那些以获取数字形式的结果为取向的行动主义,既缺少高尚的动机,也谈不上价值伸张或者执政效率,无非是把普通人庸俗的日常行为逻辑进行复制、粘贴后做成一份升级版而已。鲍辛格的书会让我们明白,你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才是那些冠冕堂皇的行动的真正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