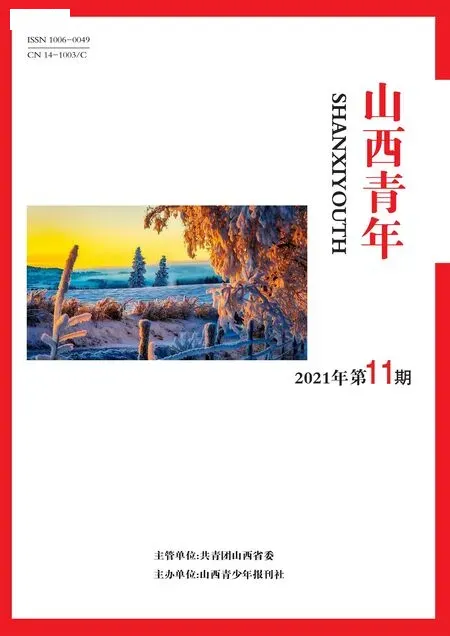文艺学与中学语文教学的主题研究
——以《背影》为例
2021-11-27文玲
文 玲
(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在现代教学活动中,张红顺在《<背影>“主题”教学的反思与重建——基于叙事学的视角》中指出:“《背影》的教学主要集中在分析文中父亲的四次‘背影’,而这四次背影中又将80%的时间集中在父亲跨过铁道为儿子买橘子时留下的那次‘背影’上[1]”。《背影》的教学设计主要是围绕父子深情、父爱如山展开,这种主题的阐释只停留在了文章的表面,没有解读出其中的深意。
《背影》作为一篇记叙散文,作者用朴实的笔调叙说他与父亲之间的故事。虽然记叙散文中的人物和情节不如小说丰满,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许多方面留下了疑问,非常值得探讨。如“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余年了”中的“不相见”是不想见面还是不能见面?在“二余年”中,作者与父亲又发生了什么?又如“那年冬天”是指哪一年?文章中的时间线索众多,作者的作品又是写于哪一年?这篇文章疑点重重,张红顺在《<背影>“主题”教学的反思与重建——基于叙事学的视角》中指出:“这一系列的疑问在文学创作中被称‘创作空白’,对于这样的创作空白,我们主要采取还原与填补的方法[1]”。针对这样的特点,本文将运用叙事学从叙事时间、叙事动机方面来解读文章的主题。
首先从叙事时间进行分析作者的心路历程,方爱玲在《朱自清<背影>的主题阐释——记录并剖析自我的心路历程》中指出:“这篇记叙散文其实是作者通过父亲的背影,深刻记录并剖析了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2]”。文章一共出现了五次时间,分别是:不相见已二余年了、那年冬天、近几年来、最近两年、我北来后。作者时空上交错的安排,如果不细细考究就很容易混淆。张红顺在《<背影>“主题”教学的反思与重建——基于叙事学的视角》中指出:“根据《朱自清传》可知,《背影》写于1925年,而文章所记叙的事情发生在1917年[1]”,所以文章的时间线索是1917-1925年。
这些叙事时间看起来比较笼统,但实际上这些时间线索中蕴含着许多的内涵。作者用寥寥几字概括了不同时期的他,这就需要根据作者的背景对写作内容进行还原和填补。这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魅力,展现出一种简洁与含蓄的美。正如“那年冬天”,作者没有指出确切的时间,但对作者背景进行填充后可知:那时的作者正经历祖母的离世,家境的衰退。又如在最后一段,作者用“近几年来”“最近两年”“我北来后”寥寥数语就概括了作者大学毕业后四处奔波的经历。作者用简略的语言,将过去的艰苦变成了值得回忆的往事,呈现出了作者成长的心路历程。
作者用简洁的语言交代了1917年时家庭状况,为下文奠基了一种悲伤的情感基调,在这样的基调之下再引出了“望父买橘”的场景,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但作者为何时隔八年才提笔写下这触动他的背影?因为在1917年,作者才20岁,而写下这篇《背影》时,作者已经28岁,八年时间的跨度,作者增长的不仅是年龄,还有他的心智,成长的心智看待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见解。20岁的作者总觉得“父亲说话不大漂亮”,还“暗笑父亲的迂”,从这些句子中能够看出,20岁的作者并没有领会到父亲对自己的爱。但随着心智的成熟,28岁的作者感慨道:“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那时真是太聪明了”,这其实是作者对20岁的自己的一种嘲讽。同样的背影,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境之下,他的感触是有差别的。作者通过对背影态度的转变来剖析自己,展现出不成熟的自己,以及多年后对这种情感的顿悟,展现出作者从不理解到理解成长的心路历程。
韩军在《生命匆匆 大去不远——朱自清阐释的<背影>灵魂》中指出:“朱自清写《背影》就是因为文中所引起的父亲来信里那一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3]”。当作者在信中看到父亲谈论到死亡时,如此沉重的笔调,让作者内心隐藏的情感喷薄而出,因此深情地写下了这篇文章,这是对父亲的爱的回应。
“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是叙事者的直接叙事动机,但细细咀嚼,便会发现这其中还暗含着关于生命的哲思。作者看到这句话后是泪如泉涌,作者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转变?作者在文末发出了:“唉!我不知道何时再能与他相见”,作者的一声“唉!”,包含着复杂的情绪,蕴含着一种惋惜,一种自责,一种悔恨,即没有早点感悟到父亲的深情,没有早点与父亲冰释前嫌。“何时再能”简单四个字中蕴含着与父亲相见的期待,又蕴含着不知何时才能与父亲再次相见的失落。这些情绪的产生都是因为作者在父亲的信中意识到了生命匆匆,刹那消逝,在死亡的面前,生命脆弱而短暂。在生命匆匆的哲思里,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他的感情经过了沉淀和发酵。他成长的心路历程,让他对生命的思考更加的深刻,让他懂得生命匆匆,应及时去爱的道理,作者在生命的哲思中幡然醒悟:趁父亲还未“大去”,要抓紧时间去尽孝、报答、爱他,不要留下亲情的遗憾。
除了叙事时间和叙事动机的角度,《背影》中的叙事视角和结构也值得挖掘。《背影》讲述了父亲和“我”之间的故事,文章的人物主要是父亲和“我”,虽然人物关系简单,但作者将两人放置在交错的时空中,使人物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过去的父亲,更年长的父亲,过去的“我”,年长的我。于泽元在《情深只因伤离别——对<背影>的深层解读》中指出:“作者正是通过时空的转换的离别的故事传递出浓郁的情感,情感因离别而深沉,离别也因情感而深刻[4]”。《背影》结构上时空的交错,形成了人物和背景的二元对立。赵炎秋在《文艺学批评教程》中指出:“二元对立是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的理论基础,他注意到人类是通过这两种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来构建世界使其产生意义[5]”。对不同时期人物关系的深度挖掘,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深意。
作者在文章中以第一人称“我”承担叙事者,赵炎秋在《文艺学批评教程》中指出:“在叙事的过程中,叙事者可以介入叙事,在故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与看法[5]”,叙事者在文章的叙事笔调中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父亲坚持去车站送“我”的场景中,过去的父亲的言行:茶房去不好,不放心“我”,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用紫毛大衣给“我”铺好座位。而过去的“我”的言行:父亲不必去车站送别,父亲说话笨拙,父亲很迂腐,父亲操心太多。这呈现出的言行都是“我”的所见所感,“我”是作为一个固定的叙事视角,真实地表达出在当时场景时的感受。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出:过去的父亲与过去的“我”在情感上是对立的,在对立的笔调中,传递出叙事者的情感倾向,突显出父亲的深情,反衬出“我”的无知,在这种反衬之中,表现出叙事者对自己当年的行为产生的深深的忏悔之情。
当叙事者时隔八年后回忆这段往事,他又呈现出不同的情感。现在的“我”认为:“那时真是聪明过分,非自己插嘴不可,那时真是太聪明了”。在过去的“我”的描述之中,表现出对父亲的嫌弃。过去的“我”对父亲的深爱是不在意的,但多年之后,经过生活的沉浮,现在的“我”开始对这种言行进行反思,在这种反思之中,开始懂得父亲的用心与深情。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情感上又是对立的,在叙事者自身情感的对立之中,表现出叙事者的情感倾向。叙事者以讽刺的笔调嘲讽过去的自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言行,从侧面表现出叙事者对过去自己言行的一种自责,对过去不在意的态度的一种愧疚,更是对过去的自己不懂父爱的悔恨。这是叙事者经过岁月磨砺之后,洗净铅华,由学生到父亲身份的转变,让他更懂得父爱的艰难与不易,对父爱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刻。
除了人物的二元对立,文章还有背景的二元对立。叙事者开篇交代了家庭的背景:“父亲差事交卸”“家中的光景很是惨淡”,父子二人都要为了生计东奔西走。但叙事者文末又写道:“父亲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从中可以看出父亲绝非等闲之辈。而作者就读北京大学,有着出众的才华,也不是庸碌之辈。那为何父子二人艰难的奔波后,家中依旧没有转变?刘保民和戎东贵在《<背影>主题思想探微》中指出:“作者笔下惨淡的家庭生活景况也不是孤立的,他其实是社会现实黑暗在作者家庭投射[6]”。结合1917年时的政治背景来看,作者写的是1917年经历的事情。那时的中国不太安稳,有着内忧外患,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的家庭在当时算是小康家庭,但在这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下,即使是小康家庭,也不能用智慧和艰辛的劳动去创造幸福的生活,更何况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在对立的叙事者的叙述中展现出家庭背景与社会背景的对立,表现出即使是小康家庭,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之下,智慧和艰辛的劳动也不能创造幸福的生活。叙事者以小见大的笔调,用自己的家庭状况来反衬底层人民的家庭状况,即自己的家庭状况如此,更何况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在这种对立之中,展现出“我”对所处的黑暗社会的不满。叙事者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而是让读者在客观的描绘之中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叙事者隐蔽的叙事声音,叙事者通过间接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倾向,即对社会的哀怨之情:哀社会给人们造成的不幸,怨人们造成不幸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