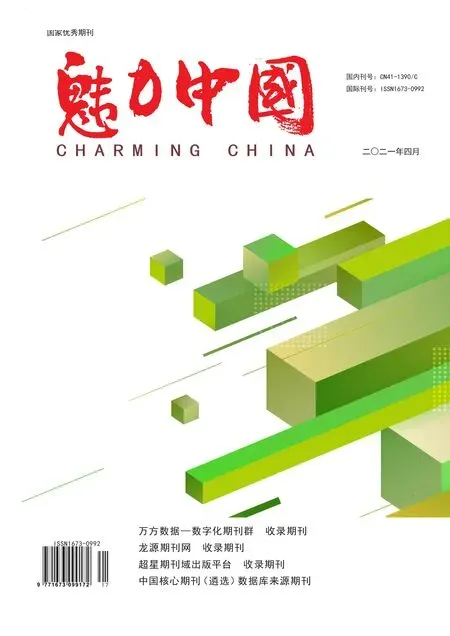扶贫驻村干部面临的治理困境探究
——以L 市C 村为例
2021-11-26陈枫季英伟
陈枫 季英伟
(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一、C 村扶贫概况
C 村的位于L 市东部,气候属于亚热带热带过渡地区,当地主要产业为经济作物和水稻种植业以及经济速生林种植,水资源较为缺乏。全村贫困户有91 户,其中该村的主要人口为中老年人,青壮年劳动力多外出打工或定居至城市。
C 村的扶贫干部主要来自对口帮扶城市F 市,驻村前均为公务员或国有企业的中高级员工,年龄多为三十至三十五岁的中青年干部,通过选派的方式入驻贫困村负责领导脱贫攻坚驻村工作组。
二、C 村扶贫驻村干部面临的主要治理困境
(一)贫困治理主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首先是扶贫干部与上级政府之间存在矛盾。在扶贫工作中,上级政府对扶贫干部只考核各项量化指标,而扶贫干部在驻地开展的长期性、见效慢的项目很难通过考核反映出来。考核的压力使得扶贫干部在决策取向上倾向于短期性、见效快的项目,但这对于贫困治理这种需要形成持续性脱贫动力,有效的永久脱贫的长期性工作而言是不利的。
其次村干部与扶贫干部之间也存在冲突与矛盾。C 村的村干部由于自身行政水平的不足和责任意识的缺失。使得C 村出现了“扶贫干部拼命干,村干部坐着看”的现象。这一矛盾又带来风险责任的承担出现混乱,各方推卸责任。C 村中投资的风险责任承担问题一直不明确,村干部不想承担,扶贫干部承担不了,上级部门又通常会推给下级部门,下级部门无力处置,最后形成一笔坏账。
(二)过高的工作强度与过低的回报的矛盾
在C 村的扶贫工作中,工作组需要进行扶贫资金的管理、扶贫信息的收集汇报、深入贫困户家中进行走访,同时需要协调扶贫产业的运转情况。由于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以及本身村干部在扶贫工作中的缺位,使得工作组在工作中不得不承担与一些扶贫以外的工作,工作强度高。
高强度的工作在回报上并不高。扶贫资金的使用上时常会收到镇政府的干涉,使得一些资金的投入效果不佳,甚至白白浪费。部分贫困户的消极心态使得一些政策的执行效果并不好,只能改变原有的补贴方式改为以奖代补的方式以到达考核目标。扶贫干部在收入和职业预期上也并不稳定,原单位薪资加补贴虽然看似金额不小,但是作为家庭在一线城市的普通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生活成本依旧不小。
(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低效与缺位
作为一个贫困村,C 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自于水稻种植和经济作物种植,较低的财政收入使C 村很难集中足够的资金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存在缺位。例如在公共安全领域,由于村中缺少足够的公共安全产品的供给,黑恶势力会以暴力或威胁的手段向当地商户收取保护费,提供所谓的“安全保护”,形式上成为公共安全产品提供者。
而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又因宗族组织影响村务决策而变得拖沓和低效。在C 村及其周边区域,一项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决策若需要顺利通过,就必须在各个宗族群体之间达成共识,因为缺少相应的规则规范,同时没有一个协调的核心,导致这种博弈漫长而低效,最后导致项目搁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C 村所在区域由于各个村庄的大姓氏宗族出于自身利益各自修路,最终导致的“主路比小路差”的现象。
三、扶贫驻村干部治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俞可平在论述有关“善治”的问题时指出,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于国家与市场之上。而善治在C 村的贫困治理工作中没能形成,扶贫干部的治理过程也由此出现若干困境。C 村的扶贫干部的这些治理困境的产生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一)贫困治理主体间协作机制未能形成
扶贫干部与上级政府之间缺乏有效信息沟通机制。这种信息沟通不畅导致扶贫干部与上级政府之间工作的不协调,其表现为三点:1.扶贫资产的使用与拨付出现了不符合当地条件的现象,扶贫干部对于贫困户的需求信息没能有效反映在政策当中。上级政府对于C村的扶贫资产划拨存在“一刀切”,缺乏对当地实际情况的充分考虑。这直接导致了C 村出现的变卖扶贫物资用于其他用途的问题;2.上级政府的考核的形式化要求与扶贫干部现实工作状况并不匹配。上级政府对于扶贫干部的考核往往是以量化指标进行绩效考核,这类绩效考核过于细致,对于长期性、见效慢的工作反馈不明显甚至呈现负的反馈。3.虽然与全省其他地方一样采用数字化管理,但是受限于本地的政务信息化水平,很多工作仍然以传统方式开展,数字化管理流于形式。
(二)扶贫干部管理中激励机制的缺失
当前在扶贫干部管理过程中采用的激励是一种以精神激励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物质激励的模式,通过对工作努力、业绩显著的干部进行表彰、树立典型来调动整个扶贫干部群体的工作积极性。从效果上来看,这种激励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干部尤其是党员的荣誉感,在参与扶贫工作初期可以给予其较大的工作动力。但是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仅仅依靠荣誉、表彰这样的精神层面的激励动员很难让扶贫干部在面对高压力的工作内容、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置以及较低的回报的时候选择留下来。只有在扶贫干部的待遇以及择优晋升上给予有效合理的保障,让扶贫干部有稳定的职业预期,再通过表彰先进等精神激励,才能够让扶贫干部有动力、有信心面对复杂、艰难的扶贫攻坚工作。
(三)传统农村利益群体对基层治理的干扰
C 村是一个典型的南方村庄,宗族文化作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当地的政治运行。在扶贫治理过程中,扶贫干部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建设项目,这就会涉及到各个宗族群体的利益,并产生相互之间的博弈。在这种博弈当中,扶贫干部往往很难作出有效的协调以使各方达成共识,在没有迫切需求的情况下有些长期项目就容易被搁置下来。项目的搁置就导致一些公共服务的供给变得低效和失败,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C 村的道路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整修,新修的市场由于黑恶势力的干涉和建设设计上的问题荒废至今。这种决策上的困境是当前C 村扶贫干部面临的主要治理困境之一。
四、应对扶贫驻村干部治理困境的对策
(一)构建扶贫治理中各主体间的协作机制
结合C 村的实际以及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要改变当前各治理主体相互冲突矛盾的问题,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协作机制,这包括:1.清晰界定工作责任,明确扶贫治理中各项工作责任划分;2.因地制宜的使用和拨付物资,减少因为物资实用性差造成的资金流失;3.建立一个由党委协调领导的有效的多方协商平台,各个主体可以在平台中有序协商、形成共识;4.决策过程以协商民主的形式做出决策,减少个人决策带来的寻租空间;5.通过规范化的程序使得资金使用公开透明,从而是资金使用得到有效监督;6.规范整合考核体系,以统一标准对扶贫工作中涉及行为失范的扶贫干部、村干部实施分级处罚;7.中央和省级政府对治理规则进行赋权,保障其合法性和有效性;8.立足于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治理规则;9.通过建设以基层数字化政务云为基础的扶贫工作数字化平台,建立扶贫干部与上级政府的有效反馈渠道。
(二)完善激励机制,提高物质激励水平
首先,在原有激励模式的基础上,依据扶贫工作的绩效,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有梯度的提升一线扶贫干部的待遇水平,在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资金奖励。其次,在公务员职务考核过程中,提高扶贫干部的经历及其绩效在晋升考核当中的权重水平,使得参与一线扶贫的基层干部有足够的晋升空间。其三,通过专门的福利政策,保障扶贫干部的住房以及子女教育,对扶贫干部子女的优质教育的分配上给予适当的优惠。从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让扶贫干部有底气面对复杂的扶贫治理工作。
(三)提升基层干部队伍治理水平,塑造乡村治理新模式
在本地干部选拔的基础上,通过“三支一扶”、公务员选调等政策措施,引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村官以及行政能力强的公务员担任村干部职务,使得基层干部队伍年轻化。在构建起人才基础后,以人才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以声望为标准选拔村干部的现象,提升公共决策能力和水平,并在此进一步对乡村宗族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