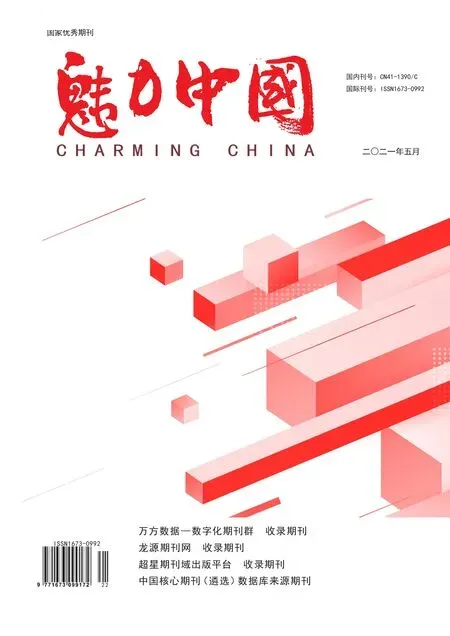人文学问的困境与方法
2021-11-26楼舒彦
楼舒彦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一、人文学问的困境
在今天,通常人们理解什么叫作“人文”,大都将其与“科学”进行对比,从而划出二者的界限,譬如“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事物,具有严谨、不做价值评判等特点,那么相对的,“人文”则意指包含现实关怀,更关注人或事的情感领域。可以说,人们从来没有深入追问过“人文”与“科学”彼此之间的对立关系从何而来。
事实上,人文学问与科学的分道扬镳同步,其现代分化可以追溯到康德关于三大批判所提出的“不可通约性”,即“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被区分为现象的知识、道德的知识和审美的知识,而各自的原理具有根本性差异,……人文话语与科学话语的区别导源于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2]。譬如当下人们对“真”“善”“美”之间的严格区分态度,也是以某种变形表现出的“不可通约性”。因此,当我们阅读八十年代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时,也能从中发现小说的明确态度——以科学、宗教、艺术作为代表,分别各自对应真、善、美三个领域,并且这三个领域各自独立,互不相关。学术界普遍认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以反现代的现代性姿态所开展的革命实践。其中,所谓“二十世纪”的定义或称谓并非笼统地按照时间的划分[3],八十年代的开启可以算作二十世纪中国的终结,同时成为人文学问与科学的新转折,《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等一系列文学作品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出现都已然预示了这种转折。“人文”的转折如此,“科学”亦是如此(因为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转折的同步性,以及它们共同受制于现代性的理性化进程)。二十世纪中国的“科学”与“人文”(乃至文学、审美等相似概念)一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知识体系,它是关于现象的知识,但同时也是道德的知识和审美的知识。譬如晚清时期知识分子们普遍以科学为前提,重新构建文学、国家、道德等各个领域,还有如从延安时期及至建国以后在农村开展的技术员下乡的革命实践,强调科学与工农兵的结合,都既是注重科学的生产性功能,也内含着提高劳动人民主体性地位的考虑。因此,借用学者南帆对民族的文化价值的定义,同样的,所谓科学(或人文)的功能,并不在于其本质化的内核,而在于它与各种对话所制造的周边关系及其生成的诸种功能。
带着这样的思考从追溯历史到回顾当下,可以发现,虽然我们可以说人文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在社会重大事件中缺席,呈现出众声驳杂的热闹场景,譬如温儒敏对八十年代“人文学科”的回忆——“1978 年北大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招考研究生,计划招收五六个人,却有六、七百人报考,简直挤破了门。别的大学情况也大致如此。那时学生高考选报志愿,中文专业是许多优秀考生的首选”[4]。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时刻认识到,此种“多元化”是建立在没有普遍适用的价值规范之上的。所以,伴随着“向内转”的八十年代的开启,文学写作逐渐要求纯文学回归,与意识形态解绑,逐渐要求“回到文学自身”,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化的、专业化、职业化的潮流暗涌。同样的,“科学”也逐渐重新退守为现象的知识。在该浪潮的波及下,人文学问开始退守为某种自娱性的“审美游戏”,并被专业化学科的框架所自愿笼罩,强调所谓“价值中立”,人文学问逐渐以既得利益者的保守姿态出现,在愈加自我封闭的学科框架之下丢失其统整某种社会共同体的组织能力,或许出现对别的领域的关心也不过是在已然建构的知识大厦中所做的无关痛痒的问候而已。在此层面上,“文化研究”的活力曾受到人文知识分子们的关注——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泛文化”的趋势和批判性的思维模式鼓舞了许多研究者。但是文化研究做法的高效率是否有理论先行的预设,以及文化研究在多大程度上离开了文学和审美,也受到了人文研究者的质疑。因此,如何在不丧失人文自身领域独特性的前提下,同时处理因为理性化进程而经常被排斥为“非人文”的内容,是人文学问在当下处于某种尴尬处境的原因之一。
二、人文研究的方法
面对人文学问的困境,本文借用学者朱羽的说法,试图从守势与攻势的两方面推进。守势关注人文学问内部对知识、学科、真理的态度,使人文研究者时刻保持清醒,攻势则在于力图破除人文学问的保守面目。当然,关于守势与攻势的辩证关系,就如同学者葛兆光所说的,要“在这样的专业知识基础上,你再谈论那些宏大的精神、认同、人格、素养等等,仿佛才有力量”[5]。
因此,福柯的研究方法对我们极具启发性。如果我们认为他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探讨的仅仅是某种病理学的知识谱系的话,那恐怕是对福柯的思考的极大轻视。福柯的工作关键在于向我们揭示了社会类型被“话语”装置不断修正和建构的过程,而这种社会类型往往被当时代的人们看作某种具有总体性、一元性的真理对待。以中国现当代学科为例,福柯的思考意味着同时需要思考“中国现当代学科”这一知识的被建构性。譬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在模式上对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影响,其“话语”(典型的如它对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文类的划分模式)甚至阻碍了我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和书写当代文学史。进一步言之,人文研究者的权力也来自于此,因为这套装置既塑造了社会类型,也塑造了个人,人文研究者便在符合某种严格学科的框架下成为辨认真理之人,形成某种身份政治。韦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了他对于教师的警告——“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6]。
概言之,福柯警醒我们的,是人文研究者需要保持自身的谦恭态度,拥有不断辨认“装置”的自觉意识,在发展的光滑面上不断探索其断裂处与各种经验事实。仍旧以中国现当代学科为例,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多将其起点放置在新文化运动,截然断裂的叙述(“新”与“旧”的断裂)给“五四”以后的叙述者以新的历史代言人的合法身份,构成某种由知识分子们发起并被民众接受的启蒙神话。而学者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确实是对上述叙述的一大突破,但我们同样不能说,后来者的建构必然地比先前更具有真理性,这样的断言和限制于言语上的纠缠并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同样处于透明的“装置”之中。而一个真正的人文研究者所做的,应当是不断深入历史细部,破除对一元真理的迷信和自得,发现呈现放射状态的多重世界[7]。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福柯与韦伯的历史观有着相似性和同构性,如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坚持认识历史过程的现象都有多元因果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拿出任何一种要素都是片面的,也就是说所谓本质化的东西在历史中并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韦伯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因所在。换言之,他批判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倾向,即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建立某种普遍有效的规则以及强迫一切历史的因果解释最终归宿到某种经济因素的做法[8],此种做法把生活中的某个片面推至绝对、推向唯一,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所谓“哲学的危机”,也是我们应当反思的内容。总体而言,当今的学科化、专业化趋势要求人文研究者有对自身专业知识的精通,认为人文研究可以极富主观性地夸夸其谈的观点和在研究之前首先设置某种价值或意义的观念首先就应当抛弃,而能够明白某种知识在何种基础上被建构。另一方面,人文研究者也不应被局限于某种学科化的分工之中,所需要的是跨学科视野,因为在辨认“装置”的多种因素时必然将牵涉到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人文研究者并不必然地要驻足或徘徊于所谓文学领域之中,福柯对疯癫史的研究,韦伯对加尔文宗的探究,都是人文研究最好的例子,虽然人文的“话语分量”在八十年代末开始衰减,但我们仍然要说,人文研究的力量仍然在于它对于不同领域的关注,并折射出不同领域的复杂面貌和多样的可能性。
因此,再次回到人文与科学的转折期,不论是对中国八十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们,还是对于当下的学者们来说,重新辨析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关系都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在其著作《学术与政治》一书中,韦伯试图通过批判心志伦理以批判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9],并没有刻意抬高责任伦理的价值。韦伯要求从事政治活动者在恪守心志伦理的同时也要保持责任伦理,要求恪守“学术”的态度,保持价值中立。但是,韦伯自身探讨责任伦理的“装置”本身也嵌在他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思考之中,并主要嵌在“一战”以后德国战败的背景之中。所以,排除对韦伯言论的字面理解和生硬解释以后,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如何一面克服人文精神的危机,深入研究现代性而非躲避之,一面不满足于保持“特殊性”的立场而拥有重构“普遍性”的气势和话语力量,便成为夺回人文研究的阵地,塑造人文研究的社会功能,祛除普遍的冷漠态度,回应当下现实的关键。在此意义上,才有可能令当下成为一个可以与新文化运动相类比的“启蒙”时代。
三、总结
因此,我们实际上也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只是从一个“装置”转移向另一个“装置”,便不得不追问的是,那么人文研究者所做的工作意义何在。事实上,福柯的怀疑论思想并不旨在让我们放弃对当下做出决断,其知识的考古学工作所提醒我们的是警惕因果性的历史叙述以及装置、知识和真理之间的糅杂,而不管是福柯还是韦伯,他们都没有陷入怀疑论的迷思之中。他们既承认自己的研究肯定将被超越,同时也认可主体的能动和经验事实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正如保罗·韦纳总结的那样,“更为有利的是,我们因而只需专注于谱系学和考古学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这样一种可能,即退后一步以获得观察我们自身和我们时代的更佳的视角”[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