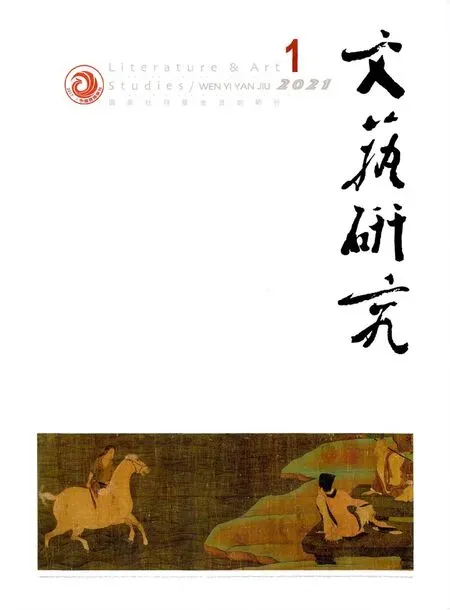近三百年《诗经》训诂学的盲点与误区
2021-11-26刘毓庆
刘毓庆
《诗经》训诂,是《诗经》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故最为研究者所关注。汉宋诸儒每有创获,清代音韵、考据之学兴起后,创获之多更盛于前。特别是乾嘉以降,出现了以王氏父子、段玉裁、马瑞辰、俞樾等为代表的一批以训诂见长的优秀学人,他们或从归纳中发现问题而寻求新诠,或以观念为先导而推陈出新,甚至以创新为目的而求新变。20世纪文化人类学引入以后,更是务求其新,异说丛见。回顾近三百年的《诗经》训诂研究,其间确有诸多振聋发聩之论,成就之大远过于前,但也存在着盲点与误区,其间自然也反映出了方法论与观念形态方面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盲点与误区,是对批量出现的训诂问题的分类,并非个案。但在阐述中,不可能将所有问题一一罗列,只能仅举其要,以说明问题为准。至于20世纪以降在“锐意创新”的风气下训诂上出现的乱象、怪象,因其所犯多属浅层次错误,历史自然会将其淘汰,故在此不予讨论。
一、《诗经》训诂学的盲点
所谓“盲点”,主要是指为习惯与成见所遮蔽、长期不被人关注的问题。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却被研究者群体所忽略。这主要有如下两类。
第一类,“成语形态”型。看似成语,实非成语,为人习惯性思维所误导,以致问题被遮蔽。如《大雅·大明》第七章云:“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之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①从语言层面上看,“殷商”作为一个固定的词组,常见于文献,《大明》的第二章就有“自彼殷商,来嫁于周”②之语,而且就“殷商之旅,其会如林”二语而言,释“殷商之旅”为商朝的队伍,亦甚顺畅,没有任何可疑之处。故自毛亨、郑玄始,历代研究者鲜有异说。其间也曾有疑之者,如于鬯在《香草校书》中就疑“殷商”当为“征商”之意③,但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故其观点几乎无人道及。若从逻辑上考虑,这一章前面言“殷商之旅”,顺势而下,应该是写“殷商之旅”的表现状态,然而各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下文“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所指的是周的军队,而非殷商的军队。这里显然出现了矛盾。研究者为了说明前后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又不得不增文为训,如朱熹说:“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维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④“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两语,即为经文所无。而唯有如此,才能使主体由“殷商之旅”更换为武王之师。但增字、增语为训,乃训诂之大忌,各家并非不知,只因泥于“殷商”成语陷阱而不能自拔。
再如《秦风·蒹葭》篇:“所谓伊人,在水一方。”⑱“所谓”二字一篇中反复出现三次。因为在人们的习惯思维中,“所谓”是常语,故诸家皆不作注。如龟井昱《毛诗考》云:“‘所谓伊人’‘所谓盟主’‘所谓故周’,古多语例。”⑲亦有人在此基础上发挥,如钱天锡云:“‘所谓’二字,意中之人,难向人说。”⑳陈组绶云:“‘所谓’二字有味。”㉑但从逻辑上讲,“所谓”用于复说、引证,前提是人已知其事或自己曾向人提及过,今则以“所谓”引出解释,表示“所说的”之某事某人就是某某。而此诗所写为男子暗恋水上女子,自是心中事,难为人道得,又会向何人复说、引证呢?此解显然不妥。但因“所谓”一词实在太常见了,故人们对其信而不疑,于是问题隐于其中,造成盲点。白平《〈古代汉语〉注释商榷》曾对此提出过怀疑,以为“谓”通“汇”“会”,指所会之人㉒。细揣其意,“谓”当通“惟”。《韩非子·解老》:“夫谓啬,是以早服。”王先慎《集解》云:“卢文弨曰:张本‘谓’作‘惟’。”又引顾广圻曰:“傅本及《德经》‘谓’皆作‘惟’。”㉓《尚书·说命中》“时谓弗钦”㉔,《礼记·缁衣》 引“谓”作“为”㉕; 《诗经·天保》 “吉蠲为饎”㉖, 《周礼·蜡氏》 引“为”作“惟”㉗。“谓”“惟”一声之转,故得相通。《尔雅·释诂》:“惟,思也。”㉘《说文》:“惟,凡思也。”㉙《生民》 郑笺:“惟,思也。”㉚《后汉书·杨震列传》:“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㉛此诗之“所谓”正同彼“所惟”,表示心中所思念。“所谓伊人”乃指心中所思念之人。
《召南·行露》中“谁谓”“何以”的语言构成,是同样的例子。其二章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三章云:“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㉜前人的关注点在“雀角”“鼠牙”的考证上,角指什么?雀是否有角?牙指什么?鼠是否有牙?长期以来为此争论不休,而对于“谁谓”“何以”二词,则将其意思固定为“谁说”“为什么”,不做丝毫怀疑,因为此是成语,不需要做过多考虑。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无论是角还是牙,都不是穿屋、穿墙的工具。动物穿屋掏墙用爪不用角或牙。若用“牙”穿墙,土必满嘴,无法忍受。动物的头角为触物自卫所设,也不能穿墙破屋。故日本安井衡《毛诗辑疏》说:“凡有角者皆走兽,我未闻牛羊麋鹿之属有穿屋者。”㉝也就是说,依雀有角(研究者或以为指雀嘴)、鼠有牙(牙齿) 之说,“谁谓”之问便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敢说麻雀没有嘴,老鼠没有牙齿;如依雀无角、鼠无牙的解释,则“何以”之问便不靠谱,因为穿墙破屋不用牙、角。因此,“谁谓”“何以”被默认的结构关系不能成立。
其实在这里,角、牙只是指尖锐之物,因为尖锐之物为穿物所用,故举以说明虽无尖锐利器,亦可以穿屋破墙的特例,以喻事有意外。这里的“谁谓”“何以”若读作“虽谓”“可以”,文理便通。“谁”“虽(雖)”“唯”“惟”等,其初文皆书作“隹”,偏旁皆后人所加,故例得相通。《易·丰》“虽旬无咎”㉞,汉帛书本“虽”作“唯”㉟。《淮南子·道应训》“谁知言之谓者乎”㊱,《列子·说符》“谁”作“唯”㊲。《左传·成公八年》:“唯或思或纵也。”㊳《释文》:“唯,本或作虽。”㊴《墨子·非儒》“用谁急,遗行,远矣”,孙诒让即认为“谁”当作“虽”㊵。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也言及读“谁”为“虽”之例㊶。“何”“呵”“阿”“可”等古皆相通。金文及简帛中,“何”多作“可”。文献中也常通用。《左传·襄公十年》:“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㊷《释文》曰:“何,或作可。”㊸同书《昭公八年》:“若何吊也。”㊹《释文》曰:“何,本或作可。”㊺石鼓文“其鱼隹可”“可以橐之”㊻,后人皆读“可”为“何”。这两句的意思是说:麻雀虽没有锐利的角,但可以穿破屋檐;老鼠虽没有尖锐的牙,但可以穿透厚墙。以此来喻男子虽没有“家”——没有大夫那样的权势,但足以撺掇弱者吃官司。
第二类是“常识形态”型。语词构成的内容从表面上看近乎常识,故在习惯性思维的误导下,按常识去理解,遂而忽略了其真实意思。如《秦风·蒹葭》首章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毛传解释为“白露凝戾为霜”㊼,今人多通俗化为“白露凝成霜”㊽。深秋白露变霜,这是一个常识,故对此两千多年来鲜有异说。但如与下两章相联系,在逻辑的层面上便出现了矛盾。因为下两章分别说“白露未晞”“白露未已”,说明“白露”还是“白露”,并没有变成“霜”。且诗以“苍苍”“萋萋”“采采”形容蒹葭之茂盛,显然不是霜后凋敝景色,何得言“白露凝戾为霜”?故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说:“白露欲为霜而未能,犹为露也。苟为霜,则不复为露矣。‘未晞’‘未已’皆未为霜之辞也。”㊾戴溪虽看出了问题,却不得破解之法,而是增一“欲”字以为训,又犯了训诂大忌。其实“为”当作“如”训。王引之《经传释词》云:“为犹如也。”吴昌莹《经词衍释》、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等皆有同说,裴氏曾举《吕氏春秋》 《战国策》 《墨子》诸书以证此说。如举《吕氏春秋·顺民》“鸮子曰:已死矣,以为生”云:“下‘以’字训‘尚’,言已死矣,尚如生也。”“为霜”即“如霜”。仲秋之月,日欲出时,地温渐升,地气上凝于蒹葭,结为白露,水珠细密,洁白如霜,故言“如霜”。随着太阳升起,细密的露珠渐渐融为一体、变大,由一层细密的白点融成几粒豆大的水珠,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此即所谓“未晞”。太阳再升,露珠蒸发,最后残留在叶尖,此即所谓“未已”。从“如霜”到“未已”,大约需两三个小时,这是一个时间过程,诗所言乃男子在水边久久翘望的情景。如果释作“白露凝成霜”,则三章层次全无,且诗味也会减少许多。
再如《大雅·公刘》第二章云:“笃公刘,于胥斯原。”毛传说:“胥,相也。”即察看。郑玄说:“广平曰原。”孔颖达疏解毛、郑之意说:“于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矣。”通俗言之,即于是察看这片平原。《大雅·緜》有“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之语,“胥”字即作“察看”解。如明沈守正《诗经说通》云:“‘于胥斯原’,犹言‘聿来胥宇’。见不遑宁处以奠民也。”“胥其原”与“胥宇”结构完全相同,是最常见的动宾式。在语言层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历代研究者多遵而不疑,只有王质《诗总闻》说:“胥,恐是地名。”但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像清代的马瑞辰、陈奂、胡承珙、王先谦等《诗》学大家,皆从毛而不疑。但如果与下几章结合起来看,问题便出现了。第四章言:“笃公刘,于京斯依。”第六章言:“笃公刘,于豳斯馆。”“于胥斯原”“于京斯依”“于豳斯馆”三句句法全同。“京”“豳”皆是地名,“胥”不应独为动词,也应当是地名。至于说其地在何处,自然还需考证。王质怀疑“胥”即汉之揟次,其说或是。“揟”从“胥”得声,例得通假。 《说文》:“次,不前不精也。”段注:“不前不精,皆居次之意。”如此则“揟次”蕴有在胥地居次之意。“胥”也有“须待”之意。《穆天子传》有“留胥之邦”,“留胥”与“胥次”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以地理方位考之,其地在今甘肃古浪西。而“于胥斯原”的“原”字,则是视察的意思。《管子·戒第》:“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尹知章注:“原,察也。”此句是说视察胥地。我们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诗篇用字之妙。“于胥斯原”“于京斯依”“于豳斯馆”,反映了周人的三次大迁徙。在“胥”是“原”,“原”是视察之意,说明公刘在“胥”地停留时间很短;在“京”地是“依”,“依”是寄居的意思,说明在“京”待的时间稍长些;在“豳”地是“馆”,“馆”有宫馆、舍止之意,说明在此地是久居。当然这里只是诗歌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不一定在“胥”就只是看而没有住,在“京”只是停留而没有生活。
最典型的是《魏风·硕鼠》的“硕鼠”,诗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郑玄笺说:“硕,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于是后之研究者便以为“硕鼠”是大老鼠。明清以前还偶尔可见、鼸鼠、礼鼠、鼫鼠之说,清以后基本上不是地老鼠(田鼠) 就是大老鼠,各家随意取释。但研究者大多忽略了一个问题,诗言:“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而无论是地老鼠还是大老鼠,都是吃粮食不吃禾苗的,“硕鼠”显然不是指大老鼠。毛传知其不妥,故释“苗”为“嘉谷”。孔氏正义云:“黍、麦指谷实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茎叶,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谷’,谓谷实也。谷生于苗,故言苗以韵句。”这个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今之学者认为大老鼠喻贪婪的剥削者,其形酷肖,故信而不疑。但对老鼠不食苗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则鲜有人思考。其实,只要结合早期记载分析,就会发现,“硕鼠”指的并非大老鼠,而是在《诗经》时代被认作农业四大害虫之一的“蟊”,即蝼蛄。《易·晋》:“晋如鼫鼠。”《释文》引《神农本草经》说:“蝼蛄,一名鼫鼠。”晋崔豹《古今注》云:“蝼蛄,一名天蝼,一名,一名硕鼠。”《尔雅·释虫》云:“,天蝼。”邢疏:“,一名天蝼,一名硕鼠,即今之蝼蛄也。”《尔雅翼》云:“蝼,小虫。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谓之土狗,一名蝼蛄,一名硕鼠。”蝼蛄属直翅类昆虫。体圆长,黄褐色,长寸余。白天多在土中,晚上出来活动。常在土中啮食植物幼苗的根,对农作物危害极大。《诗经》中又叫“蟊”,如《大雅·桑柔》云:“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小雅·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毛传云:“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陆玑《诗疏》云:“蟊,蝼蛄,食苗根为人害。”“无害我田稚”,田稚即幼苗,此与《硕鼠》“无食我苗”意正相同。
这些盲点的形成,主要是由秦汉经师从经义的角度考虑而导致的。如“白露为霜”,毛传说:“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岁事成。兴国家待礼然后兴。”这是把“霜”比作了周礼,蒹葭遇霜才能成熟,比喻国待用周礼才能得治。而“伊人”,则是指深明周礼之贤人,是人所尽知的,故用“所谓”,以告大家其所在之地。秦汉经师的这种导引,在语言层面上符合常识,故而为后人所沿袭,遂使阐释失其真而不觉。
二、《诗经》训诂学的误区
所谓“误区”,是指研究指向与事物本质相背离的区域。这主要有以下两类情况。
第一类,秦汉经师本已解决的问题,后人因生活环境与观念形态的变化,不能理解先儒之言,而在归纳、分析时发现其不合于今之逻辑,于是重新寻找解释的路径,遂而群体性地进入理解的误区。如《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毛传云:“采采,事采之也。”陈奂解释说:“‘采采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已也。”后汉高诱注《淮南子·俶真训》引《卷耳》诗云:“《诗·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满易盈之器。”高诱学《鲁诗》,此直以“采采”为动作,是《鲁诗》以“采采”为采摘。《文选》刘孝标《辨命论》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采采而不已”,是《韩诗》也以“采采”为采摘。由此可见训“采采”为采摘不已,汉以前无异说。又陆机《拟渉江采芙蓉》:“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南朝陶功曹《采菱曲》:“采采讵盈匊,还望空延伫。”“采采”皆为采摘不已之意。这个解释本来是可以通的,汉宋经师对此皆不曾怀疑。清代学者开始大量用归纳法搞训诂,发现了问题。朱彬《经传考证》云:“彬谓《蒹葭》传:‘苍苍,盛也。’‘萋萋,犹苍苍。’‘采采,犹萋萋。’《蜉蝣》‘采采衣服’,传:‘采采,众多也。’是采采亦茂盛之貌。”马瑞辰用同样的方法否定了毛传之说,并云:“《芣苢》下句始云‘薄言采之’,不得以上言‘采采’为采取。此诗下言‘不盈顷筐’,则采取之意已见,亦不得以‘采采’为采取也。《芣苢》传:‘采采,非一辞也。’亦状其盛多之貌。”徐灏《通介堂经说》也对毛传之说提出怀疑。闻一多将《诗经》中的“采采”汇于一处,又根据《大东》“粲粲衣服”《韩诗》作“采采”之文,认为“采采犹粲粲”。今人又以为《诗经》中叠字多为形容词,无用为动词者,遂而以“采采”为形容卷耳茂盛之状,或以为是形容色彩鲜明之貌。以致今日出版的几部大型词典,如《辞源》 《中文大辞典》 《汉语大词典》等,皆在“采采”词条下删除了“事采之也”这一义项。如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朱彬、闻一多等人的考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为叠字作动词《诗经》中没有,甚至古籍中少见,这不符合事实,在《大雅·公刘》中就有“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这里的叠字全部是作动词用的。《古诗十九首》云:“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行行”也是作动词用的。说明这种构词方式,在古代是常见的。二是将《诗经》中关于“采采”者汇于一处,寻求一律。这表面上很“科学”,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诗经》中“采采”出现四次,毛传皆循文释义,表现了语言的灵动性。
再如《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毛传说:“五尺以上曰驹。”朱熹说:“驹,马之小者。”这本来是很清楚的,金文如《伯晨鼎》 《兮田盘》等,皆有“锡驹车”之文,说明以驹驾车,本为常事。今人也常叫少壮的马为“马驹”。刚刚开始驾车的马,一般都是马驹,“马驹”是别于“老马”的名号。但清儒在归纳时却发现了问题,对此展开了考证,段玉裁、焦循、胡承珙、陈奂等《诗》学大家,都以为“驹”为“骄”之误。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骄”字下云:“(《汉广》) 传云:‘六尺以上曰马,五尺以上为驹。’此‘驹’字,《释文》不为音。《陈风》‘乘我乘驹’,传曰:‘大夫乘驹。’笺云:‘马六尺以下曰驹。’此‘驹’字,《释文》作‘骄’,引沈重云:‘或作驹,后人改之。 《皇皇者华》 篇内同。’《小雅》‘我马维驹’,《释文》云:‘本亦作骄。’据《陈风》 《小雅》,则知《周南》本亦作‘骄’也。盖六尺以下,五尺以上谓之‘骄’,与‘驹’义迥别。”焦、胡等诸家考证略同。孙经世《惕斋经说》“言秣其驹、乘我乘驹、我马维驹、皎皎白驹”条,则用大段文字考证“驹”字,以为“‘驹’为‘骄’之误”,其证据“一征之《说文》”,“一征之传、笺”,“一征之《释文》”。其结论是:“‘驹’之见《诗》凡五,唯《角弓》‘老马反为驹’,系是‘驹’本字。他如《汉广》‘言秣其驹’,《株林》‘乘我乘驹’,《皇皇者华》‘我马维驹’,《白驹》‘皎皎白驹’,盖皆‘骄’字之误。”这里有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信“异说”而不信“正出”,即:不相信今本《毛诗》,却相信早已不传的版本和《说文》所引(《皇皇者华》“我马维驹”,《说文》引“驹”作“骄”),此可谓考据家好异之一病。二是通过归纳,单凭逻辑推导作断语,却忽略了诗歌语言的灵动性。此处的“驹”字与“蒌”字为韵,若变为“骄”,韵便不叶。尽管段玉裁等力辨“骄”可与“蒌”通韵,但一在侯部,一在宵部,毕竟不在一个韵部。
诸家对《召南·甘棠》“蔽芾”的解释,也是很典型的例子。《甘棠》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传说:“蔽芾,小貌。”郑笺说召公“止舍小棠之下”,是与毛同。“蔽芾”双声,犹“蔽蔽”“芾芾”。《说文》:“蔽蔽,小草也。”“芾”,《玉篇》作“巿”,云:“蔽巿,小貌。《说文》普活切,草木巿巿然,象形。”《我行其野》有“蔽芾其樗”,郑笺云:“樗之蔽芾始生,谓仲春之时。”陆德明《释文》云:“蔽芾,叶始生貌。”由此看来,此诗的“蔽芾”,是形容小枝甘棠生长状态的。对毛、郑以“蔽芾”为“小貌”的解释,唐以前不见异说。但从宋代起,人们开始怀疑。因为甘棠下是召伯断狱的地方,到树下是为了蔽风日,蔽风日只能选择大树,怎么会选择小树呢?这不合逻辑,于是宋之大儒欧阳修首起发难,他说:“毛、郑皆谓‘蔽芾,小貎’,‘茇,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烦劳人,故舍于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则非小树也。据诗意,乃召伯死后,思其人,爱其树,而不忍伐。则作诗时益非小树矣。毛、郑谓‘蔽芾’为小者,失诗义矣。蔽,能蔽风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树之茂盛者也。”其后则新说时出,或承欧氏说以“蔽芾”为茂盛,如朱熹说“蔽芾,盛貌”;或以为“阴貌”,如王质;或以为“阴翳茂盛”,如严粲;或以为“乃蔽日干霄之大木”,如胡文英;或以“蔽”为遮,“芾”如蔽膝,言“设之防为藩垣状,用遮树身之下半,正如人有蔽膝然耳”,如罗典。清儒姚炳、朱彬、洪颐煊、牟庭、李富孙、马瑞辰等,皆旁征博引,以证蔽芾为言树荫之大,是茂盛义,似乎已成定论,为今之大多数《诗经》注本所信从。但是,这样理解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蔽芾”本有微小之训。如《尔雅·释诂》云:“蔽,微也。”《释言》云:“芾,小也。”则不见有训大者。第二,毛、郑并非不明白树大荫广更益于休憩,而以“小貌”“小棠”释诗,此在今人看来为常识性错误者,必然是先师传说如此。而且三家《诗》不见有异说,更见其渊源有自。宋后学者,失去传说依据,纯靠逻辑推导,其说恐难完全凭信。第三,甘棠树本为小乔木,枝干短小,一般其大者也高不过十米左右,很难长成像大槐、大杨那样的参天大树,像胡文英所说的“蔽日干霄”的甘棠,几乎见不到(长数百年者除外)。“小貌”“小棠”正说明其非大树种。后儒不知甘棠为何物,仅从书本到书本,脱离实际,遂以毛、郑为非,实属唐突。
最为典型的是对《秦风·蒹葭》“遡洄”“遡游”两句的阐释。因此篇为中学、大学教材中的名篇,故关注的人就很多。“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毛传说“逆流而上曰遡洄”,“顺流而涉曰遡游”。《尔雅·释水》释“遡洄”与毛传同,释“遡游”为“顺流而下曰遡游”,“涉”作“下”。“遡”是向、朝着的意思,即如《说文》所说:“,向也。”《桑柔》“如彼遡风”笺:“遡,乡(向)。”“洄”为“回”之孳乳字,高鸿缙《中国字例》解“回”字说:“此象渊水回旋之形,故托以寄回旋之意。动词。后引伸为回归。久而成习,而渊水回旋,乃造洄字以还其原。”此说甚是。《说文》:“渊,回水也。”孔门颜回,字子渊,即可见“回”与“渊”的原始关系。渊多为泉源所在,古文字“泉”或书作“”,象水从泉中流出成川之形。“渊”或书作“”,象泉水积为水潭之形,故“渊泉”“渊源”每连言。《慧琳音义》引《说文》说:“渊,深泉也。”《文选》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虽渊流遂往”,张铣注:“渊流,本源也。”《楚辞·招魂》言“投之深渊”,《晋书·顾恺之传》言“投鱼深泉”,《管子·禁藏》言“深原之下”,所言显然是同物,而用字或“渊”或“原”(“原”即“源”),证明其意义相联系。“游”即水流,《汉书·项羽传》注:“游即流也。”《匈奴传》注:“游犹流也。”“遡洄”即是“遡源”,向着水源方向即是逆水而上,故毛传、《尔雅》皆言“逆流而上曰遡洄”。向着水流的方向即是“遡游”,故《尔雅》说“顺流而下曰遡游”。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汉唐经师对此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而后世学者们却纷纷起疑了。如牟庭《诗切》说:“洄当读若涠。《说文》曰:‘涠,不流浊也。’”以为“洄”是不流之水,“游”是流水。俞樾《群经平议》说:“溯(遡),《说文》作,《水部》:‘,逆流而上曰洄。,向也,水欲下违之而上也。’是‘溯’字止可为逆流之名,其字本从‘’得声。,不顺也。若使逆流、顺流同谓之溯,义不可通。虽有《尔雅》明文,未敢信也。”俞樾首先是把“溯”(遡) 字之义固定在“逆流”上,然后从逻辑上推出,“遡”只可用于“逆流”,不可施于“顺流”,以此作为基点,他提出了新说:“两句之异全在‘洄’字、‘游’字。《尔雅·释水》曰:‘湀辟流川,过辨回川。’郭璞解上句曰‘通流’,解下句曰‘旋流’。此经‘洄’字即彼‘回’字,‘游’字即彼‘流’字。‘回’乃‘洄’之省,‘游’与‘流’古字通……传义虽亦本《尔雅》,然于字义不合,即非经义可知矣。”中井积德《古诗逢源》也说:“洄,回水也……盖缘旁支迂洄之水而往焉,则其水道阻长,不能达矣。”朝鲜尹廷琦《诗经讲义续集》说:“洄有回旋之意。溯而从之,则水欲流下而违之逆上,故不得如矢直往,必回旋而上,所以谓溯洄也。”陈奂、王先谦等又疑《尔雅》“顺流而下”的“下”字当作“上”字,意其是指沿流水上行。闻一多、余冠英等以为“洄”指折曲的水流,“游”指直流的水道。但在古籍中却找不到“游”训“直流”的证据。吴小如《读书丛札·三百篇臆札》也如此认为。这些论说共同进入了一个误区,在认定“遡”只是“逆流”之意的前提下,把“遡洄”“遡游”认作了是在两个不同河段的行为,而忽略了诗人是在一个地方上下徘徊的。因为“伊人”就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水洲,诗人想走近她,只能在水洲附近的河岸来回周旋,不可能离开此地一会儿沿直流、一会儿沿曲流地跑。同时也低估了毛、郑大儒的知识水平,以为其误解了“遡”字之意,却不知“遡”有向、朝着的意思。
第二类是由早期训释误导所致的误区,即研究者认为秦汉经师的训释存在疑点,或不周全,但却不能摆脱其影响,而是沿着其所误导的方向寻找答案。如《周南·葛覃》“薄汙我私”的“汙”字,毛传说:“汙,烦也。”郑笺又解释“烦”字说:“烦撋之用功深。”但“汙”和“烦撋”如何能发生关系呢?于是朱熹补充说:“汙,烦撋之以去其汙,犹治乱而曰乱也。”也就是说,“汙”之训去汙,是反义为训。其后学者便沿着“烦撋”与反训两条思路进行考证。如陈启源以为“烦”字当作加手旁的“扌烦”,“撋”本作“擩”字,表示用手反复搓揉。马瑞辰说:“《左氏·昭元年传》‘处不避汙’,杜注:‘汙,劳事。’‘劳’与‘烦’同义。”丁惟汾《诗毛氏传解故》说:“‘烦’为‘烦辱’,即首章传所云‘女工之事烦辱者’。‘烦辱’为连绵字,‘辱’亦‘烦’也。‘辱’为溽秽,‘汙’为污垢。传故释‘汙’为‘烦’。《左传·昭公元年》传:‘不辟汙。’杜云:‘汙,劳事。’‘劳’‘辱’双声通用,‘劳事’即‘辱事’,亦以‘汙’训烦辱也。衣服溽垢为‘汙’,除衣服溽垢亦谓之‘汙’。”闻一多《诗经新义》在“汙”字一条中,又认为“汙、澣声近对转,汙亦澣也”,并旁征博引以证“汙”即“澣”,而以为前人关于“汙”“澣”有深浅之别者为“蛇足”。高亨《诗经今注》在“附录”中也专为“薄汙我私”出了一条考证,认为“汙”与“沤”是一音之转,是浸在水里之意。学者们都力图破解“汙”之本义,却又群体性地离开了事物本身,只在“汙”的概念上做文章,忽略了古人浣洗衣服的实践。古时没有肥皂之类清洁材料,为了清洗衣服上的油垢,便须用汙水即草木灰水之类浸泡清洗。《礼记·内则》说:“冠带垢,和灰请漱;衣裳垢,和灰请澣。”“和灰”即是指用灰水浸泡,诗所谓的“汙”便是就此种洗涤方法而言,可惜这一记载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再如《大雅·生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毛传:“达,生也。”郑笺:“达,羊子也……生如达之生,言易也。”孔颖达疏毛意说:“‘达生’者,言其生易,如达羊之生,但传文略耳,非训达为生也。”毛、郑之说有两个意思。一是以“达”为“羍”的借字,《说文》云:“羍,小羊也。从羊,大声。”故郑玄说:“达,羊子也。”二是以“如达”形容生子之易,认为羊羔生产滑利,故以为喻,即郑玄所云“言易也”。因毛说简略,而后人又务得其详,故而便顺着这两个思路,开始了不同的研究。
顺着“达为羊羔”思路而下者,如清牛运震《诗志》说:“‘先生如达’,古人语子如此,今人定以为嫌。先生,犹言初生也,不作首生解。如达,言形状之怪如羊也,如古神圣鸟喙龙集之异,如达奇矣。生之易又奇,此所以欲弃之也。”清胡文英《诗经逢原》也说:“先生,初生时也。羍,小羊也。后稷初生,头方如小羊也。”又引其同乡蒋涑畻《楚辞余论》曰:“昔人以达为羊子,稷之为达,岂生时形与之类,故恶而弃之欤?”顾镇在“达为羊子”这一思路下,又得出了后稷“连胞衣生”的结论,其《虞东学诗》云:“反复经文,至‘后稷呱矣’,乃如有所得。盖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骤失所依,故堕地即啼。惟羊连胞而下,其产独易。诗以‘如达’为比,恐稷生未出胎,故无坼副灾害之事,而啼声亦不闻也。坼、副谓破裂其胎,灾害谓难产,皆主稷言,非言其母。姜嫄惊疑而弃之,辗转移徙,屡见异征,至于鸟去乃呱,则胎破而声载于路矣。玩两句叠用‘矣’字,知前此未尝呱也。”清代治《诗》之家持此说者甚多,如李允升、姜炳章、陶元淳、马瑞辰、魏源等,皆有类似之说。而左宝森更以此为重大发现惊喜不已,其《说经呓语》“生民说”条曰:“因复取《生民》诗细读数遍,忽跃然起曰:得之矣!‘不坼不副’非言母之身不坼副,乃言子之胞不坼副也。‘无灾无害’,言易也。其曰‘如达’者,言胞之形也。”
顺“生之易”思路而下者,如段玉裁《诗经小学》说:“按:郑笺易字为‘羍’,似太媟矣,本后稷之诗,不宜若是。传云:‘达,生也。’以《车攻》传‘达,履’之义求之,盖是‘达,达生也’。‘达’‘沓’字古通用。姜原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易,故足其义。”陈奂《诗毛氏传疏》云:“传训‘达’为‘生’,说者皆不得其解。《载芟》‘驿驿其达’,言苗之生驿驿然也。传:‘达,射也。’射犹出也,训‘达’为‘射’,与此训‘达’为‘生’,虽随文立训,而意义实同,先生如生而生也,此即如破而破、如濡而濡之例。‘如’当作‘而’字解。”陈玉树《毛诗异文笺》说:“蒙谓‘如’读为‘而’,传‘生’字乃生活之生。妇人首产多难,有甫生而不活者,‘先生而达’,言胎之不也。‘达’即‘活’之假借。”林义光说:“‘如’读为‘而’,‘达’读为‘泰’,泰之言脱也……《说文》:‘泰,滑也。’先生而达,犹言先生而脱,谓怀孕未至,当生之时而遽滑脱生子也。”
其实跳出毛、郑所设定的意义区域,从民俗、神话、方言等多个角度进行思考,问题便会得到解决。在黄土高原上一些地方,如晋南,孩子的小名,经常有个“达”字。如孩子叫“建平”,他的小名就有可能被叫作“平达”;名字叫“国庆”,小名就有可能叫“庆达”。这个“达”到底是什么意思,老人们从没有解释过,但有时也用“亲圪塔”“亲蛋子”称呼自己的孩子。这似乎透露了一点信息。“达”“塔”“蛋”乃是一声之转,这个“达”乃“蛋”之音转。像山西寿阳人卖鸡蛋,其吆喝声则是“卖鸡达”。关于肉蛋生人的故事,在许多民族中都有,如《博物志》中关于徐偃王出生的故事,流传于朝鲜族中的关于朱蒙出生的故事,黎族中流传的其始祖母出生的故事等,相传他们都是从肉蛋中生出来的。宝鸡、武功一带的民间传说中,姜嫄生下的就是个肉球,后稷就是从肉球里出来的,这更可以证明“达”为“蛋”之音转了。
总之,以上盲点与误区,是近三百年《诗经》训诂学存在的最大问题。盲点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是只看到了语言层面的合理性,而忽略了事物自身的逻辑性。无论是“殷商”“所谓”“谁谓”“何以”之类,还是“为霜”“胥原”之属,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在语言的层面没有任何可疑点,问题出在常规训释与事物自身的矛盾上。误区则相反,由于过于相信逻辑推导的力量,而忽略了诗歌语言的灵动性和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像“采采”“蔽芾”“遡游”“汙私”之类,用今人的逻辑推导,毛、郑的解释几乎是违犯常识的,然而当回到事物本身的时候,便会发现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出了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盲点还是误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脱离开了事物本身,单从语言和概念的层面上考虑问题,研究者关注语言的逻辑关系和概念的确定性远过于关注事物本身,故盲点和误区便出现在语言与概念设定的陷阱之中。要“扫盲”和“脱误”,就必须跳出语言与概念设定的陷阱,从事物本身出发,看到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从而获取真实的信息。
③ 于鬯:《香草校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7页。
⑥⑧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802页,第806页。
⑦⑨ 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4页,第103页。
⑩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6页。
⑪ 《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54页。
⑫ 陈寿祺撰,陈乔枞述:《三家诗遗说考·韩诗遗说考》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页。
⑬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0页。
⑯ 参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3页。
⑲ 龟井昱:《毛诗考》卷一一,《龟井南冥·昭阳全集》卷二,(日本) 苇书房1978年版,第150页。
⑳ 钱天锡:《诗牗》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6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79页。
㉑ 陈组绶:《诗经副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1册,第131页。
㉒ 萧泰芳、章儒、马麦贞、白平:《〈古代汉语〉注释商榷》,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㉓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9页。
㉔ 王肃、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75页。
㉗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885页。
㉛ 《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76页。
㉝ 安井衡:《毛诗辑疏》卷二,《崇文丛书》第2辑第46册,(日本) 崇文院1933年版,第9页。
㉟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册,第7页。
㊲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0页。
㊳㊷㊹ 杜预集解,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905页,第1949页,第2052页。
㊵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7页。
㊻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郭沫若全集》第9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㊾ 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一,《丛书集成新编》第55册,(台湾)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