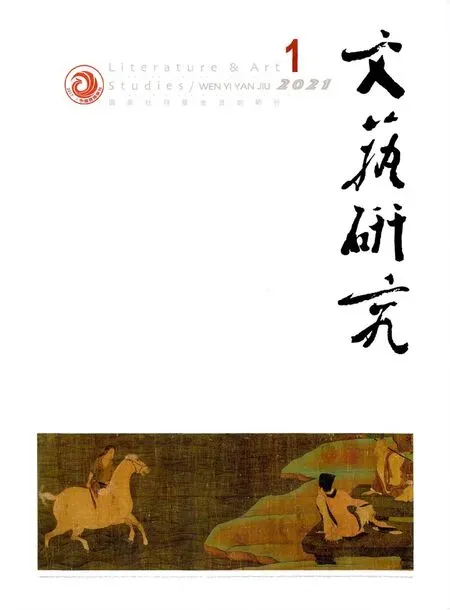论中国中古美学的“天人之际”(上)
2021-11-26刘成纪
刘成纪
做历史研究,首先面对的往往是历史分期问题,美学史研究也不例外。目前,我国的美学史研究大致采用两种分期法:一是按照王朝的兴废为历史排出顺序,如先秦美学、两汉美学、魏晋美学等,具有编年体性质;二是为整个历史理出一个有序的逻辑进程,使其显现出规律性,如将其设定为发端、展开、繁荣、总结等环节。比较言之,前者更专注于每一时代的美学创造,重点在史实;后者更重视历史的宏大叙事,重点在史观。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大抵依靠这种局部历史和整体历史之间的相互印证和相互发明。这也是人们一般所讲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法在美学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通观我国四十余年来的美学通史研究,这种“两结合”分期法的缺点日益显露。其中,以朝代更迭为基础的历史分期固然使历史失之零散,但由发端、展开、繁荣、总结诸环节确立的宏观历史框架,也极易导致逻辑对历史的强制,使历史进展看似自洽,实则与其本来面目相距甚远。在这种背景下,似乎有必要找到一种既避免王朝史的破碎、又能适当遏制人们逻辑冲动的分期方式。从中国历史看,这种更趋中性和简易的分期法是存在的,即上古、中古、近古的三分法,或者简称为“三古”法。如《易传·系辞下》讲:“《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①这里使用的“中古”,意味着上古和近古。《韩非子·五蠹》以“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近古之世”②区分过往历史,则使这一分期模式完型化。
当然,不同时代面对的历史长度不同,相应“三古”所涵盖的历史区间也不同。近年来,作为这种分期法在现代的延续,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学界引起广泛回应。在他看来,“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③。按照这一论述,先秦显然属于上古或上世,汉唐属于中古或中世,宋代以降则是近古或近世。至于在唐宋之间做出切分的依据,内藤湖南主要立足于政治,认为汉唐(尤其六朝至唐中叶) 是贵族政治主导的时代,宋以后则是君主独裁的时代。但就哲学和美学这类更具精神性的学科来讲,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上古即先秦时代,最具奠基性的命题是天人关系问题;汉唐时代,这一命题被用更趋神性和感性的方式表述了出来;宋代以后,以宋明理学为标志,时代精神变得理智清明,心物作为天人关系的变种,重要性被凸显。换言之,天人关系问题,一方面保持了对中国历史的纵贯,另一方面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差异化表述。本文致力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天人关系这一视野内,看中国汉唐美学如何确立并展开自身。
一、“天人合一”与“天人之际”
现代以来,治中国哲学和美学思想史者,几乎无一不碰触到天人关系问题,并以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二分相区别。如1990年,钱穆在其带有“学术遗嘱”性质的文章中讲:“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④以相关论述为背景,这一命题不断向美学延伸,如有论者认为:“在认知意义上,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形上学说;在伦理的意义上,它反映了古人善待自然的积极态度……而在审美意义上,它又体现了人们以人情看物态、以物态度人情的思维方式。”⑤这是将中国美学视为天人合一的分有形式。更多论者则是直接将天人合一作为美学命题来对待,认为它的理论起点、过程和目标无一不是审美化的。但是,像其他学科一样,美学也有其理论边界,逾越这一边界,要么导致对天人合一命题阐释的狭隘化,要么导致美学学科的泛化。比较言之,一般哲学和作为其分支的美学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分野:前者抽象,后者具象;前者普遍,后者感性。人类的审美活动永远离不开看和听,美学的问题必须诉诸形象,而哲学则并非这样。或者说,感性是对美学作为人类知识的最基本规定,美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是研究其感性呈现的侧面。
以此为背景看中国社会早期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人们一般认为,有汉一代,受战国稷下学派和阴阳家的影响,中国哲学逐步从传统的形而上学向宇宙论下降,原本观念性的天人问题变得具象化了。比如对于人,先秦哲学更注重对人性的探讨,到汉代则位移为身体问题;对于天,先秦诸子更注重天的形上品格,汉代则一方面将它神学化,另一方面用阴阳、四时、五行、八风等自然元素将其塞满,显现出空间化的秩序性特征。关于这一变化,徐复观曾讲:“汉人不长于抽象思维,这是思想上的一种堕退。”⑥许多哲学史家谈及汉代,也大多因此对其成就评价不高。但是,一种反向的价值也正由此生发出来,这就是审美。也就是说,天与人从抽象向具体、从观念形态向经验形态的转变,一方面使其成为更具审美价值的感性学,另一方面也是以“三古”分期法在先秦和两汉之间做出切割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学界对汉代美学中身体问题以及空间秩序审美化问题的讨论,正是以这一时代对天、人的认识向感性全面“堕退”作为前提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哲学和美学史上,真正将天人组合为一个统一概念,并大谈两者的“合一”问题,也是起于汉代。此前,先秦文献中虽然弥漫着天人合一思想,但它只是一种思想表达,而不是自觉的理论命题。唯一的例外是,荀子曾以“天人”并举谈二者的关系,但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即他是主张天人二分的。如其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⑦就此而言,说汉代才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真正自觉的时代,并不过分。如董仲舒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⑧“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⑨尤其重要的是,董仲舒论天人合一,并未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侧重其感性的构成。比如他首先将人身体化,然后在人天之间寻求匹配,即“人之身,首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人副天数》)⑩,这其实是将人体视为天地的缩影,将天地视为人体的展开,两者既是感性的、构成性的,又形成同构关系。在情感层面,他讲:“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欲出也。”(《如天之为》)⑪这样,人的情感变化与自然天道的运动节律之间也形成了一体关系。据此可以看到,在董仲舒的天人观念中,人不仅在身体结构和情感状态上被赋予了天的意义,天也相应被赋予了人的意义,这种感性化和构成性的天人合一被他表述为天人相副。以此为背景,当天具有了人的身体结构和情感,它也必然是生命性的,必然能够与人产生共感和互动,这被董仲舒称为“天人感应”。要而言之,他讲的天人合一,并不仅是人抽象的自然态度或观念,而是包含了天人相副、天人相感等诸多环节。于此,看似各是其是、各安其分的天、地、人,就借助感性化或审美化的相互勾连,成为两相匹配的互动形式,并进而显现出完美的秩序感。
但对于汉代美学,天人同构和天人共感只是天人合一命题向美生成的初步。也就是说,董仲舒借助天人同构和共感形成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感性体认,只是阐明了感性的现实或日常,而审美则总是更关注日常世界之上的超验维度,即杜夫海纳式的“超感性”或“灿烂的感性”⑫。同时,在天人之间,如果双方仅仅以具身化的感性被组合为一体,这固然有助于克服世界的分裂,但这种组合毕竟是机械的。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并没停滞于两者同构、共感的表层,而是更重视两者在互动之中向超验维度的生成。这种被生成的具有超验性质的现象被称为“祥瑞”和“灾异”。其中的祥瑞,是由天人交感生成的吉祥形象,如“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王道》)⑬,它是正常世界之上的超常。相反,灾异则是正常世界之外的反常,如“日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王道》)⑭,等等。按照这一思路,如果天人同构、共感构成了世界的常态或一般规律,那么超常的祥瑞和反常的灾异则是天道对人事的两极性反应。其中,祥瑞因为浸染了上天神性的光辉而让人追慕,具有灵韵或灵氛的性质;灾异给人传达的则是带有陌生效应的惊惧感,类似于现代美学中所讲的怪诞。
当然,在汉代,董仲舒对传统天人关系的发展乃至改造,更多是基于政治的理由。此前,孔、孟、荀及《大学》等也谈天人,更多则是基于士人的个体立场。但到汉代,儒家由传统士人的修身之学一变而化为国家哲学,它就无法使其理论继续建立在个体的道德自觉基础之上,而必须确立新的权力主体,以对人间诸多的“道德不自觉”形成外在强制和威慑。那么,在人的视野内,什么东西具有最强大的威慑力?中国传统的回答是天。就此来讲,董仲舒在汉代将天实体化,并强化其作为神意的权力主体的性质,是儒家哲学对其社会角色变化的必然回应。这是一种为先秦儒家“补天”的工作,也是儒家从追求内在超越向政治化的外在强制的重要转换。从美学角度看这种转换,它舍弃了儒家传统的心性美学,而造就出一种以天命规约人事的政治美学或制度美学。
进而言之,在汉代儒家的视野内,天命对人事的规约是通过祥瑞灾异的显现来完成的。按《礼记·中庸》:“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⑮这里的祯祥和妖孽或祥瑞和灾异,被视为国运的预兆,而国家的兴亡又被直接关涉于帝王的节制与泰侈、官僚体系的勤勉与怠惰、国风的雅正与淫邪。由此,相关预兆就成了上天评估国家现状并预测未来的信号。其中,祥瑞代表奖励和肯定,灾异代表警告和惩罚。有汉一代,史志和士人著述对这类预兆的记载不计其数。比如,帝王年号的更改往往与一次重要的祥瑞出现有关,如汉武帝的元鼎,汉昭帝的元凤,汉宣帝的神爵、五凤、甘露、黄龙,等等。而两汉帝王层出不穷的“罪己诏”,则大抵以某次被视为上天谴告的灾异作为诱因。这样,作为超感性现象的祥瑞和灾异,就既有大自然或神光灵耀、或妖祟麇集的景观性,又以美丑和吉凶的双向夹持对现实构成强制性的约束和重塑。在一种政治美学的视野下,帝王和官僚体系治世的任务,似乎就是实现祥瑞的递增和灾异的递减,并最终使人间普遍祥瑞化。同时,政治实践的过程被表象为化灾异为祥瑞、即化丑为美的过程,它的理想世界则是按照祥瑞(即美)的尺度建造的世界。简言之,这是一种在天人之间被“灿烂的感性”建构的政治,也可以直接称为“景观政治”。
可以认为,祥瑞与灾异是汉代思想者将天人合一推向极致的美学表达,它既有超越性的审美表现,又对社会现实形成强劲的建构作用。甚至可以说,不理解祥瑞和灾异对汉代人精神取向的指引和对社会的反向塑造,就无法真正理解汉代美学。如上文所言,关于汉代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将其大而化之地称为“天人合一”,也可以更直接地称之为“天人相副”和“天人感应”,但天人合一更趋于哲学,天人相副带有明显的生物主义倾向,天人感应更趋于神学,均无法充分切中祥瑞和灾异在感性与超感性之间游移的特征。那么,更具针对性的概念是什么?从汉代文献看,应该是“天人之际”。如董仲舒讲:“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汉书·董仲舒传》)⑯司马相如讲:“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⑰韩婴讲:“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韩诗外传》卷七)⑱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⑲也就是说,关于天人关系,“天人之际”是一个被汉代思想者更常使用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天人之际”?按《尔雅》:“际、接、翜,捷也。”这是在以“捷”释“际”,那么什么是“捷”?郭璞注云:“捷谓相接续也。”宋邢昺疏:“际者相会之捷也。”⑳按照这一释义链条,“际”是指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之间的接合与连续,同时强调两者相遇的偶成感和瞬间性。这意味着“际”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它既不是此事物也不是彼事物,而是存在于事物的彼此之间,是其两相交接的动态化的中间场域。又按《说文》:“际,壁会也。”段玉裁注:“两墙相合之缝也。引申之,凡两合皆曰际。际取壁之两合,犹间取门之两合也。”㉑这一释义与《尔雅》大体一致,均不是指事物本身,而是指事物之间。就天人之际而言,显然也就意味着天人之间有待弥合的缝隙,是需要建立关联的中间态。董仲舒又将天人之际称为“天人相与之际”,这里的“相与”正是强调了两者的相遇、相应和相互给予。而祥瑞和灾异则正是由两者交会生成并显现的形象。
天与人,在物理意义上,原本风马牛不相及,那么两者为什么会相交相会,并显现形象?这显然和中国古代的天人观念以及相应被置入的价值有关。按照汉代的元气自然论,无论是人体、物化的自然界还是苍莽之天,均以气为其元质。气进而分阴阳,双方相激相荡,相交相合,然后幻化出亦虚亦实、变动不居的形象,并向人间传递信息。汉代思想者将其称为“阴阳消息”。如刘向《说苑·辨物》:“夫天地有德合,则生气有精矣;阴阳消息,则变化有时矣。”㉒在中国思想史中,人们一般认为,这种元气自然观念起于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家,到汉代则形成了覆盖性影响。其中儒家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这种自然理论注入了人间道德伦理的内涵,使其与人事活动的善恶交相辉映。如董仲舒讲:“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灾害起。”(《天地阴阳》)㉓这是把“万物之美”视为从世治、民和、志平、气正到天地精气不断生成并上升的环节,而自然灾害则被视为由世乱、民乖、志僻、气逆向阴阳不调的逐步引发。比较言之,如果万物之美和自然灾害仍然是人间性的,那么一旦“世治”的祥和性和“世乱”的摧毁性达到某种极致,它们也就必然会以更强大的势能,将顺、逆二气推向天人相与之际,从而化生或召唤出祥瑞和灾异。如董仲舒所言:“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渊也;致黄龙凤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天地之行》)㉔换言之,祥瑞和灾异是天人关系的强化象征,是贯通天人的气向象的两极化生成。关于这种建立在元气自然论基础上的天人观念以及它的形象的两极性显现,西汉匡衡曾在向汉元帝上的一道奏疏中讲:“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汉书·匡衡传》)㉕这正是将自然界的精气和妖气与人间的善恶相勾连,并进而将超现实的天人之际作为两者分别向美丑两极形象显现的空域。
从以上分析可见,天人之际为汉代美学开出了一个游移于经验与超验世界之间的独特空间。在这一空间之内,气徘徊在有无之间的非确定性,使祥瑞既真实又虚幻,使灾异既基于实然灾难又引发意义,进而也使这一天人相接的中间地带很难被用一个固定的美学词汇来形容和界定。它既不是充分的天也不是充分的人,既是象征又不是充分的象征,既感性又超越了常规的感性。对此,我们只能说它是由天人互动化生出的新形象,是带有灵异性质的自然奇观。它的特征是暧昧,它的价值在于暗示。它类似于本雅明的“灵韵”,也类似于格尔诺特·伯梅的“气氛”。但无论如何,它为理解汉代美学提供了一个独特视界,同时也将汉代儒家建基于天人同构、生成于天人相感的美学之思推向了极致。
二、“天人之际”的美学构成
汉代儒学,是被阴阳五行观念重建的儒学。后世儒家,尤其是宋明以降以心性为本的新儒家,往往认为它背离了孔孟的宗旨,因而不愿将其纳入正统儒学的范围。现代以来,西方科学观念的传入更强化了这一态度,如劳思光讲:“秦汉之际,古学既渐失传,思想之混乱尤甚。南方道家之形上旨趣、燕齐五行迂怪之说,甚至苗蛮神话、原始信仰等等,皆渗入儒学。以致两汉期间,支配儒生思想者,非孔孟心性之义,而为混合各种玄虚荒诞因素之宇宙论。等而下之,更有谶纬妖言流行一时。”㉖
但是,宋明及现代新儒家的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首先,汉儒谈谶纬、谈祥瑞灾异,并没有脱离孔门“古学”的思想面貌。像孔子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㉗明显就是在讲祥瑞,《春秋》中谈及的大量自然异象,如“六退飞,过宋都”(《左传·僖公十六年》)㉘之类,则明显是指灾异。其次,汉儒谈祥瑞灾异,也没有溢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界限,而只是对其做了适度拓展。比如,我们不妨将天人关系分成天人之内、之际和之外三个层次,前者是现实界,后者是神鬼界,而作为祥瑞灾异存在空域的天人之际,至多是碰触了神鬼世界的边际线。或者说,它只是关注了神鬼世界传递的阴阳消息,并不是神鬼世界本身。就此而言,汉代儒学并没有背离先秦儒家的在世传统。它是以神鬼的显现代替了神鬼,并以此反向回护现实世界,与稍晚的道教和佛教舍身入于彼岸世界是存在重大差异的。至于劳思光指责汉儒“谶纬妖言流行一时”,则大抵是因为研究者缺乏对历史同情理解的态度。事实上,今人眼中的妖妄世界往往是古人眼中的真实世界。以科学时代的世界观评价历史,极易以后知后觉的所谓“明见”强历史所难。
汉代思想中的天人之论,以董仲舒为代表,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具有广泛共识的世界观念。武帝时代,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使谶纬化的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致“汉朝每有疑议,未尝不遣使者访问,以片言而折中焉”㉙。以此为背景,西汉言阴阳灾异者代不乏人,并渐成思想的洪流。如班固所言:“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㉚《汉书·五行志》记载了大量春秋至西汉末的灾异,其中大多配有上述诸人的解释文字。至王莽时代,自然性的祥瑞灾异开始向人文领域深化。如王莽为了给篡汉制造舆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汉书·王莽传》)㉛。其中的十二福应,即武功丹石、三能文马、铁契、石龟、虞符、文圭、玄印、茂陵石书、玄龙石、神井、大神石、铜符帛图,均不是前文所讲的自然现象,而是具有人文圣物的性质。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㉜,将其确定为治国理念,依托的大抵是这类人文性图谶。要而言之,汉人理解的天人之际绝不仅限于自然性的祥瑞灾异,而是将其深入到了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
据此,我们当能为汉代的祥瑞灾异建立一个基本的理解框架:首先,这种带有灵异性质的自然或人文现象,建基于汉儒神学化的宇宙观,它悬于天人之间,是将两者勾连为一个整体的中间环节;其次,天人之际为这个中间环节提供了存在场域,祥瑞和灾异是这个场域中两相对峙的力量;再次,祥瑞灾异有自然和人文之分,前者主要关乎自然灵异现象的空间展示,后者则通过对历史人文因素的纳入而更具预言性。要而言之,从一般性的天人关系到天人之际,再到祥瑞灾异,又到祥瑞灾异的自然、人文二分,基本构成了这一问题的延展序列。下面我将按照这一顺序,看它在汉代美学中如何呈现自身。
首先,在中国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对人命运的关切是一切哲学和美学问题的重心,但这类思考却往往从天开始,然后自上而下形成序列,汉代也不例外。按《史记·天官书》,愈是遥远的天象愈是与人形成宏大且崇高的相关性。如其中言:“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㉝但这种关联并不仅是物理性的两相匹配,而是将天象之变作为引发人间福祸的最大变数,即在两者之间,“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㉞。据此,司马迁列举了汉代一系列重大事件与天象的呼应关系,如:“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㉟在这段话中,由于“五星聚于东井”被与汉兴联系在一起,它无疑是有汉一代最重大的祥瑞㊱。其次,平城之围是汉朝建立之初遇到的最严重危机,所以“月晕参、毕七重”是最大的灾异。此后,诸吕、七国之乱,武帝时期的诸夷战争,无不关乎国运兴衰,所以也无不被认为有上天垂兆在先。就此而言,有汉一代的史志类著作中,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堪称开了相关祥瑞灾异之论的肇端,此后到《汉书》和《后汉书》的《天文志》,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基本线索。关于这一论题在汉代所涉天象的广度和丰富性,《汉书·天文志》讲:“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早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㊲
比较言之,在汉代,如果说基于天象的祥瑞灾异是关乎国运的重大事件,那么,基于地之阴阳、五行和列域的相关符应,则更多关乎国家的日常事务,两者在位阶上存在高低差异。但是,与天象相比,后者更为丰赡,这大体和人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关。按《宋书·符瑞志》等,两汉被视为祥瑞的动植物及相关自然现象不下32种。其中灵异性动物有麒麟、凤凰、神鸟、神雀、黄龙、赤龙、白龙、神马、白象、九尾狐、白鹿、白虎、白兔、白燕、白雀、白乌、白雉、黑雉、赤乌、三足乌、神鱼、黄鹄等,植物及相关物象有甘露、嘉禾、嘉麦、嘉瓜、木连理、芝草、华平、赤草、醴泉、芝英等。这类现象,既有人现实经验的基础,又在某种程度上以其灵异性与常态现实保持了距离,体现出与天文性祥瑞双向呼应并寻求衔接的特点。在灾异方面,史志中的相关记载主要见于《汉书》和《后汉书》的《五行志》,其中《汉书》记西汉宫殿宗庙火灾19起,其他涉及雨灾、旱灾、风灾、冬无冰、春夏雨雪、雨雹、地震、山崩、日食、陨石、蝗灾、螟灾、牛五足、牛背生足、马生角、人生角、男变女、双头婴,几乎凡是自然界中反常的现象皆有所录。《后汉书》的记载则更加繁多且细化,除上述灾异外,又增加了水变色、冬雷、山鸣、地陷、瘟疫、天投霓、白虹贯日。比较《汉书》和《后汉书》关于灾异的记载,后汉在数量上压倒了前汉,这大致有两点原因:一是东汉诸帝以图谶治国,进一步强化了史家对自然异象的敏感性和搜罗的广度;二是东汉王朝愈至后期愈陷入外戚、宦官和士人的权力缠斗,宣讲灾异成为士人对皇权形成威慑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量西汉时期作为祥瑞的自然现象被进行了灾异化的再解释。如汉安帝元初三年,“有瓜异本共生,八瓜同蒂”(《后汉书·五行》)㊳,这本是传统祥瑞中的嘉瓜,但在当时士人看来,则是新皇后不忠于皇室的预兆,属于草妖。另如安帝及桓、灵时代,多次出现五色大鸟引来众鸟聚集的奇观,这在西汉时期被视为重大祥瑞,甚至汉宣帝还为此改了年号,但到东汉后期,士人则认为“五色大鸟似凤者,多羽虫之孽”(《后汉书·五行》)㊴,将之视为自然神意对宦官、外戚乱政的警告和谴责。
在汉代,无论基于天文还是五行的祥瑞灾异,都是自然性的。但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文维度。关于自然性祥瑞与人文的关系,我们不妨举《汉书·五行志》中的一个案例做出阐明:“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㊵其中,倒地的柳树重新直立起来,是自然性的;柳叶被虫咬出文字,则指向了人文。以此为背景看汉代祥瑞灾异向人文的生成,可以认为,它首先奠基于当时儒家士人对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人文传统的历史回溯。像董仲舒言祥瑞灾异,其根据是《春秋》公羊学,刘向、刘歆、京房等人的相关言论也各有所本。这意味着对于儒家经典中神意维度的探究是对现实做出预言的起点,也意味着这一起点愈是被追溯到中国自然和文明史的起点处,便愈权威和神圣。按照这一思路,在汉代,作为中国文明起点的河图洛书被视为最具源发性的祥瑞。按《汉书·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㊶也就是说,河图首先是上天的给予,然后作为受命之符被伏羲领受,从而实现了天文向人文(八卦) 的转渡;《洛书》则是上天赐予夏禹的神示,属于对八卦的图说,然后被夏禹记述为文字性的《洪范》。由此,图像性的《河图》与文字性的《洛书》也就成了中国人文性祥瑞的总根源,而作为其摹本的《八卦》和《洪范》也相应被神圣化。
从以上分析看,汉人对祥瑞灾异的认识,主要在天空性的日月星辰、大地性的阴阳五行和人文性的历史纵深三个层面展开。它们共同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均显现为感性形象,而且均以异象形式保持了对人日常经验的超越,这是可以将它作为美学问题讨论的根本原因;二是,这类现象均存在于经验世界的边际地带,如日月星辰的高处、大地的远方和历史的纵深等,这种非现实性使其更多包蕴了人关于世界未知之域的想象;三是,任何由天人之际开显出的祥瑞灾异,均是对人在世命运的隐喻,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或有形式的意味,这使它的价值由形式观照直达隐喻和象征;四是,正如天人之际预示着人与超验世界的互动交会一样,作为祥瑞灾异存在境域的天文与人文也无法截然分开,而是在万物气化、古今一体中共同为其提供了情境化空域。关于这一空域的美学特质,安乐哲曾说:“中国传统一般总是将每一个情境的关系型式的独特性作为其基本前提,它从根本上说是美学传统。”㊷对于由天人之际引发的祥瑞灾异而言,它的美也正在于它的形象性、展示性和隐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情境化表达。
最后要提及的是,在当代学者关于汉代祥瑞灾异的美学研究中,人们一般将其称为谶纬美学,这是不准确也不全面的。按《说文》:“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雒所出书曰谶。”㊸《释名》:“纬,围也。反覆围绕以成经也。”㊹这是说“谶”是上古河图洛书或由此衍生的图箓上留下的隐语,“纬”是对六经文本的预言性引申。这意味着,谶纬作为美学概念,至多只言及了汉代祥瑞灾异中人文的侧面,而体量更为庞大的自然性祥瑞则无法被涵摄在内。比较言之,我们从天人之际论汉代的祥瑞灾异,一方面使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具象化、情境化,另一方面则使其摆脱了“谶纬美学”的人文限定,实现了描述区域的放大。换言之,它有天有地有人文,谶纬只能算作其中的组成部分。
三、“天人之际”在汉代的美学展开
建基于天人关系的祥瑞灾异之论,在汉代,最早可追溯到史传中关于高祖降生的神异性记述,此后代不乏例㊺。但是,它真正主导国家意识形态并普遍进入现实政治,仍要等到汉武帝时期。如武帝元光元年向大臣垂问天人之应:“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㊻同年又问:“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㊼元光五年复问:“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今何道而臻乎此?”㊽以上三问以及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回答,基本奠定了祥瑞灾异在此后两汉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为汉代政治如何以审美方式呈现提供了样本。简而言之,由天人之际绽出的祥瑞灾异,其真正的起点可以从“汉武帝之问”讲起。
从美学角度看汉代祥瑞灾异的价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从一般性的天人关系到天人之际,再到祥瑞灾异,实现了哲学问题向美学的转化。或者说,祥瑞灾异以“灿烂的感性”实现了对自然和人文现象审美价值的凸显。二是在祥瑞灾异中,无论正面的“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河洛出图书”,还是反面的“星辰孛、日月蚀、山陵崩”,均预示着自然和人文历史的神圣性和可敬畏性,这强化了汉代美学对自然美和人文历史之美的认识深度。三是在天人之际这一命题之下,祥瑞灾异是汉代的政治意象,也是文学艺术表现的重点对象。在政治层面,如上所言,西汉自武帝开始设立年号,年号的命名和变更往往与祥瑞有关,这就使国家的历史进程祥瑞化,也因此审美化、理想化了。至于这一观念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首先看王城建设。中国传统文明以农耕为本位,但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城市。围绕城市,汉代的重大创造之一就是将祥瑞灾异观念置入王城的选址和建构,使其显现天人之间的沟通和辉映,并进而“隆上都而观万国”(《两都赋》)㊾。西汉初年,刘邦选择关中作为龙兴之地,有政治和军事的现实考虑,但最终被符命化。如班固所讲:“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寤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两都赋》)这里的“寤东井之精”“协《河图》之灵”,均是讲选择关中建都具有天启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自汉初以降,对于这个王朝应该建都长安还是洛阳一直存在争论。时人一般将长安和秦王朝的暴虐相联系,而将洛阳关联于三代圣王,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则被视为接续了三代圣王传统。正是因此,东汉士人谈洛阳,往往更强调其历史感和人文性,并进而以祥瑞相夹持。如张衡讲洛阳,“土圭测景,不缩不盈”,“王鲔岫居,能鳖三趾。宓妃攸馆,神用挺纪。龙图授羲,龟书畀姒”(《二京赋》)。这些祥瑞几乎均关乎圣王故事和历史传说,从而使洛阳作为文教圣城的地位得到强化。
在建筑实践方面,汉代王城是天人观念的现实映射。如都城长安,整个空间布局模拟了南斗和北斗。最早建造的未央宫选址龙首山,则是将龙首视为新都的瑞应,即班固《两都赋》所言:“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至于王城结构则遵循了阴阳五行原则,即“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以此为背景,汉长安城具体建筑的命名基本上是祥瑞或祥瑞性的,如未央宫的凤凰殿、飞羽殿、白虎殿、神明殿,以及麒麟阁、天禄阁、青琐门、玄武阙、苍龙阙、朱鸟堂等。与此一致,汉代继承了战国至秦的高台建筑传统,并使其放大出新高度。如未央宫本建于龙首山顶,但其前殿又高出山基35丈。建章宫的凤阙、渐台高20余丈,其神明台及井干楼又高出50丈。这类宫阙楼观之所以追求高度,一方面有凸显皇家威势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借建筑实现天人交会、接祥纳瑞的意图。像建筑屋顶的瓦当上往往饰有四灵图案,高门大阙则镌以凤鸟,屋脊或飞檐部位饰以金雀,正是对相关意图的表达。在这种由高台建筑撑起的人居空间之内,祥瑞更是渗透于帝王和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目前仍多见到的汉代灯具和铜镜,其选择的动植物和天象品类,均有祥瑞的性质。再如近年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麟趾金、马蹄金,按汉武帝太始二年所下的《改铸黄金诏》,其造型和他当时获白麟、得天马等祥瑞有重大关系。要而言之,这种无所不在的祥瑞,使帝王原本常态化的生活闪耀出熠熠的光辉,也使王城成为将神意引入人间的圣域。
其次看汉代绘画。按照传统观念,中国正式的画史是从汉代开始的,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讲:“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乏贤。”尤为重要的是,鉴于《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画史著作,它对书画起源的认识,也证明了汉代思想者设定的“天人之际”这一空域重塑了中国画史。如其所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古先圣王受命应箓,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这段话首先在天人之际赋予了书画天赐的意义,然后以河图洛书(龟字、龙图) 向人间显现。如上文所言,河图洛书在汉代获得了它对中国人文历史的渊薮地位,这意味着张彦远对中国书画史起点的认识,不仅将人间画迹的起点定位于秦汉,而且对画史带有符瑞性质的溯源也沿袭了汉人的观点。张彦远前后,我国带有体系性质的画论或画史著作,大多会触及绘画起点的天人之际和祥瑞问题,如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郭熙、郭思《林泉高致》,《宣和画谱》,韩拙《山水纯全集》,这意味着汉代建基于天人之际或祥瑞的关于绘画起源的认识,对于中国绘画的历史叙事形成了源发性的建构意义。我们可以将这种叙事称为中国绘画的河图洛书模式。
正如河图洛书被视为天人交会的产物,这一交会也成为理解汉代绘画的重大枢纽所在。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所列的“古之秘画珍图”,大多是汉代的谶纬图像。以此为背景看汉代图像或画迹,对祥瑞灾异的表现堪称满天满地。首先看在天人之际中偏向天的一极,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彗星图》 《五星占》 《天象图》,西安交大西汉墓天象壁画,南阳麒麟岗汉墓天文画像石,陕西靖边汉墓天象图,均是将日月星辰云气与人化的宇宙观念相交合,然后按照“天垂象,见吉凶”的逻辑赋予其人间性。另外,“五星聚于东井”这一关乎汉代国运的重大祥瑞,也成为当时工艺或艺术品重要的表现对象。1995年,新疆尼雅古城出土汉代织锦,上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这显然是将上天祥瑞转化成了人间性的艺术表达。再看在天人之际中偏向人的一极,汉代与此相关的绘画主要涉及动植物和器物。如见于甘肃成县的《黾池五瑞图》,其中刻画的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甘露形象,是汉代文献中常常提及的基本祥瑞形式。此外,九尾狐、比目鱼、芝草也广泛见于汉画像砖石中。在器物方面,汉画最重要的表现对象是被视为神器的宝鼎,其代表性画作是广见于汉画像砖石中的同题画“泗水捞鼎图”。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汉代艺术中,虽然祥瑞表现无处不在,但仍有其专属区域。1999年,巫鸿在其《汉画读法》中,曾注意到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空间表现的“图像程序”问题。如其所言:“武梁祠画像据内容和装饰部位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祠堂内顶上所刻‘祥瑞’图像,其中心思想是‘天’以及儒家政治理想。二是左右山墙上的西王母、东王公形象,其中心思想是‘仙’或东汉人心目中的永恒境界。第三个,也是最大的部分是绘在三面墙上的44个带有榜题的人像和情节性图画,共同组成一部浩大的‘中国史’。”也就是说,在天界、仙界和人界之间,属于“天”的祥瑞,只是汉人整个有机宇宙空间的组成部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巫鸿将武梁祠内顶的祥瑞排在山墙的仙的形象前面,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祠堂三面墙壁上摹画的人间世界与屋顶的祥瑞世界更相靠近,也更有连续性,而左右山墙上的神仙世界则相对独立,也更辽远。换言之,在用历史叙事表征的人间世界和超验性的神仙世界之间,屋顶的祥瑞其实充当了中间环节。这种定位广泛存在于汉画的空间组织结构中,如马王堆一号墓帛画,大致可以分成地下、人间、仙界三个层面,带有祥瑞性质的二龙穿璧、白虎、凤鸟等图案,则存在于人间和仙界之间。同样,在汉代大量由条石叠层堆砌并横向展开的画像叙事中,祥瑞也无不处于地上的人间世界和天上仙界的中间区域。这意味着在汉人的空间观念中,祥瑞存在于人类的近空而非远空;它既非充分的天,也非充分的人,其功能在于将天与人之间的断裂区域用既理想又人间的图像塞满。这一区域就是天人之际,它不仅将原本互无关涉的天人两界连缀为一个整体,而且通过塞满这一区域,有效解决了早期中国人对虚无性空间的迷惘和恐惧。
最后看文学。像建筑和绘画一样,祥瑞符谶对汉代文学也具有弥漫性。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曾讲:“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其中提到的《白麟》 《赤雁》 《芝房》 《宝鼎》之歌,按《汉书·武帝纪》,均为武帝所作的歌诗,从题目即可看出是对祥瑞的吟诵。另按《汉书·礼乐志》,其中所录的《郊祀歌》十九章,或直接是祥瑞诗,或者浸润了浓郁的祥瑞气息。今人读汉乐府,往往更注意其中的文人或民间歌诗,这是现代审美观念导致了对历史的重新择取。事实上,在古代社会,构成主干的仍然是关涉帝王事务的典礼性诗歌。像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郊庙歌辞排在首位,正是在凸显祭祀典礼用乐对于乐府诗歌的主导性,以及祥瑞意象自上而下的弥漫性。这足以说明福应、祥瑞主题在汉代乐府诗歌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除诗之外,从班固《两都赋序》先谈“福应之盛”、接着谈诸多文学侍臣“日月纳献”的叙事逻辑不难看出,汉赋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祥瑞观念的书面表达形式。这一点在汉代城市赋、尤其是班固《两都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像《两都赋》谈西汉定都长安,直接就奠基于祥瑞或符命;光武帝“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直至“同符乎高祖”,则将自然性的祥瑞引申到人文领域。也就是说,无论其中论述汉室龙兴还是都城选择,均被赋予了上天授命的浓重色彩。以此为背景,班固对两都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充满灵韵氛围,几乎被全面祥瑞化。作为大赋结尾的《宝鼎诗》和《白雉诗》,则本身就是歌咏宝鼎和白雉这两种汉王朝重大祥瑞的诗篇。扩而言之,汉人论赋,主要涉及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扬雄所讲的“劝百而风一”(《汉书·司马相如传》),二是班固所讲的“润色鸿业”(《两都赋序》),前者指向帝王,后者指向时代,均具有夸饰的意思。鉴于当时帝王普遍把获得祥瑞作为治世成功的标志,将现实的都市和山川朝祥瑞一端渲染,也就成为当时赋家的重要取向。这一特点在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杜笃、班固、张衡等的作品中均有鲜明表现。
除了辞赋,在汉代文学侍臣写就的作品中,最具祥瑞特质的是符命文和颂赞两类。按《昭明文选》,汉代符命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三篇:一是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二是扬雄的《剧秦美新》,三是班固的《典引》。这三篇作品之所以最具代表性,是因为第一篇写于西汉王朝最强盛的武帝时期,第二篇写于西汉被新莽取代的转折期,第三篇则写于东汉经“明章之治”达至鼎盛的时期,无论在时间分布还是时代状况方面,均处于汉朝四百年历史的关键节点。其中,司马相如之所以极力鼓动汉武帝去泰山封禅,其根据就是“大汉之德,逢涌原泉”。这种普天之下遍被“汉德”的状况,促生了各种灵兽、瑞草在帝国的疆土浮现,而封禅则被视为对这种“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状况的盛典式总结。与此比较,扬雄则以秦皇的暴虐反向凸显王莽受命的正当性。按照他的叙事逻辑,秦朝是人类史上的至暗时代,祥瑞尽藏,妖孽横行,灾异频仍;炎汉代秦,大多延续了前朝的典章制度,相关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至王莽受命则“玄符灵契,黄瑞涌出”,并“登假皇穹,铺衍下土”,这明显是用从妖孽横行到常态现实、再到祥瑞世界的三重转换,表达对王莽代汉的肯定和赞美,并以此作为达至理想世界的表征。至班固,经历了两汉交替之际政治意识形态的混乱,《典引》具有重建汉室正统的用意,他一方面列举了章帝时代大量自然性祥瑞,如“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等等,另一方面将人文性的图箓符谶添加进去,从而使自然的祥瑞呈现与人文历史的遗册遗命共同围绕东汉王朝形成了聚集。这种“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谍”的状况,确实使《典引》一文达到了汉代文学“穷祥极瑞”的新高度。可以认为,这三篇文章构成了汉代祥瑞文学史的轴线,前文言及的诗赋,以及尚未提及的赞颂、诏策、疏论文字(如刘向的《高祖颂》 《爵颂》、班彪的《王命论》、杜笃的《金人论》、刘苍的《光武受命中兴颂》),则附丽其间,使这一文学主题变得连续且丰满起来。
完整看待汉代由天人之际开启的美学命题会发现,它不但有祥瑞也有灾异,不但有祯祥也有妖孽。其中,由于文学艺术天然向美向善,加上“润色鸿业”的时代要求,它重点以祥瑞为表现对象就具有必然性。但是,祥瑞在当时社会的主导性并不足以将灾异或妖孽全面逐出文学艺术。像《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大量妖孽,如服妖、诗妖、草妖、鼓妖、射妖等,其中和文学艺术的关联主要在诗妖一项。按《汉书·五行志》,国君暴虐,臣子噤言,“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这是将诗妖之诗视为对统治者充满怨恨乃至恶意攻击的文学表达。据此,《汉书·五行志》列举了从春秋到汉元帝、成帝时期的多首童谣。这些民间歌诗大多具有政治预言乃至诅咒性质,所以也被称为“诗谶”或“谣谶”。就其内容而言,它们往往被赋予了政权倾覆乃至改朝换代的严峻意义,隐含的破坏性要远远大于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 (《论语·阳货》)式的道德谴责。要而言之,汉代在天人关系中形成的诗妖及妖诗,像上述的祥瑞及相关文学一样,均将祥瑞灾异的价值从传统的伦理层面推进到政治层面,而且提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政治命运。从美学角度看,这种情景,使美与丑、或者灵韵与怪诞之间的对立显现出空前的尖锐感。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②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2页。
③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
④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页。
⑤ 朱志荣:《中国美学的“天人合一”观》,《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⑥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⑦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6—308页。
⑧ 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9页。以下引用该书随文注篇名,不再出现书名。
⑨⑩⑪⑬⑭㉓㉔ 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第418页,第441页,第596页,第116页,第125页,第598页,第590页。
⑫ 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⑮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9页。
⑱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2页。
⑳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㉑㊸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36页,第90页。
㉒ 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2—453页。
㉖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㉘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
㉙ 严可均辑:《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60页。.
㊱ 按《汉书·天文志》:“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汉书》,第1070页)
㊷ 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㊹ 刘熙:《释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9页。
㊺ 按《史记·高祖本纪》所记,刘邦母亲刘媪“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参见《史记》,第241页) 这是将蛟龙视为刘邦生而不凡的瑞应。与此一致,留侯张良从黄石公受书,也被汉儒符瑞化,如班固在《答宾戏》中讲:“殷说梦发于傅岩,周望兆动于渭滨,齐寗激声于康衢,汉良受书于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词言之所信。”(参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9—2020页) 以此为背景,文帝时期曾颁《日食求言诏》和《除秘祝诏》,证明当时以天人交感指导政治实践的倾向显露端倪。另外,士人在这一时期也已开始以自然现象占验个人命运。如贾谊在《鸟赋》中讲到,自己客居长沙时,一只鸟飞进了房间,据此,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将走向尽头,重要的验证就是他从谶书中读到了“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的预言(参见龚克昌:《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