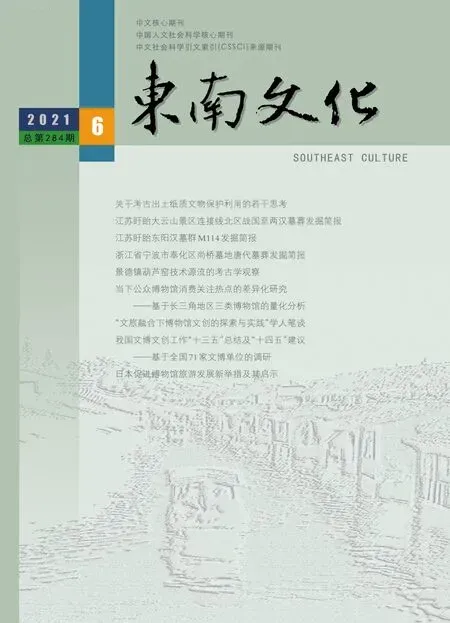江南文人审美视野下的昆曲服饰
2021-11-26汪丽丽
汪丽丽
(江苏省演艺集团江苏省昆剧院 江苏南京 210004)
内容提要:昆曲集宋元南戏和元杂剧之所长,经历代改良和传承,在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广泛传播和发展。昆曲服饰是昆曲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传统戏曲表演体系的美学特征。在昆曲的发展过程中,江南文人追求的雅致美、意境美、自然美等审美融入了昆曲舞台艺术中,并引导了昆曲剧装制作的发展方向,使得昆曲服饰形成了色彩淡雅自然、设计构图虚实相间、图案搭配重写意和象征等艺术特点。
昆曲始于元末,经明代魏良辅改良昆腔而发展为当时的第一大剧种,主要盛行于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之间。昆曲的文本诗化、服饰典雅、唱腔清雅绝俗,辅以江南丝竹伴奏和园林庭院为演出空间,这些都符合明清时期江南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旨趣。特别是在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昆曲演出之后,文人雅士的审美取向更主导了昆曲艺术的发展,使之成为“文人之曲”。昆曲服饰作为昆曲舞台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继承传统戏曲服饰的程式性、时代性、和谐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受到江南文人审美和时代风气的影响,呈现出新的艺术特点。
一、明清时期江南文人审美影响下的昆曲服饰
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园林、书斋是文人的文化空间,书、画、曲则是其具体的生活内容,诗意的文化和生活造就了江南文人独特的审美取向。在昆曲形成的这一历史时期,江南文人的审美全面而深入地融入昆曲舞台艺术之中,并引导了昆曲服饰制作的发展方向。
1.追求雅致美
明清时期江南文人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以及强烈的身份认同:在审美上,他们受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响,追求飘逸洒脱、高洁清灵,崇尚雅致和脱俗;在心理上,他们往往有较高的文化自我认同感和优越感,追求脱离俗世和张扬自我。江南文人雅致的审美追求不仅影响了当时园林、书斋、家具的风格,也影响了昆曲的文本和服饰。例如,昆曲服饰在运线行针方面以精巧的手艺构成精美和谐的图案,刺绣手工一丝不苟,但刺绣配合服饰的构图却十分淡雅疏朗,给人以雅致、清俊、整肃之感。昆曲服饰强调的不是艳丽的色调,而是高雅的意趣、美观而不落俗套的境界[1]。
2.追求意境美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概念,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明清时期江南文人非常推崇这种情景交融的诗意空间,意境之美便成为他们的审美取向,既表现在文人画、诗词之中,也表现在他们对昆曲的鉴赏品评之中。王国维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2]元曲是昆曲文学的来源,是中国戏曲文学的一个时代高峰,塑造了中国戏曲文学的曲文审美模范,奠定了昆曲文学的基调。中国戏曲的整体特征是追求意境之美,作为文人戏的昆曲,其内在精髓更是如此。这不仅体现在剧本的文学之美,也外化至昆曲的服饰之美。昆曲服饰是舞台意境美的重要组成,正如老艺人所说的戏服是“穿在演员身上的布景”,配合“一桌二椅”的极简舞美和园林厅堂的演出环境,昆曲服饰也追求舞台意境的和谐美,通过昆曲演员身段程式的运化,将舞台时空的转换通过动作点到为止,把意境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3.追求自然美
江南文人追求的自然之美在于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他们摒弃刻意雕琢,倡导自然天成、返璞归真。在艺术审美中,江南文人注重戏曲的自然之美,这与中国戏曲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王国维在《元剧之文章》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又说:“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3]元曲蕴含的自然之美这一审美传统,在江南文人的昆曲舞台艺术创作和鉴赏活动中呈现出新面貌。
明代末期,江南文人大多养家班供宴饮唱和之乐,其中的品鉴之辞可以反映出当时文人的审美倾向。明末朱隗在《鸳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记歌》中记载其所观家班演出风格清朗自然,“不须粉项与檀妆,谢却哀弦及豪竹。萦盈澹荡未能名,歌舞场中别调清。态非作意方成艳,曲别无声始是情”[4]。昆曲伴随了宴饮冶游、文人唱和,既是江南文人昆曲社交的一种常态,也是江南文人生活的“必修课”[5]。朱隗对于所观家班演出,认为其不追求场面的宏大和服饰的华丽,而是本色自然和蕴藉情韵。这一记载正体现了明清之际江南文人对昆曲作为场上之曲的自然美的追求。在这种审美取向的影响下,虽然当时奢侈之风较为盛行,但昆曲服饰并没有往奢华的方向发展,而是取法自然,注重服饰符合人物身份、行当的本来特征,利于人物本色的塑造。
二、昆曲服饰的审美特征
昆曲服饰的一整套美学特征是昆曲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吸收了宋元南戏、元杂剧的戏曲舞台艺术传统,其美学取向既具有明清社会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明清时期江南文人追求和谐典雅的审美理想。
人的审美活动、审美需求受特定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作为具有六百余年历史的昆曲,其舞台艺术的形成过程也带有浓重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的印记。艺术来源于生活,故“明代传奇服饰基本上来自明代常服,它不仅继承了元明杂剧服饰的某些特征,而且根据生活服饰的变化和演出的要求,不断地自我发展”[6]。陆萼庭指出:“明代昆剧在戏衣方面深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并多变异,还没有定型。”[7]随着明代家班的增多和追捧,昆曲服饰逐渐追求定式,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末清初之际,昆曲服饰打破了明代官服礼制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开始注重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如明代蟒服为皇帝特赐品,武官穿、文官不穿;到清代,昆曲衣箱中已有五色蟒服,文武官都穿[8],这正是戏服所体现的时代集体认同的一个例证。
除了带有时代的印记外,昆曲历来也是江南文人的风雅之物。在昆曲诞生之初,江南文人的审美倾向就深深印刻在昆曲的基因之中。据明代文徵明的《南词引正》记载,昆山腔的创始者顾坚“精于南词,善作古赋……其著有《陶真雅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区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9]。而顾坚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等文人曲友交好。可见当时的昆山腔已经在当地的文人群体中有所流传。这三人在诗词绘画等领域均有较高造诣,特别是被后世称为“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倪元镇),其文人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既没有崇山峻岭,也没有茂林修竹。在他典型的“一河两岸”构图之中,大块的留白为观者创造了一片虚静而又淡薄的灵境。但这简淡之中所蕴含的文人审美旨趣却一点也不简单。宗白华认为中国山水画趋向简淡,然而简淡中包具无穷境界。倪元镇画一树一石,千岩万壑不能过之[10]。
这种文人审美倾向也鲜明地体现在昆曲服饰中。昆曲服饰是昆曲舞台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角色都有严格而具体的穿戴程式。在视觉审美上,从色彩、设计、图案、搭配等方面均体现了江南文人的审美追求。
1.色彩:运用“淡雅自然”的色调
昆曲服饰在整体色调上往往呈现淡雅、朴素、低饱和度的特征,如在南昆传承版《牡丹亭》中,杜丽娘作为官宦之女,其服装用色多为淡粉、淡绿、淡黄等,以体现人物纯真、温婉的性格特征;而另一主角柳梦梅的服饰色彩素淡,凸显其有书卷气以及浪漫飘逸的风格[11]。昆曲服饰色彩的应用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与文人雅士所崇尚的淡雅之美,与中国的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出的飘逸风格和书卷气质融合了儒家与道家思想,是文人审美的构成要素。昆曲《牡丹亭》始于一场梦,服装色彩的低饱和度体现了整场戏梦幻、虚化等如梦境般的情景。随着剧情的发展,服饰在主体色调的应用上也发生了符合戏剧冲突的变化。如杜丽娘的服饰在《游园》和《惊梦》中为“少女怀春”般的粉色,至《离魂》时为清冷的白,通过色彩表达感情,犹如中国画中色彩可以反映花笑鸟啼,可以体现离情别怨的情感表达。服装整体淡雅的色调搭配了局部高饱和度的绣花装饰,更像是水墨画中远山与近景的呼应。
2.设计:运用“留白”和虚实相间的构图
昆曲重视塑造意境美,而意境美通过虚实关系和“留白”实现。昆曲的舞台画面与中国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线条构图或舞台人物、道具形成画面“实”的部分,留白则作为“空”的部分给人以想象空间和视觉冲击,让观者以自我为主体,通过展开想象使画面的内涵更加丰富。无论是在昆曲还是京剧等中国传统戏中,水袖的设计均可看作舞台画面构图中由实走向虚的“线”,是戏曲人物为舞台画面“留白”的引子,且通过表达剧情和人物情感的水袖表演,舞台的虚实是可流动的。这种流动的“留白”给观赏昆曲的文人士大夫以无限的想象,在这里,水袖的舞动比静态的线条更具有情韵意境。“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中国的书法、绘画以及传统园林建筑中飞檐、斗拱、柱体之间线的关系都是文人审美中“线”的表现方式,但只有戏装中的水袖是动感的线的表达且别具美感。观戏的文人士大夫亦可以把水袖的舞动看作诗。昆曲文学底蕴深厚,唱词是优美的曲牌,配合丝竹的演奏,以琴传情,以诗传意,观者在舞与乐之间通过水袖的流动性“留白”方式体会其中的意与境,形成一种美妙的享受。
例如南昆传承版《牡丹亭》的服装设计便采用了大量的“留白”方式,除水袖外,设计者依照传统在领口、前襟、裙摆使用边花、角花、折枝花等作为服装的装饰,这些绣花装饰或疏或密、左右对称,并在整体服装中设置“留白”。特别在最后一折《离魂》中,杜丽娘的服装为白色绣花披衬褶、五彩绣花裙,头戴湖色头纱,服装整体装饰存有大量“留白”、色调冰冷苍凉,将杜丽娘身体的孱弱与其凄凉的境遇表现出来,充分将诗化的文本转化成如水墨画般的视觉语言和服装语言,成就了风格显著的江南文人审美[12]。
3.搭配、图案:运用写意和象征的趣味表达
传统戏曲的舞台服装并不追求服装对比文本的真实性,观者似乎很难判断角色所处的地域或故事发生的季节,却可以从服装判断出角色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甚至性格品质。如在南昆传承版《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春香同为女性角色,服装却对比鲜明,杜丽娘均着裙装,而春香则着裤装,且二者服装中杜丽娘在色彩上偏淡雅、春香则偏艳丽和单一。这种设计与现实中不同社会角色的服装是有出入的,但是在戏曲的表演中却具有符号性、象征性的特征,与江南文人审美中关于角色的社会地位和审美定义相符。
服装在服务演员的表演之余,也通过装饰元素的形式语言为表演提供情感表达。在南昆传承版《牡丹亭》的《惊梦》中,杜丽娘服装以蝴蝶绣花为装饰,而柳梦梅的服装则绣以梅花。梅花在明清时期江南文人士大夫中极受推崇,是文人理想精神品格的象征,符合文人对于柳梦梅“君子”形象的构思。杜丽娘服饰中的“蝶”同柳梦梅服饰中的“花”,让二者组成“蝶恋花”,寓意了故事中美好的爱情。
三、结语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其传播和传承发展的媒介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士大夫这一特殊群体,因此昆曲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一种“雅俗共赏”的剧种,其中充满了文人审美趣味,其文本、唱腔、服饰等也都饱含文人审美特征。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综合了各个艺术门类,服装作为舞台美术的构成元素,亦遵循戏曲及文人审美观的留白、写意、淡雅等特征,这也是江南地区文人审美旨趣的体现。较之于西方的审美观,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审美从来都不是追求写实的,而是美在神韵、美在意境。无论是诗词、书法、中国画,抑或戏曲及其服装,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是人的情感与诗意的和谐统一,通过对生活和自然的艺术表达体现多层次的情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