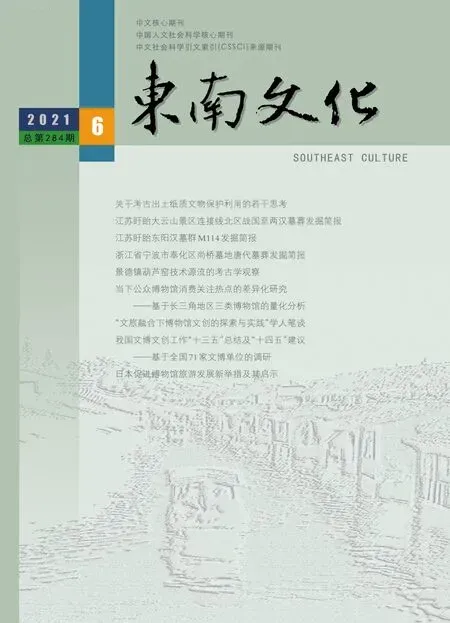关于考古出土纸质文物保护利用的若干思考
2021-11-26何伟俊
何伟俊
(纸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江苏南京 210016;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19世纪末,我国西北地区开始有纸质文物的考古发现,其后纸质文物在多地考古发掘中均见出土。它们品种多、数量大,加工工艺、写印材料独特,时代自汉代至明清,其中的早期文物尤为珍贵。因其出土环境复杂,保护修复工作难以直接借助传统技术和现有科技,特别是潮湿环境和干燥潮湿交替环境下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往往遭遇瓶颈。目前学界在科学分析检测、造纸工艺研究、科学信息提取等科学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糟朽类文物的病害机理、保护修复技术等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当务之急是开展本体材质、劣化与粘连机理研究,探究多因素协同作用对本体的长期影响和作用方式,研发新材料与新技术,并致力于探索这类文物的活化利用。
一、引言
在我国文物体系中,纸质文物作为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印刷术的承载体,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其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与创新成果,对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纸张发明以来,我国两千多年来所积累的纸质文物可谓浩如烟海,据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显示:如果综合计算书法、绘画、古籍图书、档案文书、碑帖拓本、文件等不同种类,纸质文物在国有六千多万件可移动文物中的总体比例已超过四分之一,是所有材质文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文物[1]。按照制作与加工工艺的不同,我国纸质文物大致可归纳为手工纸与机制纸两大类。手工纸主要指考古出土的纸质文物和传世的古籍、书画等;机制纸则主要见于近现代文献与革命文物。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当今通常意义上的纸指植物纤维经物理、化学作用提纯与分散,其浆液在多孔模具帘上滤水并形成湿纤维层,干燥后交结成的薄片材料[2]。与传世书画、古籍保护修复技术相对完善的情况不同,针对考古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技术,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的早期“古纸”和潮湿环境下出土的纸质文物,存在着严重的技术储备不足和保护滞后的问题。纸质文物的揭取、清洗与加固等关键技术目前相对薄弱,但这些都是抢救性保护措施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部分出土纸质文物本身已极为糟朽,对应性的现场提取方法尚待大量实践检验……种种不足极大限制了古丝绸之路沿线等考古出土重要纸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顺利开展,急需应用先进科学手段进行技术与方法的创新。
二、考古出土纸质文物概述及保护利用的难点
我国考古出土纸质文物的总体现状为品种数量多、珍贵程度高、年损毁率大、修复防治难。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纸质文物,由于本体材质、加工工艺、写印材料的独特性,能够借鉴的传统纸张保护修复技术和方法相对有限,保护利用出现瓶颈。此外,诸多现代纸质文物保护的技术、材料和工艺研究在应用于考古出土纸质文物之时,同样也面临着比较窘迫的局面。譬如在出土粘连纸张的揭取、脆弱纸张的本体加固、大量出土纸质文物的智能化处理、用纸的修复(补)、出土后纸张的脆化与粉化、黑色霉斑的清洗去除等具体的材料和技术研究上,没有或尚无完全可靠之方法,有待研发对应的新材料和保护修复技术。而这些新材料和新技术还需进行可行性、安全性、原创性研究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初步应用示范。
依照保存环境的不同,考古出土的纸质文物主要可分为三种出土环境:干燥环境、潮湿环境、干湿交替环境,其中潮湿和干湿交替环境下出土纸质文物的情况基本类似,可大致归于一类。干燥与潮湿(包含干湿交替)这两大类出土纸质文物的病害类型、劣化机理不同,出现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保护利用的需求与方法因此存在很大差别。所以,目前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考古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利用问题,就必须开展针对考古出土纸质文物造纸工艺等的深化研究,以及系列保护技术的研发与实际应用。
(一)干燥环境下的考古出土纸质文物
1.出土情况概述
20世纪以来,在我国北方地区干燥环境下的考古现场多次出土了纸质文物,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甘肃等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汉唐时期的麻纸。这些地区气候极端干燥,长期埋藏在干燥条件下的出土纸质文物保存比较完好[3]。这些出土的早期纸质文物不仅意义重大、价值较高,而且具备重大的考古学价值。如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最重大的意义是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麻质纸二十多片,为西汉宣帝至哀帝时期(公元前73—前1年)的遗物[4]。再如在甘肃兰州伏龙坪一座东汉墓中共发现三片直径17厘米的圆形纸张,除一片破碎外,两片保存完整[5]。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的尼雅纸经鉴定表明,东汉时期用浇纸法造出的纸张己出现在南疆地区,这是历史最为悠久的造纸术[6]。
以新疆吐鲁番吐峪沟为例,近年来就已经出土了数万件纸质文物[7]。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群经历了2010年和2015年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但是对于其中出土的数量巨大的文书残片的研究还很少[8]。据悉,吐鲁番出土的纸质文物只占整个新疆纸质文物的三分之二。经不完全的考古资料统计:罗布泊汉代烽燧亭故址、民丰县附近、楼兰一带的屯垦和烽燧遗址、吐鲁番地区、焉耆西南30公里的“明屋”千佛洞遗址、库车的苏巴什古城、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遗址、新和县西北的托乎拉克埃肯千佛洞、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古城遗址、若羌县米兰古城、和田于阗地区等,均考古出土了不同数量的纸质文物。其中与吐鲁番吐峪沟遗址相仿,楼兰遗址和楼兰古城出土了大量的汉文简纸文书[9]。此外,与新疆同处古丝绸之路的内蒙古黑水城也出土元代文献四千余件[10]。可以说,“一带一路”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纸质文物,年代跨度大致从汉至元明,囊括了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历史朝代。
2.保护利用的困境
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作为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以及纸与造纸术西传的重要枢纽路线,得到广泛关注,对其考古出土的纸质文物所蕴含文化价值的挖掘与提炼被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可是,目前关于新疆、内蒙古、甘肃等丝绸之路地区考古出土的纸质文物不仅在造纸工艺等特定价值的挖掘与提炼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而且还在保护利用方面面临着出土数量巨大而难以开展的困境。
干燥环境下出土的纸质文物数量大,单片居多且双面有字,理化性能较稳定,但面对大量亟待修复的文物,当前的保护修复技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首先,传统托裱技术不适宜于双面有字纸质文物的修复,且修复效率低下;其次,修复中使用的浆糊容易遭受霉菌侵害,不利于纸质文物的长期保存;再次,纸质文物自1949年之前就有考古出土,但始终未对文物本体用纸进行系统的分析检测与研究,直接影响了传统造纸技术的挖掘与凝练,对当今古法造纸也没能发挥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自然也带来了修复用纸难以匹配文物本体的困扰。
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出土的古纸最多、年代最早、意义最大,如目前所知最早的纸地图——甘肃出土放马滩纸,现存最早的纸书——新疆出土《三国志·孙权传》写本残卷,我国第一部木活字印刷版本——宁夏出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11]。关于早期“古纸”的抢救性保护,我国文博界惯用玻璃片将其夹住加以固定,这种方法至今仍在使用[12]。但使用玻璃或有机玻璃片夹住纸张和丝绸类文物固定出土纸张残片文物的保存方法,在经过较长时间之后,其不良影响正逐步显现。对于这些数量巨大的出土纸质文物而言,开展适用的修复用纸研究,研发基于古代造纸原理、利用纸张本身的氢键作用产生结合效应,取代附加的胶黏剂并能够明显提高修复效率的智能化技术当为良策。这样有望解决干燥条件下考古出土的大量纸质文物的保护,尤其是双面有字纸质文物保护修复后的利用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陆续出土的大量纸质文物,就得益于纸浆修补技术的持续进步和文物工作者对传统造纸工艺认识的不断加深,采用了与本体材料基本相同的纸浆进行了良好的保护修复,解决了当时使用传统保护修复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已在量身定制的无酸包装之中双面陈列展示。最为关键的是,针对这些大量的出土纸质文物,当下保护修复的效率依旧低下,成熟有效的智能化、科学化批量保护修复处理方法依然欠缺。
(二)潮湿或干湿交替环境下考古出土纸质文物
1.出土情况概述
处在潮湿或干湿交替环境下考古出土的纸质文物近年来也时有发现,浙江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13]、江西上饶明墓的明版古籍[14]、江苏常州芳茂山服务区宋代墓葬[15]、甘肃天祝祁连镇岔山村唐代墓葬[16]等都出土了许多此种类型的纸质文物。
毫无疑问,潮湿或干湿交替环境下出土的纸质文物虽然相对数量较少,但亦不乏填补史料空白的珍品,极具考古、历史、文化等价值。如浙江温州博物馆藏唐代写本《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和宋代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于1956年分别出土于浙江龙泉崇因寺双塔、金沙塔内[17];1970年,在山东邹城发掘的明鲁荒王朱檀墓的随葬物品中,有六种至为珍贵的元刻本书籍,有的已是海内罕见的孤本[18];1975年,江西星子县横塘乡开挖排水沟时,在一座宋墓中发现两部邵尧夫诗集[19],此前邵尧夫未见有文献记载;四川省井研县相关人员考察民俗文物时,在县文化馆意外发现一张从明墓中出土的“丰都山冥途路引”[20];江苏太仓明施贞石墓出土古籍《古今考》中存有散夹于各卷内的手抄文牍共14页,为明嘉靖、万历时期太仓州太仓卫前千户所官员奖惩履历文册[21]。这些均是对史籍资料的有益补充。
与干燥环境下出土的纸质文物不同,此类环境下出土的纸质文物往往霉变腐烂、粘连严重,不仅需要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修复,并且后续保护修复的难度极大,还会给今后文物价值的充分发掘带来极大影响。2000年3月在湖南衡阳西郊胜利山发掘了两座明代墓葬,在二号墓中出土了一沓珍贵的古籍,出土以后,考古人员将这些腐烂粘连的古籍急速送往湖南省博物馆装裱室[22];2001年上海宝山明墓出土古书的保存选用了乙醇作消毒剂,这批古书的书页之间相互粘连,散发出恶臭[23];太仓南转村明墓出土的纸制木刻版古籍,在尸体霉菌和潮湿环境的作用下,变成了又黑又臭的“饼子书”,其修复是件非常艰难的工作[24]。
2.保护利用的难点
潮湿或干湿交替环境下出土的纸质文物,在修复技术和文物本体用纸研究方面与干燥环境下出土的纸质文物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且显然还有其本身独特的个性问题,如霉变腐烂、粘连严重、纸质脆弱等,有些甚至已成为“纸饼”“书砖”。
因此,对干湿交替环境下出土粘连纸质文物的揭取,必须要解决传统蒸汽法、溶剂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深入探讨分析研究出土纸质文物的粘接机理,进而研制有针对性、普适性的揭展剂。文物保护工作者采用化学定性和仪器分析相结合的手段对出土明代历书纸张上的硬结粘着物和深褐色斑进行定性,结果表明:使纸张发硬、结块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钙盐及钙的氧化物的存在[25]。从实际情况来看,“纸饼”“书砖”的成因通常更为复杂,考古现场对其提取也相当困难,可是目前还没有适合潮湿环境下出土纸质文物的抢救性科技保护措施和手段。当前急需解决此类埋藏环境下出土纸质文物的抢救性保护,以及基于现场移动实验室的整体提取、微型发掘、粘连揭取、脆弱纸张加固等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开发研究。
现今对潮湿或干湿交替环境下出土纸质文物的损坏因素与机制的基础性研究远远不够,粘连、脆化与粉化等病害发生的劣化机理不明,导致潮湿或干湿交替环境下出土脆弱、糟朽类纸质文物的保护加固存在极大的困难。相关统计显示,2008年至今纸质文物的加固保护增添了许多新的科研内容,尤其是各种高分子保护剂的实验,但对于纸质文物的保护手段没有提出更新颖的方式,整体变化不大,并且有些保护剂只是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真正使用到纸质文物的保护中[26]。
纸质文物的保护今后应必须针对出土糟朽类纸质文物存在的脆化、粉化等主要病害,突破现有惯性的加固模式,采用低分子量官能化纤维素接枝技术在断裂的分子之间架起链接的“桥梁”;对于脆化与粉化十分严重的出土纸质文物,引入评估作用机制,研发能够精准应用、具有多重功效的纳米与生物技术,如纳米纤维素、细菌纤维素、静电纺丝技术制备微纳米结构纤维膜等。此类新型材料除具有粘合、加固、防霉防虫和抗老化等多重功效之外,还可经生物与化学结构重组、功能化,在可控制其结构、纯度及规范操作基础上在纸质文物的表面构成精准应用,是可降解、具有可逆性且无毒副作用的加固保护材料,最终能够使脆弱、糟朽的出土纸质文物得以陈列展示,达到保护利用之效果。
三、“古纸”及其造纸工艺的科学化研究
(一)科学分析检测
有学者全面论述了古代纸质文物(包括纸张原料、墨、印泥和颜料等)所涉及的各种现代科技检测技术与方法,认为上述技术的综合应用、各取所长和相互印证是揭示纸质文物的制造过程、艺术特征、保存历史、病害情况、真迹与否及如何修复等重要问题的有效手段[27]。钱存训以详实史料为基础的研究,部分结合考古发现,最终呈现出的动态画面非常有助于理解我国古代造纸原料的演变过程,对古代造纸工艺研究甚至古纸分析有很好的参考作用[28]。
出土的古纸通常会有相应的加工技术,且造纸过程与加工工艺纷繁复杂。李晓岑分析敦煌写经纸原料以苎麻为主,少数为大麻,并有少量的构皮纸或桑皮纸。这说明当时的纸张的加工技术既有淀粉施胶技术,也有涂蜡技术,出现了多样化的加工纸[29]。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一批东晋到唐代的古纸,纸张的原料主要是苎麻、大麻和构树皮,纸张的生产方法有浇纸法纸和抄纸法两种,有单面施胶、双面施胶、浆内施胶加填、染色技艺等多种加工方式[30]。
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纸药”的文献、分析、流传等方面的研究均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传统造纸过程中,造纸工将捣碎后的物料放入纸槽中加清水并用力搅拌,有时同时会加入用米浆等淀粉物质制成的糊液作为悬浮剂,即“纸药”,古时称为“纸药水汁”[31]。“纸药”对于成纸质量可谓举足轻重,甚至有“墨有配方(胶法),纸有纸药”之说,可是当前在对出土纸质珍贵文物的研究中,多利用显微观察纸张纤维以判断造纸原料来源、处理工艺,为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数据支持,早期“古纸”的分析鉴别也同样如此,诸如“纸药”之类的加工工艺的科学分析检测却迟迟未能得到有效开展。显微观察法的缺陷是容易受到学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无法获取纸张纤维的化学组成及降解老化状况。此外,针对纸张劣化程度的预测还需建立在足够已知样本的检测数据基础上,特别是涉及早期“古纸”的研究。由于目前必要与关键的分析检测数据的缺失,若想得到较为理想的纸质文物劣化模型,今后还需文物工作者长期协同努力。
(二)保护利用
目前,我国大部分博物馆所用的修复(补)用纸基本为采购而来,质量参差不齐。实际使用中发现,目前古法造纸在湿强度、形稳性、柔韧性、耐老化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出土纸张文物修复质量的需要,也就难以顾及后续保护利用的问题。
简言之,关于我国出土纸质文物的造纸及加工工艺的挖掘和基础性研究,国内尚未开展系统性的工作,造纸工艺的解读以及现今的修复用纸难以满足出土纸质文物保护修复的要求。开展出土纸质文物的传统造纸工艺研究,对提升当下纸质文物的修复质量以及加强保护利用的程度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文物工作者首先必须解读“古纸”的造纸工艺,在此基础上引入新方法与新思路、开展技术创新,研发新技术与新材料来解决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问题。例如通过模拟古代手工造纸过程中的剪切、舂捣工艺,利用纤维测量仪观察模拟试样中纤维的微观形态,与古代样品中纤维的形态进行对比,从而建立起造纸工艺与纤维微观形态特征的对应关系[32]。其次,在保护利用关键的修复技术方面,如果寄希望于找到与纸质文物同时代、同材质的修补和补配材料,无疑是可遇不可求、难以实现的。可是通过对纸质文物本体材质进行相应的分析检测,制作与本体成分、加工工艺、理化性能等类似或接近的材料用于修补和补配,则是切实可行的,明显有利于出土纸质文物的长效保护利用。
从保护利用的角度来看,我国出土纸质文物制作及加工工艺的科学研究进程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文物工作者在此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科学分析检测数据与考古资料,但目前空白点仍较多,相应的谱系与数据库尚未完善。如染色纸张的使用曾在西夏时期一度流行,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存世量,但相关的化学分析甚少开展,因此,文物工作者对于染料的使用情况和染色纸张的纤维原料并不十分清楚[33]。先前研究中,对珍贵“古纸”的研究多利用纸张纤维作显微观察法,其他的分析检测应用较少。近来不断有考古出土纸质文物出现与新资料发表,修订、检验和弥补原有不足或缺陷已日渐成为可能,关于出土纸质文物潜在意义和价值的挖掘与探索必将从量变到质变。
(三)较为特殊的出土纸质文物
“一带一路”地区考古出土的纸质文物,不单单是早期的“古纸”较多,诸如唐朝时的西域地区,与宋朝并存的金、西夏等时期的纸质文物存世量亦不少,但关于其造纸术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少或基本没有,这很可能会导致其中部分无文字的出土纸质文物难以明确具体年代。即使是书写或印刷有文字的纸质文物,也会因属于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等因素造成识读困难,目前保护利用的总体情况与前景堪忧。
此外,纸的应用至两宋已不仅限于书写、绘画,其用途之广泛令人叹为观止,已有作冠、作帐、作被、作甲、作瓦等特殊用途[34]。有些出土品虽为纸张所制,但因需要而被制作成了其他物件形态,可称之为“异形文书”。纸帽和纸鞋是该类“异形文书”中最常见的形式,例如新疆吐鲁番高昌区阿斯塔纳古墓群就出土了数十件[35]。另外,有些与传统古籍、书画装帧方法有关,例如关于“缝缋装”,在有关印刷史、版本学的论著中,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基本没有论及。这就是说,在古籍中有没有“缝缋装”,“缝缋装”是什么样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36]。而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献印证了古籍中“缝缋装”的样式及装帧方法。再如甘肃省华池县双塔寺遗址出土的金代纸质佛像画可见雕版印刷痕迹,原始状态为立轴装,但与常规立轴(宋代文献记载样式)明显有所不同。该文物无镶料,无命纸及覆褙纸,天地杆使用相对较细的树枝,当为未见于记载的金代书画“立轴”装帧样式[37]。笔者建议诸如此类具有特殊意义、用途、类别的出土纸质文物的进一步“活化”保护利用,应纳入今后的规划研究与实践。
(四)“古纸”和造纸术的起源与发展
造纸术起源于何时,依然是早期“古纸”研究以及此类考古出土纸质文物保护利用中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从宏观角度来看,20世纪以来,关于早期“古纸”的研究长久纠结于“什么是纸”“蔡伦是否发明造纸术”等问题,反而对为什么在中国形成如此这般的纸的定义,为什么在各地、各族群中发展形成如此种类繁多的造纸术等更为重要的问题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纸张起源于西汉是毋庸置疑的,考古出土的早期纸质文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譬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界陆续公布了在甘肃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包括西汉纸张的三次新的发现。尤其是西汉纸绘地图和书有大量文字的纸张的惊人发现,以十分有力的证据反复证实了我国在西汉时期就有了用于书写、绘画的麻料纤维纸[38]。但亦有诸多学者坚持“蔡伦造纸”,认为“西汉纸”难以经受各方面严谨的质疑和考证[39]。有学者撰文称,目前考古发现的代表性“西汉纸”“放马滩纸”不是地图纸,“居延查科尔帖纸”是东汉蔡伦以后的古纸,“悬泉纸”是魏晋纸,“灞桥纸”不是纸,“罗布淖尔纸”“金关纸”和“中颜纸”是麻絮纸(以“纸”的定义来衡量也不是真正的纸),因此西汉还没有任何纸书的证据[40]。其实,以研究中双方争议均相当大的纸的纤维分析来说,如能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重新取样,共同分析各种“西汉纸”的纤维状况,应可尽量避免不同人因取样差异和分析角度不同造成的异议[41]。
近来,纸质文物无损分析模型的建立以及通过古纸“指纹信息”,即特征化学标记物进行纤维种属的精确判定及化学组成判定,逐渐成为纸质文物保护研究的新趋势。所以,要厘清“古纸”和造纸术的起源与发展问题,第一,有赖于今后早期“古纸”的考古新发现;第二,需打破学科边界,融合考古、科技史、文物保护、造纸等多学科开展古代纸张认知系统研究,在我国古代纸张的缘起、发展与定型等问题上取得共识,最终集多方合力研究来解决。如此方能使得纸的发明这一跨越时空的华夏智慧能够古为今用、历久弥新。
四、考古出土纸质文物保护利用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纵观我国考古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利用过程,有关这些纸质文物的本体分析检测与研究一直未得到很好的开展,严重影响了对其制作工艺、传统造纸技术乃至所蕴含科学信息的提取与价值挖掘,同时因无法厘清病害产生的基本情况与机理,亦无法为后续良好的保护利用提供较好的参考与借鉴。
为更好地保护利用好考古出土纸质文物,从文物保护层面来看,当务之急是利用考古出土的纸质文物开展本体材质、劣化与粘连机理研究。一方面开展基于造纸原理的修复技术创新,智能化提升出土纸质文物(干燥环境)的修复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重点研发在微观层面上可以有效揭取、加固出土糟朽纸质文物(潮湿或干湿交替环境)的新材料与新技术。同时,文物工作者要做到将考古现场与纸质文物保护衔接好、配合好,之后的保管与陈列对接好、活化利用好。
长远来看,在集众家之长形成考古出土纸质文物“智库”的基础之上,还需基于造纸原理、不同环境下出土纸质文物的共性问题和传统纸质文物修复技术,在考虑保护修复材料的匹配性、修复工艺、操作规范的同时,从机理角度阐释保护修复后的主要指标在单一与复合层面的改善与提高,从分子量、单元组成、官能团等多角度剖析现今的保护处理模式,并且探究多因素协同作用对纸质文物本体的长期影响和作用方式。在保护修复好纸质文物之后,文物工作者还需要思考如何通过创新模式将考古出土纸质文物与出土遗址的考古工作、保护修复过程、文创产品开发等有机结合起来,致力于探索考古出土纸质文物的活化利用,带动文物事业和文旅融合的发展,开创考古出土纸质文物保护和利用之新路径,为其长久保护利用提供新思路。
2016年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国家文物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计划,旨在建设全国一体、区域统一、互联互通的国家文物局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共享、开放文物数据[42],这无疑是惠国惠民的系统性工程。从考古出土纸质文物进一步保护利用的角度来说,文物工作者也应打破传统工作模式与方法,思考创新普及弘扬“纸文化”的表现形式,与时俱进地应用信息化时代的多种先进技术,努力构建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的保护、管理和利用系统,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提升,力求解决考古出土纸质文物保护利用中面临的诸多难题。
从开放的全球视野出发,考古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利用需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先进技术与方法,广纳百川,与国内外同行开展合作,拓宽交流和影响范围,并力求在考古出土的纸质文物保护研究中有新发现、新突破(依以往实例来看是必然现象),进而填补我国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空白,更好地契合我国作为“四大发明”发源地的文明古国的国家形象。这样方是真正发挥了考古出土纸质文物在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关键作用,全面有效和科学合理地做好了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五、结语
考古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利用对于传承华夏文化、激发爱国热情的固有价值可谓不言而喻,其承载的文字等信息、背后蕴含的历史故事、彰显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皆是全面了解真实的古代中国,坚定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信念,弘扬中华民族由古至今的发明创造精神等不可或缺的重要教育资源。
将纸和造纸术纳入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对出土纸质文物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及与其相关的传统工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作为连接“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载体功能等问题,包括其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的研究,依旧是今后不可回避的关键话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