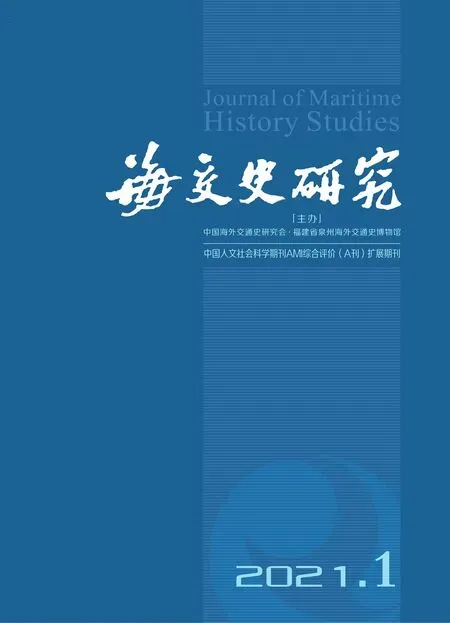“南海Ⅰ号”研究中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相互补证
——对现有研究史料和路径的检讨
2021-11-25黄纯艳冯辛夷
黄纯艳 冯辛夷
“南海Ⅰ号”提供了一个考古发掘、公众展示、学术研究同步推进的典型范例,相关研究一直随着“南海Ⅰ号”阶段性发掘成果的陆续发布而持续进行。(1)如李庆新:《南宋海外贸易中的外销瓷、钱币、金属制品及其他问题——基于“南海Ⅰ号”沉船出水遗物的初步考察》,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第121—131页;杨睿:《“南海I号”南宋沉船若干问题考辨》,载《博物院》2018年第2期,第27—32页;黄纯艳:《舶商与私贩:<“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贸易史解读》,载《丝绸之路考古》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第212—218页;叶道阳:《“南海Ⅰ号”沉船反映的宋代海上生活辨析》,载《中国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第99—104页,等等,讨论了“南海Ⅰ号”的各类文物、船舶形制、始发港口、海上生活等问题。特别是,2020年初相继刊布了基于最新发掘成果的系列研究。(2)《文物天地》2020年第2期开设“南海Ⅰ号”专辑,刊载39篇“南海Ⅰ号”研究论文,利用最新发掘成果从陶瓷器、金属器、船舶、文物保护等多个方面讨论了“南海Ⅰ号”相关问题。《客家文博》2020年第1期也设置“南海Ⅰ号”专题,刊载了5篇讨论“南海Ⅰ号”的论文。“南海Ⅰ号”发掘工作已经结束,随着“南海Ⅰ号”发掘成果日渐完整的面世,“南海Ⅰ号”全面深入的研究必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海Ⅰ号”有着迄今发现的其他古沉船难以比拟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其巨大学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的二重证据法无疑是深入推进该研究的重要途径。本文试图对已有研究的史料、观点和方法做一检讨,探讨如何更好地实现文献记载与发掘成果的相互补充、彼此映证,为“南海Ⅰ号”相关问题讨论提供共同的基础和逻辑。
一、史料性质与“南海Ⅰ号”研究
宋代由于市舶制度的建立和航海实践的空前发展,特别是到南宋,海防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有关海洋的记载大为增加,留存下来的文献较前代大为丰富。这些文献的史料来源、生成方式和书写目的各有差异,其史料性质不尽相同。宋代有关海洋的记载散见于各类官私文献,按文献类型分,记载相对较多的官方和半官方的正史、政书、方志等文献中,有《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淳熙三山志》《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及南宋临安三志等;私人文献有个人别集,代表性的有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包恢《敝帚稿略》、楼钥《攻媿集》等;笔记小说有《参天台五台山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文昌杂录》《萍洲可谈》《岭外代答》《诸蕃志》《梦粱录》《桂海虞衡志》《云麓漫抄》《桯史》《夷坚志》等。四部文献中的零散记载则难以尽举。
从史料来源考察,一是来自于官方档案记录,即中央和地方管理与海洋相关事务的典章制度、政务活动等,如上举正史、政书、方志文献记载了市舶管理、贸易活动、朝贡往来、海防设置、海船制造、民船征调、滨海民众管理等相关内容,其主要来源是官方记录;二是来自于亲身经历,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作者徐兢记录本人参与出使高丽使团的亲历亲见,《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作者成寻搭乘宋朝商船自日本来宋朝的航海经历,一些官员所言其于沿海地区任职的政务,也多有其亲历;三是来自于采集和听闻,如《岭外代答》是周去非在静江府(桂林)和钦州任官时听闻和采访,即“耳目所治,与得诸学士大夫之绪谈者”(3)[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序”,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诸蕃志》的主要信息来源于赵汝适任福建提举市舶时采访海商:“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4)[宋]赵汝适撰,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赵汝适序,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页。四是主观想象,《春渚纪闻》称安焘使高丽时,“见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佛)经轴为求”(5)[宋]何薳:《春渚纪闻》卷2,《龙神需舍利经文》,张明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夷坚志》描述海洋中有长人岛,其人“身皆长二丈余”“臂长过五尺”(6)[宋]洪迈:《夷坚丙志》卷6,《长人岛》,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6页。丈、尺,为旧制计量单位。等都属此类。上引《春渚纪闻》和《夷坚志》所载是作者主观虚构的海洋意象,固然不是客观真实的记录。但“真实性”并非取决文献类型不同或官、私之别,而需要针对具体史料加以辨析。正史、政书有关海上贸易的典章制度、管理活动,以及海防设置、滨海民众管理等多是取材于官方原始记录,相对于得自听闻或主观想象的同类记载具有更大的可靠性。但正史、政书等文献也有来自采访的内容,宋朝的市舶机构和中央礼宾机构官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询其道路风俗,及绘人物衣冠以上史官”(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天圣九年正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52页。,成为撰修国史的重要材料。官修文献还常取材各类私人著述。以《宋史》为例,其史料虽以宋朝实录、国史为主,但也兼采官、私文献,甚至广搜“杂书野史,可备编纂”,《文昌杂录》《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萍洲可谈》等都是修撰《宋史》的史料来源。(8)[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203册,第551a页。《诸蕃志》也是《宋史》的重要史源。以《宋史·阇婆国传》为例,该传如同《宋史》其他“外国传”一样,记载海外信息时为显示华夷之辨,最为关注的是两个方面的信息:朝贡、风俗。四夷朝贡可以营造王朝的正统地位,道里辽远更可显示四夷入贡之诚,风俗则可以显示奇异落后的夷狄“非我族类”,华夷有别。《宋史·阇婆国传》叙述阇婆国社会风俗部分共513字,其中442字直接取自《诸蕃志》,27字出自庞元英《文昌杂录》。(9)黄纯艳:《中国古代官方海洋知识的生成与书写——以唐宋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第175—184页。
私人著述也同样可能存在或因着意书写,或因主观选择,或因间接听闻而“失真”的问题。例如,赵汝适对于从海商处采访所得信息“删其秽渫,存其事实”,撰成《诸蕃志》时,就是对信息的处理和选择,该书保存的海外各地具体商业信息基本是海商的亲身经历,也是官方文献所缺乏的信息,而其所记某某国自宋初以来历次“朝贡”则显然是赵汝适根据宋朝官方记载做的补充,身处南宋的海商不可能详述某国两百年来历次“朝贡”。其他私人著述的类似现象,特别是作为量化的数据,下文将再论及。因而不同类型文献各有其特点,但在用以讨论具体问题时对其史料的性质则都需加辨析。我们以“南海Ⅰ号”在宋代海船中的等级大小问题为例,略谈辨析史料性质对于讨论“南海Ⅰ号”相关问题的重要意义。
“南海Ⅰ号”的绝对尺度已有科学的测量,即最大宽度为9.7—10米,残长22.1米,按宋准尺计(每尺为31厘米),梁宽约合宋制3.1丈。该船在宋代同类海船中属于什么等级,已有研究存在不同看法。叶道阳认为,“结合文献与考古发掘的沉船尺度,我们可以作相关的推测,基本上可以认为‘南海I号’属于宋代中等偏大的一条远洋贸易商船。”(10)前引叶道阳:《“南海Ⅰ号”沉船反映的宋代海上生活辨析》。赵建中也认为“南海I号”“在宋代算是中等规模的大船”(11)赵建中:《南海一号展现的宋代单体船舶水平》,载《岭南文史》2015年第3期,第23—28页。。黄纯艳则认为“南海I号”在同类海船中属于大型船只。(12)前引黄纯艳:《舶商与私贩:<“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贸易史解读》。“南海I号”的大小涉及对宋代海船种类和等级的认识,而其背后更重要的是判断其大小所依据史料的性质。
叶道阳所根据的史料是《梦粱录》所称:“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13)前引叶道阳:《“南海Ⅰ号”沉船反映的宋代海上生活辨析》;[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1页。赵建中则以下列三条记载为参照,即宋神宗和宋徽宗朝所造“神舟”、南宋大海船“深阔各几十丈”(实即《萍洲可谈》卷2所言“舶船深阔各数十丈”),以及《岭外代答》形容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尺,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14)《岭外代答校注》卷6,《木兰舟》,第216—217页。。这些记载可以反映宋代海船的概貌,而难以作为精确数据,特别是难以作为判断“南海I号”大小的准确数据。《梦粱录》是作者吴自牧对临安往日“繁华”的追忆,其对海船大小的描述也是主观记忆。宋代官方统计海船大小的标准是梁宽(又称面阔),官府对民间海船实行普查和征调时都按梁宽登记和分类。南宋海防征调民船时,因为梁宽小于一定尺度的船只难以用于海防。明州一带海船一丈以下为“不堪充军需者”(15)[宋]梅应发等:《开庆四明续志》卷6,《三郡隘船》,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91页。,征调的标准是梁宽一丈以上。“明州上下浅海去处,风涛低小”,而“福建、广南海道深阔,非明海洋之比”(16)《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30页。,征调海船的标准是一丈二尺以上。宋代内河船以“料”计算船只大小,但不能作为计算海船大小的依据(见下文论述)。
《萍洲可谈》关于航海和海船的信息是作者朱彧记录其父亲朱服的听闻,并非亲历或官方档案,所言海船“深阔各数十丈”,显然远远超出了宋代海船规模,不能作为宋代海船的实际尺度。徐兢所言“客舟”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已是大型海船。史籍所载宋代最大海船“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17)[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虞云国等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的“神舟”也不可能“深阔各数十丈”。《岭外代答》对木兰舟的记载也只是形容其大,而非实际尺度,也无可与“南海I号”比较的数据。三倍于“客舟”(梁宽2.5丈)的“神舟”虽其大小也是一个概说而非具体尺度,但长、阔大于“南海I号”(梁宽3.1丈)应无疑。因而以“神舟”为参照,称“南海I号”在宋代为中等海船,或中等偏大海船,并无问题。“神舟”无疑是宋代最大的海船。但是,“神舟”在宋代是特例,而非实际海洋生产、贸易或海防所用船舶。“神舟”曾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和宋徽宗宣和年间两次打造,共仅4艘,专作出使高丽的座船,特别是宋徽宗朝打造的“神舟”较宋神宗朝所造“大其制而增其名”(18)《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第129页。,是朝廷为耀威于域外,规模装饰尽于极致,即使由国家财政支出也难以持续,南宋已无财力和动力再打造这样的“神舟”。
南宋海船实行严格的普遍登记制度,“凡邑之有舟者不问大小,例皆根刷”(19)[宋]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3,《奏行周燮义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续修四库全书》第4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每岁遇夏初,则海船案已行检举。不论大船小船,有船无船,并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调查登记的目的主要是便于征调船只和船户管理,因而“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井然著为成式”。如上所述,浙东海防征调的标准是梁宽一丈以上船,因而按梁宽一丈区分,作两大类登记。嘉熙间明、温、台三州在“二三千里之海隅”逐一调查登记,得一丈以上海船共3833只、一丈以下15454只。(20)《开庆四明续志》卷6,《三郡隘船》,第5991页。里,旧制计量单位。福建则以梁宽一丈二尺为界分别登记,同时对梁宽一丈或一丈二尺以上船再划分等级。黄纯艳已指出,南宋海防征调福建民船,可以起征梁宽一丈二尺为中等船,大型船统归入“二丈一尺以上(船)”,雇用民船时分等标准是“上等船面阔二丈四尺以上,中等面阔二丈以上,下等面阔一丈八尺以上”(21)前引黄纯艳:《舶商与私贩:<“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贸易史解读》。。将“南海I号”放在同类南宋民间海船中才能准确地理解其在南宋海船中的等级大小。梁宽3.1丈(宋制)的“南海Ⅰ号”在宋代当属大型船。在文献记载中,面阔三丈的南宋福建海船仅见左翼水军“面阔三丈、底阔三尺,约载二千料”(22)《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第7130页。战船,浙东海船梁宽三丈以上者也仅见一例,即宝祐六年征调民间“大料船共二十四只”,海防番期结束时其中二十三只放回,“惟王绍祖一船面阔三丈五尺”,被申奏朝廷,扣留不放。(23)《开庆四明续志》卷6,《三郡隘船》,第5995、5996页。面阔三丈五尺当是难得的大型海船,方需申奏朝廷才能留用。考古发现的南宋海船泉州湾南宋海船和华光礁一号梁宽都在3丈左右。这应如《萍洲可谈》卷2所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船大人众则敢往”。(24)[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李国强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南宋往南海诸国从事远洋贸易的海船多为大型海船。讨论“南海Ⅰ号”在宋代海船中的等级大小本身是一个相对性问题,根据确定的比较对象不同而有不同判断。本文举此为例仅欲说明讨论“南海Ⅰ号”问题时对所用史料性质的辨析十分重要,惟其如此,才能准确地将“南海Ⅰ号”还原到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
二、制度背景与“南海Ⅰ号”研究
“南海Ⅰ号”是从其历史背景,具体而言,就是从宋代社会、经济和制度背景中驶出的一艘远洋商船,“南海Ⅰ号”的研究必须结合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制度背景。就制度而言,“南海Ⅰ号”研究涉及宋代远洋商船的发舶、航路、回舶、违禁品、人员搭载等相关制度。我们以存在较大分歧的“南海Ⅰ号”发舶港问题的讨论为例,检讨已有的不同观点及其依据,略述如何结合宋代相关制度厘清该问题讨论的路径。从发掘成果和现有研究来看,关于“南海Ⅰ号”发舶问题有几个基本共识:一是该船是一艘从中国出海,前往东南亚的远洋贸易船;(25)黄纯艳已经根据该船发现淳熙元宝为时间上限和南宋与南海诸国外交关系讨论了该船不可能为外国使团(参前引黄纯艳:《舶商与私贩:<“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贸易史解读》)有学者根据该船发现的最晚钱币为“嘉定通宝”和丙子年号,推测“南海Ⅰ号”的发船时间应在 1216年或稍晚(参前引杨睿:《“南海I号”南宋沉船若干问题考辨》),更可判断该船不可能为外国使团船,或以使团之名发舶船只。二是该船船型为福建海船;三是该船沉没于广州往东南亚的正常航线上;四是该船装货方式是下层主要装载陶瓷器、上层装载铁器、银器等。
对该船发舶方式和发舶港存在不同看法。杨睿认为,该船存在装载走私物品的行为。黄纯艳认为,根据该船装货方式推测,该船应是先装载陶瓷器等合法商品,从市舶港正常发舶,放洋后再装载铁器、白银等违禁品。(26)前引杨睿:《“南海Ⅰ号”南宋沉船若干问题考辨》;前引黄纯艳:《舶商与私贩:<“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贸易史解读》。也有主张该船可能不存在走私行为者,但尚未见正式研究成果发表。这可以作为我们判断该船发舶港的一个重要角度。现有对“南海Ⅰ号”发舶港存在广州发舶和泉州发舶的不同看法。赵建中认为,“从发掘出来的文物和船体造型分析,该船始发港口可以肯定是来自福建的泉州。”他还认为,“根据史料记载,在宋代,广东港的船少有向北航行的。所以综合分析,南海一号发自广州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来自福建泉州。”即根据该船装载的瓷器大多为福建及其邻近窑口,以及该船为福建海船,来判断其发舶港为泉州。杨睿根据“南海Ⅰ号”所载大宗船货瓷器主要来自福建窑口,推测其应“从福建市舶司所在地的泉州出发无疑”。黄纯艳则认为该船应是从广州港正常发舶,沿广州至东南亚的航线,经溽州放洋后沉没。(27)前引赵建中:《南海一号展现的宋代单体船舶水平》;杨睿:《“南海I号”南宋沉船若干问题考辨》;黄纯艳:《舶商与私贩:<“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贸易史解读》。已有研究尽管有分歧,但不论认为其是否存在走私行为,也不论主张从泉州发舶,还是从广州发舶,都认为该船是经过市舶港口正常发舶。
这就使得对其发舶问题的讨论必须考虑相关制度背景,以其是一艘从市舶司港口正常发舶,下层装载合法商品、上层装载违禁品,前往东南亚等地贸易的中国商船,沉没于广州往东南亚贸易航线放洋点溽州之外,这些基本特点为基础,充分结合与这些特点密切相关的南宋贸易制度,即贸易公凭制度、违禁规定、检空和放洋制度、回舶制度。第一,是贸易公凭制度。该船既然是从市舶港口正常发舶,则必已申领贸易公凭。不论近海贸易,还是远洋贸易,都必须申请贸易公凭,公凭登记了船舶情况、人员姓名、货物清单、贸易目的地等信息,并附录市舶条法,由市舶司所在地相关官员签署。如崇宁四年李充公凭开篇即是“据泉州客人李充状:今将自己船一只,请集水手,欲往日本国博买回赁,经赴明州市舶务抽解,乞出给公验前去者”,接下来登载全船69人姓名和全部货物清单。(28)《朝野群载》卷20,《异国》;[日]黑板胜美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东京:吉川弘文馆,1938年,第452—453页。在制度上,商人出海贸易是点对点的管理,如李充从明州发舶,往日本贸易,再回明州接受抽解。近海贸易也是如此。商人欲往近海某州贸易,“须于发地州军先经官司投状,开坐所载行货名件、欲往某州军出卖”“官司即为出给公凭,仍备录船货。先牒所往地头(贸易目的地),候到日点检批凿公凭讫,却报元发牒州”(29)[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9—890页。。管理方式是以公凭为验。“南海Ⅰ号”作为正常发舶的商船,必申领贸易公凭,并接受查验。
第二,是贸易禁令。宋代制定有严格的贸易禁令,一是贸易地区的禁令,北宋禁止商人往辽朝境内和接近辽朝的登州和莱州等地贸易,南宋禁止商人从海上往金朝贸易,两宋都始终禁止本国商人前往交趾贸易,一度也禁止往高丽贸易;二是贸易商品禁令,军用器甲及其制造原料,如铜、铁、箭杆、牛皮、筋角、鳔胶等都被禁止,金、银、铜钱等贵金属和货币也禁止出境。违反禁令,会有罚没船物,甚至处以徒刑,还制定了相应的告赏制度。“南海Ⅰ号”除非是获得特许,如装载回赐的“朝贡”使团(如上所论,根据南宋“朝贡”状况,显然不是),则出港时和放洋以前必受禁令的查验和限制。
第三,是检空和放洋制度。检空即商船出港前,市舶司和港口所在地地方政府联合派员上船检视,地方政府所派是与市舶贸易事务无关的“不干碍官”,清点人、船、货物,检查是否装载违禁物品。检空完备后“遣巡捕官监送放洋”(30)《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4页。,商船由检空官员监视护送,“至海口,俟其放洋,方得回归”(3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第4215页。。泉州港发舶的船只,在岱屿门放洋,“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32)《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第112页。,经七洲、昆仑、沙漠等洋到东南亚。岱屿门在泉州晋江入海口,“岱屿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称为岱屿门,乃近城控扼至要之地”。岱屿门沿海巡防严密,“巡绰海道,合令诸寨分认地界”(33)[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74册,第130b、131b页。。广州港发舶的商船在溽州放洋,“溽洲有望舶巡检司”“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34)《萍洲可谈》卷2,第148页。。所谓放洋,即径直进入深海航线。从市舶港发舶的“南海Ⅰ号”必然在被监送放洋后方有机会大量装载违禁品。
第四,是回舶制度。海商申领公凭出海贸易,“回日许于合发舶州住舶,公据纳市舶司”(3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第4207页。。必须到申领贸易公凭的市舶司所在港接受抽买,并缴回公凭。上举李充申请公凭状已说明“(回日)经赴明州市舶务抽解”。李充发舶时间是崇宁四年,其公凭所附市舶条法规定海商回舶“于非元发州舶者,抽买讫,报元发州验实销籍”(36)《朝野群载》卷20,《异国》,第455页。。但这条规定已于崇宁五年诏令废罢:按元丰三年旧条,发舶往来南蕃诸国船只回舶能赴原发舶港抽解,“今则许于非元发舶州住舶抽买。缘此大生奸弊,亏损课额”(3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第4207页。,恢复了元丰三年旧条。南宋时仍实行回原发舶港抽解的制度。隆兴二年还重申:“三路舶船,各有司存。旧法,召保给据起发,回日,各于发舶处抽解”(38)《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一》,第591页。,三路市舶司仍照旧法施行。只有缴回公凭,接受抽解后,才能合法销售贩回的商品,“未经抽解,敢私取物货者,虽一毫皆没其余货”(39)《萍洲可谈》卷2,第148页。。“南海Ⅰ号”申领公凭正常发舶,方能在回舶时合法进入国内市场。
作为一艘从市舶港正常发舶的商船,只有充分考虑上述制度因素,才能更好辨明“南海Ⅰ号”的若干问题。仅用“南海Ⅰ号”为福建海船或所载商品多为福建及其邻近地区出产,尚不能充分证明该船从泉州发舶。福建是宋代海上贸易风气最盛、海商最活跃、海船质量最高的地区,已成为当时海洋航行和贸易的代表。政府使团征调出使海船、招募为两国间官方传递信息者,乃至刺探外国讯息者,都首先想到福建商船和商人。所以福建商人和福建商船不仅前往东南亚,也遍及高丽、日本。在高丽和交趾的国都还多有福建商人留居和做官。上文言及的徐兢使团征调的六艘“客舟”就是福建商船,成寻自日本来宋朝即搭载福建商人船舶,而前往高丽和日本必从明州(庆元府),而非泉州发舶。福建商人和商船往南海诸国贸易既可在泉州申领公凭,也可在广州申领贸易公凭。所以“南海Ⅰ号”为福建海船并不能成为其必从泉州发舶的铁证。
同样,船载商品也难以作为判定该船发舶港的有力证据。商品可以通过近海市场和内陆市场流动。内陆市场自不必说,不仅瓷器、丝绸,而且金、银、铁、铜钱等都可以在国内市场流动。而且福建与浙东因海上贸易发展,沿海地区已形成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依赖浙西和广南粮食的输入,构成互补性的市场关系。福建与两浙和广南沿海地区之间有着稳定而频繁的近海贸易。因而,讨论其发舶港问题时,将“在宋代,广东港的船少有向北航行的”作为其从泉州港发舶的依据并不妥当。(40)黄纯艳:《论宋代的近海贸易》,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84—96页;前引黄纯艳:《舶商与私贩:<“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贸易史解读》。难以从“南海Ⅰ号”所载福建及其邻近地区所产商品而肯定其从泉州发舶,何况该船也载有广南地区的瓷器等商品。
因而,要证明“南海Ⅰ号”从泉州发舶,仅以该船是福建海船及装载大量福建及其邻近地区商品为证据,显然难以构成充分的证明力。如果认为该船从泉州发舶,就需要回答其为什么在领取公凭后冒着被查没的风险,离开泉州至东南亚的航线,远航到阳江海域沉没。该船下层装载合法商品,最大的可能是领取贸易公凭,通过港口检空和验证公凭,从市舶港正常发舶,离港后装载违禁品,这样既可获取违禁品高额利润,也可保障其回舶后在国内正常办理抽买手续,合法销售其贩回的商品,在国外贸易时有可以避免被“掠非诣其国者,如请占婆公据而误入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的风险。即所谓既得遵守制度之便利,又获违反制度之厚利。
而且,从《诸蕃志》记载可知,中国海商在东南亚三佛齐、佛罗安、阇婆、麻逸等多国经常贩卖的商品即有金、银、铁(包括“铁鼎”)等,可见“南海Ⅰ号”运载的大量铁锅是当时中国销往东南亚常见商品。违禁品成为海外贸易常用商品说明走私行为的普遍存在。泉州一带发舶后装载违禁品的走私方式是常有的现象。泉州有走私铜钱者“积得现钱或寄之海中之人家,或埋之海山险处,或预以小舟搬载前去州岸已五七十里,候检空讫,然后到前洋各处逐旋搬入船内,安然而去”(41)[宋]包恢:《敝帚稿略》卷1,《禁铜钱申省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第 1178 册,第714页。。还有“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舟重风急,遂沉于海”(4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0,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24页。。该小舟当然不是去远洋贸易,而是运钱到海中某处,备商船检空放洋后装载。“南海Ⅰ号”若需发舶后再装违禁品,可以不必冒离开航线而被查禁的极大风险远赴阳江海域。“南海Ⅰ号”的发舶港和发舶方式仍是一个需继续讨论的问题。本文重新检讨对这两个问题的已有研究,是欲强调我们需要重视目前对该船作为一艘从市舶港正常发舶商船这一基本特点,考虑其所置身的制度框架。
三、发掘成果对历史文献的补充
不同文献资料的相互补充,形成拼合零散的“全”,为“南海Ⅰ号”研究提供了展开背景。“南海Ⅰ号”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制度和非制度因素对贸易的影响、贸易实际开展方式,是讨论“南海Ⅰ号”不能离开的背景。另一方面,作为一艘船体和船货都相对完整地得以保存的商船,是以往发掘的沉船未曾有过的,可以大大补充历史文献的缺失,其包含的船、人、货信息的丰富和完整将极大地推进造船史、贸易史、航海史、经济史、技术史、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的认识。
“南海Ⅰ号”对宋代文献记载的补充是多方面的,本文略举宋代海船载重量问题。“南海Ⅰ号”甲板以下船体基本完整保存,在现有发掘的宋代海船中绝无仅有,对研究宋代造船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宋代是中国海船三大船型形成的重要时期,“南海Ⅰ号”所代表的福船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远洋船舶,但文献记载并不能完全复原宋代该船型的所有细节,因而保存基本完整的“南海Ⅰ号”对研究宋代海船的结构及中国古代海船的技术演进是十分宝贵的样本,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上文论及宋代海船大小则按梁宽计,宋代内河船大小以“料”计。学界对船舶之“料”有不同解释。黄纯艳辨析各说,重加考释,认为“料”用来表示船舶大小时指一石米的容积,作为船舶力胜的“料”是指有效载货容积,而并非全船总排水量或总载重量。(43)黄纯艳:《宋代船舶的力胜与形制》,载《厦门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45—56页。料,与下文的石、斛、斤均为旧制计量单位。一者宋代漕运与其他朝代一样,以粮食为主,“料”的计算直接从粮运而来,衡量一船能容载多少石米。其次内河船征收力胜税,不论装载何物,按船舶有效载货容积表示的装载能力征税,不载货的船征收空船力胜税。“料”与“石”“斛”在表示内河船载重时可相互代替,也成为人们指称内河船大小的习惯概念。
海船言及力胜单位“料”的情况有二:一是近海战船,如建康府造“三百料四橹海船”(44)[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39,《战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83页。,二是说到某船梁宽后估计其力胜,如福建左翼水军海船,“面阔三丈、底阔三尺,约载二千料”;高丽使团所雇“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45)《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第129页;《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第7130页。。其实都是用衡量内河船的习惯概念描述海船大小。如上所述,官方在统计和征调民间海船时都是以梁宽为标准。因而我们所见文献记载所呈现的海船大小的等级系列是不同梁宽。但不同梁宽对应多大载重量,史籍并无记载,所见的若干“料”都是以内河船概念的大略描述,因而会出现同一船型、不同梁宽的海船被描述为相同的“料”数,即徐兢使团所雇梁宽“客舟”“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而南宋福建左翼军战船“面阔三丈,底阔三尺,约载二千料”。
首先,并不能简单地用有效载货容积单位“料”折算今制的载重量,即不能简单用一“料”按宋制一石米92.5宋斤,合今制约118斤,来换算为今制船舶吨位。同样的有效载货容积(净吨位)因船舶形制、吃水线长宽、吃水深度、方形系数等的不同,也存在差异。有学者根据《梦粱录》中“料”的记载折算海船载重,如前引叶道阳文根据《梦粱录》所载海船五千料、二千料至一千料、一千料以下分别折算其载重为300—600吨、200—400吨、200吨以下,并相应地定为大、中、小型船。前引赵建中文认为,“南海Ⅰ号”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近800吨,出使高丽的“神舟”估计可装载2万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梦粱录》作者对海船的描述本身为一概观,非精确数据,更不能以其折算载重吨位。徐兢对“神舟”长、宽、载人皆“三倍于客舟”的描述也是一种概说,其“三倍”之数不一定为实指,即使将其折算为力胜六千料,“客舟”二千斛的力胜也是徐兢比照内河船习惯的估计。实际上,从现有历史文献难以获得南宋海船的准确载重数据以及其他完整参数。而“南海Ⅰ号”甲板以下船体基本保存,可以获得其船体的各种主要数据,对我们认识南宋福建海船,包括载重量等多种技术特点提供了文献记载所缺乏的依据。
“南海Ⅰ号”现存文物看似是缺失“人”的若干静物,但其相对完整地保存下的货物、航行和生活等相关文物构成了系统的信息链,对于揭示南宋商船的人员构成及生活方式可与文献记载相互补充。文献碎片式地记载了出海的商船会有哪些人,如何组织,如何分工,如何生活,但并不足以系统展现一艘远洋商船生活的完整细节。已有学者根据文献研究指出,海船人员可分为操作人员和搭乘人员,“南海Ⅰ号”这样规模的海船需要的操作人员超过60人。(46)前引黄纯艳:《舶商与私贩:<“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贸易史解读》。一种可能是,该船也如李充船那样,船主自任纲首(李充既是船主,又是纲首),其他68人皆为其雇佣的梢工、杂事、水手。更大的可能则如《萍洲可谈》所言“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47)《萍洲可谈》卷2,第149页。,搭乘人员的主体是商人。而且人、货各自相对独立“抽解之时各人货物分作一十五分”,其中“纲首一分,为船脚糜费”,而且市舶司对纲首货物和一般商人的货物抽解比例不同,“纲首杂事十九分抽一分,余船客十五分抽一分”(48)[宋]罗濬等撰:《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54页。。“南海Ⅰ号”这样的大型海船必有搭乘人员。那么,可能会有哪些搭乘人员呢?
除了“分占贮货”的国内商人,文献记载还可知,宋朝商船也时见搭载各色外国人。一是僧人,如日本僧人成寻和高丽僧人义天都是搭载中国商人船舶来宋,回国也是搭乘商人船舶。而且海商相信僧人可以帮助祈祷航行顺利,故“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难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49)《萍洲可谈》卷2,第150页。。成寻在海上航行时就每日念经上万遍。二是使节和外商,宋朝允许本国海商搭载外国朝贡使节和贸易商人,即 “诸蕃愿附船入贡或商贩者听”“许舶客专擅,附带外夷入贡及商贩”(50)[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卷35,《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 第889、995页。。就“南海Ⅰ号”而言,虽其所处的南宋嘉定以后已无海上朝贡往来,但搭载外国商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三是遭遇海难的人,宋朝对来华贸易遭遇海难的外国人给予渡海程粮,安排遣返本国,遣返的方式是搭乘商人的顺风船,“伺便舟还之”(5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8,绍兴四年七月辛未,第1479页。。四是“鬼奴”,即海外黑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52)《萍洲可谈》卷2,第151页。,鬼奴有多种,昆仑奴为其中一种,广南一带多有蓄养鬼奴者,特别是航海之家,因鬼奴善于潜水修船,航海时喜带鬼奴于船上。杨睿通过对“南海Ⅰ号”器物风格,特别是发现漆盒内饰物,以及人骨检验结果的分析,认为该船上有搭载外国商人和黑人的可能性。(53)前引杨睿:《“南海I号”南宋沉船若干问题考辨》。考古成果和文献记载结合,有助于进一步探讨该船是否有“蕃人”及船上可能搭载的“蕃人”的身份。
已有学者利用“南海Ⅰ号”发现的食品、生活器具分析了船上人员的生活状况。(54)前引叶道阳:《“南海Ⅰ号”沉船反映的宋代海上生活辨析》。该船发现的食品有米谷、酒类,多种瓜果、香料,以及羊、鸡、鹅、猪、牛、鱼等的骨骼,可以说印证了《岭外代答》描绘的海上生活:“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55)《岭外代答校注》卷6,《木兰舟》,第217页。的记载,但又远远超过了这寥寥数语的信息。该船发现的食品种类和数量,为我们了解当时海船上的食物结构提供了历史文献缺乏的详实细节。各种用途的生活器具,展现了船上人员对食物加工、储存的方式,以及人们日常起居等诸多方面的状况,都可以补充历史文献的不足。随着船载文物全部清理统计完备,会有更多这样的细节被发现。除了饮食生活外,行船临时社会的秩序构成、作为航海生活重要内容的信仰祭祀等都可能得到更为具体的揭示。这些信息不仅对研究一艘海船的日常生活,而且对研究南宋时期的社会生活史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南海Ⅰ号”所载近20万件货物更是丰富的学术宝库。首先,该船保存基本完整的货物呈现了一艘海外贸易商船基本的商品结构,通过文献的零散记载所能列举的种类甚多的海外贸易出口商品,大部分都出现于该船货物中,但也可相互补充,例如《诸蕃志》记载中国海商兴贩的商品除了“南海Ⅰ号”的大宗商品陶瓷、铁器、金银、酒、丝绸等外,还有香料和药材,如脑麝、檀香、干良姜、大黄、樟脑、川芎、白芷、朱砂、鹏砂、砒霜;用具,如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皮鼓;其他金属,如铅、锡,以及如米、糖、绿矾、白矾、琉璃珠、琉璃瓶子、网坠牙、臂环、胭脂等物品。而“南海Ⅰ号”各种货物的数量和装货方式较文献记载仅见种类的列举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动态的信息。一百余吨铁锅、铁条,数量庞大的来自不同产地的瓷器,为技术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广阔的空间,需要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共同研究。
结语
随着“南海Ⅰ号”发掘工作的结束,包括船舶在内的各项文物完整数据资料的发布应指日可待,必将极大地推进宋代贸易史、造船史、航海史,以及相关技术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包括本文讨论所及的多位学者,根据已发布的部分发掘成果做了很有意义的探索,这些研究不仅提出了对“南海Ⅰ号”发舶问题、船上生活、船体研究等若干看法,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推进“南海Ⅰ号”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现有研究可谓是“南海Ⅰ号”全面研究的序曲,为了更好地推动“南海Ⅰ号”研究,对现有研究的观点、路径、史料做一检讨是十分必要的。
“南海Ⅰ号”研究必然需要多学科的合作,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视角。历史文献与发掘成果的结合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南海Ⅰ号”作为一个保存相对完好的海船个体案例,其完整的船体和丰富的文物,可以极大地补充历史文献的记载不足。我们必须重视和发掘“南海Ⅰ号”这一重要学术宝库的价值,将现有基于历史文献的若干相关问题研究推向深入。另一方面,“南海Ⅰ号”作为一艘从南宋历史背景中驶出的远洋商船,对其研究中必须充分利用历史文献,结合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制度背景。这一过程中对相关史料性质的辨析、对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十分重要。离开了对史料性质和历史背景的准确理解,对“南海Ⅰ号”的认识就可能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