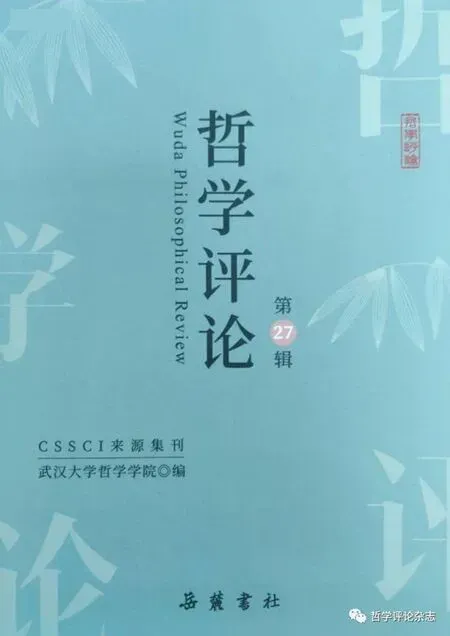王夫之“夷夏之辨”的两种主体批判
——以其对许衡的评论为中心
2021-11-25古宏韬
古宏韬
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的民族思想,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对当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观念形成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较早关注王夫之民族思想的近代学者,注意点还在古典的华夷矛盾上,他们将其作为克服清朝统治影响的思想资源。[1]可以参考:嵇文甫的《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时代中国》1943年第4期),刘国刚的《船山〈黄书〉的民族思想》(《周行(长沙)》1936年第1期),张永明的《关于王船山民族思想之一斑》(《时事半月刊》1940年第20期)等文。随着材料和认识的积累,研究者们在单纯的批评之外,看到了王夫之民族理论的一部分客观历史价值。如萧公权、萧萐父说其强调华夷的差别,主要是因地域不同导致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并总结出历史发展由野蛮而趋于文明的大方向;冯天瑜指出王夫之看到中华和夷狄此退彼进、文化中心迁移的事实,由此认识到文化中心并非永恒不变。[1]可以参考: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九卷《王夫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萧萐父、许苏民的《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冯天瑜的《王夫之创见三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现代对王夫之民族思想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并提炼转化为政治思想,成果比较丰富。[2]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水原重光的《王夫之的民族思想》(船山学社,1982年),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五章《王夫之的社会进化论》(东方出版社,2008年),余明光的《论王夫之的民族思想》(《中国史论集: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年),谷方的《论王船山的民族思想》(《中国哲学》1983年第10期),龚鹏九的《也谈王船山的民族思想》(《船山学刊》1985年第2期),胡发贵的《论王夫之夷夏观》(《学海》1997年第5期),张学智的《王夫之〈春秋〉学中的华夷之辨》(《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2期),彭传华的《王船山民族思想基本观点概览》(《民族论坛》2010年第8期),吴根友的《王夫之“文明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1期),等等。不过事实上,王夫之在讨论“夷夏之辨”的民族问题时,其批判牵涉到儒者、商人阶层等主体,转入对人之主体性的讨论,并反映出某些客观存在的时代现象,这在他对元代许衡的议论里尤其明显,而前人尚未充分关注到这方面。传统的“夷夏之辨”,自先秦孟子、汉代公羊学的发端后,需要在各种新的历史主体的语境下不断诠释,在元明清变局之时同样如此。本文从王夫之对许衡的评价切入,尝试考察其民族思想对于儒者和商人阶层的态度,审视在“夷夏之辨”投射下不同社会主体于明清之际的历史定位,以及揭示他们如何与民族兴亡发生逻辑关联。
一、许衡与王夫之:两种王朝遗民的命运和思想
许衡和王夫之,一个是元初的金朝遗民,一个是清初的明朝遗民。他们同样经历了亡国亡种的历史危机,都有着遗民的身份。但他们的命运与思想,却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两个方向,而那些分歧也构成了王夫之批判许衡的思想根源。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又称鲁斋先生,生于金朝统治下的北方中国。当时正值北方蒙古人取代金朝崛起,并逐渐吞并南宋的历史时期,许衡便成为金朝遗民。他将发扬程朱理学当作自己的学术理想并予以实践,开创了中原朱子学传承的新局面。在野的许衡引起了蒙元统治者的关注,而他也认为在蒙古政权中推广儒学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于是接受了元朝的国子祭酒和太史等职位,并一度成为太子的太傅。他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对元朝太学的组织和教学都有重要贡献。
许衡给战乱后的中国社会指出了文化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对异族大一统的元朝而言,强调了汉民族政治、学术文化的重要意义。他在给元世祖忽必烈的进言中说:“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有汉法,可以长久……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宜热,反之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1][元]许衡:《许衡集》卷7《时务五事·立国规摹》,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类似的这些言论,为元朝推行汉族政治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后人一般称之为“用夏变夷”。他亲自在太学中招收蒙古学生,讲授古典,还专门为异民族修订了一套基础课程,这种形式甚至影响到了朝鲜等地区的儒学传播。由此可见,许衡对中华文化重建的影响深远,且其影响已广布天下,遍及各蛮夷、异族之地了。
后世对许衡思想的印象,还常涉及他的“治生”理念。许衡曾告诫学者:“……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2][元]许衡:《许衡集》卷13《附录·通鉴》,第303页。许衡的这些话,事实上肯定了儒者参与农耕乃至商业活动的正当性,并因他在元代思想界的影响力广为人知,成为明清时人广泛讨论的一种话题。
异族政权给予了许衡很多褒奖。元世祖在诏书中称赞他“天资雄厚,经学精专,大凡讲论之间,深得圣贤之奥”。[3][元]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首《元朝诏诰》,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在他去世后,元朝不仅命欧阳玄专门为他撰写了歌功颂德的《神道碑》,称其为“不世之臣”,还先后追封他为正学垂宪、佐运功臣、魏国公等,并与宋代名儒一同从祀孔子,尊荣之极堪比朱熹。[1][元]许衡:《许衡集》卷13《附录·神道碑》,第286—295页。到了清朝,康熙皇帝同样对许衡评价很高,他出于表彰理学的目的,将许衡的成就与宋代大儒真德秀的功勋相提并论。[2][元]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首《元朝诏诰》,乾隆五十五年刻本。与此相对地,社会和思想界对他的评价却常常褒贬不一,明代以来人们对他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赞扬许衡“用夏变夷”的历史功劳;二是讥刺他“失身元廷”,委身服事蒙古人,“有害名教”,以至于其著作思想也统统不可取;三是认为他在元朝出仕,却不能彻底移风易俗,终究于事无补。[3]此处可参考《鲁斋遗书》卷14《先儒议论》中的一些评论性文章。如:《清江彭纲题》:“鲁斋许先生,为元一代大儒。遭逢世祖致身通显,而其成己成物、用夏变夷之功,自有不可泯者。或者訾其失身元廷,殊非公论。”《郡人何瑭题河内祠堂记》:“独近世儒者,谓公华人也,乃臣于元,非《春秋》内夏外夷之义,有害名教。……或有谓公虽臣元,亦不能尽变其夷狄之俗,似无所补者,窃以为不然。”《郑王稽古千文叙》:“或曰:‘鲁斋仕元之非士君子’,讥之以谓出处既不可取,而政事著作亦不足取也。”这些都是明清两个朝代的人对许衡常见的历史评价。在评价风向上,王夫之明显比较倾向社会上的第二种论调,对他的民族立场和思想质疑。
作为清初遗民民族思想的代言人之一,王夫之的民族立场大体上比较鲜明,如他的《读通鉴论》中就有很多非常激进的华夷论。他认为,作为异族的夷狄根本不配称为人:“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也,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4《汉昭帝》,《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10年,第155页。因此,夷狄谈不上拥有人类的伦常道德,不可能受到感化或改造,“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谊足以动诸侯,非可以动夷狄者也”。[5][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4《汉宣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169页。这种丝毫不留余地的矛盾对立关系,可以认为是王夫之的绝大多数民族思想理论的基调。当然,他民族观的时代印记显而易见,是基于明亡清兴的历史背景而成立的。其思想的形成伴随着清军入主和各种抵抗运动,因此对斗争、冲突的强调在所难免。他本人自明崇祯帝死去后辗转南明,参与民兵抗清,并坚决不剃发、不向清朝妥协,最后遁入湖南的山野中治学度过余生,未曾出仕清朝。这段略显悲壮的遗民生涯,是他民族思想的最好注脚。
许衡和王夫之在面对民族危机时的不同反应及人生结局,使他们在对民族大义的理解上截然相反,也导致王夫之注定不可能跟许衡达成思想上的和解。同时,王夫之还有意利用了许衡备受争论的遗民形象,给他对特定主体的批判打通了一条路径。这些主体批判,最终都是为王夫之确立汉民族本位思想的“夷夏之辨”立论服务的。
二、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第一种主体批判:儒者
在对许衡民族立场的评价和批判中,有关“儒者”这一重要社会群体的话题,是王夫之首要关注的重点。儒家学者,实际上可以指代为拥有理性、知识的广大士族阶层,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是创造和维护社会理想的社会中坚力量。同时,开启“华夷”分别的立场,以此确认大一统国家文化自主、自尊性,并承担“夷夏之防”舆论先锋的,也正是儒者群体。美国学者安乐哲认为,儒家民族观念的认识方式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延伸,即所谓由内至外、“推己及人”。[1][美]安乐哲:《儒家思想与实效主义》,[美]安乐哲著,温海明编:《安乐哲比较哲学著作选》,孔学堂书局,2018年,第51页。而在此过程中,儒家将“内外”、“亲疏”、有德无德等矛盾与“华夷”矛盾构建成等价关系,儒家学者也强调通过自我修行德性来确立这种差异性。王夫之要通过“夷夏之辨”为汉民族中心理论张本,首先就不可能绕过对儒者的历史主体定位的辨析。
王夫之常在批判异民族侵略华夏的问题时提到许衡。他曾列举了一些自己心目中“失身”于夷狄的儒家官员,如下列《读通鉴论》中的文字所示:“贾捐之、杨兴、[崔浩、]娄师德、张说、[许衡],一失其身,而后世之讥评,无为之原情以贷者,皆钦之类也。”[2][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5《汉成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184页。所缺失的人名按校勘记补正。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许衡、崔浩的名字被加上了括号,因为这里属于后人辑佚而来的内容。今天流行的《读通鉴论》版本,其底本主要以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负责刊印,刘毓崧、张文虎参与校雠的金陵刻本《船山遗书》为主。这很可能是当时在清廷掌握文化话语权的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注意到王夫之所述及的几人中,许衡、崔浩等人恰好是以汉人的身份为异族政权服务的儒者。如果他们的名字贸然见诸文字,可能会招来清朝统治者的非难,于是只好删去。由此也可以看出,清代思想界在议论民族问题方面始终存在着强烈的紧张氛围。
这仅是王夫之谈论到许衡的其中一段文字,似乎还没有特别严厉地指责其所作所为。而他在另一段评论中,则毫不留情地攻击了许衡:“貌君子而实依匪类者,罚必重于小人。圣人之学,天子之位,天之所临,皆不可窃者也。使天下以窃者为君子,而王道斩、圣教夷,姚枢、许衡之幸免焉,幸而已矣。”[1][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5《王莽》,《船山全书》第10册,第207页。这里王夫之将元代的许衡、姚枢比拟为两汉之际的刘歆,刘对王莽政权阿谀奉承,许、姚两人则投靠元朝以求自保,极大败坏了天下的风气。显然他认为,元朝等异民族建立的政权,属于王莽篡逆自建的伪政权范畴,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也不适用于儒学名教中的“王道”政治理念。儒者有责任跟这样的政权划清界限,明确维护上古三代王道的政治立场,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他们绝不为异民族效力,否则将在后世受到严重的道德谴责。这段话证明,王夫之在攻击异民族政权的时候,通常是与对儒者社会责任的批判相互联系的。同时他还判断,异民族不可能真正接受汉人的法则,如认为“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诚,视宏之所为,沐猴而冠、俳优之戏而已矣”。[2][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6《齐明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616页。历史上如北魏拓跋宏的汉法改革等活动,在他看来是完全失败的逢场作戏,从根本上就不符合儒家的治国理想,并且斥辅佐异主推行汉法的儒者为耻辱,其实这就等于否定了许衡“用夏变夷”的一切努力,其评判标准非常严苛。
王夫之民族思想对儒者的批判,不仅限于许衡一人,还延伸到他对待一切儒学异端思想的方面。他认为,儒者的任务还在于严防异端思想的影响,“辟异端者,学者之任,治道之本也”。违背了先儒的教诲,与经典说法不一的内容,“乃所谓异端者,诡天地之经,叛先王之宪,离析六经之微言,以诬心性而毁大义者也”,全部都应当斥为异端。据此,他指责汉儒在放纵异端方面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认为汉代以来学术的真正问题“非文辞章句度数沿革之小有合离,偏见小闻所未逮而见为异者也”,[1][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7《后汉和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279—280页。不在于考据或家法的争论,而在于儒家自乱教化,为异端外道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汉之初为符瑞,其后为谶纬,驳儒以此诱愚不肖而使信先王之道。……儒者先裂其防以启妄,佛、老之慧者,且应笑其狂惑而贱之。汉儒之毁道徇俗以陵夷圣教,其罪奚复逭哉!”[2][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3《汉武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144页。逭字从辵,从官。《说文解字》:“逭,逃也。”《尚书·太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推及近世时,在元代许衡之外,他尤其反感宋代三苏、明代李贽等人的学术,说“论史者之奖权谋、堕信义,自苏洵氏而淫辞逞。近有李贽者,益鼓其狂澜而惑民倍烈”[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东晋安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524页。,大概有两方面的考量,一则是儒者自甘堕落、不讲信义,给佛教、道教思想自宋以降在思想界的广泛渗透提供了机会,严重打击了儒学思想的地位;二则是进一步联想到明朝灭亡之事,根据他的因果判断,李贽等人败坏社会风气的学术思想也难逃干系。
总体看来,王夫之对儒者的历史地位有很高的要求。他认为,儒者不仅要在道德水平上符合成为世人准则的圣贤之道,更应进一步摆正自身在政治、学术事务方面的立场。按照他的观点,人们很容易会导出一种结论,即代表华夏文化与异民族抗衡的核心历史主体,不是任何一个皇朝或者某位帝王,而是那个特定时代里的儒者群体。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不同的是,王夫之并不时刻在政论中强调“道统”与“治统”的紧张关系,但我们依然能从他的历史评论看到“道统”“治统”交替的思想线索。例如他曾说:“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恃,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5《宋文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568页。“道统”与“治统”、儒者与帝王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而异民族崛起的历史时期,就是中国“治统”衰微的时段。儒家维系“夷夏之辨”的精神力量,无非维系于“道统”“治统”两者之上,儒者不能有效掌握“治统”的走向,但有能力也有义务在“道统”建设中延续汉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王夫之认为,儒者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只能且必须挺身而出,担负起保护华夏文明的责任;他以此为基准判断,许衡等儒者的作为与其历史期望并不相符。这种自我约束和价值衡量的严格程度,甚至让人联想到近代高度重视群体社会责任的清教主义,只是王夫之思想的范畴中缺少宗教精神的因素,更多的是一种学者型的社会热忱。当代学界对许衡、李贽等人的评价已比较客观全面,王夫之强烈的民族思想,使得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认识有所偏颇,不过其思想主张和身为儒者的责任感仍有值得肯定的积极之处。
三、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第二种主体批判:商人阶层
王夫之的民族思想重视商人阶层的作用,但认为其意义基本上是消极的。商人阶层是他“夷夏之辨”所论及的又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体,且同样是透过许衡而受到批判。元明时期的中国,商业较以往更加繁荣,对内对外的贸易活动均颇为频繁,使得现代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无论“资本主义萌芽”论成立与否,商业与商人阶层在元明清时期的中国获得了空前发展,这是明确的事实。元代的国内外贸易发达,《元史·食货志》曾提到元成宗“勿拘海舶,听其自便”,元朝廷给予贸易自由,减轻商税和鼓励通商,建设各种大都市的商业区。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一起参与经商,同时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与中国互通有无,还产生了官商合营的“斡脱”等贸易形式,虽为国营,实则给商人提供了很大的利益和机遇;这些现象使民族、公私差异的界限在商业行为中变得模糊。明代南方各地的手工业繁荣,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这在今天很多学者的研究里已有阐述,成为对明代社会的共识。自皇帝、官员到基层士民,几乎无一不参与到商业活动中,特别是一般士族,将儒家文化知识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生活方式屡见不鲜,黄省曾《吴风录》说“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1][明]黄省曾:《吴风录》,杨循吉等著,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杂刊》,广陵书社,2004年,第178页。,就是对当时士商不分、追逐财富之风气的写照。王夫之在批判儒者的基础上,自然不会忽略士人在商业上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从其中“义利之辨”的角度上升至民族大义的问题。
从经营产业的方面而言,王夫之对许衡的治生观相当反感。如前文所述,许衡曾经鼓励儒者参与一定程度的农业和商业活动,以确保自己不至于生计艰难,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现实考量。王夫之却义正严辞地予以驳斥:“人主移于贾而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而廉耻丧。许衡自以为儒者也,而谓‘士大夫欲无贪也,无如贾也’。杨维桢、顾瑛遂以豪逞而败三吴之俗。”[2][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3《汉景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123页。在他看来,似乎在任何一种公私情境下,效仿商人阶层追求利益,都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负面行为。杨维桢和顾瑛都是元明之际的士大夫代表,不同程度投身于商业中,并且思想较为开放。但王夫之无视他们的积极影响,同列两人在许衡之后,将他们与王朝和地方社会的崩溃联系起来,试图证明商业是社会风气堕落的根源。这样严厉的批判,在王夫之的其他著作或言谈中也并不多见。
此后,王夫之特意独树一帜,在他的民族观中加入了商人批判的因素。如他曾分析:
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亟者也。乃其气恒与夷狄而相取,其质恒与夷狄而相得,故夷狄兴而商贾贵。许衡者,窃附于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为商,可以养廉。”呜呼!日狎于金帛货贿盈虚子母之筹量,则耳为之聩,目为之荧,心为之奔,气为之荡。衡之于小人也,尤其巧而贼者也,而能溷厕君子之林乎?[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东晋哀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503页。
这段话的内涵十分耐人寻味。据其理论来看,商人阶层竟然与夷狄源于相同的自然之气,性质上也属同类,由此推断,历史上夷狄兴起的时期必然有商人阶层的崛起。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史实和逻辑,事实上在王夫之本人的史论中,对商人的很多零散议论,较多集中在先秦战国时期等时代,如批评吕不韦等人的骄奢淫逸。仅就这些部分而言,我们难以推导出商人与夷狄的直接关系。因此,以上一段文字可以理解为专门针对元、明时期商贾的攻击,而其矛头直接指向了许衡;特别是,文中彻底否定了许衡赞同士大夫从商的意见,理由是儒者从商只会败坏心气,斤斤计较,离圣贤之道相去甚远。其实许衡原本的意思是有限度地赞成儒家士大夫治理产业,以维持作为学者的基本生活和尊严,同时在社会实践中落实“天理”,他本质上仍然认为商贾属于末业,这与王夫之所理解的“居官为商以养廉”显然有着较大的差别。在此,对于元明以来社会上商人阶层崛起、抢占儒家士大夫阶层话语权,同时传统的士人也受到利益鼓动投笔从商的普遍现象,王夫之似感到痛心疾首。他相信这些“堕落”的现象,能够说明异族的元朝何以迅速瓦解。而许衡正好在这个时期里提倡“治生”,似乎为新兴的儒商和市井商贾提供了理论保障,便理所当然成为王夫之的攻击目标。
紧接着上文,王夫之还进一步从义、利之辨的角度来说明商人和夷狄的关联:
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生于利之乡,长于利之涂,父兄之所熏,肌肤筋骸之所便,心旌所指,志动气随,魂交神往,沈没于利之中,终不可移而之于华夏君子之津涘。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类,防之不可不严也。夫夷之乱华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贾为其最。夷狄资商贾而利,商贾恃夷狄而骄,而人道几于永灭。[1][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东晋哀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503页。
他认为,商人和夷狄的最终目标一致,即追逐利益、放纵贪欲。并且他们的共同之处还在于,无法分辨“华夏君子”的义理,没有接受古典文化的熏陶,是不符合“人道”的禽兽之类,这两类人群会为了一己私欲互相勾结,共同破坏中华文明。夷狄与中国的矛盾、商贾与儒家思想的不可调和,归根结底都是义、利价值观念的冲突。因此,王夫之在这里提出的两组概念对立,“夷狄”对“华夏”,“君子”对“小人”,实际上就变成了同等互换的一种概念,不分彼此。事实上,由“君子小人”的“义利之辨”转化为“华夷”矛盾的理论,早在先秦时就已有端倪。[1]例如,孟子理解的华夷分别,根源在于人禽之辨,他认为无君无父、“仁义充塞”者即为禽兽,而夷狄正属于此种状态。称具体个人为禽兽是个体的范畴,称夷狄为禽兽则是群体的范畴。从他的“义利”“人禽”“华夷”论推广出去,又能涉及“王霸”“理欲”等几组关系的讨论,可见这些思想理路在逻辑上是互通的。“君子小人”属于基础伦理的讨论,“华夷”区分则属于社会种群的归类法,儒家将两者联系起来,是用伦理的力量在社会上建构种群本位的思想。而王夫之在此引用这种内在理路,又为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他试图在此警告明末儒者和统治者,除非始终对商人阶层保持紧张的警惕关系,钳制他们过分膨胀的欲望,不然就可能招致民族危亡的下场。这种论述不仅来源于王夫之对理学“天理人欲”观念的直接继承,更与明朝灭国时的社会情形关系颇为密切。晚明淫靡之风盛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清朝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并且外族的武装和生产物资也经常来自与中华的贸易往来,身为遗民的王夫之对此或有着深刻体会。据此也就可以理解,他对推崇实学的许衡等人为何痛恨至极了,并且这种不可调和的思想矛盾,进一步恶化了其对待阳明后学中一部分人的态度。
在明清之际,像王夫之这样异常激进地排斥商人的思想家已较为罕见,大部分学者在谈论商业活动时总会有所让步,或者直接默许士民从商。如王阳明被门人问及许衡的治生观,曾简略地回答:“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2][明]王守仁:《传习录校释》,岳麓书社,2012年,第32页。但当有人进一步追问何以“误人”时,他又有所保留地说:“但言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3][明]王守仁:《传习录校释》,岳麓书社,2012年,第195页。他承认了许衡所说的儒者参与商业活动的正当性,只是稍微强调了治学与治生的先后优先顺序。王阳明的这种态度,跟阳明后学和清代实学思想的主流是一脉相承的。清初学者陈确明确赞同了许衡的观点,专门撰写文章指出:“唯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天下岂有白丁圣贤、败子圣贤哉?鲁斋此言,专为学者而发,故知其言之无弊,而体其言或不能无弊也。”[1][清]陈确:《陈确集》卷5,中华书局,1979年,第155页。沈垚也曾表达了类似见解。余英时注意到这些人对许衡治生观的肯定,认为他们提出“士必须先有独立的经济生活才能有独立的人格,……重视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实可看作儒家伦理的一种最新的发展”,在承认士人的世俗欲望的同时,也模糊了儒者与商人阶层的界限;以此作为铺垫,他发展出明清“新四民”的社会构成说。[2]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3—454页。赵国洪对余的表述有所商榷和修正,为确证许衡治生说对元明清三代的影响,补充了更多文献材料。[3]参考:赵国洪:《许衡“治生说”与明清士商观念:与余英时先生商榷》,《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但是学者们大多没有充分关注王夫之的意见,因为唯独王夫之在一众学者中间猛烈抨击许衡和商人的罪恶,完全站在否定商贾的立场上,显得毫无妥协的余地。而且,他并不像其他儒者一样,单纯从儒者经商谈起,而是将所有商人和商业行为囊括在内,一并批判,这实际上一定程度越过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本位观念,把商人阶层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组成部分。尽管王夫之对商贾有诸多偏见,乃至把亡国亡种归因于商业,但他对整个商人阶层力量和诉求的认识,也反映出明清商业兴起的客观事实,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当对商人的批判频繁出现在民族观相关的表述中时,说明资本的力量对当时国家政治根基的影响,可能已达到了超出现代人想象的重大程度。
另外需要指出,王夫之为了自己的价值主张而攻击的社会阶层,事实上不仅限于商人阶层。吴根友对王夫之“文明史观”的讨论显示,庶民、“丘民”等基层民众,也因为耽于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不知民族大义,是应当切割、批判的存在。[4]吴根友:《王夫之“文明史观”探论》,《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1期。可见,物质财富在王夫之这里,定性为了造成君臣人伦和种群存续之间矛盾无法调和的根源,而不知人伦即为禽兽,民众禀此禽兽之气就会转为夷狄。在王夫之设定的“进步”文明的未来,那些动摇基本伦理观念的因素只是障碍,包括从商在内的逐利行为都将难以容于他的理想儒家历史观中。
四、结语
王夫之对元代许衡苛责的态度,本质上主要与他坚定的明朝遗民立场有关,但又不止于单纯的个人立场问题。王夫之“夷夏之辨”民族思想对许衡的评价,还论及了包括儒者和商贾在内的多种群体,体现出对历史进程中具体的“人”之作用的强烈关注,而这是以往的民族思想研究里较少提及的方面。而这种对“人”的重视,正与王夫之历史哲学中“依人建极”、阐发人本主义的思想互为表里。此外,他的批判也是对一些时代风潮冲击的回应,包括明清之际思想的多元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发等。其批判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他尤为强调在华夷对立中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导地位,认为儒者有承担起民族兴亡命运的使命。晚明儒家思想的多元化,士风和学风的沉沦,加重了他对儒者历史价值的关注程度。尽管他在多数场合并没有直接讨论“道统”的问题,实际上他非常重视儒学的纲领作用。这点在其民族思想方面集中体现为抵挡异端与异民族的价值观侵蚀。因此他才会痛斥所谓“败坏风气”、没有担当的儒者,将许衡等人立为标靶来批判。
其次,他始终对商人阶层抱有义愤心态,将他们描述成唯利是图的群体,跟夷狄狼狈为奸、联手摧残华夏文明,并且严厉批评了元明以来支持商业活动的儒者。这种价值取向正与当时士人鼓励工商业的客观历史潮流针锋相对,反映出明清之际商业发展迅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承认的现实情况。商人阶层的崛起,及其在国家、民族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乃至于促成了儒商的形成和实学兴业的风气。这些状况迫使着清初思想家作出应对,王夫之借许衡批判商贾的对策也正源于此。
我们不能否认,王夫之民族思想的论述中存在很多过激或偏离事实之处。王夫之对许衡民族立场的攻击,也含有利用许衡饱受争议的遗民形象借题发挥的成分。不过必须指出,王夫之是基于重整社会风气的目的,对特定群体而非个人的问题进行回应。而且,他的理论来自道统思想和义利之辨等许多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是古典价值观在明清之际新环境下的再次诠释。这些因素表明,王夫之的民族思想兼具深刻的反思精神和完整的内在理路,值得人们去关注。同时,他提出的疑问,可以在今天改头换面后变成:掌握文化话语权、社会财富的人们,应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担当何种角色、负起何种社会责任?这是我们长期需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