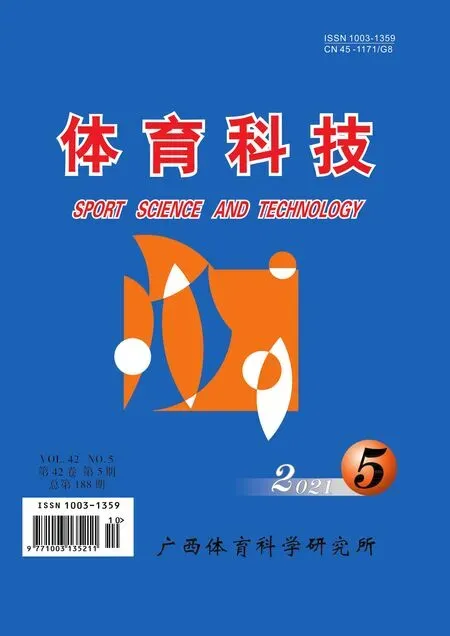基于协同理论的体医健康融合机制与实践路径探究
2021-11-22陈远莉李继军
陈远莉 李继军
基于协同理论的体医健康融合机制与实践路径探究
陈远莉1李继军2
(1.成都中医药大学 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2.川北医学院 体育部,四川 南充 637000)
协同理论作为治理理论的新发展,对系统整合、组织关系、演化转变的协同因素与体医健康融合发展不谋而合。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厘定体医健康内涵机制的基础上,探讨当今因体育与医疗协同发展的国家政策体系保障体系失效、改革实践协同研究失范、合作管理协同主体失能的主要问题,提出逐步完善政策体系,保障体医落地发展;加强融合试点改革,支撑科学化健康发展;搭建协作共享机制,实现管理主体整合的应对路径,以期为我国体育与医疗的协同发展之路提供有力支撑。
协同理论;体医;融合机制;路径;探究
协同理论亦称“协同学”,是通过解释系统内部要素间的协同作用从无序到有序结构转变的共同机理和规律[1-2]。作为治理理论的新发展,协同理论核心观念在于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将复杂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实现合作、协调、同步,从而使组织要素彼此耦合,赢得全新的整体放大效应[3-4],该理论与体医健康发展的诉求不谋而合。其一,体育与医疗协同是健康防治体系相互衔接的重要内容。协同理论可以实现统筹规划和统一安排,避免条块分割的体制,使各方资源有机融合[5]。其二,体育与医疗协同是健康改革实践的重要依托。协同理论可以将主体系统诸要素综合影响刺激下,合力形成健康发展目标与行动计划,以此带动健康生活方式、健康行动计划以及体育强国建设,为改革实践中的具体人群、试点提供依托。其三,体育与医疗协同是健康管理体系的共建共享。协同理论强调系统由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化[6]。将各自的技术、资源优势联合起来,破解各自为政的孤岛局面,使各方资源有机融合[7],是满足大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本研究运用协同理论能够较好的指导体育与医疗各系统之间的不协同状态,让构成协同的各个子系统或者子单元彼此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达到体医系统整体的演进与质的飞跃。
在健康中国建设与医疗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体育健身与医疗健康协同表达了中国新时期健康深度融合目标,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作为促进身心健康的“左右手”,二者的融合机制是“防未病、治已病”的有机体现,既通过体育锻炼手段辅助医疗,又可通过医疗诊治手段促进健身健康,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2017—2025年)中,明确指出了体医融合的发展内容,如“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体育部门要携手卫生健康部门培养运动康复医生、健康指导师等相关人才,推进国民体质监测与医疗体检有机结合,推进体育健身设施与医疗康复设施有机结合,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更加明确了国家在健康共治中的体医融合方向。基于此,本研究为实现体育与医疗联动健康的叠加效应,顺应体育与医疗的深度融合,针对协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阐释,促进二者在理论思想、科学发展、实践行动等诸多方面的实践发展。
1 体医融合协同发展面临的掣肘问题
1.1 政策体系协同保障失效
从协同主体层面上看,体育与医疗是较为复杂的系统,它是由许多要素组成的具有复杂的有机结构的整体。而体育与医疗属于不同的行业体系,主体不联动,缺乏多层级协同,在运行机制、组织结构、机构职能等呈现出剥离状态。从横的方面来看,体育与医疗专业化强,体育面向大众锻炼,医疗面向疾病患者,在各自领域分流而行,虽有国家层面的诸多政策推进体医融合发展,但在大健康领域内的跨部门合作的政策保障与研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从纵的方面来看,针对健康问题从国家到省市,乃至基层社区,体育以国家体育总局为导向,而医疗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为导向,在各自的定位、立场有着不同的诉求与意愿,导致二者在管理体制、考核指标、行动计划、执行内容等方面大相径庭,难以协同健康主体建立规范的政策、法律、规章与制度,缺乏跨部门合作的政策保障与研制。
1.2 改革实践协同研究失范
协同理论的自组织原理阐明了在系统外部具备一定条件的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的情况下,系统自身便能够有力的借助诸多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时间、空间乃至功能的有序结构。体医的改革实践率先由国家体育总局发起,成立了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分别在陕西、重庆成立了西安体育学院健康研究院和重庆医科大学体育医学学院体医融合示范区,以及各地区医学院校开展的慢病干预、社区诊疗、健康网络监控等方面的健康联合行动。目前,我国体医融合改革实践还在探索中,我国实施主体多为体育部门,对疾病的防治功效、具体病症的应用指导、科学健身理念的推行、健康计划的实施阶段,应进一步以医学主体牵头实施,通过改革实践的经验反哺其发展,通过科学与实践为体医的“破冰”改革提供可行、可控与可测支撑。
1.3 合作管理协同主体失能
协同理论认为,整合与协同都含有由不同个体为了完成共同的目标而进行互动、信息共享以及协调管理的过程,包括人、组织和环境的成本分摊、风险分担、利益分配以及激励方案的制定。从体医合作主体的协同管理来看,建立有效的体医运行机制,在组织间、部门间和机构层级的合作关系中发挥其统筹、集成、协调的优势,才能探究体医之间的深度合作。体医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健康的共建共享,而不同主体参与合作必须在政府推动、行业指导、机构合作、绩效监管以及人员协作上寻求利益共同点与联动,才能形成体医资源优势互补、相互协同的合力。就此问题,已有学者提出联合高校、研究中心、三甲医院、医联体社区医院、地方体育局、社区医疗、健身俱乐部合作的体医整合模式。但是,对于多部门主体参与的沟通对话机制、经费保障机制、监督测评机制、绩效管理改革、应用人才培养、利益分配体系等内容尚需进一步深挖。
2 体医协同的可行性路径
2.1 逐步完善政策体系,保障体医落地发展
国外部分国家的体医融合实践均有完善的政策体系保障与之并行不悖。如泰国通过《泰国健康促进法》的法律明确规定,保障了国民健康促进活动的有效执行;挪威通过立法手段,运用《公共卫生法案》中使的“卫生工作概述”方法作为促进多部门间合作的重要手段;美国加州通过建立具体项目组的形式,将数据收集、分析和总结地方政府各部门健康情况形成文件,为国家政策的规划与发展提供可行性参考,推进政策项目中健康目标的落实。芬兰搭建慢性病跨部门的合作机制,与教育、卫生、食品、体育等方面搭建健康协同保障体系,为我国体医融合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发展蓝本。
我国自《健康中国2030》提出以来,指出要强化跨部门协作,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加强制度保障治理,深化体医协同发展,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共治格局。但是,在体育与医疗庞大的行业体系中,还在探寻体医融合的理论体系及其现实路径。因此,我国体医在协同道路上政府与各地区职能机构应主动改革,打破内、外部体制壁垒,加强国家体育总局与医疗卫生事业管理部门的顶层合作,完善体医相关政策法律法规,联合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与具体计划,明确体医双方主体之间的责、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合作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构建规范的由上至下的政策保障体系。在改革中要明确体育与医疗的改革部门机构与职能目标,范围由基层走向大众,时间上由短暂走向持久,状态上由无序走向有序,效果上由低效走向高效,从体制与制度上保障体医协同工作的有序和可持续发展,以此保障体医的落地发展。
2.2 加强融合试点改革,支撑科学健康发展
美国作为体医融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协同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等多元主体通力合作,将运动与健康关系的科学证据应用于公共卫生实践,并通过“运动是良医”项目促进了体医的国际化与科学化发展。在《体力活动和大众健康指南》与《国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中均有科学化运动指导,还通过行业协会与医生团队展开合作,开展了诸如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常见病症的运动康复指导,进一步提升了体医实践应用价值,支撑了科学化的健康发展。
我国的体医改革实践正以“体医融合示范点”为切入点,不断探讨与推广体医健康共治的可行性方略。在融合试点工作中,首先应明确体医试点改革统筹协调主体,明确体育与医疗健康机构及人员的工作职责与考核标准、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各地区体医示范点的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加强科学管理效果评价,逐步建立医学主体牵头、跨部门协作和大众需求参与的体医协同机制。其次,将体医健康指南与行动计划等在体医融合示范点进行研究、实践与反馈,与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体医学术团体、融合机构、企业和媒体一起工作,充分发挥各组织机构的携手合作。作为跨学科研究,要建立体医科学研究支撑体系,通过示范、培训、交流等手段,逐步推行实践验证的体医协同理论、模式、方法与经验。针对重点健康问题与人群对象,为不同群众体育健身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健身指导,加强体育锻炼与临床疾病的联合研究,以科学量化的疾病干预研究作为体医健康防治的依据,按照具体病症、对象人群、干预手段等进行运动处方的系统研究,开设有针对性的体育健身方案,利用运动医学、康复医学的理论知识,指导健身群众进行科学运动,在临床推行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体医科学化发展。
2.3 搭建协作共享机制,实现管理主体整合
不同管理主体下的体育与医疗,如果能根据自身的目标、利益和所处环境对资源进行利用和分配,对各自领域的主要目标各有分工,就能增强合作沟通、交换优势资源及搭建利益共享平台。本研究针对合作管理协同主体失能的现状,基于协同理论,提出将体医从服务、人员与信息三个主体环节实现管理搭桥。第一,在服务管理方面,建立体医健康管理中心或治未病中心,主导医院、高校、社区、行业机构、社会组织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协商、谈判、合作、互动的沟通交流,搭建二者在体育锻炼指导、健康干预内容、场地与器材协调以及健康管理环节的综合服务。第二,在人员管理方面,从体医健康需求、优势资源、实践应用方面加强跨学科人才的培育,如定期合理的体育锻炼需要监管与评价,医生在患病人群中给予健康处方与药物干预指导,加强构建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运动处方师、康复治疗师等行业资质认定。第三,搭建体医双方在健康服务中的信息管理平台,将医疗体检中心将医疗检查内容中的亚健康人群、慢性病人群等符合锻炼需求的人群进行筛查,结合健康防治环节的临床服务形式,实现体育锻炼监测与医疗体检数据、体育锻炼场地与医疗诊治设备、体育健康方案与医疗诊治方案的有效互通,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实现体医健康资源的合理运用。
3 结语
在健康中国战略全速推进过程中,体育和医疗如何有效地融合,双管齐下,形成推动健康革命的新路径已显得十分的迫切和需要。体育与医疗的健康协同,是运动医学、保健康复、运动营养、科学运动等众多知识的集合,两个领域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其融合的对象范围很广,无论是否已经患病或是处于疾病前期的亚健康人群,还是健康人群,均可以结合医疗手段的判断、初筛、过程监督和评价,来达到健康促进的目的。本研究运用协同理论阐释了体育与医疗在政策体系、改革实践以及合作管理融合的叠加效应寻求“体医”联动改革发展的契合点,针对体医协同中的政策体系固化藩篱造成的保障失效,体医联合科学研究滞后导致的改革实践行动示范,以及利益相关协作缺失造成的体医合作管理失能的问题,提出其发展路径中的解决方略,以期为我国的体育与医疗协同健康发展提供思路与参考。
[1][西德]H·哈肯.张纪岳,郭治安,译.协同学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科研处,1981.
[2]潘开灵,白烈湘.管理协同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3]毕建新,黄培林,李建清.基于协同理论的高校协作服务模式探索:以东南大学为例[J].中国高校科技,2012(4):14-15.
[4]谭丹,朱玉林.基于协同理论的农产品绿色供应链实现模式[J]经济问题,2011(1):88-90.
[5]卢珊,赵黎明.基于协同理论的创业投资机构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演化博弈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7):120-123.
[6](德)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成功的奥秘[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9.(德) 哈肯.凌复华,译.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7]马荣超,郭建军.体育健康服务业供给侧转型下“体医融合”路径研究[J].三明学院学报,2017(6):95-100.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e Paths of Physical and Medical Health based on Collaborative Theory
CHEN Yuanli, etal.
(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611137, Sichuan, China)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四川省基层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WFZ20-Y-020);南充市社学社会科学(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项目编号:NCTY20A01)。
陈远莉(1984—),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医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