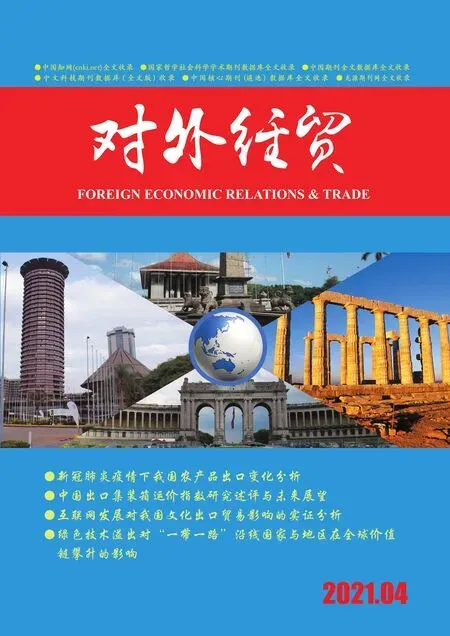国际贸易规则重构之非正式规则研究
2021-11-22谈晓文
谈晓文
(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0336;2.世贸组织讲席(中国)研究院,上海 200336)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 协议》)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的设立对世界贸易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确立了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以替代原有的以权力为导向的国际贸易。[1]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关注的是规则本身,即规则条文的可预见性、稳定性以及普适性,而非规则由谁来制定、符合谁的利益等。从此,规则贸易取代了政治贸易。[2]国家在客观、民主、合作及法治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国际贸易协议,并在协议约定的范围内开展多边贸易往来。[3]
然而,国家间的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从开始谈判经过制定到最终生效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以《GATT协议》为例,该协议历经八轮谈判,耗时四十七年。从1994 年《GATT 协议》签署至今,WTO 框架下仅于2005 年达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 协议》)以及于2013 年达成《贸易便利化协议》。传统多边国际贸易协议的磋商陷入僵局,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各国促进贸易合作的主要方式。①但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同样面临着需要国家签署、耗时长、签署后不易更改等问题。而且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往往从大方向上对某一产业进行政策指导,明确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但不经常涉及技术内容或具体操作细则。于是,制定非正式规则②作为传统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以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补充和调整已经逐步发展起来。③
近年来,非正式规则在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内蓬勃发展。以金融业为例,其内部不同行业之间适用由不同主体制定的、规范不同内容的、覆盖不同区域的非正式规则。在银行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制定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以下简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适用于包括中国、欧盟、美国等在内的二十八个成员。而在证券业,国际证监会组织覆盖了全球95%以上的证券市场,通过《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来对所有证券市场进行国际监督,并通过《关于磋商与合作和信息交流的多边谅解备忘录》促进监管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与跨境执法。
这些非正式规则,虽然没有国际法一般的法律约束力,但却在实质上被规则制定者,以及相关市场参与者,高度认同且普遍遵守。这一特征在最初引发了关于非正式规则这一议题的研究兴趣。
首先,需要考察非正式规则的定义,探讨非正式规则与国际法的区别以及这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次,考察非正式规则发展的背景,探讨哪些因素引发或推动了非正式规则的发展。再次,考察非正式规则的适用性。作为传统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以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补充和调整,非正式规则能否有效地避免或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维持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以及其能否免受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的影响,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正式规则的生存期,决定其能否被广泛适用。接着,考察WTO 对非正式规则的态度与立场,通过研究WTO 相关机构在法律解释、争议解决等方面的司法实践,来探讨WTO 对非正式规则发展的影响及该影响的界限。最后,站在中国的立场,非正式规则的发展是挑战也是契机,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到非正式规则的制定中去,抓住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良机,将贸易规则导向自由化和便利化,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为中国加强国际话语权、融入全球经济增加筹码。
一、非正式规则的定义
非正式规则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国际造法而言的。“非正式性”点明了这些规则不遵循国际造法应有的形式特征,也不依照国际造法的基本原则。这种“非正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非正式规则的制定者不仅是国家,还包括公共机构,中央银行,国际贸易组织工作组,商业及行业协会,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甚至是私人机构等。这是非正式规则与国际法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国际法的调整对象是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国际法的主体一般只能是国家,以及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非国家实体。[4]国际法上强调其主体是国家,或有国家法律人格的非国家实体,主要是因为国际法的效力依据来源于国家意志的协调,一定是经国家同意(state consent)才能使该国家受所签署或承认的国际条约或国际协议的约束,且最终受何种约束取决于各国国家意志协调的结果。[5]据此,法律约束力是国际法的重要特征,不履行条约或协议中的承诺就会违反法律义务,引发国家责任,导致条约或协议被终止或被解除,还可能承担赔偿义务。
与之相对的,非正式规则没有法律约束力,也没有国家意志的背书。而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非正式的形式制定出的仅仅是规则,而不是国际法。在没有强制约束力的情况下,非正式规则的遵守依靠的完全是市场参与者的“高度认同”。这种“高度认同”是自愿的,也是可以自由退出的。不遵守非正式规则不会引发任何法律上的后果,也不存在任何法律纠纷,尽管有时会违反道德义务或伦理义务。
其二,非正式规则制定的程序不一定是通过外交途径或贸易谈判途径签署的,不一定是基于国际条约设立的国际贸易组织(如WTO 等)的统筹安排下制定的,也不一定是依照国际组织章程中规定的严谨的程序完成的。非正式规则制定的程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会议上制定的,也可以是在国际论坛等场合达成的。但是,制定程序上的非正式性,并不代表非正式规则的制定就是随意的、可以朝令夕改的、不公开不透明的。相反,现行有效的非正式规则往往具有一定的程序性要求,包括详细的程序规则、制定时限、常驻的工作人员以及实体办公场所等。这种程序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非正式规则的稳定性,确定性,以及可靠性。
其三,非正式规则制定的最终成果,不构成条约、协议或国际法来源,而是表现为国际标准、指南、备忘录、原则等。[6]比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通过《商务旅行计划》(ABTC Scheme)来规范其成员间短期商务旅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通过制定Codex 标准来保护消费者健康并确保食品贸易中的公平贸易实践、《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UNGP)规范供应商行为等等。非正式规则覆盖面最广的还是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以及国际电信联盟(ITU)等通过制定信息通信技术标准来对技术标准、产品及服务的质量、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等内容加以规范。[7]
无论是计划、规范、原则、指南,还是国际标准,都仅仅针对某个具体行业,规范某项技术、某类产品或服务在国际或国内市场上的交换和流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专业性强导致了非正式规则在有技术突破时必须更新换代,如移动通信技术一般十年更新换代一次,移动通信技术的相关标准也是一直在换。④如此快速的技术更新与专利制度息息相关。当企业联盟共推的技术标准被政府或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纳,该标准拥有的技术形成专利池并遵循合理且非歧视的原则对外许可。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改良和创新的技术加入专利池,发展成新的技术标准。如此快速的更新换代意味着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并不稳定,而且有时效性。
所以,非正式规则无法使用统一的框架来对其制定、修订、签署、效力、适用范围等内容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一般加以规范,而只能在某个特定行业,某个相关产品或某项相关服务等有限的范围内加以适用,且只在一定时效范围内适用,因而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非正式规则只能作为传统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以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补充和调整。
但正是不正式规则的专业性和有限的适用范围,使其能有效地在某个特定领域,或就某项特定产品或服务提供质量控制和监测、消费者保护、营商环境优化等符合行业特征的、有针对性的、符合市场规律的、被市场主要参与者所期待的行为规范。因此,虽然非正式规则即使没有“形式上”的法律效力,也不是以国家为主体制定的,但在某个具体行业内部被普遍遵守,形成了行业内部的惯例。在这种意义上,非正式规则超出了一般软法的范畴,不遵循国际法传统,却有着“隐形”的约束力,被市场参与者“高度认同”且普遍遵守。这是当今世界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重要特征。
二、非正式规则的发展背景
当今世界的国际贸易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对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规则朝着更有利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更有利于市场进一步开放,更有利于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发展的方向重构。[8]而非正式规则的发展正是新一轮国际贸易构建的重要特征,其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当代社会是“知识型社会”,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更新周期不断被压缩,而知识的不断创新、积累、应用和分化正促使产业进步,也引导着个人、团体或组织以及社会的发展。新知识过快的不断更迭,导致在传统贸易协议谈判过程中,某些“陈旧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就已经不再适用了。当新的问题不断产生,程序严格的国际造法依赖外交手段和新一轮贸易谈判是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新问题的,还可能增加原贸易协议实施的难度。更不用说,贸易协议权威性的来源之一就是其作为有效力的法律文本本身具备的极大的稳定性,以应对贸易参与者的合理期待,不能随意更改。因此,国家往往来不及、也不愿意通过传统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以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来规范新出现的技术及相关衍生产业。这就为非正式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国际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时机条件。
其次,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使得即时通讯更加便捷、通讯成本也更加低廉。[9]传统的外交途径和贸易谈判手段不仅成本高,而且很耗时。如《TRIPS 协议》2005 年的修订版本,至今仍在等待2/3 国批准通过。更便捷和更低廉互联互通带来更密切的共享与合作,当传统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以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不能够及时规范某项新的技术及衍生产品或服务时,该技术或衍生产品或服务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或者相关的政府机构及非政府间组织就能够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及时沟通、评估、反馈与该技术相关的(国际)贸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为制定与该技术相关领域的非正式规则提供了通讯条件。
最后,比起由政府主导的传统的外交途径和贸易谈判手段,非正式规则的制定主体更加多样化,包括政府机构、中央银行、商业及行业协会、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甚至包括私人经营者,这就使得原本只能受规则约束的对象也有机会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有机会使制定中的规则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因此极大增加了市场参与者参与规则制定、遵守所制定的规则的意愿。因此,制定相关行业的非正式规则成了民心所向。但市场参与者的加入也局限了所制定的非正式规则或国际标准的适用范围,仅适用于某个细分行业或细分市场本身,如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而不能适用于更大的金融业或者服务业。而且,即使商业及行业协会、非政府间组织、私人经营者都有可能参与非正式规则的制定,归根结底还是由技术比较强势的一方或者市场优势更明显的一方来主导规则的制定。
以上这些条件阐明了非正式规则发展的社会背景,具备了时机条件、通讯条件、民心条件等,充分说明了非正式规则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既然非正式规则已经发展起来,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前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哪些非正式规则会在现实贸易来往中被适用以及这些非正式规则是如何被适用的,能否作为贸易争端时的解决标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补充或调整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等等。
三、非正式规则的适用
“世界贸易组织之父”杰克逊(Jackson)教授认为,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最大价值在于为国际贸易“带来可预见性,调整权力间的不平衡以及防止升级的国际紧张态势。”[10]所以,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最大的特征,其一是能够依据有法律效力的WTO 规则有效地解决贸易争端,维持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其二是使国际贸易规则不受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的影响,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来履行条约或协议约定的义务,享有对应的权利。因此,要考察非正式规则在国际贸易往来中能否被适用,如何被适用的,就要考察依据非正式规则能否有效地解决、或辅助国际贸易规则来有效解决贸易冲突和摩擦(有效性)以及能否不受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的影响(独立性)。
(一)非正式规则的有效性
非正式规则与现有的WTO 规则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规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没有法律效力并不意味着规则中的市场参与者就不去遵守这个规则了。事实上,非正式规则出现的本身就意味着该规则在现有市场环境下是被绝大多数,或者至少是被市场主要参与者所需要的。诸如数字经济、跨境数据、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等等概念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的“高度共识”的基础上的。
以联合国负责任投资(以下简称PRI)的六项原则为例,自2006 年由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发起,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纳入到投资过程中来,并支持其签署成员讲这些要素融入到投资战略和决策中来。作为非正式规则,这些原则不是由国家间通过外交途径或贸易谈判签署的,也不是通过联合国这一正式国际组织达成的,其产出的结果也没有法律效力。但截至2020 年,全球60 多个国家的3000 多家机构加入,成员机构的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100 亿美元。签署成员囊括了阿联酋海湾资本、富达基金公司等在内的全球各地主要的银行、主权基金、保险机构、投资机构等。中国的华夏银行资产管理部、中证指数等50 家机构也加入在内。⑤
由此,PRI 六项原则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其有效性就体现在市场主要参与者对该规则的内容,即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问题纳入到投资战略和决策中来这一核心思想,是高度认同且自愿遵守的。这种认同度甚至高于对传统多边贸易协议下某个条款的认同度。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来源于国家的“同意”,这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要求。而在国家“同意”了以后,还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等方面执行条约或协议实质性的内容。而考虑到以后可能的情势变更或国内政策倾向的改变,传统多边贸易协议的签署国家往往会对某项条款提出保留,或援引例外条款来为自己不遵守协议的行为辩护,这就实际上否认了该条款的效力。与之相对的,非正式规则虽然没有国家形式上的“同意”,但却是众多市场参与者都一致认可通过的,反而有了有效实施的基础。所以,有法律效力的传统贸易规则面临着无法有效实施的困境,而没有法律效力的非正式规则却被市场参与者高度认可,自觉遵守。
当市场参与者都自觉遵守这些非正式规则,那么非正式规则有效性还需要考察其实施以后能否达到其制定的目的。实际上,由于非正式规则的制定者往往是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经济实力及政治势力强大的参与者,他们主导制定的非正式规则往往有着影响公共政策,甚至影响传统贸易协议实施的能力。以ISO 标准为例,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国际标准化机构,现由165 个成员,制定的国际标准涉及除电工标准以外各个技术领域。虽然这些国际标准不构成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没有法律效力,但他们被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大量引用,实质性地规范着相关国内和国际市场,甚至成为某些市场准入的门槛。⑥即使是WTO 框架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简称《TBT 协议》)也无可避免的需要参考《ISO/IEC 技术工作导则2》,确保国际标准不会构成技术性贸易壁垒。由此可见,非正式规则的有效性毋庸置疑。
当然,也不是所有非正式规则都是有效的。但非正式规则在制定和更新中会经历被筛选的过程,以确保一定的有效性。非正式规则从制定、实施、解释、评估到修改整个过程是动态的,且不断重复循环,不断更新着规则的内容。规则的制定者本身也是规则的遵从者和实施者,因此制定者们往往能够及时发现规则中存在的问题,在便利的沟通条件下及时剔除有问题的规则,或对既存的规则进行修改,以适应不断更新换代的科技和不断发展的社会。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所以,即使非正式规则的有效性有时限,并不影响该规则在时限内被普遍遵守,也不影响更新后的规则仍继续有效。这一特征也决定了非正式规则是不能替代原有的国际贸易规则的,而只能在专业层面,对国际贸易规则进行补充或调整。
(二)非正式规则的独立性
非正式规则的独立性,即非正式规则能不能摆脱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势力等的影响,按照规则既定的内容和程序来规范贸易往来或解决贸易争端。
事实上,与非正式规则比起来,现有的WTO 框架下的多边贸易协议或自由贸易协定由于是以国家为制定主体,更容易受到国家势力的影响。比如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承诺的,同意在反倾销条款中采用替代国价格计算倾销幅度等。而且,虽然该承诺的十五年期限已过,但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坚持下,至今仍然使用替代国价格来计算我国对外出口的倾销幅度。所以,WTO规则不能做到完全抹除了国家间势力的不平衡,而只能通过规则和程序减少国家势力的影响。
其次,非正式规则的内容更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而技术的更新是跨越式发展的,经营者在这一代技术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可能在下一代技术上就落后了。[11]上一代的技术优势可能成为下一代技术发展的成本。如日本在3G 时代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而到5G 时期华为成为了领先的经营者。所以,某一经营者的领先地位,或某一国在该技术、产品贸易上的领先优势,即使只适用于某个特定市场,也不一定长久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任何国家的影响力,而只取决于某国在某一项技术上的优势。
此外,市场本身的风险加剧了市场经营的不可预测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强大到挽救雷曼兄弟的破产。说到底,现代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还是必须遵循市场的规律,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经营、竞争。这也再次明确了稳定的确定的有法律效力的国际贸易规则(WTO 规则)仍是必不可少的,而非正式规则是能在一个稳定的大框架下做补充和调整。
四、WTO 的态度与立场
既然非正式规则是国际贸易规则的补充与调整,那么作为目前被适用范围最广、最基本也最权威的WTO规则,其制定组织WTO 的态度与立场就至关重要了。因此,有必要考察WTO 对非正式规则是如何认定、如何适用的。
WTO 规则在成立之初,就设置了特别承诺使国际贸易规则能灵活适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特别承诺属于WTO 规则的一部分,一样具有法律效力。但特别承诺的灵活性是原则层面的灵活性,是关于国民待遇、市场准入等原则能否适用于某个特定行业。因此只是笼统地要求了透明度,要求了最惠国待遇,要求了开放市场等等,而不涉及对某个行业内部具体的资格性审查或程序性规定。
就WTO 内部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制定各种非正式规则,来对现有的WTO 规则进行调整或补充。比如会计行业的国内法规规范,就透明度、(会计及相关行业)的资格要求和程序、会计服务技术标准等内容设立了最低门槛,以确保这些内容不会构成国际贸易壁垒。这些内容是特别承诺中一般不涵盖的内容。就包括特别承诺本身,特别承诺委员会还制定了关特别承诺清单的指导性文件,通过对规范清单的格式等技术性内容的进一步规范,使各个承诺之间外观格式相似,于是内容上的差异就容易辨识。因此,非正式规则还能增强WTO 规则本身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所以,WTO 规则及相关机构对待非正式规则的态度整体上是支持的。
WTO 上诉机构在履行其争议解决的职责时,已经给予某些非正式规则判例法(precedential)效力。仍以《TBT 协议》中的“国际标准”为例。在2012 年的美国—沙丁鱼二这一案中,上诉机构不仅依赖于《ISO/IEC 技术工作导则2》来定义“国际标准”与“国际性”,“国际标准化组织”与“标准化”等概念,还援引了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关于国际标准发展原则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非正式规则作为依据来判定该案涉及的《国际海豚保护计划》(以下简称《AIDCP 协议》)中的AIDCP 标准是否属于《TBT 协议》第2.4 条项下的国际标准。如果属于,则AIDCP 标准可以作为依据制定技术法规。[12]
上诉机构认为该《决定》构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第3 款项下的嗣后协定(subsequent agreement),因为该《决定》实质性地对TBT 协议条款进行了“权威的解释”,明确了国际标准发展的原则,确保了TBT 协议的有效适用而且厘清了TBT 协议项下国际标准的概念,因而可以对条约或协议(即《TBT 协议》)及相关条款的适用进行解释。
然而,上诉机构也承认了,即使《决定》构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第3 款项下的嗣后协定,也不意味着该《决定》能对《TBT 协议》相关条款中的某个概念进行完全的解释,或参照该《决定》就能直接适用某个《TBT 协议》内的概念(如“国际标准”这一概念)。相反,《决定》能对《TBT 协议》相关条款中的某个概念解释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在个案中《决定》与《TBT 协议》之间有没有“特殊的关系”(bearing specifically upon)。此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决定》中关于国际标准的制定需是“开放的”(open),这一特征构成对《TBT 协议》附录1.4 条的直接且权威的解释,因此可以作为判案的依据。
依据《决定》中关于“开放的”国际标准的制定这一要求,上诉机构提出,AIDCP 标准制定的法律依据——《AIDCP 协议》需是非歧视性地对所有的WTO成员开放。然而,本案中,包括美国与墨西哥在内,一共仅有十三个WTO 成员参与了这一协议。而且根据AIDCP 协议,其成员必须是对捕捞金枪鱼有兴趣的国家,而其他仅仅对环保、海洋研究等有兴趣的国家无法参与加入该协议。这一规定违反了非歧视性原则,不符合《决定》内对“开放的”国际标准的制定这一要求,因此AIDCP 标准不是《TBT 协议》第2.4 条项下的国际标准。
判决中关于《决定》这一非正式规则的性质判定,即其构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第3 款项下的嗣后协定这一法律性质的判定,虽然简短,但其中关于成员“合意”的认定有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
该《决定》并没有在制定出来以后,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或贸易谈判途径,经所有成员批准通过或承认。按照上诉机构的逻辑,基于任意国际条约或国际协议,该条约或协议的相关委员会只要有所有的条约成员或协议成员的参与,其制定出的非正式规则就当然的具有了所有成员的“合意”,而无需所有成员“形式上”的批准通过或承认。这就在实际上赋予了该条约或协议的相关委员会超越其权限范围的“立法权”,无限放大了相关委员会的权利,也模糊了非正式规则与国际条约、国际协议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在厘清非正式规则的定义时就强调,非正式规则之所以造出来的不是法律,而仅仅是规则,就在于其没有通过外交途径或贸易谈判手段,经过国家在形式上的“认可”或“承认”。所以,国家没有表达受该条约或协议约束的意愿,因而不具有国际法意义下的法律效力,所谓成员的“合意”没有法律基础。⑦况且,该非正式规则的制定主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也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 条以及第5 条下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定义,其制定的规则即不属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约章,也不属于该组织内达成的条约,所以该《决定》从性质上说就是非正式规则。
在认定《决定》属于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无论该规则的内容如何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原条约或协议,也无论该规则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对原条约或协议进行解释说明,《决定》本身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也是无法作为判案依据的。上诉机构将《决定》认定为嗣后协定的判决实质上是给予了《决定》这一非正式规则有限的判例法效力。如此,在专家组或上诉机构遇到与国际标准相关的贸易争端时,也能够引用《决定》来对《TBT 协议》作解释。
虽然上诉机构的裁判可能存在争议,但其对国际标准进行探讨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至少与在2002 年欧盟—沙丁鱼一案中,视而不见的态度相比,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13]当前,也正需要上诉机构来对国际标准等概念的定义和范围作一定的限制,以此构建非正式规则与(WTO 规则)条约规则之间的桥梁,以现有条约规则的基,非正式规则加以补充,完善国际贸易规则。而且经过上诉机构的认可,非正式规则能就某一条约规则附加一定的法律义务或权力,这样就将某些非正式规则纳入到了WTO 规则内。在这个意义上,上诉机构承担着发展非正式规则、完善WTO 规则的重任。
五、中国的立场
当前,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构建国际贸易新规则,中国决不能置身之外。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将决定未来贸易规则和产业标准的走向,决定哪些国家在未来战略竞争和贸易往来中占据优势和主动地位。而非正式规则的发展作为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权的归属将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增加砝码。
通过外交手段或贸易谈判签署的国际贸易规则往往是一些原则性的方向性的条款,需要各个成员颁布具体的法律法规或实施细则来落实。而非正式规则可以通过对资格性审查、程序性规定等具体的细则性的规范来条约条款实施的标准、程序、范围等等加以约束,将不利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所以,中国一定要参与到非正式规则的制定权中来,尤其是在将要主导未来大国竞争的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的竞争方面,[14]夺取相关非正式规则——包括各类技术性国际标准、技术贸易投资原则、技术实施规范等等的制定权,为中国在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甚至是未来国际规则的博弈中增加筹码。
而中国参与非正式规则的制定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对非正式规则的制定要把握重点领域进行突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所有新技术中均占有领先优势,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应当把重心放到未来大国竞争战略的核心技术以及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关键议题,如数字经济、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等相关行业及相关技术的非正式规则的制定上来。其次,非正式规则毕竟只能作为正式国际贸易规则的补充,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参与、引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尤其是WTO 改革为主要任务,参与非正式规则制定为次要任务,主要任务与次要任务相结合,探索我国与国际贸易新规则接轨的路径与做法。最后,我们要以参与国际规则重构、参与非正式规则的制定为契机,探索继续深化国内市场改革、扩大开放,进而寻求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格局、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途径。
[注释]
①目前,WTO 框架下签署有超过560 个条约。准确数据,请参见联合国条约库。
② 由于文本研究的对象是非正式规则,没有法律效力,无法被称为是立法行为。所以,作者在此特意将informal lawmaking 翻译成“非正式规则的制定”,而非“非正式立法”。
③作者认为非正式规则是作为传统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以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补充和调整存在,与作者观点完全相反的是鲍威林(Pauwelyn)教授认为的,非正式规则是替代传统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以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他称非正式立法(informal lawmaking)为是国际贸易规则的2.0 版。参见J.Pauwelyn,Rule-Based Trade 2.0? The Rise of Informal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How they May Outcompete WTO Treat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17,2014,pp.739–751。
④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1G)采用的模拟技术和频分多址(FDMA)技术,1989 年(2G)欧洲以GSM 为通信系统的统一标准,2009 年中国颁发3 张3G 牌照,2013 年工信部宣布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颁发4G 牌照,到2019 年6 月6 日,工信部正式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广电四家企业发放5G 牌照,平均十年迎来一次移动通信技术的大变革。
⑤ 资料来源: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官方网站:https://www.unpri.org/about-the-pri,2020 年10 月7 日访问。
⑥ 如中国将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系列标准转化为我国国家标准,使质量管理制度化、体系化、法制化。只有通过ISO 9000 认证的企业,其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也符合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质量的要求。
⑦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 条。其中,关于政府的承诺行为,使用了“ratification”,“acceptance”,“approval”以及“accession”,并强调这些行为旨在表示“consent to be bound by a trea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