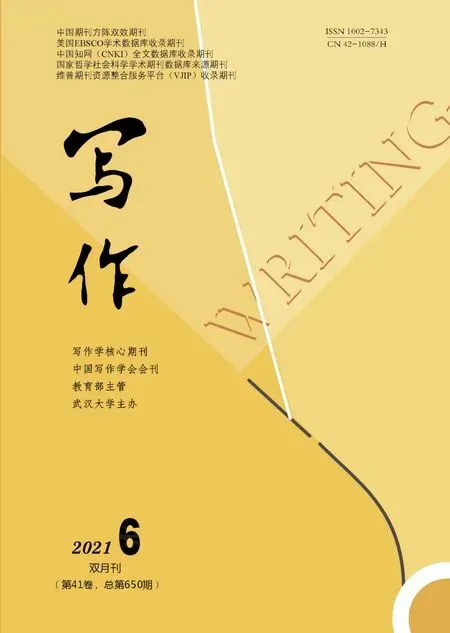中国现代散文语言的典范:京派散文的语言形象
2021-11-21陈啸
陈 啸
在现代汉语界,语言(language)被具体分为“语言”(language,语言系统或代码)、“言语”(parole,个人的说话或信息)和“话语”(discourse,单个说话者的连续的信息传递或具有相当完整单位的本文)等。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存在之域①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03页。。而文学的语言则不仅具有言语或话语组织的本来之意,而且还包括独特的文体及各种修辞的手段。“形象”意指艺术中由符号表意系统所创造出来的能显示事物深层意义之想象的具体可感物。语言形象则是指文学作品的具体话语组织所呈现出的,富有作者独特个性魅力的语言形态,也即如何再现语言的形象问题。京派散文语言形象作为现代“中国语言形象”②参见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在审美表达中,内在且不同程度地再现着中国现代整体性及中国现代艺术性等不同方面,具有着传统与现代、审美与文化的多重内涵。
一、反复“抟弄”
京派散文的语言给人的整体感,也即第一感觉是“陌生化”。根据俄国形式主义理论,“陌生化”就是在描写一事物时,不用指称及识别之方法,而用一种非指称、非识别的仿若首次见到这事物而不得不进行描写的方法。京派散文陌生化的语言就如汪曾祺所谓的“揉面”③汪曾祺:《“揉面”——谈语言》,《花溪》1982年第3期。,将古今中外、方言土语以及不规范的言语和自造词放在一起,下笔之前反复抟弄。化为自己的血肉,铸成作品的筋骨,以炉锤之功或化腐朽为神奇,或点铁成金,或匠心独具,或秀外慧中……一词一句,痛痒相关,互相映带,姿势横生,气韵生动,璀璨夺目,妙趣横生。这就是中国人常讲的“文气”。要之如下:
(一)古语镶嵌
京派散文行文,非纯粹的现代汉语方式,时或古今糅合,在保持现代汉语为基本的前提下,常于局部镶入古汉语的词汇、词语组合、从句、修辞术等,巧妙地抟弄与糅合,化为自己的血肉,形成古今对话之新格局,没有丝毫的生硬拼贴、非驴非马之感。意义丰富,促人联想,言简意赅,半文半白,古色古香,明白无误。如废名《菱荡》中的描写段落:“塔不高,一大枫树高其上,远行人歇脚乘凉于此。于树下,可观菱荡圩。不大,花篮状,但无花,从底绿起。若荞麦或油菜花开之时,便尽是花了。稻田,树林堆成许多球,城里人不能一一说出,村、园,或池塘四周栽了树,树比之圩更来得小,走路是在树林里走了一圈。除陶家村及其对面一小庙。时或听斧斫树响,但不易见。小庙白墙,深藏到晚半天,此地首先没有太阳,深。有人认为是村庙,因其小,城里人有终其身没向陶家村人问过此庙者,也没再见过这么白的墙。”①吴福辉编选:《京派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语言干净,短句居多,时或以“其”“于”“之”等文言词汇穿插其间,古雅利落,清爽干脆。
李广田的《山水》行文基本都是以现代汉语娓娓述说自己如何因读“先生”之山水的文章而生平原之子的欣羡、寂寞与悲哀,并以一个平原之子的心情诉说多山之地的缺陷和不足,同时想起自己故乡,以及平原的子孙对一洼水一拳石的喜欢和身处平原之地对远方山水的想象,并述说自己的祖先如何来此平原,如何改造平原。最后总结说,这是一个大谎,因为是一页历史,简直是一个故事。“那里仍是那么坦坦荡荡,然而也仍是那么平平无奇,依然是村落,树木,五谷,菜畦,古道行人,鞍马驰驱。”“我在那平原上生长起来,在那里过了我的幼年时代,我凭了那一块石头和几处低地,梦想着远方的高山,长水,与大海。”②李广田:《李广田全集》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223页。而中段部分写祖先对平原的改造即穿插了大段的古语描述,几近于文言文述说。请看:“以己之力,改造天地,开始一伟大工程,凿成一道大川流。从此以后,我们祖先才可以垂钓,可以泅泳,可以行木桥,可以驾小舟,可以看河上的烟云。我们的祖先仍是觉得不够好还要在平地上起一座山岳。用一切可以盛土的东西,运村南村北之土于村西,又把那河水引入村南村北的新池,于是一曰南海,一曰北海,山是土的,于是采西山之石,南山之木,进而成为:峰峦秀拔,嘉树成林,年长日久,山中梁木柴薪,不可胜用,珍禽异兽,亦时来栖止,南海北海,亦自鱼鳖蕃殖,萍藻繁多,夜观渔舟火,日听采莲歌。”③李广田:《李广田全集》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223页。大量的文言字词与四字句,读之朗朗上口,古色古香,亦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
梁遇春的《春雨》在表述自己喜欢春雨、喜欢春阴以及厌恶晴朗日子的原因时,于基本的现代汉语表述中,也时或有古汉语表达方式,或引用,或化用,读来古雅:“我向来厌恶晴朗的日子,……阴里四布或者急雨滂沱的时候,就是最沾沾自喜的财主也会感到苦闷,因此也略带了一些人的气味,……至于懂得人世哀怨的人们,黯淡的日子可说是他们唯一光荣的时光。穹苍替他们流泪,乌云替他们皱眉,他们觉到四周都是同情的空气,……‘最难风雨故人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人类真是只有从悲哀里滚出来才能得到解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很可以象征我们孑立人间,尝尽辛酸,远望来日大难的气概,真好像思乡的客子拍着阑干,看到郭外的牛羊,想起故里的田园,怀念着宿草新坟里当年的竹马之交,泪眼里仿佛模糊辨出龙钟的老父蹒跚走着,或者只瞧见几根靠在破壁上的拐杖的影子。……临风的征人,……无论是风雨横来,无论是澄江一练,始终好像惦记着一个花一般的家乡,那可说就是生平理想的结晶,蕴在心头的诗情,也就是明哲保身的最后堡垒了;……‘小楼一夜听风雨’,……喜欢冥想春雨,也许因为我对于自己的愁绪很有顾惜爱抚的意思;我常常把陶诗改过来,向自己说道:‘衣沾不足惜,但愿恨无违’。”①载《新月》1932年11月1日第4卷第5号,署秋心遗稿。
(二)融外化生
京派文人通晓古今,博贯中西,在语言操作中,常常能够不自觉地移植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外语词汇、词语甚至句法,巧妙地为我所用,将文言、现代口语、西化语完美化生。典型的如林徽因《蛛丝和梅花》中:“同蛛丝一样的细弱,和不必需,思想开始抛引出去:由过去牵到将来,意识的,非意识的,由门框梅花牵出宇宙,浮云沧波踪迹不定。是人生,艺术,还是哲学,你也无暇计较,你不能制止你情绪的充溢,思想的驰骋,蛛丝梅花竟然是瞬息可以千里!……就在这里,忽记起梅花。一枝两枝,老枝细枝,横着,虬着,描着影子,喷着细香;太阳淡淡金色地铺在地板上;四壁琳琅,书架上的书和书签都像在发出言语;……你敛住气,简直不敢喘息,巅起脚,细小的身形嵌在书房中间,看残照当窗,花影摇曳,你像失落了什么,有点迷惘。又像‘怪东风着意相寻’有点儿没主意!浪漫,极端的浪漫。‘飞花满地谁为扫?’你问,情绪风似地吹动,卷过,停留在惜花上面。再加减看看,花依旧嫣然不语。”②林徽因:《蛛丝和梅花》,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6年2月2日第86期。古典秀丽,色彩斑斓,中西合璧,色味俱全,给人一种浪漫而迷丽的感觉。
(三)以俗现美
京派文人多来自乡间,乡间日常生活习用的语言以及内在的语言精神,也常常成其为散文语言的妆饰和内在的神韵。代表性的如萧乾,常常在散文中使用一些汉语区域内大致都能懂的北京地方话,即所谓的“蓝青官话”,同时把北京乡土文化特有的“雅”幽默情趣浸润其间,使得语言鲜活、风趣、精辟、深刻,雅俗共赏。譬如《过路人》(1934年5月)写自己一次坐船的经历:天刚亮,船进港,渐渐,“我”读到巍峨建筑上的字:洋行,洋行,横滨的,纽约的,世界各地机警的商人全钻到这儿来了。“好一条爬满了虱子的炕!”③萧乾:《萧乾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精彩比喻的背后隐藏着幽默。严肃之事以诙谐、滑稽的用语喻之,使人在低迷的微笑中获得雅化的情绪体验。同一文本中还有:“汽车多啊,多得像家乡池塘雨后的蜻蜓。费了老大气力提炼成的汽油全在马路上变成一阵臭烟了。那烟还得通过人们的五脏。”④萧乾:《萧乾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雍容之事以嘲弄、揶揄的语调写,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让人产生一种会心的微笑。林徽因的散文同样有着北京特有的雅幽默意味。如《窗子以外》中,写两个妇人与伙计争秤,“必是非同小可,性命交关的货物”“必定感到重大的痛苦”;写坐车过站的老太太挟着行李,“是在用尽她的全副本领的”;写她突闻村落之人为明庆王的后人,“这下子文章就长了”“这样一来你就有点心跳了”⑤林徽因:《窗子以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9月5日第99期。,平常之事以严肃、夸张的口吻写之,使语言本身蕴涵着冲突,逸出了文字本身的语义。“雅”幽默背后深隐的是深刻的文化知识基础,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中深刻的意义和精神的闪光。沈从文的语言整体上皆为湘西水上的言语。此种语言虽来自乡民,但已“面目全非”,它抛却了乡民口语中的那种缘于种种原因及基本精神而与全民族语言结构不相符合的如偶然、临时、非巩固、含糊及发音不正等的部分。如:“我一个人坐在灌满冷气的小小船舱中”的“灌”字(《箱子岩》)⑥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247页。,“把鞋脱了还不即睡,便镶到水手身旁去看牌”的“镶”字(《鸭窠围的夜》)⑦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247页。等,真实、质朴、形象,富有动人的生活情趣,以俗现美。沈从文的文学语言整体上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显,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京派散文还常常以词类的活用等违反常规之手法使语言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如废名的《沙滩》中“草更不用说除了踏出来的路只见它在那里绿”①废名:《废名散文选》,冯健男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中的“绿”字以及沈从文的《湘行书简·过新田湾》中“我好像智慧了许多,温柔了许多”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中的“智慧”一词,即为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二、譬喻奇警
京派散文有着浓浓的“诗质”。其实,京派文人很多就是诗人,而诗人写作几乎没有不用比喻的。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比喻”成为京派散文的一个显著的文体特征。京派散文的比喻精当贴切,垂手天成,自然奇警。温而雅,皎而朗,譬喻引类,幻拟心理,能量无比,着眼环境,揭示本质。
如何其芳的《墓》中:“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夕阳喻示着美好和短暂,红色的唇代表着温暖的爱情,把“夕阳”比喻成“温暖的红色的唇”,易于产生对爱的怅惘与失去爱的凄惶、失落、哀悼之情。“他们散步到黄昏的深处,散步夜的阴影里。夜是怎样一个荒唐的紫语的梦啊。”以“荒唐的紫语的梦”比喻“夜”,充分感觉化了,“荒唐”一词是“我”的感觉,是“我”抚今追昔,痛定思痛,哀惋凄切等情感的外化,以“紫语的梦”极言过去美好时日的苍凉、幽暗、遥远、空幻。“夕阳如一枝残忍的笔在溪边描出雪麟的影子,孤独的,瘦长的。”③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页。把“夕阳”比喻成“残忍的笔”,情感化,形象化,“夕阳”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苍凉、忧郁、孤独、寂寥的感觉,再施之于“残忍”一词,更进一步突出雪麟的孤独与忧郁。《秋海棠》中:“庭院是静静的。仿佛听得见夜是怎样从有蛛网的檐角滑下,落在花砌间纤长的飘带似的兰叶上,微微的颤悸,如刚栖定的蜻蜓的翅,最后静止了。夜遂做成了一湖澄净的柔波,停潴在庭院里,波面浮泛着青色的幽辉。”④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页。把无可言之静夜动态化、形象化,先细致描述“夜”从檐角滑下,落于兰叶上,这分明是观察者主体的内心感觉,突出了主体的静、思、寂寥、孤独,同时把“夜”又写活了,可感可触可观,这其实都是主体的思绪在动。“夜”如蜻蜓的翅膀、一湖澄净的柔波,又是极言“夜”的静谧、美妙,但这一切都是在突出主体的幽孤,对“夜”的比喻其实也是对思妇主体的形容。“夜的颜色,海上的水雾一样,香炉里氤氲的烟一样的颜色,似尚未染上她沉思的领域,她仍垂手低头的,没有动。但,一缕银的声音从阶角漏出来,尖锐,碎圆,带着一点阴湿,仿佛从石的小穴里用力的挤出,珍珠似的滚在饱和着水泽的绿苔上,而又露似的消失了。没有继续,没有赓和。孤独的早秋的蟋蟀啊。”⑤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页。这里把蟋蟀的声音比喻成银样的声音,然后再以“尖锐”“碎圆”等充分物质的形容词述之,以用力的“挤”出,珍珠似的“滚”在饱和着水泽的绿苔上……其实,把蟋蟀声音的强化、物质化,意在突显思妇主体孤独感觉的强化、物质化。“这初秋之夜如一袭藕花似的蝉翼一样的纱衫,飘起淡淡的哀愁。”⑥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页。把虚空之“夜”比喻成可触可感的蝉翼样的纱衫,“夜”成了实体化、美妙化了的感情载体。“她素白的手抚上了石阑干。一缕寒冷如纤细的褐色的小蛇从她的指尖直爬入心的深处,徐徐的纡旋的蜷伏成一环,尖瘦的尾如因得到温暖的休憩所而翘颤。”⑦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页。把寒冷的感觉比喻成褐色的小蛇,陌生化、物质化、恐怖化、形象化,重情感的相似性。“就在这铺满了绿苔,不见砌痕的阶下,秋海棠茁长起来了。两瓣圆圆的鼓着如玫瑰颊间的酒涡,两瓣长长的伸张着如羡慕昆虫们飞游的翅,叶面是绿色的,叶背是红的,附生着茸茸的浅毛,朱色茎斜斜的从石阑干的础下擎出,如同擎出一个古代的甜美的故事。”⑧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页。想象化、感觉化、联想化、引申化的比喻,拓宽了理解空间,丰满,圆润,温厚,蕴藉。《雨前》中:“一点雨声的幽凉滴到我憔悴的梦。”⑨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页。自然界的雨声赋予拟人化、情感化的幽凉,自我的玄想比之为梦,颇渲染出一种迷离恍惚、凄切、怅惘之感。《迟暮的花》中:“在你的眼睛里我找到了童年的梦,如在秋天的园子里找到了迟暮的花……”①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121页。情感的牵连,相似性、相关性、陌生化的比喻,把对青春的伤感,对纯洁爱的孤独的呼唤,形象昭示。《货郎》中:“于这些大宅第,他(指货郎)象一只来点缀荒凉的候鸟,并且一年不止来一次”②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121页。,此一烘托性的比喻,恰似那“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功效,更突出和昭示出大宅第的荒凉、古旧、冷清。
汪曾祺《牙疼》:“牙疼若是画出来,一个人头,半边惨绿,半片炽红,头上密布古象牙的细裂纹,从脖子到太阳穴扭动一条斑斓的小蛇,蛇尾开一朵(什么颜色好呢)的大花,牙疼可创为舞,以黑人祭天的音乐伴奏,哀楚欲绝,低抑之中透出狂野无可形容。”③汪曾祺:《牙疼》,《文学杂志》1947年9月第2卷第4期。比喻感觉化,感觉物质化、形象化、幽默化,可触可感可思可想,且充满着丰厚的文化想象。师陀《还乡——掠影记》中写西方楚先生回乡寻梦却失落:“西方楚先生感到一点不同,同时又觉得没有什么两样,也说不出自己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那不是哀伤,不是痛苦,不是失望,也不是细碎的纷乱,而是咸水鱼游到淡水里的极轻微的不适。”④芦焚:《还乡——掠影记》,《文丛》1937年第1卷第3期。芦焚即师陀。把不可言明之情绪以类似的物象喻之,形象明了,含蓄蕴藉,耐人回甘。
比喻是语言艺术中的艺术,具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多彩的比喻,使京派散文诗情蕴藉,回味无穷,也成为京派散文文体的一个显在标识。
三、行文似绘
京派散文行文似绘,绘画中的各种技巧及艺术,比如空间艺术,皴染烘托及映照生辉的主次艺术、白描艺术、光线艺术以及色彩的搭配等,很多都被京派文人创造性地移用于散文创作,有着精妙的呈现。以沈从文《桃源与沅州》中对白燕溪的描写为例:“沅州上游不远有个白燕溪,小溪谷里生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罅隙间,或蔓延到松树枝桠上,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花叶形体较建兰柔和,香味较建兰淡远。游白燕溪的可坐小船去,船上人若伸手可及,多随意伸手摘花,顷刻就成一束。若崖石过高,还可以用竹篙将花打下,尽它堕入清溪洄流里,再用手去溪里把花捞起。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崖下繁殖。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那种一丛丛幽香眩目的奇葩,那种小小洄漩的溪流,合成一个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⑤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整个白燕溪在作者笔下就似一幅中国水墨画。画面的中心和显要位置是芷草,长叶飘拂,形象楚楚。芷草的周围则饰以多样的香草香花,为衬托宾者地位,描写也较芷草渺茫不清。芷草及各种香花香草的背景则是高的黛色悬崖,下配以清淡的小船及船中人伸手摘花,用竹篙打花,清流里捞花,等等,整幅画面,有主有次,多少、藏露、浓淡合宜且相生相应。
再比如废名《沙滩》一文中对史家庄的描写:“站在史家庄的田坂当中望史家庄,史家庄是一个‘青’庄。三面都是坝,坝脚下竹林这里一簇,那里一簇。树则沿坝有,屋背后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草更不用说除了踏出来的路只见它在那里绿。站在史家庄的坝上,史家庄,史家庄被水包住了,而这水并不是一样的宽阔,也并不处处是靠着坝流。每家有一个后门上坝,在这里河流最深,河与坝间一带草地,是最好玩的地方,河岸尽是垂柳。迤西,河渐宽,草地连着沙滩,一架木桥,到王家湾,到老儿铺。”⑥废名:《废名散文选》,冯健男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整幅画面采用的是两个观察点的散点透视,分别从史家庄的田坂当中和史家庄的坝上,远景扫描,而画面的中心是史家庄。通过两个观察点,由近及远依次展开了史家庄周围的画面:坝围以内,处处竹林、茂树、青草等等,把史家庄点缀成一个“青”庄。坝围以外,河流、垂柳、木桥等等,则把史家庄装扮成一个诗意的水的世界。文本除了精心营构空间艺术而外,还化用了唐代王维以来中国绘画惯用的皴染烘托、映照生辉艺术。此一艺术本为画家用水墨或淡彩在物象的外廓渲染补托,使其艺术形象鲜明突出的一种艺术手法。宋代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一书中说:“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①郭熙:《林泉高致》,梁燕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清代画家笪重光在《画筌》中说:“山本静,水流则动;石本顽,有树则灵。”②笪重光:《画筌》,关和璋译解、薛永年校订,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废名写史家庄,不重实写史家庄内部如何如何,而是写它的外围之竹之林之草之水之柳之桥等,通过外围之景,烘托出一个诗意的史家庄。
“白描”,原是中国画技法之一,源于古代的“白画”,指仅用墨线勾描物象而不着或少着颜色的技法。在古典小说中,“白描”手法也用来指以最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地描绘形象以达到传神的目的。可以说,古代白描语言的基本精神在于以简练笔墨或素淡笔墨描摹事物的本相,意于“神似”而非“形似”。“扫去粉黛,轻毫淡墨”,“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③朱铸禹编纂:《唐宋画家人名辞典·李公麟》,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即鲁迅先生所谓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④鲁迅:《作文秘诀》,《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74页。无中生有、虚中见实、以形写神、以少总多、气韵生动、客观真实、质朴传神等中国古典文化核心概念是其主要美学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京派散文语言的“白描”属于现代性的白描,是在现代白话语言整体中限制性地吸收了白描语言的以形写神、以少总多及意境等美学“形式”,扬弃了诸如古典宇宙观和美学精神及文化意韵等的传统的“内容”。京派散文现代性的白描,典型表现在意境的创造上,它已经不似单纯的中国古典文论中由王昌龄的“心中了见”,释皎然的“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以至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及司空图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的以道、禅之说揭示的“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得其环中,超以象外”的“意境”说的美学本质,而是带有了现代理性的思考。如沈从文《湘行书简·夜泊鸭窠围》一文中对鸭窠围的描写,这里吸取了古代白描以少总多、临境生情的古典神韵,但显然也趋向于一个分析的体系,超越完全感性和经验的世界,追求一个体验和恒久的真理世界。沈从文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已不仅仅是湘西那种人与自然和谐融合、与“道”合一的高远境界,同时更多带有了现代的理性思考。沈从文关注的已不是现象本身的意义,即超越了“天人合一”的物我合一精神境界,开始寻找现象背后的本原和认识论的知识。
线性与非线性叙述的交融也是京派散文白描手法现代性表现的重要方面。所谓线性叙述,即是指那种由远而近、自上而下、从大到小、先物后人的讲述方式,是对古代文学叙述方式的概括。线性叙述的内在根据是中国古典宇宙观:人生存于宇宙整体之中,与之同流依存,却又能以开放之心灵及流动之目光作远近、大小、上下、物我间的仰观俯察,感受其生动气韵,并因此发现到人本身所存于其中的宇宙的线性特征,以及人与自然的循环往复、“氤氲化生”的生动画卷与深长韵味。其所蕴涵的显然不仅仅是语言的本身,但这种线性叙述却成为中国古典诗、词、小说、绘画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一个表征。由远而近、自上而下、从大到小、自物到人的线性叙述,表现在语言组织上即是白描,以简洁素朴传神为要。京派散文的白描语言突破了线性叙述的单一限制,是线性与非线性叙述的交融,形成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杂语喧哗格局。
以何其芳的散文《墓》为例。文本的开头,对铃铃之墓周围环境的渲染所遵循的大致是线性叙述:初秋的薄暮,翠岩的横屏环拥着草地,高大的柏树,幽冷的清溪,阡陌高下的田亩,黄金稻穗的波浪,柔和的夕阳,等等,共同组成了一派清幽凄冷的从大而小、从上而下、由远而近的环境。
接着叙述了相较完整的三个片段:1.铃铃十六载寂寞而快乐的成长过程。2.铃铃的期待与希冀及短暂的生命。3.雪麟的“独语”。完全是跳跃式的心理写实,并具体采用了印象式、意识流、蒙太奇等现代性手法。
片段1:作者一任意识的流动,诗意叙述了铃铃过去的生命:那“茅檐”“泥蜂做窠的木窗”“羊儿的角尖”濯过其手,回应过其寂寞的捣衣声的池塘是她过去生活的环境;“她的眼睛、头发、油黑色的皮肤,时或微红的脸颊、双手,照过她影子的溪水会告诉你”①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她的善良、和气、谦卑,“亲过她足的山草,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请过的小蚁”等会告诉你;“她会天真地对着一朵刚开的花或照进她小窗的星星寻索一个快乐或悲哀的故事”②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农事忙时,她会给她的父亲送饭到田间;蚕子出卵之际,她会小心地经营着蚕事;她会同母亲一起,收割屋后的麻,绩成圈圈的纱;她有一个祖母传下的小手纺车……她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
片段2:她常常以做梦似的眼睛迷漠地望着天空或是辽远的山外;她有些许的忧愁于眉尖,伤感在心头;她紧握着却又放开手叹一口气地让每一个日子过去,她病了;秋天的丰硕依旧,铃铃却瘦损了。黑暗遮到她眼前,无声的灵语吩咐她休息。
片段3是对雪麟的描写:他有铃铃一样郁郁而迷漠的眼神,他是铃铃期待的。雪麟见了铃铃的小墓碑,便踯躅在这儿的每一个黄昏里,猜想着这女郎的身世、性情、喜好。于是一个黄昏里他遇见了这女郎,他向她诉说着外面的世界及美丽的乡土;他给她讲《小女人鱼》的故事,向她诉说着爱的痴迷……
显然,三个片段又分别由更小的片段与所要表达的中心片段串联组接,而一个个小的片段基本上都是作者内心的独白、自由联想、现实与虚构等心理意识内容,这种心理意识突破了时间与空间为序的传统,将过去、现在、未来时序颠倒和空间相互交错、渗透,重视表现式的主体因素对客体的渗透,追求心灵的写实化。同时,心理意识的内容又多是写意的、感觉化的、碎片化的、印象式的内容。
京派散文很重视语言的色彩,但不完全同于绘画中对色彩的运用,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具体表现为:有时为了强调色彩美,往往运用各种色彩涂抹周围一切物象,呈色彩斑斓之韵调。如何其芳的《墓》(1933年)中对初秋的薄暮描写:“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有常绿的柏树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阡陌高下的毗着,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黄昏和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从树叶探进来,落在溪边的一个小墓碑上,摩着那白色的碑石,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柳氏小女铃铃之墓。”③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作者所见到的一切都赋之于颜色,产生油画般的效果。
有时则带上浓烈个人的情感色彩,作者对色彩的选取与调配有时甚至有绝对的支配权,流露出鲜明的主体情感的痕迹。如何其芳《秋海棠》(1934年)中的一段:“景泰蓝的天空给高耸的梧桐勾绘出团圆的大叶,新月如一只金色的小舟泊在疏疏的枝桠间。粒粒星,怀疑是白色的小花朵从天使的手指间洒下来,而碎宝石似的凝固的嵌在天空里了。但仍闪跳着,发射着晶莹的光,且从冰样的天空里,它们的清芬无声的霰雪一样飘堕。”①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由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感情是一种忧郁和伤感,故在色彩的选择上也是冷色调为主导。景泰蓝的天空、金色的新月、白色的小花似的粒粒星……都给人一种苍凉和冰样的感觉,与主体的情思相映衬。沈从文《鸭窠围的夜》中:“河面上一片红光,古怪声音也就从红光一面掠水而来。原来日里隐藏在大岩石下的一些小渔船在半夜前早已悄悄地下了栏江网,到了半夜,把一个从船头伸出水面的铁兜,盛着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用木棒槌有节奏地敲着船舷各处漂去。身在水中见了火光而来与受了柝声吃惊四窜的鱼类,便在这种情形中触了网,成为渔人的俘虏。……这时节两山只剩一抹深黑,赖天空微明为画出一个轮廓。但在黄昏里看来如一种奇迹似的,却是两岸高处去水已三十丈上下的吊脚楼。这些房子莫不俨然悬挂在半空中,借着黄昏的余光,还可以把这些希奇的楼房形体,看得出个大略。”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248页。这里作者的主观感情似乎也在影响着色彩的选择。红色为主色调,熊熊烈火的油柴把整个河面照成红的了,仿佛那古怪声音、木棒槌有节奏地敲着船舷的柝声都变成了充满色彩美的音乐。这一切是那么的朴素、那么的平常,却又那么的丰腴灵动,有着暗示性与音乐性的色彩美。
有时则不直接用青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本身,而是借助形象化的语言,以深浅浓淡等各种不同的语言色调,摹画出更加鲜明强烈的色彩,造成极为状貌传神的艺术效果。这种手法常常为了强调情感的流露。如汪曾祺《花园·茱萸小集二》中所写的花园,就很少写颜色本身,而是写了记忆中菖蒲的味道,及巴根草、臭芝麻、腥味的虎尾草等各种草给“我”的乐趣;玩垂柳上的天牛、捉蟋蟀、捉蝉、捉蜻蜓、捉土蜂等童年的欢乐;故乡的鸟声及童年养鸟;自己掐花及花给一家人的幸福等,作者所要表达的是浓烈的乡情与逝者已矣的伤感。为了表达此生命的体验,则用了各种浓淡深浅的语言色调及形象化的描述,极写童年家中最亮的地方,并强调说:“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虽未直接写颜色,但却能感觉到色彩的韵调。林徽因的《窗子以外》由窗子产生联想,她从窗外四个乡下人的背景谈起,浮想联翩,想到了平原、山峦、麦黍、米粟,由家里的雇工想到了拉车的、卖白菜的、推粪车的、买卖货物的、追电车的,还谈到了坐车过站的老太太等等,对颜色未着一词,却有五彩斑斓之感。
另外,像以形传神、形神毕肖的中国画法在京派散文也有表现。以形写神,重在一个“形”字,“形”是重点是基础,无“形”而传“神”则易空洞无物,但一定要抓住能传达人之心灵的那个独特的有意味的“形”,是属于心灵的“这个”的“形。传神写照的绘画方法在中国由来已久,古代艺术理论史上,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最早提出“以形传神”。相传他画人常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③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5页。其所强调的即是“眼睛”,是属于“形”的“这个”,以之传神,则神情活现,神理如画,形具而神生,而不必在“四体妍媸”等枝上多费笔墨。但写“形”一定要意在传神,传其神,着力于写其心。如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中对女人的描写:“女人脸上呈块红色,头发披下了一缕,又用手抓上去。”④林徽因:《窗子以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9月5日第99期。短短一句话,就把女人那种慵懒、闲散、郁闷的神态写活了。
四、“文”“乐”相融
京派散文有着很强的节奏感,这“节奏感”原就属于音乐的,指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而京派散文的节奏是引申了的音乐的节奏。具体表现在声音的节奏、句型的节奏、描写力度的节奏等。节奏艺术的精心营构,亦让京派散文充满了乐感。
(一)声音的节奏
“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①[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84年版,第166页。此话主要是针对诗歌说的,对散文也同样适合。声音当与情绪有关,通常意义上说,散文的情韵节奏不讲究押韵,不讲究整齐的句法(当然也不排斥整齐的句法)。然而,有时散文中插入少量有韵的句子,则能使语言在五音错落中呈现重复与再现,读来铿锵、有韵。沈从文、何其芳、汪曾祺等的散文语言都具有着抑扬顿挫、音节变化、语调流转、优美和谐的节奏艺术。
比如沈从文《白河流域几个码头》中,在叙述自己游踪时多用的是散句,但叙述之中也间有句式整齐、颇有韵味的四字句:“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黛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353-354页。铿锵有力,且充满着稳定感。这种长短句式参差有致,整齐和不整齐处的和谐统一,产生了一种错综的美。《沅陵的人》的中:“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堆蓝。早晚相对,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驾螭乘霓,驰骋其间。绕城长河,每年三四月春水发后,洪江油船颜色鲜明,在摇橹歌呼中,联翩下驶。长方形木筏,数十精壮汉子,各据筏上一角,举桡激水,乘流而下。其中最令人感动处,是小船半渡,游目四周,俨然四周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画。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③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353-354页。也是长短句交错,以及大量的四字句式,呈现出整齐与不整齐和谐统一。
声音的节奏,使京派散文充满着音乐性,既有着诸多因排比、对偶的运用而产生的整体美,更有着因句子长短参差、伸缩有致的参差美。
(二)句型的节奏
好的散文在句型上也有着一定的节奏感。通常,动作快,节奏强烈,急促,宜用短句;重说理,重抒情,节奏舒缓处,则常常用长句。以汪曾祺《风景》系列散文之一的《堂倌》为例,文中说自己对坛子肉不感兴趣的很大原因与那个堂倌有关,堂倌低眉,对客人的下作让人感觉生之悲哀,他很干净,但绝不是自己对干净有兴趣。简直说,他对世界一切都不感兴趣。这里,作者感情平稳,以长句叙述,节奏比较舒缓。但接下来对堂倌的具体描述中,则有:“他不抽烟,也不喝酒!他看到别人笑,别人丧气,他毫无表情。他身子大大的,肩膀阔,可是他透出一种说不出来的疲倦,一种深沉的疲倦。座上客人,花花绿绿,发亮的,闪光的,醉人的香,刺鼻的味,他都无动于衷。他眼睛空漠漠的,不看任何人。他在嘈乱之中来去,他不是走,是移动。他对他的客人,不是恨,也不轻蔑,他讨厌。连讨厌也没有了,好像教许多蚊子围了一夜的人,根本他不大在意了。他让我想起死!……说什么他都是那么一个平平的,不高,不低,不粗,不细,不带感情,不作一点装饰的‘唔’”,“我们叫了水饺,他也唔,很久不见,其实没有,他也不说,问他,只说‘我对不起你。’说话时脸上一点不走样,眼睛里仍是空漠漠的。我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④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7页。显然,这里短句居多,节奏强烈,急促。
(三)描写力度的节奏
京派散文的语言节奏有时还通过描写的力度来呈现,以使文本力量的发展方向与变化自然地交织起来,形成鲜明的节奏。
仍以李广田的《山水》一文为例。文本的起始,娓娓叙说平原之子因读山水之文而产生的寂寞、悲哀,以及对远方山水的想象与神往。行文至此,节奏都比较舒缓。接着述说自己的祖先如何来此平原,如何改造平原。以己之力,改造天地,开始一伟大工程,凿成一道大川流。从此以后,“我们”祖先才可以垂钓,可以泅泳,可以行木桥,可以驾小舟,可以看河上的烟云。“我们”的祖先仍是觉得不够好还要在平地上起一座山岳。用一切可以盛土的东西,运村南村北之土于村西,又把那河水引入村南村北的新池,于是一曰南海,一曰北海,山是土的,于是采西山之石,南山之木,进而成为:峰峦秀拔,嘉树成林,年长日久,山中梁木柴薪,不可胜用,珍禽异兽,亦时来栖止,南海北海,亦自鱼鳖蕃殖,萍藻繁多,夜观渔舟火,日听采莲歌。描写的力度增强,节奏开始加快。接下来在文本末尾却总结说:“然而我却对你说了一个大谎,因为这是一页历史,简直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永远写在平原之子的记忆里的。……那里仍是那么坦坦荡荡,然而也仍是那么平平无奇,依然是村落,树木,五谷,菜畦,古道行人,鞍马驰驱。……我在那平原上生长起来,在那里过了我的幼年时代,我凭了那一块石头和几处低地,梦想着远方的高山,长水,与大海。”①李广田:《李广田全集》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节奏再度松弛。行文一波三折,以描写的力度控制行文的节奏。
结语
京派散文的语言是一种古今中外狂欢化的语言形态,其“陌生化”的“整体感”,以及奇警的譬喻,似绘的行文,音乐的节奏等,集中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审美与文化的多重内涵。它以较为纯熟的现代汉语句式,融合感性与理性,以精英化独白等表现形式,为读者营造了一种感性与思辩、平淡而丰蕴、古典而现代的语言盛宴,让人产生鲜活与无尽的现代性的形象想象。它弥漫着中国固有的神韵,又氤氲着现代性的美感。在一定的意义上,京派散文的语言标识了京派散文的艺术高度,是京派散文甚至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散文艺术的集中体现。或者直接地说,京派散文的语言是中国现代散文语言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