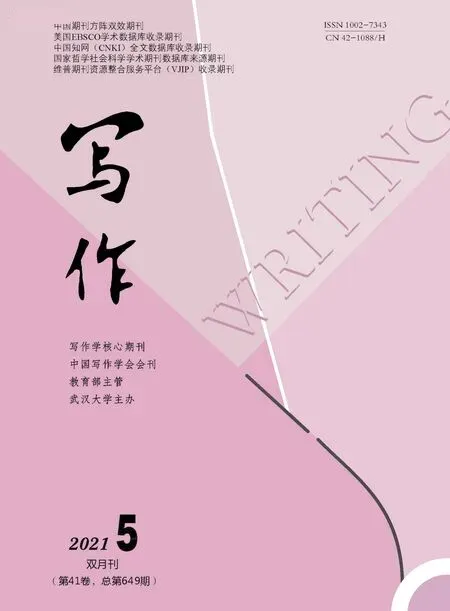灾难中的大地和灵魂之思
——读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
2021-11-21樊义红
樊义红
在以往的中国当代小说中,以地震作为直接表现对象的作品几乎可说是一个空白。这本身就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殊不知在中国的疆域内和历史中,地震其实频繁发生,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大的地震就有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等。当然,我们有其他的艺术形式做了这个工作,比如大量的新闻报道、电影《唐山大地震》和诗歌集《汶川大地震诗歌经典》等。在这个意义上,阿来的小说《云中记》首先具有一种突破性,这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来挑战这一题材,本身就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对新的经验的书写固然不易,不过作品最终还得靠质量说话。《云中记》面世以来,就收获了不错的反响,一时好评如潮,得到了一些著名的评论家如陈晓明、谢有顺等人的高度肯定。
或许更多地受到主流新闻报道的影响,关于地震或其他天灾题材的书写,容易被简单地处理为“地震无情人有情”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或“多难兴邦”之类的固定模式,这些写作套路确实能发挥一定的抚慰人心作用。但若以真正文学的眼光来看,其一,这些表达显得过于雷同,因而缺乏新意。这是文学写作的大忌。其二,它们缺乏一种直面悲剧的勇气和精神。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曾说:“悲剧这种戏剧形式和这个术语,都起源于希腊。这种文学体裁几乎世界其他各大民族都没有,无论中国人、印度人,或者希伯来人,都没有产生过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①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20页。悲剧的匮乏其实源于悲剧精神的缺失,这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过于务实,以至于缺少了对务虚的、沉重的和虚无的对象的关注和思考。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处理地震这类灾难题材时所应当面对的问题。其三,它们往往浮于表面,缺乏一种对自然、生命和灵魂的深刻透视。地震往往不仅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更带来大量人员的残疾甚至是死亡。特别是面对后者时,过于轻巧的表现和简单的反思似乎都显得有些不负责任,暴露出文学的某种无力甚至是无能。对于以往地震书写的上述弊端,阿来或许也是深有感触,所以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迟迟不愿动笔写作。“那时,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地震题材,我也想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这种警惕发生在地震刚过不久,我们写作地震题材的作品,会不会有意无意间带上点灾民心态?让人关照,让人同情?那时,报刊和网站约稿不断,但我始终无法提笔写作。苦难?是的,苦难深重。抗争?是的,许多抗争故事都可歌可泣。救助?救助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但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自己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①阿来:《不只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文艺报》2019年6月12日第3版。终于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后,阿来开始动笔写作小说《云中记》,这是“十年磨一剑”的写作,也是痛定思痛的写作。《云中记》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和思考?
一、地震书写和灾后的生活
地震或许只会不定时地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地域,但是地震之类的天灾却从未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上消失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地震和地震后人们生活的书写首先具有一种认知上的价值,并能带给我们别样的生命感受和启示。而且相较于其他文体,小说以其较长的篇幅和强大的叙事潜能,在这方面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未曾经历过地震的人们看来,地震可能只是一方地域的灾祸,是一个个死亡、伤残和失踪的人的抽象数字,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生命极端体验。《云中记》却告诉我们,地震不仅仅是人类不愿面对但又难以逃避的一种劫难,虽然在此意义上它意味着生命失去、身体伤残、房屋毁坏、财物埋葬和家园不再等诸多不幸。小说中对地震发生时的惨状有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描写:
“大地失控了!上下跳动,左右摇摆。轰隆作响,尘土弥漫!
大地在哭泣,为自己造成的一切破坏和毁灭。
大地控制不住自己,它在喊,逃呀!逃呀!可是,大地早就同意人住在大地上,而不是天空中,所以人们无处可逃。
大地喊:让开!让开!可是人哪里让得开。让到路边,路基塌陷!让到山前,所有坚硬的东西都像水向下流淌,把一切掩埋。
大地喊:躲起来!躲起来!人无处躲藏!躲在房子里,房子倾倒。躲在大树下,大树倾倒。躲进岩洞里,岩洞崩塌!”②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9、166页。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地震对人类生命的毁灭是无所谓标准的,不论人的善恶和信仰如何。在汶川大地震中死去的不仅有云中村的恶人,也有好人。在地震中“消失的村庄有汉族的村子,有羌族的村子,也有藏族的村子。这些村庄的信仰各式各样”③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9、166页。。地震还给那些侥幸生还的人们带来无法消除的心灵痛苦和精神创伤,而这是他们的余生都不能彻底治愈的。小说中祭司阿巴曾经历过一次发电站的滑坡,他虽然奇迹般地生还,却因此失去记忆十多年,给母亲、妹妹和自己都造成了巨大的心灵痛苦。地震还可能造成一方人群的历史和文化的终结。地震让云中村彻底消失了,与之同时消失的还有关于云中村的许多历史和文化记忆。云中村曾经存在了一千多年,云中村人的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了一代又一代,它不仅仅是一块栖居之地,还沉淀了漫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记忆,这对于居民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让云中村人生活得完满而自足。地震后云中村人搬迁到移民村,却感觉“移民村好是好,就是心里总有一块地方空着,脑子里也有好多地方都空着”①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6、195、202页。。这种精神的“空缺”状态其实源于人们对居住之地文化记忆的缺乏,它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无所依凭。而这种心灵的窘况有待漫长的时间去修补。
灾难虽然发生了,但生活还得继续。地震后生还的人们将何去何从?云中村的百姓先是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进行艰难而坚强的灾后救援,后又被迫迁往移民村开始新的生活,对死去亲人的思念和异地生活的不适却时时萦绕于心。小说中写到了灾民们因为地震对干部和政府毫无理由地抱怨,对志愿者们借机释放心中的负面情绪,这都是一些非常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体现了阿来对生活独具慧眼的发现。小说中还写到,云中村人不愿意听从救灾干部的安排在电视台记者面前唱《感恩的心》来“表演”感恩,而要以自己的方式自然而真实地表示感恩,比如父亲替解放军补鞋、老奶奶吻解放军的手、孩子送解放军野草莓等。这类细节折射出汉、藏两个民族的人民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属于对“民族性”的深层把握,虽着墨不多但意味深长。关于文学的民族性,阿来曾这样说道:“文学意义上的民族性,在我看来,不只是由语言文字、叙述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而主要还是由行为方式、生活习性所体现的一定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意识。这种内在的东西,才应该是民族性的魂魄。”②张江、朝戈金、阿来等:《重建文学的民族性》,《人民日报》2014年4月29日第14版。可以说,上述描写就是阿来对这种“内在的民族性”进行表现的最好写照。当然,这种所谓的“民族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处于变化发展之中。经历过地震的摧残之后,云中村人也一改之前含蓄内敛的性格,学会了直接地表达心中的爱意。“地震前,云中村人不会这么直白地表达感情。地震后,人们学会要直接地把对亲人的爱意表达出来。地震前,阿巴不会拉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外甥的手。现在,他已经学会不要只把爱意留在心里了。”③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6、195、202页。这是因为,“爱这个东西,在心里藏得太深,别人也就感觉不到了。”④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6、195、202页。年轻而能干的乡长任钦作为从云中村成长起来的优秀领导者,积极而有效地带领大家进行灾后救援和重建。一方面,作为一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基层干部,他扮演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形象。另一方面,他也是土生土长的云中村人,并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这使得他又时时和云中村人站在一起,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小说对他的这种双重身份的分裂、斗争和统一的表现作了相当细腻和有分寸的刻画,这使他成为小说中除主角外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还有借助云中村和自己的灾难博取公众同情的舞蹈演员央金和妄想靠消费云中村的苦难赚取游客金钱的恶人中祥巴,虽然一开始暴露出人性的丑恶一面,后来也在良心的复苏和舆论的压力之下幡然悔悟。对这种转变的描写虽然带有阿来小说中一贯的理想主义特色,但也表现了他们对家乡所怀有的一种朴素而深厚的感情,以及灾难之后人性的复杂变化。
小说主人公祭司阿巴的选择尤其让人颇费思量和唏嘘感叹。他在移民村生活了四年之后,不顾众人的劝阻,毅然选择回到将要消失的云中村,祭祀山神和安抚鬼魂,最后终于被彻底滑坡后的云中村埋葬。阿巴的选择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寻死行为,甚至不是极端意义上的殉葬行为,我们必须从云中村的文化和个人性格两个角度来理解阿巴的所作所为。云中村的文化实际上属于藏族文化之一种,这个村子的百姓一直以来普遍笃信苯教而非藏传佛教。“苯教作为藏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承袭了比它更古老的藏族先民的原始文化,是佛教传入藏区之前藏族人普遍的信仰。”①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可以说,云中村的文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更为传统的藏族文化。这种文化认为,祭司是不可或缺的,对山神的祭祀和对鬼魂的安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阿巴身为云中村的祭司,回到山上做上述事情其实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从阿巴自身来看,他生性善良而执拗,有舍己为人的精神,热爱自己的家乡,因为妹妹和村民的死去而怀着巨大的痛苦,并且有着高度的职业信仰。凡此种种,终于使他放弃了在移民村的安定生活,回流到云中村,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应该说,阿巴是阿来创造的一个带有藏族文化色彩的新人形象,这可以看作小说《云中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二、人与大地的冲突与和解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已有着漫长的历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立足于大地,即便借助现代的飞行工具,人对地面的逃离也只是短暂的,大地才是我们生活的根基。人与大地的关系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关系,也是文学应该重点关注的主题,不过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小说中书写这方面内容的作品委实不多。或许由于这个对象过于宏大难以表现,又或许由于这种关系过于稳定和缺少变化以至难于觉察。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受限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既往的人们包括作家还无法深刻地认清这个宏观的问题。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航空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的时空观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开始习惯不仅在地球甚至在整个宇宙中来观照人类的生存。表现在文学领域,比如近些年科幻小说的兴盛就给以往的文学时空观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风靡一时的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和文学背景下,阿来的小说《云中记》借助于所书写的地震这一特定对象,致力于对人与大地的关系进行宏观和深度的思考。
小说中的云中村存在的历史有一千多年之久,传说中这本是矮脚人的住地,云中村的祖先阿吾塔毗率领着部众打败了矮脚人,从此云中村人世世代代居住于此。这里地形隐蔽,风景优美,土地肥沃,是一个世外桃源和人间天堂般的存在。云中村人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不愿意像其他六个村子一样搬到山下和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时的云中村人自觉有山神庇护,虔诚地祭神敬神,在云中村诗意地栖居,与大地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这可说是一种理想的人与大地的关系。但地震终究无情地发生了,带给云中村人无尽的痛苦。更可悲的是,由于地质运动,云中村还将彻底滑坡和消失,这毁灭了云中村人灾后重建的最后希望。感觉被山神和云中村彻底抛弃的云中村人,心中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怨恨,人与大地这时貌似呈现为互相敌对的关系。这好比小说里在地震中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而自己也失去了一条腿的姑娘央金的舞蹈所表达的内容——“姑娘身体的扭动不是因为欢快,不是因为虔诚,而是愤怒、惊恐,是绝望的挣扎。”②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25页。以往表现地震的作品如汶川大地震后出现的众多诗歌较多地表达着这种情感,大地被描绘为一个无情无义的终结者形象。但人对大地的这种怨怼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人无处可逃,终究要在这大地上生存,这是人类无可选择的宿命。祭司阿巴终于在地质学余博士的启发下明白了大地其实并非与人为敌,只是自身自然运动的结果。“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大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腰。唉,我们人天天在大地上鼓捣,从没想过大地受不受得了,大地稍稍动一下,我们就受不了了。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①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45、376、306页。由此,人与大地取得了最后的和解。和解,或许是人类面对地震的最好态度,以此人类才能在这大地上更好地生活,跳出我们的生命之舞,那舞蹈是在“柔和中又带着更深沉的坚韧和倔强”②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45、376、306页。,彰显着人类生存的坚强和生命的尊严。
纵观上述人与大地的关系嬗变历史,可以看出,小说《云中记》不同于以往对这一主题的表现,而闪耀着最为前沿的生态观念的光辉,故而借用生态批评的理论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更为有力地透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当代一种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学批评,它承袭了自然文学的传统,但又有别于自然文学。生态批评旨在对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等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述与研究,同时又倡导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从而使人类建立强烈的生态观念及忧患意识。”③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487页。在《云中记》中,当云中村的灾民们因为地震而怨恨曾经承载和孕育了他们的土地时,其实是一种在我们的文化中流传已久的人类中心思想作祟的体现,以为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应该是被征服和被驾驭的对象,必须为人类服务,至少不能与人作对。大地成了一种人类的附属物而无主体性可言。当今世界的发展已经证明,正是人类这种思想和实践让今天的地球生态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已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而生态批评的理论假设之一是“假定自然、世界和人类拥有本体论地位,也就是说,自然确实存在,而且人类的语言、概念或信仰不能涵盖或充分描述和编码自然。”④[美]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赵勇、李莎、常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7页。所以,当阿巴领悟到地震并非大地与人为敌,只是自身运动的表现之时,这真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重大时刻。这种领悟虽然带有阿巴为云中村的不幸命运寻找精神解脱之目的,但何尝不是一次对人与大地的关系进行的全新考量?不错,自然本身是有本体性地位的,只不过被后来人类文化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人类中心思想所遮蔽和无视了。这就像小说中的地质学余博士所说,自然也有自己的意志,而且“人再强,也强不过自然意志”⑤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45、376、306页。。面对具有自身意志的自然,在地震这类地质灾害面前,人类除了与大地和解别无他途。
和解何以可能?它要求我们在面对不可抗拒之物譬如天地运行之道、历史和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个人无力把握的命运等对象之时,不以人类主体的意志强加于这些客体,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这些客体的规律,并坦然接受那些外物赋予我们的命运。小说中的阿巴和任钦都具有这种可贵的品质,所以阿巴最终理解了云中村的命运,而乡长任钦面对自己因为舅舅不肯下山而被撤职的命运也可以平静接受,并不怨天尤人。其实,这种与不可抗拒之物进行和解,坦然接受自身命运的现象在阿来的小说中颇为常见。比如《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就是因为看到了藏族不可逆的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和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从容地选择了被仇人所杀。小说《蘑菇圈》中的斯烱面对自己不幸坎坷的命运也是坦然接受,并不想刻意地去反抗某些人和事。阿来倡导的这种“和解”的精神不同于海明威小说中打不垮的“硬汉精神”,也不同于加缪笔下对抗自身的荒谬命运、进行坚强而徒然抗争的“西绪福斯精神”,它与藏传佛教的“随缘”思想有关,也类似于道家所说的“道法自然”的精神。它看似消极和保守,其实未尝不是在明白了天地和人事之道后的一种大彻大悟和明智之举,对于今天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其实不无启发意义。
三、灵魂的有无及其归处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对于全书而言至关重要,但又颇费思量,这就是祭司阿巴不顾生命的危险,执意回到云中村祭祀山神尤其是安抚鬼魂。这一举动让外甥任钦因此受过,也让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也正是这一情节,让小说始终游走在魔幻现实主义写法的边缘却保持着理性的克制,而终于走向了对灵魂有无及其归处的存在主义式追问,使小说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超越意味。
祭司阿巴选择追随云中村走向灭亡,使整部小说都笼罩在悲剧的氛围中。但他安抚鬼魂这一举动却曾令许多人不解,甚至被副乡长洛伍斥为装神弄鬼。更为尴尬的是,就连阿巴本人,对鬼魂的存在其实也是半信半疑。小时候听老师讲鬼故事和看见祭司父亲半夜里祭祀做法时,他对鬼魂的存在有一种本能的惧怕。长大后他上了农业中学,还成了云中村的第一位发电员,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无神论教育基本上让他否定了鬼魂的存在。虽是家传,他并没有随父亲习得多少祭祀的本领。地震后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村民的心,鼓舞他们开展灾后重建,他才被迫走上了祭司的道路。但因为没有亲见,他对云中村人都相信的鬼魂的存在还是将信将疑。返回到云中村后,他甚至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夜晚在废墟中寻找鬼魂,但还是无所发现。身为祭司却对鬼魂的存在并不坚信,看似有点自相矛盾,这一方面与他年轻时受过的无神论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不过是正迈入现代社会的云中村人普遍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传统的宗教文化观念正日渐式微,人们关心现世的事情甚于一切超验的鬼和神。这正如文中所说:“地震发生前,云中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谈论鬼魂了。人在现世的需要变得越来越重要,缥缈的鬼魂就变得不重要了。”①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311-312页。虽不坚信,却要与时日无多的云中村共存亡,这更可以见出阿巴一心为公的高尚情操——他担此重任与金钱无关,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好地生活,不要有精神上的牵挂。
不过,富于理性探究精神的阿巴却一直想要看清鬼魂的存在与否。在这里,阿来保持着相当的克制精神,没有采用以往藏族小说中司空见惯的魔幻现实主义笔法让鬼魂不负责任地出现,给阿巴和读者以廉价的精神安慰。而正是这种处理方式让小说转向了对死亡的存在主义式追问。人的生命的过程,必经生老病死这几个发展阶段。死亡是生命的终结,这是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节点,但关于死亡的思考却是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一个较大缺陷。阿来认为:“我们中国人实在不会面对死亡,我们对待死亡大概是这样的过程,一时悲痛,然后交给时间去打磨,然后遗忘,而不能从死亡中得到更多。”②转引自毛亚楠:《〈云中记〉:大地并不与人为敌》,《方圆》2019年第12期。由于普遍受到儒家思想(如孔子的观点——“未知生,焉知死”和“不语怪力乱神”)和无神论教育的影响,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汉族作家们很少在作品里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其实抛开所谓科学的解释,关于人死之后灵魂的存在哪怕只是一种无法证实或无须证实的信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死亡带给人们的痛苦和绝望,给活着的人特别是亲人们以莫大的精神安慰。正如文中的地质学余博士对阿巴安抚鬼魂这一举动的评价:“博士也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一个残酷的事实。也是一个美丽的事实。是身旁这个人关于人死后那些鬼魂的信念使得残酷的事实变得美丽。”③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311-312页。人类无法改变死亡的事实,却可以通过鬼魂之类的信念给人以精神的慰安,让活着的人可以更好地生活下去,也更从容地面对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表现的正迈入现代社会的云中村人宗教观念的淡化甚至消失,何尝不是文化发展中的一种损伤,它让云中村人在亲人的死亡面前悲痛之余只剩下精神颓唐,一时间丧失了好好生活下去的意志。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受过现代教育的阿巴要重新做回祭司,这绝不是一种所谓精神的倒退,而恰恰是在面对死亡一类的人生难题时,人们无法找到精神的“解药”,只能通过对传统宗教的皈依来救赎自己的灵魂。阿来曾说过:“我的宗教观我觉得永远面临着困境,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有着强烈的宗教感,但是我从来不敢说我是一个信仰什么教的信徒,比如说佛教。”①转引自夏榆:《多元文化就是相互不干预——阿来与特罗亚诺夫关于文明的对话》,《花城》2007年第2期。虽非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阿来的创作却从藏传佛教中受益良多,在这里阿来无疑是寻找到了佛教在处理死亡问题时的精神抚慰功能。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此意义上来理解小说《云中记》的意义。面对地震之类的天灾,小说何为?它无法起死回生,没有任何实际的效用,但如果它可以“安魂”——安慰死者和生者的灵魂,那也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小说中阿巴曾与多人讨论过人死之后的归处问题,藏族苯教和佛教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苯教认为人死后变成鬼,鬼存在一段时间以后要么消失于大化之中,要么变成精灵(由小鬼所变)。佛教则认为人死后变成鬼,然后转生为人或畜生。阿巴作为信仰苯教的祭司,倾向于相信苯教的观点,虽然这种说法看似不如佛教的说法对生者的所作所为具有规训作用。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阿巴却对这个问题作了这般总结:“我以前想的是,我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了,这个世界就等于没有了。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在,世界就没有消失。只要有一个云中村的人在,只要这个人还会想起云中村,那云中村就没有消失。”②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58页。人死之后魂归何处?他将活在后人的记忆里。人类的记忆是抵抗死亡的最后堡垒,生命将以延续的方式来对抗自身消失的悲剧性。人类就是这样生生不息,从古至今,直到未来。这种对“灵魂”归处的理解不再带有任何超验的色彩,但却道出了人类的生命、历史和文化延续至今的奥秘。
综上所述,小说《云中记》以一种直面悲剧的勇气和精神,不仅正面地展开了对地震和灾民的出色书写,而且在此基础上深刻地探讨了人与大地的关系、灵魂的有无及其归处等问题。在以上书写过程中,小说始终渗透着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悲悯精神,虽写绝望也给人希望,虽写消失也展望来世,给读者以莫大的精神抚慰。在此意义上,小说《云中记》堪称灾难文学领域一部难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