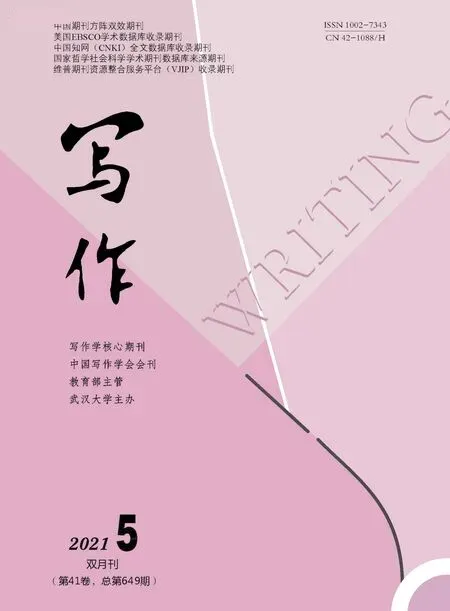鲁迅小说中绽现的现代诗
2021-11-21骆冬青
骆冬青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狂人日记》有一文言小引,叙述者似属于时代结点上的人。从此小引起,预示了文本的断裂——果然,白话文一开头,就将我们带入现代的情境。古典的月光,一旦接上“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便令人陡然心惊,充满疑惧、不安。不过,下转一句:“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爽快”得怪哉!这是精神觉醒么?但何以“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且“然而须十分小心”呢?因为怕么?“我”的“怕”,凝聚在“看我两眼”的狗眼中,让这“有理”的“怕”更加恍惚游移。
窃以为,这个开头,无须分行,就是精妙的现代诗!
那种神经质般的敏感,那种迫害狂般的惊悚,那种对自然物的无感和猝然的锐感,那种突然的陌生和茫然的醒悟,岂非现代诗歌内在精神特质的显露?或曰,20世纪西方的“荒原”感,来自失去信仰、传统价值观衰败、新价值观尚未建立之际的绝望。其实,鲁迅笔下的狂人,所处境遇,尤其如此。借着狂人之口,鲁迅以白话文发声,一出口便是惊悚诡谲的现代诗!当然,此时西方现代诗《荒原》尚未出场,《荒原狼》尚未嚎叫,可是,“赵家的狗”却已莫名地、令人慌乱地、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并且在我们的耳边叫了又叫。
这部堪称现代文学开山的小说,其实乃诗性的小说。其中蕴涵的现代诗歌,“于无声处听惊雷”,惊雷阵阵,当我们在某种震撼中忽地警醒,往往却忘掉其诗性的特质——“无声”——传统诗歌的韵律、声调消失了,与“无声的中国”相合拍的,却是“荒原”般的呐喊。这是中国现代诗诞生的真正标志。
一
《摩罗诗力说》提出的“撄”,是一个现代人已然陌生的动词,指向的是反抗,是触犯、冒犯、抵触,是扰乱和排击,是以摩罗诗抵抗黑暗政治。其中所涉及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诗人,如柏拉图、尼采,乃是具有诗性的哲人。以摩罗作为诗性反抗的代表性符号,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在诗学上,从异邦求来的“新声”中,包含的诗人均有现代性的因子。落实到诗本身,“撄”则表现为感觉方式上特殊的“隔”,对世界的“膈应”或“硌硬”,从而猛然惊觉自身存在的某种真相;在诗意的建构上,则以现代诗歌的无规则联想、超越传统诗歌的特殊通感来表达某种意图。
但最根本的,是西方诗歌传统中那种强烈的哲理倾向。从哲思中引发诗意,以哲学的方式感觉世界事物,乃西方现代诗歌的重要特性。不同于宋人的以理入诗,鲁迅注重的摩罗诗人往往具有精神界战士的特点,从他们开辟的精神谱系中,不难寻找到现代性的因素。鲁迅小说的诗性,每每具有现代诗的气质。
人们常称道鲁迅小说中一些特别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成为一篇之魂。如《明天》中,单四嫂子在她的宝儿死后,“他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苦苦的呼吸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自己听得明白。”似乎不是一个“粗笨”无文的妇女的感觉,而是作者渗入的某种现代感。这种将“屋子”以“太静,太大,太空”的存在主义式处理,必然导致“自己”孤立地突出,所以才会“自己”不明白的“听得明白”。苦苦的呼吸,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作者的描摹中,用了何等气力!不过,这却和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有了异样的疏离,令我们不安,却又感觉到一种特别的痛快。那种诗意领悟,以及与小说人物既亲近又疏离的感觉,似乎给我们特别的体验。叙事者与人物之间,分隔着一重诗性的藩篱。
熟悉的《故乡》中,也有出人意料的意象,带着某种奇怪的特质,那是现代诗歌所特有的气质。回故乡时的心情描绘,“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似古典的韵致,却又有某种现代的气息。而作为抒情的分段:“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曲折潆洄,一个元音“阿”(啊),呼出却又唏嘘回去那种无奈的情怀。但其自故乡归去的书写,更有现代诗歌的特色:“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隔”,这个王国维悬为诗歌厉禁的字,在我看来,却是现代诗之精魂。那种“高墙”感,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可怕分隔,乃《故乡》之魂,也是存在主义者如萨特思想的核心,萨特甚至有冠名为《墙》的小说。著名的末尾:“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分明是思绪的“隔”:那个童年幻梦般的世界,却“断裂”式地指向了关于希望、关于人与路的思索。分行写下来,更能表现其诗性特质。
或许,该注意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与通常解读不同,看似在赋予“路”以某种积极意义,却又因为谈论“希望”而令此意义有所消解:“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失落乃至虚无,正喻示着鲁迅思想中某种扭结,通向希望与绝望的深思。那么“这正如”三字下连接的人与路之思,意在“本无路”,还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恰如一首诗,留下的是不尽的咀嚼回味。这里,事、诗、思熔融为一,令这篇以抒情为主调的小说,具有别样的风情。
《孤独者》中的狼嚎,乃叙事者意想之中的,却成为此文不可或缺的意象。“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匹受伤的狼,是小说主人公魏连殳么?还是叙事者心造的幻象?“耳朵中”挣扎的那个“什么”,所来无踪,却似乎有特别的指向,指向什么,却只能意会。不过,叙事者转下一语:“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却以反激的方式,实现了张力的消解。两者之间,显然有着以“撄”人心的方式产生的荒芜,反而形成了心灵的“坦然”。最终是宁静么?“月光底下”的“潮湿的石路”,可以如古典诗歌般感悟么?恐怕,深夜的狼嗥,“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引向的还是某种哲理的思索。
尤其是《阿Q正传》,当阿Q面临观摩死刑的人们时:“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这已经是诗,“阿Q”的意识中不可能出现的“诗”;可是,另起一段:“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则更强化了诗意,以分隔的形式所作的强调,显然,是诗的、尤其是现代诗的技巧。传统诗学难有这样的诗意,它具有异化、冷峻、震惊的效果,尤其是那种穿透灵魂的哲思,更为现代诗独有。
这些现代诗的精魂,飘荡在鲁迅小说的天际,有点疏离、怪异,甚至令人产生某种不适感。可是,却又深深地契合鲁迅小说的特质,若将其取出,则令小说失去了“鲁迅”的魂魄。所以,我大胆地说,正是这个现代诗人,乃鲁迅小说中那个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二
现代诗注重断裂,令意象飘忽无定,尤其是诗的结构,以意为主,但其意却是复杂多变,遂使意脉在情灵的战抖与激荡中奔突裂变。
《狂人日记》的结构,亦是诗性的。现代文(窃以为,鲁迅文字并非“白话文”)十三节,长短无定;鲁迅根于“迫害狂”心理,以一种特殊的冷冽,凝聚到节奏中,令“情节”与“情”感本身的节奏、节律,以及“结点”(“情结”)相合为一,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断裂与耦合。断裂,以割开生活的剖面,展现出某些意象:“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直到最终:“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不妨说,《狂人日记》中,以一种特殊的自由感,放开了结构——甚至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结构,鲁迅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诞生了一种新的诗意。因此,中国现代诗歌的起始,乃是《狂人日记》。《狂人日记》以现代诗歌的叙事形式,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所罕见的另一途径。
而借着这种现代诗的形式,中国传统小说的格套被彻底打破。这是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上最大的贡献。鲁迅论《红楼梦》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0页。打破“传统的写法”,实是文学家鲁迅特别的关注。《狂人日记》创作的成功,应当是鲁迅引入现代诗的形式来结构小说的重要思路。
这一思路的延展,最为明显的征象体现在《伤逝》这样的诗体小说中。试看其从头至尾,全部是以抒情诗般的节律运行自己的思路,即可知这样的结构形式,在鲁迅已是炉火纯青。但是,却又有某种特别的阴冷感攫住我们:“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了。/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但是,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现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里,我以“/”分隔原来的段落,可令我们体会到如同《草叶集》般流动的激情与思致。但其中所蕴涵的意念,却是现代的。那就是绝望与虚无,罪感与颓靡,忏悔与沉痛……这构成某种阴郁的旋律,急促而深沉地如刀刃般切入心底。
鲁迅还有一些小说,如《孔乙己》《社戏》《兔和猫》《鸭的喜剧》以至《一件小事》等,带着淡淡的诗意的小说。窃以为,鲁迅的这些小说,也是汪曾祺小说的一种来源,即以散文式思维方式、看似随意的语言来结构小说。鲁迅还有《故事新编》这样以现代诗性重构中国古典的小说。固然,亦如鲁迅先生自言,《故事新编》的一些篇章,因题旨的不同、文学性不足,自是缺少诗的韵味,有了某种虚无的乃至油滑的东西。但是,其中的《补天》《铸剑》却带着奇异的诗性光芒。“忽然醒来了”的女娲,在古典中只是一个意象,以此构思小说,当有诗性的冲动。小说中有着诸多笔墨,都带着印象派画家的彩色:“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䀹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补天而死的女娲:“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但不知道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这时候,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女娲死了,古典却在现代诗心的熔铸中重生、复活。其结构固然以时间为经纬,可是,唤起女娲神话的诗性智慧,却以自己的意念,将许多事情“新编”进《补天》的结构中。尾声中,许多年后出场的是跨时空的人,如椽大笔扫过许多时代,让扎寨于女娲膏腴肚皮上的“人类”作出的表演,与女娲的事业之间,形成某种巨大的空洞。神话中的巨鳌出现于结束:“大约巨鳌们是并没有懂得女娲的话的,那时不过偶而凑巧的点了点头。模模胡胡的背了一程之后,大家便走散去睡觉,仙山也就跟着沉下了,所以直到现在,总没有人看见半座神仙山,至多也不外乎发见了若干野蛮岛。”这似乎不是诗,却更像诗的结句,将创世的女娲与中国人的历史作了某种怪异的总结。
《铸剑》亦有诗性冲动为根柢,且显然更深挚地表现鲁迅的某种寻根意识。眉间尺赴死的场景:“笑声即刻散布在杉树林中,深处随着有一群磷火似的眼光闪动,倏忽临近,听到咻咻的饿狼的喘息。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最先头的一匹大狼就向黑色人扑过来。他用青剑一挥,狼头便坠在地面的青苔上。别的狼们第一口撕尽了它的皮,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他已经掣起地上的青衣,包了眉间尺的头,和青剑都背在背脊上,回转身,在暗中向王城扬长地走去。/狼们站定了,耸着肩,伸出舌头,咻咻地喘着,放着绿的眼光看他扬长地走。”酷烈而冷峻的笔调中,横流而出的现代诗,置之眼下,仍然有若新发于硎的莫邪剑,剑气凛凛,似欲夺人首级。其结构亦具更强诗性,自夜间眉间尺与一只老鼠的关系写起,曲折进行到复仇的主要情节,若现代诗人所吟之叙事诗,事件之间激荡着无形的诡异与深挚的情致。似乎荒诞悖谬的结局中,以尸体发出的楚辞体现代诗歌唱,诱引大王的头颅,更令这篇小说尤其能够“撄”人心。
福楼拜说,凡小说家,最初均是意欲写诗者。可是,在小说中是否融化着诗意的冲动,则是另一回事。以现代诗的用意,形成冲动,构成小说之魂,则是鲁迅独擅之秘。“无中生有”地营造独特的诗性氛围,乃其作品絪缊着某种奇特感的因由。
最重要的,当然是小说选择的叙事者。这个叙事者,常常变化,如代数式中的x、y、z,可以“代”入各种情境,求解各类问题,但其根本,却是一个独特的现代诗人。
三
人们多认为,诗人鲁迅集中呈现于《野草》中,我却以为,小说家鲁迅,内心蕴藏的那个诗人,更充分的表达形式,还是小说。以现代诗的方式结构小说,是鲁迅小说创作冲动的深层奥秘。《野草》中一些篇章,带着鲁迅构思小说的影子。姑且不论其中的叙事性文字占有绝大多数的分量,就是纯粹抒情的文字,也深蕴着那种“情节”与“情(感)节(律)”的转换关系。解读《野草》,从小说的现代性诗学着眼,或许是一个重要途径。
例如,《在酒楼上》:“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这里涵茹着《野草》里《雪》的精魂:“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那么,是否可以从《在酒楼上》的主人公以及叙事者的心迹,追摩《野草》中鲁迅的灵台?《孤独者》:“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是否也有《野草》中关于死亡、关于秋夜的影子?不好言说。但是,其中之诗意却一脉相承。
至于《铸剑》,许多研究者指出,它与《野草》中的《复仇》《复仇之二》,乃至《影的告别》之间具有可以相互阐释的关系。其实,更重要的,当是以“诗”解“诗”,从鲁迅诗性思维,尤其是具有现代诗特质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鲁迅文学的诗性风格。
这里需特别指明,鲁迅小说之现代性,正在于以现代诗歌的方式来打破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尤其是颠覆传统小说,当然也包括许多现代文学中的小说中特有的叙事惯性,即叙事连贯性的追求。以某种刻意的断裂结构小说,造成“不适”——这与鲁迅提倡的翻译中的“硬译”也一脉相承。造就不同于一般“白话文”的现代汉语特质,恐怕主要还是要靠文学家以“现代诗”式的表达“硬写”,即以“隔”和“撄”的反常、疏离、陌生化等方式,唤醒我们的语感,让我们如女娲般“忽然醒来”,发现惯常语言中的反常,改变、改造我们的语言。
大先生的小说,其形式相当自由,有些似乎是对体裁的有意蔑视。正如他的杂文、散文、散文诗等,皆有此倾向。我想,这正是鲁迅错综诸体而进行的独特创造。《野草》中,恐怕并非皆是散文诗,有的乃是杂文,以及其他体式的文字。其因由,当与章太炎有似当今解构主义式的文学观有关。章太炎曰:“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国故论衡》)鲁迅则曰:“连属文字,亦谓之文。”(《汉文学史纲要》)德里达说:“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行动》)如此开阔的文学观,令鲁迅作品最终归宿成为“杂文”;可是,另一方面,却使其作品之间具有了丰富的“文本间性”。文本体裁的错综,在当代世界文学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在鲁迅时代,却因西方影响,而强调“文学的自觉”。鲁迅尤其是一个重要的倡导者。故而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无疑是文学独立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而生的文学以及艺术自律,乃西方学术倡导的重要主题。
可是,即使在散文诗般的结集文字《野草》中,我们还是能读到不甘驯服于某种文体规制的文字,而这种情形,自然也存在于鲁迅的三个小说集中。那么,其中还激荡着文学反抗一切规制的自由精神。这既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化那种笼罩一切的气概,更来自西方文学的激发,尤其是现代诗性的觉醒——摩罗诗——构成鲁迅精神世界的底蕴。
所以,鲁迅在小说中,以现代诗歌的意象,解体了中国古典诗歌,更以诗性的构思,解放了小说的形式结构,打破了传统小说思维的惯性。其内在动因,乃现代的诗歌冲动。
“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随乎都骤然失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眉间尺凝神细视,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却并不见得怎样锋利,剑口反而有些浑圆,正如一片韭叶。”鲁迅小说中的诗,正如这柄“青光充塞宇内”的剑器,隐匿于黄土深处,挖掘出来,“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然而这一片韭叶般的存在,不妨说,恰是鲁迅小说的真正秘藏。
四
大先生神往魏晋,深于楚辞。所擅旧体诗,颇有晚唐风格。李贺的诡谲奇特、穿幽入仄、荒寒阴郁,李商隐的绵邈深邃、情致婉约,固然凝集其中,窃以为,大先生旧体诗更孕有某种浓郁的感性的冒犯和看似鲁钝的折挫,以及由此而来的兀傲①钱锺书《谈艺录》论李贺兼及李商隐,颇与西方现代诗人如波德莱尔等相印证。亦可见晚唐诗与现代诗之款曲相通。钱锺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9-189页。。其意象构成,恰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契合,有着斑斓的古旧的现代感。“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其中,大泽、菰蒲、空云,与“梦坠”所感到的“齿发寒”,颇有意味。“竦”然而“听”,荒鸡阒寂;泠然而“起”,星斗阑干。均自出手眼,在古典意象中,袭入现代情调。再如,“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绵密深邃的意象中,似乎透入楚辞式的骚怨,但被一种排奡孤愤所超拔,令鲁迅旧体诗中总有着冷冷的反抗传统诗性的现代韵致。这,正是小说家鲁迅背后的诗人鲁迅之神韵所在。
鲁迅同乡先辈徐渭,论“兴观群怨”之诗品,曰:“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②徐渭:《徐渭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2页。“月光如水照缁衣”,常常见,却常常“不见”的月光,与从远古而来的深沉意绪融汇一气,正构成鲁迅小说惊心动魄的现代诗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