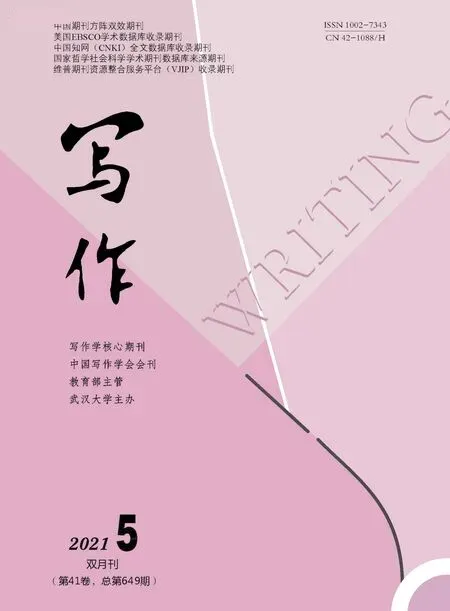“谁能够筑起墙垣,围得住杜鹃?”
——论朱英诞诗歌中的“飞鸟”意象
2021-11-21王泽龙张嘉琪
王泽龙 张嘉琪
朱英诞素喜自然风物,对其体察之精微,感悟之幽深,在诗人中独树一帜。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在诗人巧思妙语间,被赋予人格,化为诗中意象。纵观朱诗丰赡的诗意园地,飞鸟频频点染为意象,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是现代诗歌中是首屈一指的。诗人无疑钟情于对飞鸟的吟咏与书写,但他不囿于物象的描摹,而是融入人生际遇和知性思考,展现诗性思维过程,彰显文化心理积淀。此外,朱英诞深谙古典诗歌传统,以古为新,飞鸟从与古典诗歌意象的互文情景中走出,更多地被观念意义赋形,注入现代哲思,彰显独特的人生况味与审美意趣。
一、以鸟叹己:渴慕自由的精神追寻
1932年,年仅19岁的朱英诞只身前往古都北平,暂居于亲戚的老屋;一年后,便举家从天津迁至北平的寓所,即西单旧刑部街38号。诗人喜静,更喜城居而享乡居之乐,于北平一住便是四十多个春秋。在漫长而单调的岁月里,诗人孤居于一方斗室,独饮缠绵病榻的困顿,深夜难寐,沉吟思索。时年70,喜得王森然先生《雄鹰展翅图》一幅,感慨万千,题诗以自慰:“杜鹃香啭越岩墙,风外鸡啼海上桑。/曾抚涧松望山月,我知愧怍作鹰扬!”①朱英诞:《梅花依旧——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的自传》,《朱英诞集》第9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72页。年逾古稀的诗人,抱此残病之躯,却始终渴慕着翱翔天际的自由,求索着诗意人生的真谛。
(一)临水展翼的精神还乡
朱英诞常自嬉,“家在江南也在江北;我个人却生长于津沽与北京——我家寄籍是宛平”②朱英诞:《神秘的逃难》,《我的诗的故乡》,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身处“北平”、心系“江南”的朱英诞感受着生存体验与文学版图的错位。一方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一方是魂牵梦萦的乐土,面对着“在故乡”与“去异地”的现实矛盾,诗人自喻为青空之鸟,翻山越岭,直抵梦中的氤氲水乡。江南是春光明媚、万象更新的,“画眉鸟儿啊花瓣作巢/袅袅的竹竿晒上衣裳/东风盘旋着解冻的歌/江南的春天是江南梦”①⑥朱英诞:《江南》,《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页。;江南是惠风和畅、草长莺飞的,“思路如天外寒鸦招来的如远方有幸福的家。”②朱英诞:《秋晚》,《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对朱英诞而言,江南,便意味着诗意的栖居,静谧的归宿,它是鸟儿飞倦的港湾,温暖的窠巢;同时,现世的江南恍如一场春梦,了无痕迹可寻。诗人在冬日里思忖着,“逡巡到江南了/海鸥在烟波间哀鸣”③朱英诞:《枯树》,《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在春寒中寂寞着,“打更的鸟儿,像我的沉默/越过我们的家乡多远又飞回的呢?”④朱英诞:《春寒》,《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91页。无枝可依的飞鸟,穿过窗棂,越过家乡,无声又不息地飞动着,独自徘徊。它为何不择佳木而栖?为何不达乐土而止?这或许是“故乡不可见”⑤朱英诞:《怀江南江北故乡》,《朱英诞集》第2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57页。,又或许是“蓦地失去了无限江山”⑥,迢迢江南便如镜花水月,纯美易碎而又神秘虚幻。
随着卢沟桥的一声炮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伫立在异地边缘的诗人感受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惶恐,江南之梦在风雨飘摇中染上黯然的色彩。如果说战前的朱英诞,虽苦于身心异处的割裂和游子身份的消解,但尚能在浑融着情感经验和传统文化的烟水南国里栖息的话,当古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对抗时,诗人稳定的地理空间岌岌可危,自如地想象、建构精神乐园的情状难以为继。“在而不属于”的悖谬式处境更为突出,肉体的威胁与理想的匮乏,使得朱英诞无法自持地对“辽远的江南”展开神往与怀想。江南是他理想的归宿地,诗人许一颗诗心给展翼南行的北雁,动情地勾勒远方的乐园。“一道阳光,一道流水,/安得促席,说彼平生,/无惊叹的赞美吧,/那流水至今还奏着沉哀,/母亲,你在那里/那海鸥们在那里/白孔雀的眼睛完全合上了。”⑦朱英诞:《远水》,《朱英诞集》第2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48页。江南,花草鲜美,落英缤纷,花树下伫立的母亲,翩飞啼叫的海鸥,构筑成静谧的桃花源境。但是流水鸣奏着沉哀,诗人化用“濮上之音”的典故,暗指家难寻、园难觅,亦真亦幻的江南笼罩着战火的阴云,梦境终将消逝。
在茫然无向的岁月里,现世的宁静和煦被战争无情打破,江南也好,桃源也罢,朱英诞们动情勾勒的精神家园,宛如空中楼阁,摇摇欲坠。朱英诞的同代人,诸如现代派诗人们,他们并非对乐园梦的脆弱易碎缺乏体认,但因对远方乐土的魂牵梦萦,注定了他们迁徙不断、漂泊无定的生命状态。探访而无路,求索而无依,诗人们化身往返于人间和天国的乐园鸟,“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是从乐园里来的呢,还是到乐园里去的?”⑧戴望舒:《乐园鸟》,孙玉石主编:《戴望舒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昼夜不歇、四季不止的鸟儿,不得不面对家园荒芜,乐土难觅的生存困境,于那青空中负起永恒的生之行役。无论朱英诞书写无根流浪的南行鸟,还是戴望舒咏叹荒原跋涉的乐园鸟,鸟儿盘旋、徘徊的姿态与时代苦闷、躁动的气息相吻合。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诗文里也呈现出与之同构的意象,如“异乡的倦行人”(《道旁》)、“被放逐的流浪人”(《树荫下的默想》)等,以抒发无所不在的孤寂和怅惘,暗示孤立无援的精神失落。至此,朱英诞诗歌的飞鸟意象,不仅暗示着以诗还乡的心理情结,而且包蕴着缥缈虚无的生命体验,成为时代的一种符号。
(二)隔梦筑巢的哀思怀母
幼年丧母的朱英诞,曾自称“失恃之子”,典出“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①孔一标点:《蓼莪》,《诗经 楚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面对着人世的沧桑变迁,孤苦无依的诗人如失群之鸟漂泊无向,他无限渴望在诗歌的国度里,再次“抓住母亲的衣襟”②朱英诞:《风雨归舟》,《朱英诞集》第4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8页。,如雏鸟在诗梦中归家回巢,一尽对母亲的怀想。但乌鸟私情,再难表露,母亲便是伫立在南国云树之下,冷清而迢远的“伊人”,可望却难即。“年轻的母亲/你到哪里去了呢/生命树没有阴凉/因之也没有光明啊/抛弃你手种的年龄/如一个木马或喇叭/对未来常如往昔而沉思着/一只留鸟又叫着了。”③朱英诞:《失恃之子》,《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诗人以懵懂无知的孩童视角与母亲展开对话,失去凉荫庇护的诗人不断追问母亲身处何处,进而由孤苦伶仃的现实联系到世事无常,前途未测,“留鸟”喃喃“像号角,还零落着哀音。”④朱英诞:《风雨归舟》,《朱英诞集》第4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8页。巢,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是雏鸟栖息的家园,也是夜梦里呵护诗人入梦的港湾。“破晓时,月如一个鸟巢,/夜作了我的摇篮,谁呀拍我安眠?/鸟唱的风里,无边的和平,/也拍抚着流水享有一个美丽的秋睡?”⑤朱英诞:《流水》,《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页。母亲轻柔的拍抚,巢穴温情的庇护,鸟儿啁啾的鸣唱,构成了诗人远离现实战乱的精神旨归。现世的求而不得,迫使朱英诞于缥缈的梦乡里筑巢怀母,但弥散于幻境里挥之不去的无定性和虚无感,终究使其陷入与母亲“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无可奈何。
二、以鸟结思:心物契合的诗性思维
在动荡的年代里,朱英诞远离广场与中心,格物致知,于山川草木间汲取灵感,“感觉自然的呼吸,窥测自然的神秘,听自然的音调,观自然的图画”,于是“风声水声松声潮声”都成为“诗意诗境的范本”⑥宗白华:《新诗略谈》,《艺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4页。。在心灵与自然、现实与虚幻的神秘互动中,朱英诞茕茕孑立,苦吟结思,他善于捕捉富有暗示性的意象,赋予个体生命的幽深情韵,并以灵魂为出发点,不断深挖诗意的井,营造深邃的境,生发出古今互涉的诗情理趣。
(一)心物相融的意象凝结
意象是景与情的和谐统一,是心与物的浑然交融,正如钟嵘《诗品》所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⑦王叔岷撰:《诗品总序》,《钟嵘诗品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7页。在中国古典传统浸润下的朱英诞,深谙“瞻万物而思纷”的诗意生发过程,尤其明了心物相融的意象思维方式。一方面,诗人摒弃一切外在纷扰,收敛感官,睹物而兴情。或翔或栖,或啼或默的鸟儿,与心灵不期而遇,构成了诱发诗人感悟、想象的机缘;另一方面,以我观物,物以情观,“物皆着我之色彩”。在诗人凝神观照之际,物我会通,日常的自然飞鸟与诗人的生命体验相融合,新鲜的诗情与知性的诗思相交织,构成诗歌意象,呈现诗歌本真之美。
朱英诞久宿世俗樊笼,渴望着御风而行的自由舒放,勾勒着自然飞翔的“物象”之鸟,望鸟生情,抒己心胸。当啁啾的鸟语闯入诗人敏感而紧闭的内心世界,他便以窗为临界点,触景而生情,观景而兴意,反复吟咏、描摹、点染小小鸟雀,化入诗行。诗人临窗伫立,感知自然,状眼前之景,听耳畔之音。西窗外“满院的阳光和杨柳/鸟儿整日歌唱”⑧朱英诞:《西窗》,《朱英诞集》第2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04页。,小园里“一只美妙的黄鸟/落在小园花树的枝头/向川田的窗子里窥视谛听”⑨朱英诞:《小园的春天》,《朱英诞集》第5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33页。,日出时“阳光挂在枝头,鸟儿的歌,像一条河/横在我的眼前了”⑩朱英诞:《日出》,《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狂风中“窗外的鸟已唱得娇好”[11]朱英诞:《狂风的春天》,《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页。。这些自然“飞翔”的物象之鸟,大多融在清新明丽的小园环境里,山川草木与飞鸟鸣禽情景逼真,相映成趣。面对多元的物象,慧心智灵的诗人善用全身的感官,精心地感受物象之鸟的声色光影,酝酿充沛鲜活的诗情,营造鸟啼花落的灵妙诗境。
为远离纷扰人世,诗人自觉地“退却到高高的小屋里”①朱英诞:《写于高楼上的诗》,《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25页。,自如悠游于诗歌的象牙塔内,巧思描摹着幻想飞翔的“心象”之鸟,吟鸟结思,引之自喻。诚如其所言“现实与幻美如此深妙地交错,分明是一种单纯的怡悦”②朱英诞:《〈春草集〉序》,《朱英诞集》第9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19页。。当室外的景转物移与室内的幻想沉思相汇合,诗人由实见虚,景致与心胸相融,凝神致思,虚实相生。一方面,诗人诉诸身外,驰想于无边的江南春色,描摹着灵魂的风景。朱英诞虽终其一生未踏足江南,但常常动用丰富的想象,化身为飞鸟,经过重叠的山水,飞抵春日的江南。另一方面,诗人诉诸己身,对自然万物进行拟人化想象,赋予人的特性,与之倾心交流。飞鸟或是诗人自我的外化,是迷惘时代里追寻自我意义的精神载体;或是诗人感官的延展,于凝神屏气之际,物我交感。“浅睡时如静水盈盈的/荷花呈献,共我浮沉/想起是天罗地网/虫鱼鸟兽,我在其中。”③朱英诞:《夜(一)》,《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恍惚之际,旧我开始分裂、破碎、颠倒、变形,重塑一个洗尽铅华、不设机心的新我,静赏灵魂之风景。诚如宋人杨简所咏:“山禽说我胸中事,烟柳藏他物外机。”④罗大经撰:《鹤林玉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物我交流之状,诗情孕育之况,便于主客相融、物我相忘之际,欣然融洽,回归本真。
(二)缘情说理的诗意抒发
潜心于山水之间的诗人,多默多思,将独特的感性情思与智性哲思融入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之中,再经反复酝酿,转化为诗歌意象,进而呈现出情理盎然的智性诗美。朱英诞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智慧,“我们的时代所经历大概与以往有所不同了,诗仿佛本质上是需要智慧的支柱。”⑤朱英诞:《〈盾琴抄〉序》,《朱英诞集》第9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页此智慧源自对自然造化、社会规律的观察和体悟,它在诗人认知把握外物时,生发而成。朱英诞由思成诗,落笔成言,其抽象的诗思往往蕴藏在具象的表现里,尤其是经情、理点染的山水田园,演绎出由景及理、景理相惬的诗意呈现。
朱英诞常常埋首书斋,或燃灯冥想,或捧卷吟唱,以窗为媒介,属于自然天地的飞鸟对于静居室内的诗人而言,处于“有距离”的观赏范围里,山林间栖息的飞禽染上想象的色彩,真与虚,现实与想象得以角力,进而弥合。诗人以鸟结思,展开对宇宙与人世、时间与空间、沉默与言说等哲学命题的玄思冥想。“椿树和天空成了好风景,/孤独者的窗乃多画意了;/时有飞鸟如浮海的小船,/做一个过客像我走过时间?”⑥朱英诞:《树》,《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48页。孤独的诗人因窗外辽阔的景致而诗意盎然,由窗外现实之景陷入飘渺的沉思,无垠的天空就好似那蔚蓝的大海,振翅欲飞的鸟儿如同在碧海浮沉的小船,朱英诞由空间的感知引向对时间的思考,不由得诘问:渺小如同沧海之一粟的芸芸众生,该如何行止?宏大无垠的宇宙与幽深微眇的内心,构成了强大的张力。个人主体意识化身飞鸟,振翅盘旋于碧落黄泉之间,实现了大我和小我的和谐共鸣。
与此同时,飞翔驰想的鸟儿不仅间接构成触发精神遥念的因子,更直接成为诗人求索宇宙奥秘的“客观对应物”。沉吟作诗的朱英诞,思接千载,心游万仞,“这宇宙的徘徊。/看风景的人,/一块空白。//我在写诗,这时候?/这时候,你在归航?//二十世纪的梦寐,/很相像,/于任何别一个世纪,/它是过去或未来的巢。”⑦朱英诞:《飞鸟》,《朱英诞集》第3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于深邃的宇宙里徘徊的鸟儿,成为诗人哲思的载体。谁是看风景的人?谁又成为被看的风景?相对性的探究,世纪性的回荡,诗人不禁发问:那归航的鸟儿终究将停留在过去、未来的哪一处巢穴?此外,诗人还面临着言说与不言的选择困境,“疏雨落在素手上/一念的无限/云缕为我捕一只白鸟/由学舌喃喃道无言。”①朱英诞:《石像》,《朱英诞集》第1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22页。由转瞬的一念窥见时空宇宙的无限,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诗人触雨就好似佛祖拈花,由微小之末感知到世界的本质,参悟人世之苦,人世之乐,因此便步入欲辨忘言、希声静言的境界,不言便是一种囊括万物的言说状态,是诗人向内自省的澄澈心境。
三、以鸟抒怀:感知山水的审美趣味
作为“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朱英诞从未真正入世,始终踽踽山水之间,诗意栖居。于大处茫然,于小处敏感,游目骋怀,纵情山水。诗人以鸟抒怀,古今对话,融知性诗思于山林花鸟间,彰显平淡清远的京派趣味。
(一)以古为新的知性诗思
吟鸟结诗的传统由来已久,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贯穿着对飞鸟的歌咏和描摹。秉持着“诗近田野,文近庙廊”理念的朱英诞,自觉承袭中国诗歌传统中寄情山水、物我两忘的审美趣味。面向传统,化古为新,朱英诞的山水田园诗,自成一格,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借景抒情之作,而是在诗行间蕴藏深远意旨。以传统意象为依托,表达对自然宇宙、时代际遇的现实慨叹,借助象征性的意象,传达诗人的智性体悟。
首先,诗人善于化用传统意象,酝酿新鲜情思。古人常喟叹道,杜鹃啼鸣,唤君归去,杜鹃花与杜鹃鸟同音同构,为凄苦悲愁的象征。像李白的《宣城见杜鹃花》:“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②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7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263页。朱英诞爱化杜鹃入诗,古今对话,他常引塞万提斯的名句入诗,如“‘谁能够筑墙垣圈得住杜鹃’?/杜鹃鸟啼着杜鹃花,/美丽的过客,/邂逅,夕阳沉沉。”③朱英诞:《抑郁》,《朱英诞集》第4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杜鹃是自由的精灵,美丽的过客,其翔动不息的姿态与文人漂泊无定的体验互动共生。传统意象一经转化,便被诗人赋予了独特的现代意蕴和审美取向。其次,诗人创设象征意象,抒己之怀。“飞鸟”意象是诗人创设的核心意象,它是生命意识的高度凝合,也是时代气息的突出表征。“飞翔吧,过去的鸟,/飞翔吧,未来的鸟。”④朱英诞:《飞鸟》,《朱英诞集》第3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诗人心神摇荡,化身飞鸟,领悟四季更迭、宇宙无垠,彰显其对生命、时空、主客的别样思考,最终实现对生命本源的回归与升华。无论是意象的互文,还是意象的营造,朱英诞都致力于探索古今互设的意象思维与表达,追求在意象组合中寄托智慧的凝聚,在节制表达中彰显情感的变化,构筑融化古今的知性山水。
(二)走向自然的心性陶冶
自然山水构成朱英诞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大到宇宙洪荒,小到一花一石,都沟通着诗人的心灵世界,与之和谐共振、感性同一。对自然万物的涵咏与抒怀,不仅体现出朱英诞知性山水的诗学主张,更关涉着以朱英诞为代表的京派文人的文化心理,表达着其清淡朴讷的文人情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英诞、周作人、废名等人因厌弃城市的喧嚣,现世的动荡,转而返归乡野,隐居山林,安于诗书,秉持静默和谐的态度观望世间百态,试图建筑自己闲适、理想的诗歌小园。朱英诞的隐居,虽是时代所迫,也是性格使然。“世事如流水逝去”,“我一直在后园里掘一口井。”①陈子善:《朱英诞诗文选·序》,《朱英诞诗文选》,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诗人以此自况,身心俱隐,穷山水之趣,品自然之真,追求着于山水钟灵中悠游感悟、陶冶心性的处世之道。朱英诞是如此,京派诸文人莫不如此。诚如废名所言:“自然好比是人生的镜,中国诗人常把人生的意思寄之于风景。”②废名:《悼秋心》,《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第236期。沈从文同样凝神静观,山水花草、飞鸟虫鱼皆融入特殊情趣,创设出独具匠心的自然园地,他如此赞叹,“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受到生命的尊严。”③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因此,京派文人常性情所至,文思泉涌,建构着纯美至善的艺术世界,崇尚人性的本真,呈现出逍遥无拘、自然蓬勃的生命状态。沈从文的湘西、废名的黄梅、师陀的果园城,还有朱英诞的江南,无一不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精神风景。幽静退隐的京派文人们,笃定纯粹的艺术追求,摒弃世俗的杂念,拥怀澄澈的心境,欣赏生命的自洽与圆融,最终抵达自由无限的精神家园。正如朱英诞所歌咏“谁能够筑墙垣,围得住杜鹃?”思绪蹁跹,化身杜鹃,终将跨越斑驳墙垣,自由翔动,率性而飞。
步入朱英诞诗歌的意象森林里,神秘而晦暗的尽头不时传来一二啼鸣,远处诗意的青空里,划过飞鸟翔动的痕迹。在现实与梦幻交织的情境下,“飞鸟”不再仅仅作为自然山水间的飞禽而存在,它更多地指向情感与思维,与诗人的生命体验高度契合。可以说朱英诞的一生是精神流浪的一生,也是飞鸟不断飞动求索真诗与真理的一生,从精神寻乡、故土失落再到诗国重筑的漂泊轨迹,他终其一生,颠沛流离,在现实深巷里静听啁啾鸟唱,在幻想江南中寄托精神遥思,在诗歌小园里挖掘真诗的理趣和人生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