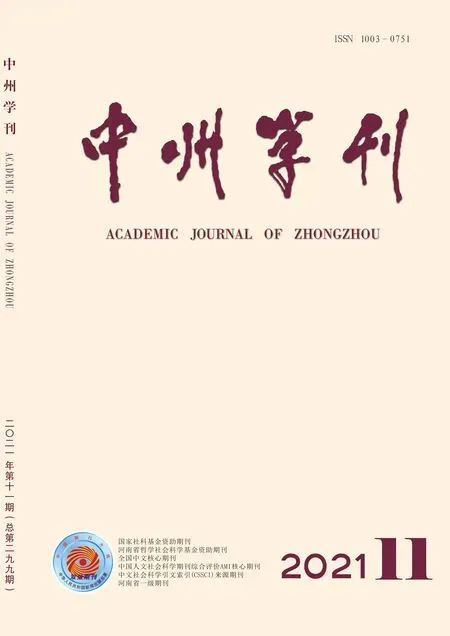难民伦理的理由:道德义务、人道关怀与体系责任*
2021-11-21张永义
张 永 义
难民问题对当代国际伦理和国际社会的影响愈加显著。虽然联合国于1951年、1967年和2018年分别通过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但是国际社会对难民的救助依然处于众所周知的不稳定责任关系状态,“许多国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对难民的重大责任……(虽然)大多数国家认为他们应该帮助难民,但很少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政治或法律责任”①。而难民救助责任是难民伦理的基本理由,是难民伦理的核心问题之一,直指难民的非来源国或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承担对难民的道德义务。对此问题的探究,深度关涉难民救助责任的哲理与法理根基。因此,人们需要首先厘清的是,因难民问题而形成的难民伦理之理由何以存在、难民救助责任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叩问意味着,关于难民伦理之理由的探究主要围绕难民救助责任而展开,难民伦理的理由问题——致力于难民救助责任之合理性说明,则是难民伦理探究的基点,是国际社会正确应对难民问题的前置条件。
进而言之,难民伦理的理由,主要涉及主权国家如何看待具有强道德属性的难民问题、在难民问题上采取何种基本立场与基本认知、实施难民救助的动机与目的等。毕竟,难民是特殊移民和被迫移民,被普遍认为是广义跨国移民范畴中的例外情形。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难民的需求是紧迫的且通常是生死攸关的、事关底线尊严和基本保障的;虽然与基于改善性动机的主动移民一样不必然享有“不受阻碍地跨越国界的人权”②,但是,基于生存性动机的难民因其失去“拥有权利的权利”③、失去作为人应有的生活条件或安全保障,而被普遍认为在道德层面比主动移民拥有更大获助权。二是令当事国难以承受的道德因果关系——当事国若拒绝救助或袖手旁观,则它在客观后果上成为加剧难民问题的责任方之一,实质上等同于间接甚至直接地对难民“施加伤害”④。因此,难民伦理是强道德属性的范畴,难民问题是强道德驱动的问题。然而,强道德属性与强道德驱动依然受限于主权国家体系和边界管制权。因此,难民的获助权是受限的、不完全的权利。目前,学界“关于难民的哲学思考仍然处于起步阶段”⑤,对难民伦理之理由的认知或对难民救助责任的推定,存在多元解释,社群主义、现实主义、世界主义、主权主义、民族主义等多种思想流派都对难民伦理及其理由抱持各自不同且有所交叉的观点。无论这些观点的终端认知与基本主张呈现何种差异,但它们的推论基点都主要来自三个不同视角之一:道德义务、人道关怀、体系责任。
一、道德义务
在人人平等、人人都应该享有底线尊严与基本保障之观念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现今世界,道德义务论从义务论伦理观出发,以人类社会每位成员的道德平等,尤其是道德地位平等和道德价值平等,作为难民伦理的前提和主旨,将道德平等视为正义事业,将难民救助视为基于正义的必需义务,或曰正义责任。这意味着道德义务论的观点在本质上不仅基于义务论,也基于正义论;既有别于人道关怀论的互助论与结果论,也有别于体系责任论的平台论与失灵论。道德义务论虽然认可人类社会所处的世界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就一直处于主权国家体系状态,但同时认为难民救助不是也不应该沦为泛泛的人道事务,而是具有刚性道德驱动的正义事业,是人类社会所有成员责无旁贷的普遍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的价值位阶高于或者平行于国家利益的价值位阶,或者这种道德义务就是国家利益的必然组成部分。因此,人们在难民伦理之理由的认知上,应该淡化而不应该突出强调国家利益,至少不应该将难民救助置于国家利益计算之下;并且,难民救助也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道德平等之自我期许与自我承诺的体现,人们不应该将这种道德期许与道德承诺悬置为自我道德标榜,而任由数以千万计的难民继续处于困绝境地,毕竟“我们都是道德意义上的世界公民”⑥。
作为道德义务论之重要理据的是边界怀疑论。在道德义务论看来,主权国家体系背景下的边界管制权与入境管辖权是难民救助的主要障碍之一,而边界的形成与现状在道德合法性上却是非常可疑的,更何况“边界没有深刻的道德意义”⑦。边界的形成及其获得国际法认可的过程,包含着大量的人为因素、随机因素、地理因素、偶然因素、强权因素和妥协因素,这些因素无一不充斥着非道德成分,对于某些居于边界内外的居民群体而言,有时甚至意味着反道德成分或违逆人性的成分,遑论在很多历史背景下,土地占有和边界划分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血泪史,“充满了征服、暴力、欺诈和剥削”⑧。当然,对边界在道德意义上的怀疑与批判,并不意味着对边界在国际法意义上的驳斥与否定,也远不意味着所有既定边界都充斥着非道德成分,但是由此至少可以说明的是,人们在国际法意义上肯定边界合法性的同时,也需要充分意识到其在道德意义上的非正当因素,并以此促进对难民伦理的正确认知和对难民救助责任的积极担当。
由边界怀疑论衍生而来的是更加有助于道德义务论证的公民特权论。处于不同边界范围内的居民,因非道德的边界而获得了非道德的公民身份,公民身份遂与既定边界一样具有随机性、偶然性、人为性和非道德性;而不同的公民身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不同福祉与命运,先天自然优良或后天治理善政的共同体公民身份由此形成随机特权、偶然特权、人为特权和非道德特权——至少在成为难民的可能性上的低概率特权。更糟糕的、对难民(和在一定意义上对移民)更加不公平的是,非道德边界所注定的非道德身份及其特权还是固化的、继承性的,这就导致一个二元悖论:公民身份及其特权的非道德性在法理上被公认为是代代继承的和永久固化的,在哲理上却是备受质疑的和常受驳斥的。因此,道德义务论认为借由非道德边界而形成且以代代继承方式得以固化的公民特权,与历史上被批判和被剥夺的种种封建特权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不公平的表征。封闭固化的非道德身份特权的存在,严重剥夺了难民绝境求生的机会,导致在同一个世界的表象之下,存在严重的道德割据和道德落差,这与道德平等承诺背道而驰。那么,面对难民救助问题,面对各种先天因素、外界因素和人为因素对难民造成的深重苦难,人们需要做到的是补偿正义和充分救助。
边界怀疑论和公民特权论都与道德义务论的一个基础性观念——世界公民观——密切联结。道德义务论以世界公民身份视角看待难民的道德地位平等和道德价值平等,认为处于苦难境地的难民失去了底线尊严和基本保障,这就使得难民与其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实质上是完全断裂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亦即难民完全地或部分地失去了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公民身份。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难民依然具有世界公民身份,依然享有与国家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同时充分兼具的人一样的道德地位和道德价值,国家公民身份和共同体法律关系的完全或部分丧失,并不会湮灭难民的世界公民身份及其道德地位和道德价值;而道德又是先在于法律的,那么,无论对于世界公民身份,还是对于国家公民身份而言,公民身份的道德属性也就先在于且独立于其法律属性,在现实逻辑层面也统摄着且优先于法律属性,法律属性就只是道德属性的衍生品,是对道德属性在契约关系上的后期非充分确认。因此,难民在国家公民身份上和共同体法律关系上的完全或部分丧失,不影响其在世界公民层面上的道德地位平等和道德价值平等。人们在难民伦理之理由问题上的种种争议,在相当程度上就来自于人们以国家公民身份视角和法律属性视角来看待难民问题的旧有思维习惯,因此,道德义务论认为在严峻的难民危机下和现今的时空背景下,人们需要以世界公民身份视角和道德属性视角来审视难民伦理的理由,以道德平等主义看待难民救助责任。
但是,道德义务论的平等主义主张可能引发难民救助责任的极大化,这显然与共同体权利和国家利益形成现实冲突。道德义务论的功利主义主张则是一种将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结合考虑的思路,该思路旨在实现难民伦理之理由的某种平衡,认为高价值位阶的难民救助责任并非无限责任;如果相关方为难民救助付出的综合成本不超过难民救助的正面效益,则应该实施并持续实施难民救助,反之则停止。换言之,道德义务论的功利主义同样主张难民伦理的理由必须出于义务论和正义论,但是需要坚持“平等考虑原则”⑨,顾及难民权益与共同体权益的均衡,难民救助义务应该兼具某种功利计算,平等考虑所有受影响者的利益;国家必须尽可能承担难民救助义务,尽可能为难民救助支付各种必要的财力和物力,并给予难民以入境居留权乃至入籍归化权,直到上述综合成本依据某种评估标准体系超过综合效益时,难民救助方可停止。综合成本超过综合效益的标志,包括但不限于财力与物力支出超过难民群体综合收益、财力与物力支出超过施助国的承受能力、救助行为对难民群体的正面效益明显超过对共同体成员的负面效益等。功利考虑是道德义务论的功利主义主张与人道关怀论之间的联结点,因为同样的功利计算,不仅出现于前者,而且更多地存在于后者——典型观点之一是“只有当救助难民的成本较低时,国家才有义务帮助难民”⑩。
二、人道关怀
人道关怀论坚持道德怀疑主义,强调社群自主和国家利益至上,捍卫国家的边界管制权和入境管辖权;具体到难民伦理及其理由认知,人道关怀论虽然承认难民群体在道德意义上某种程度的特殊性,甚至承认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世界公民地位和道德平等地位,但是这一切都不可以冲击边界的法理地位、影响国家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国家利益、消解共同体的民族特性。面对带来道德压力的难民群体,国家只有人道义务,可以出于人道关怀并基于互助精神和同情心理,实施人道关怀行动以救助难民,因为宽松的难民接纳和沉重的救助负担可能引发巨大的连带负效应,而且在现行法理依据上,无论难民群体有何种特殊情况、难民问题有何种道德属性,都不应该导致共同体成员利益沦于作为外部人的难民利益之下。因此,只可以在国家公民的福祉背景下和国家利益的整体考量下,秉持人道关怀和互助精神看待和处理难民问题;在难民救助与国家利益取向一致的时候,在公民意愿与道德动机协调平衡,例如施助国面对具有共同历史渊源或文化认同的难民群体的情形下,施助国可以“寻求保障国内社会的合法利益,同时(为难民)提供人道主义关怀”。在救助程度上也比道德义务论薄弱的是,人道关怀论认为即使施助国实施了难民救助,被救助的难民也只是获得底线尊严与物质条件的基本保障,而不应该归化入籍,“尽管政治团体遵循‘互助’原则,应该在必要和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难民无权要求被接纳”。由此观之,人道关怀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认可难民问题的特殊道德属性,但是拒绝为难民群体提供充分的救助机会,这就使难民救助的责任与程度问题面临着非常复杂的考量,因为人道关怀论认为责任与程度问题不仅是道德驱动问题,也是需要与施助国的利益取向、群体认同、文化身份、历史传承和价值观念紧密关联的问题。这意味着与道德义务论相比,人道关怀论视角下的难民伦理及其理由呈现高度的复杂性,不仅关涉施助国的历史发展、当前需求和未来预期,而且关涉国家利益、国际道义和国内民意。
因此,人道关怀论首先是互助论的而非正义论的。互助指涉一般性的互相帮助,在施助国有余力且不对自身造成明显消极影响的前提下对难民实施一般性救助,“各国没有完美的义务让难民结束他们的痛苦,他们至多有不完美的互助义务”。不完美的互助义务带来的是低限度责任,而不是道德义务论者将难民救助问题视为正义问题所引发的高限度责任。人道关怀论同时也是结果论的而非义务论的。从结果论出发,人道关怀论不仅强调难民救助的成本支出与收益结果计算,而且注重道德理念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匹配,深度关切人道义务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必然差距。这里的计算、匹配与差距,尤指施助国在难民救助中和救助后如何妥善协调难民利益与契约共同体利益之间的适切性,毕竟,基于现行的契约法理体系及其原则,“考虑到国家体系的道德前提,一个国家优先保障本国公民和居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相对紧迫的外来者的基本权利,这当然是合理的”;并且,不同于道德义务论将“应该”视为“必须”的应然理念,人道关怀论坚持结果论的道德观,“应该”只意味着“可以”,“如果一个行动没有取得好的结果,良好的意图就没有意义”。人道关怀论也是慈善论的,因为出于公共政策制订上和共同体资源运用上的审慎性,即便是强道德属性的难民救助也只能出自仁慈与同情,不能因难民救助导致边界管制权的消解、共同体特性的改变和对国家公民福祉的冲击。因此,在人道关怀论者看来,“对难民的反应,不是正义问题,而是同情问题”。由此可以推论的是,作为难民伦理的保守立场,人道关怀论与社群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共享国际伦理的某些既有观念,“传统的道德假设是,我们对难民没有约束性的道德义务,任何接纳难民的行为都是自由裁量的慈善行为”。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人道关怀论必然是现实论的:尊重公民契约共同体现状,坚持国家对即便是难民群体也持有充分而现实的边界管制权,政治理论在国际现实应用上的非可行性。人道关怀论认可非国民义务的合法性,尤其对难民救助之类的非国民义务,适当而必要的人道关怀行动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将其上升到完全意义上的道德平等则会与国际社会现实相冲突。道德平等主义可以容易地论证难民救助责任,但是它却模糊了国家对国民福祉的首要责任;若以高价值位阶的视角承担难民救助责任,很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长远危害。因此,对于难民伦理的理由,人们需要以现实的和妥善的方式,接受国际制度的正当性假设,将难民救助视为在现实中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国际制度下的人道关怀行动与人道互助行为,视为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慈善之举,视为基于仁慈与同情的人道关怀而非使命性的道德义务。如此,难民救助不仅不涉及对既有国际制度的否定和对边界的道德质疑,而且人道关怀与互助可以成为难民救助的主要形式,也应当是难民救助的最大边界,从而在现实中形成“对难民的道德和法律义务的政治共识:各国没有安置难民或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的法律义务,亦不承认安置难民的道德义务”。如果人们接受道德义务论对于难民救助的正义性质认知,则需接受国际制度的非正当性假设,认为难民救助是普遍的、必须的道德义务行为,难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制度现状的不合理性、边界性质的非正当性和难民制度的非道德性导致的,而这些认知都将对现实层面的国际社会建构和国内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冲击。
尤其对于道德义务论的边界怀疑论和公民特权论观点,人道关怀论抱持反对立场,其理据建基于国家理论和契约理论。对于道德义务论所指摘的在难民救助问题上不应该只狭隘地坚持契约共同体背景下的国家公民及其法律属性视角,而应该更多地或主要地秉持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公民及其道德属性视角,人道关怀论诉求国家公民身份是人们安全保障、福祉增进和认同归属的根基,为求难民救助而抛却这个根基,则会引发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两方面的失序甚至崩溃,而作为根基的国家公民身份,本身就以排他性为前提,这是难民伦理之理由的滥觞所在,也是推论难民伦理之理由的原始基点。由于不可抗拒的多种历史原因和主客观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暴力占领、殖民统治、传统习俗、文化分际、自然界线和群体认同,在法理上早已得到默认和确认的边界现状和社群成员身份,都不可能绝对符合无知之幕下的正义原则和道德法则,人们需要做的,只能是对此予以承认和尊重,而非否定它们并进而强制施行绝对化的道德义务;边界是秩序稳定最大化的核心保证,其价值位阶高于难民的需求与救助;人们不应该既享受着边界保障带来的秩序感,又为难民救助的普遍义务主张做出损害秩序根基的行为,遑论任意性、偶然性和非道德性是边界的固有原罪,人们不可能生活在无罪化边界的世界。在一个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原罪化边界但稳定运行的世界里指责边界的原罪,如同一个如所有人一样家庭出身在出生前已命定的人,在成年后因其发展后果差异而回溯否定或指责其家庭出身一样没有意义。同理,公民特权论没有充分认知的是,国籍出身与家庭出身同样是不可自主选择的,只能是随机的、任意的或偶然的,也同样在一般情形下是继承性的公民身份,且作为契约共同体的国家与作为血亲共同体的家庭一样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建构的基本逻辑;如果边境管制权在难民群体面前失效,则如同家庭边界或家庭成员身份的开放一样导致严重失序,而人道关怀则是对道德合法性先天缺失所做的补偿正义行为,也是对难民伦理之理由的有力诠释。
三、体系责任
理想正义色彩和道德平等基调都过于浓厚的道德义务论,和在现今国际伦理背景下依然坚持相对薄弱的难民伦理观的人道关怀论,都各有利弊长短。那么是否可以从其他角度,而非单纯以道德平等理念的践行程度和道德义务的得失计算等义务论或结果论的视角,来探究难民伦理的理由呢?作为基于平台论和失灵论的观点,体系责任论由此进入致思范畴;致思之结果使得难民伦理的理由不再局限于个体道德与群体伦理的背景,而是在国际伦理框架之下,从主权国家体系入手,以体系责任解释难民伦理的理由。体系责任论认可和尊重主权国家体系,回避边界怀疑论和公民特权论,亦不考虑互助行为和利益计算的是非得失,只论证和厘定难民伦理的理由和国际伦理意义上难民救助的责任,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之后的主权国家体系或许是所有不尽理想的现代世界组织方案中最务实可行且最易于接受的方案,也是消极面相对较小的方案。在主权国家体系方案中,世界被分割治理,呈现碎片化状态,国家主权平等并立、至高无上,拥有统揽和主宰单元内外一切分内事务的权力,每个治理单元亦即主权国家,都对国家事务和民众福祉负责,每位个体都被边界划入特定的治理单元,“一个人要么是公民,要么是外国人,没有第三种选择”,都接受对自己和其他契约成员负责的治理结构;所有治理单元组合起来,就是完整的世界和人类社会。在这个方案的道德假设中,主权国家体系为所有治理单元提供或造就了一个共存平台,所有治理单元都在这个体系平台上互动互利——至少是理念和目标上的互动互利。由此,每个治理单元都可以从这个基础性共存平台上寻找获得公共益品与福祉的机会。
但是,现实世界远远没有如此简单。任何组织方式都必定有缺陷,都不完美;消极面相对较小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体系方案同样不完善,远不意味着没有消极面,也不意味着即便就世界范畴层面而言相对较小的消极面就不是特定群体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巨大灾难,任何系统性平台都必然有失灵、失序甚至崩溃的可能,比如难民问题的出现,而“难民和国家体系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参照后者就无法理解前者”。主权国家体系方案却先在地隐含着体系永不失灵失序的假设,忽略了治理单元各有不同的脆弱性,湮灭了即使沦为难民也不可丧失的自然权利和应然机会,毕竟,即便“一个人作为群体成员拥有特殊权利,也不能排除他/她是一个更大群体的公民”。并且,就治理单元的脆弱性而言,主权国家体系完美运行的前提是所有治理单元都善政善治、风调雨顺、经济平稳、生活安定,这就不会有难民的产生和溢出。但是,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着气候与环境脆弱性、安全脆弱性、治理脆弱性、民族脆弱性、宗教脆弱性、身份与认同脆弱性等众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国家脆弱性溢出从而导致体系失灵等系统性风险问题——难民问题即为其典型之一。因此,难民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体系不可避免的后果”;或者说,只要存在边界、存在主权并立的治理单元,且只要体系成员存在败政或恶治的可能、存在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可能,并“对内部人和外部人做出明确界定,就会有难民”。更进一步地看,难民与主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构成关系,如体系责任论的重要主张者艾玛·哈达德(Emma Haddad)所言,在主权国家体系之下,所有个体“都必须被嵌入国家—公民—领土三位一体结构”,难民遂被创造为“他者”,与主权概念密切相关的内部人和外部人概念得以强化,从而使主权国家及其体系获得更大的认同与合法性,而难民就成为主权国家体系的必然构成要素。
经由体系平台论和体系失灵论推导而出的难民产生之体系根源,便可自然推导出主权国家必须承担的体系责任:体系平台不仅是共存的、共享的、互利的,在某些情形下也可能是互相争斗的平台,同时更是共治的平台,难民救助就是共治的组成部分;而作为国民在国际社会中的道德代理人和道德责任者的主权国家,需要承担的体系责任自然就是共治责任,这也是权责利三位一体原则的使然。这就意味着难民与主权之间不仅存在着前文所述的相互构成关系,还存在着直接责任关系。既然难民问题的出现与持续是主权国家体系建构和运行过程的必然组成部分,那么,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史与运行史,就不仅是难民问题的持续存在史,也是体系成员对难民救助责任的承担史,也是体系成员对体系平台的共治史,这便是难民伦理的第三个理由。换言之,在国际伦理框架之下,难民问题产生于体系,难民救助自然就是体系责任,而构成该体系的是主权国家,该体系就是公认的主权国家体系。因此,难民救助责任就归于作为体系成员或体系构成者的主权国家,难民伦理的第三个理由便由此成立——在难民救助问题上,其道德责任应当来自主权国家体系的成员,亦即主权国家。此外,体系责任论也应该被理解为修复责任论,体系平台上的主权国家承担着平台修复责任,难民问题就是该平台需要修复的显著体现;而主权国家不仅是国民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代理人,同时还是道德代理人。在难民救助问题上,主权国家就因此成为道德责任者,其对难民的救助行为,既是它对国民的道德代理,也是它对平台共治与修复的体系责任。进而言之,主权国家在难民救助问题上的体系责任,是修复责任和共治责任,是体系成员加入共存共享体系平台时默认的先定责任;既是道德攸关者的责任,也是利益攸关者的责任;既是国际伦理责任,也是国家“政治责任”。在此意义上,与道德义务论和人道关怀论都不同的是,体系责任论致力于难民问题与主权国家在国际伦理层面的制度性和解,摆脱了冗长而又传统的义务论与结果论之争辩;体系责任论意味着边界不需要消解,边界的道德意义不必被过多关注,只需明确主权国家的体系失灵责任和平台修复责任,亦即在承认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以体系责任视角建构具有坚实国际伦理基础的难民伦理之理由,接下来只需做的,则是另外一个主题——主权国家之间对难民救助责任的具体厘定与承担。
四、结语
难民伦理的理由,在上述道德义务论、人道关怀论和体系责任论之外,还有一种由于争议很小而不在本文探究范畴的因果关系论——主导或参与在一国的军事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该国难民的产生和溢出,则主导国和参与国应该承担相应的难民救助责任,这是一种由因果关系推定而来的责任关系。
若以横向视角来看,道德义务论诉求强道德、强责任,人道关怀论主张弱道德、软责任,体系责任论则强调国际伦理框架下的非道德、硬责任;在责任关系界定上,道德义务论主张完全义务,人道关怀论主张不完全义务,体系责任论主张先天义务——不事先界定责任关系的强弱程度,但在实际推导上易于产生硬责任关系。道德义务论是高标准的伦理责任观,强调道德平等,着眼义务动机;人道关怀论是低限度的伦理责任观,立足特殊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和特殊纽带,着眼人道动机;体系责任论以淡化个体道德色彩并尊重国际伦理框架的务实视角,基于权责利三位一体,强调主权国家的体系责任,着眼责任动机。人道关怀论和体系责任论可以认为道德义务论的道德平等,有时可能成为道德泛化,难以广泛且深度应用于所有的契约共同体,亦可能造成对既定体系秩序的反噬,因为道德平等与契约关系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道德平等的核心诉求与契约关系的封闭排斥机制之间存在不易调和的矛盾;道德义务论和体系责任论则可以指责人道关怀论的弱道德和软责任观念是“被计算的仁慈”,与身处苦难境地的难民群体、国际社会持续严峻的难民危机和不断更新的国际伦理都格格不入,是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由此观之,体系责任论对难民伦理的理由做出了更具坚实基础的回应,争议相对较小,也包含着对某种潜在而真实的全球契约共同体的默认,可以增进人们对难民伦理之理由从弱责任到强责任再到硬责任的认知变迁。但是,基于难民救助供给与难民救助需求之间的长期失衡关系,以及难民伦理之理由与威斯特伐利亚道德假设之间的非协调性,接下来的责任厘定与承担问题依然难解,或许,某种形式的体系平台税将是可能的考虑方向。
注释
①Serena Parekh. Beyond the Ethics of Admission: Stateless People, Refugee Camps and Moral Obligations.Philosophy&SocialCriticism. 2014, vol.40, No.7, p.650.②David Miller. Border Regimes and Human Rights.TheLaw&EthicsofHumanRights. 2013, vol.7, No.1, p.22.③Hannah Arendt.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p.298.④Joseph H. Carens. Who Should Get in: The Ethics of Immigration Admissions.EthicsandInternationalAffairs. 2003, vol.17, No.1, p.101.⑤Matthew J. Gibney. The Ethics of Refugees.PhilosophyCompass. 2018, vol.13, No.10, p.8, p.4.⑥Ann E. Cudd, Win-chiat Lee.CitizenshipandImmigration:Borders,MigrationandPoliticalMembershipinaGlobalAge, Springer, 2016, p.46, p.231.⑦Richard Shapcott.InternationalEthics:ACriticalIntroduction, Polity, 2010, p.93, p.113.⑧Peter Penz. Et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Institution of Asylum.Refuge:Canada′sJournalonRefugees. 2000, vol.19, No.3, p.47.⑨Alexander Betts, Paul Collier.Refuge:RethinkingRefugeePolicyinaChanging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16.⑩ Matthew J. Gibney.TheEthicsandPoliticsofAsylum:LiberalDemocracyandtheResponsetoRefuge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31.Mark R. Amstutz.InternationalEthics:Concepts,Theories,andCasesinGlobalPolitics,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p.163.Joseph Carens.TheEthicsofImmig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19.Jack Snyder. Realism, Refugees, and Strategies of Humanitarianism, In: Alexander Betts and Gil Loescher, ed.Refugee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2.Peter Singer and Renata Singer. The Ethics of Refugee Policy, In: Mark Gibney, ed.Openborders?Closedsocieties?TheEthicalandPoliticalIssues, Greenwood Press, 1988, p.114.Serena Parekh.RefugeesandtheEthicsofForcedDisplacement, Routledge, 2017, p.138.Rogers Brubaker.CitizenshipandNationhoodinFranceandGerma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6.Alexander Bet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ced Migration, In: Elena Fiddian-Qasmiyeh, Gil Loescher, Katy Long, and Nando Sigona, ed.TheOxfordHandbookofRefugeeandForcedMigration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60, p.62.Steven P. Lee.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 In: Ann E. Cudd and Win-Chiat Lee, ed.CitizenshipandImmigration:Borders,MigrationandPoliticalMembershipinaGlobalAge, Springer, 2016, p.55.Emma Haddad.TheRefugeeinInternationalSociety:BetweenSovereig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 p.88.Gil Loescher, John A. Scanlan.CalculatedKindness:RefugeesandAmerica′sHalf-OpenDoor, 1945tothePresent, The Free Press, 1986,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