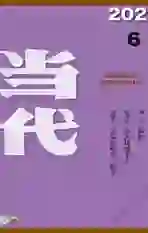长勿相忘
2021-11-20刘东黎
刘东黎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王风·黍离》
1.那一个历史瞬间
1937年的七月,确实比往年更炎热一些。
敏感的人们已经嗅到些许不祥的气息了。当时就有市井流言,说上天警示,有兵戈之象,接下来的这些年头,恐怕不会宁静。
多数的国人,也是后来才体会到,这个夏天,是无数苦难生命的交汇,尘封着离乱时代的颜色、声音与味道,是改变几代人命运的一场梦魇的开始。
在7月6日,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似乎仍美丽如常。天色将晚,吴宓和陈寅恪仍在清华园里很有兴致地徜徉。吴宓在当天的日记里写:“晚7—8,偕陈寅恪散步。坐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至美。”天地间满溢着柔和与安详的情调。也许在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在彩云之南的晨风昏雨中,悚然想起那天傍晚如血的云霞。
7月8日清晨,北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听到稀稀疏疏的机关枪声,便以为是普通的打靶演习,当时并不在意”。这一天,他和北大物理系另几位教授饶毓泰、郑华炽等一同游西山,玩兴颇佳。诸人这时都有耳闻和预感,但最后大家认为,此次同以往一样,只是双方驻军的局部摩擦,经过交涉,事态应该很快得到平息。
然而一周之内,一切都变了。战云笼罩之下,北平岌岌可危。
各城门每日均要关闭,只开放片刻,晚上因恐日本浪人便衣队起事,八点天刚黑就戒严,大街小巷都不许行人通过。东单设了防御工事,长安街上堆起了沙包,其他重点地段也到处都是沙袋战壕,有枪口在上面闪着寒光。风高浪急、流血漂杵的战争年代,正狂飙般向故都北平席卷而来。
地处北海西沿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直接处在敌人凶极一时的锋镝之下,正常的学术研究被突然打断。7月18日,日军飞机轰炸西苑,中日两军在沙河与清河之间激战,炮声、机关枪声时远时近传到城内。
静生所的同人每天都在焦虑的心情里熬煎着。晚上组织人员加强巡查。一轮皓月当空,偌大的城市,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都在想,若以后日本军队正式进来,到处接管,此时的护卫有什么意义?事实上是替日本军队保管,等他们来接收。那么静生所是不是应该做南迁的准备?
也有人认为,一个研究植物的私立机关,危险应该不大,且一旦搬迁,许多冒着生命危险采集来的标本,随时都有损失之可能。很多珍稀标本对防潮、防水、防火、防虫等有较高要求,静生所藏标本数量巨大,更是难保万全。当然华北形势终难乐观,研究所还是将贵重物品装箱保存,以防万一。
北平城里的空气一日比一日沉重,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了。8月的一天,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等人围坐,把数年来编纂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相关资料,投入熊熊燃烧的火炉中。乱世浇漓,这样的情景真让人倍感伤惘。
一旦城破,人们在敌军铁蹄下生死沉浮,将被奴役驱使,还可能被逼充当宣传战争的工具,在半死半生中卑怯苟活,这样一种人格上的侮辱可谓生不如死。能走就走吧,好在中国地方大,危急时候,衣冠南渡,偏安江左,无论后事如何,总能有个进退的余地。
中国历史上几次南渡,都没有再回来,这样的事实固化了一种心理体验:南渡即亡国。“往南往南再往南,从来不见北人还,腥风血雨艳阳天。”这是那几年民间流传的一首民谣。人们想起这首民谣就心烦意乱,因为它散发着为历史阴影所笼罩的亡国气息,是一个不祥又摆脱不掉的命运谶语。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兴亡”自励,他们不顾妻儿高堂之累,不畏颠沛坎坷之苦,匆忙收拾行囊,义无反顾地奔走在充满荆棘与炮火的征途上。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酷时刻,他们深信抗战必胜,纵今不胜,尚有来年,己身不达,尚有子孙,终会有驱除仇寇、还复河山的一日。
日本学者竹内好获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奖学金,到北平做为期两年的学术访问和文化交流。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编撰中日双语的语言学工具书,同时渴望能借机与北平知识界进行思想上的交流。然而他失望地发现,北平的文化人已经集体南下,整个文化圈由南京到重庆,从长沙而至昆明,离北平越来越远。他连11月撤离北平的最后一批教授都没有见到。他期待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盛景,完全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可笑想象。此时的北平,已是一座没有生机的死城。这座文化古城彻底隐去了它婉约清丽的春明秋景,以死一般的沉默昭示着某种信念的永恒。
2.长勿相忘
回望中国近代最早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那一代学人,顿感时空错杂、人物纷纭、事件繁多。一个多世纪的星移斗转、岁月嬗替,我们所触及的,似乎总是历经岁月冲刷的那一部分。且将时钟拨回到1913年5月17日,地点是大洋彼岸群山环抱的一处小镇。虽是陈迹残影,也让那个时代多了几分缤纷的色彩。
几张刻印着36人签名的卡片,记录了中国留美学生学会第8届年会及聚餐会,在位于美国东部的绮色佳小城举办。绮色佳(Ithaca,又译伊萨卡),与希腊神话中尤利西斯的故乡伊萨卡岛同名,景色秀美,与其译名一样安静纯朴。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贡献和影响的著名学者,如胡适、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等悉数到场,流连觞咏、畅叙终朝的雅致时光仍依稀可见。这也为我们追寻中国科学社成立的足迹提供了重要线索。
然而世界的压抑、窒息和动荡,几乎是那一代人无从摆脱的梦魇。“花近高楼伤客心”,绮色佳的玫瑰和黄色水仙开得越盛,游子们的心境越是怔忡不安。谁都无法成为一个不闻窗外事的人。
惊心动魄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急切地从科学文化、学术教育中去寻找救国御侮的富强之路。早在留学大潮初起之时,郑观应就对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和教育方式提出了激烈而尖锐的批判:
无论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而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土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弭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乂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
王国维评说晚清的留学运动:
夫同治及光绪初年之留学欧美者,皆以海军制造为主,其次法律而已,以纯粹科学专其家者,独无所闻。其稍有哲学之兴味如严复者,亦只以余文及之,其能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者,吾决其必无也……况近数年之留学界,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怀实利之目的,其肯研究冷淡干燥无益于世之思想问题哉!
及至民初那一代留学生,则注定要承担超出学业之外更为沉重的责任。中国现代社会的建立,本就具有一种强烈的外来文化导向特征,自留学运动开始后,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和融合,变得更为剧烈和痛苦。当时留学生选择专业,“法政科多如牛毛,格致、博物、矿业、农林则几近无人问津”。1914年,任鸿隽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谓“自清末以来,吾国虽有数千博士硕士进士翰林,却不过是饰己炫人,为利而学而已”,这使中国无法产生一个货真价实的学界,也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
在绮色佳,大家经常讨论如何挽救国家危局,感叹中国自然科学之不发达,人们只是将“格物致知”四字挂在嘴边,但天文地质、动植物学始终没有成为一门学问,治学者对于自然少有关心,即使偶有触及,也多与人事牵连,尤其缺乏实证精神,常常以讹传讹。如此格物,焉能致知?
有了这样一个缘起,从第二年开始,大家分头募集资金,要创办一个名为“中国科学社”的学术团体和一份名为《科学》的科普月刊。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一定要刊行一种靠谱的杂志,向中国大众介绍科学。而高层次的学术与教育,一定要凝聚自由、理性、逻辑、实证、批判、求索等品质,也一定要深植于一个多元宽容、自由探索、坚持真理的学术共同体中。
3.“如今我们归来,诸君且看分晓”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及至海外学人陆续归国,由于科学社经济拮据,无力筹建所需费用较多的研究所,遂决定先从生物研究所开始建立。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中说:“先开办生物研究所者,则以生物研究因地取材,收效容易,仪器设备需费亦廉,故敢先其易举,非意必轩轾也。”生物学也就成了中国近代兴起最早、取得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学门类之一。
到1922年,科学社第一个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这也是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成立当日“名贤毕集,一时称盛”,梁启超做了题为《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的报告。
1928年,静生所也宣告成立,积极与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机构合作,进行全国性的动植物种类研究,两家单位“本若同源,事类一体,典籍文物,时相资借,或互为馈遗,间且合组远征队,以从事采集,相维相系,有如指臂”,甚至静生所早期的成员,不少就来自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底色,使他们渐渐融为一个意气相投的群体,有着可以辨识又具有共性的人格特质和价值体系。中国动植物的来龙去脉、详细家底,以及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及相关问题,逐渐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在抗战前相对稳定的时期里,他们每年皆派人员至全国各地,进行中国动植物的调查研究。他们行动的范围非常广泛,“北及齐鲁,南抵闽粤,西迄川康,东至于海”,在广大的乡村,在绿野烟雨之中,“做那些牧人与农民的伴侣”。学问的种子,“因为得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从中可以发育起来”。
知识普及和基础教育等工作,都得从零做起。1923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辟标本陈列馆,后发展为博物馆,用于举办科学展览。1931年静生生物调查所设立通俗博物馆,推广和普及自然知识,陈列动植物标本和照片,免费对公众开放。开放头两月内,前来参观者达八九千人,大多为中小学学生。
为牖启民智,消除愚昧,增进公众自然科学素养,倡导科学文明,科学社经常举行学术性演讲,有时国外科学家来华访问,生物研究所也会热情延请,如美国生物学家尼登就曾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讲演过。久被忽略的科学精神开始受到重视,有品质的学术活动不断,思想激荡,振奋人心。
“国内习动物学者,不乏其人矣。而散在四方,彼此莫知。山河隔阻,音讯疏阔,或累年睽索,或平生未展,江湖寥落,雁影参差。潜修所得,既苦于篇菀,精心所作,又失之重叠。且以幅员之广袤,物藏之宏多,不有信会,何以博洽?”1934年,秉志等著名动物学家在庐山莲花谷组织了中国动物学会,并积极发展会员,开展活动,定期举行学术会议,使会员互通声气,相互切磋砥砺,以互换新知。
除了着重匡谬正俗、推崇科学精神、纠正传统理学的缺陷,生物研究所和静生所的使命,还包括培养中国人健全的常识,纠正伦理化的自然观。对于自然世界,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的分类体系和描述方式有很大差别。西方自然研究的学问进入之后,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人们开始从五百年以来浩如烟海的多种文字记录的文献中,思考、考证中国动植物规范的科学名称,从这里起步,他们成了从事自然研究的第一代中国学人。跋山涉水的田野考察自然也必不可少,往往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进行。
1934 年,生物研究所同静生生物调查所、中研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山东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合作,赴海南岛采集热带和亚热带动物。同年,又与中央大学农学院合组远征队,去云南调查滇缅边境植物。另外几支小分队转赴青海、甘肃、新疆等地,进行为期一年的植物调查。1935年,又派员参加了“浙赣闽林垦调查团”采集植物。江苏昆虫局技师和一些大学的生物学系、病虫害系师生,也是生物研究所的常客,进行短期的合作研究。
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说:“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同样地,从白山黑水到黄河两岸,从中原大地到苏杭沃野,都留下了我們科学家寻访的足迹。他们所到之处,不乏一些盗匪猖獗的“烟障之区”,“均为外人所罕至”。从异邦到故土,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循环中,他们发现了大量前人未知的物种,清查着世界动植物分类体系所缺少的中国部分,思考着生物的多样性,努力寻求着自然的启迪。
随着从事自然研究的留学归国人员不断增多,国内相关课程也得到扩充和更新,如吴蕴珍的植物分类学、李继侗的植物生态学、戴芳澜的真菌学、赵以炳的生理学等。北京大学有杨钟健的古生物学,燕京大学有胡经甫的昆虫学,东南大学有秉志的动物学、钱崇澎的植物分类学、伍献文的鱼类学,浙江大学有贝时璋的实验生物学,武汉大学有高尚荫的病毒学……他们陆续为现代新青年开设人生必备的自然科学的崭新课程,中国近代生物学高等教育也渐入正轨。
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所的建立,使中国的自然研究事业犹如焦渴的生命注入了碧绿清醇的汁液,开始焕发出惊人的生机。他们形成了一种不务声华、唯重实践的研究精神与学风,凝聚成了一个精神磁场,彼此之间有一种竞争的气氛,“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一个以科学为支柱的崭新文化价值系统逐渐成形。
“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任鸿隽认为,“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这种秉承造化旨意,参悟自然奥妙的科学精神,贯穿于他们对现代学术的诉求之中。“科学”不仅限于自然的知识积累,更是在其上提炼出的一种方法,一种形式,一种操守的集合,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潮起潮落而失却本色。
在此意义上,“科学”便不仅是科学社成员的专利,它代表着那一代留学生最不同以往的色彩,它宣告着那一代人最本质地抓住了西方科学理路之精髓,因缘巧遘,得天独厚。当他们陆续完成学业,纷纷回国的时候,这种科学精神就沉淀在他们身上,挥发出生生不息、深邃高远的生命意识。
北至满蒙,南登琼崖,西南达云贵,东极海滨,真正是“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草芥之微”。他们与大自然倾心交流,在一草一木间,领悟精练深微的天地之德、四时之序。
然而,这是一个风雨欲来、朝不保夕的乱世,铁蹄之声已逼近耳畔,华北危难已达极点。1937年,烽烟惊天,鼙鼓动地,这一批青年学人知行合一探求科学的美好时光,被强行打断。
4.南渡与西迁
为免科研设备落入敌手,保存中国动植物研究领域初步形成的科研队伍,保存科研实力并支援抗战,1937年10月,地处南京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钱崇澍的带领下,也启动了内迁工作。
新所址在重庆北碚。重庆四川一带自然资源蕴藏丰富,早已引起中国生物、农林学家的关注。早在1933年8月,中国植物学会就在北碚宣告成立。
生物所暂借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场所办公。西部科学院于1930年在北碚成立,卢作孚为院长主持院务,下设生物、理化、农林、地质四个研究所,其研究人员亦多从事野外考察、标本采集制作,危难时世,流离奔徙,少有宁日,能遇到专业同道,自是难得的慰藉。
历尽艰苦奔赴人地两生的环境,所遭受的痛苦也会达到极点。兵荒马乱之际,人们往往会被挤得东倒西歪,有时遇到日机跟踪轰炸,甚至要躲在火车下面逃命。路上盗匪横生,导致骨肉失散的亦有发生。内迁途中,生物所的几十箱物资曾阻隔于嘉兴,当时去往重庆的轮船大多拥挤不堪,竺可桢受托指派浙江大学负责护送,拟由汉口转渝,但因汉口形势迅速转为紧张,只好转道广西或湖南,经萧山、建德、泰和时几度停转,终运抵北碚。
当时还有更为传奇的“动物西迁”。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职工不愿将一草一木、一鸡一犬资敌,更何况,这其中有很多高价买来供研究用的珍稀物种。他们把数千畜禽装笼置于牛背之上,驱赶牛、羊、猪等徒步离开南京,奔向重庆。这支难以想象的“动物大军”,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约克夏猪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驮着长毛兔……在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后抵达湖北宜昌,这才首次乘坐交通工具,由卢作孚派渡轮送抵重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牧羊塞外归来”,校长罗家伦出城迎接,“相拥大哭大笑,像疯子一般”。
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没有这样的幸运。限于人力物力,他们只将小部分书籍标本迁出,当时迁移工作还未完成,所里还留有专门人员看管价值不菲的书籍、仪器和标本。北方既不能瓦全,身处东南人文渊薮的上海、南京也未能幸免于难。日军在占领研究所之后,迅速掠走未来得及转移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三幢研究楼先后被烧毁。目击者云:
南京失陷是夜即有日军驻于所内,至一月十二日渠在五台山瞭望,忽见文德里火光烛天,惨不忍睹。翌日调查,生物实验馆新厦,北楼及白鼠实验室均已化为灰烬,南楼虽存,亦已破坏不堪。十余年惨淡经营,尽付东流。
當时与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近在同一街道的政府衙署和其他学术机关都安然无恙”,后来细究根源,竟是因为生物研究所曾经抢了日本学者岸上谦吉一批人的上风,所以引起仇恨。早在全面战争爆发前,日本觊觎中国的自然资源,多次派出先遣队多方勘探,1930年初,岸上谦吉一行5人,在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上海前往四川。以秉志为首的中国科学社成员,预感日本此行居心叵测,急电重庆中国科学社成员,全力阻止岸上谦吉的行动,同时,在卢作孚的帮助下,抓紧进行四川的相关国土资源的调查工作,将长江中下游与南北沿海的主要动物种类先行勘测完毕。岸上谦吉在重庆遭到抵制,退返成都后病亡,也埋下了生物所遭致凶狠报复的前因。
日本《支那文化动态》编辑部对生物研究所所长秉志很感兴趣,少不了骚扰和利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避敌伪的耳目,秉志从明复图书馆躲到震旦大学,最后躲到友人方庆咸经营的中药厂里,同时打听去往后方的路线,但总是落空。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他还在考虑去内地的问题。
秉志对生活质量并不讲究,战时他陷入山穷水尽之绝境,家书里满是生活的忧急和经济困窘之愁苦。不过在其所著《竞存略论·叙言》中,秉志还是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来激励国人奋起直追,以保全国家与民族:
自然界之有竞争,无时或息。动物不胜竞争之烈而绝种,与夫互助奋斗而蕃衍者,亦在在可以察见……
吾国今日所罹之大难,为历史以来所未有;然推原其故,皆夙昔涣散因循之所致。凡立国于大地之上,其人民必精诚团结,日夜淬砺,方不为人所夷灭。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所那一代人,他们身上也没有什么“风云之气”,寻常生活没有什么传奇色彩可以给以后的人们作为谈资。他们只是持之以恒地做着学问,在兴亡时代,更有精神深处的一脉真火,周行上下,生生不息。
5.弦歌不辍
山河板荡,神州陆沉。不到一年时间,日军就已经攻陷上海,沿江而上,1938年7月5日湖口失守,7月23日日军在九江附近登陆,中国军人顽强抵抗,由此拉开武汉会战的序幕。
为躲避即将到来的残酷战事,国民政府开始疏散庐山附近的居民。山下隆隆炮声近在耳畔,大路已不能通行。秦仁昌和陈封怀坐镇指挥,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员工陆续挥泪下山,随着难民潮,或江西,或云贵,颠沛流离,辗转跋涉。国势盛衰的生死歌哭,浸透了整个中国的一草一木。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庐山植物园大多数员工陆续到达昆明后,即加入静生所在昆明刚刚建立的云南农林植物调查所的工作。翠湖堤畔的柳影婆娑,碧波荡漾,偶尔也使人能忘却战争,给心力交瘁、苦苦撑持的流亡者们提供了一方歇息之地。
既来之则安之。植物园本就有志于高山花卉研究,于是决定在高山花卉资源极为丰富的丽江设立分所。由于战乱和经费短缺,到野外考察的计划大多搁浅,这时正好因地制宜。
次年1月,秦仁昌率领庐山森林植物园部分技术人员建立丽江工作站。静生所早就无力担负经费,部分人员不得不种药养猪,以维持生活。至1940 年,植物园工作站几乎陷入绝境。秦仁昌想方设法,谋得金沙江流域林业管理站负责人一职,勉强让植物园丽江工作站人员进入战时编制,有了一点微薄的收入,使植物园的日常工作得以维持。
静生所的研究人员蔡希陶,在四川大凉山和云南等地,历尽千辛万苦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植物考察,回北平不久就接受静生所派遣,会同俞德浚等人再赴云南,着手创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作为战时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后方的研究基地。研究所还是发不出工资,蔡希陶和俞德浚就带领职工集资办了一个小农场,种些蔬菜、花卉、烟草出售,还在昆明开了一间鹦鹉商店,专营花鸟虫鱼,靠这些维持职工生活。
与此同时,在胡先骕与农林所前静生同人们的倡导下,木材试验室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起初选址北碚,陆续有从北平和海外归来的静生所人员内迁至此。后因新建的房屋被燃烧弹命中,又把木材室迁往乐山。乐山地近峨眉,水路交通便利,木材资源丰富,迁至此处便于研究。
早在1932年,静生所就建立了国内第一家木材实验室,研究各种木材的性质,使其可以被合理地因材施用。另外,鉴于“各省造林年糜巨款,然收效微薄者,盖树种既未能辨认,森林面积亦未调查,木材之性质,造林之宜忌,咸未加以研究”,静生所还与相关部门一起,试验各种适合造林之树种,以求逐步解决林业技术问题,为全国造林提供指导。
科学精神的构建和学问的延续,从来不是一日千里的奇迹,只能是缓慢积累、自然生长的过程。与国家一时的战争胜负、兴衰消长相比,这甚至是更加重大的责任。科学社的学术领导人不分地位高低,与同事一起勉力经营,弦歌不辍,在遍地烽烟的土地上勤勉深耕,留下了无数带着生命温度的风景与传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关系破裂,日军将与英、美沾边的机构全部封锁、接管,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苦苦支撑的工作彻底中断。1941年12月8日,日军莜田部队封闭了静生所,所有员工皆被驱逐,全部图书及动植物标本概未救出,只有植物模式标本照片之底片、野外采集所用的各省陆军测量地图等少量珍贵资料被提前寄存到大陆银行,幸免于难。所中人员虽曾被日本宪兵传讯多次,幸未受到凌辱。
侵占静生生物调查所后,日本人又以重金聘请时任代理所长的杨惟义为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遭拒后将其扣押。后经多方营救,杨惟义举家迁至江西泰和,受聘于当地大学。
在庐山坚守到最后的英美侨民也受到冲击,被迫撤离,寄存在美国学校的物品终被日军霸占。当日军获悉植物园与静生所的关系后,便把部分物品运往北平,与所霸占的静生所物品放在一起,供日军使用,所有图书都盖有“北支派遣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番号印章。植物园园林遂沦落为无人看守之境,任其荒芜,房屋也任人拆毁。
战前仅用了十几年,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构群就发展起来,盛极一时,冠于中国。战端一开,在上海孤岛的科学社被一把火烧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被封,庐山植物园全员星散,颠沛流亡,存留物资遭到破坏,中国的动植物研究事业进入分崩离析、难以为继的状态。“上自独立之研究院,下至各大学之研究院与研究所,多是经济苦难,不能发展。”
从北平到上海,从静生所到科学社,中国早期从事动植物研究的学者们流徙于天南海北,他们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又同仇敌忾、相濡以沫。残酷的战争现实让他们认识到,非常时期再也不能只埋头于学术理论,他们开始努力将研究方向调整为应用科学。胡先骕指出:
研究经济植物学、经济动物学以求开辟吾国之新富源;研究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寄生虫学以求防治农产之损害,与增进人类之健康;研究遗传学与育种学以求改进农产、林产、畜产之品质;研究农林畜产利用学以辅助工业之发展与增益农产品之价值;研究生理学、营养学以改进国民之体质。
1939 年,四川省的桐油产量锐减,害虫肆虐。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昆虫专家苗雨膏因此注意研究除桐害虫的新法,经长时期的实地试验,成效大著,后在西南五省推广施行,桐油产量大为增加。
生物研究所还对寄生人类及家畜的原生动物进行研究,为资源委员会调查适于发展畜牧业的草原,为经济部调查各处的森林状况和造纸原料,为中华自然科学社调查西康之云南昆明的森林状况,辅助江西省经济委员会调查水产……大量的成就,就是在温饱无着、教学与科研设备极其简陋、图书资料相当匮乏的条件下取得的。科学社和静生所的同人,坚守在云横雾纵、山高水长的西南地带,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
风雨绸缪,瞬间已过数载。
抗战胜利后,蔡希陶没有跟着复员的大军回北平,也没有随着出国潮到国外深造,他的目光掠过苍茫滇水、原始森林还有苍黛耸翠的群山,听从了命运的召唤,留在云南这块红土地上,继续自己的植物研究。他是第一個在云南省进行植物考察和采集标本的中国人。
科学社生物所和静生所的其他同人,都像一捧被礁石撞碎的水珠,散在了天南地北。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堪称权威,有不少是中国动植物学科的开创人。大江大海,水深浪阔,他们身历半个多世纪的忧思和苦楚,上下求索,每个人的沉浮故事都打动人心。
1949年11月,在接受了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的接收改组之后,静生生物调查所从此告终。在近代中国政治鼎革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的环境中,静生所苦心孤诣,惨淡经营,走过短短十几年的时光,中间还夹着一个血与火的时代,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竟能取得显赫成就,完成继往开来之使命,实在令人神往。
庐山森林植物园先是被江西省政府接管,改名为庐山植物研究所,不久后,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成立,又被纳入该所工作站。1954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
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于1950年转属中国科学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1959年4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因着时代的风云际会,这几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近代动植物学术团体,其思想面貌与器识格局,傲立于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的辉煌篇章里。仿佛被历史大风拂乱的正册之外的残篇断章,更显凝重苍远。他们相互之间有过认同也有过质疑,有过友谊也有过隔阂,但还是能够默契地维护某一种精神传统的生长。
受难和荣耀,不曾改变他们的儒雅风貌和家国情怀。颠沛流离之中,他们教学研究未断,须臾未忘家国之难和肩头重任,韵味醇厚的世纪往事也历久弥新。在先驱者们绿色精神的涵养与文化血脉的培植之下,近代中国的自然研究事业逐渐根深叶茂,亭如华盖,蔚为大观。
责任编辑 于文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