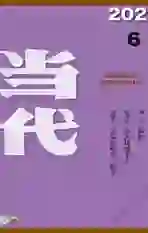遗产
2021-11-20蒋在
蒋在
1
父亲去世后半年,黄杰明收到叔父发来的邮件,信中提到父亲的遗产,要他尽快去处理。那封信隐藏在一堆广告打折邮件中,要不是他多看了一眼,就删掉了。
黄杰明租住的公寓在通往海天99号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晚上他和李俏躺在床上听汽车不断经过,想象那是瀑布下落的声音。卧室里有一扇小小的通风窗,打开它时要站到椅子上去,李俏总是抱怨窗口太高太小。窗上有上一任租客遗留下来的用细小的铁丝绑着的紫色蝴蝶。她冲完澡,卫生间的热气难以散去,扑扑地在往他们脸上灌,热得他们整夜醒着。
夜里,他打开了风扇想开灯去喝杯水。可灯和窗不能同时打开,灯源会吸引体积更小的虫子穿过纱窗。这会儿,窗外的声音并不比风扇的声音小——激烈的风声,树叶的抖动,还有拉货的火车呼呼向前,不停地鸣响汽笛。每一辆火车经过时,厕所的水管都会震动,像是要爆炸了似的。他睡不着。他数不清楚旋转风扇到底有几个扇面,仿佛越数就会越多。风扇只有两个挡位,开或是关。
收到叔父的邮件后,黄杰明每晚入睡前或半夜醒来,都会沉浸在杂乱或想象出来的声音里。李俏躺在黄杰明的手腕上,想象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那意味着未来的房子和生活,她几乎躺在钱哗哗作响的幻觉里。无论如何叔父邮件里提到的遗产都让人振奋,那是绝处逢生的希望。遗产是多少叔父没有说,只留下一句,你父亲的遗产还需要你来处理,像故意留个花样百出的谜底让他们去猜。
如果不是李俏对这笔遗产抱有热情和想象,黄杰明几乎不想去处理。父亲的病将他们家消耗一空。那些年他在建筑工地挣的钱,还不够付他的治疗费。黄杰明无法想象父亲怎么还会有遗产?
中国人。中国人。这是黄杰明到加拿大后听得最多的話。
爸爸在哪?
“加拿大温哥华。”
那时候东方电视台每天都在重播《别了,温哥华》。爸爸在电话里告诉他,温哥华的大街上,有一种很久很久以前的煤气钟,每个准点都会发出汽笛声。他想象煤气钟发出的呼呼声从开满鲜花的大街一直传到广州。那时奶奶随着叔父投资移民去了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后来搬到了暖和点儿的安大略省,只有他和母亲留在了中国。
他和母亲来的那天被称为登陆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挤满了人,一个挂着工作证的女人走向他们,一边对折单据,一边在上面画圈标出重点,引导他们向前走。那里面站满了妇女和小孩。
父亲来接机那天,冲他们挥舞着加拿大的小国旗。他们抱了又抱。父亲把行李塞进出租车的后备厢,司机打开车门,又帮忙把最后一件行李放了进去。
刚上车,黄杰明就感到眩晕。他分不清楚这是在飞机上还是在陆地上。那些远处的海和雾气都像是货船上飘出的蒸汽。他从后视镜里打量司机,司机是个外国人。在飞机上他也看见很多外国人,想和他们说话,把学校里学的都讲出来,你好,再见,晚安。他却不敢与他们的眼睛对视。只有在后视镜里,他才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外国人。
“在这里开出租车的都是印度人吗?” 母亲问。听到印度,司机仿佛听懂了似的,从后视镜里打量着这个中国家庭。父亲点了点头,不去回应印度司机的目光。
“印度人开车,中国人就是开开饭馆,做做厨师,还能有什么?”
父亲把跷起来的腿又放了下去, “他们喊我们chichong, 像剁菜板的声音。”
他不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笑没有。父亲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他在加拿大的工作,好像总是不停地换。黄杰明印象最深的是他忙碌的厨房,他在中国餐厅从早忙到晚,加上时差的原因,他几乎听不到父亲别的消息,挣了多少钱也是未知。他从来没有给他们汇过钱,寄过一张照片,唯一一张照片。让黄杰明记住的不是照片上胡子拉碴的父亲,而是他抬起一只脚踩在一辆红色吉普车的踏板上。他曾无数次梦见过自己坐着那辆红色的吉普车去学校,小时候他对父亲的所有记忆,就是从红色的吉普车开始的。
在黄杰明的记忆中,有那么一两年,他的父亲是缺席的。偶尔会听到母亲与父亲通电话时的哭声。有时候,父亲会安慰哭哭啼啼的母亲,有时候他会听不下去,直接挂断电话,说是消耗不起电话费,有事写信说。
母亲甚至都不知道父亲究竟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给她留了一个打工餐馆的地址,她常年往那个地址寄信,有时也寄照片,父亲却再也没有寄过照片回来。
那时候洗照片很麻烦,母亲拿回洗好的照片摊开在饭桌上来来回回地选,最后选了一张举在手里看了又看。照片里,她穿着黄色短袖衫配一条碎花雪纺裙站在家门口。她在照片背面喷了自己用的香水。香水的味道让人晕眩,还没等味道全散去,她将信和照片快速放进信封,希望将味道锁住。她想着照片和信要飞很久,飞越太平洋飞越大西洋,到达时味道会淡一些。父亲会顺着这淡淡的奇异清香想起他们。
2
黄杰明一家人最初住在一间小屋子里。他们到来的前一日,父亲专门在进门的墙上装了一面镜子。他的母亲在进门时站到镜子前照了又照,父亲知道她喜欢镜子。她说,国外的镜子是要比国内的亮些。
黄昏到来时,他和他母亲走在社区后面的小路上,那儿长满了荆棘和杂草,太阳强烈的光一直照射到晚上九点才渐渐散去。小路用铁丝网拦出来的地方爬满了刺莓,他和母亲提着小桶沿路采着,看见远处有人走来,他们就假装什么也没有干。他们不想让路过的外国人投来打量的目光,其间包藏着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干的轻蔑。
起初母亲的身体里还活跃着对新生活的热情,在屋子里唱来跳去,对着镜子排练她过去学习的舞步。不同的是比起家里的镜子来,这面镜子更小,站得太近就会看不到脚的动作,所以她总是不停地做着朝后挪步的动作。出国前她在文化馆搞舞蹈,负责百姓健康舞的传播,大十字中心广场上跳舞的人遍地都是,她带领着群众在文化馆整天唱唱跳跳过得很热闹。父亲出国后,她在客厅里安装了一面镜子,挡住了一堵墙。她每天站在镜子前排练舞蹈,心无旁骛。镜子让家显得更空旷了,而她在这样的家中更加看不到边界。现在到了温哥华,她一个人还继续在镜子前跳着,似乎只有这样她才能找到自身的存在。
父亲介绍她去中国城的一家汽车旅馆做清洁。汽车旅馆不是真正的汽车旅馆,它只是为了和正规的旅馆区分开。她在房间走廊外挨个用蹩脚的英文喊:“Room Service” ,喊完一遍再用粤语说一遍,“搞卫生。” 起初她很不适应这份与她的职业天差地别的工作,但却很卖力。那时候不需要说普通话,说普通话的大陆客极少。
每天她用两个超大型的拖布从两头对着跑一遍,再跑一遍,周而复始地这样跑来跑去。来回跑动的时候,确信没人看见,她对自己说权当是练功,身体前倾抬起一只脚,然后放下来再抬起一只脚,反复这样抬着抬着直到黄昏降临。
最初每天出门上班前,她还照一下镜子,扭扭身体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合适。慢慢地就不照了。她开始无数次重复那些对于父亲已经没有意义的责问,说没想到他在温哥华过得这么糟糕,还把他们也弄来了。她不愿过这种看人脸色的工作,整天一个人埋头苦干却没有尽头。
她问,我在这里到底是个什么?
父亲问,你在国内是什么?
她说,我是舞蹈家。
父亲说,不过也是个卖艺的,现在你卖劳力,都一样。以后会好的。
她就哭起来,原来以为外国的月亮会很圆。是啊,圆得我们都站不稳,被人踩在脚下。父亲就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的孩子以后就好了。她不听,继续哭闹,边哭边进厨房,看见什么就摔什么。摔得黄杰明惶恐,放声大哭。她才会跑过来抱住他,直到这间屋子,再也包不住他们一家的哭喊。
3
黄杰明翻来覆去调整姿势,睡不着是常事。白天他在建筑工地穿着深筒雨胶鞋,准确迅速地将水泥搅拌器送来的水泥浆护送进地基的坑道管里。午休吃饭时,他坐在钢管上越过停止工作的吊车,看到工地外的马路上车来人往,两个穿着工装服的女人戴着安全帽,嘴巴里的哨子和她们的手势一样一起一落。她们举着大红色写着“停”的牌子左右晃动,指引行人走到对面安全的路上去,这儿在施工。这些单亲母亲,她们在工地上干不了沉重的体力活,只能在工地外面指引行人和车辆。夏天,她们也必须戴安全帽,穿着宽大的黄外套,汗流浃背地站在太阳底下。
下班后,黄杰明把脏雨鞋带回家,他没有把它放在门口,而是直接提进家来。李俏问他想做什么。他叹口气朝洗手间指了指说,脏得没法穿了,得洗一洗。李俏抱着双腿半靠在地上的弹簧床上,懒洋洋地看着他把外衣脱下来说,等拿到你爸的遗产,就去租一套好一点的房子。
黄杰明不理她,走进洗手间关了门。李俏看着他映在玻璃门上的影子,走过去调皮地敲敲门说,你不要装没有听见啊,钱怎么花我都想好了。
黄杰明没好气地回答,钱在哪里?
你不是说你爹有段时间很神秘吗?钱可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天黑前,乌鸦飞过小小的窗口,它们一闪而过,像是天上散落下来的黑色碎片,呼啦啦坠落下来,然后又在风中被扬起。风的声音和汽车的声音,在李俏的嘴里变得格外特别了。她说,心情变了,外面的声音就好听了。黄杰明不理她,继续把一块鱼类的拼图,往一块小木板上粘贴。
李俏侧着头看了他半天说,你有点无聊。
黄杰明埋着头,从小木块堆里捡起一块黑色的颜料,认真地填到鱼的眼睛部位。李俏静静地看着他把别的颜料抹了又抹,一块木板被他染得很乱。她用力往床上一坐,嘟着嘴说,你对遗产到底有什么打算?
黄杰明说,我想不出我爹会有什么东西留给我。
李俏笑起来,她看着那扇被风吹动的小窗户说,你就想象一下嘛,想象一下总是可以的。
黄杰明已经把拼图完成了,他端详着手里的作品说,我想不出来。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租一套新房子,我在网上都看好了。
李俏也跟着看黄杰明手里的拼图,一条张着嘴巴的鱼,想往树上跳。
黄杰明从来没有想过要搬家,那得多花多少钱,他只是工地上掙时薪的杂工,一小时二十块,每天和混凝土吊车搅拌机打交道,工作毫无技术可言, 明天说没也就没了,他可以被任何人替代。
夜里窗外滴滴答答地下着雨,李俏走进卫生间,撕开验孕棒的塑料包装纸,做了尿检。 她从厕所出来时,情绪有些低落,郁郁地躺到床上。
黄杰明翻了个身转向她,“结果怎么样?”
她不说话,缓缓地拉过他的手,放在她的腹部上。 他突然翻身跃起,再将头埋下,贴近她的肚子,他不敢靠得太近,生怕她会感到不适,她感到他在颤抖。
李俏侧身靠在他身上说,我想把它生下来,你爸的遗产可以让宝宝长大,我们还可以带着宝宝周游世界,你说好不好?
黄杰明一动不动地躺着,他清晰地感觉到她呼出的气,在自己的皮肤上酥酥软软的,和着雨点慢慢地植入另一个黑夜。
4
他想起父亲,想起自己曾经画过父亲临死前脑袋凹陷进枕头的模样。父亲去世后一个月,他画过九幅这样的画。黄杰明是左撇子,一到画父亲的衣服时,他的手腕总会碰花已经画好的父亲的脸,像故意不想记住父亲的模样。
他听着外面的声音,想象父亲肺部感染的颜色,和父亲画像的颜色一定一致。尼古丁侵蚀了他的每一寸肺叶,把它们染得像炭一样黑。不用凑近也能感知到他最后呼出的一口气,带着比平时更难闻的气味扩散在冰凉的空气里。
那年父亲离开家后,母亲整天坐在社区后面的小路上,也许她是在等他回心转意,也许是回忆他们初来乍到时的快乐。很多年后,她真的把父亲等来了,离家几年后的父亲患上了绝症,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在父亲身患绝症走投无路时,她同意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来。在此之前,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这是黄杰明始终坚守的父亲的秘密。
母亲在父亲临终前最后的三个月里,不停地把父亲的菜谱,他各类关于设计的书,拿到中国城的书店里去贱卖。那些大大小小的图册,她每一本都会翻开,看到复杂的设计图纸,她又从中抽回一本,想着也许将来黄杰明做建筑师还用得着。她从老板手中接过钱,直到推门走出,呼呼的风朝她脸上使劲地刮。
父亲在家里发出的气息越来越弱。母亲却开始忙碌,先从储藏室的砂轮钻头开始处理,然后是客厅和卧室,最后打开衣柜,把父亲冬天的呢子外套也收了起来,放进了储藏室之前放五金工具箱的位置,她坚信父亲熬不过这个冬天。
父亲最后的气息落到了床上。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人也就该走了。父亲走后,母亲的恨意无处释放,将这些年的埋怨都指向了黄杰明。他也就如逃难一般离开了家,再没有回去过。后来她将房子变卖住进了疗养院。他想父亲离家是对的,如果不是死亡突然来袭,他永远也不会回到他们身边。
那个下午,太阳煌煌地照在屋外的草地上。母亲坐在屋子里,屋子朝北,没有光。她叫他进屋去,声音像从很远很黑的洞穴里出来。他感觉自己是飘着进去的,脚没有着地。她坐在床上,他看不清她蓬乱的头发垂下脸的样子。
坐着的母亲和他站着一样高,她手里拿着一张相片,问上面的人他认不认识。他低头不敢看母亲,不明白为什么母亲连照片中的父亲都认不出来。那个看起来高耸,胡子刚修过,甚至还有些意气风发的父亲。是他和一个女人的照片,两人手里都抱着一个孩子,站在商店的大门口,侧面是一排他叫不出名字,在加拿大随处可见的树。那个紧紧挨着父亲站立的女人,一头卷曲的乌发,黑皮肤笑容灿烂,露出一口雪白的牙。女人的脚踝很粗,踩在地上的一缕光里。照片像是对折过后印下来的,那时他还小无法把父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
他不敢说话。
上高中时,他的母亲突然会在他埋头沉思时,拿着他小时候她给他看过的照片在空中挥几下说:“你想知道照片里的那些人是谁吗?” 不等黄杰明回答,她就会告诉他,那些黑人就是他父亲的野女人,还有那异母同父的妹妹们。这个女人为父亲生了一对双胞胎,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孩。为此她们在纽奥尔良的61站旅馆旁边得到了一处房产。
他们是怎么好上的?他记得母亲咆哮着问过,父亲说你们在中国,我一个人在这里,她对我好,就这么简单。母亲怒不可遏,说就这么简单,像动物一样。父亲说对,就这么简单。
5
天还没亮李俏就把洗手间的水放得哗啦啦响,她走起路来还用手撑着腰说她腰扭着了,说弹簧床直接放在地上不利于健康。她说她要去看看在网上才看过的房子,做好搬家的前期准备。黄杰明不愿听这样的唠叨,就假装还没睡醒。
李俏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地说了一阵走到厨房里,一个杯子随后摔碎,她大叫起来,黄杰明只好起身。李俏并没有去扫地上的杯子,而是把他头天拿回来洗的雨胶鞋提起来,对着黄杰明比画着说,你看看这个家哪里还有一点生活的样子?连一双破鞋都挤不下了。你赶快把它洗了,我弯不了腰。以后这些东西不要往家里拿,脏了就扔了。
黄杰明不说话,打开水龙头冲洗胶鞋。李俏站在洗手间门口说,我在网上看好了一张床,要九百五十加币。黄杰明听到这个数字哆嗦了一下,水哧啦一下淋到了他的身上。她问他,你激动什么?他说你是不是疯了,那么贵的床买来摆哪。李俏冷笑了一声说,不是有遗产吗?黄杰明急了,说你拿到了?李俏生起气来,她说他这个人最没有想象力,钱虽然没有拿到,计划一下,想象一下总该可以的吧。
6
黄杰明的脑子轰轰地响,他相信那个声音绝对不是来自水泥搅拌机。一个上午他都站在搅拌机前,看着水泥翻倒进凹槽里,想象着李俏在太阳底下去看房子的样子。大门外举旗吹哨的两个妇女,一个将手举得高高的,一个正引导一辆大型货车开进工地,路上的行人驻足在太阳底下等待过马路。
他回过头,吊车起降时在空中划出来的弧度,让他感到了一丝担忧。太阳直射在他的脸上,他不得不眯起眼睛。哐啷一声巨响,那辆开进来的货车撞到了一堆横在地面上的钢筋上,司机的急速反应是在刹车的瞬间扭转方向盘,工地上尘土飞扬。
他们都看到了,司机坐在高高的驾驶座上,他被扭转的方向盤呈45度斜角卡住了。工地上几个人围过来,他们抬来梯子试图打开车门,将受伤的司机弄出来。救护车来了,受伤的司机被人从车里抬下来。
黄杰明从一股巨大的呛人的灰尘里冲出来,耳朵里灌满了搅拌机和金属撞击的声音,他看见司机的手从担架上垂下来。
那天下午,黄杰明不再照管搅拌机,他坐在高高的钢筋上面,太阳将粉尘扬出来的颗粒在光里分离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黄杰明没有等到下班就走了。他脱下工装,换上自己的衣服,还特意将脱下的那双雨胶鞋,举起来高高地抛向一堆木料。他听见工友在他身后大声叫他的名字,还骂了脏话,起吊机叮里哐啷地上下移动,这一切似乎都与他无关了,他大步流星地走出工地大门。
李俏开门进屋,没有发现床上的黄杰明。她的心情似乎比往日舒畅。黄杰明听到她唱歌的声音,心跳还是加快了。
他一动不动地等着她打开灯,然后尖叫一声站在他面前,等待她问一个自己也无法回答的问题: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然而灯亮了,一切并不如他所想。李俏走到床边,仰靠在他身上长叹了一口气说,今天看了好几处房子,心里有数了。
那天晚上,李倩拼尽了全力,换来了黄杰明去处理遗产的决心。
7
黄杰明不会想到从西雅图来的这段路程非常折腾。他下了飞机后坐上灰狗大巴,到他们要去的村庄已是终点。这里离市中心相距二百三十八公里。大巴司机下车抽烟,看见一个中国人下来,司机指了指大巴侧面的行李储藏室。黄杰明摇了摇头表示没有行李。
大巴司机对黄杰明的回答难以置信,抖了抖烟,把手环抱着靠在柱子上斜眯着眼说:“来玩?”
黄杰明灰头土脸地朝远处看:“来找人。”
司机困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在这里要做些什么买卖。的确,这里什么也没有,贫瘠一片。近处有一家破败的加油站,宽宽的沙地周围稀稀拉拉长着几棵树,开着火红的花。这个村落只能作为一个城市衔接另一个城市的中转站,休憩点。正是这里,叔父和他的堂兄,还有几匹德国运来的马生活在不远的农场里。
早晨,太阳从远处的树林缝隙里,大片地倾泻下来照在草地上,整个草地和那座孤孤零零的木屋被光染成金红色的薄雾缭绕,空气里全是籽香味,还有马粪的气味,城市的杂乱一下子被甩到了九霄云外。
是堂弟来开的门,他们没有料到黄杰明这么早到,他的脸在突然而至的晨光里,像种子裂开时那样乍然有声。他们就杵在强烈的光里,一个从背面挡着光,一个正面迎着光。
还是黄杰明先开口,他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堂弟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也没说是,只轻轻地笑一笑。叔父弹奏《教堂序曲》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叔父是当地中国教会的钢琴师。曲子停顿,堂弟才生涩地拍拍他的肩膀说:“节哀。” 黄杰明知道要让一个高中生明白生离死别,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黄杰明朝他点点头,表示一切已经过去了。
叔父是听到了他进门的,琴音还是没停,直到弹错了一个音符,才停顿下来,然后缓缓地走出房间站在黄杰明面前。他们很多年没有见面,平时也鲜少联系,他们现在是靠约定的见面来确认对方。叔父苍老慵倦的身体正好挡住窗户的光,以及外面地上吃草的马。
他说:“你好不好?”
没有等黄杰明开口,转过身从冰箱上取下一把钥匙说:“跟我来,” 然后又转过身,对黄杰明说,“生老病死没什么好固执的。”
黄杰明还是没开口。他也奇怪,跟在叔父身后,没有丝毫的亲近感,像跟着一位陌生人。他们出了屋子,外面的阳光比之前炽热,从山林那边打过来一片金光。
叔父回头看了一眼黄杰明说,你做什么工作?黄杰明埋着头说,刚刚辞职。叔父陷入沉思,好像黄杰明从来就这么大,这些年他如何成长,如何面对父亲的死,都被自己这个叔父忽略掉了。
黄杰明尾随叔父绕过马厩,太阳光下立着几匹闪闪发光的马,白色的,红色的,它们在栅栏边甩动着蹄子。黄杰明这会儿更加无法想象,父亲会留给自己怎样一笔遗产。在他来的三个小时里,两个半小时,他都在预想叔父怎样将他领进书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银行卡或支票,也许因为不信任,还会让他写一张收据。
为了让叔父觉得他不是专程为了钱来,拿了钱就走,他也许会和叔父在门口抽上几支烟,留下来吃午饭。这就足够了,对叔父和父亲这一代人来说,不需要啰里啰唆的表达。任何过分的流露情感,都是可耻的。
他想抓紧返回城里,然后赶下午六点到温哥华的飞机。也许在候机时他会给李俏打一個电话,告诉她钱终于拿到了,接下来的三年他们不用再愁,或许十年……可这也有苦恼,他不知该不该用光父亲苦心经营攒下来的钱,他甚至还想起了另外三个人,他的三个黑妹妹。她们在哪里?过得好不好?知不知道爸爸死了,或者会不会怀疑爸爸究竟是如何死的。
8
现在,叔父没有领他进书房,他们已经走过马厩,沿着一条开满小花的山路往下走。难道是山脚下的另一间屋子?那也不错,他可以改掉晚上的机票,在屋里住一晚,顺便检查一下屋子里的暖气照明等设施,对房屋价格做出评估。不用等估价员来,他就能判断并锁定一个价格,没有任何让人议价的余地。剩下要做的只是程序问题,估价员只需要挂到当地的网站上,联系当地的买家来看房或者看地。这些他们在行,黄杰明做不了什么,等钱到账,他就会永远离开这里。
叔父说,有几匹德国运来的马。黄杰明看见了它们,草使得空气更加冰凉,雾气在阳光下已经渐渐散开,和蓝蓝的天空拉开了距离。近处两匹成年的白马被栅栏隔开,有一匹小马驹跟在母马的身后。
叔父指着不远处的那匹马说:“本来还有一匹马,” 叔父目光聚集在了那头独身的马上,“是只小马驹,是这两匹马的孩子。”
他们走下了几道土坎,阳光下开白花的植物有些闪亮。 “有一个冬天,晚上,我们开车去镇上加油,回来时汽车轮胎被钉子扎破了,到家时已经很晚,马没有关进马厩,结果郊狼咬死了一个小的。” 叔父顿了顿,好像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我们回来的时候,只看到那匹公马浑身是血。”
叔父说到这儿停了下来,两个人的脚踩踏地面的声音覆盖了刚刚的故事。黄杰明倒觉得叔父像是动物园的讲解员,才不理会黄杰明这会儿想什么。“我们给它洗了好几天,血洗也洗不掉。” 叔父扭转回头,耸了耸肩表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随后又补充一句:“那只活下来的小马,从此以后离它离得远远的。”
黄杰明不知道叔父为什么告诉他这个,两人埋头向前走,风从远处吹来,带着各种混杂的气味。他们来到山下,叔父把仓库的门往里面推,用脚一踢,门才打开。叔父用手掸开眼前的灰尘说:“就是这个。”
黄杰明站在拉闸门外,他转身去看之前在山上看到的那栋木楼就在近前,屋前有两棵开花的石榴树。叔父对着他招招手,他走进去拉开了落满灰尘的挡车布,那辆小时候梦里,载着他穿越加拿大许许多多城市的红色吉普车,突然现身在眼前。
叔父也像刚才堂弟那样拍拍他的肩膀,显然不是出于同一个目的,从黄杰明还未进门那一刻,他就完全能把控得住黄杰明的失落。
责任编辑 孟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