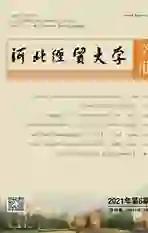我国乡村治理方式的检视、转型困境及破解之策
2021-11-19杨丽
杨丽
摘 要: 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乡村治理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国家治理的基石。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我国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变革,乡村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过程异化、治理保障不到位等治理瓶颈。因此,提升与改善乡村治理方式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可以通过构建和完善“三治融合”、多元共治、外部保障等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
关键词: 乡村治理;转型困境;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6-0073-08
(一)新中国成立前:“皇权不下县”的“礼治”方式
1.“皇权不下县”的自治方式。中国传统社会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拥有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很难将统治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组织细胞——乡村。乡村治理主要委托当地士绅集团,辅之以宗法制度,实行“皇权不下县”的士绅自治方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史学界一般定义为从西周分封以来到鸦片战争前夕,也就是从公元前11世纪中期到1840年,大约3 000年的时间。西周实行分封制,所谓“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准确概括了周代乡村治理格局,其核心是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从秦朝到隋朝,“乡”为属于郡县之下的国家政权治理。唐中叶后,“村”正式上升为地域性治理层级;从王安石变法到清代,开始了“乡、村”自治制度。
中国传统乡村自治是一种成本极低却又极其稳定的国家二元体制,乡村治理主要倚重精神因素,靠民俗和乡规来维系和发展,倡导“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自治理念,构成了一种国家最节约成本的治理方式。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体系土崩瓦解,士绅自治的孑遗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2.“政权下乡”治理方式的过渡。清朝晚期计划在全国推行城镇自治,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统治集团提出的乡镇自治理念。但随着清朝的覆亡,乡镇自治失去了它应有的政治实践作用。晚清至民国初期,地方治理上实行“地方精英自治方式”,也就是经历了一个“政权下乡”的过程,力图在乡村建构起县、区、乡的政权体制。国民党统治时期,乡镇政权设置有了一些变化。1928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规定以“地方自治”原则建立区、村(里)、间、邻制度[8]。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农村政权的建立,这一情况发生了局部改变。1932年8月,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为严密民众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起见”[9],废除了地方自治,实行保甲制,建立高度集权的“自管管人、自教教人、自养养人、自卫卫人”政教合一体制,乡镇最终还是纳入到国家行政体制,实现了乡、镇长行政官僚化,地方自治空有其名。
从总体上看,尽管中国历史上素有“皇权不下县”的思想,但在绝大多数时期,都一直把基层政权建设作为国家对乡村地区实行有效统治的基础,并加以巩固和调整,乡村治理经历了由外向到内敛、由简约到复杂,由开放到封闭的历程[10]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政社合一”的管治方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将基层政权与乡村政治联系起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成功地完成了将政权直达乡村。乡村普通农民第一次与国家政权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政权全方位管理乡村。
1.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村庄行政化治理。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确立,各级组织正式建立。乡村基层政权的性质和地位有了本质的变化,采用的是“乡村”两级政权机构,“乡”是村的上级机关,“村”是最底层的国家政权组织。新中国成立之初,“村”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出现是民国时期“行政村落的延续”[11],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治理方式的直接遗产。
2.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乡村治理方式。1958—1983年,人民公社制在我国存在了25年。人民公社是合作化运动升级的产物。1952年冬,全國掀起了第一次农业合作化高潮,全国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达4 536.4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9.9%,到1955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上升到6 038.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0.7%。[12] 1952—1955年,初级合作社发展由点到面,稳步推进。1952年底,全国有3 600个初级社,1953年11月发展到1.4万个,1954年3月达7万个,1955年1月达48万个。[13]1955年7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合作化运动迅速升级,到1957年底实现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入社农户达11 945万户,占总农户数的95.6%,农业已实现全盘集体化。1958年8月,在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同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社改组为23 630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比重上升到99.1%,总数1.27万户,我国农村全面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4]。
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其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基层政权组织——乡政权及其之下的村政权,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方式。生产队属于基本核算单位,绝大多数土地和生产资料都掌握在生产队手里,其拥有独立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3.“包产到户”乡村治理体制。1977—1978年,中央为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产品价格,提倡家庭副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适度扩大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发展社队企业等政策相继出台,给农村带来了新景象。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通过“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包产到户”的兴起,同时也意味着人民公社制度“日落西山”[I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源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逐渐推广到全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使得人民公社体制逐渐瓦解。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乡(民族乡)、镇成为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特别强调“在政社分设后,基层政权组织依照宪法建立”,表明乡镇政府代替了人民公社职能。
(三)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乡政村治”礼治与管治并存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国家政权上移,乡村治理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型,实行了“乡政村治”方式。
“乡政村治”体制下的“乡政”是指国家在乡镇一级建立的国家政权,对本乡镇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村治”则是指在乡镇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展开工作。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建立乡政府,并要求这项工作在1984年底完成,使得人民公社这一基层政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国家根本大法的角度奠定了我国乡村政治的治理方式和法律基础。
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我国“乡政村治”体制得到确立。1982—1985年,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逐渐解散,代之而起的是乡镇建制:人民公社被乡政府取代,生产大队被村民委员会取代,生产小队则演化为村民小组,权力也由行政村负责。在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法制化轨道,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了很多法律和具体政策与之相配套,使得“社改乡”工作始终有政策指导和法律依据,在“乡政村治”体制下,虽然乡镇党组织在村庄治理中仍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但村民委员会占主导地位,村委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村庄治理面貌。1987年,我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选举”等内容,赋予村委会一定的自治权,基本确定了我国农村“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从而大大降低了国家的行政成本。
“乡政村治”是中国农村从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的主要体现,传统乡村自治源于共同的外部风险而逐步形成的村民向心力和凝聚力,主要依靠乡村内生治理力量和乡规。从整体来看,易于构成具有较强内聚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得到乡村普通民众的心理认同,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价值体系和能够为村民自觉遵守的公序良俗,使家族文化和乡村文化得以绵延永续,充分发挥稳定社会、维护民生、凝聚人心和规范行为的主体性作用。
(四)21世纪以来:乡村治理法治化、现代化
21世纪,中国乡村治理进入了新阶段。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开始;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部署;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农村彻底取消农业税。2004—2010年,中央连续发出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对乡村建设给予政策支持。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治理也迈入了新发展阶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16],并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开启了我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征程,推动了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强调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保障。[17]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亮出“中国之治”旗帜,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8]2020年5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乡村治理。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19]乡村治理作为中国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完善、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有利于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不少地方新的乡村治理方式已初见成效,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国的乡村治理方式将朝着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前進,实现乡村善治成为未来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愿景。
三、内卷化:乡村治理方式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传统性乡村治理方式日渐式微,党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及社会秩序等治理方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囿于历史、地理环境、人文、资源等因素,乡村治理仍存在“内卷化”现象。所谓“内卷化”,指的是乡村治理在新环境变化下,没有及时做出与时俱进的创新而引发的诸多异化现象,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导致治理能力下降。
(一)治理主体困境:治理主体原子化倾向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机制下,士绅阶层是治理乡村的核心力量。当前,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基层党委领导、基层政府主导,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为基础,农民群众为治理主体,多种社会经济组织共同参与的乡村多元治理格局。[20]然而,在乡村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进程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原子化倾向,产生了治理乏力共生困境。
1.从基层政府角度看。基层党和政府是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和重要践行主体,在乡村治理中承担更多的乡村治理服务性工作。但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基层乡镇党委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容易成为基层治理的权力集结点,导致基层党组织缺乏与其他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主动性,影响了基层党组织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基层党组织权力过于集中,难以形成统一的协调机制,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绩效。
2.从基层组织角度看。乡村基层队伍整体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位”或“越位”现象,在履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职能欠缺,制约了村民自治的成长,导致乡村治理中很多方面存在组织保障功能落实不到位情况,影响乡村治理的绩效与水平。
3.从村民角度看。当今我国处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随着现代村民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大,农村主体成员流动频繁,尤其是青壮年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由于常年外出,不再以地为生,这部分村民的生活重心已不在农村,他们和村庄的关联性越来越小、家园归属感日渐淡薄,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意识越来越淡漠和疏离,导致传统乡村村民之间凝聚力趋于弱化。
4.从社会组织角度看。农民合作组织、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发挥,但是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化程度的制约,以及缺少专项法律支撑,组织自治性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在乡村治理中参与乏力。
总而言之,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农村基层治理主体格局,但由于治理主体原子化的实然生存方式,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离散,乡村公共精神缺失,极大地降低了乡村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乡村治理出现松散化现象,陷入治理行动困境、乡村治理低绩效趋向。
(二)治理过程困境:治理过程异化倾向
乡村治理成效只有付诸于治理过程才能彰显,乡村治理过程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但当前乡村治理过程存在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基层党组织功能异化等方面的不足。
1.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化倾向。“利益格局是指在一定社会和制度环境下形成的以经济效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利益形态。”[21]中国传统农村的利益格局是以皇权为中心,族权、宗权和绅权主导的“礼治”格局,这是一种整体上比较均衡的利益格局,村民之间在劳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很小。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处于不断变化与流动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政府权力的运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促使村民进一步分化,产生不同的利益格局。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积累了巨大经济财富的村民,在职业、社会地位、价值观等层面也发生了改变,逐渐成为新时代的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逐渐成為乡村治理的带头人。而其他大多数普通村民,只能在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充当精英的附属物,使得原本比较简单、均衡的村内分配逐渐朝着分化的路径演绎,乡村贫富分化差距拉大,乡村利益格局也处于重塑之中。随着村民阶层分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给乡村治理增添了新的矛盾。
2.基层党组织功能异化,农村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间接影响乡村治理。我国部分乡村治理法治化程度不高,乡村治理中规范化、法治化和制度化程度不高,影响了治理的质量和效率。首先是乡村宗族势力间接干预乡村治理。受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在乡村治理进程中,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宗族势力”并未被外力肢解,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宗族势力在农村地区有不同程度的抬头和蔓延,并成为影响农村基层治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乡村治理中“谋取家族利益”的行为仍然存在。部分农村以亲情、宗族为纽带形成的宗族势力,间接干预农村换届选举、民主选举,视换届为宗族、宗派势力的比拼,暗地里操纵选举工作,对农村基层的社会稳定、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等构成一定的威胁。此外,宗族势力也常常介入村内纠纷。有些村民的矛盾纠纷常常在强大的宗
族势力影响下以打压、调控等方式平息,严重损害了村民的正当权益。其次是黑恶势力影响乡村治理。在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随着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和农村内生权威的衰落,给乡村黑恶势力的滋生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黑恶势力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一些“村霸”、宗族恶势力等长期盘踞于农村,损害群众利益。在特定条件下,农村多重利益的叠加驱动着势力化现象的加剧,基层灰色利益链的出现为黑恶势力的生长提供了空间,破坏了乡村的公平正义,加大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难度。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对黑恶势力的纵容、包庇使黑恶势力难以被彻底清除。如操纵破坏农村换届选举、把持基层政权等乡村黑恶势力污染了基层治理生态,损害了基层党组织形象,影响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还有一些村霸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中侵吞集体资产,为个人谋取暴利, 侵害群众的合法利益,法治建设与“人治”传统的矛盾冲突严重。国家“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权力全面向乡村社会回归,尤其是自2018年开始,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乡村黑恶势力从其所占据的治理空间中逐渐被清除。
(三)治理环境困境:保障措施不到位
乡村治理环境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和保障。近年来,虽然乡村治理环境得到普遍改善,但仍然存在组织保障弱化、制度保障不健全、物质保障欠缺、法治保障不完备等问题,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1.组织保障弱化。乡村治理环境复杂,在治理过程中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基层党组织只有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增强本领,充分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组织保障作用,成为乡村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才能应对各种严峻挑战。但在新形势下一些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出现不适应、不能为、不作为等问题,削弱了其在乡村治理中作为一线堡垒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2.制度保障不健全。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制度完备性,乡村治理只有在全方位的制度保障下才能全面推进。首先,基层党组织在具体工作中不能正确平衡“管理”和“服务”的关系,存在服务活动形式单一、组织协调能力差等现象,多元主体难以实现利益协商。其次,基层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个别村干部工作能力欠佳,缺乏责任心和事业心。再次,村民自治机制不健全。村民自治在维护农村稳定和基层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当前随着乡村治理环境的变革,村民自治组织管理还存在能力有限、缺乏积极性、监督不到位等情况。最后,基层社会组织功能发挥乏力。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亟需基层社会组织的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我国乡村社会解决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我国基层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却面临着深刻矛盾:由于村民参与程度低,导致基层社会组织的运行效率与作用的发挥逐步减缓;基层社会组织的培育所需要的社会环境供给不足,导致其依附性强;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参差不齐,导致其定位模糊,公益性与互助性不明。
3.物质保障欠缺。物质保障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当前,乡村治理在物质保障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财政对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支持力度不够,部分村民自治组织运转过度依赖上级拨付;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绝大多数依赖于土地承包费,自身产业发展乏力;社会资金对基层社会治理投入匮乏等问题。
4.法治保障不完备。乡村治理的建设必须运行在法治的框架内,要保证村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治权。但当前乡村法治建设相对滞后,基层党组织和村民法律意识仍较为淡薄,影响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四、困境破解:多元机制同频共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对乡村治理也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需要有效的“中国之治”来予以解决,要引入现代治理理念和要素,构建现代化治理机制,破解当前乡村治理的低绩效困境,有效回应乡村社会的治理需求,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一)制度保障:完善“三治融合”机制,构建治理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根本遵循。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方式,构建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的“三治一体”“三治并进”良性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重点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
1.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乡村自治代表现代乡村的“民主秩序”,是乡村治理目标,也是法治和德治价值目标。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要通过自治来实现和推进。要坚持乡村自治为本,在乡村治理中更好地体现和维护村民群众权益,调动村民关心乡村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增强乡村治理活力。要健全科学的村级治理机制,完善村民自治的法规体系,发挥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的治理作用。要构建科学化的村级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机制和村“两委”的關系协调机制,促进基层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高乡村治理效率。
2.加强乡村法治体系建设。乡村法治代表现代乡村的“法治秩序”,是实现乡村有序治理的保障和防线,也是自治和德治的规范与保障。在执行治理中坚持法治为本,将各项治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乡村良好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首先,要树立起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切实依法保障村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其次,加强基层法治的基础建设,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夯实法治基础,确保村级治理依规依法,实现基层服务和管理精细化精准化。再次,培养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提高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最后,加快基层法治网络平台建设,搭建多主体合作共建共享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3.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乡村德治代表传统乡村的“礼治秩序”,德治为乡村治理提供价值支撑,为自治和法治提供思想和情感支撑。在乡村治理中要坚持德治为先,以德治弘扬乡村正气,以德治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首先,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新时代农村价值体系的建立,形成涵养乡风文明的长效机制。其次,重视乡规民约在移风易俗、改善民风中的引领作用。通过村规民约教育、引导、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促进公序良俗的形成。再次,以新乡贤文化引领村民道德实践,搭建乡贤文化平台,更好发挥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让新乡贤成为推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展的强大动力。最后,全面加强乡村思想道德阵地建设,充分汲取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智慧,营造风清气正的新时代乡风,全面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达到乡村善治的最终目的。
总之,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不可割裂,要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内化合一,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方式。
(二)发展引擎:构建多元共治机制,夯实治理制度建设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润滑剂”,需要建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机制。党的十八大提出“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2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遵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要求,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的转型,构建由多元主体、要素共建、共商、共治、共享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7]为了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构建多元共治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格局,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人民群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管理。
首先,要确保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凝聚社会治理力量。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政策来源和决策者,在新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创新新时代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科学定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加强农村党支部基本队伍的建设,巩固其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教育引导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17],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统领作用。
其次,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治理作用,构建乡村治理主体全方位协同、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要把广大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9]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农村致富带头人的作用,要积极引导、培育和发展志愿者组织、非营利性的环保组织、公益慈善机构等,实现村两委领导与村民个人、村民组织、集体经济经营者等多元主体的全方位的合作与协商。建好、管好、用好村级社会组织,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形成乡村治理合力,构建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最终实现乡村善治。
(三)政策落实:改善外部保障机制,优化治理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善治,要不断完善乡村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发挥好社会保障在乡村治理中的兜底作用。
1.组织保障。“只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强、把基层政权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才能稳固。[19]提升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美丽乡村的建设者。乡村治理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最终实现乡村善治,要增强乡、镇党支部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有效领导,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首先,落实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功能,“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23]。持续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建立和完善基层党支部培训教育机制、奖惩激励机制,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加强和完善对农村党支部的监督和约束,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其次,落实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协作功能,加强农村党支部基本队伍建设,进一步依法理顺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会、村集体等的权责关系,严厉依法整治侵害农民利益的基层党组织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充分调动各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最后,落实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真正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推动乡村治理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2.制度保障。实现乡村善治,需要多措并举,健全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和政基体系,形成乡村治理的制度环境。首先,构建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力量发挥渠道,真正做到村民事务决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健全农村党群沟通保障机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借助网络媒介、采取多种方式畅通协商、沟通渠道,鼓励村民投身乡村治理与建设,保障民主决策。其次,完善人才保障制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要选优、配强乡村基层领导队伍,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做好宣传组织工作,形成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对乡村现有人才的专业化培养,同时加强对返乡人才的支持力度,鼓励乡村精英返乡,为家乡发展作贡献。引导退伍军人、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到农村定居和创业,鼓励优秀大学生人才加入到乡村建设中,让“乡村要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24]。最后,完善乡镇备案制度,保障公序良俗合法合规。村规民约具有维护社会秩序、引导风俗文化的功能,是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要完善村规民约备案审查机制,结合乡村实际,对其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倡导村民移风易俗,真正发挥村规民约的教育和惩戒作用。
3.物质保障。 乡村治理的开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保障。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滞后与短缺,是乡村善治的障碍之一。首先,要拓宽融资渠道,为乡村治理提供经费支持和物质保障。安排专项资金,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积极吸收多种形式社会资金,对农村耕地保护补贴、经济林种植补贴等专项经费保障及时拨付到位,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推进精准脱贫。其次,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实现城乡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之地。再次,加强农村养老资源建设,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方式,解决好农民的养老问题。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最后,加强乡村公益事业建设,积极开辟乡村公益事业多元化新路径,激励农民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积极完善农村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制度,逐渐改善乡村治理的物质保障。
五、结语
“乡村孕育了乡土文明,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5]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乡村治理要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国家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结合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特点、新情况,把握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转变乡村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乡村善治格局,早日实现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 //www. Stats.gov. cn/tjsj/zxfh/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2020-02-28.
[2]陶学荣,等.走向乡村善治——乡村治理中的博弈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
[3]周文,司靖雯.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问题与改革深化[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1):16-25.
[4]高其才.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N].光明日报,2019-02-26.
[5]单俊宇,单连春.新媒体环境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问题与对策[J].领导科学,2020(4):110-113.
[6]王敏,杨兴香.构建法治框架下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J].人民论坛,2018(11):98-99.
[7]诗经·大雅[M].北京:中华书局,2006:13.
[8]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
[9]中华民国大陆史料汇编4[M].中国台北:文津出版社,1965:876.
[10] 张要杰.中国村庄治理的转型与变迁[M].长春:吉林出版社,2010:272.
[11]熊秋良.建国初期乡村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为考察对象[J].贵州社会科学,2010(6):125-128.
[12]馬晓河.中国农村50年:农业集体化道路与制度变迁[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Z1):3-5.
[13]建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回顾[M].北京:党史文献出版社,1982:6.
[14]王贵宸.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308-379.
[15]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508.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3-11-13.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1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9-11-01.
[19]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0.
[20]袁金辉,乔彦斌.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J].行政论坛,2018(6):19-25.
[21]汪玉凯.利益格局扭曲的政治学分析[J].同舟共进,2013(2):22-23.
[2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8.
[2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
[24]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N].人民日报,2015-01-22.
[25]加芬芬.传统文化复兴与村庄文化功能优化[J].探索,2019(2):181-192.
责任编辑:艾 岚
Inspection, Transformation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Yang Li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Farming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Rural governance is the basic link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w era,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a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in China's rural society. Rural governance is faced with bottlenecks such as weakening of governance subjects, governance process alienation, and governance guarantee. Therefore,upgrading and im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new era. We can solve the dilemma of rural governance
by buiding and improving mechanisms for integration of three governance, multi-governance and external security.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dilemma; mechanism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