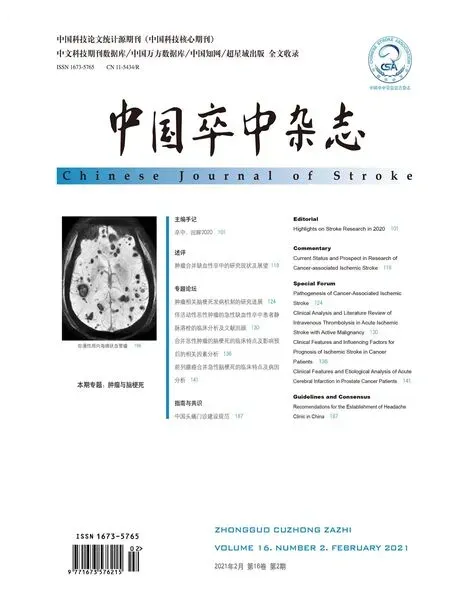高海拔地区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2021-11-19刘著樊青俐吴世政
刘著,樊青俐,吴世政
卒中已跃居为中国居民的第一大死因[1],高海拔地区缺血性卒中发病风险较平原地区明显增高[2-3],且呈现年轻化趋势[4]。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是引起缺血性卒中最重要的病因,且与卒中复发和残疾风险增加密切相关[5-7]。高海拔地区居民长期生活在低氧、低压的特殊生态环境中,导致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危险因素与平原地区有所不同,了解高海拔地区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形成的危险因素对该地区卒中防治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影响高原地区脑动脉狭窄的危险因素及对应的病理生理机制进行整理,作以下综述。
1 海拔环境因素
国际上通常把2500 m作为高海拔地区的阈值。随着海拔的升高,大气压逐渐下降,吸入氧分压也随之下降,从而导致“低压缺氧”现象。动脉低氧血症不仅可刺激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管收缩,而且还可引起血管退化、损伤。长居高海拔地区人群出现红细胞增多、血红蛋白水平升高等一系列改变,以适应特殊的地理环境。然而,随着海拔高度增加,人体血液黏稠度呈明显增高的趋势,血液流动明显减慢,血小板聚集性增强,易于附着在损伤的血管壁上,从而影响脑微循环的有效灌注量与氧的运输功能,容易导致脑动脉血管附壁血栓形成,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程度。
1.1 低氧、低气压 高海拔地区特殊的低氧、低气压环境特点所引起的一系列循环、炎症介质等变化在脑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一项研究显示,相对于海平面的大气压力760 mm Hg、氧分压21%,2500 m和8000 m高海拔地区分别下降为560 mm Hg、15%和267 mm Hg、8%[8]。高原低氧、低气压的环境特点使得肺泡及毛细血管氧分压差减小,氧的弥散速度减慢,从而引起脑循环血流量改变。一项关于夏尔巴人儿童(3800 m,尼泊尔)与居住在海平面地区儿童(344 m,加拿大)的对比研究显示,高原儿童脑血流减少约30%,具体表现在颈内动脉、椎动脉及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下降[9]。安静状态下,流经脑组织的血液占每分心输出量的20%,氧消耗量占全身耗氧量的20%~30%,且主要依赖糖有氧代谢提供能量,上述特征使得脑细胞、神经元等组织在缺血、缺氧条件下易受到损伤,并可引起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2020年一项研究发现,颈动脉狭窄与同侧脑灌注减少密切相关[10]。
缺氧对血管有众多“负面影响”。正常氧状态时,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ed factor 1α,HIF-1α)可被蛋白酶快速降解,并刺激内皮细胞和巨噬细胞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但在高海拔缺氧条件下,HIF-1α被保护免于降解,并在细胞核中与低氧调节基因中的特定DNA序列结合,以避免低氧引起的细胞损伤,导致VEGF分泌减少[11]。既往一项针对不同高原生存期健康成人血液临床指标的变化研究中发现,高原生活组人群血液VEGF水平显著低于平原组[12]。VEGF水平升高可为新生血管形成和维持血管完整性提供条件,并可促进已损伤的血管内皮细胞愈合以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再狭窄[13]。反之,VEGF水平下降,则这种维持血管内皮完整性及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作用被大大削弱。
内皮细胞具有形成血管和招募壁细胞(周细胞和平滑肌细胞)的能力,其中壁细胞为血管壁提供结构、弹性和收缩特性。研究发现,缺氧导致新生血管失去周细胞,变薄并逐渐破碎[14]。缺氧还会显著降低VEGF的表达水平,从而明显抑制了新生血管生成进程。同时低氧可促进细胞凋亡、抑制NO释放,增强炎性因子和内皮素基因表达,促进血管炎症反应发生,造成血管壁损伤;低氧条件下HIF-1α诱导Krüppel样因子-4上调,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迁移,在血管重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5],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发生,而动脉血氧含量下降又引起交感神经介导的血管收缩导致动脉管腔缩窄,进一步促进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发展。
1.2 与高原环境相关的疾病 高原长居人群因长期暴露缺氧的独特环境中,而导致一种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慢性高原病(chronic mountain sickness,CMS),CMS表现为头痛、头晕、呼吸困难、睡眠障碍、高血压、心力衰竭和红细胞增多症[16]。而高原红细胞增多症(high altitude polycythemia,HAPC)是CMS的主要表现。HAPC由长期慢性高原低氧刺激引起的以红细胞过度代偿性增生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发病率随海拔升高而升高,尤其在安第斯山脉常见[17]。红细胞过度增生引起血液黏度升高,导致血流缓慢,又因血小板黏附聚集作用的增强,易导致血栓形成。高原人群的脑动脉顺应性及弹性比平原正常人群低,外周阻力升高[2],这无疑会进一步加重体内微循环的黏聚性,尤其脑部微循环可出现无复流现象。红细胞水平升高还可增加促炎症标志物的产生,造成血管内皮的炎症反应和氧化损伤[16]。另外有研究指出,HAPC患者具有血脂紊乱、高血压、肥胖这三种重要的动脉粥样硬化高危因素,促使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风险增高[18]。
2 高原地区人群适应性及遗传变异
全球有超过1.4亿人居住在3000 m高海拔地区,主要包括亚洲青藏高原的藏族、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及非洲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阿姆哈拉族等。长期居住高海拔地区低氧环境会引起人体细胞组织、生理功能等遗传和适应进化,以提高机体对高海拔环境的生理适应能力[19]。在自然选择下,高原世居人群出现不同程度的适应性改变,与此同时,也影响了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发生。
高原世居人群通过提高血红蛋白水平及氧饱和度的方式来提升动脉血氧含量,以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是决定血液黏度的重要因素。既往通过影像学检测发现,随着血液黏度增加,不仅使得脑循环血流下降,还可引起脑血管功能损伤,为后续脑动脉粥样硬化及狭窄病变提供了一定的病理生理基础[20]。
高原世居人群为了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会出现显著和持久的交感神经激活。既往一项研究发现,丹麦平原地区健康人群在海拔5260 m的安第斯山脉上驻留4周后出现交感神经功能亢进;当该人群返回到正常海拔地区4~6个月后,这种交感神经激活状态仍然持续存在[21]。去甲肾上腺素是交感神经兴奋时释放的主要内源性神经递质,可激活平滑肌α1肾上腺素受体导致平滑肌细胞收缩、局部血管狭窄、痉挛,进而促进内皮细胞收缩,影响血管完整性。另外,交感信号介导造血干/祖细胞从骨髓到髓外组织动员,导致大量单核细胞进入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促进粥样斑块的不稳定重塑,从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进展[22]。
肺循环血管收缩是局部肺泡缺氧的另一种适应机制,但血管收缩同时也导致了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压力增加[8]。肺动脉高压可引起系统性动脉硬化增加,使得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疾病的风险增大[23]。同时,肺动脉压力增高又会刺激血浆内皮素-1(endothelin-1,ET-1)的产生。ET-1作为血管内皮产生的最有效的血管收缩剂,与内皮功能障碍、炎症和血管重构等密切有关,ET-1水平升高可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细胞外基质沉积和炎症介质的分泌,从而激活动脉粥样硬化进程[24-25]。
在高原环境影响下,肠道微生物群多态性也发生一定的变化,有助于宿主适应特殊的生态环境[26]。多态性的改变造成一定程度的代谢障碍,加之慢性缺氧导致胃上皮细胞再生能力降低、黏液分泌减少等导致胃肠黏膜屏障损伤,进一步引起严重的代谢紊乱及营养不良,造成高海拔地区特别是藏族居民幽门螺杆菌感染检出率高[27]。目前有研究认为,幽门螺杆菌可诱导炎症介质,如IL-6、CRP等分泌,激活血管内皮细胞,加速动脉粥样斑块形成甚至破裂[28]。
3 饮食习惯差异
高海拔干旱少雨及低温环境使得人群依赖的营养资源贫乏。一项对不同地区人群饮食习惯情况的调查发现,与欧洲地区平原人群相比,尼泊尔人和玻利维亚人在食物种类方面比较贫乏,主要以淀粉类与肉类(包含动物内脏)等食物为主[17]。高海拔地区人群高脂、高胆固醇的饮食习惯容易造成机体血脂水平异常,尤其是胆固醇水平升高。血脂异常不仅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还可通过改变血液流变性而引起微循环障碍,导致动脉硬化狭窄的发生和进展[29]。另外,高海拔地区人群水果和蔬菜摄入较少,导致世居高海拔地区人群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30-31]。高同型半胱氨酸可导致血管内皮损伤、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从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及狭窄的发生,目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已被证实为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32-33]。
综上所述,高海拔地区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危险因素具有一定特殊性,除常见传统危险因素外,还与高原独有的环境、适应性与遗传变异、饮食习惯等因素密切相关,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点。了解高海拔地区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形成的危险因素对于该地区卒中的防治有重大意义。
【点睛】高海拔地区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危险因素具有一定特殊性,除常见传统危险因素外,还与高原独有的环境、适应性与遗传变异、饮食习惯等因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