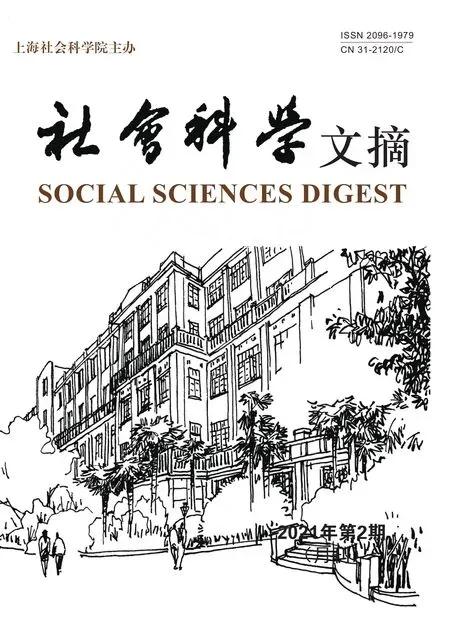论经典传注的阐释学意义
2021-11-15李春青
文/李春青
引言
在西方,阐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他是奥林匹亚山上诸神的信使,负责把神的信息传递给人世间。中国古代阐释学的最早称谓是“传”,而“传”也是信使的意思。依《说文解字》,“传”之本义就是驿使,后来引申为经典阐释。二者不同之处是,赫尔墨斯是神与人之间的信使,而驿递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使。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传达、转达的中介作用。这也正是阐释的根本意义之所在。任何阐释都是一种传达,是在两者之间的中介。阐释使单个人成为群体,也使无数具有独立性的文化因子构成一种文化传统。因此阐释是文化传承的基本手段。传注作为中国古代的经典阐释学与西方现代阐释学有诸多相通之处,也存在不少差异,有其独特性。以西方阐释学的观念和术语为参照,在“间距与之间”的框架下对这种传注之学予以新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建构当代阐释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传注之学的基本形态
对经典的阐释是西方哲学史的基本言说方式,也是中国儒学史的基本言说方式。在西方阐释学史上先是形成了文献阐释学和圣经阐释学,后来产生了一般阐释学和哲学阐释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则存在着源远流长的传注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注之学就是中国古代的经典阐释学。
对周代典籍的传注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大量存在。吕思勉先生尝云:“然孔子以前,《诗》确已自有传,《史记·伯夷列传》引《轶诗传》是也。以此推之,《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书传二字,盖平举之辞。孔子序《书》,盖或取其本文,或取传者之辞。故二十八篇,文义显分古近也。”吕先生此说是有根据的。现存先秦典籍中有大量“传曰”之类的引文,历代注者大多不明其出处,皆可视为孔子前后关于经典的解读性文字,即所谓“传”。在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史上,“传”是最早的阐释方式。概括言之,自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王室史官整理制作了一批记载先王事迹与政教典章的文献,颇有存档备查之意,后来这些文献便成为贵族子弟教育的基本内容,所谓“六艺”是也。可以想见,从西周中期乃至春秋后期,这四百多年中此类“千万数”的文献,不仅是孔门儒学之嚆矢,亦无疑是诸子百家之渊源。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相对于《礼》《易》《诗》《书》之类的西周典籍而言,先秦儒家的阐发性著述都可以称之为“传”,如此则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传”就应该是孔子的《论语》。在西周史官整理彼时政典、记载周王政绩之时,并没有把这些文献视为“经”,由于周代贵族秉承敬天法祖、慎终追远之文化精神,常常把祖先的事迹、言论神圣化,予以格外的尊崇,久而久之那些记载了先王政典和事迹的文献就成了经典。当那些关于此类文献的解读出现以后,便有了经、传之分。久而久之,前辈的“传”也渐渐获得尊崇,被后学加以注释解读,从而也升格为“经”。“十三经”中的《论语》《孟子》《春秋三传》《尔雅》《礼记》《孝经》皆属此类。
孔子本人屡次声称自己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阐发西周典籍,最著名的提法便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这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古代经典阐释者的自觉意识。这里的“述”就是“传”的意思。“述”和“传”都是指对古代典籍的传承与阐述,与“作”,即“制礼作乐”意义上的创造相区别。
然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绝非仅仅是传述古人的思想而已,他们在传述中融进了新的思想观念。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为什么孔子之“述”,其功竟“倍于作”呢?那是因为他能够“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这“折衷之”便包含了他的创造。儒学之所以为儒学并不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周人的礼乐文化传统,而是因为它提出了一套新的价值观而为后世所接受。从孔子以降,阐释便成为儒家学说发展传承的基本方式。经典阐释学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作为一种文体的“传”,现存最早的一批应该是《诗》之《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春秋》之《三传》《周易》之“十翼”、“礼”之《礼记》、“乐”之《乐记》等。这些“传”或“记”应该都是战国后期儒者根据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传注整理加工而成。比如《易传》,即古人所谓“十翼”或《易大传》,与《论语》《孟子》等相近,都是通过具有充分创造性的论说来阐明古代典籍所蕴含的某种道理,即所谓“道”或“大道”“先王之道”,不像汉儒的章句之学那样逐章逐句注释解读,看上去似乎主观发挥极强,虽名为“传”,实近于“作”。然而从思想内核来看,这些“传”的继承性因素绝不会弱于其创造性因素。虽然孔子的“仁”的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确实具有很大的创造性,但作为儒学内核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与周代贵族是一脉相承的。宋代以前儒者常常“周孔”并称,把周公视为儒学的开山鼻祖,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相比之下,“传”的其他形式与“经”的文本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例如与《易传》不同,《左传》乃是通过“属辞比事”,即叙事来阐明经义的。《左传》把《春秋》这个“文章提纲”扩充为文情并茂的丰满文章,在人物与事件的描写中蕴含了礼乐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虽属于“传注之学”,却开了后世“史传”传统之先河。《公羊》《谷梁》二传虽然开启了为后来汉代经生所热衷的“章句之学”的形式,但其对《春秋》之“微言大义”的挖掘却充满了想象力,其创造性甚至不亚于《易传》,其“过度阐释”之处比比皆是。唯有《毛传》比较尊重经典字句的本义,近乎后世的训诂之学,至今依然是欲读懂《诗三百》所不可或缺的参考。
除“传”之外,较早的经典阐释方式还有“记”和“说”。《说文》:“记,疏也。”又“疏,通也”。可见“记”字原有“疏通”之义,它是一种对经典的特殊阐释方式,并不依附经文,而是根据经义作补充性、拓展性阐述。“记”与“传”有诸多相同之处,不同处在于在用法上诸经各有侧重。观《汉书·艺文志》所载,对《诗》《书》《易》《春秋》各经的阐释性文字多称为“传”“故”“说”“微”等,唯独对“礼”的阐释多称为“记”。“记事”之“记”,即“史记”之“记”,正如“史传”的“传”一样,都是史学传统的概念,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记典礼”之“记”,我理解,应该包含对典礼仪式之意义的阐释,而不仅仅是对礼仪的记录。
早期另外一种阐释性文体名曰“说”。《说文》:“说,释也。”又“释,解也”。可见“说”的本义并不是说话,而是解释。其实“说”和“传”“记”一样,原本都是一种关于经典的阐释性文体,但后来都没有作为文体发展起来。“传”和“记”都演变为叙事性文体,属于“史传”类而归于“史部”或“集部”了。“说”则成为一种议论性短文文体,通过记一事或一则寓言来说明某种道理,诸如《师说》《捕蛇者说》《卖柑者说》之类,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阐释功能。吕思勉先生说:“传、说二者,实即一物;不过其出较先,久著竹帛者,则谓之传;其出较后,犹存口耳者,则谓之说耳。”谓“传”先而“说”后,言之有据,而谓二者“实为一物”则忽视了它们的微妙差别。
我们再来看“注”,这是一种比“传”“记”“说”都要后起,与之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经典阐释方式。“注”的本义为“灌”。清儒王兆芳云:“注者,俗作“註”,灌也,传释若水之灌注也。贾公彦曰:‘注义于经下,如水之注物。’主于灌注经义,与传同意。”按照贾公彦的意思,“注”乃“灌注经义”,是指经义简而不明,需要注释方可以解。在张舜徽先生看来似乎“传”“注”除了出现有先后之外并无其他区别,实则不然。细加考察,二者的区别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传”是不定型阐释方式,“注”是比较成熟化、固定化的阐释方式。即使孔子之前“传”的漫长历史忽略不计,就从孔子到战国之末的两百多年中,“传”的形式也出现了多种变化。《论语》《孟子》《荀子》作为“传”的早期形态,可以说是一种“非文本阐释”,就是说,这种阐释不是针对某一种具体文本展开的,而是对某种文化系统的整体性阐释。因此这种阐释主要是一种精神阐释,而不是对具体观点、概念或词语的解读。其二,“传”比较注重文本整体意义,“注”比较关注字句的具体意义。在这方面,《毛传》虽然称为“传”,实则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注”,而且是现存文献中最早的“注”。其他称“传”者则大多以阐发大义为主。汉代的经典注释多称为“章句”,如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等,也有不少直接以“注”为名者,如杜子春《周官注》《仪礼郑氏注》、郑玄的“五经”及《孝经》《论语》的注本等。
除了传、说、记、注之外,中国古代传注之学的具体方式及其称谓尚有许多,诸如解、释、故、微、笺、义、论、辨、评、驳、叙、引、章句、义疏、申义、讲义、衍义、集义、正义、口义、疏证等,都代表着某种传注方式,包含着阐释学意义。但或则由于所用较少,或则因其与传、说、记、注所含之义相近,故不再一一辨析。
中国古代经典阐释的意义建构模式
如前所述,一部中国儒学史也就是一部经典阐释学的历史,阐释在儒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形态与发展方向。前述传、说、记、注等所代表的古代传注之学可以归纳为古代经典阐释之意义建构的三种模式,我们分别称之为衍义性阐释、因循性阐释和修正性阐释。这三种阐释模式在中国阐释学史上各自占有一片领地,并且产生出不同的经学流派。下面分述之。
我们先看衍义性阐释。吕思勉先生尝言:“六经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则又自有其义。孔子之义,不必尽与古义合,而不能谓其物不本之于古。其物虽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别有其义。儒家所重者,孔子之义,非自古相传之典籍也。此两义各不相妨。”这是极为精辟的见解,是对“衍义性阐释”最准确的说明。所谓“衍义性阐释”就是指那种以阐释对象为基点,但具有超越于阐释对象之上的明显创造性的阐释模式:看上去是阐释已有文本,实则建构新的意义。《论语》《孟子》《荀子》作为对周代经典的“传”,最突出地表现出了“衍义性阐释模式”的创造性特征。这些先秦儒家学说,作为对古代典籍的阐释,是在继承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其创造性的,通过他们的“衍义性阐释”,从古代典籍中孕育出了儒学这一具有整体性、独立性的思想系统,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这种“衍义性阐释”的创造性也是儒家“春秋学”的一大特征。一部《春秋》,不管是否孔子所作,其“历史大事记”的性质是无疑的。王安石称之为“断烂朝报”,梁启超称之为“流水账簿”,都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经过儒家的阐释之后,其“微言大义”就被建构起来了。而且这种意义建构往往是“层累式”的,是通过阐释的阐释或阐释的阐释的阐释来展开的。在今天看来,《春秋》不过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极其简明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重要事件,但在公羊学看来,这部书可是非同小可,是一部体现着“圣人之志”的“拨乱反正”之书,其意义与作用甚至可以比肩功业彪炳千秋的夏禹、商汤、周文武。而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认为:“《春秋》曰:‘杞伯来朝。’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这里“以《春秋》当新王”也就是“《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的意思,是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与作用是使这部书承担起一代“新王”的责任,就像夏禹、商汤、周文武三代圣王那样。如此,则从文化传承或者价值观念体系的角度看,《春秋》接续了“三代”传统,特别是周人的礼乐传统,保存了评价是非善恶的基本标准,因此也就当得起一代圣王的历史使命了。董仲舒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是儒家士人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整个“《春秋》大义”的核心——被公羊学总结出来的所谓“三科九旨”之说,都是遵循了这样一种阐释逻辑。
通过这一例证可知,“《春秋》三传”及《春秋繁露》这类所谓“传”“说”,是很有创造性的。所谓“《春秋》大义”,如“王鲁,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类并不一定是“经”的固有之义,而是那些“传”“说”等“翼经之作”建构的产物。到了后来的宋学那里,这一“衍义性阐释”的创造性同样得到了充分发挥。即如“二程”代表的理学,其阐释对象主要是《孟子》《易传》《大学》《中庸》等几部典籍,是先秦“思孟学派”的延续。其所讨论的核心概念,如心、性、诚、敬、理、气、情、欲等,虽然都是思孟学派曾经谈论过的话题,但在理学家这里,无论是意义的深度还是广度都是他们的前辈无法比拟的。
“因循性阐释”是指那种更加尊重经典文本之“原义”与作者之“本意”的阐释文字。“传”这一文体原本大都属于“衍义性阐释”,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毛传》。这里的“传”是一种近于汉代经学之“章句训诂”的阐释方式,也就是“注”。《毛传》的随文释义乃是因循性阐释,《毛序》《郑笺》的主观评价则属于衍义性阐释。这里的“传”与“笺”都是属于对词语的注释,但一者按照文本呈现的样子注释,使难以理解的词语明白起来,一者则除了字词释义之外还有明显的意义建构。在今天看来,《毛传》对诗歌的注释依然是我们读懂《诗经》作品基本意思的重要参考。《郑笺》在阐释诗句句义上也有一定参考意义。至于《毛序》,就诗歌文本阐释而言,可以说参考价值最小。
“修正性阐释”是古代经典传注的另一种阐释模式,其基本特征是既有章句训诂的形式,随文释义,又有衍义性的阐发,表面上是挖掘文本本义和作者原意,实际上乃是对阐释对象加以修正,从而建构一种新的意义系统。对于这种阐释模式,最突出的代表便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了。总的看来,“修正性阐释”可以说是“衍义性阐释”与“因循性阐释”的结合。因此,一部《四书集注》,既有对文本固有之义比较符合实际的解读,也有程朱理学体系的话语建构,二者并行不悖,既是对古老传统的继承,又是新的意义之建构,体现出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