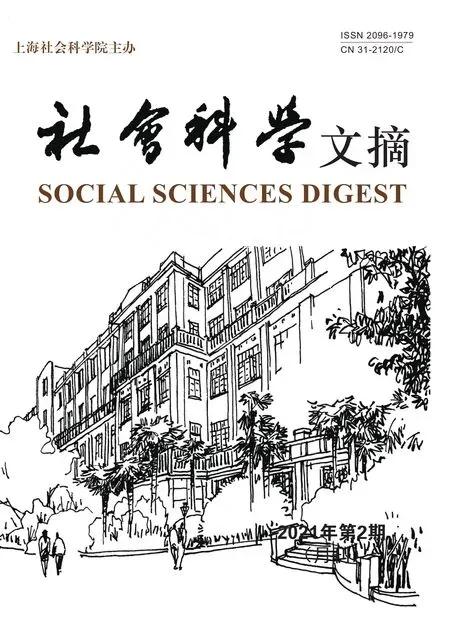古典美学的现代转场与当代创新
2021-11-15管宁
文/管宁
传统的现代性转化需要确立科学的理念,以此进行宏观鉴照,提出战略思路、方法与途径,这是一个不断调整、校正和完善的过程。任何宏观构想与现实境况之间都难免存在偏差乃至脱节,理念引导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始终停留于宏观层面,在发展理念确立之后,中微观层面的具体展开成为关键。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进入传统、把握传统,又走出传统、转入当代,再到融合传统精华、结合当代需求进行超越和创新的实践活动。
本文在新时代文化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重新进入传统文化之中,通过提炼中华美学的核心内涵与精髓,探讨现代转场的可能与方式,包括转场之后传统美学基因的现代呈现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世界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期待与需求。
文化原点:传统基因的选择与提炼
人们感受一个民族文化的伟大,往往先是从直观领略其文化创造成果开始,继而才认同其文化观念及其所蕴藏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后者无疑是构成一个民族独特文化身份的内在因素与核心所在。
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的语境中,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重要主题与学术热点,各种理论探索在不同维度上延伸与扩展,人们就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更多共识,也提出了关于传统再生的各种理论设想,以及实践层面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无缝对接等问题。
中华艺术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与表征,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与意趣构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核心。新时代的文化创造离不开对传统艺术资源与美学基因的选择和提炼,文化创新的过程就是对富有时代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元素与审美精神的辨识、认知过程,也是对文化基因进行提纯和重新编码的过程。因此,继承传统应从文化原点开始,追溯和聚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本源,选择传统中最富有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基因作为创新起点。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的关键性概念入手,从中捕捉和把握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或许是实现传统之现代转化的基本进路。中国古代在文化艺术领域经由长期实践,形成一套独特的美学概念体系,诸如意境、气韵、形神、中道、谐和等,它既是艺术创作的特征描述,更是艺术观念的特质体现,构成了中华古典审美的重要观念元素。在这些艺术概念下形成的审美意趣与风格,在世界艺术殿堂中可谓孤标高致、魅力独具。总体上看,在艺术领域中,西方更多地偏重于具象化、描述式、叙事性的表现,是色彩、画面的视觉冲击与场景讲述,更侧重于诉诸外在感官;而东方中国则偏倚于抽象化、象征式、感悟性的表达,是意境、韵致的营造与境界构筑。意境美是中国山水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的特征。唐中期以来,逐步成熟的文人山水画,在笔墨韵致上更加注重依照主体的想象与意趣进行创作,现实形象退居其次,代之以抽象之形和象征之形,并于其中寄寓主体自身的艺术情怀与境界,由此形成“以形捉神”的独特审美创造方式。这样的艺术表现,通常不以外在直观视觉感受为审美特征,而以整体气氛营造构成独特意境,需深度品味方能体悟和捕捉其微妙神韵。
对中国艺术史的检视及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提炼出古典美学的若干主要特征。第一,注重以形捉神。中国山水画自中唐以降,便属意于“以形捉神”的意境表现,这虽然有着艺术本身发展的内在必然,但随着“树石云水,俱无正形”等山水审美认知的深化与观念的改变,技法上有了“破墨”革新,水墨画由此兴起而丰富了意境的表现。第二,推崇静谧空灵。传统美学中静气、禅意的意境之美,是古典美学的主要基调。禅宗避世归寂的境界追求、老子哲学中“为腹不为目”“致虚极、守静笃”的精神内蕴,不仅深刻影响着艺术家的审美观,而且充分体现于艺术创作和表达之中。第三,追求动静相生。静气与禅意不是静止不变,更不是枯涩板滞,古典山水画中“山静日长”的独特意境,是一种在“极静中追求极动”,进而使“心灵从躁动归于平和”,走向宁静的艺术创造过程。第四,崇尚自然本真。古典美学崇尚内在真实,不求外在形似,认为神似是更深刻、更本质的真实。很显然,中国古典艺术并非不擅长客观叙事与描摹、造型与写实,而是更关注如何借助于物质形态的提炼、重构与凝定,去表达对整体生命的认知与感受,去寻求诗意栖息的心灵之所。由此,铸就出简括空灵、大巧若拙的独特东方美学旨趣。
虽然中国传统艺术以意境、气韵为主要特征,但也同样有写实一脉传统,彰显出传统艺术既有独特审美基调,又有多样性表达的文化包容特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仇英的《南都繁会景物图》《清明上河图》《汉宫春晓图》、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佚名的《宪宗元宵行乐图》、计盛的《货郎图轴》等,在大空间尺度里进行写实风格的创作,其中所运用的散点透视技法独步世界画坛,成为中华绘画艺术的独特创造。
中华美学不仅体现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之中,也反映在历朝历代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和平与繁盛时期,更能看出精神与美学的追求在日常起居以及造物中的表现。《红楼梦》作为传统文化的结晶,凝聚了中华数千年古老文化的精髓,大观园中的生活,既有抚琴、对弈、书法、绘画之雅好,也有吟诗、作赋、猜谜、品茗之雅趣,还有观戏、游园、赏花、宴饮之雅集。日常起居充盈着文化内涵,休闲娱乐更是文气浓郁。撇开豪门贵胄的奢靡与浮华,《红楼梦》中相当一部分表现的是富有浓厚文化气息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活动,就其所追求的生活品质和趣味而言,体现了我们民族所独有的生活美学与智慧,是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在生活领域的重要表现。
造物智慧:审美延展与伦理精神
中华古典美学不仅融注于社会文化乃至日常的文娱活动中,而且借助器物嵌入日常生活起居乃至生产活动中。器物设计源于审美观念、艺术趣味,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元素,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美学趣味、生活品位,提升人们的审美素质,规约着人们的礼仪举止,由此塑造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形象。
艺术设计是中华美学进入日常起居的重要方式与手段,也是审美基因在造物领域的延伸与扩展,古代造物也因熔铸了独特审美精神而呈现出迷人的东方神韵。园林山水建筑是山水画之笔墨意境立体、现实的呈现;明式家具是书法线形艺术的气韵转换与抽象表达;瓷器美术是书画艺术在瓷胎载体上的展现;丝绸图案是经典审美符号或具象或抽象的表征。事实上,古代造物智慧中,技艺与匠心固然值得称道,但艺术审美意趣的融入与精准表达,使得器物拥有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与美学价值,成为中华造物最具民族性和审美性的文化创造。
关于古代学者对中华传统造物文化的研究、现代学者对造物文化探索的现状,笔者曾有详细梳理和阐述。针对以往研究之不足,现提出若干宏观性思考。第一,造物文化以物质形态呈现,往往被纳入制造业等经济领域,不被文化专家、美学家所关注,这是人为地将精神文化与造物文化加以分野,应予以纠偏。第二,造物设计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和生产效率,而且在今天更成为打通各行各业之间界限、实现产品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第三,以往我们忽略了造物文化的传播,其实造物文化既是精神文化的物质显现,又是全球化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媒介,因而也是树立国家形象最有效的方式。第四,造物文化的现代转型、变革与创新,要有先进科技、先进人文思想的支撑与引领,才有望领先世界潮流。
关注造物文化,必须深入把握其与精神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艺术史角度看,艺术与造物本就存在互融互通、互渗互鉴的密切关系。就诗歌绘画艺术与园林的关系而言,概括说来,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园林树石成为诗文绘画主题。隋代之后,以园林树石为山水题材的诗文绘画大量出现,体现出这一时期山水观念的演变与成熟,以至于形成画松石的审美风气。其次,园林树石成为文人创作场所。自宋代至明清,“西园雅集”主题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中是一个不断被描摹和演绎的题材,历代画家创作的各具意境的《西园雅集图》竟有47幅之多。再次,艺术家多重身份现象颇为普遍。自魏晋肇始,文人士大夫便在山水审美观念确立之时,将审美理想延伸至园林建造之中,甚至存在兼具艺术家与匠人双重身份的现象。
文人艺术家深度参与造物活动,将山水诗画里表现的审美理想,熔铸于各种造物过程,形成全然不同于西方园林的独特美学风格。而置放于园林屋宇之中的家具陈设,也具有相同的审美意趣,形成东方独有的简括、洗练和写意的美学特征,营造出禅意的氛围。明式家具深得书法绘画中所凝练出的抽象与还原的艺术精神,构成其生命力的深层文化诠释。感悟性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特性,也是包括明式家具在内的器物设计的特质。园林之中的盆景艺术是浸透着浓厚艺术审美趣味的造物,这使得器物高度艺术化而成为文人精神审美的另一种表达和存在方式。
不难看出,传统造物,尤其是由文人直接主导和参与的造物,不只关注由工艺和技术所形成的功能性,更关注器物两个层面的精神属性。第一是审美情感。物以传情的造物理念,使得古典造物不仅注重器物的艺术视觉美及其对生活的装点美化,而且注重借助器物表达人格理想、品德情操的精神功用。第二是礼仪伦理。虽然古代造物也关注器物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宜性,讲求舒适性、便利性与科学性,但在功能性与伦理性发生冲突时,总是倾向一定程度地牺牲功能性而突出伦理性,这使得古代家具往往拥有规范行为、礼仪建构的礼制功能。
“天人合一”理念在传统造物中有鲜明体现,中国古典园林以及乡村民居在空间营造、审美意趣上,始终遵循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构建法则,如同古代山水画中房屋建筑总是显得渺小而又恰切地与自然山川相融合,构成自然的组成部分,从不抢自然景观的风头,使得建筑与自然浑融一体,形成心物相照、巧法造化、顺乎自然的美学特征。园林所具有的虽由人作但宛自天开的境界,与诗词绘画的师法自然如出一辙,以至于黑格尔认为中国园林作为建筑而言是一种不完备的艺术,甚至不是一种正式的建筑。
我们今天要创造美好生活,既要继承古代精神文化美学基因,也要传承造物文化精粹,从传统造物中提炼凝定出的韵致之美中汲取养分,为当代设计文化发展提供卓殊的美学资源,探索实践现代条件下艺术与造物的有机融合。
蜕故孳新:现代转场与当代创新
中国古代在精神文化和造物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农耕时代创造的审美典范与话语体系,在工业、后工业乃至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实现现代转型,进入新时代的文化场域,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思考的重要时代命题。
新时代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的,是为美好生活的建构提供基于传统文化根基的当代美学支撑,在文化资源的援引、选择和汲取上,既不能以古典审美与生活模式为样本,也不能以西方的美学与生活方式为模板,而应从当代文化发展和生活需求出发,以传统审美为主基调,融合域外优秀文化,创造属于当代中国、具有鲜明中华美学特征的文化艺术,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支撑。这无疑是一项关乎传统延续的重大系统工程,而要在“现代主义成功地编织出一种新语言”,并且能满足所有的变化性需要,“形成了这种现代社会的主流语言”之后实现传统的创新发展,更需要长时间的艰辛探索与努力。
赓续传统文脉应尊崇先进理念与科学方法。第一,要对古典美学遗产有正确的认知和态度。面对先人伟大的创造,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可厚今薄古。第二,从深刻把握传统文化内在本质与精神内蕴层面上维系历史根脉。虽然在今天保护与继承传统文化的意识不断提升,但仅仅以表面的符号呈现与消费来表达对传统的礼敬,或者以传统的简单移植和借用来实践对传统的继承是远远不够的。第三,要在主体人格层面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现代人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场的实践主体,其自身必须同时具备传统文化功底与现代文化修养,偏倚任何一方都难以实现真正的传统再生。当然,构建中国当代话语体系应摒弃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尊崇传统“和合”理念,倡导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增进世界审美文化的多样性,与西方审美共同构成和丰富人类文明的历史创造,达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
传统文化现代转场是一个复杂、系统和连续性的历史过程,涉及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文化转场存在于任何时代,尤其是文明转型时期往往出现大的转场;而同一文明形态下的文化变革,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小转场。每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势必以新的文化观念去观照传统文化,并获得新的发现。这种发现之所以产生,在于从新的时代诉求出发,进行全新的评价与阐释。我们要善于把握时代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当代是对传统的赓续、延展、超越,而不是隔绝、阻断、取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适应性和生命活力,更具有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中国古代从佛教文化发展出禅意的美学,唐代更显现出对其他民族文化开阔包容的胸怀,由此铸就了中华文化一个时代的辉煌。这种包容厚重的文化赋予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与根基,但这种底气与自信不是来自简单的挪用传统,而应当建立在对文化基因甄别与提炼的基础之上。继承传统应有符合当代发展需要的理念指引,在进行宏观鉴照的同时,不能停留于凌空蹈虚、华而不实的泛论,而要深入传统内部进行微观质析。古典审美中一系列传承有序的美学观念是中华文化基因的内核所在,经典则是承载这些基因的文化母本,而文人艺术家对于经典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人艺术家的创造不仅形成独特的精神审美意趣,而且深刻影响着造物设计,涵养和提升了中华造物的文化品位,使传统造物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华文化的世界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素以为绚、以形捉神的美学意趣是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理念也延伸融入古代造物之中,形成传统造物设计大朴不雕、简中求繁的美学精神,如园林设计中所遵循的“白本非色,其色自丰,池水无色,其色最丰”的美学原则,与现代主义的简约美学具有共通之处。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古典造物美学毕竟是农耕时代艺术实践的产物,其内在精神以及造物方式等,还是与当代造物之间存在诸多区别。在工业设计迈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既要以传统造物思想和造物经典涵养中国本土设计,还要有全球视野和科技意识,把握包括生态环保理念、智慧设计、信息设计以及纳米材料、3D打印技术等在内的新理念和新科技,全面提升富有东方审美意趣与时代特色的造物设计水平。
新时代开启了文化创造的新境界,但要形成完整的现代文化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还需假以时日的探索和经典序列的形成。任何时代的文化繁荣,都必须拥有一批能传之后世的文化经典,新时代需要创造新传统,推出新经典。真正的新经典必须是原创的。现代背景下新经典的形成,还需要运用最新的传播方式和手段,在实践创造过程中,进行持续的阐释与多元的传播,唯有在持续的创造和阐释中,才能建构属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形式、概念和范式,形成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体系,让中华美学辉耀寰宇、流芳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