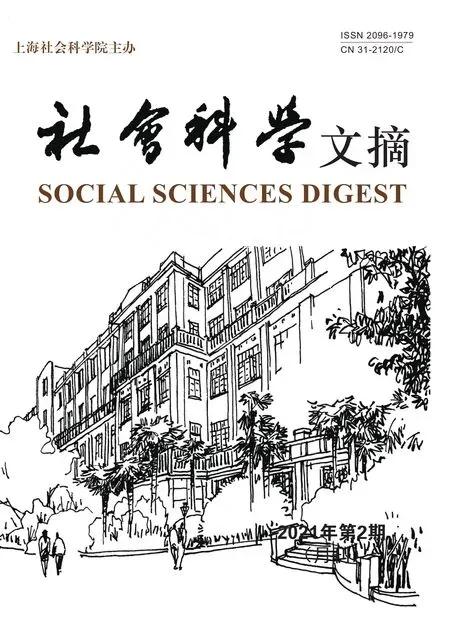中国小说的“中国性”管窥:以汪曾祺为例试驳“葛浩文之问”
2021-11-15欧阳灿灿
文/欧阳灿灿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批评中国当代小说受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偏好描写与情节无关的场景而显得过于冗长。他从结构严谨的角度来评价中国小说,认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小说沉迷于描写琐屑的生活场景,情节不够紧凑,因而小说有丧失文学性与审美性而变成“百科全书”之嫌。我们认为,葛浩文所说的与情节无关的生活细节描绘,源于中国文学的“文”“人”以及“世界”相融合的表现传统,体现的正是中国小说的“中国性”,亦即“中国特色”。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自称“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甚至因喜好描写从表面看来与故事情节“无关紧要”的地方风俗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我们将以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为例进行管窥式考察,以期回应葛浩文先生所质疑的问题。
文学能否独立于世界与人
汪曾祺在其文章《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推崇。他并没有明确解释现实主义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将两者并举,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重视真实、表现现实这一特点的察觉。但是,“现实主义”这一标签掩盖了汪曾祺所继承的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的诸多差别,对此我们尚需细心加以甄别。
西方文论的重要传统,是理性地处理、制作文学作品,重视作品形式本身的美。前苏格拉底时代,毕达哥拉斯就把美归因于事物各部分的对称与合适的比例,从事物的“数理形式”的角度阐释美。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情节的组合形式要有逻辑性,要具有整一美,这样才能客观真实地表现出对象超越个别的、真理性的意义,情节因其形式的整一美而获得内容上的概括性,凭此作品才得以独立于现实甚至获得超越于现实的价值。康德提出美具有无利害性的特点,试图使艺术摆脱社会现实的附庸地位,从艺术本身的形式要素如色彩、线条、音响来认识艺术的美。黑格尔强调真正的艺术品是内容与形式的密切结合,理念内容须呈现为感性的外在形状,形式本身的美感问题不容忽视。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流派,把形式提升至文学的本体,挖掘文学作品的形式规律,并希望以此来概括文学生成的原因。叙事学理论更是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完全来自其形式结构,文学是独立于社会人生的理性意识制作品。
西方文论家要求作品在形式上“合目的性”,根本原因是认为文学只是对自然或“理念世界”的摹仿,缺乏自明的独立性、自足性,因而作家要以其主观意志介入创作甚至作品,使作品的形式具有独特的美感,从而摆脱对模仿对象的依附。具体到与我们的论题相关的现实主义文学,不仅重视文学的形式与结构,还力图使文学在内容上成为现实生活的“理念”表征,具有类似真理一样的概括力与表现力,从而如科学一般具有认识论的价值。18世纪的启蒙文学把现实世界明确为理性主导的世界,并试图引导人们以理性精神,即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个世界。19世纪司汤达、巴尔扎克、哈代等诸多现实主义作家受到各种科学思潮的影响,更是致力于建构科学认识论为原型的文学世界。作者从广延的维度想象、创造虚构的文学世界,从科学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人物性格与情节结构是否清晰合理,正如人们从牛顿力学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去认识日常生活世界。在其后遵循并着力表现遗传学与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自然主义文学中,科学性取代审美性成为文学的第一性,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理性精神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现实主义文学以科学世界观与认识论为理论原型,目的是使文学获得独立的地位与价值。
汪曾祺在创作上受到归有光和好述“因文见道”之言的桐城派的影响,因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论可溯源至文道论。虽然在“道”是什么,文学作品是不是应该表现“修、齐、治、平”之道等问题上,汪曾祺与归有光及桐城派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对于“文”“道”之关系,也就是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首先,文道论表现了文论家对文学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从根本上推定了“文”对“道”的依附以及贯通关系,因此他们从不认为“文”能脱离现实生活而独立存在,也不认为“文”有独立于“道”的价值与意义。明代王祎在《文原》中言:“妙而不可见之谓道,形而可见之谓文。道非文,道无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与道非二物也。”“道”无“文”表现,则无法为人所明,“文”离开“道”也无以立。文学因其与真实世界相关联而具有价值。
其次,中国古代文论家承认“文”与“道”的合一性关系,他们并不着意探究“文”的独立性与区分性价值,他们所侧重思考的问题是文学作品如何抓住并表现心灵对“道”的感悟与体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意、事辞、肌理、华实、文情、文理、情采、辞理等范畴都是探究如何用真诚细腻的“心”去感受体验“道”,然后用适当的文辞表现出来。在中国古代文论家看来,文学要表达真实的事理情感,是毋庸置疑的先决条件,他们从不质疑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作者及世界的关联性,也从不怀疑作品在表达情感体验与社会生活经验方面的真实性,而是特别关注如何巧妙地使“文”“道”“心”融合为一。“道”“心”“文”之间具有同构同感的关系,“心”能够感知领会“道”,“文”也能表现“心”感知的“道”。这既是中国文论家思考问题的起点,也是彼此共享的不言自明的前提。
再次,是否偏好强调文学作品的形式从而突出其独立的地位与价值,还体现在汪曾祺与西方作家对小说情节结构的不同看法上。18世纪英国小说兴起之时,作家们致力于通过描写大量的物质生活细节以使这种表现普通人的体裁获得“现实感”,但他们逐渐认识到,作品的意义要通过建构因果序列的情节结构表现出来,因此,18世纪英国后期的小说情节结构逐渐走向了整一与紧凑。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更是重视表现有因有果、首尾呼应、脉络清晰的行为事件,以此构建统一完整、疏密有致的情节结构。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必须“挂”在情节上,指向通往结局的情节,为展示人物的行动服务,这些细节因指向人物行动的结局而表现出了某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小说中的日常生活描写由此克服了描写对象的个别性、或然性与庸常性,获得了高度的必然性与概括力。
这似乎让熟悉外国文学的汪曾祺感到不安。我们从其创作谈文集《晚翠文谈》中,也能感受到他以外国小说的要求审视自己“结构尤其随便”的小说时所隐约表现出来的焦虑。但他还是确信小说的意义来源于与现实生活、真情实感的关联,而非其整一的形式结构。
建构“真”与“美”的“日常生活美学”
在文学文本与世界、人的关系上,西方文论普遍认为应该对文本进行理性“制作”,追求文本的独立性价值,而中国传统文论强调三者的合一性、同构性与合作性关系,倡导文学作品要真实自然地表现现实。但是,如果在表现现实时完全遵循生活的逻辑与常态,又该如何使得琐碎平凡的生活具有美感?汪曾祺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处理“真”与“美”如何结合的问题时展现出了浓厚的“中国特色”。
汪曾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是唯一但也十分重要的一脉传统,即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但又不脱离现实,发掘并表现凡俗人生的“不凡”之处,建构日常生活的美学。
首先,凡俗生活中的人物可能社会地位卑微,没有刚毅果敢、斗志鲜明的意志,缺乏朝向目的、强有力的行动,但他们不乏在平凡生活中寻找、发现、表达情致与趣味的倾向与能力,从而使凡俗的生活充满温情与滋味。汪曾祺不仅多次表明了要在凡俗人生中寻找乐趣和情味的人生态度,更认为这种人生态度具有真实地面对现实却又不被现实打败的强大韧性,是中华民族普遍的品德。
其次,这样的生活是在直面现实生活的庸俗、痛苦甚至因死亡所带来的虚无的基础上,寻找发现人的智慧及“生”之乐趣,其人生态度依然是真诚地面对真实的人生。寻找理想生活与生命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全盘否定,更不是在直面现实生活的痛苦与虚无时彻底丧失活着的勇气与尊严,而是清醒地活着,踏实地活着,感受活着的力量与趣味,因此能够疗愈人心,彰显小人物存在的意义。《受戒》十分有代表性。这部小说完全剔除了宗教超越抽离于日常生活的维度,直面真实的人性需求,并且通过对各个人物的生活细节尤其是小英子一家吃穿住行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日常生活的美好。小说以宗教为起始,在日常生活与宗教的两极所构成的张力中,通过对各种生活细节、风俗人情的描写,悄悄地消融了宗教压抑欲望、远离日常生活的冷漠与疏离的刻板印象,尽情开掘绽放出了人性以及日常生活温暖美好的光辉。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一方面真切地表现了凡俗人生的经历及体验,对其不作“英雄主义”的拔高,小说情节的发展因此而遵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另一方面又试图大力发掘并表现日常生活中非功利性的诗意、趣味与温情,由此超越生活的琐屑、平庸甚至虚无。汪曾祺小说中的日常生活描写也因此有着独立于情节叙事的审美价值。
再次,如何能够发现“生”之乐趣与美好,主要凭借的是前文述及的能够感知“道”、“贴着”人物、与他人同情共感的“心”。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心中的温情,使得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既不回避现实,又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存在的乐趣与生活的意义。世俗生活中充满温情、能同情共感的“心”是汪曾祺日常生活美学的基础,它既非巴尔扎克小说中追求“典型性”的物质描写所体现出来的认识论价值,也非《包法利夫人》中展现物品之美却受控于商品逻辑的消费主义。紧贴现实生活的同时以审美的方式对待生活,我们认为汪曾祺的创作体现了真正的“日常生活的美学”。
葛浩文批评中国当代小说受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偏好描写与情节无关的场景而显得过于冗长,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使得叙述不够流畅。我们认为,西方文学自古希腊起以摹仿论为基本理论模型,在人物行为动作意志的冲突中提炼高度浓缩的意义,思考对人性的认识与探究,以严谨的结构形式传达具有普遍性的象征意义,体现文学超越生活的独立性价值。但中国古代文学重视作品、世界与人之间的同构性与合一性关系,强调作品以合宜的方式与分寸表现人与世界的融合性关系,在那表面看来无关紧要的、琐碎的细节描写中,其实包含着人的眼光、人的情感、人的体验,这使得作家在对凡俗生活的描写中建构起一种“日常生活的美学”。中国小说中许多在表面上看来与主要情节无甚关系的“琐碎细节”与“生活记录”蕴含着人的情感甚至是人情世故的“韵味”,充分体现了中国小说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美学追求与对“原生态生活”中人的理解。而葛浩文过于拘囿于西方小说的审美标准,未能很好地察觉到这一点。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这些特点实际上也是中国明清小说评点家津津乐道的小说妙处,当然也是小说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审美性与文学性。
作者与语言、读者的关系
与真实自然的审美内容相一致的是,汪曾祺作品中语言的平淡、自然与真实。他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要以日常化的语言真实、贴切、自然、自由地表达平凡的生活世界。他说,“写小说决不能做文章,所用的语言必须是活的,就像聊天说话一样”。这句话清楚而又巧妙地解释了中国古代文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要求与目的,即强调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贯通而非隔离,以及二者所用语言的贯通而非隔离。这句话也表明了强烈的“朋友式”读者意识,即把读者设定为彼此平等而又心意相通的朋友,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含蓄方式感动读者,而不是以充分有力的说理以及紧凑清晰的形式去说服、征服、启发读者。
中国传统文论家虽然认为文学形式技巧很重要,但又认为文学形式的最高境界是自然,形式应该消融于意蕴之中,其实也就是认为文学形式不具有完全独立于内容之外的价值,语言形式应与所表现内容合一。他们虽讲究形式与技巧,但是认为它们只是通达意蕴美的手段,在熟练掌握技巧之后,就要巧妙自然地运用技巧,自如地表达心灵世界。因此最好的文学作品浑然天成,没有斧凿的痕迹。宋代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诗语固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他还对比了“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与唐代诗人杜甫《水槛遣心》中的诗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认为两者同为写景,但是有造作与自然之别。前两句是叶梦得根据晚唐和宋初西昆派的诗歌风格自己拟作的,意在讽刺只重形式、矫揉造作的诗风。而杜诗虽似平常,实十分工巧自然,每一字都非虚设。春天的细雨落在水面上,小鱼儿常常会浮上来,如果是大雨,则不会有此情景。燕子的身体轻弱,非微风则不能借助风势,以轻盈的身姿飞在空中。此诗句对仗工整,流畅自然,而又入情入理,浑然天成。追求自然和谐之美的文学家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界的主流。
汪曾祺所说的“写小说决不能做文章”,其实就是叶梦得所言“不见刻削之痕”。语言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与表现力的日常语言中,“人”“道”“文”自如地结合在一起。它既真实地表现了世界,又意趣天成,浑然一体,巧妙自然地体现了“人”“世界”“文”的同构性与合作性关系,以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合一性。
汪曾祺强调小说语言“就像聊天说话一样”,体现了他“朋友式”而非“受启式”的读者意识。“世界”“人”与“文”彼此依存、彼此同构合一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作者与世界的关系上,还体现在读者与作者的关系中。作者要对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能力有足够的信任与尊重,不能居高临下地教育、告知与启示读者。汪曾祺相信,读者与作者一样有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与诗意的要求与能力,而文学创作的乐趣与意义就在于以含蓄、简练、生动、形象的语言,激发调动起读者的这种能力。因此文学创作不能过分直露地表达作者的观点与思想,而应该以含蓄自然平淡的状物摹情,达到与读者交流的目的。
综上所述,汪曾祺继承了着意于“世界”“人”与“文”彼此依存、彼此同构合一的关系的文学传统,而西方探索文学的独立性价值。葛浩文对中国小说大量描写与情节无甚关系的日常生活场景的质疑与不解,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文学具有无法被西方文学及其诗学审美惯例拘囿的“中国性”。此外,如何重新认识并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把它广泛有效地应用于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使它积极地介入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在这方面,汪曾祺建构“日常生活美学”的文学创作实践及创作论具有典型案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