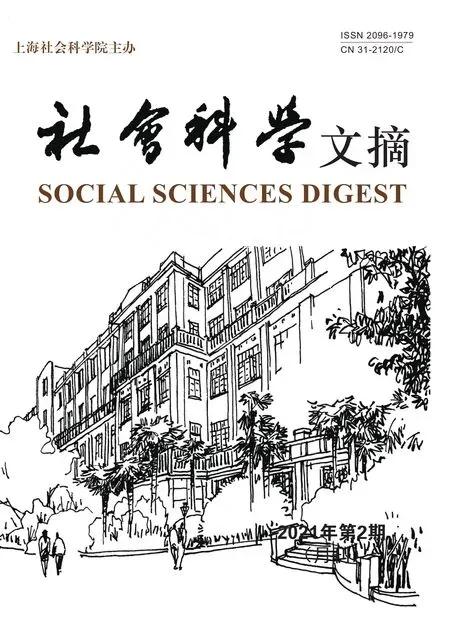地中海共同体:古代文明交流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2021-11-15李永斌
文/李永斌
近年来,海洋史研究和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就包括“海洋史研究的新拓展与新特征”;2019年5月,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两个学术热点的基础上,还存在不少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研究领域。在海洋史研究的新拓展中,地中海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但是对于古代地中海史,大多数人还了解不多,学术界也缺少相应的讨论。在文明交流互鉴的研究热潮中,学术界主要关注的还是丝绸之路东段的文明交流,对前丝绸之路时期亚欧大陆西段的文明交流关注不多,对地中海文明交流的研究则更少。本文尝试将地中海史研究与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作为古代文明交流研究新范式的“地中海共同体”的相关问题。
古代文明交流研究的范式转变
在经历了晚期青铜时代文明的普遍崩溃以后,公元前10世纪—前8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几个主要文明区域又逐渐恢复了生机,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也变得日益频繁。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的研究兴趣日增。通过对相关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研究大致经历了“比较研究—地中海共同体—网络理论”的范式转变。
(一)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第一种研究范式,也是一种传统的研究范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到希腊与近东地区神话和文学作品中的相似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线形文字B的破译,比较研究的领域被进一步拓宽。研究的集大成者是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德国籍古典学家瓦尔特·伯克特,他于1984年在《海德堡科学院会刊》发表了德文著作《希腊宗教与文学中的东方化时期》。他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诸多具体的文化事项进行了细致考证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领域中另一位成就卓著但也备受争议的学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马丁·伯纳尔。1987年,马丁·伯纳尔出版《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东方之根》第一卷,随后20年间,又相继出版了该书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尽管马丁·伯纳尔的激进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但也激发了学界对早期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比较研究的热情。
(二)地中海共同体
第二种研究范式可概括为“地中海共同体”。早在1949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就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这部名著中将16世纪后半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这一做法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地中海共同体”的观念。他的这种研究方法也逐渐为后来的古代史学者所接受和借鉴。明确提出“地中海共同体”(Mediterranean Koine)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学者斯波尔德和斯登伯格,他们在1993年的一篇论文《阿莫斯与赫西俄德:比较研究的几个方面》中提出了这个概念。美国布朗大学的德国籍学者科特·拉夫劳伯于1998年在芬兰举行的“亚述的遗产”学术研讨会上再次提出这个概念。尽管他们没有深入论述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都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认为古风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是一个文化上相互交汇的共同体。除了斯波尔德、斯登伯格和拉夫劳伯等少数几位学者,其他学者谈及这一问题时,通常是说“一个关于地中海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Mediterranean),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共同体是一个特定的实体存在,只不过是借用“共同体”这样一个术语来表达地中海地区从青铜时代开始就存在的密切联系和交往。
(三)网络理论
2003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家伊莱德·马尔金提出了“网络理论”这样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可以算是古代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研究的第三种研究范式。网络概念是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标志性概念,这一概念取代了“中心—边缘”分层结构的构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地域和人类空间的研究视角。基于罗斯托夫采夫和亨利·皮朗将地中海视为一个“商路交织而形成的网络”的观点,马尔金借鉴网络概念进一步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古代地中海在古风时代(约公元前8世纪—前5世纪)第一次形成了“地中海文明”,这个文明主要由各个独立的政治和商业共同体组成,并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散布。在这个由各个沿岸城市和海岛组成的海洋文明的整体网络中,希腊人、埃及人、埃特鲁里亚人和腓尼基人是主要的活跃者。在这些族群所形成的各种文明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文化边界,整个地中海区域形成了一个文明交互的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尔金没有明确使用“地中海共同体”这个概念,但是他所说的“文明交互的共同体”显然受到了相关学术潮流的影响。
当然,上述三种研究范式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分界线,本文所说的范式转变,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基本按研究成果出现的时间顺序,归纳出来三种有比较明确特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其中,比较研究当然是基础,也是基石。只有对基本的、具体的史料进行详细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才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宏观理论研究。但是,比较研究侧重于对具体材料的分析,目的在于提供证据,而材料本身并不能提供文明交流的绝对可靠的证据,并且比较研究还缺乏在较为宏观的历史背景下的解释框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交流中的变化和差异性。因此,比较研究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所提供的证据也未必准确。马尔金的“网络理论”实际上是“地中海共同体”观念的某种延伸,并在延伸的基础上有所反思,但是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超越“地中海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探讨的范畴。笔者认为,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地中海共同体”或许是可资借鉴的最佳理论范式。
不同历史学家笔下的“地中海共同体”
英国伦敦大学的佩里格林·霍登和牛津大学的尼古拉斯·珀塞尔于2000年出版了地中海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他们力图从微观生态的视角,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角度来重构地中海的形象。尽管霍登和珀塞尔强调地中海地区存在多种多样的微观生态,但也强调地中海的连通性。地中海复杂的海岸线和数不尽的岛屿、环环相扣的低地、能够频频通行的滩涂与河流,这些地理条件使得密切交流成为可能。他们强调不同微观生态之间的人们因便利的海上联系而发生互动,这样就抓住了历史“区域”因联系而形成的这一根本属性。不过,书中关于古风时代地中海的讨论并不多,仅仅是将这一时期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点顺便提及。因此,关于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文明交流互动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英国剑桥大学的大卫·阿布拉菲亚在他的名作《伟大的海》中将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00年的地中海称之为“五个地中海”中的“第二个地中海”。他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的地中海,出现了一些新的贸易网络,东方文化此时被传至西方,最远到了埃特鲁里亚和南西班牙。阿布拉菲亚对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描述,主要是基于腓尼基等族群的商贸活动而勾勒出一幅整体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主要的活跃者还包括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尽管阿布拉菲亚没有提供更多文明交流的细节证据,但是他道出了古风时代“地中海共同体”的核心,那就是基于商贸活动而进行的文明交流。这也为我们在“地中海共同体”视野下研究文明交流及互鉴提供了一个宏观层面的指南。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中海研究中心主任威廉·哈里斯主编的《重新思考地中海》一书中,也有几位学者探讨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和流通性。其中,阿兰·布莱松在《生态学及其他:地中海范式》一文中指出,《堕落之海》所讨论的关键主题——高水平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是由地中海独特的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布莱松认为,海运在成本和速度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尤其是在重型货物的运输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认识到地中海可能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连通空间。这一特点适用于地中海的每一个海岸,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的半岛,因为它们的海岸线特别长。应当补充的是,地中海中的岛屿也为潜在的连通性提供了额外的补充。在爱琴海空间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因为这里存在着一系列较小的岛屿,并组成了群岛,这些群岛内部的交流为整个地中海区域内的连通空间提供了样本。布莱松指出,地中海地区的流通性大大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公元前1000年,地中海地区财富的集中程度以及思想文化所达到的水平和多样化形式,对于地球上任何其他地区的人群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
尽管《堕落之海》《伟大的海》和《重新思考地中海》这几部著作并没有直接论及“地中海共同体”,但讨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致的,即如何处理地中海世界的碎片化与统一性,实际上也就是在讨论“地中海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单元的合法性问题。当然,对这个核心问题的回答是不相一致的,这也反映了地中海史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传统。
第一种传统是研究“在地中海的历史”,始自罗斯托夫采夫。他强调人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强调地中海范围内的宏观互动,将地中海视为商路交织而形成的网络,而这一网络中的商贸活动非常显著地受到了希腊殖民活动的影响。罗斯托夫采夫关于地中海是一个统一体的观点得到了亨利·皮朗和阿布拉菲亚的继承。后来的“地中海共同体”概念和马尔金的网络理论,实际上是这一传统的进一步延续。这种传统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文明交流互动的主体是人以及人的活动。
第二种传统来自布罗代尔。布罗代尔虽然也将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但是更强调地中海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力图在整合差异性的基础上来探寻地中海的统一性。这种传统在《堕落之海》中得到了继承,《堕落之海》的研究方法的典型特征是从地中海的具体场景出发,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微观生态的形成,进而关注因“连通性”而形成的地中海历史的整体性。《重新思考地中海》对于地中海研究的“重新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对布罗代尔模式的“重新思考”,以及对这些“重新思考”的再思考。但是,这些重新思考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布罗代尔开创的“属于地中海的历史”的研究范式。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从公元前8世纪前后地中海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来看,完全可以用“地中海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来研究这一时期文明交流互动的情况。尽管很多学者没有直接论及这个概念,但他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与“地中海共同体”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地中海的整体性问题。在论及“地中海共同体”的学者中,有人认为地中海是一个“政治和贸易共同体”,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尽管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归纳出“地中海共同体”的几个一般特点:第一,基于商贸活动而进行的文明交流;第二,因联系而形成的“区域”;第三,统一性与独特性紧密联系;第四,独特的生态环境所决定的高水平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这几个一般性的特点中,最突出也是最基本的特征是基于商贸活动而进行的文明交流。
作为学术研究范式的“地中海共同体”
我们在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文明交流之时,可以将“地中海共同体”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但是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地中海共同体”这一概念不仅适用公元前8世纪这一时期,也适用于后来更长时段、更大空间范围内地中海的文明交流与互动。虽然最初提出“地中海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学者们所指称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8世纪左右,但是地中海世界的商贸和文明交流却一直延续,并且随着航海技术的改进和周边一些国家实力的增强而进一步加强。因此,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应该视为地中海共同体的形成阶段。随着地中海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中海共同体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也有所变化,甚至可以说一直在变化。直接论及“地中海共同体”的学者们所关注的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地中海共同体的文明交流,主要还集中在东部地中海。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文明交流互动的范围就真正扩大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甚至超出了地中海的范围,包括西亚地区和不列颠地区都受到地中海地区商贸活动的影响。罗马帝国时期的地中海共同体,不仅是文明交流的共同体,更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的共同体。罗马帝国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地中海世界被成功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过程,而这种以帝国为组织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又为地中海世界经济、社会、商贸、文化等多方面的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安全保障。
第二,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地中海沿岸大多数地区仍以本地农业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形式,商贸活动和文明交流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古代希腊的工商业和航海业比较发达,但本地农业仍然是主要的社会与经济基础。希腊城邦的社会与政治力量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古代埃及社会,农业的地位和重要性也远远高于商业活动。由于尼罗河三角洲是适于耕作的宝地,只要尼罗河保持正常的水位,整个国家的供给就不成问题。埃及人虽然很早就与周边的民族有交往,但这种交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原料和一些贵重物品,如金属、宝石、油料、酒料等。早期阶段的地中海共同体主要是一种文明交流意义上的共同体,并没有改变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也没有改变牵涉其中的各个文明所独具的基本特征。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希腊殖民运动,已经开始有了政治组织朝向更紧密的共同体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缓慢发展,最终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顶峰。
第三,就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来说,各文明之间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仍然远远大于共性,局部的交流远远多于整体性的交流。“共同体”是一个学术名词,表达的是某些方面的联系和共性,这些联系和共性与网络理论所探讨的联系和共性有着同样的对象。但是,这一时期的地中海共同体,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整体。正如前文所述,地中海范围内存在着诸多贸易网络,这些贸易网络共同构成了以商贸和文明交流为基本特征的地中海共同体。在这些贸易网络中,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各有不同,有的以希腊为中心,有的以埃及为中心,有的是以希腊—埃及为主要交流路线,有的是以希腊—小亚细亚为主要交流路线。从整体上来说,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仍然处在早期阶段,更多的还是局部的、相对短途的交流,大范围的长途贸易和文明交流主要是由这些局部的交流衔接和交织而成的,而未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因此,以“地中海共同体”为范式的古代文明交流研究,还是要强化对各个文明区域的具体研究,才能在此基础上对文明交流作出更具体、更细致的探讨。本文即是在这方面的初步尝试,期待学者们在相关问题上有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