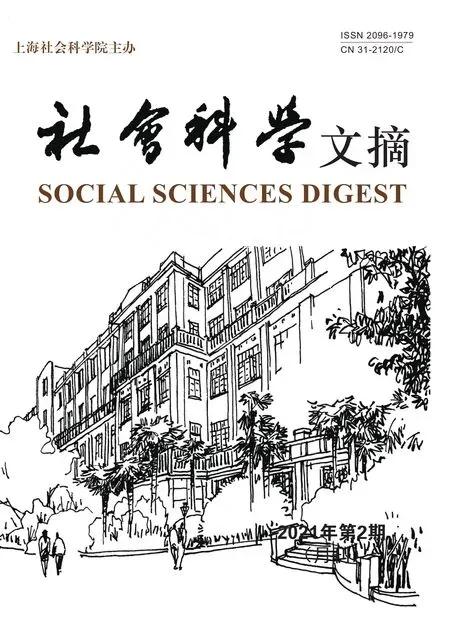从正统异端之辨看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探究
——评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2021-11-15于涛
文/于涛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在现代性视角下对中西方文化展开比较研究又一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将关注点聚焦于对中国崛起的文化因素的探讨,其中以反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东方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现代性研究尤为突出,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诠释与解读,一时间众说纷纭,争论不断,在学术界重新掀起了一轮文化研究的“韦伯热”。韦伯所提出的“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独树一帜,特别是他对近代西方文明兴起和东方文明衰落的解释为20世纪以来东西方现代化发展与交流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也从一个方面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韦伯命题”与现代新儒家的回应
马克斯·韦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与中国传统社会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两本著作中。韦伯将原因归结为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派天职观念等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内在支撑,由此激发人们积极投身于资本主义发展浪潮之中,后世学术界将此归纳为“韦伯命题”。从韦伯思想的整体来看,“韦伯命题”具有“新教伦理产生现代性”和“儒教文化阻碍现代性”的双重含义。他们更是进一步将“韦伯命题”细化为两个子命题:“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韦伯命题I”;“在经济方面,中国有大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而在文化论方面,儒教文化缺乏孕育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生。”——“韦伯命题Ⅱ”。这一理论归纳将韦伯关于东西方不同文明的现代化发展进路观念清晰地展现出来。然而,受到当年资料局限等因素的制约,“韦伯命题”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产生了一些偏差与谬误,引起了后世学术界的批评与争论。
对韦伯的批驳以新儒家的牟宗三和杜维明最具代表性。牟宗三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将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分为“尽理之精神”的综合与分解:中国文化是以心智、道德、理性等由内而外的综合;相反,西方文化则突出“知性形态”,其外在表现就是分解为概念的心灵。进而他又提出“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两个概念来归纳中西方哲学的理性观。在牟宗三看来,中国儒学注重发挥个人德行的内圣之功,形成仁智合一的文化,以仁统智的社会政治体系,即理性之运用表现;西方文化则将个人的德性纳入到非道德理性之中,由此建立起西方的国家制度、法律体系、逻辑和科学等,即理性之架构表现。为了使中国文化由“综合的尽理之精神”转化出“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由“理性之运用表现”转化出“理性之架构表现”,从儒学的内圣中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牟宗三提出“道德理性自我坎陷”来解决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即道德理性只有通过自我否定的“曲通”办法才能成为观解理性(理论理性),从而成就民主与科学。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就是使仁让开一步,使智在仁智合一的文化模型中暂时脱离仁,成为“纯粹的知性”,进而开出智之独立系统。
杜维明提出的多元现代性思想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具有更积极的态度。首先,杜维明承认新教伦理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上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必要条件,它只是一个背景或者历史的偶然,二者之间缺乏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换言之,“韦伯命题”并不是历史规律,它不具备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导向性作用。其次,对于“儒教文化不能生发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杜维明指出韦伯因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产生了误解和歧见,用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文化传统,这是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思维。在此基础上,杜维明利用“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来论证儒家伦理观念在现代工商管理和社会的道德规范等方面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竞争模式”的“和谐模式”,也印证了反“帕森斯化韦伯”诠释的合理性。由此不难发现,杜维明在反思“韦伯命题”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模式,打造一条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现代化之路,以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共融共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与异端之辨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以正统和异端来划分儒教(儒家)和道教,以此凸显儒教代表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他借用“卡里斯马”来概括中国政治的基本体系,即君主的神圣使命是统治国家的基础,而支撑这一神圣使命的就是儒家思想,包括道教、佛教在内的其他思想则均属于异端。儒家思想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都具有统治性,而道教更接近于一种体现在民间迷信巫术层面的神秘主义宗教。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上的终极寄托,一直以来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力完全不逊于任何一种西方的宗教伦理。韦伯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政治文化正统思想的看法过于片面,没有把握住中国文化的实质,势必对其研究结论造成误导和偏差。
自汉武帝将儒家思想树立为中国正统社会政治价值观开始,到五四运动之前,儒家思想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倡导,其间虽有一些调整,但其作为统治旗号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被动摇过。而其他先秦各家的思想大部分时间被置于异端地位,受到官方的迫害和打压。韦伯认为:“即使在城邦被驯化,从而在太平的世界帝国里消除了纯粹的政治障碍以后,那些并存的哲学流派中,也没有一个取得了儒教在中国的那种独尊的地位。因为,这无异于接受一种唯一正确的国家哲学。”这体现出韦伯将儒家思想的正统性上升到国家哲学的高度;然而同时他也将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的宗教文化完全置于儒家知识分子阶层的统治之下,一切政治文化都是在“等级制”儒家哲学以及士大夫阶层的道德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甚至帝王也无法脱离。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韦伯已经在政治实践维度上把摆脱了巫术束缚的道教归入了去除了神秘主义色彩的儒教之中,将儒教的正统性推向了极致,儒家“孝悌”的等级伦理成为决定正统的核心因素,而以异端来标记反对者便成为了正统在受到利益威胁时自我保护的一种政治手段。可见,韦伯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完全认同了中国古代的官方主张,将中国的政治文化归纳为儒家思想,忽视了对其他各家思想乃至民间文化传统的研究与分析,这导致他对中国政治文化作出了片面的判断,引起了后世的众多批评。
我们可以将韦伯关于正统性问题的论述归纳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传统政治统治思想等同于封建官方确立的“儒家思想”吗?答案是否定的。汉代的董仲舒以阴阳之学起家,借儒家的礼乐之名,行法家的威德之权,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的思想统一方针。这为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理论贴上了“儒”的标签,但这个“儒”并非是孔孟创立的正统儒学,而是“兼儒墨,合名法”“博采诸家,自成一体”(《汉书·董仲舒传》)的产物——“儒术”。即使汉代的官方史书也不认同董仲舒提出的“儒术”是正统儒学。有学者认为:从韩非建立的以法家思想为主的封建理论发展为董仲舒提出的以儒学面貌出现的封建理论,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千方百计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主的专制地位,以保护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理论。因此,区别主要是形式上的,董仲舒的理论实际上是在韩非理论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件儒学的外衣。例如,作为“儒术”纲常伦理核心的“三纲”,其含义绝非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各司其礼、各持其德的自律标准,而是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的忠君尊长的维护专制等级的治国之道。需要指出的是,“术”不等同于“学”,“术”是手段,“学”是思想,二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汉宣帝刘询也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其后经过宋明理学的再改造和明清两代帝王数百年的推崇,早已经演变为正统的“儒学”得以广泛传播开来,学术界将这一现象归纳为“外儒内法”,以此来揭示其欺骗与虚伪的“术”性。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独尊儒术”之说法不能全面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全貌,秉持“独尊儒术”的观念很容易使如韦伯一样的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陷入正统与异端对立的理论陷阱中,造成理论的偏差与谬误。
相比于同时代其他学者,韦伯虽然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几乎涵盖了从国家到基层的各个层面。但是,这一考察仍然只是对每一个外在社会现象的分析,且多为对官方文献的解读,而并没有将这些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性地综合把握,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内在深层次的思想观念的研究明显不到位,仅仅用儒教和道教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更是远远不够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其结论(“韦伯命题Ⅱ”)更多带有理论假设的味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研究没有价值,作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开创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范式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笔者只是想说明,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韦伯等西方学者的分析性研究方法是不充分的,不能深入中国社会且不秉持整体性的研究范式,就很难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有全面的认知。
整体性:中国文化的探究范式
整体性(Holistic)或整体论(Holism)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产生于20世纪初期,是由南非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扬·斯穆茨(J.C.Smuts)在1926年出版的《整体论与进化》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斯穆茨认为,整体是进化发展的方向与精神。整体并不机械地等同于组成它的各要素与属性的总和,事物的整体性是由组成它的各要素(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整体性研究范式,或称整体性原则,要求研究者先把研究对象看作由各个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再从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中找出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及属性规律,从而实现对研究对象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具体到社会科学领域,整体性研究范式就是要对社会事物从最宏观的方面去认识把握,而不是从该事物的某一点或某一局部凭主观概念去判断、推理,也不是将事物套上一种既定的理论模型,从而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万事一律”的偏狭认识。
中国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因此,在研究中要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而非选取其中一家之言或某一方面来展现整体特征,否则无法全面透彻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整体性研究范式没有被大多数研究者所秉持,特别是很多国外学者受到语言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对中国的研究很容易陷入片面化的窠臼中。研究中国文化需要有对中国文化整体性状的深刻认识,也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理论素质和修养。只有这样,其研究成果才能体现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清晰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精髓,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演进的历史脉络。更为重要的是,整体性范式应该最广泛地落实在对中国具体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倡导培养研究者从整体出发去看待文化现象的思维习惯,对文化的宏观理论有一定的思考和认识,增强理论素质和思维能力,以实现在研究具体文化问题时,时刻保持宏观性思维的广阔学术视野,以及立足整体去认识微观现象要素的研究习惯。这样,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某些具体现象时,就会自觉地将研究对象视为其所属中国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觉地用宏观视野去归纳整合这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将这种整体研究观念渗透在每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中,使我们对具体文化现象的解读映射出中国文化整体的内在精神和基本内涵,从而使具体研究成为整体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总之,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必须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范式,以宏观联系微观,将各种特殊现象加以整合,准确地把握具体的文化现象,从中找出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清晰地认识中国文化,将依旧在我们身上并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性格和行为的那些几千年的文化基因解读出来,进而构建出既符合逻辑又具有指导意义的文化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须坚定自信
近些年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没有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更多地是以一种迎合西方的姿态,大谈特谈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优长,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对民族文化的不自信。究其根源,莫过于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百年苦难所造成的文化自卑感。这种心理影响了人们更加清晰和完整地认识中华文化的精髓、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以及中国文化在稳定国家和民族延续的大方向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殊不知,科技先进与否不等于文化是否强大,文化更多地是在维系国家、延续民族等方面体现其价值。可以说,没有中国文化的强大包容性、统合性,我们不可能维持国家的长久统一与稳定发展,并在历次外劫中战胜敌人、生存下来。
纵观世界历史,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幸存者,正是依靠其背后强大的文化力量来支撑。几千年来,中国以巨大的文化优势将众多的民族融合进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依靠武力征服而是通过文化感召使其主动归化。放眼现今,在吸收中国文化的东亚国家中,文化传统无一例外地都被保留了下来,即使在科技发达、西化严重的日本也是如此。中国文化这种强大的包容性正是其整体性的外在体现;换言之,包容和合正是我们重视整体的一种外在表现方式。中华民族是包含56个民族的现实整体,中国文化也是一个汇集五千年历史传承的精神整体。没有包容的整体性乃是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恰恰是中华文明所唾弃与不齿的;相反,达济天下、怀柔四方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追求,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处世哲学,以德报怨、宽宏大量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
因此,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必须坚定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只有在研究中坚持文化自信的基本心态,运用整体性的研究范式,才能对中国文化有全面清晰的认识,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实现立足自身、放眼世界的目标,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研究进路,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