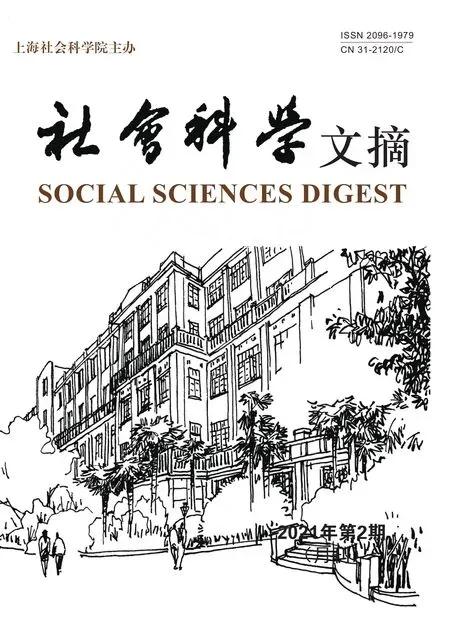农地政策调整的民情基础
2021-11-15狄金华
文/狄金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中国农地的整体性制度变革虽未发生,但围绕具体的经营制度却发生了诸多调整。要把握这些政策调整的内在机理,既要理解农地制度在中国体制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洞悉国家在农地制度调整中的实践机制与治理逻辑;同时也必须理解不同时期民情的变化,要把握具体的民情如何影响农地政策,并与体制性的力量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农地制度的调整。
民情:理解农地制度变迁的视角
体制与民情、规制与顺从构成了围绕社会秩序达成的一切治理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作为理想状态,体制与民情可以处在一种良性的互动结构之中,然而在实践中,体制总是试图对民情进行引导和规制,而民情却不总是按着体制所规训的方式来实践;当民情与体制不匹配,而民情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来“抵制”体制时,体制要么陷入“空转”的困境,要么进行自我调整以顺应民情。
体制与民情间关系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会挤压体制与民情之间的互融空间;同时也表现在民情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样态。民情自身的复杂性在于:在横向上表现为其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具有不同的秉性;在纵向上表现为时势变动而致使它随之发生改变。
在中国的语境中来理解农地政策的民情时,首先需要洞悉农地对于农户的意义:一方面,农地既是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政府赋予他们的一种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作为一种劳动过程,农户总有劳苦规避的动机。追求劳苦规避与农地收入的最大化构成了围绕农地民情中最为关键且又相互矛盾的部分,二者的此消彼长则构成民情变动的核心,民情的结构往往因不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如非农就业机会的多寡等)的差异及其变化而发生改变,进而形塑出一个变动的民情谱系。
农地制度实践的体制性空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对农村的整体性政策仍是“以粮为纲”。在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压力下,地方政府必须保证粮食产量,而它们又不得不面对集体化经营方式效率低下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能进行的“制度创新”只能是在不改变土地生产经营方式的前提下,改变组织内部的结算方式,以形成对农户的激励。真正促成地方政府在农地经营方式上做出调整的则是自然灾害。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作为最早实施“包产到户”的区域,于1978年春推行这一经营制度调整的诱因即是当地遇到了大旱。换言之,正是体制性压力加大,促成了地方政府释放了民情实践的空间。
因为工业化建设的过度投资、政府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减轻部分地区农村税收负担等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积累率大幅度下降,政府财政赤字增大,由此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的“内源性的经济危机”。作为危机应对,中央政府在体制层面做出调整来顺应“包产”的民情,“开口子”允许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
虽然农地制度的改革具有“甩包袱”的功利主义诉求,但因为农地制度及其治理本身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因此无论是在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的延承上,还是在整体耕地规模的稳定上,中央政府都设置了底线与红线,一旦农地经营产生负外部效应(如诱发干群冲突),中央政府就会进行干预。正是顾及其外部性,所以政府一方面强调要将农地经营权交给农户,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让分发到农户手中的农地产出更有效率。因此,在农地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个体的保障与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自治与官治就形成了一对相互影响的逻辑,彼此之间的空间也影响着农地制度实践探索的路径,以及民情得以实践的空间。
“让土地承包起来”:“单干”诉求与农地分配
包产到户因为将生产经营单位重新调回到了中国传统的家户层面,加之其采取定额租的合约体系,因而激发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与农民平均占有农地诉求相对应,社区内农地因为水利、交通、地理等因素造成农地产出不均。为了实现农民的平均占有,包产到户的制度导致农地在各家庭之中的占有呈现细碎化特点。
对于当时的农民而言,土地均分虽然会对水利、耕作带来一定的冲击,并使劳苦程度有所增加,但它却满足了农户对于公平占有的诉求。换句话讲,在分田到户之初,农户在农地分配之中,对公平占有的偏好是胜于对劳苦规避的偏好。形塑这种民情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包产到户政策实施之初,由于各种非农就业机会缺乏,导致农户只能通过无限劳动力的投入来保障家庭所占有的土地收益最大化。
包产到户政策实施之初,农地分配所面临的民情基础表现为,以村庄共同体的社区成员为边界,以“家户”这一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单位来分配土地和组织生产,其中土地分配中的公平观胜于耕作的便利观,农户对土地收益的追求重于对劳苦的规避,且这种民情结构在各地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上述民情特征的形成正是以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缺乏、农户异质性不高为前提的,而一旦这个前提发生变化,民情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同时亦引起农地制度的调整。
“让地权模式丰富起来”:农户差异化需求与地权多样化实践
伴随着包产到户制度实施时间的延长,这一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效应和边际收益逐渐下降,而外部结构的变化也使得民情本身发生了改变。
在政策层面,成员的变动导致附着在成员权上的农地亦随之变动,由此要求通过农地的动态调整来应对社区成员的动态变动,在此过程中,农地调整与分割导致细碎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生不增、死不减”的框架之下,政策将社区成员设定为分田初期的社区成员,并允许其在家庭内部传递,则令人口增长等原因使家庭间的农地占有产生巨大分化。另外,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部分地区的农民有了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这一部分农户要求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民情的发酵与演变同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共同构成了体制力量改变农地政策的决心。
1987年,中共中央提出在农村建立改革试验区,其中围绕农地制度建设,中央层面建立了三种地权模式的探索,即贵州湄潭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模式,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有偿承包使用,切断了人口增长与土地再分配之间的关系;山东平度“两田制”模式,在农地整治和田块连片的基础之上区分出按人口均分的“口粮地”和按竞争招标承包经营的“责任田”,并配套进行地力管理、农业服务等制度探索;苏南、北京顺义和广东南海以土地规模经营为主要特征,试图“利用大量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的现实条件,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实现土地相对集中和规模经营”。这种多样化的地权探索背后是因为各地因其区位、非农发展及各种土俗不同而形成了农户对农地的不同诉求。
20世纪90年代,当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自主地进行农地政策调整之时,“两田制”被广泛采纳;同时,“两田制”的制度设计在被其他地方学习时,其他地方也依据自身的民情特征进行了一定的“改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自然是地方社会基于地区性的民情特征进行的调整。然而由于“两田制”制度实际上是将农地调整的控制权分配给村集体,而其他地区在引入“两田制”时既没有平度配套的对村集体的制度监管,又没有相应的社会结构对村干部的谋利行为进行钳制。这种制度实践自然引发民众的反抗,由此而引起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地方治理的冲突化。考虑到“两田制”因为放权给村集体而造成代理人成本增加,中央政府出面压缩了“两田制”的制度空间,同时将有助于限制村集体自由裁量权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地制度纳入到中央主推的地权模式之中。
纵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农地政策实践,其本质上是分化的民情结构诱发了多种样态的地权模式。当这些地区模式“自由”地进行扩散时,由于不同地区的民情结构存在差异,具有“选择权”的利益主体则可能选择合乎其自身群体利益而悖于民情的地权模式。当多样化地权模式“自由”地扩散导致基层社会矛盾冲突时,体制性力量便再次进入其中,“干预”地方社会对地权模式的选择。
“让土地流动起来”:体制与民情双重作用下的土地流转
随着湄潭模式上升为全国主导性的地权模式,该模式背后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农地资源的诉求也随之在全国推开。但与体制设计及体制的治理诉求不相匹配的是,起初农民并没有强烈的农地流转诉求。这一格局的形成既与长期以来形成的恋土情结相关,同时也与农户从土地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关。
这种农地流转民情发生改变首先是发生在1998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已经建立的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因无法向外出口而使得生产过剩问题首次在中国出现。作为应对,“当时中央的做法是推出农业产业化,为已经处于过剩阶段的工业资本找到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的机会”。当城市的工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它必然需要土地进行流转与集中,这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农地流转的诉求。第二波农地流转的诉求则始于21世纪之初,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以及政府对于农业生产的补贴加大,农业生产的获利性增加,加之农业机械化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业生产的劳苦程度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之下,小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及农业公司等不同主体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都有所高涨,而此时仍然延续自包产到户以来的细碎化地权结构,就越来越不能满足他们的诉求,改变这种细碎化的地权样态就成为当下农村民情的核心。
农户对因地块分割、细碎化所导致的耕作不便(尤其是因为地块分割而限制机械化使用)形成普遍不满,这也形成了此一时期农户针对农地经营的民情特征。这种民情在地区之间亦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对于平原地区而言,丘陵地区因地形地貌及水资源分布而在包产到户初期,农地分级级别更多,故农地的细碎化、“插花”程度更高,当前进行按户连片和按片耕种的诉求更高,进行相应实践创新的动力也越强。
体制治理与民情回应:农地政策调整中体制与民情的互动
(一)体制的压力与民情的诉求
农业与农地政策所具有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体制对于其民情考量的特殊性。中国农地生产经营的基本特点是:第一产业的收益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第一产业内部粮食作物的收益又弱于经济作物。因此,无论是农民还是村集体或是地方政府,都有足够的动力与热情将农地非农化或是从粮食作物转向其他高附加值的作物;但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它却不得不考虑整体层面的粮食安全问题。刘守英、卡特和姚洋的研究业已指出,对于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流转限制最多的地区主要是国家粮食采购依赖的重点粮区,而在非主要粮食产区,国家对农民的自发选择则予以了高度的弹性空间。
整体性的体制性压力并不总是以牺牲局部的民情为代价;相反,它亦可能成为释放局部民情的契机。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的启动虽然最终是体制对民情作出了让步,赋予了民情得以实践的空间,但这一体制变革的结构背景恰恰是体制治理所面临的整体危机需要释放农村的民情来予以化解。换言之,当民情与体制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且这种张力逐渐累积诱发成体制治理的困境时,它则需要释放民情来化解这一困境。
(二)体制内部的张力与民情实践的空间
中央在农地政策的设计中总是试图限定代理人的自由裁量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被中央“吸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此一时期民情的主导是希望地权结构能契合农民对于农地灵活、多样化的占有,但当这种灵活占有的处置权交由村集体时,村集体的自利行为反而伤及了农户的利益,并诱发了农村社会的冲突,构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种农地政策实施的“非预期后果”使得农村社会的主导民情从“配置农地资源求发展”转向“配置农地求稳定”,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由于有助于约束村集体的自利行为受到中央政府的青睐,该政策的推广与“主流化”背后显然是基层治理的民情影响了中央,并主导了农地政策的走向,但这一政策与农民农地配置的诉求相比却相去甚远,农民通过农地配置谋求发展的民情被掩盖和搁置。
除此之外,中央与地方的张力也可能使得地方得到“授权”以释放民意实践的空间。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之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尤其是这一任务需要释放民情来完成时,地方政府则可能在体制内进行释放,并引导政策以顺应民情的方式来发展。只是这种地方政府的努力有时候是显性的,有时候则是隐性的。
(三)民情的变动与体制性的回应
民情的生成机制决定了它与特定自然、社会条件及时势特征是相关联的,因此民情并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复数。围绕农地的民情,在平原农村与丘陵山地农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与兼业化程度高的农村,农户在农地诉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用一种统一性的农地政策很难回应这种多样化的诉求。同样,由于土地分配所依凭的社区成员的权利既源自于法律的授权也源自于社区情理的认同,因此不同地区对于“成员权”的界定亦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反过来也要求中央政府在农地政策的设定上应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以给予地方政府结合具体民情特征进行选择执行的空间。
民情亦会随着时势的变动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在包产到户之初,围绕农地的诉求表现为农户对于公平性追求为主,而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比重的下降,农户对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便利化诉求逐渐上升,成为民情的主导。民情的变动意味着虽然政策最初与民情相匹配,但随着时势的发展,其与民情则可能出现张力,此时政策必须随着民情结构的变动而变动。
小结
本文以农地政策的变动为线索,分析了包产到户之初,均分土地所带来的规模不经济及相互性困境,发现民情中存在两股反向的力量——通过尽可能公平地占有土地而获得家庭受益的最大化以及因农地平均分配导致细碎化后劳苦程度增加而无法有效进行劳苦规避。在包产到户之初,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户对农地收益的追求胜于劳苦规避,这导致土地的细碎化;随着非农就业机会增长及农业机械化运用,农户对劳苦规避的诉求胜于对经济收益的诉求,进而导致对土地连片的政策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