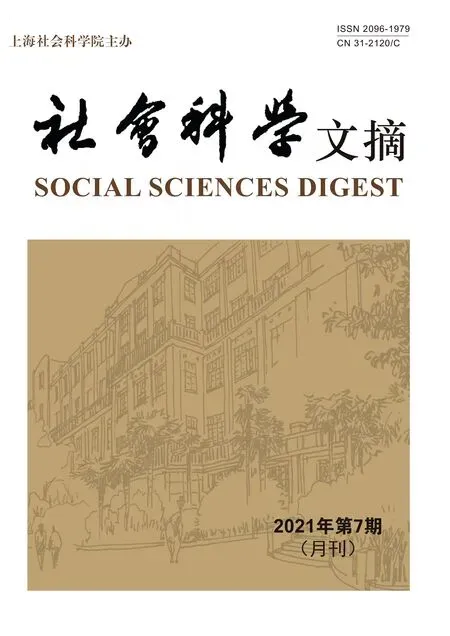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
——“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2021-11-15魏旭
文/魏旭
从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张灏先生称这一时期为转型时代,这是中国思想文化承先启后的关键时期,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和内容有了突破性巨变,逐步产生了栖身其中的新的社群媒体——现代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总体上是指靠某种专业知识谋生、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在萨义德看来,重要的是“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这意味着现代知识分子批评政治,却未必以政治为业。不过,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倒是很大程度上以政治为业,如果说他们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那么转型时代呈现的正是知识分子身上学术与政治分离的转型过程。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而相当一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成为职业革命家。陈独秀是在转型时代崭露头角的,从早年大搞革命活动到突然“不谈政治”,再到五四运动后发表《谈政治》,他与政治的纠葛一直备受瞩目。陈独秀对政治的态度变化与知识分子的时代转型有着时间上的耦合,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这个转型的复杂过程。
悬而未决的张力: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学术
中国古代有读书人群体,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形成的“士”阶层开始,尔后数千年一直在历史演进中发挥着主持与领导作用。他们不像现代知识分子那样受到知识专业化影响,道德和知识训练通常是一些“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传统读书人兼得政治和学术,转型时代则要求知识分子“仕学分途”。随着清末废科举,读书人以政治为业的制度通道被正式割断,转而栖身于各类依靠专业知识的社会职业,成为游离于政府之外的自由人。然而,读书人肩负的道义责任还在,转型时代的政治也需要他们来过问。这样,清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便不是简单的态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面临的时代命题。
转型时代要求知识分子褪去政治的一面,但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反而成为许多读书人化身为政治行动主义者的动力。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视拯救国家为己任,这是自古以来读书人肩负的道义和责任所激发的,但又不可避免受到自身转型的大势束缚。学术与政治间的张力终究是要解决的,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何时二者能真正切割开来?何时这种徘徊的状况变得不可能了?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差异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历史舞台上出现了相当一批多的职业革命家,随后的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似乎被边缘化了。
之所以认为五四运动前后是知识分子转型的重要时点,还在于五四运动本就有着从学术转向政治的一面。胡适曾称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傅斯年亦认为,“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酝酿些时,中国或又有一种平民的运动”。陈独秀更是清楚表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是一件事”。如果把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看成是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从事的两类活动的话,那么在五四运动之后,从事学术和政治在知识分子身上变得难以兼得。这一变化在陈独秀身上颇为直观,作为曾影响一代人的著名知识分子,追求学术和政治在他身上演绎着双重变奏。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常宣称“不谈政治”,五四运动后又迅速成为职业革命家。他有关政治的谈与不谈,与知识分子的时代转型密切相关。
革命者的政治疏离:陈独秀的“不谈政治”
陈独秀踏上政治之路很早,早在20世纪初就成为务实的革命派。他因曾在杭州求是学院发表反清演说遭到当局通缉,可以说这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开始”。1902年,在日留学时,他加入青年团体“励志会”,当年又在安庆与柏文蔚等人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开辟“藏书楼”展出革命书刊,还曾被清廷列为首要叛乱分子追捕。1904年,陈独秀参加了杨笃生等人组织的上海暗杀团,后来他回忆,当时“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后来对吴樾预谋暗杀清廷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革命事件也有参与。1905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岳王会”并担任会长,该会宗旨就是推翻清王朝。民国建立后他又积极为革命奔走,先是应孙毓筠之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后又协助柏文蔚治皖,并在二次革命中追随柏文蔚积极反袁,直至反袁失败后被迫流亡。
陈独秀的革命活动是隐藏在学人身份下的。他职业相当多样。他当过报人:1904年应邀担任《国民日日报》编辑,并在1904年到1905年间创办《安徽俗话报》,后又成为《甲寅》杂志的撰稿人。他当过教员:1905年担任安徽公学的国文教员,1909年又到杭州任职浙江陆军小学国文史地教员,1912年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自任教务主任,常就教育发表演讲。他写书译书:1903年出版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作为小学堂的教材,1913年又撰写了《字义类型》和编纂了《新华英文教科书》,留下不少诗词作品。这些职业身份当然是为政治活动服务的,这些靠知识谋生的活动是其公开的本职。
辛亥革命的失败致使陈独秀思想发生转变,出于对政局的极度失望,他产生了不谈政治的想法。1914年11月,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发表了著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声称已经对现实政治失去了热情,并指出问题在于民众的觉悟。文章将人心分为“情”和“智”,爱国心是“情之属”,自觉心是“智之属”,前者是立国之要素,后者则辨别“用适其度”。“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结论就是“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文章透露出了陈独秀的伤感,或可视为他疏离政治的告别书。但不能据此认为他已无心政治了,陈独秀所传达的既是悲叹更是不甘。他疏离国家和政府,却逐步酝酿出一条“不谈政治”的新路。据好友汪孟邹回忆,“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刊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这份杂志也随迁北大,由此聚集了一批致力文化革命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吴虞、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轰轰烈烈的新浪潮向全国铺开。
走向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政治抉择
在陈独秀看来,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后者“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在《新青年》上,他反对孔教,对于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高扬自由,称自由意味着“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职能”。他倡导科学和民主:“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创刊之日即号召:“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新文化运动被视为思想启蒙运动,一系列活动展示出陈独秀宣扬学术的一面,因为他不光远离政治活动,而且“不谈政治”。
要说“不谈政治”,陈独秀确实曾经下过决心,只是既谈不上严守,也没有持续多久。《青年杂志》创刊初期便定下基调:“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同人和读者也认同《新青年》不探讨时政。然而,这只是就总体而言,实际上他所主编的《新青年》前三卷,都设有评点政治事务的“国外大事记”和“国内大事记”,后来他也解释:“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不过,对“不谈政治”总体上的严守也没有持续多久。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宣称“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相比于《新青年》,它的出版周期短、板块划分灵活,正适合大谈政治,陈独秀每期都发表点评国内外政治的“随感录”若干条。《每周评论》还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带动了一批学生团体和学生刊物的创立,新文化运动的政治一面越来越明显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又迈出一步,不光大谈政治,而且重新开展政治活动。他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发表多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他在6月8日的《每周评论》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同时,又连载14则“随感录”,其中包括著名的《研究室与监狱》,鼓励人们“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监狱就入研究室”。他还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其后在北京街头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的陈独秀对政治更具热情,开始专心从事社会运动。1920年初南下后,陈独秀真正走进工人运动,在武汉、上海密集参与劳工集会,宣扬阶级斗争。比如,在上海演讲时,他号召工人有觉悟,当年底,他又强调工人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功夫”,而不可像过去的政客活动那样带了“政治的臭味”。
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参与社会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在1919年底的《新青年》宣言中,他明确表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头篇文章正是著名的《谈政治》,不失为他投身社会运动的宣言书。陈独秀开宗明义地指出:“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并明确表示要开展阶级斗争和“劳动阶级专政”,今后努力的方向就是“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当年11月,《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立。1921年1月,他在广州再次论证,唯有社会主义能“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应该采用俄国共产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半年后,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当选中央局书记,成为一名专心于社会运动的职业革命家。
政治的谈与不谈之间:作为社会运动的政治
回顾陈独秀这些活动轨迹,他在转型时代与政治的纠葛尤为引人注目:他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都是活跃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唯独在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到五四运动前竟声称“不谈政治”。列宁精辟地指出:“公开声明不再过问政治,这也就是政治。”或许应该这样理解,“不谈政治”确是对有关政府的政治活动既不参与也不公开谈论,但并非无心政治本身,可以说陈独秀没有改变对政治的关心,只是对政治的理解变了。既然陈独秀身上的政治线索并未因“不谈政治”而有所中断,那么他在五四运动后逐步走向职业革命家也不能以偶然事件来解释:当陈独秀在一战后选择了公开重谈政治,便很可能进一步重新投身政治活动;当他产生了无产阶级觉悟,从事工人运动也势所必然;而当他在五四运动后继续“消耗在政治生涯中”,是否离开北大已不影响他是否成为革命家了。时人郭湛波曾提到:“中国研究马克思学说最有心得,介绍最早的就算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尤以陈氏的影响为大。”那么当时陈独秀是怎么介绍的呢?他将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对他而言,“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对比陈独秀“不谈政治”前后,虽然都从事革命活动,其性质却大不相同。著名革命史学家斯考切波曾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改造的是政权结构而非社会结构,而且并不必然要经由社会冲突来实现”;社会革命则“社会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与之相伴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陈独秀在清末民初和五四运动后的不同表现则反映了这样的转换。比如,他早年多是参与暗杀团、会党活动,这些活动对象很有限,目标也很明确,革命领袖的视域很难超出国家层面。五四运动后的社会革命则不同,比如出现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大众政党,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旗帜,着眼广泛的社会动员以争得民众支持,目标直指社会的根本变革,手段多样且富有公开性。总之,两相对比,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于关注国家政权,而是更加下沉到广泛的社会运动中了。
“不谈政治”的背后正是对社会的大发现。清末民初陈独秀面对的是社会之上的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政治,革命活动多是会党结社和秘密行动之类,而他的社会职业是报人或教员,学术和政治之间虽有张力但毕竟仍是兼具的。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宣告放弃对国家政权的幻想,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是享誉全国的北大教授,他的确不再谈过去那种政治了,经由“发现社会”,政治早已拓展到社会中,可以说学术是明线、政治是一条暗线,一明一暗之间,政治和学术尚能兼容。五四运动后,政治既不是秘密行动,也不是隐性活动了,而是一项需要大众参与的关涉全社会的“直接行动”了,这时政治和学术便只能二择其一了。进一步而言,当政治须在社会运动中进行时,选择政治便成了一条通往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列宁曾谈道:“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共产党)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此外,学术也成了避免政治干涉的专业活动,徐复观注意到过去学术与政治现象的混杂,直言五四运动时期只是学术研究的“宣传时代”,到北伐后才成为“研究时代”,这时“‘打倒孔家店’这一派的人,已失掉了对学术界的影响力”。
结语
对于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和学术之间是存在张力的。传统读书人具有学术身份的同时又以政治为业,而现代社会则要求知识分子褪去政治的一面。以陈独秀为例,他在转型时代经历了从积极反清到“不谈政治”再到成为职业革命家的转变,展示的正是知识分子身上政治和学术的分离,政治本身影响了这个过程。当五四运动后,政治本身成了一项面向大众的社会运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张力也达到了顶点。这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之中有所体现。胡适奉劝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李大钊则强调根本解决之道,认为要提取共同的社会问题,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就论战的实质而言,其实并非要不要“学理”抑或“纸上的学说”,而是关于要不要继续做研究室里盯着具体问题的专家,抑或用某种一揽子方案来促成社会运动的职业革命家。
学术和政治既然成了二选一的抉择,知识分子本身也就完成了转型。要么以政治为业,比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大都受过良好的中西学教育,成为革命者之前很多人从事教员或编辑等职业。要么专注学术身份,成为报人、教授、科学家等各种凭借专业知识的谋生者。可以说,一条路通往的是居于舞台中央的职业革命家,视政治使命的实现为天职;另一条路则通往专注学术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的分流正是转型时代带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