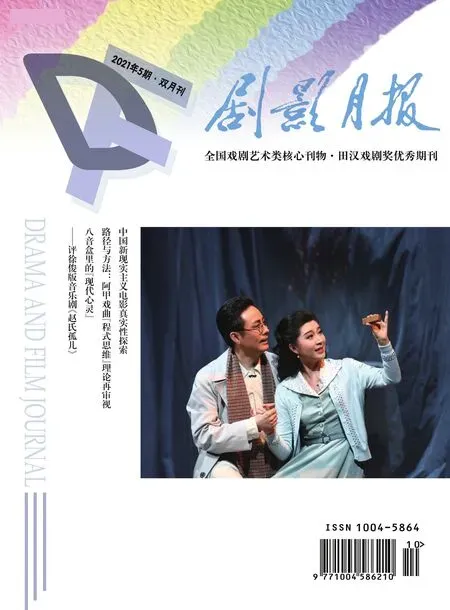跨文化翻拍片的中国化改编探究
——以电影《误杀》的改编为例
2021-11-14叶艳琳
■叶艳琳
近十年来,跨文化翻拍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制片方开发电影项目的重要模式之一,跨文化翻拍已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一种备受关注的电影创作路径。一方面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在全球化文化市场放开的大背景下,跨文化翻拍是中国电影人向国外优质影片的致敬和学习,“它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和改编国外优质电影资源,致力于实现国外经典电影的中国化,在促进文化交往、增添电影新鲜元素、激发电影创作的本土化创新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中国电影走国际化路线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它迅速地填补了庞大的中国电影市场在优质剧本上的缺口,并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力原片的故事创意和话题资源,既节省了宣传成本,又降低了投资风险。然而,能够经受住观众将其与原作的严苛对比,在口碑和票房上双丰收的影片可谓是凤毛麟角。
翻拍的原片都是制片方精挑细选的国外优秀甚至经典影片,但经过跨文化翻拍之后放映效果却有着天壤之别。决定跨文化翻拍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于是否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改编,周文萍指出:“中国电影人无论翻拍哪个国家的电影,要想将其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中国故事,必须解决外国电影的本土化改造问题。”翻拍失败的电影往往都只是停留在“翻译”的层面,对中国化改编的理解过于肤浅,仅仅对服装、道具等细节进行了简单的中国式改造。他们没有根据中国特定的文化氛围对人物和故事情节进行合理改编,最终导致情节的走向和人物情感不合理,同时也极少触及中国当下社会现实,最终导致无法与中国观众产生共鸣,比如《嫌疑人X 的献身》《深夜食堂》。与之相反,翻拍成功的电影大到故事框架、人物形象,小到服装、道具、语言风格都能够在原作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和当下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合理且具创造性的改编,将原作改造成为符合中国观众审美心理和情感诉求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比如《十二公民》《重返二十岁》。
电影《误杀》是继2018 年上映的《十二公民》之后跨文化翻拍片中的难得的一部佳作,2019 年12 月在中国大陆上映后获得票房、口碑的双丰收,2020年7月20日,新冠疫情低风险地区的影院复工后,《误杀》作为过去几年优秀影片的代表作品复映,并且连续三日蝉联票房冠军。此外,它还在2020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获得多项提名。张颐武称这部电影“无疑是华语电影的独特收获,也是华语类型电影现阶段快速走向成熟的标志。”本文通过对比《误杀》和原片《误杀瞒天记》,从人物塑造、美学风格和主题呈现三个主要方面探讨如何在跨文化翻拍实践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改编。
一、丰富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打造中国化的人物
人物是电影的核心,是“电影剧本的心脏、灵魂和神经系统”,是剧本创作的起点。合理、丰满的人物形象才能获得观众的心理认同,翻拍片也不例外。它将外国故事通过跨文化改编成中国故事,首先是要在保证人物形象合理、丰满的基础上,将人物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在外在需启用中国或者东方面孔的演员、穿中国服装、说中国话、保持中国人的仪态等等,更重要的是要赋予人物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征,设计由此驱动的行动,总之,要让人物散发出中国人特有的气质。《误杀》在人物设计上超越了原作,李维杰、拉韫、都彭等主要人物形象都较原片更加丰满、立体。同时,在丰富人物的过程中将当下中国社会里典型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注入不同的人物,其中改动最大的是两位父亲都彭和李维杰,分别代表着传统专制型父亲和理想型父亲。
1、传统专制型父亲
在原片《误杀瞒天记》中,受害男孩的父亲玛赫斯的形象极为单薄,他每次出场都只是母亲米拉身边的陪衬,对于儿子的失踪他自始至终都表现得过于平静和理性,不时地劝告米拉相信维杰全家和证人的供词以及提醒米拉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而在《误杀》中,父亲都彭的形象不仅饱满了很多,还充分显现出中国封建极端父权的典型特征。编导增设了一个父子冲突的情节,都彭得知儿子素察戳伤了别人的眼睛,不问缘由冲上前便狠狠地给了儿子一记耳光,儿子破门而出。因为这次激烈的冲突,再加上素察本就不学无术,都彭一直对他恨铁不成钢,所以当母亲联系不上素察时,起先都彭并不担心,并扬言封素察的信用卡逼他回家。由此可见,父亲都彭是他们这个小家庭的绝对权威,当儿子素察挑战父权时,他就要行使他的特权加以训诫和威胁。此外,他对权利的迷恋从他的小家庭延伸至整个族群,集中表现在他醉心于竞选市长,即便是儿子失踪之后,也一直忙于竞选,只是偶尔打电话询问妻子调查情况以及在案件调查出现重要转机时匆匆赶到现场。最后,李维杰也正是利用都彭的这一弱点成功扭转了局势。因此,都彭在享受权威的同时却未尽到一个父亲的义务,缺席了孩子的成长。有一处细节极为讽刺,透过母亲拉韫办公室的大窗户能清楚看到对面楼上挂着一幅大大的带有都彭头像的竞选海报,生动直观地刻画出都彭作为缺席式父亲的形象。尽管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父亲的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同时女性经济地位提升和独立意识觉醒,但时至今日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残留,母亲仍然是家庭中养育子女的直接承担者,像都彭这样的专制且缺席式父亲也依然是当下中国父亲的典型代表。
2、中国式理想型父亲
影片中的另一位父亲男主角李维杰,是翻拍过程中改造程度最大,且最复杂的一个角色。原作中的男主角维杰被塑造成了一个神化的英雄形象,他用勇敢和智慧对抗国家暴力机器,成功拯救了全家,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李维杰则被改造成一个平凡、真实的小人物,无论他的性格还是他在家庭中扮演的父亲角色都较维杰复杂、生动,并且兼具传统与现代中国父亲的特质。像都彭一样,他身上具备了中国式父亲的最大特点——他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家里的大事小情都需要他做决定。与此同时,他还有着中国传统型父亲的诸多特征:勤俭朴实、为家庭无私付出、深沉内敛。如果说都彭靠物质的满足和暴力来维护权威,那么李维杰靠尊重和爱来维护;都彭是典型的专制且缺席式父亲,而李维杰则愿意放下身段,幽默亲和,并亲自参与家庭中的日常琐事以及孩子的成长过程,并渴望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领路人,这一点正体现出现代理想型父亲的特点。这种理想型的父亲在中国社会中极为罕见,因此在中国影视作品中也鲜少出现,其中往往充当孩子领路人角色的往往是某个除父母以外的人,比如《小兵张嘎》的游击队排长、《长大成人》中的火车司机。除此以外,中国观众只能在西方电影中满足对理想型父亲的情感诉求。像李维杰这样的中国式理想型父亲既满足了中国观众对亲和的父亲形象以及平等的父子关系的强烈渴求,同时他身上具备的传统中国父亲的特质让观众倍感真实、亲切,欣然接受,他是中国影视剧中父亲形象的一次突破。
二、在改编中继承中国电影的抒情传统
周星曾说道:“中国电影的成功之中恰恰是以中国传统的继承发展为条件的”,跨文化翻拍电影的成功亦是如此。异域故事被移植到中国,要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必需入乡随俗,继承中国电影的美学传统,也就是说中国化的改编要赋予影片中国电影的美学气质。中国电影深受诗歌的影响,重抒情言志,因此抒情性是渗透在中国电影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基因,它“从内在和外在都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作为中国电影传统的一个重要内质”。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出了两条重要的脉络,一条是注重故事完整统一的叙事类电影,另一条则是注重抒情的诗意电影。两者并非二元对立,即便是叙事类电影,如若让观众产生深度的心理认同和移情,保持持久的生命力,抒情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电影史上也不乏此类经典作品,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甲午风云》。电影《误杀》对原片《误杀瞒天记》所做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在充满了惊险刺激的故事里注入了丰富细腻的情感元素,实现了叙事与抒情的完美融合。
正如前文所述,《误杀》中的人物尤其是两对父母较原片《误杀瞒天记》更加饱满,这就为细腻、深刻的情感表达打下了基础,反之,抒情又进一步丰富了人物形象。此外,导演在拍摄中充分调动了电影语言的视听表现力来营造气氛和抒发情感,虽然《误杀》较原片时长缩短了50 分钟,但在明快、精练的镜头中积蓄着一股强烈的情感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擅长使用细节去传达情感,在不动声色中直击观众的心灵,其中创作者不仅在剧作层面上设计了大量细节,还在拍摄层面上用特写镜头、高速摄影等手法去强化细节。首先,导演给演员的表演设计了很多外部动作上的细节,将角色抽象、细腻的心理活动外化成具象的外部动作的细节。当警察先后去平平的学校和家里调查之后,当天他们家的晚饭氛围显得格外紧张,阿玉和平平呆呆地坐着,安安一直用叉子划桌子,只有李维杰故作镇定地吃饭。当平平问李维杰警察是否会相信他们时,李维杰夹了一口菜稳稳地放在平平的碗里,朝平平微笑,然后继续大口吃饭。李维杰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平平的疑问,但这一口菜和一个微笑仿佛是爸爸给女儿下的一颗定心丸。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的沉默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个羞于表达情感的中国父亲暗下决心要拼尽全力去保护妻女的深沉的情感。其次,片中还设置了很多道具细节,作为细节的道具不仅具备了电影中普通道具的基本功能,而且还参与到叙事之中,成为了情感表达的点睛之笔。影片中戏剧张力和情感爆发力最强的“雨中认尸”这场戏中,大暴雨不仅渲染了紧张的气氛,还充分表现出围观村民的愤怒。最终当警察撬开棺材盖,只发现一具原本埋葬在这里的死者的尸体和羊的尸体之后,插入了一个由高速摄影机拍下的拉韫的大特写镜头。其中一个雨滴重重地落在拉韫的帽檐上,雨滴撞击帽檐的音响被放大,拉韫对于真相的最后一点期望就像那颗雨滴被重重击碎。倾盆暴雨中拉韫戴的墨镜显得格格不入,拉韫用墨镜和现实隔绝,平日里果敢强势的她此时已无力再去面对现实,也不愿意被人看见她的脆弱。雨滴和墨镜这两处细节,表现了拉韫在雨中认尸过程中的复杂细腻的心理过程,进而抒发了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和担忧。
中国电影的抒情传统最早起源于中国早期喜剧电影,它们非常注重抒情的段落,尤其是注重细节的表现来突出情感的表达,从而激发观众的移情。此后,中国电影一直把细节看做是创作中至关重要的元素。蔡楚生导演曾在他的文章《对分镜头剧本和文学剧本的一些看法》中用朴素、形象的语言强调了细节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一个作品是一棵树,那么,主题思想,故事情节应该是树的骨干和枝叶,而这些细节就应该是树上的花朵——它是艺术的花朵。人很喜欢树,但更喜欢有花的树,尤其是喜欢花又多又香的树。”他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里表现张母挑灯给儿子缝棉衣的细节精准地传达出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情感,素芬寄给张忠良的信被张撕碎之后其碎片在长江上随波飘荡的细节让人看了顿生寒意。影片《南海潮》中金喜给阿采掷鱼干的细节表现了这对年轻人之间的爱慕之情。如果删除了这些细节,影片主要情节线还是完整的,但其质感和情感分量就会单薄很多,正如潘桦所说:“细节可以看做是艺术作品的细胞,没有细胞就不会有艺术的整体,没有细胞的整体必将是僵硬的、概念化的。”
三、继承中国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捕捉当下社会现实
中国电影要想深入人心,与中国观众的心理产生连接与共鸣,需要在尊重并反映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及时触摸时代脉搏、真实再现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与心理状态。跨文化翻拍片作为中国电影的一部分,也必须要在影片中注入中国文化精神、反映当下社会现实,这也是翻拍片能够成功塑造中国化的人物、抒发中国式情感的大前提。
中国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家在儒家思想中是主导中国人行为的主要层面,是每个人的生存价值基础和情感核心,个人价值在家庭角色中得以确认,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家族情感高于其他一切情感。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必须从伦理本位的社会本质来认识。所谓伦理本位,是指由家庭生活所产生的人伦关系推及渗透于社会各层面而成其基本结构的社会与文化特征。”因此,家庭伦理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文化精神,是极易引发中国人情感共鸣的神话模式,对中国电影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电影诞生初期,电影人就努力挖掘家庭伦理题材,拍摄出《难夫难妻》《孤儿救助记》等一批符合国人心理和审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影片。此后,在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史中,家庭伦理片和武侠片是仅有的两个伴随中国电影发展整个过程的类型,在中国电影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同时家庭伦理片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发展最为成熟和类型特征最为明显的一种电影形式”。此外,家庭伦理不仅作为一种类型或者题材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发光,还被视作一种方法,作为“一种破解所有题材的‘万能钥匙’”被运用于家庭伦理片之外的各个电影类型。无论是家庭伦理片还是其他类型电影中的家庭伦理,通过对家庭中的人伦关系的展现,构建戏剧纠葛和矛盾冲突,往纵深处挖掘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从而折射出中国社会积淀数千年的恒久、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以及社会变革引发的心灵变迁。
《误杀》在翻拍过程中将家庭伦理作为一种方法运用到原片的犯罪片结构中。《误杀》精简了原片《误杀瞒天记》中案件侦查过程中警察与嫌疑犯之间斗智斗勇的情节,削减了由此产生的悬念感。原片的主角维杰最终战胜了强权,还成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翻拍跳脱出传统犯罪片中善恶的简单对立模式,在原片结局处加了一个大反转,李维杰后来出于良心、道义以及为女儿树立榜样的目的投案自首。于是,警察侦破案件、嫌疑犯洗刷罪名的故事被演绎成母亲寻找儿子、父亲保护女儿的故事。无论是拉韫和李维杰逾越了法律的不择手段,影片高潮处温柔怯弱的阿玉对拉韫的对抗和嘶吼,还是结局处李维杰投案自首,人物所有的行为动机都是出于他们对各自孩子的情感和家庭的责任,这与法律、道德的冲突构成了影片最大的戏剧张力。因此相较于原片,《误杀》对于复杂人性的呈现和迸发出的情感力量都被放大,也极易获得以家为本位的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正如张颐武所说“这个故事的力量在于,其完整的精彩故事里那种人的生命不能须臾离开感情和欲望的要素呈现”。
除此之外,《误杀》还在原片主要情节线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次要情节线,它们围绕拉韫和李维杰两个家庭内部的亲子矛盾展开,这是家庭伦理片中惯常构建的矛盾,也是备受中国观众关注的话题。原片中对男孩萨姆家庭关系仅做轻描淡写,只呈现出他是一个被父母极度宠溺的小孩,而《误杀》在增添了多个情节去表现素察在享受溺爱的背后承受着强大父权的控制、打压以及强烈的情感忽视。因此,素察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寻求补偿,他伤害平平的深层次的动机是对父权的挑战和报复。如此设计,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性格都更丰满,故事也更具合理性。此外,父亲都彭一方面对儿子严加管教,另一方面又在儿子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严重缺席,这种复杂矛盾的父子关系以及延伸出的“丧偶式婚姻”问题真实地反应了正处于传统与现代共存的中国社会里人们家庭生活的真实状态。除此之外,当下中国人对于家庭伦理的矛盾心态还体现在,一方面由于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对父权为代表的传统家庭伦理提出批判和挑战,另一方面又始终对温馨完整的家庭亲情保持超越理性的眷念。《误杀》中在案件发生前增加了李维杰和大女儿平平的冲突,这就给后面李维杰制造伪证这条行动线增加了他试图与平平和解这一动机。李维杰不仅凭借智慧使女儿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最后还替女儿顶罪,这些举动让一度轻视自己的女儿再次看到了父亲的伟大和力量,最终父女达成和解。翻拍中的这些调整正反映了当下中国人对传统家庭伦理既批判又渴望回归的复杂心态。
结语
事实证明,跨文化翻拍不是市场和口碑的绝对保证,它顶着原片的光环还将承受更严厉的评判。跨文化翻拍片如果想成功,需要在具备一部优质电影应具有的基本特质的基础上,继承原片的精髓,并进行中国化的改编和创造,用中国电影的美学语言去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从而赋予它中国电影的独特气质。因此,创作者不应把跨文化翻拍当作是通过成功的捷径,而是应该报着创作原创影片的态度在翻拍中把艺术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注释:
[1] 苏喜庆、杜平:《行为链视域下的电影跨文化翻拍》《电影评介》2017年第15期。
[2]周文萍:《外国电影的本土化改造研究》《当代电影》2016年第5期。
[3][12]张颐武:《误杀》的魅力[J].中关村,2020年第1期。
[4][美]悉德·菲尔德著,钟大丰、鲍玉珩译.:《电影剧本写作基础》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34页。
[5]周星:《对中国电影传统特征的世纪回顾》《戏剧艺术》1999年第3期。
[6] 周星:《中国电影学派建设视野中的改革开放40 年抒情传统嬗变》2019年第1期。
[7] 转引自周伟、文伦、舒晓鸣:《深切的怀念——学习蔡楚生电影创作札记》《电影艺术》1980年第1期。
[8] 潘桦、刘硕、徐智鹏:《影视导演艺术教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9]转引自陈雷程、宣霖:《中国家庭伦理片的类型意识探析》《电影文学》2014年第2期。
[10]宋家玲、周冬莹:《中国当代类型电影的建构与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
[11]万传法:《家庭伦理作为一种方法:历史、类型及其生产》《当代电影》2019年第12期。